伯林自由观批判邓晓芒详解.docx
《伯林自由观批判邓晓芒详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伯林自由观批判邓晓芒详解.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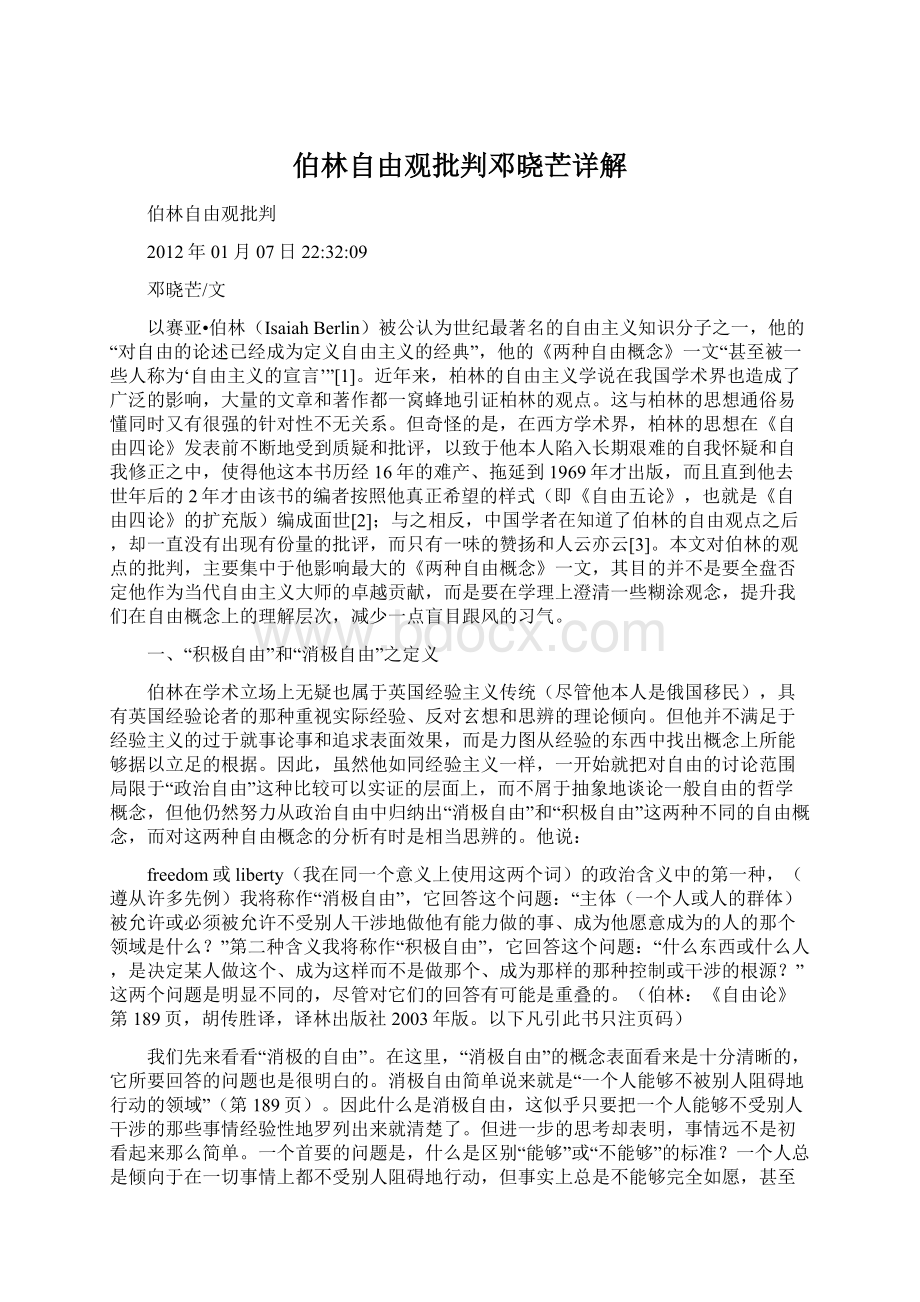
伯林自由观批判邓晓芒详解
伯林自由观批判
2012年01月07日22:
32:
09
邓晓芒/文
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被公认为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对自由的论述已经成为定义自由主义的经典”,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甚至被一些人称为‘自由主义的宣言’”[1]。
近年来,柏林的自由主义学说在我国学术界也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一窝蜂地引证柏林的观点。
这与柏林的思想通俗易懂同时又有很强的针对性不无关系。
但奇怪的是,在西方学术界,柏林的思想在《自由四论》发表前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批评,以致于他本人陷入长期艰难的自我怀疑和自我修正之中,使得他这本书历经16年的难产、拖延到1969年才出版,而且直到他去世年后的2年才由该书的编者按照他真正希望的样式(即《自由五论》,也就是《自由四论》的扩充版)编成面世[2];与之相反,中国学者在知道了伯林的自由观点之后,却一直没有出现有份量的批评,而只有一味的赞扬和人云亦云[3]。
本文对伯林的观点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他影响最大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其目的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他作为当代自由主义大师的卓越贡献,而是要在学理上澄清一些糊涂观念,提升我们在自由概念上的理解层次,减少一点盲目跟风的习气。
一、“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定义
伯林在学术立场上无疑也属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尽管他本人是俄国移民),具有英国经验论者的那种重视实际经验、反对玄想和思辨的理论倾向。
但他并不满足于经验主义的过于就事论事和追求表面效果,而是力图从经验的东西中找出概念上所能够据以立足的根据。
因此,虽然他如同经验主义一样,一开始就把对自由的讨论范围局限于“政治自由”这种比较可以实证的层面上,而不屑于抽象地谈论一般自由的哲学概念,但他仍然努力从政治自由中归纳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对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有时是相当思辨的。
他说:
freedom或liberty(我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遵从许多先例)我将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
“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
”第二种含义我将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这两个问题是明显不同的,尽管对它们的回答有可能是重叠的。
(伯林:
《自由论》第189页,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以下凡引此书只注页码)
我们先来看看“消极的自由”。
在这里,“消极自由”的概念表面看来是十分清晰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很明白的。
消极自由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第189页)。
因此什么是消极自由,这似乎只要把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干涉的那些事情经验性地罗列出来就清楚了。
但进一步的思考却表明,事情远不是初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区别“能够”或“不能够”的标准?
一个人总是倾向于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受别人阻碍地行动,但事实上总是不能够完全如愿,甚至在很长时期内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完全不能如愿,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来划定我们必须保有的“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的领域”(第194页)。
这个领域,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如贡斯当、柏克、穆勒等)所开列的“清单”有所不同,它取决于人们对于“人性的本质”的理解。
而由于这种理解“曾是且将是无尽的争论的话题”,伯林没有在这上面花费力气的兴趣,但他坚持说,无论如何,自由就是“免于……”的自由,“就是在虽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界内不受干涉”(第195页)。
自由就是不受干涉,这的确再简单不过了。
但在什么范围内不受干涉?
如果不深入到“人性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不探讨人类自由概念的变迁史及现实的人类历史,那么“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界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
我们可以设想,奴隶时代的奴隶所拥有的“自由”就是“免于被吃掉”的自由,但我们今天并不把奴隶称之为“自由人”,我们认为还应该有更多的内容才能称得上是真正“自由的”。
但问题在于,这些不断增加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标准和限度。
今天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内容如财产权、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等等,在若干年以后或许也会被认为需要进一步增加(如当今国际上“废除死刑”或“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趋势所表明的),有些则会逐渐消亡。
既然奴隶当年的“免于被吃掉的自由”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现代人对于吃人肉有种本能的拒斥),那么将来财产权和信仰自由也有可能失去意义。
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标准,那么消极自由的这一变动不居的疆界怎么可能“清晰可辨”?
再者,一种消极自由的增加难道最初不是被世世代代的人们作为“积极自由”、当作“理想”而努力去争取,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后来才得到普遍认可的吗?
如果没有人积极地去建立一个人人可“免于”某些强制性干预的法制社会,这种思想中或口头上的“免于……”的自由是不会生效的。
因此所谓“免于……”的自由同时就是能够通过某种手段(如法律)而在某种范围内有效制止其他人干预的自由。
换言之,消极的自由的另一面同时就是积极的自由。
这两种自由绝不只是“重叠的”,而就是同一种自由的两个方面、两种说法,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就不可能存在。
当然,伯林的“积极自由”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比起“消极自由”的概念来,它要晦涩和复杂得多。
一般来说,他承认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别在于“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第200页)。
但通常他不愿意以这种直接而明晰的表述来规定积极自由,因为这种表述太容易使人想到,在任何情况下要“免于”什么,就必须“去做”点什么,否则就不能“免于”什么。
他就是要把这两种自由完全割裂开来,即使事实上不能割裂,也要在观念上割裂开来。
所以他更愿意采用的表述方式是将这两种自由归于对两个不同的“问题”的回答。
比如积极自由所回答的问题,在上引那段话中被表述为:
“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这种表述够绕弯子的了。
较简洁的表述是:
“当我们试图回答‘谁统治我?
’或‘谁告诉我我是什么不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而不是回答‘我能够自由地做或成为什么?
’这个问题时,自由的积极含义就显露出来了。
”(第199页)但这种表述仍然晦涩不清。
这里至少有两种情况。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中,我当然可以援引某条法律的权威去做一件我愿意做的事,在这里,积极自由并不在于对法律权威的服从,而在于我认为这种法律权威是我和其他人为了保证我们去做某种事的自由而建立起来的,我们服从它就是服从自己,因为只有在它的“控制”下,我们的行动才能(或有最多的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对绝对权威的服从,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追溯到这个“根源”,而这个根源却不受我们的“控制”。
这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包括“积极自由”)了。
当然,现实中后一种情况经常被披上前一种情况的“自由”外衣,因而“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第200页);但正因为如此,哲学家的任务不就是要把这两种情况明确区分开来吗?
伯林把它们归结为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不正好混淆了积极自由和专制暴政的区别吗?
他无条件地赞同贡斯当的观点:
“为什么人对于他是被一个大众政府或君主碾碎,还是被一套压迫性的法律碾碎,要那么关心。
”“没有限制的权威不管掌握在谁的手中,或早或晚,注定会毁灭所有的人。
”“压迫的真实原因便是纯粹的权力积聚这个事实,而不管这种积聚发生在什么地方。
”(第236页)但难道民主政治的提出和建立!
"#不正是要限制政府权威的滥用、分散权力的积聚吗?
难道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这样做才有可能成功吗?
在正式阐明“积极自由的观念”的那一节,伯林写下了被称为“集中论述了伯林关于积极自由的观点”[4]的一段话:
“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
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
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
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
我希望是个人物,而不希望什么也不是;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而不是如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一个无力起到人的作用的奴隶那样只受外在自然或他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
当我说我是理性的,而且正是我的理性使我作为人类的一员与自然的其他部分相区别时,我所表达的至少部分就是上述意思。
(第200页)
显然,就连伯林自己也觉察到,这段话中对“积极自由”的阐述怎么看都像是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的阐述:
“我希望”就是想要“去做”什么,是积极自由;“而不是”则是“免于”什么,是消极自由;但“而不是”不过是对“我希望”的进一步说明而已。
所以他接下来说:
“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与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的自由,初看之下,似乎是两个在逻辑上相距并不太远的概念,只是同一个事物的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而已。
”(第200页)但他马上又否定了这种观点:
“不过,历史地看,‘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不总是按照逻辑上可以论证的步骤发展,而是朝不同的方向发展,直至最终造成相互间的直接冲突。
”(第200-201页)当然,他在这里诉诸的“历史”,只是“现实”或“经验”的代名词(因为他自己早已经把历史中的“决定论”或“发展规律”等等视为一种“催眠性的公式”了,见第185页)。
就是说,概念上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似乎是不可分割的,但现实中它们常常是完全对立的。
如何对立呢?
他举的例子是柏拉图和黑格尔所强调过的,当一个人自以为“我是我自己的主人”的时候,很可能他恰好是他自己的激情的奴隶。
于是一个想做真正的自由人的人就必须弄清楚他的“真实的自我”是什么,以便用这种“真我”来约束和强制自己,同时更用他人的“真我”去约束和强制他人。
而这实际上就以“自由”的名义导致了奴役。
因为我相信:
我对别人的强制是为了他们自己,是出于他们的而不是我的利益。
于是我就宣称我比他们自己更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
随之而来的是,如果他们是理性的并且像我一样明智地理解他们的利益,他们便不会反抗我?
?
因为在他们当中存在着一个隐秘的实体,即他们潜在的理性的意志,或他们的真实目的,而这种实体虽然被他们公开的感受、言行所掩盖,却是他们“真实的”自我,是处于时空中的可怜的经验自我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自我;我有可能声称这种内在的精神是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自我。
当我采取这种观点的时候,我就处在这样一种立场:
无视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愿望,以他们的“真实”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迫与拷打他们,并确信不管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幸福、履行义务、智慧、公正的社会、自我满足),它们都必须与他的自己——他的“真正的”、虽然常常是潜在的与未表达的自我的自由选择——相同一。
(第202页)
不过,伯林的这一番论证所阐明的,并不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冲突”,而是一般自由自己与自己的冲突。
正如伯林接下来自己所承认的:
“这种魔术般的变化或变戏法(就像詹姆斯恰如其分地嘲笑黑格尔派的那样),无疑可以轻易地施之于‘消极’自由的概念;在这里不受干涉的自我,不再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具有他的实际愿望与需要的个体,而是成了内在的‘真实’之人。
”(第203页)但伯林仍然试图强调在自由的这种自我分裂中,积极的自由更为恶劣,因为“就‘积极的’自由的自我而言,这种实体可能被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民族或者历史本身的长征,被视为比经验的自我更‘真实’的属性主体”“很容易把人格分裂为二”(第203页)。
然而,这种“实体”的膨胀、这种“分裂为二”,对于消极的自由难道不是同样容易的吗?
当孔子坚持自己的天道而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标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时[5],所依据的正是“超人的实体”。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是哪一种自由,是“免于……”的自由呢,还是“去做……”的自由,而在于如何把自由和不自由(哪怕它打着自由的名义)区别开来。
真自由既是积极的同时也是消极的,而不自由也既可以伪装成积极自由也可以伪装成消极自由,就是说,消极自由同样有可能把“真实的自我”膨胀为“超人的实体”而对人的“经验自我”施以强制。
其实,伯林自己在“退居内在城堡”一节中对极端消极自由的这种伪自由的特点做了很好的分析,如斯多葛派、基督教禁欲主义和康德的“自律”以及“东方圣者的寂静主义”,都是通过压抑和减损自己的感性需求来坚持自己不为外界所控制的“不动心”,他认为:
“这不折不扣是一种酸葡萄学说:
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就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由此所感到的抽象的自由“绝非政治自由,而是其反面”(第209、210页)。
由此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应当是:
把这种以“自由”面貌出现的不自由归咎于“积极自由”,而以为“消极自由”不在此列,这是站不住脚的。
伯林的区分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的实质。
那么,这种不自由为什么能够打着“自由”的旗号而能对人产生如此大的迷惑呢?
对此伯林做了自己的解释。
他承认:
“使这类语言显得貌似合理的,是这个事实:
我们认识到,以某种更高目标的名义对人施以强制,这样做是可能的,有时是有理由的;关于这种目标(譬如说,公正或者公共卫生),如果受强制者更开化一些,他们自己就会主动追求,而他们没有追求,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或腐败。
”(第201-202页)显然,伯林并没有说“这个事实”本身是对自由的剥夺,相反,在他看来,公正、法律、秩序和公共卫生一类的社会行为规范至少“有时是有理由的”,没有这种强制,一切积极的或消极的自由都不可能。
所以每个想要自由的明白人都会去“主动追求”建立一种秩序规范,并将其视为自己自由的保障。
但伯林认为,正是这种本来是有其合理性的追求,使得某些人以自由的名义行专制之实显得“貌似合理”,成为了剥夺个人的自由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很明显,伯林在这里实际上承认了,关键问题并不是要不要强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强制的问题。
以为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强制,这只是小孩子的想法,任何自由要能够现实地实现出来,都有赖于某种强制(包括自己对自己的强制)。
不能因为不自由也以“保障自由”的名义施加强制,就否认真正自由的保障也需要合理的强制。
我要使自己的财产免于被剥夺,我就要克制自己贪图他人财产的欲望;我要保有言论自由,我就得小心不要辱骂和诽谤别人;我要有人身自由,就不得伤害或拘禁他人,甚至我要呼吸新鲜空气,首先自己就不要随地大小便;否则法律和有关部门就会来找我的麻烦。
伯林既然把自由放在政治自由的层面上来考量,就应该想到它本质上是一个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也就是怎样一种互相强制能够为人的(互相不强制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留下最大余地的问题,而不只是单个人主观的“我希望……而不是……”的问题。
所以,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于没有任何强制,而在于这种强制是大家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不受强制而自愿接受的。
而这个“最大限度”就在于自己的自由以不要损害他人的自由为限,这就是穆勒早就揭示出来的“群己权界”。
孟德斯鸠说得更明确:
“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6]
当然,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却是伯林所不乐见的,他宁可赞成边沁的观点:
“法律所从事的不是解放而是限制:
所有法律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即使这种侵犯导致自由的整体增加。
”(第220页)其实伯林更想说的是,积极自由是对真正的自由即消极自由的侵犯,这种侵犯往往会导致自由的整体的减少。
例如他说:
“为了防止太明显的不平等或到处扩展的不幸,我准备牺牲我的一些甚至全部自由:
我有可能非常情愿地、自由地这样做;但是我失去的毕竟是自由。
”(第193页)在他看来,即使人们自由地选择了一条制止种族压迫的法律,这也不是自由的胜利,而是自由的损失,因为他赞同边沁的“做坏事的自由也是自由”的说法(第219页注35),却不承认“制止做坏事也是自由”。
他认为,不存在什么自由的法律,任何民主的法律跟专制统治下的恶法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民主可能会解除一个既定的寡头、一个既定特权个人或若干个人的武装,但是它会像任何一个先前的统治者一样残忍地压制个人”(第236页)。
所以伯林的自由是不受任何法律所限制的,他说:
“我必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其中必须存在着自由的某些疆界,这些疆界是任何人不得跨越的”(第237页),不论是以法律的名义还是人民的名义。
但是,人们自然要问,为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这些“不得跨越的疆界”本身是不是要由法律规定下来呢?
伯林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他只是说:
“这些疆界之划定,依据的是这样一些规则:
它们被如此长久与广泛地接受,以致对它们的遵守,已经进入所谓正常人的概念之中,因此也进入什么样的行动是非人性与不健全的概念之中。
”(第238页)他举例说,一个人未经审判就被宣布有罪、孩子被命令去诋毁父母、少数派因激怒多数派或暴君而被屠杀等等,这就违背了一个“正常人的概念”及其所认可的“规则”。
然而,这些“规则”有没有强制性?
如果有,那它们就相当于法律的权力,伯林就只是换了一个字眼而已;如果没有,那它就只是“正常人”脑子里的一些主观想法,顶多是一种舆论压力,它们对于“建立这样一个社会”是远远不够的,而只能更加突显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必要性[7]。
更何况,“正常人”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是他所说的“长久与广泛地接受”某种规则,那不正好就是他一贯反对的“多数人”的规则吗?
那么,“不正常”或“不健全”的少数人是否也应该得到尊重呢?
伯林对他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显然并没有想清楚。
二、自由如何成了不自由
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其实伯林一开始就把问题提错了。
应当追问的并不是:
不自由为何能够打着自由的旗号来迷惑人?
而是:
自由为何成为了不自由?
后一种提法更带本质性,因为不自由在个别情况下虽然有可能是欺骗的产物,但欺骗不可能成为常例。
尤其在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大部分的不自由最初都是人们自由地选择的。
你可以说这种自由选择是形式上的,但你不可能抛开这种形式而获得任何自由。
伯林由于不能解释这种形式的自由为何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实质上的不自由,于是就对一切形式的自由绝望,而执著于“最低限度的”实质上的自由。
这就是他提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区别的初衷。
但由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或者说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本身所具有的不可分割性,伯林的解释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相矛盾。
其实,走出这一陷阱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伯林当作主要论敌而大力批驳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自由观。
伯林的这些随处可见的批驳其实绝大部分是一种误解甚至歪曲。
例如前面所引伯林批评柏拉图和黑格尔的那段话中,他所引述黑格尔的那些观点,并未引证黑格尔的任何原话,可以说是强加于黑格尔的。
其实,对黑格尔哲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黑格尔对于人的“真实的自我”抱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发展观。
人们最初的确只知道“处于时空中的可怜的经验自我”,但绝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等待他们的自由意识在历史中自行发展。
所以黑格尔认为:
“真理具有在时间到来或成熟以后自己涌现出来的本性,而且它只在时间到来之后才会出现,所以它的出现绝不会为时过早,也绝不会遇到尚未成熟的读者;同时我们还必须相信,作者个人是需要见到这种情况的,为的是他能够通过读者来考验他的原属他独自一人的东西,并且能够体会到当初只属于特殊性的东西终于成了普遍的东西。
”[8]作者自己的真实自我都必须在他人或读者身上得到验证,其普遍性还需要由他人得到批准,他又如何能够代表他们的自我来“威逼、压迫与拷打他们”呢?
更何况,即使一个人坚信自己看到了他人的真正自由之所在,并把这一点告诉他人,这与“强迫他人自由”还根本是两码事[9]。
黑格尔的确说过:
“加于犯人的侵害不但是自在地正义的,因为这种侵害同时是他自在地存在的意志而且它是在犯人自身中立定的权利。
”“认为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权利,所以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
”[10]但这并不是“迫使他人自由”,恰好相反,是指应尊重犯人自己所立的法,让他自由地惩罚自己,而排除任何“威逼、压迫与拷打”。
又如对马克思的误解:
“对马克思来说,理解就是适当的行动。
并且仅当我的生活计划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安排的,我才是自由的;计划包含着规则,而一种规则当我有意识地强加给自己或者因为理解而自愿地接受它的时候,它就不会压迫或奴役我,而不管它出自我自己还是别人之手,只要它是理性的,也就是说,只要它遵循事物的必然性。
理解事物何以如此也就愿意它们果然如此。
”(第214页)[11]因此,在伯林眼中,马克思就应该会去劝说工人服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因为这是合乎理性、合乎规律的,而且劳动合同是工人自愿签订的,所以不存在“奴役或压迫”[12]。
但马克思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做了激烈的批判,并致力于推动对未来更高自由生活的追求,这对于伯林这样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
非历史主义的自由观一般说来就是如此看问题的,所谓“任何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自由就是自由”(第193页)。
至于自由是如何变成了不自由的,对此伯林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唯一知道的自由就是一种平面化的、直观经验的自由感受,即“为所欲为”“任意”和不受强制。
但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
自由变成了不自由,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核心,它表达了一般自由自身的自相矛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超越的历史性。
在这种理论中,伯林所理解的那种自由并没有被否定,但只是处于最基本的层次中,它有待于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解。
所以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看作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即从(东方)“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进到(古希腊罗马的)“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再上升到(日耳曼世界的)“一切人是绝对自由的”[13]。
伯林所理解的自由应该说还停留在“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即每个人只知道自己一个人是自由的这种幼稚的感性冲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都处于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或者黑格尔所说的“生死斗争”及其所导致的“主奴关系”中[14]。
所以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自由的倾向必然会要求建立某种社会秩序,以期他人在某种范围内对自己的自由加以“承认”乃至于互相承认。
人对自由的追求哪怕只要稍微超出“一个人是自由的”这种层次,就需要对他人自由权利的一种建立在普遍理性之上的估计,并使之固定为一种法权原则乃至于制度,而不能单凭自己个人的感觉和亲身经验了。
但伯林并不把最初那种追求个人感性自由而不得的状态看作人类自由意识不成熟的必然结果,反而仅仅立足于这种幼稚的自由观,而期望借助于大多数“正常人的概念”来维持“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
这种一厢情愿的劝导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说这种劝导在当今西方社会居然也能够发生一定的效果的话,那也决不是像伯林所设想的那样单凭“正常人的概念”做到的,而是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做到的。
只有一种完备的立法才有可能把正常人的合理的道德诉求反映出来并有效地实现出来。
当然,在黑格尔那里,即使人们意识到了“一切人都是自由的”,这种普遍自由要实现出来仍然会导致异化。
例如法国革命就是这样,它本来是要把人们所意识到的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在现实中实现出来,但“它根本不知道,意识的个别性本来为了能够作为这一特定的直接的个别性而存在,将自己委托给现实,竟反而在这个自身普遍的东西里把自己毁灭掉了;它因而并未达到它的这种存在,而毋宁是在存在里完成了它自身的异化”[15]。
黑格尔把这种状况称作“心的规律和自大狂”,普遍自由的心的规律只有扬弃它的自大狂而进入到现实的“世界进程”,才能学会如何实现这种自由。
对法国革命的这种批判,比起伯林以及他所援引的贡斯当等人的一味的道德谴责和小家子气的退守“直接的个别性”来,要深刻得多。
伯林只是把法国革命归之于“‘积极自由’要求的大爆发”(第235页)而了事。
在他看来,法国革命的教训就在于,我不要再去管“谁来统治我”,只要他能给我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就行。
但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