吻别.docx
《吻别.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吻别.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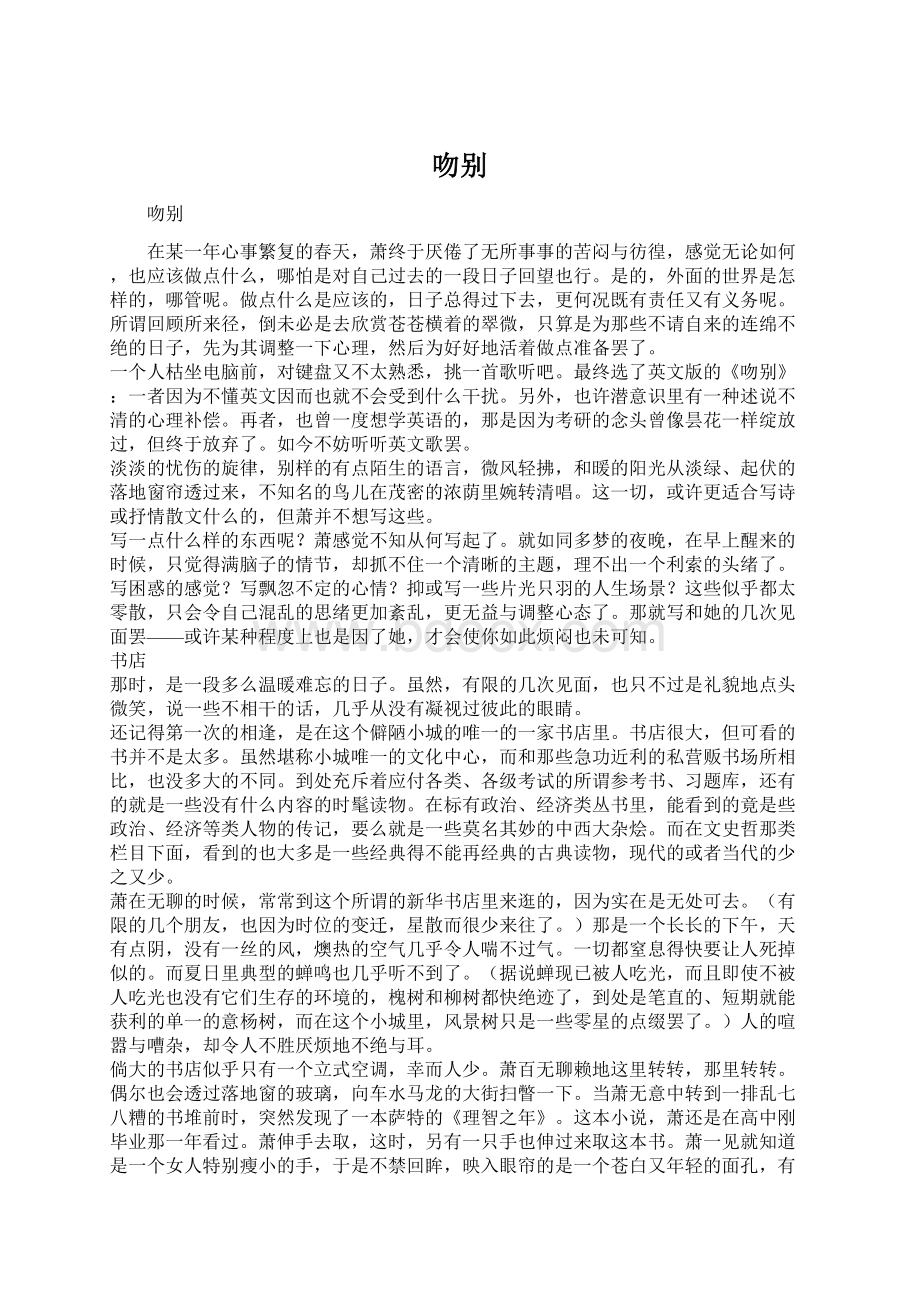
吻别
吻别
在某一年心事繁复的春天,萧终于厌倦了无所事事的苦闷与彷徨,感觉无论如何,也应该做点什么,哪怕是对自己过去的一段日子回望也行。
是的,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哪管呢。
做点什么是应该的,日子总得过下去,更何况既有责任又有义务呢。
所谓回顾所来径,倒未必是去欣赏苍苍横着的翠微,只算是为那些不请自来的连绵不绝的日子,先为其调整一下心理,然后为好好地活着做点准备罢了。
一个人枯坐电脑前,对键盘又不太熟悉,挑一首歌听吧。
最终选了英文版的《吻别》:
一者因为不懂英文因而也就不会受到什么干扰。
另外,也许潜意识里有一种述说不清的心理补偿。
再者,也曾一度想学英语的,那是因为考研的念头曾像昙花一样绽放过,但终于放弃了。
如今不妨听听英文歌罢。
淡淡的忧伤的旋律,别样的有点陌生的语言,微风轻拂,和暖的阳光从淡绿、起伏的落地窗帘透过来,不知名的鸟儿在茂密的浓荫里婉转清唱。
这一切,或许更适合写诗或抒情散文什么的,但萧并不想写这些。
写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呢?
萧感觉不知从何写起了。
就如同多梦的夜晚,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只觉得满脑子的情节,却抓不住一个清晰的主题,理不出一个利索的头绪了。
写困惑的感觉?
写飘忽不定的心情?
抑或写一些片光只羽的人生场景?
这些似乎都太零散,只会令自己混乱的思绪更加紊乱,更无益与调整心态了。
那就写和她的几次见面罢——或许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了她,才会使你如此烦闷也未可知。
书店
那时,是一段多么温暖难忘的日子。
虽然,有限的几次见面,也只不过是礼貌地点头微笑,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几乎从没有凝视过彼此的眼睛。
还记得第一次的相逢,是在这个僻陋小城的唯一的一家书店里。
书店很大,但可看的书并不是太多。
虽然堪称小城唯一的文化中心,而和那些急功近利的私营贩书场所相比,也没多大的不同。
到处充斥着应付各类、各级考试的所谓参考书、习题库,还有的就是一些没有什么内容的时髦读物。
在标有政治、经济类丛书里,能看到的竟是些政治、经济等类人物的传记,要么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中西大杂烩。
而在文史哲那类栏目下面,看到的也大多是一些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古典读物,现代的或者当代的少之又少。
萧在无聊的时候,常常到这个所谓的新华书店里来逛的,因为实在是无处可去。
(有限的几个朋友,也因为时位的变迁,星散而很少来往了。
)那是一个长长的下午,天有点阴,没有一丝的风,燠热的空气几乎令人喘不过气。
一切都窒息得快要让人死掉似的。
而夏日里典型的蝉鸣也几乎听不到了。
(据说蝉现已被人吃光,而且即使不被人吃光也没有它们生存的环境的,槐树和柳树都快绝迹了,到处是笔直的、短期就能获利的单一的意杨树,而在这个小城里,风景树只是一些零星的点缀罢了。
)人的喧嚣与嘈杂,却令人不胜厌烦地不绝与耳。
倘大的书店似乎只有一个立式空调,幸而人少。
萧百无聊赖地这里转转,那里转转。
偶尔也会透过落地窗的玻璃,向车水马龙的大街扫瞥一下。
当萧无意中转到一排乱七八糟的书堆前时,突然发现了一本萨特的《理智之年》。
这本小说,萧还是在高中刚毕业那一年看过。
萧伸手去取,这时,另有一只手也伸过来取这本书。
萧一见就知道是一个女人特别瘦小的手,于是不禁回眸,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苍白又年轻的面孔,有点羞涩的笑意淡淡地挂在嘴角,眼睛大而略显忧郁,见有陌生的目光向它射来,迅疾地垂下长睫毛避开了。
萧感到自己似乎不太礼貌,于是歉意地对着这个女人点了点头,走开了。
萧又在空荡荡的书店里转悠了一圈,有一搭没一搭,随便地翻了几本书,心不在焉地转到一处,竟又意外地看到了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也是一本中学时读过的书。
在那非常年轻的日子,也只不过是稀里糊涂、囫囵吞枣地匆匆浏览过,并不十分理解其中的意思。
在那之后,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常会看到有人不断提起这本书。
一直想重读的,但一直没有机会。
今天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了。
萧伸手去取,又是一只女人的手,而且仍然是那只手:
又瘦又小。
萧不禁问:
“你买吗?
”那个年轻的女人显然有点局促,轻说一句:
“你买吧。
”然后似乎也歉意地点点头,走了。
萧看着那位个子不太高的女人姗姗离去,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差点说:
你买吧,我可以借你的看。
萧下意识地摇了摇头,感觉自己冒出这个念头真是荒谬!
彼此不仅素不相识,而且还可能离得十万八千里呢,怎么可能相互借书看呢。
萧不由得想起一部根据同名漫画改编《向左走,向右走》的电视剧,还记起了曾读过的一部外国现代小说:
说的是两个陌生人偶然在一块聊天,聊着聊着,知道两人住在同一条街区,再聊发现还住同一栋楼,最后才明白两个陌生人原来不仅住同一间屋,而且还睡同一张床,是一对已经在一块生活好多年的夫妻了。
萧想到这,不禁模糊地记起自己似乎确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
直到现在,萧几乎仍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确实曾结过婚又迅疾地加入离婚大军了。
而如今他是什么呢?
是个所谓的单身贵族?
贵族?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是什么样的?
现在的白领?
啊不,有钱有闲,还要有特权的——《红楼梦》里那一群痴男怨女应该算是了:
有闲情逸致,又锦衣玉食、养尊处优。
还有魏晋时的那些士大夫们?
……
又不着边际的想这些干什么呢,毫无一点用处。
这时,萧看见那个瘦小的女人径直向他走来,并且微微一笑:
师院那条路刚开了家“三联书店”,里面有些书还不错。
萧客气地点点头:
谢谢。
有空去看看。
“有空”两个字刚在空气中回响,萧不由得自嘈地笑了笑:
除了时间,我还有什么?
就和那歌唱得一模一样:
一无所有!
如今不是一直“赋闲”在家么。
幸而有两块菜地被所谓的开发区开发成了两套房子,出租了尚有点微薄的收入,否则,怕几乎连最起码的生存的支点都没有了。
(当然,那也是姊妹们都有份的,暂且她们没计较,也是权宜之际罢。
)除了老大不小的岁数,他有什么呢?
无背景,无硬的学历——既不是科班出生,更没有所谓名牌学校的毕业文凭(起初是稀里糊涂花钱上了几年学,稀里糊涂地拿了个假文凭,到处碰壁后,一生气参加自考才混了一张真的)。
原以为有了张真文凭,就可以参加各级各类考试,就可以谋一份所谓既有保障又相对稳定的职业了。
可是,老大不小的年龄却硬是成了铁门槛:
招工,招聘,企业,事业,什么公务员,几道年龄关卡着你:
28,30,35,40(范进是什么年代?
老头了尚可以中举呢。
)孔老夫子还说三十而立呢,而30岁至45岁,应该是一个人智力成熟、精力还充沛的黄金年龄段啦,怎么却偏偏成了被隔离于所谓主流社会的“另类老人”了?
!
另有各种五花八门、或明或暗的就业歧视、就业潜规则,对既是草根族又没什么特长的人而言,想谋一个所谓体面的职业,通过所谓的招考,即使不是难于上青天,也差不了多少。
自主创业?
那似乎既要天分,又要有所谓创业的财力的。
这对极其平庸的小人物而言,难度也蛮大,似乎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萧还记得自己曾经做蓝领的那几年的日子,那真正是一个流浪汉的生活:
行走在一个个既繁华喧嚣又陌生冷漠的都市里,像会说话的动物似的被呼来喝去,像无根的飘篷似的不断迁徙搬移。
力出了,汗流了,却未必及时、如数得到所谓应得的报酬。
什么保障也没有,更枉论人的尊严与人格了。
萧在外流浪的那几年的感觉,套用一句现成的话说:
如此惨淡的生活,比睡在坟墓里也差不了多少。
虽然,也曾拿出一部部先哲和智者的书,希望把心放到一个所谓塌实、稳当的地方,可是,心果真是有来路无回路的!
压抑、苦闷、彷徨、迷惘等诸如此类灰色的情绪,仍然像害怕孤独似的如影随形。
萧再次耸耸肩:
又想这些无聊的东西!
世上本无事,确实是庸人自扰之。
那个给他提供书讯的女人呢?
已经不知什么时候早走了。
后来,萧确实去了三联书店。
在那里,他们彼此不期然地又邂逅了几次,也只不过是礼貌地点头微笑,偶尔说一些不相干的话。
像熟人似的道别,像陌生人似的默然地擦肩而过,既不过问对方的生活情状,甚至连对方的姓氏称谓也从没有相互提及过。
见了面,就如同老朋友似的,默契地点头微笑,但几乎从没有凝视过彼此的眼睛。
那一段日子,萧已记不清那是一个怎样的季节了,只是感觉天气格外地宜人:
和煦的风,很惬意地又轻飘飘地吹在身上;透明的阳光,很温和地又懒洋洋地四处洒着。
一切变得近乎美好了,心情也格外地与往日不同:
心里面似乎模糊地涌动着既微茫又十分切近的希望,虽然,也许未必会有什么光明的前景,在不远的未来的某个地方,亲切又和蔼地注视着,耐心地等着自己。
但那种好象是来自于内心的某个温柔又静悄悄的角落,情不自禁地流泻出的、不绝如缕的喜悦,仍然似乎是不动声色地泄露出了一种淡淡的幸福的味道……那些蜿蜒起伏、千转百回的心情,以及那些意象纷繁又飘拂不定的思绪,令萧不禁犹如身处寒凉灰冷的冬季,却忽然从遥远的天幕凭空射来一缕橘黄色的暖阳,有一种诗意融融、如沐春风的感觉了。
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日子:
似乎只要门一开,那些伸手可及的美好的未来,一下子就会不由分说地涌进来……
医院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提着粗糙的篮子回家在什么样的石头路上踽踽独行而且那家已无法说明是我的
再次见到她时,已是飒飒西风满园起的寒凉的晚秋时节。
虽然,那一年秋天,相当地暖和,简直可以说是有一点炎热了。
在立秋后好长一段时间,天气仍然像夏天似的闷热,又一直无雨。
(仿佛有好多年都是这样的了。
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唔,还有春天,都太短暂。
而炎热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却相当地漫长。
)天高气爽、风轻云淡的秋天,似乎成了久远的记忆中的季节了。
如今的秋天,几乎都是蓦然地从闷热的夏季,一下子就踱到了一个万木凋零、萧索冷落的深秋时节。
那天,萧忽然接到所谓前妻打来的电话。
她说,孩子住院了,请他到医院看看孩子,他当然可以拒绝,只是,她说,她非常希望他能来。
萧刚接到电话,有一阵头脑一片空白,他像一只受伤的困兽,在自己略现狭窄的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一年来,他几乎都在尽力忘却那段婚姻,关于她一切的一切。
如果可能,他都想为此洗一次脑。
他以为再也不会和这个女人发生任何联系了,她已经从他的生活中永远消逝了。
可是,他又和她有联系了——以后一定也不会彻底了断的。
对,就是那个孩子,他虽然和她毫无一点关系,但别人都知道他是她的父亲。
事实上,他不是!
而那个漂亮的女人也不知道谁是那个可怜的孩子的父亲!
萧极其厌恶地记起他荒谬婚姻的开始:
那时候他正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间流浪,确切地说,应该是在打工吧。
那种居无定所、漂泊无依又孤寂无望的日子,正使他倍感身心疲倦,所谓正是灵魂孤单久了,忽然非常希望用世俗的感受来填补虚空的人生的时候。
家里人催他回来相亲,他也就回来了。
相亲的对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于是,所谓谈了三个月结了婚,三、四个月后,早产下一个女儿,不到半年便发现漂亮的女人是极不安分的——哪怕是包法利夫人,都还有点可爱;就算是卡门罢,也还能接受。
可她只是一个将骚首弄姿当风情万种、将虚荣自私当天真可爱,既无灵魂而又靠本能生活的雌性动物罢了!
那次,也是孩子生病,需要输血,结果发现这个体弱多病的女儿竟不是自己的!
于是迅即地办了离婚手续。
前后一年多的婚姻生活,仿佛是做了一个既逼真又荒诞的梦:
与一个很陌生的女人闪电般地结婚,在很短的时间,稀里糊涂地生了个女儿。
然后,又在周围人闲言碎语中,很快地离了婚。
整个过程虽很简单,也很复杂,也可谓影响深远:
那种令自己极其厌恶又极其可笑的感觉,就像讨厌的污迹似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在记忆的屏幕上,似乎再也涂抹不去了。
现在,她要他去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了。
萧原以为一次性付了生活费,就会和过去的那段日子彻底了结、彻底告别了呢。
她当初不是答应再不来找他么。
但这种很会算计又好逸恶劳的自私的女人的话怎么能信?
而且,周围的人谁不知道他是孩子的父亲?
虽然,当那个无辜的女孩刚被抛到这个看似精彩其实很无奈的人世的时候,引来了不少地非议——即使早产,似乎也不大合乎常理,更何况那个孩子无论是肤色、还是形貌,与他这个父亲都毫无一点相似之处呢。
如果长得像她漂亮的母亲,也还说的过去,可这个孩子谁也不象。
邻居们的微词,萧起初很不以为然,但后来的事实却可耻地证实了那些好事者的猜忌。
虽然不事张扬地迅速地离了婚,但周围人的眼神里仍然明显地含有一种意味深长。
而一切过去了也就过去罢。
是的,原以为一切都彻底了结了呢,但是却没有。
萧孤零零地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他看到一张张痛苦、焦急、麻木、平淡的面孔,在眼前飘忽地流过去。
萧依稀记起一句诗: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写的似乎是地铁里转瞬即逝的面孔。
萧不禁冷笑:
在这人流中,自己不知是一副什么样表情的花瓣?
萧正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辆急救车怪叫着驶过来,也不知道又是一个怎样的重症病人?
萧不由得多看了一眼。
怎么?
救护车上抬下的女人有点眼熟?
虽然离得略远了些,但萧仍然觉得似乎认识那个苍白的女人,或者还很熟罢。
萧走了过去,问陪护的两个女人:
她怎么啦?
其中一个快嘴的女人脱口说:
还不是又被她那个畜生丈夫打的!
另一个女人却抬眼问萧:
你是——。
萧赶紧说:
我们认识。
——是同学。
那个躺在担架的女人无力地张开了眼,向萧望了一下——原来确实是书店里的那个女人!
又是有点羞涩的笑意,更加苍白的她似乎想点头但不能够。
萧示意她不要乱动,跟着她一起走进医院的门诊大楼。
一路上,那个快嘴的女人一直絮絮地抱怨着、责备着。
萧从这些不连贯、零乱的絮叨中知道了原委:
这两个陪护的女人原来是热心的邻居,肇事丈夫到银行提钱还没赶到这。
丈夫是个成功人士,有权有钱,外面免不了有女人,婚姻自然不大和谐,吵架打架再所难免。
当然,妻子精神和肉体遭殃也就很正常。
这次,这位妻子被医生初步诊断可能是脾破裂,很可能要手术。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萧打断那个正在喋喋不休的女人:
她孩子多大?
才两三岁。
他们还是自谈的呢,才发达几天呀,就这样?
!
躺着的妻子轻咳了一下,萧知道她可能有点难为情。
他安慰她道:
现在这种事习以为常的。
这时,一个衣冠楚楚的高大的男人走过来。
萧知趣地走开了。
他得看自己生病的孩子去了。
萧在光线暗淡的通往病房的甬道上,默默地走着。
狭窄的过道上,出来进去的人很多,显得既拥挤又嘈杂。
现在的病人不知怎么这么多!
心理的、肉体的病人似乎都太多了。
也许是人们在拥挤吵闹、阴暗浑浊的欲望的甬道上,既相互需求又相互妨害牵制,精神紧张又压抑的缘故?
再加上吃穿住行,又都是防不胜防的假冒伪劣产品,想不生病还真难!
而所谓供无常又多灾多难的人生停靠的港湾——家,在这惟利是图、物质至上、一切以自私自利为准则、变幻莫测又极其现实的汪洋上,却已像千疮百孔的一叶破船,风雨飘摇,不堪外力的一点打击了。
什么道德,什么良智,在这个蒸蒸日上、一派繁荣的社会,早成了太落伍的笑柄了——它们管吃吗?
管喝吗?
管玩吗?
管乐吗?
现在哪里是疲惫的人生歇脚的地方呢?
家,原本应该是这样一个温暖、可避风雨的所在的,可如今呢。
萧不由得记起一首最近刚读过的诗: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提着粗糙的篮子回家在什么样的石头路上踽踽独行而且那家已无法说明是我的喏,这几乎就是现状的精彩诠释了。
墓园
时间不舍昼夜地奔流,在某一个地方,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平静,既模糊又分明的轮廓成为定格,而她的目光却向着远方。
萧带着孩子在冬日有点凄凉的墓园里,有点茫然地走着。
这是这个小城简陋的墓园,简单的园门,连围墙都没有。
大大小小的坟茔和高高低低的墓碑,使墓园显得既狭小又拥挤。
在这寂寥冷落的冬日的墓园里,有的是一些泛白的衰草,风中摇曳的枯藤——倒没见着寒鸦,还有的就是一些随寒风偶尔旋起又四散飘落的纸灰,风雨还没来得及毁损、醒目的鲜艳的花圈,逝去的人用过的又被丢弃的东西。
这是一个荒凉又寂静的地方,虽然不远处人世间的热闹依稀可闻,但在这里,确实真正远离了滚滚红尘的喧嚣与浮华。
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一切都安分、沉寂了:
无论是思想混乱、琐碎、平庸,还是见解独到、系统、明晰,也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布衣贱民,都平等地、安静地躺在了这里。
什么信仰、自由、精神、物质,在这里,一切都化作了虚空。
人是否真的有灵魂呢?
现世的一切能否带到另一个世界呢?
在另一个未知的世界,一切也和这一样还是迥然不同?
萧不禁自嘲地耸耸肩:
祥林嫂式的追问。
很愚蠢啦。
爸爸,我要回家。
突然,一个女孩稚嫩的声音吓了萧一跳。
唔,我从现在开始,有了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儿了,完完全全。
她死了:
车祸——兜风——坐在副驾座,撞在桥栏杆上。
(那么巧,车里其他人都好好的,她死了。
)这个孩子理所当然得跟她这个父亲。
她的母系亲属没人想要这个包袱,要是男孩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只是一个女孩罢了。
那只小手拉了拉父亲的大手,小手冰凉。
萧低下头:
你冷吧。
那张可怜兮兮的小脸正眼巴巴地望着他:
爸爸,我要回家。
好,我们回去。
萧看着这个女儿想:
回家?
你真正的家在哪儿呢?
但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你也一样呢:
我们都是异乡人,真正的家都不知道在哪。
萧拉了拉那冰凉的小手,说:
要爸爸抱吗?
不,我自己走。
萧不由得想到那个只图自己快活的女人,是不可能娇惯这个女儿的。
爸爸抱你到那边平整的水泥路上。
上中班了?
老师喜欢你吧。
我帮老师叠被子,盛饭呢。
是吗,真乖!
阿姨好!
是你!
萧和那个阿姨异口同声地说。
自从那次在医院见了以后,他们彼此就再没见过面。
年轻的女人还是那么瘦小苍白,眼神还是那么忧郁。
她解释说:
今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萧想起他父母的忌日可能是在春天罢。
不肖子孙——也就十多年就忘成这样了。
萧顿了顿问:
过的还好吗?
那个女人也顿了顿,回答说:
唔,也还好罢。
——你知道,一个完整的家,对孩子女人来说很重要的。
她停了一下:
我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不想——那个女人忽然打住不说了,伸出那又瘦又小的手,摸了摸萧怀中那个被冬日的寒风吹得有点红紫的小脸:
你的女儿也很可爱,也上中班了?
是,阿姨。
阿姨再见!
爸爸,我要回家。
好,我们回家。
再见。
再见。
那个女人瘦小的身影,渐去渐远,起初是一个黑点,最后终于消失在傍晚的暮气里。
爸爸,太阳好大,像个红红的大橘子。
是,像个红红的大橘子。
萧看到西天边疏密的树梢间,静静地挂着一颗红红的大橘子。
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
——夕阳西下几时回。
——残阳如血。
——伫立门外,等待落日的人。
不知怎的,萧忽然零星地记起了几句有关夕阳的句子,又忽然记起一句朦胧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却要我寻找光明。
那个久远的诗人,婚姻的结局是那样的惨烈而又令人惊惧——可怜无辜的妻子,不知当时是怎么一副情状!
也许,婚姻中的宽容与隐忍未必换来光明的前景罢。
可是,人生中的诸多无奈,又有谁能够不偏不倚、完满解决呢?
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萧不自觉地叹了口气,他脑海中不由得掠过不知在哪读过的一句话来:
时间不舍昼夜地奔流,在某一个地方,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平静,既模糊又分明的轮廓成为定格,而她的目光却向着远方。
萧不禁暗想道:
也许一切的一切,就如同谶言,总有前因后果的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