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docx
《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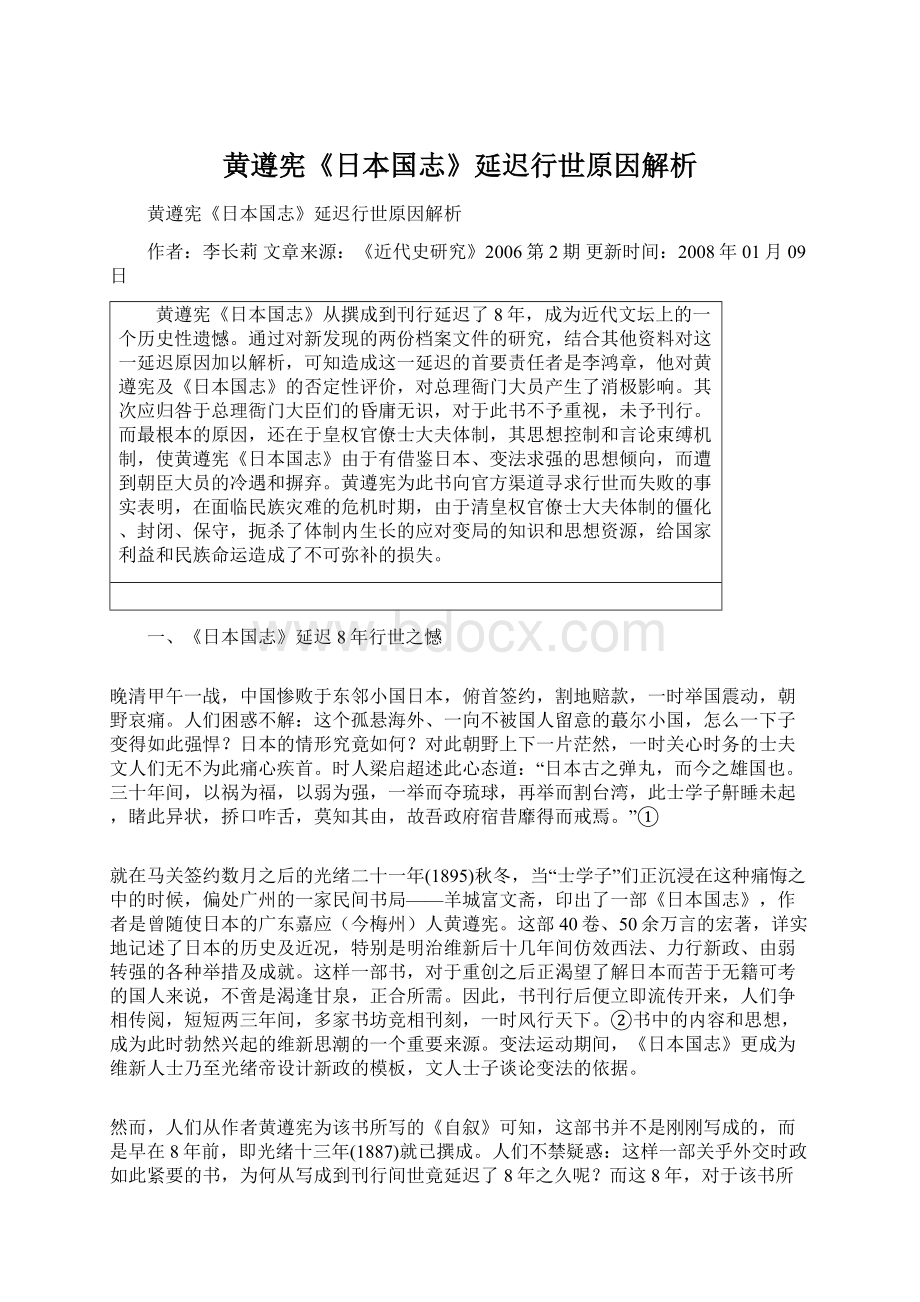
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
黄遵宪《日本国志》延迟行世原因解析
作者:
李长莉文章来源:
《近代史研究》2006第2期更新时间:
2008年01月09日
黄遵宪《日本国志》从撰成到刊行延迟了8年,成为近代文坛上的一个历史性遗憾。
通过对新发现的两份档案文件的研究,结合其他资料对这一延迟原因加以解析,可知造成这一延迟的首要责任者是李鸿章,他对黄遵宪及《日本国志》的否定性评价,对总理衙门大员产生了消极影响。
其次应归咎于总理衙门大臣们的昏庸无识,对于此书不予重视,未予刊行。
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其思想控制和言论束缚机制,使黄遵宪《日本国志》由于有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思想倾向,而遭到朝臣大员的冷遇和摒弃。
黄遵宪为此书向官方渠道寻求行世而失败的事实表明,在面临民族灾难的危机时期,由于清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的僵化、封闭、保守,扼杀了体制内生长的应对变局的知识和思想资源,给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一、《日本国志》延迟8年行世之憾
晚清甲午一战,中国惨败于东邻小国日本,俯首签约,割地赔款,一时举国震动,朝野哀痛。
人们困惑不解:
这个孤悬海外、一向不被国人留意的蕞尔小国,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强悍?
日本的情形究竟如何?
对此朝野上下一片茫然,一时关心时务的士夫文人们无不为此痛心疾首。
时人梁启超述此心态道:
“日本古之弹丸,而今之雄国也。
三十年间,以祸为福,以弱为强,一举而夺琉球,再举而割台湾,此士学子鼾睡未起,睹此异状,挢口咋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
”①
就在马关签约数月之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冬,当“士学子”们正沉浸在这种痛悔之中的时候,偏处广州的一家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出了一部《日本国志》,作者是曾随使日本的广东嘉应(今梅州)人黄遵宪。
这部40卷、50余万言的宏著,详实地记述了日本的历史及近况,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十几年间仿效西法、力行新政、由弱转强的各种举措及成就。
这样一部书,对于重创之后正渴望了解日本而苦于无籍可考的国人来说,不啻是渴逢甘泉,正合所需。
因此,书刊行后便立即流传开来,人们争相传阅,短短两三年间,多家书坊竞相刊刻,一时风行天下。
②书中的内容和思想,成为此时勃然兴起的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来源。
变法运动期间,《日本国志》更成为维新人士乃至光绪帝设计新政的模板,文人士子谈论变法的依据。
然而,人们从作者黄遵宪为该书所写的《自叙》可知,这部书并不是刚刚写成的,而是早在8年前,即光绪十三年(1887)就已撰成。
人们不禁疑惑:
这样一部关乎外交时政如此紧要的书,为何从写成到刊行间世竟延迟了8年之久呢?
而这8年,对于该书所系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对于中国的命运而言,又是何等重要、何等关键的8年!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此书延迟这8年问世,使中国朝野人士错过了在甲午战争之前了解日本情况、预作防范的时机,错失了借鉴日本、变法求强,以避免战争、至少不致惨败的契机。
正因为如此,这部书的延迟刊行令识者为之扼腕。
即在当时,就有黄遵宪的两位知友当面为此责备过他。
一位是与黄遵宪有多年交谊的同辈知友袁昶,在马关签约后不久见到黄遵宪,其行箧中就携有《日本国志》,他当面责备黄氏道:
这部书如果早一点刊行流布,可以省去战败输银二万万两!
③另一位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遵宪招来上海一起办《时务报》的维新志士梁启超,在当年给《日本国志》所作“后序”中,一腔“懑愤”、直言不讳、言词痛切地对年长25岁、以师事之的黄遵宪责备道:
“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就在于你黄先生“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④后来黄遵宪之弟黄遵楷也曾深为痛惜地谈到此书延迟刊行的遗憾谓:
黄遵宪撰成此书,“意在借镜而观,导引国人,知所取法。
然至甲午以后,始有知者。
虽风行一世,而时已晚矣。
”⑤
这些知友亲朋充满痛惜的责备与遗憾之语,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如果在他写成后即能很快印行流传,会使国人较早了解日本的崛起并以为借鉴,或可减轻乃至避免七八年后的悲惨败局。
虽然这一说法对此书的作用或有夸大,但这部《日本国志》的延迟刊行,对时人时局而言,确实是一个令人痛惜的历史性遗憾!
因一部史书的延迟行世而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命运如此之重者,恐怕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故此书的延迟行世,实为近代百年学坛的一大憾事。
那么,为什么此书写成后未能及时刊行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历史性遗憾?
谁应对此负责任呢?
对于上述问题,当时人虽多有责难,但未言其详,后世历史研究者则少有关注,也未见有专门的讨论。
而这一问题不只是关系一部史书的命运,实则是关系到在晚清中日关系转折的关键时期,官僚士大夫内部,对于有关日本威胁和国家命运的知识资源的利用,以及应对危机的机制问题。
而解明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晚清皇权官僚士大夫体制在应对国家危机时,知识资源、资政渠道及权力决策之间运作机制的缺失,以及由此给国家利益和民族命运造成的危害。
以往对上述问题不能明了的主要原因,一是黄遵宪本人没有作正面的回答,二是关于黄遵宪对《日本国志》撰成后的处理情况缺乏确实的资料。
以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日本国志》初刊本前黄遵宪的《自叙》,及所附的李鸿章《禀批》、张之洞《咨文》,由此可知黄遵宪在此书撰成后曾将稿本上呈于李鸿章、张之洞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
据此,研究黄遵宪较早的权威钱仲联,在所撰《黄公度先生年谱》(以下简称“钱谱”)中述此书撰成后抄写四份,一上总署,一上李鸿章,一上张之洞,一自存。
⑥而初刊本所附的李氏《禀批》和张氏《咨文》并未注明年月,故“钱谱”将上呈之事系于光绪十三年(1887)此书撰成的当年,而对上呈稿本的具体情况则没有说明。
此后各家论著皆沿此说。
⑦此外,张氏《咨文》按当时的公文程式录有黄遵宪的禀文,而李氏《禀批》中却没有黄氏之禀,同式公文一有一无,不合于常理。
这些资料的缺失都为此书撰成后的出路及刊行问题留下了疑问:
黄遵宪向上述三处上呈稿本究竟在何时?
上呈稿本与此书刊行是否有关?
初刊本所附李氏《禀批》中为什么没有黄氏之禀?
李氏《禀批》与此书的刊行有无关系?
这些都关系到黄遵宪对书稿的处理问题,而由以往这些残缺的资料则难以说清。
笔者2004年11月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看到了李鸿章和张之洞向总署上呈《日本国志》的批咨全文抄档,其中不仅有两文上呈总署的具体日期,还录有黄遵宪上李鸿章的禀文,这些都是初刊本李氏《禀批》和张氏《咨文》所缺的资料。
⑧这两件档案,为解明《日本国志》延迟刊行问题,提供了一些关键性的信息。
下面就结合其他资料,对《日本国志》一书延迟刊行的原因作一解析。
二、黄遵宪对《日本国志》行世用世的态度是否消极?
前述梁启超对于黄遵宪的责问中,有“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⑨之句,虽然梁氏语气中或有因痛之深而不免责之过切的因素,但他显然将此书延迟行世的责任,归之于黄遵宪本人的过于“谦让”,即不积极谋求刊行使之流传的消极态度。
黄遵宪对袁昶责问的回答中也有“我笑不任咎”之语,似乎袁昶也有归咎于黄氏之意。
此外,黄遵宪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改订此书时,也曾对友人说过,此书“成书十年矣”,“其迟迟印发之故,弟固不任受咎也”。
⑩可见,当时一般舆论似都有将此书迟刊归咎于黄遵宪本人态度不积极的意思。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看黄遵宪对梁启超责问的回答。
他说:
此书只是一部史书,是为了“使千万里之外,若千万岁之后”的后世“读吾书者”,能够据此了解日本,进而“知吾世,审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荣其国,言焉者辅其文”,如不用我言,则会受到人们的批评,“咨嗟之,太息之”。
他说这才是史书的“经世”之义,自己只是想作这样一个“良史之才”。
(11)由黄遵宪的这番回答,似乎他并不求此书对当下的时政直接起作用,不急于用世,而只是期以在“千万岁之后”发挥启发后人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从其为此书所写《自叙》述及写书缘起时,强调以使官写史书为主旨,似可以相互印证。
由此看来,他似乎对此书行世的态度的确不大积极急切。
然而,这果真是他的真实心态吗?
揆之事实,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黄遵宪撰写这部书具有十分强烈的用世之志。
他自光绪三年(1877)以参赞身份随使日本,不久便立意撰写《日本国志》,在日本4年多时间,撰写此书成了他使事之余的重心。
他利用各种途径广搜资料、多方咨访,同时随着对日本明治维新的了解和认识渐趋深入,其撰书意旨也渐由述史而趋重借鉴,并初步形成了仿效日本变法求强的改革思想。
他在撰成初稿后即调任美国,任旧金山总领事。
在美3年余,虽对使事多所措置,但他自感满腔抱负不得施展,遂乞假回籍,抑郁而归。
由美返乡途中,他写下了不少失意悲凉的诗句。
如《归过日本志感》诗有云:
“旧游重到一凄然,电掣光阴又四年。
”《今夕》:
“已去年华一弹指,无穷心事九回肠。
”(12)正是在这种失意抑郁的心绪之下,他决心暂离官场,回乡著书,完成自己多年的心愿。
他摈绝了留任美国使事及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巡南洋之邀,乃“闭门发箧”(13),潜心撰述,两阅寒暑,终于定稿。
这时他正值40岁的盛年,在此前8年间,居日本、游美国,目睹东西洋的富强之业,其心志已为之大变,效日本、仿西洋,变法求强,用世救时,已成为他的明确志向。
他在这时中断仕途,摒绝外务,闭门撰述所成之书,乃是其凝聚一腔抱负、满腹才志的发愤之作。
只是迫于清朝廷的言论钳制和士林的舆论束缚,他的变法思想还不能公然表达出来,因而他是借助史书形式,借记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救时思想。
故其自谓该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特别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
(14)所谓近者、今者,即主要记述明治维新的情况,因此他自称此书为“明治维新史”(15)。
他在书中穿插的以“外史氏曰”的形式直接抒发的议论,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对日本变法维新的赞赏及借鉴之意。
故此,这部书虽然形式上是一部史书,实则倾注了他积蓄已久的经世用世、救时变法的深思大志。
他在后来补作的《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一诗中,追述自己撰成此书时的感想道: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入境庐。
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
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
”(16)诗中表达了他当年白海外归来,由东西洋的强盛而反观我国上下锢蔽自封、不思变革的忧愤之气,以及空怀一腔“忧天热血”,只有“洒泪挑灯”、冒罪议政、闭门撰述的悲愤与孤寂。
虽然这些话是他在戊戌遭罢黜以后才敢说出来,但却是他撰成此书时真实心境的写照。
(17)故而,他撰述此书,绝非作藏之名山、留待后人、许以“良史”的迂腐之想,而是要用之于当下,作为救时与劝世的资政之方。
对于这一点,他虽然因避时忌而不便公然明言,只是在《自叙》中含蓄地说了一句:
“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但通篇来看,他的忧时忧国、志在变法求强的用世之意贯穿全书。
可见他对于梁启超责难的前述回答,并非出自真意,而只是对这位相交未久、涉世不深、意气激昂的年轻后辈的敷衍搪塞之辞。
黄遵宪既然撰写此书有如此强烈的用世之志,那么,他撰成此书后,对其行世之出路是否积极地作了考虑和安排了呢?
事实上,他确实为此书的刊行问世而积极奔走,首先选择的出路就是他认为最正常、最合理、最快捷、最有效的官方途径。
三、黄遵宪为《日本国志》刊行寻求官方途径
由《日本国志》初刊本所附李氏《禀批》和张氏《咨文》可知,黄遵宪在撰成此书后,曾将抄本上呈总署、李鸿章和张之洞。
但其具体情况怎样?
目的为何?
与此书刊行有无关系?
以往这些问题皆不详。
现据档案之件可知,李鸿章的这篇代呈《日本国志》的批咨呈文,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十一月十七日呈给总署的。
而据“钱谱”所载,黄遵宪正是在这年十月、亦即李氏呈文的前一月离乡由海路北上进京的。
此时距其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撰成书稿有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段时间他仍居乡,应当是在抄写书稿、处理家事等以做北上赴京呈书的准备。
可以推测,正是此次黄遵宪携书稿北上入京,取道天津而将稿本及禀文上呈给北洋大臣李鸿章。
而此次黄遵宪北上进京,并非承朝廷或任何官员的招募任用,而完全是他个人的自主行为,是他经两三年的闭门著书、潜居乡里之后,谋求出山用世以大展其志的举动。
他此次携带着倾注多年心血的《日本国志》稿本北上进京,其意就在于呈书自荐、藉书进身、为此书此身寻求用世的出路。
因此,黄遵宪给李鸿章的禀文内容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自荐《日本国志》,并请其将书稿代呈总署。
那么,黄遵宪为何急切地请李鸿章将此书稿代呈总署呢?
这与他对此书行世的设想有无关系?
对此虽然禀批文因遵循事决于上、不可逾权的官场规制而并未明言,但我们可据情势作出以下两点分析:
第一,黄遵宪认为《日本国志》是遵行总署之命的奉职之作,故理应上呈总署,以尽使官之责。
请李鸿章代呈书稿给总署,是他认为此书最为直接、有效的上呈渠道。
出使海外事务例归总署管理,自从光绪初年清廷开始向海外正式派驻出使人员,鉴于朝臣对外国情形几无所知,为了解外情的需要,总署便规定,各出使大臣需逐日记述所驻之国政情民俗及交涉等诸情形,上呈总署以备考察。
光绪元年(1875)清廷派出的第一个出使大臣郭嵩焘就曾说:
“初议至西洋,每月当成日记一册呈达总署,可以讨论西洋事宜,竭所知为之。
”(18)次年总署在奏订出使章程12条时,又附片奏请饬令出使东西洋各国大臣:
“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
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即办理一切,似不至漫无把握。
”并作出具体规定:
“务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仍按月汇一册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即翻译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随时咨送,以资考证。
”(19)此奏获得旨准后便颁发各驻外使臣,使依例而行,遂成定制。
此后不仅各出使大臣皆需定期向总署呈送日记,而且其他随使人员如有相关著述也可呈送。
如黄遵宪到日后不久所撰写的以诗歌形式记述日本政情民俗的《日本杂事诗》,以及后任使日随员姚文栋撰写的《日本地理兵要》,便都被呈送总署。
正是这一制度,使黄遵宪深感肩负的责任,也是促使他到日不久便起意编撰《日本国志》的一个主要动因。
所以,黄遵宪在上李鸿章禀文中,开篇就是抄录总署颁发的这一奏议,以为其撰写此书的动因及呈送总署的依据,意在向李鸿章和总署大臣表明,撰写《日本国志》一书是承总署之令,履行使官之责,依制而为的行为,所以将之上呈总署就是循例而行、顺理成章的事。
但依规制,只有出使大臣及督抚大员,才能直接与总署公文来往、上呈书函等,黄遵宪身处下位不能越级自行呈送,因此,他必须找一位够级别的大员为其代呈。
那么找谁呢?
作为使日的奉职之作,理应找主持对日交涉的大员。
黄遵宪已离开日本使任6年,并已无职乡居3年之久,不可能再请现任驻日大臣为之代呈。
而荐领其出使日本、并支持他撰写《日本国志》的前使日大臣何如璋,卸任归国后任船政大臣,已于光绪十年(1884)因中法战争获罪而被罢官遣边,不可能再为之举荐了。
当时最有资格和权位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他既是朝廷和总署深相依靠的洋务大僚、外交重臣,也是实际主持外交事务、亲手处理对日交涉的首辅,其言对于总署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而且黄遵宪出使前早在光绪二年(1876)上京乡试时就曾谒见过李鸿章,李氏曾许以“霸才”(20)。
使日期间黄遵宪协助何如璋处理琉球问题等对日交涉,与李鸿章也多有公文往来。
所以李鸿章对黄遵宪应是熟悉和了解的。
因而对于黄遵宪来说,李鸿章是托付代呈此书的最佳人选。
此外,当时清廷对外交人员还没有正式的登进制度,而实行大员保荐制,随出使大臣卸任回国的随使人员只有通过大员的保荐,才会得到官职,受到任用。
(21)故黄遵宪此番呈书李鸿章,也会有借助李氏之大力而求得以书荐人、人书共进的考虑。
他在上呈李鸿章禀文中说,此书“兹已缮录成帙,谨呈典签,赐以训诲,无任欣幸……伏俟中堂(即李鸿章——引者)训谕后,拟赍之以呈总署。
如钧旨以为不谬,可否俯赐大咨,移送总署,以备查考,敬候卓裁。
”显然,他是想首先得到李鸿章对此书的嘉许,“赐以训诲”,然后由其举荐代呈于总署,以得到总署大臣的重视。
第二,黄遵宪请李鸿章将书稿代呈总署,其目的不只是仅供总署大员“查考”,而是希冀总署依例为其刊印行世,这是他认为此书最适当、最快捷、最有成效的刊行渠道。
黄遵宪在禀文中讲述完撰写此书的缘起、过程及此书的主要内容之后,接着写道:
“职道自奉使随槎,在外九载,尝慨中国士夫于外事不屑措意。
通商五十年,惟《瀛寰志略》、《海国图志》二书椎轮创始,粗具大概,积岁已久,未有续书,即留心时务者亦无所凭藉以资考证。
东西之人多谓中国士夫昧于外务,职道心焉惜之。
职道……前后八载成此一书,实欲以拓中土之见闻,杜外人之讥议。
区区微意,盖在于此。
”
这段文字明白地指出,他上呈此书的目的,并不只是仅供几个总署大员“查考”,而是“欲以拓中土之见闻”,希望此书能够刊行流布,使国中广大“留心时务者”能够藉以了解外国情况,“以资考证”,以矫正“中国士夫昧于外务”之弊。
他还标举早已广为流传、名满天下的早期记述西洋的史书《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二书为例,将自己所撰的《日本国志》比之为“续书”(22),其自期之高可以想见。
在这些言词之间,其希望此书刊印行世使之流布天下的意愿,虽格于出自上裁的规制而不便明言,却已经十分明白地表达出来了。
黄遵宪希望总署为之刊行的愿望并非无因,而是有例为据、有章可循的。
总署附设的培养翻译人材的同文馆,其师生在教学之余也翻译一些书籍,最初总署择其有用者临时印行,后因需要增加,于同治十二年(1873)购买了活字4套,印刷机7部,正式在馆内设立印书处,专门承印总署及同文馆的各种书籍文件等。
(23)一些总署认为对于洋务外交有用的书籍,往往刊印后免费分发给京内外官员。
故由总署印行的书,不仅标志着朝廷的看重,而且流传也广,在官场士夫中颇有影响。
清廷派出使外官员以后,总署也选择一些使臣的出使日记由此处印行。
如第一位出使大臣郭嵩焘使英之初的日记,总署便冠以《使西纪程》之名为之印行。
但由于其言辞间对英国政教风俗有称许之意,被朝野士夫大加攻击,遂诏令毁板,酿成震动朝野的一大风波。
(24)虽有此挫折,但此一制度并未废止。
黄遵宪本人,也曾受益于这一制度。
他到日本后作为撰写《日本国志》的准备而于光绪五年(1879)写成的《日本杂事诗》,就上呈给了总署,当年即由同文馆印书处印行(25),在官员士夫中流传开来,黄遵宪也因此而文名始播。
此事对黄遵宪来说,无疑是一极大的鼓励。
在他看来,《日本国志》的价值远在《日本杂事诗》之上,理应刊行。
况且,就在不久前的光绪十年(1884),清廷出于对中法战争的反省,据使日大臣徐承祖、福建巡抚刘铭传等奏请,谕令总理衙门组织使外官员收集汇刻有关西洋及海防的书籍,谕称:
“即行知照出使各国大臣,将西洋各书及舆地图说,分别选择,咨送该衙门,酌量汇刻,颁发各省,并将中国所有论海防各书,一并采择。
”(26)当时的使日随员姚文栋所撰述的介绍日本军事及地理情况的《日本地理兵要》一书,就在当年上呈总署并被刊印出来。
黄书内容远比姚书详备,因而黄遵宪认为自己的书比姚书价值高得多。
(27)所以在黄遵宪看来,《日本国志》由总署为之刊印行世,应当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
由此可见,在黄遵宪看来,《日本国志》既为使官奉职而作,书稿经由李鸿章举荐上呈总署,希望由总署刊印行世,使他在书中对日本维新的记述及所阐释的思想,既能影响当政大员,又可借官力而影响朝野广大“留心时务者”,使之发挥最大的影响,这是此书最适宜、最合理、效益最大的首选出路。
这一出路也许是他在撰写此书时就早已想好的。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改订此书时给友人的信中,述及初刊本附有李氏《禀批》和张氏《咨文》的原因时曾说道:
“弟之初意,往用公牍文字,义系于官。
”(28)意谓此书之撰写及上呈,皆属自己身为使官而循章尽责的奉职行为,故由官方渠道上呈总署及希望印行该书,也是义之所在。
由上可知,黄遵宪撰成《日本国志》书稿后,对于此书的行世态度并不消极,而是积极地循官方途径,为此书寻找最佳的行世出路。
其意在希望借助李鸿章和总署之力,使此书由官方刊行流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得到以书见重、书与人并进以大展其才志的最佳效果。
然而,作为这一途径的关键的第一步,将书稿上呈李鸿章,希望首先得到李鸿章的赞赏和肯定,由这位具一言九鼎之力的当权重臣举荐转呈总署,其结果又如何呢?
我们从《日本国志》初刊本所附之李氏《禀批》可知,李鸿章对此书确实作了评价并将此书上呈给了总署,但是我们知道,总署后来并没有刊印此书。
那么,李鸿章的批文从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
以往只从李氏之批文看不出什么明显意味,现在我们将档案原件中黄遵宪之禀文与李氏批文加以对照分析,便会看到其中大有深意。
四、从黄禀李批对照看李鸿章对《日本国志》的评价
单从李鸿章这篇批文字面来看,对黄遵宪《日本国志》一书多有“博稽深究”、“订证赅备”等肯定之语,而没有明显否定的文字,似乎李鸿章对此书是表示肯定与赞赏的。
而黄遵宪后来将其附入书前一并刊印,也显然有借重李鸿章的褒扬以自重之意。
但是,附刊的李氏《禀批》中没有黄遵宪的原禀,而按当时公文规制,上呈给总署的批咨需录有原禀以便上司了解其事之原委。
李氏之《禀批》与排列其后的张氏《咨文》是两篇规制相同的公牍文字,都应是黄遵宪本人提供的,为何后一篇禀咨并存,而前一篇却有批而无禀呢?
再者,黄遵宪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改订此书时,将李氏《禀批》和张氏《咨文》一并撤掉了。
虽然这两篇文字与此书体例有不合的因素,但初刊时既已附上,显有借重之意,如果这两篇文字都对此书起到正面作用,何以黄遵宪改订时又要撤掉?
如果说撤掉李氏《禀批》是由于甲午战后李鸿章因主持和议而颇受国人诟病,以避其形象之污,则张之洞此时尚属上升之势,与这时活跃的维新人士多有呼应,名望甚佳,何以连其《咨文》也一并撤掉?
显然,黄遵宪对于这两篇文字是有所不满的,但其原因何在?
这些都是以往不易弄清的疑问。
现在看到了总署档案中保存的附有黄遵宪禀文的李鸿章批文的全件,将黄氏的禀文与李鸿章批文一加对照才终于发现,原来一禀一批大异其趣!
黄遵宪上禀之时,是否曾与李鸿章见面交谈已无籍可考,现在只能根据这一禀一批的内容进行对照分析。
黄禀共计600余字,除了开头引述总署令使臣记载咨报之奏议外,其余皆为对《日本国志》一书的自荐之语。
其内容,虽有小部分词语表面上与其为该书所作《自叙》中的语句相似,但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其主旨,则与《自叙》显有区别,要皆不便公然表于世,而只可向当政者上言的“内部”之语,同时又因有所避忌而语词隐晦。
李鸿章在接到黄遵宪禀文并对此书“详加披览”后,作了批文,仅200余字。
如果单看此批,表面上并无明显的否定之语,但与黄禀一加对照,便可看到其关键词句都是直接针对黄禀所言,甚至可说是直言相驳,对黄禀、黄书的消极评价跃然纸上。
二者主旨之异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二人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评价不同。
李鸿章驳斥黄遵宪对日本明治维新变从西法、新政即是西国富强之政的肯定评价。
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的主旨,就是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就。
他在书中列举了日本全面仿效西法的诸项新政,对此多所赞誉,谓为富强之举,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明显持肯定态度。
他在禀文中委婉地指出了这一点:
“其国自德川将军主政以来,禁绝通商,锁港二百载。
暨一战于马关,再战于鹿岛,乃隐忍成盟,联衡诸大,其变迁情势与亚细亚诸国略相仿佛。
而维新之后,如官职、国计、军制、刑罚诸大政,皆摹仿泰西,事事求肖,又足以观泰西政体。
但能详志一国之事,即中西五部洲近况皆如在指掌。
”
这段话对于日本维新前后作了比较,维新前闭关锁国、“禁绝通商”,与中国情况相似。
对其维新后的情况,则指出其诸大政“皆摹仿泰西,事事求肖”,即全面地变从西法,而且他认为仿效得相当成功,其诸大政已经与西国之政相类,故谓由日本新政即“足以观泰西政体”,而自己记述日本新政的这部书,也可看作西国富强之政的简要教本,故谓之“但能详志一国之事,即中西五部洲近况皆如在指掌”。
黄遵宪在禀文中虽言语简短,用词隐晦,但他对于日本诸大政全面变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