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的赋税制度.docx
《关于秦的赋税制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秦的赋税制度.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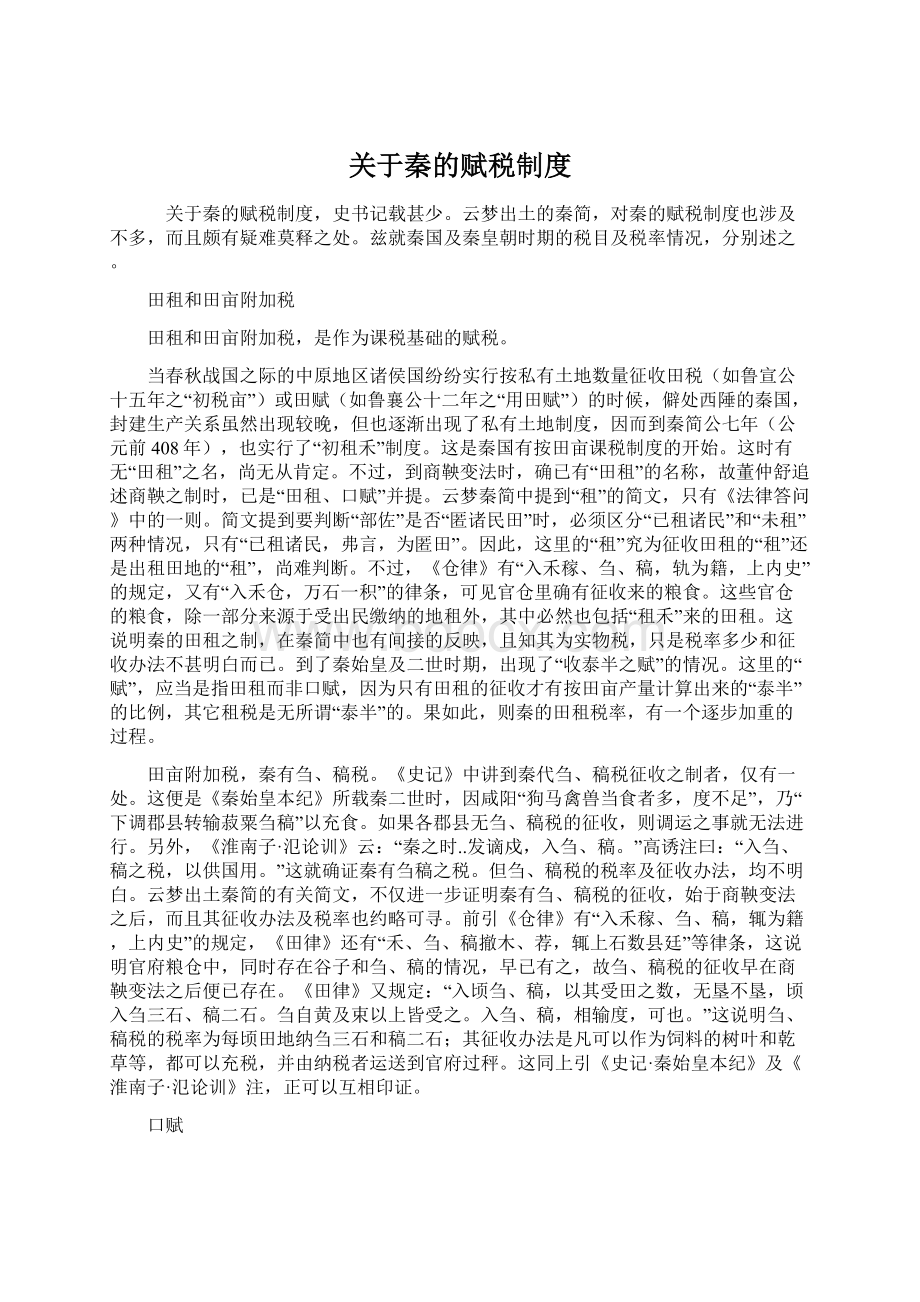
关于秦的赋税制度
关于秦的赋税制度,史书记载甚少。
云梦出土的秦简,对秦的赋税制度也涉及不多,而且颇有疑难莫释之处。
兹就秦国及秦皇朝时期的税目及税率情况,分别述之。
田租和田亩附加税
田租和田亩附加税,是作为课税基础的赋税。
当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原地区诸侯国纷纷实行按私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税(如鲁宣公十五年之“初税亩”)或田赋(如鲁襄公十二年之“用田赋”)的时候,僻处西陲的秦国,封建生产关系虽然出现较晚,但也逐渐出现了私有土地制度,因而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也实行了“初租禾”制度。
这是秦国有按田亩课税制度的开始。
这时有无“田租”之名,尚无从肯定。
不过,到商鞅变法时,确已有“田租”的名称,故董仲舒追述商鞅之制时,已是“田租、口赋”并提。
云梦秦简中提到“租”的简文,只有《法律答问》中的一则。
简文提到要判断“部佐”是否“匿诸民田”时,必须区分“已租诸民”和“未租”两种情况,只有“已租诸民,弗言,为匿田”。
因此,这里的“租”究为征收田租的“租”还是出租田地的“租”,尚难判断。
不过,《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轨为籍,上内史”的规定,又有“入禾仓,万石一积”的律条,可见官仓里确有征收来的粮食。
这些官仓的粮食,除一部分来源于受出民缴纳的地租外,其中必然也包括“租禾”来的田租。
这说明秦的田租之制,在秦简中也有间接的反映,且知其为实物税,只是税率多少和征收办法不甚明白而已。
到了秦始皇及二世时期,出现了“收泰半之赋”的情况。
这里的“赋”,应当是指田租而非口赋,因为只有田租的征收才有按田亩产量计算出来的“泰半”的比例,其它租税是无所谓“泰半”的。
果如此,则秦的田租税率,有一个逐步加重的过程。
田亩附加税,秦有刍、稿税。
《史记》中讲到秦代刍、稿税征收之制者,仅有一处。
这便是《秦始皇本纪》所载秦二世时,因咸阳“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乃“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以充食。
如果各郡县无刍、稿税的征收,则调运之事就无法进行。
另外,《淮南子·氾论训》云:
“秦之时..发谪戍,入刍、稿。
”高诱注曰:
“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
”这就确证秦有刍稿之税。
但刍、稿税的税率及征收办法,均不明白。
云梦出土秦简的有关简文,不仅进一步证明秦有刍、稿税的征收,始于商鞅变法之后,而且其征收办法及税率也约略可寻。
前引《仓律》有“入禾稼、刍、稿,辄为籍,上内史”的规定,《田律》还有“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等律条,这说明官府粮仓中,同时存在谷子和刍、稿的情况,早已有之,故刍、稿税的征收早在商鞅变法之后便已存在。
《田律》又规定:
“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
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
入刍、稿,相输度,可也。
”这说明刍、稿税的税率为每顷田地纳刍三石和稿二石;其征收办法是凡可以作为饲料的树叶和乾草等,都可以充税,并由纳税者运送到官府过秤。
这同上引《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淮南子·氾论训》注,正可以互相印证。
口赋
口赋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赋税。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后,于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初为赋”。
按“赋”,本为军役及同军役有关的军用品征发的专称,如《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晋国的“城濮之赋”、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国的“量入修赋,赋车借马”、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国的“赋皆千乘”及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的“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等语中之“赋”,都是这个意思。
在国有土地制度下,军赋同土地的授予联系在一起。
私有土地制出现后,军赋就逐渐转化成为对人口的课税名称。
尽管“赋”与“税’的区分日益显得不严格,但班固仍在《汉书·食货志》中称:
“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谓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府库赐予之用。
”颜师古在注中也说:
“赋,谓计钱发财,税谓收其田入也。
”
秦时之“赋”,因为系以人口为课税对象,故其征收方式,谓之“头会”;其名称,又谓之“口赋”。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谓秦有“头会箕敛”之制;《淮南子·氾论训》有“头会箕敛,输于少府”的记载。
高诱注“头会箕敛”曰:
“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敛,似箕然,敛财多取意也。
”证以秦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的规定,则“箕敛”确有以课税之钱封藏于箕畚的意思。
又《汉书·食货志》载西汉董仲舒追述秦制时说: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
”一名“头会”,一称“口赋”,可证“赋”是按人口征收甚明。
故“赋”本质上是人口税或人头税。
据汉制,人口税又分为两种类型:
一为课取于十五岁以上成年男女的人口税,谓之“算赋”;二为课取于七岁以上和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者的人口税,谓之“口钱”。
秦之“赋”有无此类别区分,史无记载,但“算赋”之名,秦时确已有之。
故秦昭王与夷人约时规定:
“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
”汉人晁错,也谓“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出秦时确已有“算赋”之名,而且每个成年男女缴纳算赋的量为“一算”。
这表明“算”已经是一个固定钱数的计量单位的名称,只是每算的定额不明而已。
秦时既已有课取于成年人的“算赋”的专称,则课之于未成年者的“口钱”之制,秦时也应当存在。
因为这时已存在“口赋”的名称,而“口赋”一词,在《汉书》及《后汉书》诸帝纪中凡单称时,均系合“口钱”与“算赋”二者之称;《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所引《汉仪注》,把“口钱”与“口赋”等同;《后汉书》诸帝纪,又往往“口、算”并称;《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条李贤注“口赋”时,也引《汉仪注》所载“口钱”与“算赋”二者为证。
以此言之,则董仲舒所说的秦之“口赋”之制,实包括“口钱”与“算赋”二者,只是“口钱”的征收量不明而已。
户赋
跟口赋有密切关系的,还有“户赋”。
据秦时史籍,无“户赋”这一税目。
但云梦秦简的《法律答问》简文,却提出了秦有“户赋”的问题。
简文问曰:
“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
”回答是:
“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也。
”意即被隐藏的户口,可以不服徭役和不纳户赋。
以此言之,秦时确有“户赋”的征收。
但是,在秦简的其他简文中,再无“户赋”的痕迹。
汉制大都本于秦制,在汉代史籍中也无户赋的迹象。
因此,秦时究竟有无“户赋”?
只有等待其它地下材料的出土才能明白。
关市之税和商品税
关市之税和商品税是以商贾和他们的货物为课税对象的税。
早在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表明私营商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在城市中设置固定市场的需要。
及秦孝公徙都咸阳,同样在这里设置了固定市场,故商鞅得以“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
随着民营商业的发展,征收关津、市井之税就出现了。
故商鞅变法时,已有“重关、市之赋”的措施。
所谓“关”,即指关卡;所谓“市”,即指固定的贸易市场。
因此,“关、市之赋”应包括关卡税与市税,前者为商贾货物通行税,后者为商贾贸易税。
《商君书·垦令》还有“市利之租必重”的立法精神。
所谓“市利之租”,实可简称为“市租”。
到了汉代,果然出现了“市租”之名。
这可见“市租”之制实始于秦国商鞅变法之时。
结合秦时存在严格的市场管理以及商贾另立“市籍”等措施来看,秦时确有“市租”的征收④,而且是课之于商贾的贸易税。
商品税,包括盐、铁、酒、肉之税。
据现在的史料考察,秦时确已有商品税存在,只是未及于所有商品,只限于盐、铁、酒、肉等民用所必需的商品。
早在秦穆公时期,对盐商的课税就开始了,故《说苑·臣术》载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征诸贾人”。
商鞅变法之时,商品税的征收,已扩大到了酒、肉、铁等商品。
《商君书·垦令》云: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
”这不仅表明酒、肉等商品已有“租”,而且其租重到十倍于其成本。
其目的在于减少商贾从事酒、肉贸易的量和使农民不事饮酒作乐,借以发展农业。
这同云梦秦简《田律》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的精神是一致的。
除酒、肉外,还有对铁的课税。
故董仲舒说:
商鞅之时,“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秦惠王时,命张若于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
司马迁之祖司马昌,曾为秦铁官。
这些事实,说明秦已有官营盐、铁之制,不仅课取盐、铁的商品税而已。
山海池泽之税
《盐铁论·非鞅》云:
“商君相秦,..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而师以赡。
”《汉书·百官公卿表》也说:
“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
”所谓“山海池泽之税”,包括范围至广。
由于奴隶社会普遍实行国有土地制,到秦、汉时期国有土地制虽在逐步崩溃之中,但还有相当残留。
因此,“山海池泽”,一般被视为封建国家所有。
所谓山泽之利就其广义而言,凡名山大泽的土特产、木材、鱼类、飞禽走兽以及地下矿藏都包括在内,正如《盐铁论·复古》所云:
“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
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
”这显然包括盐、铁等税在内。
但狭义而言,则仅指入山伐木、采薪、放牧及下水捕鱼、采珠之类而言。
可以简称为渔采畜牧税。
秦时史籍,没有说明“山海池泽之税”的具体内容及征收方法和税率等。
云梦出土秦简的《田律》,有禁止百姓伐材木山林”,“取生荔、麛卵豰”、“毒鱼鳖、置阱网”等法令,即不准砍伐山林,不许采取植物的嫩芽和不准捕捉幼兽、幼鸟及毒杀鱼鳖、捕杀鸟兽,也许正是为了征收山海池泽之税的缘故。
如以西汉末期王莽时的规定准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泽及畜牧者”,“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
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实者,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则山海池泽之税,确可概括为渔采畜牧税,且其税率为所采取之物的价值除去成本后的十分之一。
依上所说,秦的赋税制度,包括货物流通、商贾贸易、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渔采畜牧及每个人的人身,都在课税之列。
其课之于商贾者,又通过商品价格而转嫁于消费者。
故最终是劳动人民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剥削。
这就无怪乎“赋税大”,为引起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汉承秦制,在赋税制度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凡秦已实行的税制,汉代均继续实行。
如果说有所变化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新的税目的增加和旧税税率的增减等方面。
今分别述之。
田租及其税率的下降和征收的办法
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刘邦立即恢复了按民有土地数量征收田租的制度,只是其税率从秦“收泰半之赋”减到了十五税一。
《汉书·食货志》所谓“汉兴,接秦之弊,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即指此而言。
但是,随后不久,田税税率又有所增加,是以到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又“减田租,复什五税一”的田租率,终惠帝、高后之世无变化。
到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下诏:
“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虽然这次所减仅当年田租,但开了田租三十税一的先例。
及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一次“赐农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三年,又下令“其除田之租税”,接连出现了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和无田租征收的状况。
不过,孝文帝十三年的“除田租”,恐仅限于十三年一年,并非自此年至景帝初年均无田租。
因为根本不征收田租的作法,既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又无以支付官府的廪食和官吏的俸禄,还与《史记·孝景本纪》所载景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除田半租”之事矛盾。
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益知孝文十三年之“除肉刑及田租税律、戍卒令”等,乃是指废除秦时苛重的田租律而言,并非根本取消已经减了的田租。
因此之故,景帝元年,未云复田租,而可以有“除田半租”之事发生。
景帝的所谓“除田半租”,即在十五税一的田租基础上再减轻一半,这就变成了《汉书·食货志》所说的: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
”在这里,《史记》、《汉书》所载虽有景帝元年与二年的差别,但田租税率的变化,至此形成了定制,迄于东汉之末而无所改易。
需要说明的是:
东汉初年,曾因用兵之需而提高田租税率为什一征收制,但到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令郡国收见田税,三十税一如旧制”,又恢复了自景帝之初确立的三十税一的田租制,故田租税率的改变时间,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
其间虽有人主张增加田租率,也未被采纳。
是以西汉的田租,地主阶级政治家认为是“轻税”。
关于汉代田租的征收办法,首先,系以实物缴纳,属于实物税,与秦相同。
这从漕运、官吏俸禄开支与兵士廪食支出等可以获得证明。
其次,是按固定税率以田地多少与产量高低相结合的办法征收。
这是因为,如果按颜师古所说的“租税之法,皆依田亩”征收,则否定了定率三十分之一的作用;既按定率,则非以产量为基数计算不可。
因此,汉代田租的征收,必然是按定率结合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征收。
正如《盐铁论·未通》所说:
“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
”其三,田租征收时,还需要逐户估产:
正因为征收田租时要看产量高低,故仲长统有“今通肥饶之率,计稼穑之入”以征收田租的主张;东汉山阳太守秦彭,也有“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专立文簿,藏之乡县”以为征收田租依据的作法;就全国而言,则有各乡设“乡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的制度。
这就是说,田租的征收,还有一个按户估计田亩产量的过程。
田租的征收,既按定率又结合田亩多少与产量高低进行,就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不利。
这是因为,按田亩多少课税,虽然田多者税多,田少者税少;但又按产量定率征收,因多施肥、勤用力以及精耕细作获得的高产,也同样按比例变成了田租而流入了官府的仓库。
贫苦农民田地虽少,但税率甚低,故田多的地主因轻税而获厚利;反之,贫苦农民却因定率而多输田租。
故两汉田租虽轻,获利者仍是地主而非贫苦农民。
刍、稿税的加重
除按私有土地的数量征收田租之外,整个西汉时期,也同秦一样还有田亩附加税--刍、稿税的征收之制。
西汉政权建立之初,就已有征收刍、稿税的制度,故萧何为民请求入田上林苑空弃地时,要求官府给予这些农民以“毋收稿为兽食”的优待。
元帝时,贡禹上书言及当时农民的痛苦之状时,也说农民“已奉谷租,又出稿税”。
东汉时期,不论是光武帝,还是和帝、殇帝和安帝,都有因自然灾害而“勿收田租、刍、稿”或“勿收租、更、刍、稿”的诏令,事详《后汉书》诸帝纪。
正因为刍、稿税存在于整个两汉时期,故王充在其著作中发出了“今量租、刍,何意?
”的疑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汉官仪》,也有“田租、刍、稿,以给经用”之语。
汉代刍、稿税所不同于秦者有四:
一为刍税出现了田刍和户刍的区分,其征收方式也产生了按田亩与按户的差别;二为刍税重于稿税,刍税之中户刍又重于田刍;三为刍可以折稿充税和以钱折纳,刍一石当稿二石;四为刍、稿税税率的增加。
其主要证据,就是1973年9月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的第六号木牍。
据木牍内容,知为记录平里与稿上里的刍、稿税征收情况的牍文。
记录的格式二里完全相同,即先讲应征户刍若干,再讲应征田刍若干,总计应纳刍税额为若干;缴纳时规定以钱折纳者若干,以刍当稿者若干,然后才得出当纳刍税的定数。
接着才讲应纳稿税若干,缴纳时规定以刍当稿者若干,合计稿税若干。
以平里的情况而言,户刍与田刍合计为卅一石三斗七升,除去以钱折纳者和以刍当稿者外,应输刍输总额廿四石六斗九升;其田稿原额为二石二斗四升半,加上以刍当稿者十二石,共计应纳稿税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以稿上里而言,户刍与田刍合计为十四石六斗六升,除去以钱折纳者和以刍当稿者外,应纳刍税总额为十三石四斗六升;其田稿原额为八斗三升,加上以刍当稿者二石,则应纳稿税二石八斗三升。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与牍文中所列数字无不契合。
因此,以刍当稿的折合比例是:
刍一石折稿二石。
从上述平里、稿上里的刍、稿税缴纳实况来看,清楚地反映出如下几个特征:
(1)刍税,已区分为户刍与田刍两种类型。
这是在刍税的类别上不同于秦的第一个变化。
(2)刍税额重于稿税额,刍税之中,户刍又重于田刍。
如平里,刍税总额为三十一石多,而稿税仅二石多;稿上里的刍税与稿税,则为十四石多与八斗多之比。
再以平里的刍税而言,其中户刍为二十七石,田刍仅四石多;稿上里的户刍为十三石,田刍仅一石六斗多。
这都反映出刍税重于稿税,户刍又重于田刍。
此不同于秦制之二。
(3)缴纳刍、稿税时,按里规定了以刍折钱和以刍当稿的完纳方式,刍一石当稿二石,刍税折钱缴纳的数量同应纳刍税的总额成正比。
如平里应纳刍税总额为卅一石三斗七升,其中折钱缴纳者为八斗;稿上里应纳刍税总额为十四石六斗六升,其中折钱缴纳者仅为二斗。
此不同于秦制之三。
(4)从征税对象来说,秦制的“顷入刍三石、稿二石”,明显地都以土地的多少为征税的对象和依据,但汉制,除田刍、田稿是按土地多少征收外,户刍应当是按户征收的,否则无以区别于田刍。
上述出土木牍,据裘锡圭考证,应为西汉景帝初年之物。
从史籍中,也可以看到以刍折成钱缴纳的情况。
《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元年(公元23年)条注引《东观汉记》,载刘秀曾为其季父舂陵侯刘敞“讼逋租”,为此他“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公元20年)十二月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
农民拖欠的舂陵侯家的“逋租”中,除粮食外,还有“刍、稿钱若干万”,可见农民缴纳的地租中,也包括有刍、稿税,而且二者都系以钱折纳。
然则缴纳给官府的刍、稿税,也必然是如此。
田亩附加税:
“亩敛税钱”
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八月,“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这显然是按田亩征收田租、刍、稿等税之外的又一项田亩附加税,只是其税率多少不明而已。
李贤认为这次按亩税钱的附加税是“亩十钱也”,他的根据大约是《后汉书·张让传》所载张让劝灵帝“今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一事。
实则这里讲的,是灵帝增加按亩税钱之制的税率,即增加部分为“亩税十钱”,并不等于说桓帝始创“亩敛税钱”之制是亩税十钱。
以上,田租,刍、稿税,亩敛税钱,都是以私有土地为课税基础的税目。
较之秦的同类税目,明显增加“亩敛税钱”制,而刍、稿税的类别与征收办法变异更多。
口赋
口赋(内含“算赋”、“口钱”)、更赋和献费,都是以人口为课税对象的税目。
口赋,秦已有之,已见前述。
汉继承了秦的这一制度,刘邦于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八月,正式宣布“初为算赋”,即恢复了人口税中课之于成年人的算赋。
这里虽未提到“口钱”征收之制,但据江陵凤凰山汉简,西汉文帝时的人口税征收中,除“算赋”外,还有“口钱”的征收,而从高祖四年到文帝时期,史籍中并无再“为口钱”的记载,因此,知汉高祖四年“初为算赋”之时,很可能同时恢复了口钱与算赋二者。
更值得注意者,整个西汉与东汉的史籍,关于记载口钱与算赋并征者不少,却均无始创“口钱”之制的记载,这也反证“口钱”之制早已存在,且历两汉而无变化。
特别是《汉仪注》谓口钱本为二十钱,“武帝时,加三钱以供车骑马”,足证武帝之前确已有“口钱”之征。
至于口钱、算赋的税率、用途与征税的年龄等,则颇为复杂。
以税率言,据《汉书》注及《后汉书》注引《汉律》、《汉仪注》、《汉旧仪》和《说文解字·贝部》段注引《汉仪注》及王充《论衡·谢短》等,知“口钱”又叫“头钱”,系课之于七岁至十四岁的不服徭役的未成年男女;“算赋”则为课之于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女的人头税。
前者每人每年原纳税二十钱,至武帝时每人每年增加三钱,合计为二十三钱;后者每人每年纳税一算,为钱一百二十文,故曰“算赋”。
关于二者的用途,据《汉书·昭帝纪》注引如淳所引《汉仪注》,口钱二十三钱中,“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也”。
《说文》段注引《汉仪注》与此同。
但《汉旧仪》却载二者都是“以补车骑马”或“以给车骑马”,并无“口钱”、“算赋”在用途上的区分。
按秦制为“头会箕赋,输于少府”,同汉制之以“口钱”中的二十钱“以食天子”或“以供天子”者一致。
故以算赋“补车骑马”,似为汉代的新制。
证以江陵汉简五号木牍所载当利里的赋钱“定算”及分配情况,除以“赋钱”充“吏俸”及上缴外,还有以赋钱“缮兵”的话,可见用赋钱供天子之经费及以补车骑马,都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口钱”征收的年龄规定,《汉仪注》及《汉旧仪》均以七岁至十四岁为征收口钱的年龄标准;但《汉书·贡禹传》却作元帝之前“口钱”以三岁起征,到元帝时因接受贡禹建议,才改为七岁起征。
同一系列史籍所载矛盾,因疑贡禹有误。
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算赋的征收量问题。
在《史记》、《汉书》与《后汉书》中,均无每算为一百二十钱的记载。
算赋的征收既以“算”计,则算赋的多少,实同每“算”定额的多少直接相关。
据《汉书·晁错传》所载“秦之发卒”,“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的话,则“一算”的定额早在秦时就已有之,只是多少不明而已。
到了汉代,据应劭引《汉律》及《汉仪注》,均言每算为一百二十钱,于是人皆从之,并无异议。
然而,据江陵汉简,文帝时市阳里的算赋征收,从二月到六月分十四次进行,每次征收一算的一部分,到六月才征完。
合计十四次所征为二百二十七钱,则这里每算的定额应为二百二十七钱而非一百二十钱。
至于何时才改每算定额为一百二十钱以及为何改为一百二十钱等问题,目前均无法回答。
关于汉代的口钱、算赋的征收办法,据江陵汉简,开始并无固定征收时间,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乃至八月、九月均可征收;每月征收的次数,也无固定,可以每月征二次、三次、四次不等;每次只征收每算定额的一小部分,最少者每次征收每算的八钱,最多为卅五钱,直到每算定额征足为止。
但据文献记载,后来逐渐形成了每年“八月算民”的制度,故居延汉简中称赋钱为“秋赋”;东汉时,甚至有“八月算民”的制度。
故口钱、算赋的固定于每年八月征收之制,可能形成于东汉时期。
至于口钱、算赋的征收机构,据江陵汉简,是以“里”为单位进行,里正是征收口钱、算赋的主持人。
其征收步骤是:
先以里为范围,按口定“算”多少,然后分次征收;征收之后,由里正将每月几次征收的口钱、算赋归总并上缴于所属之乡的乡佐;最后,再由乡佐按照一定的分配比例,把征收口钱、算赋的钱按“给转卖”、给“吏奉”、“缮兵”和“传送”等项用途分成若干份分别上缴或留用。
代役钱:
“更赋”
“更”,早在商鞅变法前的秦国,就是徭役的名称。
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公元前578年),晋伐秦,“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杜注曰:
“不更,秦爵。
”商鞅创立赐爵制,仍有“不更”爵名。
《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曰:
“不更,谓不豫更卒之事。
”可见“更”为徭役之名。
云梦秦简《厩苑律》有考课时获优等的“皂者除一更”的规定,也证明“一更”代表固定的服役时间。
因此之故,秦称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服的一月之役叫“月为更卒”。
于是亲自服“更卒”之役的人叫“卒更”,以钱二千雇人代役叫“践更”。
此外,还有“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之役,“亦名曰更,《律》所谓徭戍也”。
这种更役,不可能人人都亲自去服役,去服役者也不可能完成三日之戍就返回,而是“一岁一更”,即实际上服役者一人代替了许多人的三日戍边之役。
于是,“诸不行者”,便得每人每年“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
因此,如淳所说的“更有三品”的“卒更”、“践更”、“过更”,实为服更卒之役与戍边三日之役的三种方式。
其所以都称为“更”,就在于“更”是当时徭役的代名词。
“更”既为徭役之名,因而用以代替徭役的赋税便叫“更赋”。
故“更赋”即代役钱之意。
但是,从史籍中看,秦无以钱代役之制,故无“过更”之名,也无“更赋”之称。
“过更”与“更赋”的概念,始见于汉代史籍,故知“更赋”为汉代新出现的税名。
“更赋”既为徭役的替代税,那么,是不是所有徭役都可以用钱代替呢?
并非如此。
据如淳的“更有三品”说,只有两种情况可以用钱代役:
一是“一月一更”的更卒之役,凡当服每年一月的更卒之役的人,如不亲往服役,可出“雇更钱”给“次直者”,每月出雇钱二千,这样就算服役者“践更”了。
但是,这种“雇更钱”不叫“更赋”,因为以这种方式雇人代役者并不普遍,官府也没有硬性规定必须人人这样作,故“雇更钱”只是雇者与被雇者之间的自由雇佣关系,而不是法定的制度。
二是戍边三日之役的代役钱,税率为每年每人三百钱。
由于戍边三日之役不能人人皆往,因此,就由国家统一规定缴纳代役钱三百。
所谓“更赋”,就是指这种代役钱而言,它本质上是徭役剥削的货币表现。
由于一旦缴纳了“更赋”,就算服过了每年的戍边三日之役,所以纳“更赋”又叫“过更”,其所纳之钱又叫“过更钱”,欠纳的钱叫“逋更赋”或“逋更钱”。
这种制度第一次见于史籍,在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即《汉书·昭帝纪》所载是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