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作文600字.docx
《小小说作文600字.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小小说作文600字.docx(1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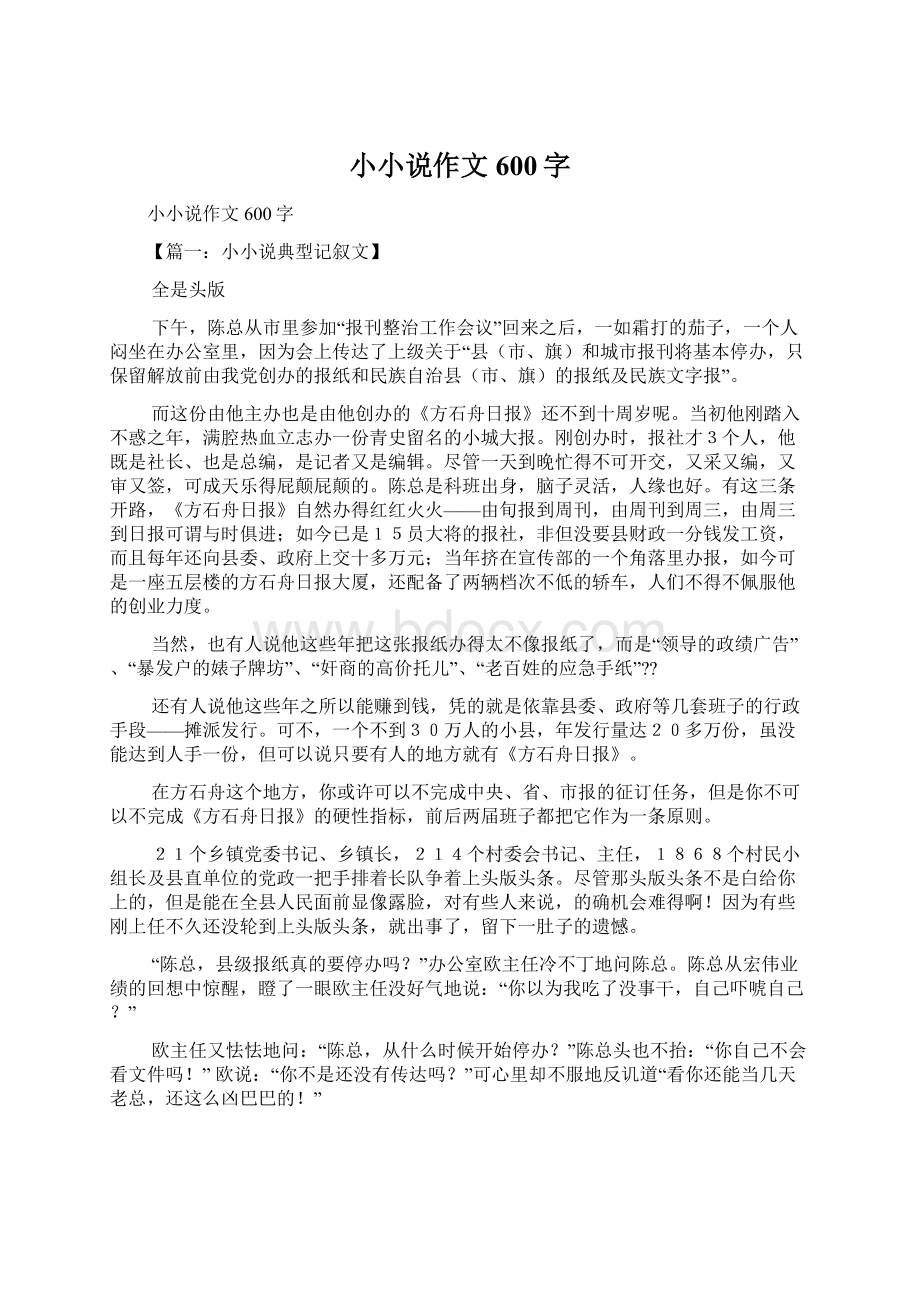
小小说作文600字
小小说作文600字
【篇一:
小小说典型记叙文】
全是头版
下午,陈总从市里参加“报刊整治工作会议”回来之后,一如霜打的茄子,一个人闷坐在办公室里,因为会上传达了上级关于“县(市、旗)和城市报刊将基本停办,只保留解放前由我党创办的报纸和民族自治县(市、旗)的报纸及民族文字报”。
而这份由他主办也是由他创办的《方石舟日报》还不到十周岁呢。
当初他刚踏入不惑之年,满腔热血立志办一份青史留名的小城大报。
刚创办时,报社才3个人,他既是社长、也是总编,是记者又是编辑。
尽管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又采又编,又审又签,可成天乐得屁颠屁颠的。
陈总是科班出身,脑子灵活,人缘也好。
有这三条开路,《方石舟日报》自然办得红红火火——由旬报到周刊,由周刊到周三,由周三到日报可谓与时俱进;如今已是15员大将的报社,非但没要县财政一分钱发工资,而且每年还向县委、政府上交十多万元;当年挤在宣传部的一个角落里办报,如今可是一座五层楼的方石舟日报大厦,还配备了两辆档次不低的轿车,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的创业力度。
当然,也有人说他这些年把这张报纸办得太不像报纸了,而是“领导的政绩广告”、“暴发户的婊子牌坊”、“奸商的高价托儿”、“老百姓的应急手纸”?
?
还有人说他这些年之所以能赚到钱,凭的就是依靠县委、政府等几套班子的行政手段——摊派发行。
可不,一个不到30万人的小县,年发行量达20多万份,虽没能达到人手一份,但可以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方石舟日报》。
在方石舟这个地方,你或许可以不完成中央、省、市报的征订任务,但是你不可以不完成《方石舟日报》的硬性指标,前后两届班子都把它作为一条原则。
21个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214个村委会书记、主任,1868个村民小组长及县直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排着长队争着上头版头条。
尽管那头版头条不是白给你上的,但是能在全县人民面前显像露脸,对有些人来说,的确机会难得啊!
因为有些刚上任不久还没轮到上头版头条,就出事了,留下一肚子的遗憾。
“陈总,县级报纸真的要停办吗?
”办公室欧主任冷不丁地问陈总。
陈总从宏伟业绩的回想中惊醒,瞪了一眼欧主任没好气地说:
“你以为我吃了没事干,自己吓唬自己?
”
欧主任又怯怯地问:
“陈总,从什么时候开始停办?
”陈总头也不抬:
“你自己不会看文件吗!
”欧说:
“你不是还没有传达吗?
”可心里却不服地反讥道“看你还能当几天老总,还这么凶巴巴的!
”
陈总打开公文包把会议材料抖落在桌上,“你看吧,这上面说是这个月底。
”接着又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
“你通知报社所有人员,晚上七点半在五楼会议室开会。
”
大家准时到会,鸦雀无声地听完了陈总的传达,人们各怀心事。
这时,王副总编手拿一摞稿子,似有些幸灾乐祸地说:
“这下好,我们的《方石舟日报》就要‘寿终正寝’了?
?
可是前天陈总去市里开会的时候,二十多个乡镇局领导亲自把这些稿子送来而且都要求上头版头条,实在不行最起码也得上头版。
如今既然咱们这张报要停办了,也就不存在什么头版二版,头条二条了。
我们也省得为按排版面而绞尽脑汁还得罪人。
”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可是,咱们上个月就收了人家各5000元的版面费,这下子还不得退还人家十几万元?
?
”
“根本不需要把钱退还他们!
”办公室欧主任打断王副总编的话接着说:
“我倒有一个主意,统统给他们上最后一个头版。
”王副总编不屑地瞅了欧主任一眼说:
“说得轻巧,二十几个单位,一期头版能摆得下吗?
四版合起来才安排二十几篇呢!
总不能在这最后一期头版上只登二十几个标题吧?
”欧主任胸有成竹地一笑说: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说话间拿起一张《方石舟日报》比划着“把八个版面连在一起,正面正好四版,(但别写一、二、三、四版),每版安排6个单位,正好二十四个头版。
然后取一个总的大标题——“前进中的方石舟”。
反面四个版也做一个版,就索性给它写上“庆祝方石舟日报诞辰十周年”。
然后将21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十年来的成果组成画面错落有致镶嵌其中,或者干脆留下空白。
这样,展开一看就全是头版没有二版。
”一气说完之后,得意地环视一下各位?
?
起初,大伙都默不作声,突然间几乎是异口同声说:
“高!
实在是高!
”
无题
一大早,秀水乡政府办公室就接到一个电话通知:
上午县委组织部要来人,请组织委员将年初下发的中心组学习笔记及有关材料准备好,迎接检查。
组织委员赵大慌了神:
年初组织部开过会,要求各乡镇办班子成员一周搞一次政治学习,并要做详细记录。
为了将这项制度坚持下去,还统一印发了硬塑料封皮的笔记本,每个单位十本。
当时赵大心想,不就那么回事,形式主义罢了。
领回后将本子往办公室一撂,跟书记、乡长一汇报,也就完事了。
没想到上面还动真格的了。
要检查,工作汇报没问题,赵大的嘴上功夫,可是全乡有名的。
只是笔记咋办?
赶制?
六个多月的东西,怎么来得及?
干脆说丢了?
那更不行。
赵委员背着双手,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脑门上沁出了一层亮晶晶的液体。
“赵委,电话!
”声音脆脆的,是办公室守总机的胖妞。
跑到办公室,拿起话筒,赵大脸色变了:
组织部的领导已到了毗邻的横山乡,一个小时后就过来!
“嘭!
嘭!
嘭!
?
?
”赵大几乎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他习惯性地咳嗽了两声,极力想掩饰心里的慌乱。
“赵委,怎么了?
”正在伏案疾书的秘书小王抬起头。
赵大转过头,叹口气,张嘴想说什么,却被一片熟悉的红色吸引住了——小王的办公桌上,摆着个长方形的笔记本。
他走过去,拿起来端详着。
“中心组学习笔记”——绛红色的封皮上,几个金字熠熠发光。
小王站起来,颇有些尴尬地挠着头:
“柜子里的本子?
空搁着怪可惜的,我?
就拿出来做了自考笔记?
?
”
赵大没吭声。
他一页一页地翻阅着:
市场经济概论,现代企业制度?
?
分门别类,排列工整。
倏忽间,一个大胆而独特的念头涌上脑际,他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上午11∶00整,组织部的领导如期而至。
他们对秀水乡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党政班子政治学习笔记给予了高度评价,拿钱部长的话来说,就是:
“赵大同志,你们的基础工作,很扎实嘛!
中心组的学习笔记,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有一定深度,可作为典型在全市推广。
”
半年后,赵大被任命为秀水乡党委书记。
小王亦因记笔记有功,被提拔为组织委员,从此坐上了赵委员的那把交椅。
渴望母爱
我一岁多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有母亲的印象。
我想知道母亲是什么样子的,就问奶奶,奶奶说:
“你母亲长得很漂亮,跟阿香的妈一个样。
”从此,我常常对阿香的妈出神,望着她,就像望着我的妈妈。
我叫阿香的妈做二婶,其实她不是我的亲二婶,只是同村人,大家都习惯叫得亲热一些。
二婶对阿香很好,帮阿香编辫子,扎蝴蝶结,漂亮极了。
我说:
“二婶,你也帮我编辫子,扎蝴蝶结,好吗?
”二婶说:
“我现在没有空,过两天吧。
”我以为二婶过两天真的会帮我编辫子,扎蝴蝶结,就准备好扎蝴蝶结用的花布条,可是两个月过去后,我的头上依然只有一头乱发。
这使我更加羡慕阿香。
我差不多天天到阿香家去玩。
她家院子里有一棵红枣树,红枣还没有熟,阿香就邀我偷红枣吃。
我说:
“我不敢,我怕你妈打。
”阿香说:
“我妈不在家。
”我说:
“你妈不在家我也怕。
”阿香嫌我胆子小,就自己偷红枣。
红枣树上有很多刺,阿香上不去,就用棍子打,正打得起劲,二婶就回来了。
二婶气得破口大骂,揪住阿香,举起巴掌就打。
我想,这回阿香苦了,谁知,二婶的手掌举得高高的,落下来却轻轻的,印在阿香的脸上简直就是抚摸。
阿香丢下竹棍,嘻嘻哈哈地笑着跑了。
那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二婶也像打阿香一样,轻轻地打我。
她的手掌那么软,那么温柔。
第二天,我也像阿香那样,用棍子打她家的红枣树。
打得三四下,二婶就从屋里出来了,她大骂:
“小畜生,你竟敢偷我的红枣!
”我扔掉棍子,站着不动,等二婶来捉我。
二婶抓住我,又高高地举起巴掌。
我闭上眼睛,等待她的巴掌轻轻地印在我的脸上。
可是,我听到“拍”一声脆响,左边脸又辣又痛,嘴里又咸又甜,吐一口到地上,竟是红红的鲜血。
二婶的一巴掌,使我一下子长大了,从此,我再也不做渴望母爱的白日梦
无名母亲
我带母亲去医院看病,要打针,吊四瓶点滴。
打针的人真不少,注射室里几乎座无虚席。
医生插好针头,就叫我和母亲到走廊去。
走廊里贴墙放着两排椅子,我把药瓶挂在高处,让母亲坐在椅子上。
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农村妇女,年近四十,也可能只有二十多岁,因为她的脸黑黑的,皮肤也粗糙,很难估计年龄。
女人不但脸黑,长得也不好看,尤其是嘴巴,牙齿太突,嘴唇太短,即使闭着嘴,也总有两颗牙齿露在外面。
她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白白胖胖的。
这么黑的母亲,竟能生下这么白的孩子,真是奇迹。
孩子最多只有一岁,还没学会说话,但会哭会笑。
这对母子的上面也挂着药瓶,药瓶连着管子,管子连着针头,针头插在小男孩的额角上。
可能是小孩手上的血管不显眼,医生常在小孩的额头上打针。
我和母亲坐下一会儿,小男孩就哇哇直哭,还使劲挣扎。
女人一边用手护着小孩头上的针管,一边把嘴凑近孩子的脸,叽叽咕咕地逗孩子玩。
我正担心她吓着孩子,那孩子却咯咯地笑了,还抬起小胖脚,兴奋地拍打椅子。
也许在这个小孩子的眼里,母亲的叽叽咕咕,就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母亲唇短牙露的嘴脸,就是人间最美的容貌。
小男孩一兴奋,就往母亲的怀里拱。
女人撩起衣服,大大方方地给儿子喂奶。
她喂着孩子喊:
“医生,药水完了。
”一个护士过来,给小孩换一瓶药水,忽然惊叫说:
“不准在这里小便!
”原来小家伙一边吃奶一边撒尿呢。
女人毫不迟疑地一伸手,用手掌接住儿子的尿。
护士把远处的痰盂踢过来,女人接满一手,倒到痰盂里。
快下班时,母亲才滴完一瓶。
我要回家给放学的女儿开门,就把母亲托付给护士,又叮嘱母亲:
“有事你就喊医生,我尽量快点来。
”
等我重新回到医院时,对面那个乡下妇女和她的孩子已经走了。
我问母亲刚才有什么事吗。
母亲说:
“没什么事,就是上了一次厕所。
”我问母亲是怎么上厕所的,母亲说:
“对面那个小孩刚好滴完,那位大姐就一手抱孩子一手帮我提药瓶,陪我去厕所。
”
注射室和走廊里都有许多两手空空的人,没想到关键时候帮助母亲的,却是这位抱着孩子的女人。
我问母亲知道她是哪里人。
母亲说:
“她是长坪人。
”长坪是全县最偏僻的一个乡,在大山里。
我又问:
“她叫什么名字?
”母亲说:
“不知道,她没说。
”
女人坐过的椅子上,有一处湿漉漉的,那是从她的指缝和手掌边沿漏下的儿子的尿液。
别的母亲,也是这样照顾儿女的吧?
可惜我们长大后,很少记得母亲伸手接尿这种感人的动作。
信仰
下午两点半,下着细雨,天阴得有点发冷。
我刚打开办公室的门,他也跟进来了。
我沏了一杯茶,坐定,自顾喝茶,没理他。
他没有像以往一样,毫不客气地在沙发上坐下来,而是局促地站在屋子中间,抖瑟着。
我没叫他坐,他也不坐。
他姓蔡,70多岁了,是上访专业户,我们都叫他蔡老头。
办公室的人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看见他,都乐了,都说,蔡老头,又到北京回来了呀?
见到某某了吗?
某某指的是中央的一个大人物。
他说,回来了。
又给每个人都敬上烟。
抽的是大中华。
老头今天有喜事了?
我不问,其他人也不问,都去忙自己的事,把老头一个人撂在屋中间。
他有话自然会说。
他果然就说了,他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将头抬了起来,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都一齐看着蔡老头。
老头高兴了,自个儿搬了个凳子,坐了下来,猛吸了一口烟,说,解决了,我的问题解决了。
我说,这么说,他们认定你是1940年入党的了?
老头说,不,他们说我是1949年入党的。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几个人差点笑出了眼泪。
只有老头不笑,像看着怪物一样看着我们。
我们也看着怪物一样看着他。
蔡老头真是个怪物。
就为到底是哪一年入党的问题,十几年来,他一直在上访。
本来,不管是1940年还是1949年入党的,他都享受离休待遇。
可是他固执得很,死认定自己是1940年入的党,
十几年里,他跑广州跑北京,几个工资都倒贴进去了。
这一次,他去北京,是去找一个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蔡老头说,是真金,就不怕烈火烧。
我对他说,这么说,蔡老头,这一次你没有找到你那位战友?
不,找到了。
老头说,他也说我是1940年入的党,我确实是1940年入的党。
就是那一年,日本鬼子的炸弹炸伤了我的左腿。
老头说着就卷起他的裤腿,把那一个碗口大的疤指给我们看。
老头的固执劲又来了。
屋子里的几个人又都笑了起来。
按惯例,老头接下来会呈上他那一叠厚厚的材料。
那一叠材料里有上至中央下至村委会的公章,老头每到一个地方申诉,就一定叫人家盖上公章,明明那公章一点也不管用,可老头信它。
那一叠材料里,就有我亲自给他盖上的十九个公章。
我拿出公章来,准备给他盖上第二十个公章。
可这次老头没带材料来,见我们都笑,老头张开的嘴又闭上了。
我说,蔡老头呀,你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呀?
老头搓搓手,说,嘿,我要干什么呀?
突然又说,你们都是党员吧?
办公室里几个年轻小伙子打趣道,蔡老头,党员又有什么用呀?
你还是先弄清自己是哪一年入党的吧。
老头激动起来了,满脸通红,牙齿格格地响。
他大声说,我告诉你,小子,我是1940年入党的,我是老党员了。
入党没用,干啥有用?
你说说,你说说。
泡歌厅、包二奶,这些就有用了吗?
你们这些人,还是共产党员吗?
老头几乎要跳起来了。
他说,我这次去北京,我那位战友死了,他死了,我突然想开了,他干了一辈子革命,死了还将遗体捐献给国家,我还在哪一年入党的问题上争什么,我还算个共产党员吗?
!
老头突然“啪”地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
清脆的一巴掌,像打在办公室每个人的脸上。
大家都不说话,老头脸色发紫,我脱下一件衣服,披在他身上。
我的心里,流着长长的泪。
女儿的婚事
晚饭后,阿茂让老婆拿出早已买下的一沓大红烫金的请柬,伏在饭桌上郑重其事地填写开了。
女儿的婚期定在下月初,该把帖子派发出去了。
第一张帖子写给谁?
阿茂想也没想,提起笔就在“恭请”后面的空白处工工整整地填上了“贾文彬”三个字。
贾文彬是他的顶头上司,几次在关键时刻帮过他的大忙,例如去年公司组团到柬埔寨考察,阿茂由于业务关系不大,险些入不了围,幸亏贾文彬在会议上慷慨陈词、力排众议,才使阿茂好歹出了一次国。
如今女儿结婚,不请此公,还请何人?
考虑到时下有人把请客的帖子戏称为“罚款通知书”,为避免变相罚款之嫌,阿茂决定对单位里的同事只象征性地收受一两块钱礼金,其余的在餐后退回。
好了,现在开始填写第二张了。
第二张又该给谁呢?
这一回阿茂可费了点踌躇。
他?
阿茂脑子里随即出现了一个表情严肃、办事呆板的领导人——新来的秦书记,这位在部队里当过副营长的书记大人很难相处。
记得有一次阿茂擅自将两箱碱性电池低价批给他的一个老同学,便被秦书记毫不留请地克了一顿,把阿茂弄得好不狼狈。
说实在话,阿茂简直有点恨他。
只是手臂拗不过大腿,作为下属就得永远扮笑脸。
如今家里有喜,要是光请经理而置书记大人于不顾,不等于剃他眼眉?
经过反复权衡得失,阿茂终于下了决心:
为搞好上下级关系——请。
第三张该轮到在香港开杂货铺的那位远亲了。
对于这位颇有家财的远亲,阿茂有时候简直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称呼。
他是阿茂老婆表舅父的堂兄,据说也该称他为表舅父。
舅父而表,相互之间又极少交往,本来是请不请也罢。
怎奈老婆今年以来老是吵着出香港去开开眼界,若能趁此次女儿结婚之机巴结上这位亲戚,日后到了香港不就有了一个落脚点?
要知道到了香港最大的开销正是食和宿。
于是,他提起笔信心不大地在请柬上填上“表舅父大人阖家”七个字。
接着,阿茂又一鼓作气地填好了十余张,几乎全是派给他的关系户的,例如证券公司的肥佬刘、建设银行的高佬忠以及工商局的大个王,等等。
随后阿茂便点燃一支烟,美滋滋地吸了一口,忽然就一拍大腿,自言自语道:
“限些忘了徐大姐!
”徐大姐是儿子单位人力资源部的经理,有一次在市里听报告时偶然谈起时才认识的。
阿茂对儿子在单位里当维修工一直耿耿于怀,迟早得拉拉关系把儿子弄
上科室去。
总不能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吧?
于是,他赶紧给徐大姐填了一张。
这时候茶几上的电话“嘀铃铃”地响了起来。
阿茂走过去拿起话筒一听,是乡下的堂弟打来的长途:
“听说月霞侄女要结婚了,到时候别忘了通知我们前来喝两杯哪!
”阿茂听了心想:
究竟是谁向他透露了风声?
八成是月霞那疯丫头!
喝两杯?
凡沾亲带故的都来喝两杯,我岂不要把整座饭店全包了?
阿茂沉思片刻,当即回话:
“……眼下提倡新事新办,月霞的婚事就一切从简了。
摆不摆酒席,还说不准呢!
”
邻居算账
周华去医疗保险所领医保费,共七百多元,他自己只有十来元,其余都是老张的。
医疗保险所不给现金,给支票。
周华拿了支票就搭三轮车去银行取钱,取了钱却忘记自己的是多少了,好像是18元多,又好像是16元多,因为钱太少,他在保险所没有仔细看单子,更没有记到心里去。
周华想,就要16元吧,几毛钱零头算了。
于是他拿出16元,把剩下的都给了老张。
老张和周华在同一个单位,又是对门邻居,他刚刚退休,闲得慌。
第二天下午,周华去上班时,看见老张在门口和门卫说话,周华一到他们就住了声。
周华逗趣说:
“老张,什么好消息不告诉我?
”老张涨红了脸说:
“没什么,没什么。
”周华也不介意。
下班回来,周华看见老张的妻子正在门口和一个女人说话,样子很神秘。
她们背对周华,所以周华走到身边她们也没发现,这样周华就听到了她们的谈话。
老张的妻子说:
“真想不到,医疗费周华都敢贪。
”另一个女人说:
“不会吧?
周华看上去挺不错的。
”老张的妻子说:
“他真的少给我们一块多钱,本来我不想说的,大家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
?
”另一个女人一眼瞥见了周华,就碰碰老张的妻子。
被人说三道四,周华心里很不是滋味,就特意到医疗保险所去查底单,结果发现自己该得的是14元5角,也就是说他少给了老张1元5角。
从医疗保险所回来后,周华立刻到老张家,郑重地把一块五毛钱给他。
老张却死活不要,还生气地说:
“小周,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一块五毛钱也计较!
”周华真想说:
“那就请你和老婆闭上臭嘴。
”可想到和老张是邻居,不能闹得太僵,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家了。
这一块五毛钱成了周华的心病,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把钱还给老张,或者让他夫妻闭上嘴。
妻子说:
“你去银行取钱的时候不是坐过三轮车吗?
车费报销没有?
”周华说:
“两块钱,谁好意思去报销?
”妻子说:
“这就对了,按领钱的比例,这两块钱里,最少有一块九毛以上应该是老张出,他还欠我们的钱呢。
”周华说:
“账是这么算,可怎么好意思跟人家说呀?
”妻子说:
“你不好意思,我好意思。
”妻子真的打电话给老张说:
“周华去银行领钱时花了两块钱车费,请你自己去医疗保险所查一下,看那七百多元里你占多少,周华占多少,然后再算算两块钱车费该怎样分摊。
”她不等老张回话就撂了话筒。
当天晚上,周华就发现自己的信箱里有四毛七分钱。
两家人从此以后像陌生人一样,见面都不打招呼了。
淑女
许昀和主任狠狠地吵了一架,吵过之后,气得趴到桌了上哭了一场,哭得天昏地暗的。
其实,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在我们这些旁观的人看来,芝麻大的一点事,根本没必要吵那一架。
但他们吵了,吵得还挺凶,这就给人一种莫名其妙、多此一举的感觉。
但仔细想想却又觉得完全不必大惊小怪的,各人自有各人的生活习惯,也许是许昀心里的郁闷压抑得久了,需要释放一下,也许是在家里有了什么不痛快,带到单位里来了。
那天一大早,主任从他的小办公室踱出来,慢慢腾腾地进了我们的大办公室,顿着脸走到许昀的办公桌前,把一沓材料不轻不重地搁到许昀的桌子上。
主任说,你把这个材料重新搞一下,最好用心去搞!
这是主任平常交待工作惯用的语言和方式。
许昀就不愿意了,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站得太猛,带倒了后面的椅子。
她说,重搞就重搞,你没必要这样变脸带色的,黑着脸给谁看!
争吵中许昀指出了主任两点错误,一是交还材料的态度不对,不该摔摔打打的;二是主任最后那
【篇二:
感动中学生的100篇小小说】
一、我想听听你唱歌
两年以后,陈处终于来到了羊谷山村。
小车在坑坑洼洼的泥石公路上跑了老半天,才在一个四野看不到人的地方停下来。
天上飘着绵绵不断的毛毛雨。
陈处下了车,踮脚站在泥泞四溢的乡村公路上,张望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了凹隐在山冲里的小村庄。
从公路到村里还有一段山路要走。
陈处一边走,一边向路上遇到的几个农民打听谢小华的家。
呶,就是村里最后头那栋房子。
陈处看清了,那几乎是村里唯一的茅草屋。
整日在城里机关上班的陈处,与羊谷山村挂上钩,与羊谷山村的那栋茅屋挂上钩,或者更直接地说,与茅屋里的女孩儿谢小华挂上钩,这事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上级安排机关干部与偏远山区的贫困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
陈处帮扶的对象就是羊谷山村的谢小华。
名单是由上面统一定的。
陈处按规定每学期开学前给谢小华寄200元钱。
谁料谢小华这女孩儿挺让人上心的。
每隔一月两月,谢小华来一封信,向陈处报告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谢小华在信里说:
尊敬的陈伯伯,这学期期中考试考完了,我考了班上的第三名。
陈处回信:
加油,等你考第一名了,我来看你。
陈处随信给谢小华寄200元,作为奖励。
谢小华又来信了,陈伯伯,我们放寒假了。
村里回来了一个学音乐的大学生,说我有唱歌的天赋,要我买把小提琴,好教我学音乐……
陈处又寄了200元。
陈处在回信里说:
去学吧,下次来时,我想听听你唱歌。
陈处的眼前,甚至很清晰地出现了一个蹦蹦跳跳的、欢快地唱着歌的山村小姑娘。
当谢小华再次来信时,陈处多了一份担心。
因为谢小华在信里说:
陈伯伯,昨天我上山砍柴,肩上被蛇咬了一口,半边脸都肿了。
脸肿得老高,只怕以后唱不成歌了。
陈处又寄了200元,要谢小华拿去治伤。
陈处回信说:
你的脸会好的,以后还可以唱歌的。
下次我来,好好看看你的脸……
两年了,终于来到了这羊谷山村!
谢小华的学习怎么样了?
她脸上的肿早消了吧?
她唱歌唱得好听吗?
这回,一定要好好听听她唱歌!
敲了好一阵门,里面才传出一个妇人的声音。
陈处推门进去。
床上躺着的妇人是谢小华的娘,脸色苍白得像一张薄纸,仿佛一碰就会碰出一个洞来。
陆陆续续来了几个邻居。
陈处左右观望,没有他想见的女孩儿。
谢小华不在家。
通过和她娘以及邻居们的交谈,陈处才知道事情和他想像中的大不一样。
谢小华早就不读书了
在陈处和谢小华结对帮扶才一两个月后,谢小华的父亲一次在山上砍树时被倒下的大树压死了。
那时候,谢小华的娘卧病在床已有几年。
她娘那病,每月要一百多块钱的药来维持。
司机问:
陈处长寄来的钱没给谢小华读书?
陈处说:
都给你买药了是不是?
过了片刻,她娘耷拉着的头点了一下。
司机问:
谢小华没有买小提琴吗﹖陈处说:
她是找借口要钱给你买药是不是?
又过了片刻,她娘耷拉着的头又点了一下。
司机问:
谢小华没有被蛇咬伤过吧﹖
陈处说:
她的脸没有肿是不是﹖
又过了片刻,她娘耷拉着的头又点了一下。
司机显然有点气愤了。
他说:
原来你们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陈处摆摆手,让司机平静下来,也是让自己平静下来。
司机仍然无法平息怒气,司机对转身的陈处说:
陈处,我们走
陈处再次摆摆手,问:
谢小华哪里去了﹖
旁边的邻居说:
她到后山薅草去了,她家一对猪靠她喂的。
陈处出来,抬头望望,往后山方向走去。
刚出村,陈处蓦然看到一百来米远的山坡上,有一个女孩儿坐在一块山石上。
石头高高地从土里长出来,女孩儿坐在上头,安然地唱着歌。
天上的毛毛雨仍在下。
女孩儿的歌声穿透薄薄的雨幕,悠然而至。
陈处循着歌声走去。
100米,80米,50米……
陈处离女孩儿越来越近。
还差二十来米远吧,女孩儿突然站起来,跳下石头,沿着横贯山坡的小道,飞奔而去。
陈处愣愣地望着奔跑着远去的女孩儿,耳里满是女孩儿的歌声。
那是一首名曰《戒指花》的歌,有几句歌词,陈处记得很清楚:
你说你想听听我唱歌
你说你想看看我的脸
我不能唱歌给你听
因为一唱我就要流眼泪
我不能让你看我的脸
因为一看我就要流眼泪
【篇三:
小小说的写作要求】
微型小说的写作
微型小说在写作上追求的目标是四个字:
微、新、密、奇。
一、微。
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