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音论.docx
《介音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介音论.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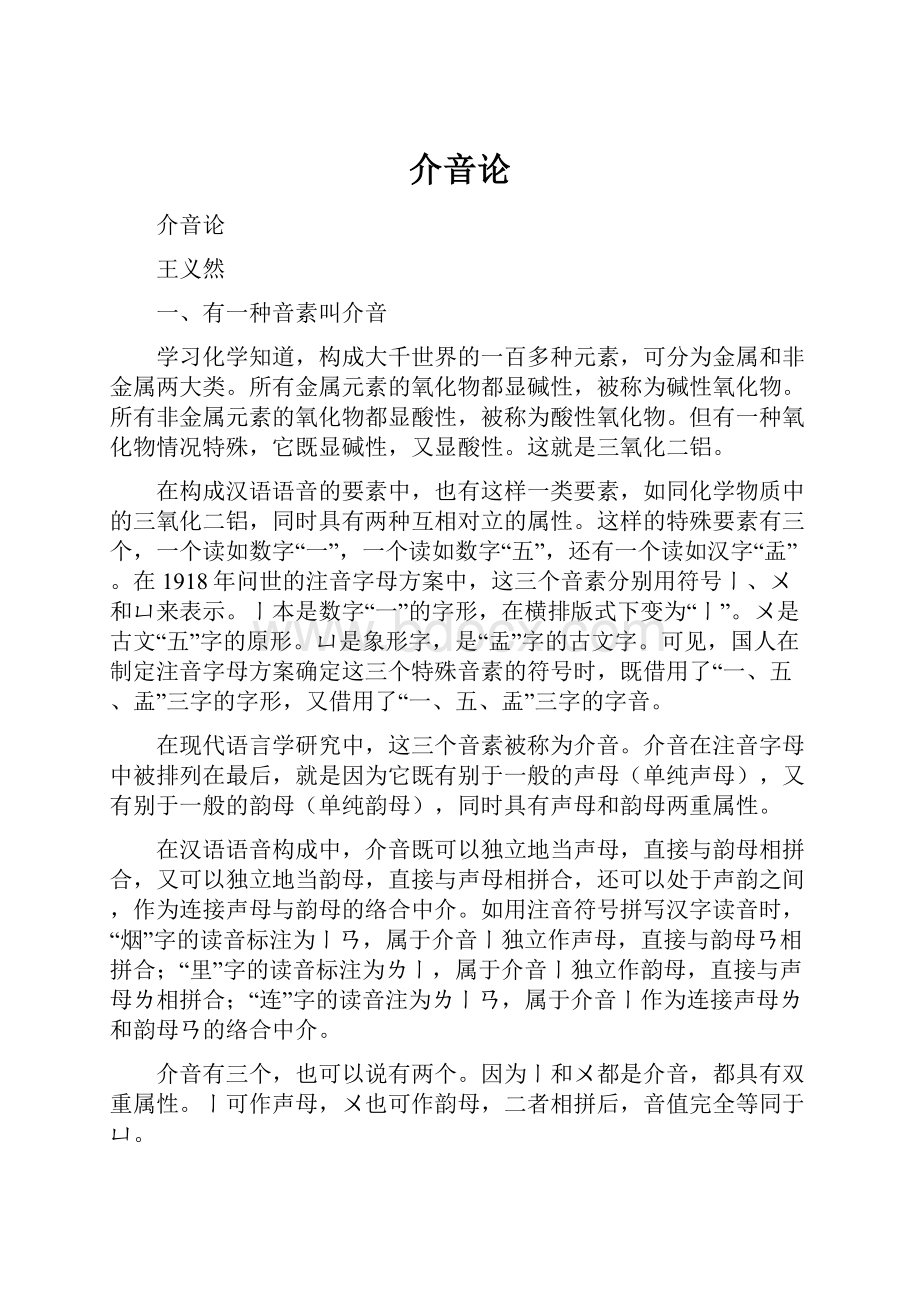
介音论
介音论
王义然
一、有一种音素叫介音
学习化学知道,构成大千世界的一百多种元素,可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两大类。
所有金属元素的氧化物都显碱性,被称为碱性氧化物。
所有非金属元素的氧化物都显酸性,被称为酸性氧化物。
但有一种氧化物情况特殊,它既显碱性,又显酸性。
这就是三氧化二铝。
在构成汉语语音的要素中,也有这样一类要素,如同化学物质中的三氧化二铝,同时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属性。
这样的特殊要素有三个,一个读如数字“一”,一个读如数字“五”,还有一个读如汉字“盂”。
在1918年问世的注音字母方案中,这三个音素分别用符号ㄧ、ㄨ和ㄩ来表示。
ㄧ本是数字“一”的字形,在横排版式下变为“ㄧ”。
ㄨ是古文“五”字的原形。
ㄩ是象形字,是“盂”字的古文字。
可见,国人在制定注音字母方案确定这三个特殊音素的符号时,既借用了“一、五、盂”三字的字形,又借用了“一、五、盂”三字的字音。
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这三个音素被称为介音。
介音在注音字母中被排列在最后,就是因为它既有别于一般的声母(单纯声母),又有别于一般的韵母(单纯韵母),同时具有声母和韵母两重属性。
在汉语语音构成中,介音既可以独立地当声母,直接与韵母相拼合,又可以独立地当韵母,直接与声母相拼合,还可以处于声韵之间,作为连接声母与韵母的络合中介。
如用注音符号拼写汉字读音时,“烟”字的读音标注为ㄧㄢ,属于介音ㄧ独立作声母,直接与韵母ㄢ相拼合;“里”字的读音标注为ㄌㄧ,属于介音ㄧ独立作韵母,直接与声母ㄌ相拼合;“连”字的读音注为ㄌㄧㄢ,属于介音ㄧ作为连接声母ㄌ和韵母ㄢ的络合中介。
介音有三个,也可以说有两个。
因为ㄧ和ㄨ都是介音,都具有双重属性。
ㄧ可作声母,ㄨ也可作韵母,二者相拼后,音值完全等同于ㄩ。
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介音ㄧ、ㄨ、ㄩ被拉丁字母i、u、ü所取代。
根据前面的论述,这里的ü也可用iu来代替。
而根据介音在汉语语音构成中的作用,现代汉语拼音中的i、u可视为介音ㄧ和ㄨ的韵母形式,用于承担ㄧ和ㄨ作韵母和作络合中介的职能;而y和w则可视为介音ㄧ和ㄨ的声母形式,用于承担ㄧ和ㄨ的声母职能。
不难看出,构成汉语音节的要素有三类。
一类是单纯声母,如现代汉语拼音中除j、q、x之外的所有声母,它们只能做声母,不能做韵母;一类是单纯韵母,如现代汉语拼音中的a、o、e、an、en、ang等,它们只能做韵母,不能做声母;还有一类是介音,只有i、u、ü三个,它们既可做声母,又可作韵母,还可作为连接声韵的络合中介,是汉语语音构成中最活跃的音素。
介音的两重属性和三个用途,使汉字读音有了三拼音节,有了无介和含介之分,有了含此介与含彼介之别,有了后来被国人称之为“开、齐、合、撮”的四类划分。
所以,介音牵连着音韵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是澄清传统音韵学领域许多是非得失的关键所在。
正确认识介音的属性和功能,全面分析介音在汉语语音构成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望能引起学界注意。
二、有个问题叫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
自汉代末,国人开始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
反切注音是古人创造的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明读音的方法。
其基本原则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
”即把反切上、下字的读音都分成声、韵两部分,用反切上字的声母与反切下字的韵母相拼合,组成被反切字的读音。
然而,由于介音的存在,使汉字的音节出现了含介的三拼音节。
而反切注音法的规定却是一律用两个反切字为被反切字注音。
这就是说人们在切分或重组字音的时候,所有字音均被视为由两部分构成,因而,只能进行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一次操作。
这样,对一些含介音节来说,在反切注音的实践中,在选择切分字音的分界点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的问题。
例如“边”字的读音为bian。
这个音节包含b、i、an三个音素。
当我们打算把这个音节一分为二的时候,既可以把切分点定在b、i之间,也可以把切分点定在i、an之间。
前一种切分就属于介音从韵,而后一种切分则属于介音从声。
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是在反切注音实际操作中回避不了的的问题。
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无法对从声还是从韵做出统一的规定,具体怎样选择,全凭人们各自临机处断。
正因为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在古今的研究资料中,既有介音一律从声的例子,也有介音一律从韵的例子,还有介音i从声、介音u从韵的例子。
笔者在《浅析三十六字母的缺陷》一文中,通过分析“端”与“定”、“帮”与“并”、“照”与“状”、“禅”与“穿”四组现在看来是同声母的字对,发现其前后读音有共同的差异。
“端”与“定”、“帮”与“并”共同的前后读音差异是:
前者的读音都不含介音i,后者的读音都含有介音i;而“照”与“状”、“禅”与“穿”共同的前后读音差异是:
前者的读音都不含介音u,后者的读音都含有介音u。
据此作出判断,三十六字母中的“并”与“定”是按介音i从声的原则选定的,而“状”和“穿”则是按介音u从声的原则选定的。
选定三十六字母时的介音处置总原则是介音从声。
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用同样方法分析了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的字母表,断定,李汝珍在厘定三十三个声母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
介音i一律从声,而介音u一律从韵。
在《兰茂的早梅诗和李汝珍的字母表》一文中,笔者断定,兰茂在《早梅诗》中厘定二十个声母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
不管介音i还是介音u,都一律从韵。
国人1918年拟定的注音字母方案,从字母的排列顺序看,ㄧ、ㄨ、ㄩ被排列在最后,从注音的实例看,ㄧ、ㄨ、ㄩ既可直接做声母,也可直接做韵母,还可充当三合音节的中介音素。
无疑,注音字母方案所采取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单列。
正因为是介音单列,所以在注音实例中,既适用两拼法,又适用三拼法。
如在教学中“镰”字读音的拼读过程标注为ㄌ→ㄧ→ㄌㄧ→ㄢ→ㄌㄧㄢ,读若“勒一里、里安连”。
这就是典型的三拼法。
195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沿用了注音字母方案的全部声母,废止了拼读过程的三拼法,并为介音i和u拟定了两个担当其声母职能的符号y和w,显然,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一律从韵。
可见,从古到今,人们在音韵学研究中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各不相同的。
而介音处置原则的不同,就是不同学者之间意见分歧的关键所在。
所以,在反切注音规则下,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是音韵学者一直在考虑且一直未取得统一意见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先秦古人知介音
西汉王充(27—约97)在《论衡》中提到一位齐国的东郭牙先生,他能够根据齐桓公的动作表情和说话时“口垂不噞”的口形,断定齐王与管仲所言是伐莒之事。
可见这位后来被管仲举荐为监官的东郭牙对构成“莒”字读音的韵母――介音ü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先秦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可见一斑。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已经认识到在构成汉语语音的要素中有介音这样一类音素。
并且很明白,这类音素既可以直接用作声母,又可以直接用作韵母,还可以置于声韵之间作为连接声韵的络合中介。
当然,古人对介音的这种认识,找不到文字记载。
因为当时诸如声母、韵母、介音之类的现代语言学概念尚无明确的语言称谓,无法纳入文字记载的内容。
因而,这种认识只能存在于当时人们的思维状态之中,形不成能够言传笔记的资料,没有可供世代传承的典籍可考。
但是,古人对于介音这类音素的认识水平却仍然是有据可寻的。
因为据笔者研究,在古人的造字方法体系中有合音造字法和复合造字法。
汉字构成类型除了传统六书之说界定的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假借字、转注字之外,还有合音字和复合汉字。
合音字的构成原理如同反切注音,通过切分重组音节拼合汉字的读音。
复合汉字是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字方法制造一个汉字。
复合汉字一般都有一个用合音法制造的表音偏旁。
既然要切分和合成字音,那就躲不过三拼音节,无法回避对介音的处置问题。
所以,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必然会反映在古人制造合音字和复合汉字的过程中,表现在造字者在切分和重组音节时对介音的处置原则上。
所以,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解读合音字和复合汉字参悟出来。
下面,便是笔者通过剖析一些汉字构成原理,揭示先秦古人对介音认识状况的例子。
1、用介音直接作声母或韵母。
①关于“寅”字构成的解释。
“寅”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穴”、从“一”、从“申”,造字者用“穴”字表达“寅”的字义,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申”字读音的韵母en合成“寅”字的读音yín。
据此笔者断定,“寅”字的本义是地窖,“寅”是“窨”的本字或异体字。
②关于“余”字构成的解释。
“余”字应是一个复合汉字。
其构成应为从“人”、从“一、木”,“人”是形旁,表字义。
“一、木”是声旁,表字音。
造字者用“人”字表达“余”的字义——人之自称,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木”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余”字的读音yú。
③关于“玉”字构成的解释。
据篆文字形“
”,“玉”字应是一个合音字。
其构成应为上从“一”、下从“土”,“一”是声部,“土”是韵部,造字者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土”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玉”字的读音yù。
④关于“立”字构成的解释。
“立”字应是一个合音字。
其构成应为上从“六”、下从“一”,“六”是声部,“一”是韵部,造字者用“六”字读音的声母l和“一”字读音的韵母i合成“立”字的读音lì。
⑤关于“朮”字构成的解释。
“朮”字应是一个复合汉字。
其构成应为从“卜”、从“十、兀”,“卜”是形旁,表字义。
“十、兀”是声旁,表字音。
造字者用“卜”字表达“朮”的字义——卜巫祈祝之类的技能,用“十”字读音的声母sh和“兀”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朮”字的读音shú。
显然,在复合汉字“寅、余”和合音字“玉”的构成中,都是用介音i直接作声母,而在合音字“立”和复合汉字“朮”的构成中,则是用介音i和u直接作韵母。
2、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从声原则。
①关于“量”字构成的解释。
“量”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里”、从“旦”,“里”是声部,“旦”是韵部。
造字者用“里”字的读音li与“旦”字的方言韵母ang合成“量”字的读音liàng。
“旦”字的韵母被视为ang,是受an—ang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旦”如“宕”,形声字中存在的“赣戆、半胖、石宕”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②关于“桓”字构成的解释。
“桓”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木”、从“
”、从“旦”。
“木”是形旁,“
”是声部,“旦”是韵部。
造字者用“木”字表达“桓”的字义,说明“桓”是一种树木,用“
”字读音hūn的声母h、介音u与“旦”字的韵母an合成“桓”字的读音huán。
“
”,《玉篇》注:
古文“昏”字。
这里“桓”字的声旁不是现成已有“亘”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
、旦”二字临时合成。
“
、旦”二字字形合并采用公用笔画“日”,故与“亘”字形偶合。
显然,在合音字“量”和复合汉字“桓”的构成中,“量”字读音的介音i和“桓”字读音的介音u都取自声母,属于介音从声原则。
3、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从韵原则。
①关于“
”字构成的解释。
笔者根据“边”字的一个篆文字形“
”右边由“白、天、囗”三部分组成推定,“
”是古代“边”本字。
“
”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下从“囗”,中从“天”,上从“白”。
“囗”是形旁,表字义,“白、天”是声旁,表字音。
造字者用“囗”字说明围成一定图形的轮廓、周缘谓之“边”,用“白”字读音的声母b和“天”字读音的韵母ian合成“边”字的读音biān。
②关于“黄”字构成的解释。
经仔细观察,认真对照“黄”字的篆体字形“
”和“光”字的篆文异体字形“
”,笔者发现,“
”实际上就是在“
”的中间加入了一个“申”字。
于是悟出:
据“黄、光”篆体字形,“黄”字应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申”、从“光”,“申”是声部,“光”是韵部,造字者用“申”字方言读音(hin)的声母h和“光”字读音的韵母uang合成“黄”字的读音huáng。
可见“黄”字是一个用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
这里“申”字读音的声母被视为h,是受sh—h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申”如“欣”。
形声字仲存在的“术訹、舌絬、晌向、湿显”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显然,在复合汉字“
”和合音字“黄”的构成中,“
”字读音的介音i和“黄”字读音的介音u都取自韵母,属于介音从韵原则。
4、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单取原则。
除了构成类型念的,其构成应为从“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关于“卞”字构成的解释。
“卞”字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卜”、从“一”、从“丶”,造字者用“卜”字读音的声母b、“一”字读音的韵母i和“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卞”字的读音biàn。
②关于“截”字构成的解释。
“截”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属从“隹”、从“十”、从“戈”,“隹”是声部,“十、戈”是韵部。
造字者用“隹”字读音的方言声母z、“十”字读音的韵母i和“戈”字读音的韵母e合成“截”字的读音jié(zié)。
“隹”字读音的声母被视为z,是受zh—z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隹”如“最”(阴平)。
形声字中存在的“捉足、庄赃、乍咋、斩錾”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
③关于“贵”字构成的解释。
“贵”字的构成其实很简单。
据“贵”字的篆文字形“
”和“入”字的篆文字形“
”,“贵”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
”、从“入”、从“贝”,“
”是声部,“入、贝”是韵部,造字者用“
”字读音的声母g、“入”字读音的韵母u和“贝”字读音的韵母ei合成“贵”字的读音gui。
可见“贵”字是一个用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
“
”,《说文解字》徐铉注音,居入切。
读音应为ju(giu),属于现代声母j来源于古声母g的范围。
④关于“短”字构成的解释。
“短”字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豆”、从“午”、从“丶”,“豆”是声部,“午、丶”是韵部,造字者用“豆”字读音的声母d、“午”字读音的韵母u和“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短”字的读音duǎn。
“午、丶”二字字形合并,其形如“矢”。
这是偶然的巧合,笔者称之为汉字构成中的字形偶合问题。
很显然,以上四例在“卞、截、贵、短”四字读音的合成中,介音i和u是作为独立的音素来处置的,属于介音单列原则。
大量事实证明,古人对介音i和u的认识水平是相当惊人的。
在汉字构成中表现出来的介音从声、介音从韵和介音单取三种处置方法并存于世的事实,充分说明,先秦国人不仅已经发现了介音的存在,而且已经能够在制造表音汉字和汉字表音偏旁的实践中,得心应手地处置三拼音节中的介音问题。
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华夏古代文明的骄傲。
四、方言特征中的介音特征
1、介音特征的表现形式和描述方法。
笔者曾反复强调,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只有方言。
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
那么,从语音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应当如何去描述一种方言特征呢?
笔者分析认为,如果撇开声调问题不谈,汉语音节系由声、介、韵三要素构成。
方言语音的音变也理所当然的就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因而,研究方言语音,描述方音特征,就要贴近实际,紧紧围绕这三要素去分析。
以三要素作为区别标志,笔者把方音特征分为三类,即声母特征、韵母特征和介音特征的。
研究发现,介音特征的音变形式与其他两类有明显的不同。
声母特征和韵母特征的音变形式是混读,即把一个声母或韵母读成另一个声母或韵母;而介音特征的音变形式则表现为介音的添加或舍弃。
如在吴方言中有一种“同、洞”不分的方言特征,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声母t混同为d;在南方不少地方有一种“回、徊”不分的方言特征,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开口呼韵母ei混同为ai。
所以描述方言的声母特征和韵母特征,只要把一对相互混同的声母或韵母列示出来就可以了。
介音特征则不然。
如上海话把“江”读若“缸”,把“鞋子”读若“孩子”,很明显,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丢掉了介音i;在扬州方言中把“慢”读若“面”,把“山”读若“仙”,很明显,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添加了介音i。
所以,要描述方言的某个介音特征,就必须说清楚,这个特征的表现形式是添加还是舍弃介音,添加还是舍弃了哪个介音。
2、介音特征的的伴随现象。
在湘方言、赣方言和四川话中,有一种方言特征,把“非”读若“灰”,把“饭”读若“换”。
笔者把这种方言特征称之为f—h混读特征,因为从声母音变角度看,这种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f混同为h。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方言特征在把一个声母混同为另一个声母的同时,还伴随着介音的添加。
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就是在声母f—h混读的同时,韵母也添加了介音u。
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介音特征的伴随现象。
有一种方言特征,把“展”读若“减”,把“陈”读若“琴”,这种方言特征属于zh—g混读声母特征伴随添加介音i的例子。
介音特征的伴随现象,在本文引用的1图“根”摄章和“干”摄章(见附件)都有清晰的表现。
图中在“非、敷、奉、微”四母下,一、二、四等韵都是空白,只有三等韵合口呼排得满满的。
韵图把“分、芬、反、凡”之类的字,都按三等韵合口呼来处理,这就是韵图编纂者f—h混读方言特征伴随介音u添加的典型例子,证明编纂者读“分”如“昏”,读“凡”如“桓”。
无疑,在其心目中,这些字的韵母都含有介音u,所以被视为合口呼。
3、介音特征在注音错误识别中的作用。
笔者发现,在现在通行的字典上,有些字的读音标注是不符合古今汉语语音实际的。
如在各种字典上,“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其读音都用jie、xie两个音节来标注。
笔者认为这种标注与现实语音不符。
这种不符,可以用一种介音添减特征来验证。
如在上海等地,把“世界”读若“四盖”,把“鞋子”读若“孩子”。
这种方言特征的表现形式就是丢掉了介音i。
据此分析,既然“界、鞋”二字的读音丢掉介音i后就与“盖、孩”二字读音相同,韵母变成了ai,那么在介音丢失前,这些字的读音韵母就应是iai。
所以可断定,用jie和xie标注“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的读音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以上判断的正确性,可通过反切注音和有关古今诗词的用韵情况加以证明。
如在《唐韵》中,“介、界、戒”三字的注音均为(古拜切),“解”字的注音为(佳买切)。
其反切下字“拜、买”等字韵母都是ai。
唐代张籍的五律《赠太常王建藤杖笋鞋》,全文是:
“蛮藤剪为杖,楚笋结成鞋。
称与诗人用,堪随礼寺斋。
寻花入幽径,步日下寒阶。
以此持相赠,君应惬素怀。
”诗中“鞋、阶”二字与“斋、怀”押韵,证明所有韵脚读音都含有开口呼韵母ai。
闻一多的诗《死水》中有: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中“界”字与“在”押韵,韵尾也都是ai。
据以上诸多实例,笔者断言,“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的读音,声母古从g、h,韵母就是iai,确凿无疑。
现代字书上这些字的注音属于错误,应当改正,现代汉语拼音韵母表中没有这个韵母,属于遗漏,应当增补。
不难看出,通过方言语音的某些介音特征,判定某些汉字现代注音的错误,是非常有效的。
五、尖音、团音与含介声母j、q、x
在构成汉语语音的音节中,有一类音节被人们称为尖音,如“尖、千、鲜”等字的读音;有一类音节被称为团音,如“坚、牵、掀”等字的读音。
从音节构成要素的角度观察,尖音与团音都有显著标志,很容易区分。
所谓尖音,就是以发音部位属舌尖的z、c、s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所谓团音,就是以发音部位为上腭的g、k、h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
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的字母表里厘定了三十三个声母,其中包括“将、枪、厢”和“姜、羌、香”两组字母。
这两组字母就恰好分别与尖音和团音相对应。
所以,笔者认为,李汝珍之所以要按照介音i一律从声、介音u一律从韵的原则编制字母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区分尖音与团音。
虽然从要素构成上分析,尖音与团音既有鲜明的共性,又有显著的区别,但在现实的文字训诂领域,在注音字母方案和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却存在着尖、团混淆甚至是尖、团颠倒的错误。
关于这类错误的各种表现,笔者在《现代汉语拼音中的j、q、x》一文中有具体例子,不复赘述。
这里只对形成这些错误的根源稍作探究,以期学界重视。
笔者研究认为,注音字母方案的颁布,是造成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起点。
前已论及,注音字母方案是以介音单列为基本原则的。
既然介音单列,在整个方案中,就不能再有含介声母和含介韵母。
但实际情况却是方案中既有含介声母ㄐ、ㄑ、ㄒ,又有含介韵母ㄝ。
这一方案的拟定,说明当时国人对介音的认识还有些混乱,在介音的处置原则上还有违同一律。
ㄐ、ㄑ、ㄒ三个字母,来源于三个古汉字的字形。
ㄐ即古文“纠”字,古声母从g;ㄑ即古文“畎”字,古声母从k;ㄒ即古文“下”字,古声母从h。
从这三个符号的取形来源看,当时所确定的这三个含介声母是仅限于g、k、h与介音i相结合而形成的团音声母。
但从应用实例看,所有以z、c、s为声母的尖音音节也都以ㄐ、ㄑ、ㄒ为声母去标注。
如“精、青、星”三字,其《唐韵》或《广韵》注音分别为子盈切、仓经切和桑经切,声母分别为z、c、s无疑,但注音字母却把它们的读音分别标注为ㄐㄧㄥ、ㄑㄧㄥ、ㄒㄧㄥ。
很显然,ㄐ、ㄑ、ㄒ三个字母的采用,抹杀了舌尖音z、c、s与上腭音g、k、h同介音i相结合之后的区别,把尖音音节和团音音节混为一谈,合二为一。
从而,使语音标注与语音实际相背离。
这就是造成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发端。
195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承袭了注音字母方案的缺陷,使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历史错误进一步固化。
据笔者所知,国人在制定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经过了一场相持不下的关于尖音存废的争论,最后无果而终,只好糊里糊涂,以默认ㄐ、ㄑ、ㄒ的形式,废止了尖音。
在确定j、q、x这三个声母时,只是本着拉丁化的原则,简单地为ㄐ、ㄑ、ㄒ指明了三个对应符号了事。
尖、团混淆的历史错误,一刀割断了古今汉语语音联系,使古今汉字读音标注的对应性遭到严重破坏,为人们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平添了不少障碍。
如“见、贱”二字,其现代注音的声母、韵母、声调都完全相同,但其《唐韵》注音则大相径庭。
“见”字的《唐韵》注音为古甸切,其声母从g,而“贱”字的《唐韵》注音为才线切,其声母从c。
明明声母都是j,却一个变成了g,一个变成了c。
相信绝大多数的汉语使用者都会感到难以理解。
而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中,要讲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恐怕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奏效的。
汉语拼音方案以国家名义颁布,成为华夏大地语音教学的标准,面对尖、团混淆乃至尖、团颠倒的事实,学界哑然,见怪不怪,百姓习以为常,历史错误就这样凝固了。
笔者慨叹,如果当初注音字母方案不设ㄐ、ㄑ、ㄒ,那该有多好!
六、声母、韵母知多少
唐末,人们开始编制等韵图,试图把构成汉语语音的所有音节的声、韵拼合匹配情况反映在一个图表上。
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前已论及,构成汉语音节的要素包括声、介、韵三类,而等韵图只能是一个声、韵相交的二维矩阵图表,因而,所有的汉语音节都只能划分为声、韵两部分。
另外,反切注音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音的基本原则,也要求人们在切分字音的时候,只能一分为二。
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切分含介音节时的分界点做出选择,认真考虑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的问题。
而无论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都会直接影响声母和韵母的多少。
对声母而言,如果介音从声,声母的总数就应包括所有单纯声母和所有含介声母。
如果介音从韵,声母的总数就只包括单纯声母。
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
对韵母而言,也是一样。
所以,人们很难回答构成汉语语音的声母和韵母到底有多少。
在这方面,国人从来也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从来也没有编制出一个介音处置原则统一,声母、韵母界定确切的声母表和韵母表。
在此,笔者对传统的三十六字母、李汝珍的字母表、兰茂的《早梅诗》、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