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与叙史之别.docx
《史鉴与叙史之别.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史鉴与叙史之别.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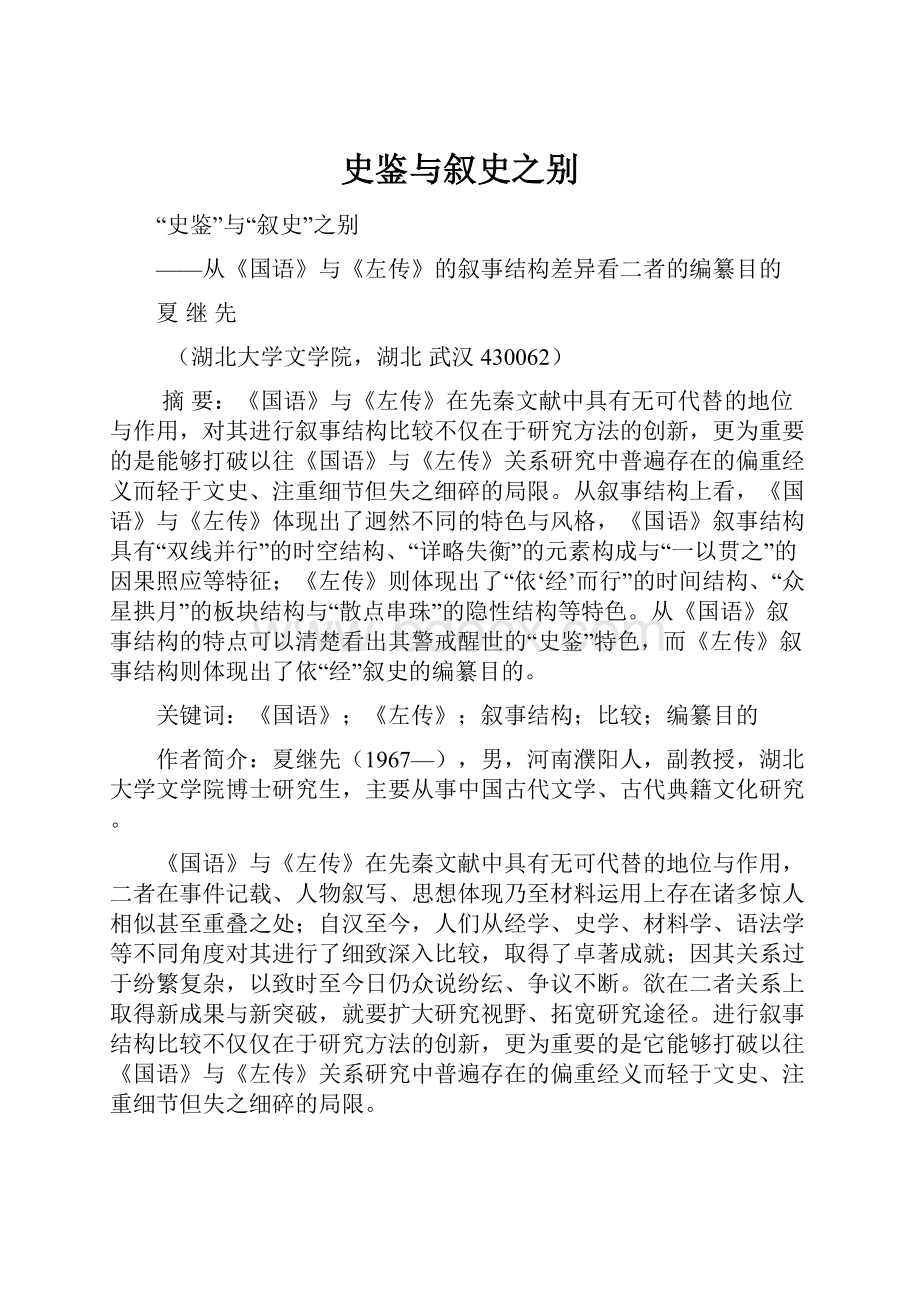
史鉴与叙史之别
“史鉴”与“叙史”之别
——从《国语》与《左传》的叙事结构差异看二者的编纂目的
夏继先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要: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对其进行叙事结构比较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
从叙事结构上看,《国语》与《左传》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与风格,《国语》叙事结构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与“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等特征;《左传》则体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等特色。
从《国语》叙事结构的特点可以清楚看出其警戒醒世的“史鉴”特色,而《左传》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依“经”叙史的编纂目的。
关键词:
《国语》;《左传》;叙事结构;比较;编纂目的
作者简介:
夏继先(1967—),男,河南濮阳人,副教授,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典籍文化研究。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二者在事件记载、人物叙写、思想体现乃至材料运用上存在诸多惊人相似甚至重叠之处;自汉至今,人们从经学、史学、材料学、语法学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细致深入比较,取得了卓著成就;因其关系过于纷繁复杂,以致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争议不断。
欲在二者关系上取得新成果与新突破,就要扩大研究视野、拓宽研究途径。
进行叙事结构比较不仅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
关于《国语》与《左传》叙事方面的研究,虽有万平《<国语>叙事刍论》(《北方论丛》2000年第6期)、李佳《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张新科《<左传>叙事文的艺术结构》(《人文杂志》2005年第3期)、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方铭《<左传>的叙事方式与文体特征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等论文出现,但对于二者进行叙事结构比较的成果还很鲜见。
因此,从叙事结构角度入手,全方位对《国语》《左传》进行比较研究或许会有新的收获。
一、
《国语》向来被人们称为“国别体”,此言固然不错,但仔细分析,它的叙事结构特色绝非“国别体”三字可以概括,复杂多样的叙事特点应是其最大特征;具体而言,“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体现了其宏观结构特色,“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则是其微观结构特点,“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特征彰显了其编写目的。
(一)“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
分析一个作品的叙事结构特色,首要之处在于弄清楚其顺序安排。
杨义说:
“叙事作品的众多片断在素材形态的时候,是东鳞西爪、零散杂乱的。
顺序性要素的介入,于无序中寻找有序,赋予紊乱的片断以位置、层次和意义。
结构之所以为结构,就在于它给人物故事以特定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安排,使各种叙事成分在某种秩序中获得恰如其分的编排配置。
因此顺序性要素,是结构得以成形的要素。
叙事结构顺序之妙,在于它按照对于世界的独特理解,重新安排了现实世界中的时空顺序。
”在杨义看来,叙事作品的素材均是凌乱的,要使其获得恰如其分的编排配置,关键在于给它合适的时间和空间安排;同时,作品的时空顺序安排还体现着作者对于世界的独特理解。
因此,对读者而言,弄清楚作品的顺序安排,不但可以了解作品故事的框架结构,还可以探究作者的思想意图。
《国语》在叙事结构上的最大特点表现为以国别分卷,从叙事角度看,它属于典型空间结构,传统称之为“国别体”;它每一国别内部又按历史顺序编排,呈现出时间演变的特点,我们称之为“时序法”。
以空间结构为骨架的分国结构与以历史进程为顺序的时序叙事,互相补充,互相映衬,表现出了突出的“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特征。
首先,《国语》呈现出分国记事的空间结构特点。
它汇集了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重要的历史资料,以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为单位分国编辑。
《周语》位于《国语》卷首,共有三卷,起于“祭公谏穆王征犬戎”,止于“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
次编为《鲁语》,共两卷,起于“曹刿问战”,止于“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总体风格类似《周语》,重在人物言论。
第三编为《齐语》,只有一卷,起于“管仲对桓公以霸术”,止于“桓公霸诸侯”,均为管仲与齐桓公事叙述霸政意味清晰可见。
第四编为《晋语》,共九卷,起于“武公伐冀止栾共子无死”,止于“晋阳之围”。
第五编为《郑语》,仅一卷两则,分别为“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与“平王之末秦、晋、刘、楚代兴”。
第六编为《楚语》,共两卷,起于“申叔时论传太子之道”,止于“叶公子高论白公胜必乱楚国”,重点记述出国贤相名臣治国言论。
第七编为《吴语》,仅一卷,包括9则材料,起于“越王勾践命诸稽郢行成于吴”,止于“勾践灭吴夫差自杀”,重在记述吴越争霸。
第八编为《越语》,共两卷,起于“勾践灭吴”,止于“范蠡乘轻舟以浮于五湖”,内容与《吴语》大致相同。
其次,《国语》结构的时间顺序十分明了。
刘节说:
“把《国语》里记事的部分都抽出来,可以成编年体著作。
”确实如此,《国语》各编历时情况大致如此:
《周语》记事起于公元前967年,止于公元前510年,历时约500年,包括西周与几乎整个春秋时代。
《鲁语》起于公元前687年,止于公元前483年,大约200时间。
《齐语》起于公元前685年,止于公元前643年,约40年时间。
《晋语》起于公元前709年,止于公元前476年,约200时间。
《郑语》起于公元前774年,止于公元前720年,50年左右时间。
《楚语》起于约前公元613年,止于约公元前591年,大约100余年的时间。
《吴语》起于公元前493年,止于公元前476年,约20年时间。
《越语》起于公元前493年,止于公元前493年,与《吴语》所叙历史时间大致相同。
(二)“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
叙事作品由不同元素共同构成,如谭家健先生认为先秦散文可分五个元素,作者创作思想、目的、爱好、兴趣等的不同往往决定着元素构成比例的不同。
《国语》叙事结构便存在明显不均衡特征,诸如《国语》各“语”之间叙事时间长短不一,叙事过程详略不一,所叙事件关联关系疏密不一等。
从历时范围看,《周语》最长,大约500年,《吴语》、《越语》最短,20年左右;从记事详略看,《周语》记言甚为详尽、叙事过程极为简略,《吴语》、《越语》在注重记言的同时,叙事过程较为详细;从关联关系看,《周语》事件之间关系较为疏远,《吴语》、《越语》记事密切相连。
各种不均衡之间,最为突出的是言、事比例不均衡,“略于记事,重在记言”是最大特色,尽管各“语”之间叙事风格差别巨大,但这种言详事略特点贯穿始终。
具体而言,《周语》、《鲁语》、《齐语》、《楚语》等“重在记言”的特点最为明显。
《周语》主要记载祭公、密康公之母、邵公、中山父、内史过、王孙满、单襄公、单穆公等人言论。
《鲁语》重在记载曹刿、臧文仲、展禽、里革、季文子、叔孙穆子、公父文伯之母、孔子等人的言论。
《齐语》集中写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有关言论。
《楚语》主要记载申叔时、子囊、蔡声子、伍举、左史倚相、观射父、王孙圉等人言论。
《晋语》、《吴语》、《越语》虽然叙事成分明显增强,但言语在其中之地位同样重要。
“重于记言,略于记事”贯穿《国语》全篇,离开了人物言语,不但《周语》、《鲁语》、《楚语》将不复存在,《晋语》、《吴语》、《越语》也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三)“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
罗兰·巴特批评早期的叙事研究者对叙事结构的研究过于简单、肤浅,他说: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
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
在单一的结构中,现于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当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
”罗兰·巴特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叙事模式果真如此简单的话,恐怕它早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类似情况的存在,因为在叙事作品(尤其是早期的)中类似的情形确实不乏其例。
《国语》就具有典型的整体性结构特色,具体而言,《国语》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极为重视,所叙之事“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必有其因”,叙事结构在形式上呈现出典型的因果照应方式,此特点不但在《周语》、《鲁语》、《齐语》、《楚语》表现得淋漓尽致,即使叙事较为详细的《晋语》、《吴语》、《越语》亦概莫例外。
这种因果照应关系在《国语》中存在“显性因果照应”与“隐性因果照应”两种情形。
1、显性因果照应
此类因果照应结构简单、一目了然。
它具体表现为,先简单讲述事实或缘起,进而引出评论对象,接下来往往是长篇大论式的劝谏或分析,最后说明结果。
由于因果关系极为分明、显而易见,我们称之为“显性因果照应”。
在侧重人物言语记述的《周语》、《鲁语》、《齐语》、《楚语》与《晋语五》至《晋语九》中,此类情形尤为经典。
以《周语》为例,它记载了自周穆王至周敬王时期约500年的历史事件。
在所记33则事件中,叙事模式几乎完全相同——首先介绍事情起因,起因往往源于天子、国君或其他人做出了不符合礼义德行之事;然后有人认识到此举危害,于是进行进谏;最后展示事情结果,当事者听从了谏言便会逢凶化吉、趋利避害,但绝大多数情况是当事者固执己见,或自取灭亡、或贻害后代
2、隐性因果照应
除简单明了的显性因果照应外,《国语》还有一种因果照应情形较为复杂,表面上难以发现其照应关系,只有从全局角度出发,才能发现作者叙述之根本目的在于探讨事情原委,揭示成败根源;由于这种因果关系隐含在叙事之中,需要拨云见日,我们称之为“隐性因果照应”。
此类“隐性因果照应”在记事成分突出的《晋语一》至《晋语四》、《吴语》、《越语》之中表现最为经典。
它们以叙事为主,甚至其中不乏精彩绝伦之描述,以至于人们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其叙事过程、叙事方式与文学表现上,从而忽视了编纂者记录这些材料的真实意图。
以占据《国语》篇幅最重的《晋语》为例:
《晋语》由九编组成,从叙事特点上看可分为两部分,《晋语五》至《晋语九》结构近于《周语》、《鲁语》与《楚语》,显性因果照应特色明显;《晋语一》至《晋语四》风格与《吴语》、《越语》类似,行文细致委婉,情节曲折,人物形象塑造丰满,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以至于王世贞赞其为“极组织之功,鼓陶铸之巧,学者稍稍掇拾,其芬艳犹足以文藻群流,黼黻当代,信文章之巨丽也。
”单单从文学鉴赏的角度看,如此评论可谓中肯不虚,如《晋语一》至《晋语四》较为完整的记载了晋国从献公伐骊戎、骊姬之乱、惠公即位、重耳逃亡至文公称霸一系列重大事件,再现了晋国这一时期历史面目,可谓“组织之功”;形象刻画了荒淫无道、一意孤行的晋献公,背信弃义、肆无忌惮的晋惠公,历经磨难、终成大器的晋文公,阴险狡诈、心地歹毒的骊姬等形象,不可不谓“鼓陶铸之功”。
《晋语》具有很高的文学技巧无可置疑,但是,隐藏其后的因果关系才是编者最终目的所在;即使在精彩绝伦、令人称道的记述中,因果关系之表述目的与《周语》、《鲁语》也毫无差异。
如“寺人勃鞮求见”一事,此段记载先运用补叙交代十九年前事情原委,接着详细叙述君臣二人的对话,最后交代事情结果,结构完整;同时,在叙述之中,对人物言行、心理又有详细刻画,重耳最初的怨恨与后来的宽容、寺人勃鞮的毫不畏惧与慷慨陈词跃然纸上。
其实,本段文字不但具有如此令人赞叹的艺术表现力,同样蕴含着强烈的因果关系——晋文公之所以能有惊无险、转危为安,是晋文公深明大义、摒弃前嫌,接纳了自己从前的仇敌并听从了他忠贞规劝的结果。
《吴语》、《越语》同样如此。
从叙述事件看,二语主要记录了吴越争霸的历史面貌,且不乏精彩绝伦的人物刻画、情节安排与场面描写;人物如伍子胥的忠贞耿直、文种的足智多谋、范蠡的虑事周全、夫差的刚愎自用等无不活灵活现,情节上《越语》记载勾践复仇之事步步推进、环环相连,《吴语》记载此段历史更是环节全备、背景宏阔,至于《吴语》记载吴晋争霸的“黄池之会”对吴国战阵的场面描写更是令人称道。
此类叙述与描写有其必要性,而隐藏于其后的叙述目的则更为重要,仔细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吴语》、《越语》叙事之中体现着与《晋语》相同目的,这就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同为时代雄主,同样拥有智慧超群的贤臣智囊;夫差呼风唤雨、叱咤一时却落得兵败自尽的下场,是因为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不能听从伍子胥的逆耳忠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勾践忍辱含垢、卧薪尝胆终于灭亡吴国、成就霸业,是顺从文种、范蠡劝诫的结果。
二
《左传》的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与《国语》迥异的风格特色,具体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三大特色。
(一)“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
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
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他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对一条直线上。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乱象纷纷,“春秋百国”事绪纷乱,如何将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有条不紊的给予记录,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人们阅读《左传》并没有凌乱纷纭之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者使用了“线性时间”结构,正如王靖宇所言:
“就时间的流动来说,《左传》情节的性质是线性的,书中按年代顺序从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63年,即通称为春秋时期的主要政治、社会、军事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传》把春秋200多年的历史视为一个不间断的发展过程,通过编年方式将众多重大、复杂的矛盾组织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中,从而使《左传》在纵的方面呈现出一种开放延伸的线性结构;从具体事件记录情况看,虽然有倒叙、插叙、补叙、预叙等不同情况存在,但在总体上,它们丝毫不影响这种线性时间结构特色。
究其渊源,《春秋》是依照时间顺序进行记事的编年体体例的开创者,《左传》这种线性的时间结构特色无疑借鉴于《春秋》。
《春秋》以鲁国的隐、桓、庄、闵、僖、文、宣、成、昭、襄、定、哀十二代国君为序,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共记242年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
《左传》同样以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昭、襄、定、哀十二君为序,记事亦起于隐公元年;略微不同的是,在记事范围上比《春秋》多出13年(终于哀公二十七年),从宏观结构上看,《左传》对《春秋》编年体例的继承显而易见。
《左传》不但从宏观时间框架上与《春秋》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微观时间序列上也采用了《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表述方式。
(二)“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
《左传》采用以时间为纲纽的叙事基本结构,并不意味着春秋200多年的每一历史事件都严格按照这一顺序安排,“众星拱月”式板块结构是它叙事结构的又一突出特色。
所谓“众星拱月”式板块结构是指《左传》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时,打破原有的时间顺序,采用倒叙、插叙等等手法,紧紧围绕中心事件或核心人物组织、安排材料,以达到突出中心的目的。
这种“众星拱月”板块结构又分为以人为中心的“人物版块”与以事为中心“事件板块”两种情形。
1、人物版块
春秋时期是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旧有的国家制度、思想体系在走向衰落、崩坏,新的体系尚未建立,郭沫若将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总结为“一切都在变”。
何新文先生说:
“(这一时期)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价值和作用的被认识,是最显著、最引人瞩目的。
”《左传》作者以机敏的目光,捕捉到了时代的变革,认识到了人的价值,因此,它极力突出人的作用与影响;这不但表现在对管仲、子产的高度赞扬与对齐桓晋文之事的高度肯定;也表现在其叙事结构上。
具体而言,作者在叙述历史之时时,往往以关键人物为中心,将与之相关的因素放在一起,以突出人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即使记述涉及范围特别广泛,无法集中一处者,也往往分为几个相对集中的片段叙录之。
郑庄公、晋文公、子产等等莫不如此。
郑庄公是一个在春秋历史上影响巨大的国君,他凭借自己深邃的思想、超人的才智,“相机而动,量力而行”,开创了春秋一个新的时代,被后世称为“小霸”;同时,又由于郑庄公冒犯天子,做出了“周郑交质”、“射王中肩”等这些在当时及后来儒家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而备受人们贬讥。
对于如此复杂而重要的人物,《左传》开篇第一年便集中笔墨叙述了历史上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此段叙述涉及范围广泛、事情复杂、人物众多:
前后跨度达20余年;事情经过涉及郑国两代君臣以及国君家庭内部纷繁复杂的矛盾;关涉郑武公、姜氏、郑庄公、公叔段、祭仲、公子吕、颖考叔等诸多人物,行文之中,每个人物即使寥寥数语也都跃然纸上,如郑武公的秉正守礼与坚持原则、姜氏的自私狭隘与狠毒偏心、公叔段的肆无忌惮与愚昧无知、郑庄公的深谋远虑与爱恨情仇、祭仲的远见卓识与忠心不二、公子吕的简单直率与粗鲁无礼、颖考叔的忠孝两全与巧于谋划等等。
重大事件、复杂矛盾、众多人物,简直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是,略加梳理,我们便可清楚看到,作者在叙述事件经过时,始终围绕一个目标——郑庄公。
郑庄公是整个事件的中心与枢纽,其他一切因素均与之相关。
就事件而言,其母“爱共叔段,欲立之。
亟请于武公”与“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有关,以下发生的姜氏“请制”、“请京”……颖考叔“有献于公”等皆与郑庄公相关;就人物而言,祭仲、公子吕、颖考叔甚至姜氏、公叔段等莫不是郑庄公的陪衬。
事件的进程叙述与人物的展现,无不围绕郑庄公进行,“众星捧月”式的板块结构在此处彰显无遗。
晋文公重耳与贤相子产等人是《左传》极力肯定与赞扬的对象,他们涉及的事件更多、时间更长、情形更复杂,限于编年体的时间限制,对于此类人物记载不能集于一处,作者便尽可能地将其言行集中于若干片段之内。
以晋文公重耳为例,重耳从避难出逃到霸业已就,前后历经24年。
在《左传》中,作者不是将其事迹分散于24年进行记载,而是集中于僖公四年、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四年、僖公二十七年、僖公二十八年这五个年份记载,在这五个年份中又以僖公二十三年为最详,集重耳逃亡十九年的经历于其中。
统而观之,以重耳为中心枢纽安排材料的特色显而易见。
2、事件板块
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牵涉到众多细小事件与人物,以大事为中心而从小事入手揭示重大事件的产生原因、发展趋势及最后结果,是高明的记史之作的惯用手法,《左传》的特别之处在于尤其重视细小因素的作用,它常常将这些细小事件集中在一起,通过诸多细小事件的纵横交织去揭示重大主题。
如僖公二十八年的“城濮之战”,围绕晋楚主战双方记录了晋军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侵曹伐卫,“卫侯出居襄牛”,“曹人尸诸城上”,晋人“舍于墓”,退避三舍,晋人离间曹、卫与楚之关系……事件;甚至纪录了战争过程中许多细节,诸如魏犨“距跃三百,曲踊三百”的举动,“舆人之诵”的插曲,“胥臣蒙马以虎皮”的战术等等。
这些事件是城濮之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揭示了晋文公取威定霸的内在根源。
围绕重大事件进行人物叙写是《左传》“众星拱月”的又一突出特点。
李梦奎说:
“(《左传》)作者在记叙一次战役时,常常描写较多参战者的活动,而不是集中笔墨刻画主要人物。
在这方面,它与《史记》有着明显区别。
……而《左传》写战争时,往往顾及到战争全过程和各方参战者的活动,把处于战争发展各阶段的人物依次写来,以多触点的人物塑造勾勒出战争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刻画人物时呈现出开放式特点。
”李梦奎点出了《左传》战争描写中人物刻画的“开放式特点”,“顾及到战争全过程和各方参战者的活动,把处于战争发展各阶段的人物依次写来”形象道出了《左传》叙事结构的“众星拱月”特色。
以“鞌之战”为例,《左传》在描述这场战争时,涉及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如对于狂傲轻敌、目中无人的齐顷公,作者刻画只用了“齐侯曰:
‘余姑剪灭此而朝食!
’,不介马而驰之。
”寥寥数字,人物形象便表现的入木三分。
当然,通过这些人物言行揭示战争成败根源才是作者主要目的——实力强大的齐军为何会被中衰的晋军击溃?
齐国军队不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也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甚至到了“不介马而驰之”的狂傲程度,焉有不败之理?
而这里表现出的围绕事件组织人物言行的板块特征毫不令人怀疑。
(三)“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
叙事作品的结构,最要处往往体现作品之隐义,因为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与理解。
太史公说: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表十,本纪十二,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处虽然谈的是《史记》体例、结构及创作意图,但是通过“略考其事,综其终始”以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之写法不惟《史记》所特有,《左传》之中已见端倪。
“散点串珠”的隐形结构是《左传》叙事一个重要的结构特色,也是体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的典型例证。
所谓“散点串珠”的隐形结构就是,《左传》叙事之时按时间顺序记述了一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零碎事件,粗略看来,这只是简单的事件实录;但是,只有当我们将相关的事件放在一起,才可以看出其中的关联,才可以理解作者的意图所在。
吕祖谦说:
“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
”吕祖谦告诉我们,阅读《左传》要前后关联,从整体上把握其实质,可谓切中肯綮,因为在某个片段之内就事论事,往往会导致因一叶之见而断章取义。
梁启超说得更为清楚,他说:
“左氏之书,其片段的叙事,虽亦不少,然对于重大问题,复溯原竞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亦解。
”这里“复溯原竞委,前后照应”几个字非常精辟地概括出《左传》叙事的隐形结构特色。
张竹坡评《金瓶梅》时说:
“凡一人一事,其用笔必不肯随时突出,处处草蛇灰线,处处你遮我映,无一直笔、呆笔,无一笔不作数十笔用。
粗心人安知之。
”此评论用于《左传》叙事亦无不可,《左传》记载中,许多形影相吊的只言片语,看似无关轻重、可有可无,但它们往往是一颗颗看似凌乱的珍珠被一条无形的线贯穿,只有从整体上分析,才能看出其价值与奥妙。
《左传》对楚国的记载便是经典例证,楚国第一次在《左传》中出现是在桓公二年,文中仅仅用了11个字——“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
”四年之后,从楚武王侵随开始,才对楚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高士奇称这一段楚国历史为“楚伐灭小国”,其后称为“楚令尹代政”。
只有将这些有关资料集中在一起,才能清楚看出一个不被中原诸侯重视的“蛮夷”小国是如何走向强大的。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真理解桓公二年的这只言片语的妙处:
“惧楚”二字道出了楚国的强大;“始”字含义尤深,说明在此之前人们不把楚国放在眼里,到了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之时,看到了楚国已经在悄无声息中快速崛起,即使当时纵横中原、被后世称作“春秋小霸”的郑庄公也心生怯意,我们就不难理解楚庄王称霸的历史积淀因素了。
再如僖公二年有一条记载:
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
粗略看来,此记载孤单、生硬,使人不知其然。
但是,将其与后文统照,《左传》叙事之妙就清晰可见了:
僖公二年,齐桓公霸业虽正处极盛之时,但已暗伏危机,齐国内部竟然出现了透露情报的内奸;十五年之后,齐桓公霸业盛极而衰,寺人貂再次出现,他与易牙勾结,在齐桓公死后,残杀群吏,终酿成齐国宫廷内乱。
“寺人貂漏师于多鱼”这一孤单事件与十五年后的齐国内乱就这样串联了起来。
《左传》记事如此,写人亦然。
如对秦穆公的记述分散在从僖公九年至文公六年的二十一年中,我们只有将其零碎记录综合在一起,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秦穆公形象。
具体而言,僖公十三年至十五年《左传》着重突出了秦穆公从善而择、仁德宽厚的形象,如晋国发生饥荒,“乞籴于秦”时,秦穆公充分听取不同意见,最终“输粟于晋”,规模之大甚至达到“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的程度。
接着,秦国发生灾荒,晋国却拒绝援助,而在晋国再次发生灾荒时,秦穆公仍然慷慨大度赠送粮食,这里虽不乏战略目的,但秦穆公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