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学生应该学习怎样的中国历史.docx
《张元学生应该学习怎样的中国历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张元学生应该学习怎样的中国历史.docx(2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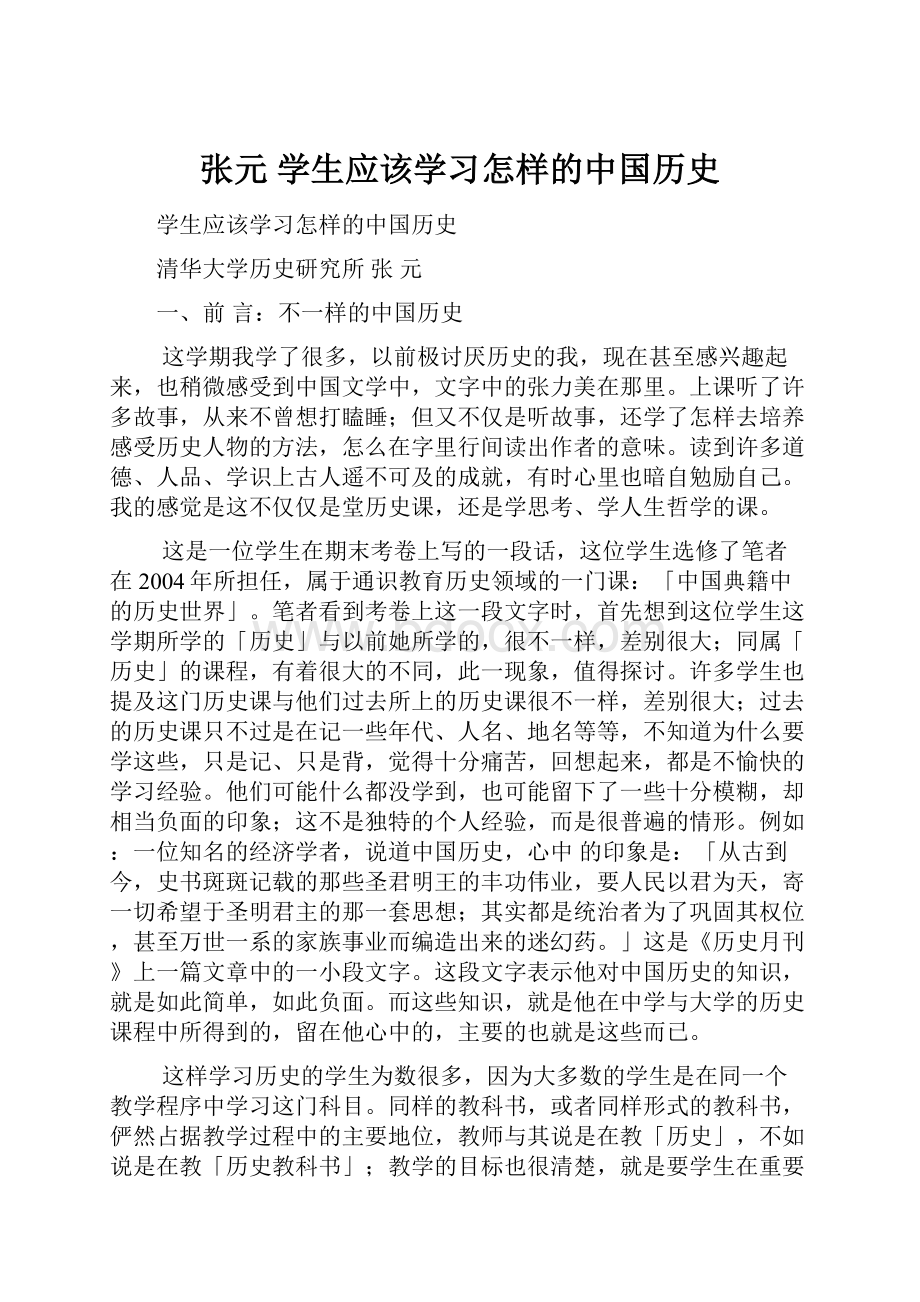
张元学生应该学习怎样的中国历史
学生应该学习怎样的中国历史
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元
一、前言:
不一样的中国历史
这学期我学了很多,以前极讨厌历史的我,现在甚至感兴趣起来,也稍微感受到中国文学中,文字中的张力美在那里。
上课听了许多故事,从来不曾想打瞌睡;但又不仅是听故事,还学了怎样去培养感受历史人物的方法,怎么在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意味。
读到许多道德、人品、学识上古人遥不可及的成就,有时心里也暗自勉励自己。
我的感觉是这不仅仅是堂历史课,还是学思考、学人生哲学的课。
这是一位学生在期末考卷上写的一段话,这位学生选修了笔者在2004年所担任,属于通识教育历史领域的一门课:
「中国典籍中的历史世界」。
笔者看到考卷上这一段文字时,首先想到这位学生这学期所学的「历史」与以前她所学的,很不一样,差别很大;同属「历史」的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此一现象,值得探讨。
许多学生也提及这门历史课与他们过去所上的历史课很不一样,差别很大;过去的历史课只不过是在记一些年代、人名、地名等等,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只是记、只是背,觉得十分痛苦,回想起来,都是不愉快的学习经验。
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学到,也可能留下了一些十分模糊,却相当负面的印象;这不是独特的个人经验,而是很普遍的情形。
例如:
一位知名的经济学者,说道中国历史,心中的印象是:
「从古到今,史书斑斑记载的那些圣君明王的丰功伟业,要人民以君为天,寄一切希望于圣明君主的那一套思想;其实都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权位,甚至万世一系的家族事业而编造出来的迷幻药。
」这是《历史月刊》上一篇文章中的一小段文字。
这段文字表示他对中国历史的知识,就是如此简单,如此负面。
而这些知识,就是他在中学与大学的历史课程中所得到的,留在他心中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些而已。
这样学习历史的学生为数很多,因为大多数的学生是在同一个教学程序中学习这门科目。
同样的教科书,或者同样形式的教科书,俨然占据教学过程中的主要地位,教师与其说是在教「历史」,不如说是在教「历史教科书」;教学的目标也很清楚,就是要学生在重要的考试中,如各级的升学考试,取得高分,顺利进入理想的学校。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教师为考试而教,学生为考试而学,其方法只有一项,就是死记硬背教科书中的文字,因此,在学生的心目中,历史只是一门「背诵的科目」,简称「背科」。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优秀的历史老师,一直努力把历史教得既让学生喜爱,又让学生感到真有收获,只是这样的老师有多少呢?
为数似乎不多。
优秀老师的精彩教学,其他老师知道吗?
似乎知道的也不多。
在这样的以升学为导向的教学环境中,举目所见,无非升学参考书,考试测验卷等,便于学生死记硬背的工具;相对而言,提供教师正常教学的各种教学理论,以及课堂教学中实用的资料、教案,也就十分有限。
所以,一位历史老师要成为深受学生喜爱与怀念的老师,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需要抵抗的压力也很大。
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历史老师在艰困的环境中坚持理想,努力不懈,可以说是台湾教育界最宝贵的资产。
中国大陆的情形,笔者所知有限,就一点亲身的经验看来,情况甚为类似。
三年前的一个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几个人走进了著名的江苏省扬州中学,见到教室大楼灯火通明,但却鸦雀无声,趋前一看,每一个学生的桌上摆满了各科的书科书,这幅景象,对我而言,只能用「怵目惊心」来形容。
大概也在同一年,东吴大学举办一场关于文献学的研讨会,来了几位大陆这方面的专家。
其中有一场的研讨主题是历史教学,主持人请大陆的学者谈谈对历史教学的看法,其中有一位学者说,我们对进到系里的学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把中学所学的历史都忘掉,不然很不好教。
许多人听了,都觉得十分新奇,甚至感到不可思议。
最近读到大陆历史教学的著名学者写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相似的看法。
这位学者写道:
「前些年,就有些教师反映,刚进大学的高分学生『左』的可爱,要帮他『洗脑子』。
还有学生大骂中学历史教育是骗人的。
这样的情况现在是少了呢?
还是更多?
这些学生是幸运的,他们进了大学,还有机会『洗脑子』,那么大量的没有进大学的学生又如何了呢?
只要我们负责任的『灵魂工程师』,就应当把它当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看一看,想一想。
」
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的历史教育长期以来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影响,所以有「左得可爱」之说。
今天,随着马克思思想唯物史观的退潮,历史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今年(2006年)9月3日,台湾的《中国时报》上有一篇有关上海历史科新教材的报导,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新版历史教材作者之一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春生指出,新教材借鉴法国历史家布劳岱尔的观念:
应当用一种包容文化、宗教、习俗、经济和思想的『总体性历史』的新方法来解析历史,新教材目的是强调领导人和战争的传统中解救历史教学,让人民和社会成为新的重点课题。
」我读了这段报导,感到马克思唯物史观退位了,布劳岱的年鉴学派史观取而代之;苏联的影响退去了,欧美的影响立即补了进来。
我想要问的只是:
中国的历史教育一定要有一个西方的理论来做为指导思想吗?
台湾的情形如何?
台湾继承民国初年以降的历史教育,难道就未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吗?
值得我们好好地反思一下。
二、强调讲述历史事实,有其背景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的民族,各个时代都有杰出的历史家以及精彩的历史著作,这些丰厚的史学著述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所在。
但这一史学传统到了近代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史学的挑战,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出现了所谓的「现代史学」。
现代史学怎样从传统史学中演绎、变化、发展出来,至今仍与传统史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中,「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个部分,也是至今仍然需要学者仔细研究的一项课题,不是我的这篇小文所能讨论,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处理。
我们不妨略述学界的一般观点,作为讨论的背景。
如果我们说,中国大陆以外,台湾的中国史研究是继承着民国以来,「科学史学」为主的这股潮流继续前进,大概不会遭到太多的反对。
「科学史学」指何而言?
最早可以追溯到「新史学」的呼唤者梁启超,在这场史学革命中,梁启超无疑是首揭批判传统史学大纛的旗手,而他就是以「历史科学」或「科学的历史」为主要观念,致使「新史学」的主流始终环绕着「科学化」的观念。
接着有重大影响者,应推胡适,胡适一再强调「实验主义」,同时提倡「科学方法」。
他的一些话,直到今天,人们仍能琅琅上口。
如:
「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话。
」以及「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不跟着感情走。
」至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句名言,更是无人不知。
但对于台湾史学影响来说,大概没有人超过傅斯年。
而傅斯年的史学理念明白见于所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在这篇重要的文献中,傅斯年明白表示,「史料中可以得到最大量的客观知识,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
」以及「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
」而「史学本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同样也是傅氏的名言。
傅斯年尽管未再强调「科学」二字,但其精神仍然是偏重于这一方面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在经济上接受美国援助的浥注,思想文化上向美国学习也成了时代的潮流与趋势,史学自不例外。
于是,向社会科学学习,成了研究历史的重要取向;社会科学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传统典籍只不过是供人驱使的一堆材料而已。
这样的观念,似乎仍然瀰漫在台湾的历史学界,只不过「社会科学」的具体内容有了一点改变而已。
历史研究的观念与态度,必然对历史教学产生重大影响,然而,这种观念与态度不可能直接反映在历史课堂教学上,而是经过一个「简化」的过程。
例如,昔日强调的科学与方法,不可能用于课堂教学,于是科学与方法的结论就成了它的化身,老师教、学生学这些结论,就好像学到了科学与方法。
昔日重视的史料与证据,同样不可能用于课堂教学,于是藉由史料与证据得出来的事实就成了它的化身,老师教、学生学这些事实,就好像可以取代了史料与证据。
所以,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历史课堂所呈现的,就是对于「事实」的讲述与记忆。
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老师自然认为,教好历史就是讲很多的「事实」,补充许多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事实」;历史老师犯的最大过失,就是把「事实」讲「错」了。
其结果,历史课就成了一门「背科」,一门学生学习之时不觉丝毫乐趣,学完之后回想起来十分厌烦的课程。
历史研究的方法,无法完全用于课堂教学,这一点无人置疑。
但历史教学只是老师只是讲述事实吗?
等而上之,把学者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学生,也都只教「现成的知识」,这样就可以了吗?
学生学习「历史」这门课程,连一点历史知识的性质、结构和方法都不涉及,就能够达到「强化学生思考与分析能力」的教学目标吗?
教历史要教历史知识的性质、结构和方法,这个观念并不复杂,何以长期以来未能落实于课堂教学?
历史学的研究态度与观念,特别是对于「事实」的强调,是否造成一定的影响,致使历史老师认为只讲事实,就符合历史学的研究,就等于教了历史知识的性质、结构与方法?
更进一步,强调历史知识就是「事实」的知识,是否成了历史老师探究历史知识的性质、结构和方法时难以超越的障碍?
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学生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小学、中学的历史课只需讲述「历史事实」,学生只需记得重大的事件,杰出的人物,主要的制度和大概的学说;至于对历史知识性质的了解,结构的掌握和方法的练习,那是大学历史系,甚至是历史研究所学生的学习对象。
这种说法十分普遍,我不知道是否受到上述「科学」的历史学,追求「事实」的影响,但它确实是老师讲历史不谈知识结构、方法的重要理由。
这个理由可以成立吗?
笔者不认为中学阶段不适宜讲述历史知识的结构与方法。
西方学者研究得知,历史知识的最基本工作,如利用原始材料,作为证据,讨论问题,在小学阶段即可实施,而且可以取得一定成果。
笔者自已虽然没有在中、小学担任历史课程的机会,但在大学的一些通识课程中,可以了解学生在前一阶段的学习情况。
笔者可以清楚感到,学生对于着重历史知识结构与方法的教学,十分陌生,却甚感兴趣,同时也觉得很有收获。
2006年,笔者在清华大学开了一门讲述近代史学大师钱穆的课:
「钱穆与中国传统史学」,原先当作人文社会学系历史学程的进阶课程,但全校各系、各年级学生都来选修,其性质已从一门「历史系」的专业课程,转变成为「历史领域」的通识的课程。
一位化工系一年级的学生,在期中考的试卷上写道:
「读钱先生的作品,那种严谨的思辨过程,循序渐进,铺陈事件的历程有条不紊,思绪清晰,对于历史资料的搜集的精细,熟读牢记,更进一步可揣想当时情境、对话、心态。
在我的看法中(不知是否恰当),传统史学就像一本理性中不失感性的厚书,既是逻辑严密,却又自然而然于字里行间透露着感情。
中国数千年来,先人的智慧、思想,如同大浪侵袭而来。
(过去对于历史的理解似乎停留在老师所说的『历史资料』层面,总是在了解过去的教训与事实,徒有什么鉴往开来的空洞思想。
)」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学生把一年级下学期所上的历史课与过去的历史课作了对比,过去的只是一些资料,一些事实,却要从中得到什么教训,自然感到相当空洞。
但这一门历史课,所看到的是历史家的工作,包括精细的搜集资料、严谨的思辨过程、有条不紊的铺陈事件、揣想当时情境心态,这样的历史,既有严密逻辑的理性,又有字里行间的感情,于是,古人的智慧、思想就如同大浪袭来。
笔者认为「如同大浪袭来」不失为一个很漂亮的形容,相信也是一种很真切的感受;学生上历史课,老师能够引导的极致,不也就是如此吗?
值得一提的是,与这位学生相同的看法,一样的感受,占了班上的大多数。
所以,笔者在检讨这门课的教学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讲述历史知识的组成结构、研究方法,不但不会过于艰深枯燥,反而会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比起只教历史上的表面现象,或只讲述一些历史学者的论点,也就是一些『现成』的知识,讲结构与方法,更会受到学生的欢迎。
我相信,不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喜欢,所有的大学生都喜欢;不只是大学生喜欢,中学生也会喜欢。
」
三、试拟传统史学的理论结构
如果,我们要问,人类的历史知识中,有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结构和方法?
我们应该首先要问,所谓的「结构和方法」指何而言?
如果只是在最基本的层次,就是谈及「历史知识」,必须想到:
问题、资料、分析、论证,以及最后回答问题、加以表述等,如同MaryFulbrook在HistoricalTheory一书中所说历史的「典范」(paradigm)中的第一层次(A.theoretical,internalorimplicitparadigms),我想,这应该是古、今、中、外,无有不同的。
举例来说,宋代大学者朱熹(1130-1200),认为关于井田被废的既有解释,无论从资料的解读,史事的理解,意义的阐释等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撰有〈开阡陌辨〉一文,对于井田之废,详加述论。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举凡今天史学家无不重视、强调的治史要项,诸如:
提出有意义的问题、选取重要资料、进行严谨论证、结合历史情景、运用历史想象等,朱熹此文无不具备,而且十分细腻精审,至于说明事物情理以及阐述历史意义,虽然不为今天历史学者所赞同,却也突显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色。
我们可以说,八百年前的中国学者,探讨历史问题,其严谨、细密、深刻,较诸受到西方影响下的中国现代史学,可以说是毫不逊色,完全符合历史知识结构和方法的基本要求。
基本上结构和方法上的相同,并不表示中国传统史学的「结构」和「方法」和今天所见深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现代史学完全一样。
如果,我们再问:
中国传统史学的结构与方法,有何特点?
我们固然可以在一些专精传统学术的近代学者的著作中,见到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但总觉得欠缺较为完整,便于现代人们阅读或认识的论述。
阐述传统史学的理论结构,这项工作原非笔者所能胜任,由于不把传统史学的结构和方法大致描绘出来,做为历史教学上选取资料、解读文本,以及理解过去的依据,则此一议题难以为续,故而只有抛砖引玉,略作尝试。
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惟有敬请方家多予指正。
传统上,对过去的理解来自典籍。
如何读懂典籍呢?
最初步的工作就是认识其中的字与词,这是最初步的工作,也是真确地认识过去的第一步。
于是,我们看到重要的历史典籍都有相当详尽的「注释」,其中大部分就是对于字和词的解释。
当然,史书的注释,其形式多来自经书的注释,但不要忘了,所谓「经书」,在大多数古人观念里也是一种「历史典籍」。
例如:
在朱熹观念里,《易经》与《诗经》都是「历史典籍」,都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重要依据,《尚书》、《春秋》、《周礼》更是如此。
所以,《史记》有三家注,《汉书》有颜师古注,《后汉书》有李贤注,《三国志》有裴松之注。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其中《三国志》注较特殊,字、词的解释不多,而其他三史的注释,字、词的解说俨然成为主要部分。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史书的注释不只是一个字或词的解说,不是前人做过后人就不再做的工作;这是一种前后相继的传统,后人对前贤的解释有所不满,就提出新解,新的解释不但更有理据,而且更为深入。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略作说明。
汉武帝天汉2年,公元前99年,李陵孤军进击匈奴,匈奴单于调动八万骑兵对付李陵,双方激战。
《资治通鉴》卷21,记有其中一个片段,曰:
「陵军步鬪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胡三省的注释,重点在「连弩」一词,是这样写的:
「服虔曰:
三十弩共一弦也。
张晏曰:
三十絭共一臂也。
贡父曰:
皆无此理。
盖如今之合蝉,或并两弩共一弦之类。
余据《魏氏春秋》,诸葛亮损益连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今之划车弩,梯弩亦损益连弩而为之,虽不能三十臂共一弦,亦十数臂共一弦。
」
我们看到,颜师古引用了服虔和张晏的注,刘攽(贡父)不同意,提出新的解说;但胡三省也不同意刘攽的意见,再提出一个解说。
刘攽是北宋时人,也是《资治通鉴》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本人专精史学,与其兄刘敞、侄刘奉世,有汉史「三刘」之称。
刘攽不赞同前人解释的理由是「无此理」,因为他想不通一弦如何可以射出三十支矢,他认为射出两支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胡三省又怎么看呢?
胡三省从资料之中,以及实际事物中,找出证据,认为三十支矢共一弦确实不大可能,但十支矢共一弦,应有其可能。
我们可以看到,史书上一个「词」的解说,愈到后代愈为精细,而且理由更为充足,既是史学注释上的明显发展,也是历史知识的思考更加细致深入。
我们读懂了资料中的文字和词汇,就可以相信这些资料了吗?
也就是说,古代留下的资料,可以不加甄别地采信、利用吗?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号称「圣人」的著作,其真实性如何,到了宋代也不免遭到质疑,皮锡瑞在其所着《经学历史》一书中,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特加说明。
其实,对于资料的考信,最晚可以追溯到司马迁所说: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这里特别提到宋代,主要鉴于宋代在史籍资料考信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出现了《通鉴考异》这样一部精细辨别资料可信与否,如何解释的专著,徐炳昶称之为「全世界最早批评史料的一部大书」,指出其特点,说明其意义。
到了清代,乾嘉学者对于典籍校刊、版本整理、史事考证、名物训诂等用力甚勤,成就可观。
王鸣盛说他的著作是:
「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
」虽为王氏自述之言,庶几可以反映学者的努力与其取得之成果。
这是传统史学另一着重之处。
若问:
传统中国史学家选取资料,加以组织、安排、表述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可以说,那是以「人」为主的叙事方式,「人」的表现最受重视,相比之下,人所做的「事」,则是第二义了。
我们可以从传统史学著作的体裁中明确看到,主要的史书属于「纪传」与「编年」二体,但编年体的史书,其内容与重点基本上与纪传体无异。
也就是说,按时间序列编写的史书,其中所陈述者,仍是一个个人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与纪传体无大差别。
此外,就是像《通典》、《文献通考》,属于的「政书」类史书,其中许许多多的人们意见,仍是构成此类著作的重要成分,「人」依旧扮演重要角色。
于是,我们在史书中读到的,几乎都是一个人的出身,幼年时的独特表现,进入官场或社会后的所做所为,对时政或时代的批评和意见,以及,当时人们对他的评论与观感等等。
就像钱穆所说:
「历史记载人事,人不同,斯事不同。
人为主,事为副,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于其事者。
」今天看来,这样的史学观点显然偏颇,有久全面,但这也说明了传统中国史学的特色所在。
也许,此一颇具特色的「观点」,似可符合MaryFulbrook所说的「典范」中的第二层次(B.contextualorperspectivalparadigms)
由于传统史书的记载以人为主,而其表述方式则以摘录这位人物的资料,加以编排、组织而成,其目的无非是要将这位人物最直接、最具体的呈现出来。
除了「曰」、「论」、「赞」、「议」、「评」和「按」等明确表示是著者意见看法,其他皆从资料中选录、撷取、安排,铺陈一篇完整的叙事。
这种让资料说话,撰者在叙事过程中,尽量以资料为主,只是扮演辅助的角色。
这种表述方式,沿袭已久,直到今天,我们心目中的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和钱穆,其史学论著,无不保有此一形式与精神。
最后,我们要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
培养学生理性地理解过去的能力,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能力,或许是今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
这样的答案当然不错,甚至很好,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问:
学生有了历史思维「能力」,又是为了什么?
如果只是增强学生对「过去」的「认知」,只是强调「知识」的「能力」,而不能用于实际的生活,不能有助于实际事务的处理,不能有益于人的一生,这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知识态度,或许可以得到今天学者的称赞,但与主张「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显然大相迳庭。
关于历史有其致用的目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句话,讲得很清楚。
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
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着,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王夫之的意思是史的目的或功用,在于作为今人的典范或诫鉴;而能否有此功效,则端看史书是否具备「经世之大略」,也就是历史中人们如何面对问题,如何处理事情的情况。
如果史书中具备了这样的内容,读者得以掌握「得失之枢机」,也就是懂得了成败的道理,这样的历史才是有其效用的。
不然,写得再多,也属徒然。
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知道,「得失之枢机」只是道理而不是技巧,有其深义在焉。
朱熹对学生讲历史,十分强调从历史中只能学到人世间的「道理」,学不到任何做事的「技巧」或「计谋」。
从历史中学习前人的谋略、技巧,依样画葫芦,是做不成事的,是不对的。
因为人世间的道理,是历史知识中的「人文价值」,也是学习者应该认真理解的「基本观念」。
这些人世事务中的道理,甚至可以与自然界相呼应,应是我们立身行事的依据。
再举王夫之的话,作为此一理念的例证。
王夫之谈到三国人物时,非常推崇管宁,他说:
「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管)宁持之也。
」理由呢?
管宁在辽东讲授诗书,提倡礼仪,就是为天下存道统,为君子续学统,不因动乱而文明无以为继。
王夫之说:
「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
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
」就是进一步探究人世的道理,把人的作为,与人的心意,以及自然万物的理据(天地之心),综而论之,得出的一个十分深刻的看法,以褒扬管宁。
现代学者如何谈论此一观念?
深于传统史学者,仍然坚持此一理念与目标,并依之撰述。
例如,王国维轰动一时的大文章〈殷周制度论〉,主要立论在于: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立制之本,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回非后世帝王所能梦想也。
」又说:
「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其立论之依据仍在圣人之心术,此今人久已不弹之旧调。
柳诒征在其阐明传统史学大义的名著《国史要义》中,也多有论述。
例如,他说:
「吾国圣哲深于史学,故以立德为一切基本。
必明于此,然后知吾国历代史家所以重视心术端正之故。
若社会上下道德荡然,且无先哲垂训,诏以特立独行,绝不能产生心术端正之史家。
」又说:
「谓史之义出于天,读者亦且茫昧而不解。
是又可以董子之言解之。
《春秋繁露.玉杯》篇曰: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癯而不可得革也。
』是故史之为书,所以善善恶恶也。
善善恶恶者,人之性受命于天者也。
吾国之为史者,其浅深高下固亦不齐,而由经典相传,以善善恶恶之性从事于史,则一也。
」全书最后,柳诒征是这样写道:
「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
其由简而繁,由繁而简,固少数圣哲所创垂,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
此史迁所以必极之于究天人之际也。
《大学》曰: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进道矣。
』又曰: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吾之人本主义,即王氏所谓合全国为一道德之团体者。
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
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
所愿与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
」在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象是「吾国圣哲」、「先哲垂训」、「心术端正」、「受命于天」、「道德之团体」等现代史学非但不谈,甚且避之唯恐不及的词汇与观念,既可以说明传统史学与今天我们史学观念相去之遥远,也可以作为传统史学有其独特个性的明证。
至于柳氏最后所言,「通万方之略,弘尽性之功」,终究不失为一极崇高之理想与极伟大之抱负,即使不能使人心向往之,也应足以让人赞叹不已。
人之本性秉于天,乃传统史学最为基本之观念,因之可以说学术大原出于天,学术发展之目的,无非促使人人发挥本性。
此一理念之下,期勉人人的所做所为,一言一行,皆合于义理,使社会成为一道德之团体。
而史学之目的也不外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贵意义,加以呈现;人世间的理想社会,加以实现。
这固然是一个十分「主观」的观点,我们今天非但不能接受,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