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质与功用.docx
《文学的本质与功用.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的本质与功用.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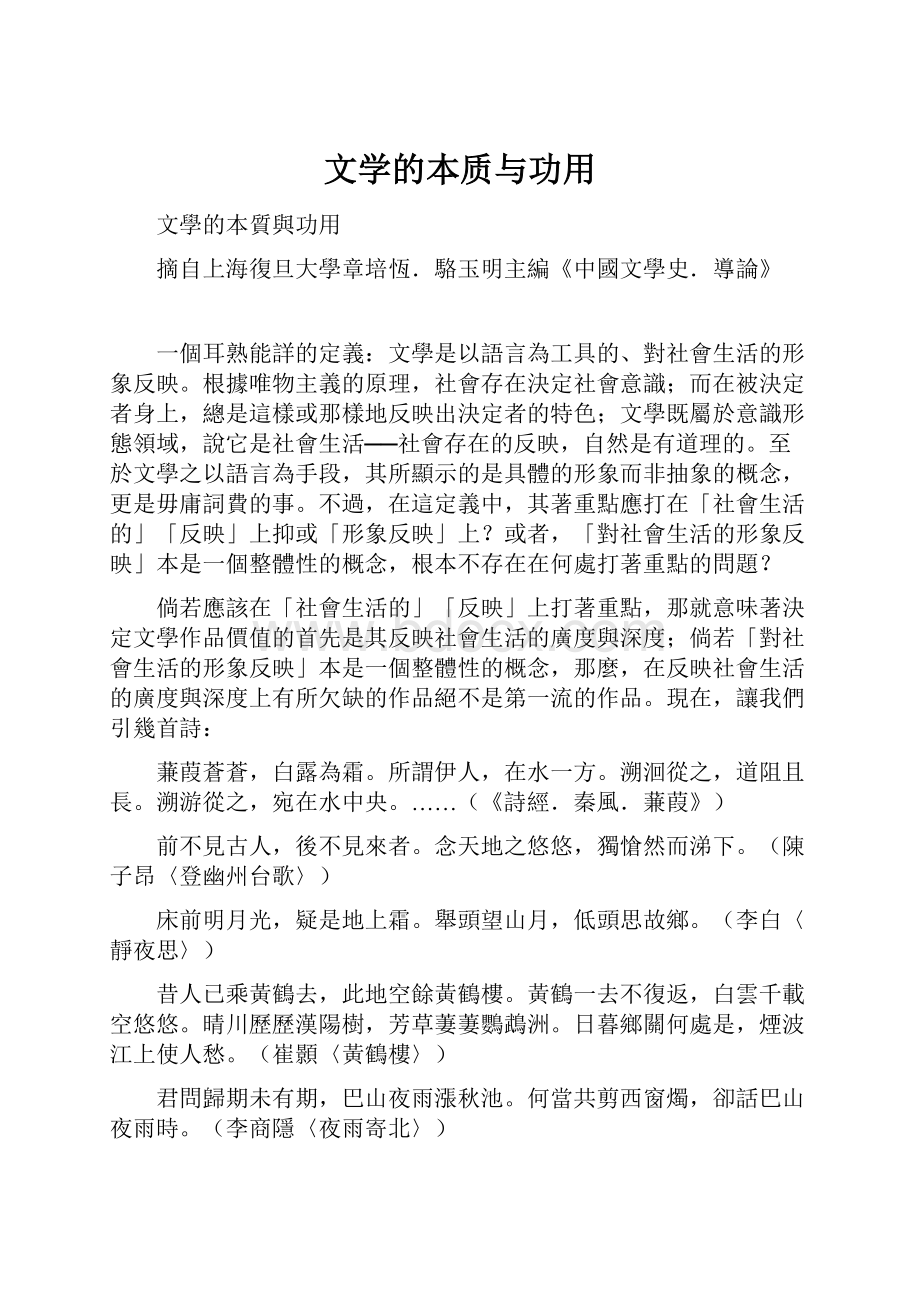
文学的本质与功用
文學的本質與功用
摘自上海復旦大學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導論》
一個耳熟能詳的定義:
文學是以語言為工具的、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
根據唯物主義的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在被決定者身上,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反映出決定者的特色;文學既屬於意識形態領域,說它是社會生活──社會存在的反映,自然是有道理的。
至於文學之以語言為手段,其所顯示的是具體的形象而非抽象的概念,更是毋庸詞費的事。
不過,在這定義中,其著重點應打在「社會生活的」「反映」上抑或「形象反映」上?
或者,「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本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在何處打著重點的問題?
倘若應該在「社會生活的」「反映」上打著重點,那就意味著決定文學作品價值的首先是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倘若「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本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那麼,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上有所欠缺的作品絕不是第一流的作品。
現在,讓我們引幾首詩: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從之,道阻且長。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詩經.秦風.蒹葭》)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陳子昂〈登幽州台歌〉)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
(李白〈靜夜思〉)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崔顥〈黃鶴樓〉)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李商隱〈夜雨寄北〉)
這些都是千古傳誦的名篇。
但若就其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加以考察,實算不上有突出成就。
以李白的那首來說,所寫是十分單純的遊子思鄉之情。
如果我們要從中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至多只能知道當時有些人旅居異鄉,並對故鄉頗為懷戀。
至於這些旅居異鄉者的具體生活,詩中卻毫無反映。
比較起來,早在李白之前的樂府詩〈艷歌行〉、〈悲歌〉寫遊子的生活和感情反而具體得多。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
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
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
賴得賢主人,攬取為吾綻。
夫婿從門來,斜柯西北眄。
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
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
(〈艷歌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思念故鄉,鬱鬱累累。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
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悲歌〉)
前一首寫遊子生活的艱辛。
衣破無人補,欲製新衣也無人縫,幸而其所寄住之家的女主人頗富同情心,代為操作,卻不料引起了男主人的猜疑,因而最終發出了「遠行不如歸」的慨歎。
後一首則寫遊子親屬死絕,無家可歸,心中痛苦萬分。
以反映社會生活而論,這兩首都比李白〈靜夜思〉具體、豐富,但就讀者的評價之高及傳誦之廣而論,它們卻遠不如後者。
例如,明代頗有識見的胡應麟在《詩藪.內編》卷六中就推許李白〈靜夜思〉為「妙絕古今」,唐詩選本收入此詩的很多;〈艷歌行〉及〈悲歌〉則不但從未受過這樣高的評價,被收入選本的次數也不多。
這都可見〈靜夜思〉對讀者的吸引力大於其他兩首。
即使〈靜夜思〉的形象性強於另外兩首,但如上述關於文學的定義中「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佔有首要地位,那麼,〈艷歌行〉及〈悲歌〉的總體成就縱或不在〈靜夜思〉之上,也應與之並駕齊驅,為什麼這兩首詩受讀者歡迎的程度還不如〈靜夜思〉呢?
類似的情況在文學史上並不鮮見。
試再以崔顥〈黃鶴樓〉與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為例。
崔詩已見上引,李白的詩如下: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相傳崔詩先作,李白此詩有與之較高低的意思,《苕溪漁隱叢話》、《唐詩紀事》等都有類似說法。
孤立地來看,李詩固很動人;若與崔詩比較,那麼,就算上引傳說可靠,崔詩由於先作而更顯示出創造力,但李白在此一佳作的籠罩下,能夠另闢蹊徑,雖有貌似之處,精神上卻頗相乖異,其功力之高也極驚人。
且李詩的最後兩句,是用陸賈《新語.慎微篇》:
「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明也。
」間接揭示出讒佞當道、朝政混濁。
像這樣的反映社會生活的內容,顯為崔詩所無。
若以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來衡量,李詩自當在崔詩之上。
但從歷來的有關詩評中卻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嚴羽的《滄浪詩話》並明確地說:
「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
」
這些都說明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並不是決定一篇作品高下的主要尺度。
甚至在像小說這樣的文學體裁中,也並不例外。
試將《三國志通俗演義》與《西遊記》比較一下看。
《三國志通俗演義》當然是反映三國時期社會生活的作品,至於《西遊記》,則正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說,乃是神魔小說。
雖然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主義原理,作家的意識及其作品是被社會存在所決定的,因而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反映了社會生活,並且正如魯迅所說:
「《西遊記》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惚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說.中〉)但其獲得讀者激賞的,究在「構思之幻」(《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
除極少數研究者外,廣大讀者也從不根據《西遊記》去認識或觀察當時的社會生活;而且,即使是研究者,主要也只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生活去解釋《西遊記》的某些內容。
若就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與深度來說,《西遊記》自然不如《三國志通俗演義》。
但二者在中國小說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它們在反映社會生活方面的差異並沒有成為判定其高下的標尺。
既然如此,那麼,關於文學的上述定義中的「形象」二字是否更為關鍵,從而可以成為決定文學作品優劣的標準呢?
不過,「形象」如果是指人物形象,則許多詩裡根本沒有人物形象;更多的是寫了詩人的某種感情。
以上引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來說,就是如此。
首兩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其登上幽州台時的感受。
由於獨立在廣漠原野的高台上,四望無人,他覺得茫茫天地、古往今來,只有「我」才是真實的存在,這使他感到孤獨而自豪。
洋溢在「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這兩句中的,並不是孤立無援的恐懼,而是睥睨世俗的氣概。
然而,這個如此自豪的「我」,跟天地的永恆一比,又是如此地短暫和脆弱,於是詩人又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並深為悲哀,是以「獨愴然而涕下」。
在短短的四句中,體現出極其巨大的感情上的反差,從而強烈地撼動了讀者的心。
倘若聯繫詩題仔細體味,讀者也許能想像出廣漠高台上的詩人的孤單身影。
但在想像出這身影之前,讀者早就被上述的感情所打動了,在想像出來之後,也未必再能增加原來的感動程度。
所以,以人物形象的是否完整、鮮明、生動等等作為決定作品成敗、高下的尺度,至少對詩歌是不合適的。
關於文學的上述定義中的「形象」如是指感性形象,係與「抽象」相對而言,這樣的「形象」自為文學所必具,但那只是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標準。
不符合這標準的作品,即使掛著文學的招牌,我們也可說它不是真的文學作品,至少也可說它是失敗的作品;但如果是符合這標準的作品,是否在文學成就上就完全一樣,沒有高下之分了呢?
倘若確是這樣,那麼,李白的〈靜夜思〉和樂府〈艷歌行〉、〈悲歌〉既然從「形象反映」的角度來考察並無高下之別,就反映社會生活而論,後兩篇還高於前者,為什麼前一篇對讀者的吸引力反而更高?
倘若文學作品在符合感性形象的要求的基礎上,其藝術成就仍有高下之別,那麼,我們又憑什麼來區分其高下?
在上述關於文學的定義中很難找到依據。
任何一個能夠讀懂文學作品──我們在這裡說的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作品──的人,在閱讀過程中及讀完後的某一時間內,總會引起若干感情的波瀾。
即使是一些以情節取勝的作品,甚至是寫得相當粗糙的,只要能獲得部分讀者的愛好,那麼,這些愛好它們的讀者在閱讀時同樣會產生感情的起伏。
三十年代曾產生過個別小學生在讀了武俠小說後到深山中去尋師學道的事,也正意味著小說中的武俠打動了這幾位小讀者的心,引起了他們的羡慕甚或崇敬。
由此看來,文學作品是一種以情動人的東西,它通過打動讀者的感情,而使讀者獲得某種精神上的愉悅。
一般說來,這就要求作者首先在感情上被打動,否則便無以感動別人。
當然,如果讀者知識貧乏,或幼稚易欺,有時也會出現作者自己未必受感動而讀者卻被打動了的現象,上面提到過的導致小學生到深山尋師學道的武俠小說,恐怕就屬於這一類。
不過,這些都只是文學中的平庸、低劣之作。
絕大多數讀者都不會被它所感動。
這裡需要進一步討論的是:
在作者自己不被打動時,是否也有可能寫出優秀之作呢?
大致說來,文學作品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作者寫其真情實感的,如詩詞;一類是虛構性的,如小說、戲曲。
在寫前一類作品時,如作者自己沒有受到強烈的感動,則其所寫的感情倘非淡薄,即為虛假,自不能打動讀者,其作品也自然不是優秀之作。
但此類作品中有一部分是寫所謂「無我之境」的;既然無「我」,則作者──「我」──之是否感動似乎就與作品之優劣不相干。
至於虛構的作品,更易被誤解為只要虛構得巧妙就行,未必需要作者自己的強烈感情。
所以應略加辨析。
「無我之境」是王國維提出的。
他的《人間詞話》標舉「境界」,以為「詞以境界為最上。
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同時又說: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有我之境也。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
按照他的理論,有「無我之境」的都是佳作,而這些作品既是「以物觀物」的結果,似乎作者只需靜觀默照,不必也不應有感情參與其間。
但如仔細考慮一下王國維的話,就會發現並非如此。
第一,所謂「有我之境」,並不是就詩句中提及的那些具體事物而說,而是就其所構成的總的境界而言。
如其所引秦觀〈踏莎行〉的「可堪」二句,其中「孤館」、「春寒」、「杜鵑」、「斜陽」都無從證明只是秦觀「以我觀物」的結果:
只要那館驛附近沒有其他的房屋,只要當時雖是春天卻比較寒冷,那自然是孤館、春寒;至於春天之有杜鵑,晴日之有斜陽,更毋庸詞費。
那麼,為什麼這兩句詞是「有我之境」呢?
在《人間詞話》的另一處,稱這兩句的境界為「淒厲」。
這顯然是就此二句的總體而論。
而其所以被視為「有我之境」,當是因為在王國維看來,雖是較為寒冷的春天薄暮,又處在孤館之中,景色也不應淒厲若此;秦觀這樣寫,乃是以「我之色彩」塗於景物上的結果。
第二,「有我之境」既是就總的境界言,「無我之境」當然也是如此。
而詩詞中的境界全都滲透著作者的主觀感受。
就被王國維作為「無我之境」例證的「採菊」兩句(出陶淵明〈飲酒〉詩「結廬在人境」)和「寒波」兩句(出元好問〈潁亭留別〉)來看,都具有寧靜、淡遠之致。
這大概也就是其境界之所在。
不過,就是以唯物主義觀點來看,寧靜、淡遠也都只是人的主觀感受,而非景色的物質屬性。
(就唯心主義觀點來看,當然更加如此)。
自然,有些景色本身所具的特點有可能引起某些特定的感受,但卻並非一定要引起這樣的感受。
如我國古代的詩人中有不少人讚美過秋天的寧靜、淡遠,但也有許多人感慨過秋天的寂寞、淒清,很難說哪種感受更符合秋天景色的本身特點。
恐怕兩者都有其相符之處。
換言之,即令人的主觀感受與景色的某些特點確是相應的,但為什麼他所產生的是跟某種景色中這些特點相應的感受,而不是跟同一景色中的那些特點相應的感受呢?
為什麼他所感到的是寧靜、淡遠,而不是寂寞、淒清呢?
在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歸根結蒂還是人的主觀──「我」。
何況在這過程中移情作用又往往難於避免。
就說被王國維作為「無我之境」的那幾句詩吧:
「白鳥悠悠下」的「悠悠」,是悠閑自在的感覺,但鳥在這樣飛翔時到底是否悠閑自在,人是無法知道的,只不過人在看到鳥這樣飛下來時產生了悠閑自在的感覺,就把它加到了鳥的身上,所以,這正是「以我觀物」,而非「以物觀物」;至於「悠然見南山」,既可解釋為悠然地見到南山,也可解釋為見到悠然的南山,但如是前一種解釋,則此句和上句只不過是描繪了詩人的兩個動作,說不上「無我之境」;因而只有採取後一種解釋才與「無我之境」相合,而以「悠然」形容山,正與以「悠悠」形容鳥一樣,也是移情作用。
由此可知,所謂「無我之境」,其實並非「以物觀物」,它跟「有我之境」一樣,都是「以我觀物」,從而都「著我之色彩」,只是「有我之境」的這種特徵鮮明一些,「無我之境」則隱蔽一些而已。
第三,這些被認為寫「無我之境」的作品,雖因其多具寧靜、淡遠之致,而易使讀者誤會為作者並無強烈的感動,但在作者的內心卻充盈著對其所寫這種生活內容的摯愛。
如陶淵明的〈飲酒〉: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與「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出馮延巳〈鵲踏枝〉)等句相比,確似感情色彩並不強烈。
但且讀一讀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他對自己的得以歸來過田園生活,是懷著怎樣喜悅的心情!
甚至「載欣載奔」,似乎又回到了童年。
而且,這不是一般歸鄉的喜悅,而是意識到自己走上了一條新的人生道路、終於從「心為形役」的困苦中解脫出來了的喜悅。
所以,在那些似乎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他都感受到大的快樂: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既窈窈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同上)
他不僅天天趣味盎然,看到庭中的樹木就「怡顏」,而且還領悟了生命意義:
隨著自然的運行,快樂地走到生命的盡頭。
換言之,這樣的生活既時時使他感到平安喜樂,又是其安身立命所在;他對這些的深厚感情也就可想而知。
正因他對此是這樣摯愛,才能在〈飲酒〉中寫出它那恬淡、自然的美,並引起讀者喜愛和感動。
所以,作品的寧靜、淡遠之致,是與作者對這種生活內容的深厚感情、全身心的投入同在的,絕不是冷淡地靜觀默照的結果。
它使人覺得感情色彩不如上引秦觀等詞強烈,是因感情已滲透到其描寫的景物之中,水乳交融,讀者在閱讀時便只覺察到景物、境界,而不易察覺其感情了。
但讀者被詩中的境界所打動,實際上也就是被作者的感情所打動。
至於元好問,乃是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經受了種種痛苦的人,他在遠離政治喧囂的大自然中獲得解脫感,從而幻想自己如寒波似地澹澹、白鳥似地悠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此,他之寫出這樣的句子,實出於內心對寧靜的渴求和對於寧靜的景色──業已經過了移情作用──的愛好,而不是對景物冷靜地觀照的結果。
總之,即使是被認為寫「無我之境」的作品,仍然離不開作者深沈、濃厚的感情。
讀者在讀這些非虛構性的詩詞時,無論是被其「無我之境」抑或「有我之境」所打動,都是在感情上與作者共鳴。
現在說虛構的作品。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虛構之作,主要是小說和戲曲。
戲曲本來自有其獨立的藝術特徵,並不是文學的一個部門,但是雜劇、南戲和傳奇(不包括後來那些以情節熱鬧取勝的傳奇)常把曲詞放在首位,而把情節放在次要的地位(情節常有所本,說明劇作家的獨創性實在彼而不在此;折子戲的經常上演,說明很多觀眾欣賞的重點在演員的唱做和曲詞本身),抒情性很強。
所以,作為中國文學史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元、明和清代前期的戲曲,其所承擔的抒情的任務實不下於唐詩、宋詞,不過其所抒的不是作者自己的情,而是劇中人的情。
中國古代小說所經歷的從不成熟到比較成熟的過程,大抵是這樣的:
先是重情節,或將一些不應作為小說的成分的東西引入,其後逐漸進到人物、情節並重,不適合於小說的成分也相應減少。
在這過程中,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的具體情況並不一樣,但總的趨勢是一致的。
被稱為「四大奇書」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詞話》是小說比較成熟時期的代表作,都已很注重人物描寫。
《三國志通俗演義》在寫人物的成熟上雖不如其他三書,以致如魯迅所說:
「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上〉)但它要想「顯劉備之長厚」,「狀諸葛之多智」,也正說明了它對人物描寫是重視的,只是這兩個人物寫得不算成功罷了;何況寫得成功的也有,關羽就是顯例,「義勇之概,時時如見」(同上)。
「四大奇書」以後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更進而以寫人物為主,情節成了寫人物的材料。
(這種情況在《金瓶梅詞話》中已開始出現,但為數不多;在《儒林外史》、《紅樓夢》中則為常見現象。
)
小說要把人物寫好,作者就必須深入體會人物的內心世界。
戲曲要代劇中人物抒情,作者也必須體驗其感情。
所以,戲曲,小說雖是虛構的作品,但與那些寫作者真情實感的詩詞相比,在對感情的要求方面絕不稍低。
換言之,虛構作品的作者必須經驗其作品中各種人物的感情,而且必須與處在作品所寫的種種境遇裡的人物,所可能和應該具有的感情,同樣真實而強烈。
關於這一點,明末清初的金聖嘆已經意識到了。
他說:
《水滸》作者寫豪傑、奸雄、淫婦、偷兒都很逼真,其能寫好豪傑、奸雄,可能因為施耐庵本身就是豪傑、奸雄,但何以又能寫好淫婦、偷兒呢?
施耐庵自己絕不會是淫婦或偷兒。
對此,他解釋說:
非淫婦定不知淫婦,非偷兒定不知偷兒也。
謂耐庵非淫婦非偷兒者,此自是未臨文之耐庵耳。
‥‥‥若夫既動心而為淫婦,既動心而為偷兒,則豈唯淫婦、偷兒而已。
惟耐庵於三寸之筆、一幅之紙之間,實親動心而為淫婦,親動心而為偷兒。
既已動心,則均矣。
又安辨泚筆點墨之非入馬通奸,泚筆點墨之非飛檐走壁耶?
(金聖嘆評本《水滸傳》五十五回總批)
他的意思是說:
作者在寫作時,必須「親動心」而為作品中的人物,與之融為一體,具有同樣的想法,經驗同樣的感情,所謂「既已動心,則均矣」。
當然,傑出的作家在創作時,除了體驗人物的感情以外,恐怕還滲透了作家自己對人物的愛憎,因此,其感情實較作品中人物遠為豐富而強烈。
總之,即使是虛構性的作品,感情也是很重要的。
其優秀之作所以能打動讀者,也是基於讀者與作者在感情上的共鳴。
這與寫作者親身經歷的作品並無二致。
對於讀者,文學作品首先(第一步)要打動他的感情;就作者來說,創作也必須具有激情。
既然如此,我們如果要給文學下定義,似乎不應該忽略了這一點,而應把其打動讀者感情的作用包括在定義之內。
由此,我們就可以給文學的成就確定一個與其定義相應的標準,那就是作品感動讀者的程度。
越是能在漫長的世代、廣袤的地域,給予眾多讀者以巨大的感動的,其成就也就越高。
而且,越是這樣的作品,越能使讀者在感動之餘受到某些啟發,領悟到某種哲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其人生態度;但這一切都是以讀者受到強烈感動為前提的。
如果根本不能感動讀者,這一切也就根本無從發生。
不過,對於讀者的感動,也還應該區別對待。
先引一段魯迅的文章:
當我在家鄉的村子裡看中國舊戲的時候,是還未被教育成「讀書人」的時候,小朋友大抵是農民。
愛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煙焰,現出一個妖精來;對於劇情,似乎都不大和我們有關係。
‥‥‥但還記得有一齣給了感動的戲,好像是叫作「斬木誠」。
一個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殺不可了,他的家裡有一個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
那悲壯的動作和歌聲,真打動了看客的心,使他們發見了自己的好模範。
(《淮風月談.電影的教訓》)
魯迅當時看的是紹劇。
這齣戲源於明末清初劇作家李玉所編的傳奇《一捧雪》。
在《一捧雪》中,這位忠僕的姓名為莫成。
寫作「斬木誠」,恐是魯迅的記憶之誤。
這是一齣宣揚奴隸道德的戲。
在上引的文字之後,魯迅接著寫道:
為要做得像,臨刑時候,主母照例的必得去「抱頭大哭」,然而被他踢開了,雖在此時,名分也得嚴守,這是忠僕,義士,好人。
很清楚地指明了其主旨所在。
今天的青年如果看到這樣的戲,大概未必會再受感動,但魯迅所說的那個時候──清代末年,它卻「真打動了看客的心」。
這種差別的造成,不僅僅是由於時代的不同;因為,比這戲的時代早得多的文學作品而至今仍能感動讀者的,為數仍然不少。
例如〈離騷〉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這樣的句子,今天仍能打動若干青年的心──當然是指讀得懂它的青年。
那麼,為什麼有些很古老的作品仍能感動我們,而有些作品儘管在一段時期內也能獲得許多讀者的真心喜愛,過了幾百年甚至幾十年就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了呢?
這應從人類發展歷史和人性的角度去考慮。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然後要研究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9頁)。
這也就意味著「人的一般本性」和「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是既有聯繫也有差別的。
後者如與前者沒有差別,就不能說它「發生了變化」;如果沒有聯繫,就是兩種互不相干的東西,後者就不是前者「歷史地發生了變化」而形成。
換言之,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中,既有與「人的一般本性」相通之處,也有相異甚至相反的一面。
所謂的「人類本性」或者「人的一般本性」也就是要求自己──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而馬克思所說的「自我克制」則正是與這要求相違背的,所以它也就起了剝奪「人性」的作用。
就文學作品來說,它要在自己那個時期裡感動讀者,必須與當時的「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相適應,這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然而,如果它僅僅是或主要是與其中的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卻不符合「人類本性」的內容相適應,那麼,在那個時代過去以後,它的魅力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甚或全部消失;如果它較多地與其中符合「人類本性」的內容相適應,那麼,在那個時代過去以後,它仍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動後世讀者的心。
理解了這一點,也就可以懂得為什麼有一些看來似乎沒有多大社會意義的作品卻能在許多世代中引起廣大讀者的強烈共鳴,成為千古名篇。
例如李白的〈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這首詩的內容可用以下三點來概括:
一、對於以喝酒為中心的享樂生活的讚頌和追求;二、對個人才具的自信;三、對人生短促的悲哀。
而第一點尤為突出。
若從通常所謂的社會意義或教育意義來要求,這首詩並不可取。
但如根據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人性──人類本性的內涵來看,那麼,詩人所謳歌的人生態度顯然是與違背人性的「少吃、少喝‥‥‥」的「自我克制」相對立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豪情,實可視為對自己強大的生命力的自許,而以「黃河」兩句來形容生命的流程,也間接顯示出生命的強大有力,雖然同時含有慨歎其一去不復返之意;至於對人生短促──個人生命的易於消逝──的悲哀,如從「人對於和自己同類的其他存在物的依戀只是基於對自己的愛」的角度說,也正是難於避免的吧。
所以,此詩之獲得千古讀者的共鳴,正是由於作者率真地、富於感染力地表現了他那從人性出發的強烈感情。
再看陸游的兩首詩和辛棄疾的一首詞。
陸游〈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二首:
迢迢天漢西南落,喔喔鄰雞一再鳴。
壯志病來消欲盡,出門搔首愴平生。
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
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
辛棄疾〈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
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
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休說鱸魚堪膾,盡西風,季鷹歸未。
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
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
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
這三篇都含有恢復中原的渴望和對南宋政府苟且偷安的不滿,〈水龍吟〉的「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是說遠望中原群山只能滋生愁恨,也與陸游的「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含意相近;就通常所謂的思想意義來說,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