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docx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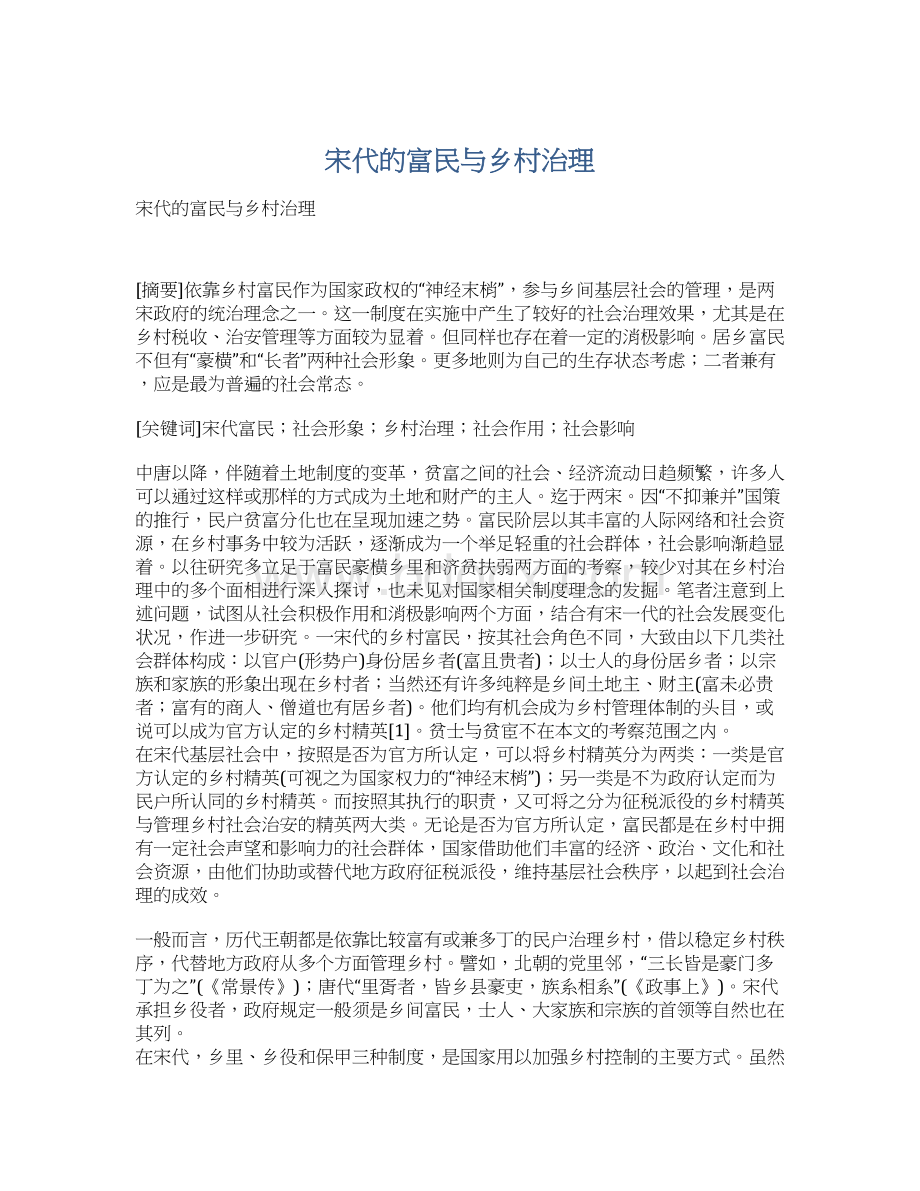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摘要]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
这一制度在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着。
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
居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
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关键词]宋代富民;社会形象;乡村治理;社会作用;社会影响
中唐以降,伴随着土地制度的变革,贫富之间的社会、经济流动日趋频繁,许多人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土地和财产的主人。
迄于两宋。
因“不抑兼并”国策的推行,民户贫富分化也在呈现加速之势。
富民阶层以其丰富的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源,在乡村事务中较为活跃,逐渐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群体,社会影响渐趋显着。
以往研究多立足于富民豪横乡里和济贫扶弱两方面的考察,较少对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多个面相进行深入探讨,也未见对国家相关制度理念的发掘。
笔者注意到上述问题,试图从社会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结合有宋一代的社会发展变化状况,作进一步研究。
一宋代的乡村富民,按其社会角色不同,大致由以下几类社会群体构成:
以官户(形势户)身份居乡者(富且贵者);以士人的身份居乡者;以宗族和家族的形象出现在乡村者;当然还有许多纯粹是乡间土地主、财主(富未必贵者;富有的商人、僧道也有居乡者)。
他们均有机会成为乡村管理体制的头目,或说可以成为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1]。
贫士与贫宦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在宋代基层社会中,按照是否为官方所认定,可以将乡村精英分为两类:
一类是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可视之为国家权力的“神经末梢”);另一类是不为政府认定而为民户所认同的乡村精英。
而按照其执行的职责,又可将之分为征税派役的乡村精英与管理乡村社会治安的精英两大类。
无论是否为官方所认定,富民都是在乡村中拥有一定社会声望和影响力的社会群体,国家借助他们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由他们协助或替代地方政府征税派役,维持基层社会秩序,以起到社会治理的成效。
一般而言,历代王朝都是依靠比较富有或兼多丁的民户治理乡村,借以稳定乡村秩序,代替地方政府从多个方面管理乡村。
譬如,北朝的党里邻,“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常景传》);唐代“里胥者,皆乡县豪吏,族系相系”(《政事上》)。
宋代承担乡役者,政府规定一般须是乡间富民,士人、大家族和宗族的首领等自然也在其列。
在宋代,乡里、乡役和保甲三种制度,是国家用以加强乡村控制的主要方式。
虽然这三种制度前后错综复杂,甚或有相互兼充、重合的现象,但是从国家的规定来看,其中的头目都要求由乡间富足(或兼多丁)的乡村民户承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替国家承担着乡村治理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不太富有的民户(第四、五等主户和广大的客户),则只能充当次要角色——丁、承帖人等,其所谓职责就是被用于驱使。
至于广大客户,一般是没有承担职役资格的。
关于充当乡役的富民,我们先检视两宋各个时段的政府规定。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诏令:
“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
”(淳化五年三月戊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诏废里正,户长一役主督赋税,以第二等户充役。
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推行募役制时,应募户长役者,规定须是第四等以上的乡村民户“有人丁物力者”方可承担(《转对论役法札子》);元丰八年(1085年),经过一番反复,重行募役时,仍规定户长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元丰八年十月)。
元佑以后,重新推行差役制,沿用熙宁前的制度,以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户长。
此后,但凡以户长催税,大致沿用了这一规定。
关于耆长、壮丁,据《嘉定赤城志》卷十七和《淳熙三山志》卷十四载,耆长“以第一、第二等户差”,壮丁从属于耆长“于第四、第五等差”。
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乞伏矩奏云,“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这说明,宋初以来,一直以第一或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耆长,以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
熙宁年间推行的募役法中,关于充募耆长的户等规定,也可从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再次下诏恢复耆壮之法中找到根据,即耆长允许募第三等以下民户充应(元丰八年十月丙申)。
元佑之后,复更为差役制,耆长、壮丁的应役户等则一如熙宁前旧制,此后也大致沿用未变。
保甲制被混同于乡役制后,宋政府对于充担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承帖人等乡役的民户,也均有具体规定。
熙宁三年(1070年)初行保甲制时,朝廷规定充任小保长须是主户中“有才干、心力者”,充任大保长须是主户中“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充任保正副者须是主户中的“最有行止、心力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兵二之五)。
这时,由于以乡间中下民户充任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等缺乏参加训练的马匹、武器和衣食等,所以必须用富民承担。
此后,宋政府也一再强调,“在法:
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食货六六之八二)。
南宋林季仲《竹轩杂着·论役法状》引述绍兴二年(1132年)和四年(1134年)的臣僚上奏,称他们要求轮派差役,“欲不拘甲分,总以一乡物力次第选差,非第一等[户]不得为都[保]正,非第二等不得为保长”。
早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被差派为甲头之役者,政府强调须是以乡村“有物力”(食货四之十九)的第三等以上民户方可充任。
南宋时期曾有“自高至下,依次而差”(食货六五之八五)的情况。
然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二月,朝廷又同意一位官员的奏章,以“甲内税高者为[甲]头催理”(食货六五之九二)赋税。
“税高”之家,当然是指较为富有的乡村主户。
总之,大致而言,两宋政府一直贯彻着以乡村中较富裕(一般为三等以上主户)的民户充任里正等重要乡役的制度,并凭借他们实现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有效管理。
而乡役户的社会交际网络、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以及“因役致富”和行政经验的积累,有利于他日的举业和仕业(P441),也构成为其社会资源的一部分。
居乡的士人、形势户,有时他们并非官方认定的乡村精英,算不上协助政府管理广土众民的、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但在基层社会中,他们同样起着乡村治理作用。
如所周知,读书和考取功名所需的费用,是很可观的一笔开支,没有一定经济能力的民户,是很难加入到科举人仕的行列中的。
宋代科举的发展,相当可观。
社会上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而考取功名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即使是考取到功名,由于宋代官多阙少的矛盾也很突出,所以,为数不少的落第士人和待阙、丁忧、致仕的官员仍会有很多可能生活在乡间。
虽然有些士人并不富裕,被目为贫士但从总体上看,这个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比较富有,或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在乡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由于各种因素居乡的形势户,因其所拥有的财富以及其他政治、社会资源,一般也比较富有。
而按照宋政府的规定,所谓形势户,“谓现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长]、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
“非贫[户]、弱者”,意即非富有者不能列入形势户。
他们也往往参与乡村治理,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
另有一类乡村富民,是以大家族、大宗族的形象出现的,他们同样对乡村治理影响较大。
南宋汪藻《浮溪集·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中的这则史料,大致可反映出他们在乡间的经营和社会影响:
迨宋兴百年,无不安土乐生。
于是,豪杰始相与出耕而各长雄其地,以力田课僮仆,以诗书训子弟,以孝谨保坟墓,以信义服乡间,室庐相望为闻家,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无世无之。
再如,为了延续家族的兴旺和昌盛,李筠死后三年。
其妻耿氏吩咐三个儿子分别“吏而役”、“耕而食”、“使就学”[10](P394)。
自南宋初延续二百六十多年的浦阳郑氏家族,其族规中虽然有着“子孙勿习吏胥”的条款,但却又强调“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厥中”,要求凡是“子弟当随掌门户者,轮去州邑,练达世故,庶无懵暗不谙事机之患”[11]P13,P5)。
即要求族人到县司熟悉官民交接的门道。
上述两例,都是家族、宗族要培养同县司官吏打交道的族人,使他们参与到国家权威的范畴之中。
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自家受到蒙蔽,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着借以发展家族的理念。
换言之,这也是家族、宗族的首脑与乡役等交叉重合的例证。
他们对于地方、对于家族的治理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居乡的官户、形势户,一些富有的士人和家族,他们的各种社会行为,或成为民户心目中的“豪横”,或被目为“长者”。
富民豪横乡里的情况,史例颇多。
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四年(1020年)四月丙申所载:
浮梁县民臧有金者,素豪横,不肯输租。
畜犬数十头,里正近其门,辄噬之。
绕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
每岁,里正常代之输租。
及临泾胡顺之为县令,里正白其事。
顺之怒曰:
“汝辈嫉其富,欲使顺之与为仇耳!
安有王民不肯输租者耶?
第往督之。
”里正白不能。
顺之使手力继之,又白不能;使押司、录事继之,又白不能。
顺之怅然曰:
“然则此租必使令自督耶。
”
再如,袁采在《袁氏世范·子弟宜常关防》中所载:
贵宦之子孙……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
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凌人;侵害善良,则多致饰词以妄讼。
乡人有曲理犯法事,认为已事,名曰担当;乡人有争讼,则伪作父祖之简,干恳州县,以曲为直。
差夫借船,放税免罪,以其所得,为酒色之娱,殆非一端也。
反映南宋时期东南地区社会现实的《明公书判清明集》,其《士人因奸致争既收坐罪且寓教诲之意》、《贡士奸污》、《士人教唆词讼把持县官》以及《豪横》类目下各篇所反映的,许多都是居乡富民所为不法之事的记录。
其中,《为恶贯盈》条所载“鄱阳之骆省乙者,以渔猎善良致富,武断行于一方,胁人财,骗人钱,欺人孤,凌人寡,而又健于公讼,巧于鬻狱。
小民思其罗织,吞气饮恨,敢怒而不敢言”,更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
富民被乡户目为“长者”的史例,也颇为丰富。
例如,刘挚(忠肃集·赠刑部侍郎孙公墓表)所记,孙成象之子孙隽居乡时,“轻财乐施,教子有方,里人以为长者”。
再如,胡铨《胡澹庵先生文集·易长者墓志铭》载,易啼“乡人有斗者,踵门求直,闻君言羞缩辍讼”;洪咨夔《平斋文集·罗迪功墓志铭》记载罗介圭事迹云:
“乡邻信其长者,有讼不之有司而之君取平相踵也。
”他们有的虽非官方备案的乡村治理头目,其实即使在暗中,他们仍是乡村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社会效用有时也远远超过乡村管理头目。
譬如,前揭乡民争讼者会主动找他们平决词讼,社会救济、桥道、水渠等公益事业的兴建,教书育人,解读官方文件,向广大不识字的民户传达国家的题壁公告、赋税征收条款及状纸的书写和案件判决结果,等等。
这些连接于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的事务,依赖这些人的活动,方可达到官民相接的目的。
总之,他们在乡间的威望很高,影响力很大,在乡村治理和秩序维护方面作用显着。
此外,乡间富民当还有兼具二者的另一种社会形象——充当国家和社会间的缓冲剂。
就宋代而言,国家的治理理念是以在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富民治理广大的贫苦民户。
如果依傅衣凌的“公”和“私”的两大系统的划分[12],则这些乡间富民,一方面他们代表着“公”(国家)的系统的功能,为征收国税和社会稳定而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往往代表着“私”(社会)系统的利益,为了地方与乡村民众的生活和生存,与官方做着这样或那样的融通的事情,甚至会或明或暗的与国家抗衡,化解国家和基层社会间的矛盾与冲突,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缓冲剂。
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往往是公、私交融在一起。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些富民更多的会从自身的利益着想:
对自家有利的事情,或争或抢,极力为之;对自家不利或是利益较少的时候,他们则避之唯恐不及。
例如,据袁采《袁氏世范·处己·官有科敷之弊》载,在应付州县官员的各种钱物需求时,“为手分、乡司者,岂有将己财奉县官,不过就簿历之中,恣为欺弊”,是其更多为一已之利考虑的表现。
柳立言在讨论家族问题时指出,士大夫并非不留意宗族的命运,但更关心本家的前途(P438)。
这当然也是出于对一己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