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及时间导论.docx
《存在及时间导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存在及时间导论.docx(4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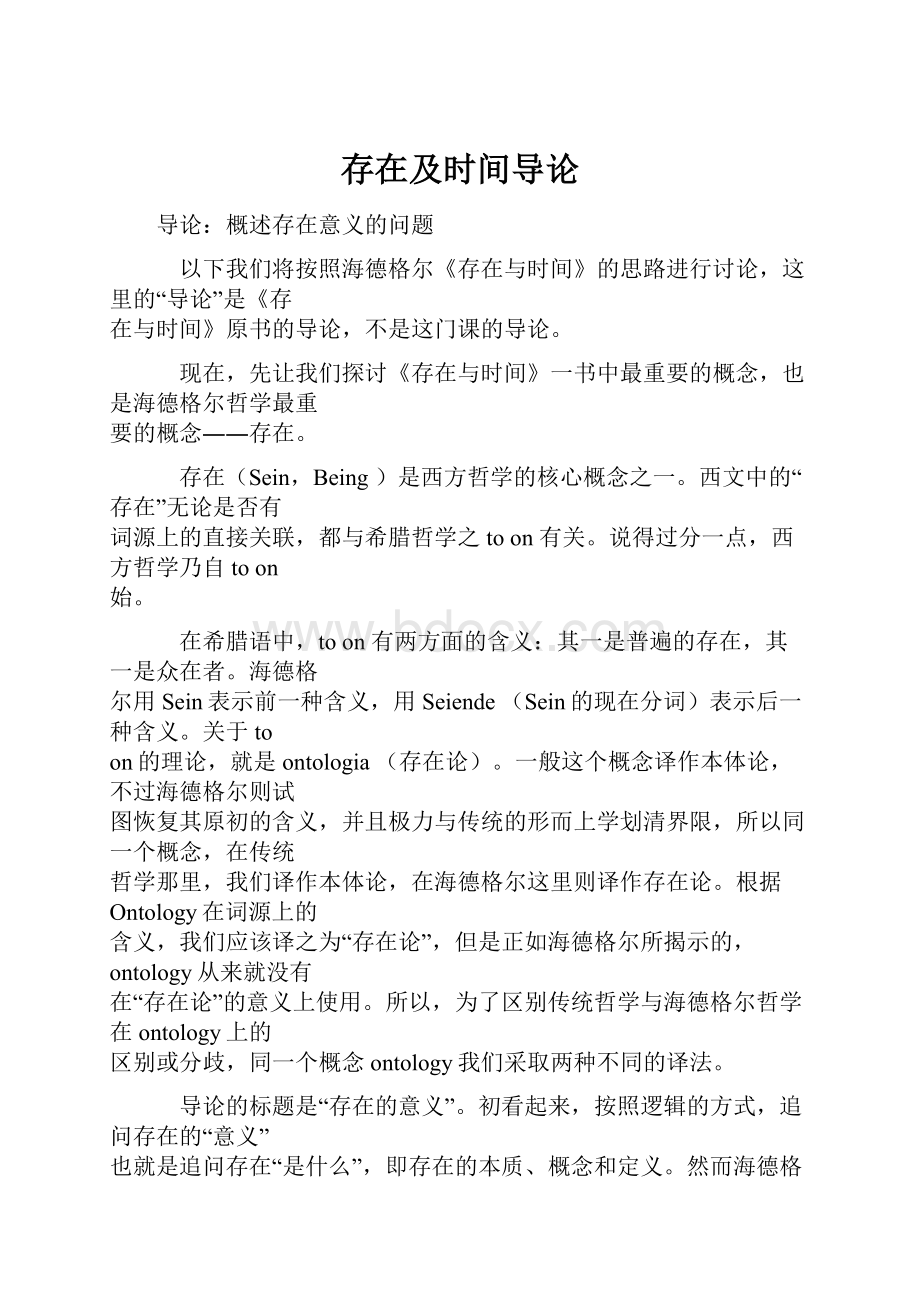
存在及时间导论
导论:
概述存在意义的问题
以下我们将按照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思路进行讨论,这里的“导论”是《存
在与时间》原书的导论,不是这门课的导论。
现在,先让我们探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最重要的概念,也是海德格尔哲学最重
要的概念――存在。
存在(Sein,Being)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
西文中的“存在”无论是否有
词源上的直接关联,都与希腊哲学之toon有关。
说得过分一点,西方哲学乃自toon
始。
在希腊语中,toon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普遍的存在,其一是众在者。
海德格
尔用Sein表示前一种含义,用Seiende(Sein的现在分词)表示后一种含义。
关于to
on的理论,就是ontologia(存在论)。
一般这个概念译作本体论,不过海德格尔则试
图恢复其原初的含义,并且极力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所以同一个概念,在传统
哲学那里,我们译作本体论,在海德格尔这里则译作存在论。
根据Ontology在词源上的
含义,我们应该译之为“存在论”,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ontology从来就没有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用。
所以,为了区别传统哲学与海德格尔哲学在ontology上的
区别或分歧,同一个概念ontology我们采取两种不同的译法。
导论的标题是“存在的意义”。
初看起来,按照逻辑的方式,追问存在的“意义”
也就是追问存在“是什么”,即存在的本质、概念和定义。
然而海德格尔所说之“存在
的意义”有所不同。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要象追问在者那样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
另有所指: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之为存在就在于存在出来的显现,换言之,海德格尔
不是从现成所与的、“固态的”名词方面理解存在,而是从动词的角度、动态的方面理
解存在。
因而,海德格尔是从zusein的角度追问Sein(从tobe的角度追问Being),
追问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追问存在是如何存在的,如何显现出来而成其为存在的。
关于存在的译名,有必要多说两句,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讨论非常热烈。
的确,无
论是toon也好,sein也好,Being也好,都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译名。
就希腊语来说,
toon是动词不定式einai的中性现在分词形式,而不定式einai作为系动词本身原来
是没有实指性含义的,它只是在主词与宾词之间起连接作用,表示的是XX“是”XX、XX
“有”XX、XX“在”什么状态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是”、“有”和“在”又都不是
系动词本身的含义,而是它所表示的主词与宾词之间的关系。
一句话,它只是表示关系、
状态、功能等等的系词。
然而,久而久之,这个系动词不定式逐渐有了分词和动名词的
形式。
既然有了名词性质,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像追问一切名词所表示的事物那样,追问
toon“是什么”。
显然,由于汉语本身没有系词结构,没有系动词,因而难以用一个概念来翻译这个
toon、Sein、Being,许多学者主X按其本义译之为“是”,即将“是”理解为名词
――“是论”、“是者”……。
不过我总感觉这样翻译很别扭。
其实只要我们明白它们
的本来含义,不如约定俗成更好,虽然容易“望文生义”――汉语的确容易望文生义,
因为它有象形的一面――从而引起误解。
学者们为什么如此在乎“存在”的译名?
因为这个译名的确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甚至可以说,不是学西方哲学的人,不是很懂外语的人,百分之百地不可能准确地理解
这个概念。
汉语之“存在”,无论是“存”还是“在”,都具有太强的质料含义,给人
的印象是现成所与地占据着空间的对象,总之,空间感太强,而实际上存在恰恰是与空
间相对的。
其实不只是我们有这方面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
历史也就是存在越来越空间化、实体化、质料化的过程。
所以乃有海德格尔的革命。
总之,存在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崭新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几乎自
哲学产生就出现,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有效的解答。
《存在与时间》一开始就在扉页上引用了柏拉图《智者篇》中的一段话:
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了,不
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
海德格尔在导论中所做的是引导我们进入《存在与时间》的准备工作。
导论分为两
章,各有四节。
第一章主要说明存在问题的必要性和优先地位――为什么要重提存在问题?
第二章则意在说明探讨存在问题的方法――如何解决存在问题?
我想就“导论”的内容多讲几句,因为这是入门,也是熟悉海德格尔概念的开始。
以后不可能所有的内容都这样讲,我还希望给课堂讨论留一定的时间。
第一章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结构和优先地位
第一章包含有四节,目的是提出问题,说明问题的结构,以及存在问题的意义和优
先地位,即重要性。
第一节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
在导论中,海德格尔试图从几个方面说明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在第一节中,主
要探讨的是在理论上、学理方面,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
海德格尔第一句话就说到形而上学。
我们都知道,20世纪西方哲学是以反形而上学
为其基本标志的,海德格尔为什么说“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呢?
我理解,20世纪初,哲
学还处在徘徊彷徨之中,而德国当时正处在古典哲学的复兴――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
主义。
因而,海德格尔所说的“重新肯定形而上学”指的是当时――海德格尔走上哲学
舞台之时――德国哲学界的状况:
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对世界观的渴求,使黑格尔重新
获得了意义,吸引着我们年轻的一代。
新康德主义从科学方法转向了价值论,转向了人
文科学,有些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如文德尔班变成了新黑格尔主义者,而且生命哲学等也
试图从新的角度恢复形而上学。
虽然20世纪西方哲学以反形而上学为其基本特征,但是
在世纪交替之时,哲学还在寻找出路。
然而,尽管人们试图重新肯定形而上学,但是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形而上学最基
本也可能是惟一的问题,即存在问题,却久已被遗忘了。
人们以为用不着纠缠什么“巨
人们关于存在的争论”了。
所谓“巨人们的争论”典出柏拉图的《智者篇》。
当柏拉图
讨论存在问题时,他将以往的观点分成两大派,称之为“巨人与诸神的斗争”。
“巨人”
(Titan,Titanic)是天神乌拉诺斯与地神该亚所生的子女,共有12人,他们反抗天
神宙斯,失败后被打入地狱。
柏拉图用它来比喻自然哲学家或通常普通人的观点。
巨人
派认为只有可感知的形体才是真正的存在,另一派(诸神)则认为只有无形体的理念才
是真正的存在,形体不过是某种运动变化的过程。
这也可以看作是关于唯心主义和唯物
主义之争的最早的规定。
形而上学还在,存在问题却久已被遗忘了。
不仅是我们遗忘了存在问题,实际上在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存在问题就已经被遗忘了。
海德格尔经常说,形而上学是存
在的遗忘史。
众所周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存在问题被遗忘了呢?
海德格尔简略地回顾了这个过程:
早在希腊人对存在的最初的阐释中,就逐渐形成
了一个教条,它不仅宣称追问存在问题是多余的,而且还认可了这个问题的耽搁。
所有
这些都根源于人们对存在问题的“成见”。
关于存在的成见很多,海德格尔在此举出了
三个,用以分析人们认可存在问题之耽搁的理由。
1、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共相),因而一提到存在就达到了
界说的极限,那意味着我们的探索到此为止,用不着再追问下去,一切都清楚明白了。
换言之,一切问题只要抽象到“存在”,就算是解决了任务。
但是,存在的“普遍性”并不是“类属意义上的普遍性”:
兰花-→花-→植物…
…。
这种“类属上的普遍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定义”,对某个事物的规定是以最
终追溯到它的最高类属(共相)为目的的,这也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是什么”的追问。
然而,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的根据,不是这样的普遍性。
我们不能说“存在”是最高最
后的共相,因为即使是最低级的事物,也“有”存在性。
因此,存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遍共相,因为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抽象”、“归
纳”出来,更不是一个清楚明白的“概念”,好像一说到“存在”就可以把一切问题都
说清楚了。
退一步讲,即使可以说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也不意味着存在是最清楚的概
念。
实际上正好相反,存在这个概念是最晦暗的概念,因为我们用通常意义的办法根本
无法触及存在。
2、存在是不可定义的如果存在是最高的普遍性,最高的概念,那么按照形式逻辑,
存在就是不可定义的。
因为按照形式逻辑,一个概念的定义来自“种加属差”,即它与
同级事物之间的区别和它所归属的更高级的类。
如“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人归属于
“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是“有理性”。
然而,存在作为最高的普遍性,既不可能
从属更高的普遍性,也没有与之平列的东西好作区别。
因而存在是不可定义的(亚里士
多德)。
所以,“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描
述”――令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不能使存在得到任何规定。
但是,说存在不可定义,只能说明存在不同于存在者,形式逻辑给存在者下定义的
办法在此行不通,却并不意味着存在不构成任何问题,用不着追究了。
“存在的不可定
义性并不取消存在的意义问题,它倒是要我们正视这个问题”(P6)。
3、存在是自明的概念我们的一切知识、判断以及对存在者的一切陈述,都在使用
“存在(是)”:
一切存在者首先“是”,然后才“是什么”。
谁都知道“天是兰的”、
“花是红的”……这些判断陈述的含义没有什么晦暗不明的东西,一开口说话,谁都知
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里的“存在(是)”是自明的。
但是,海德格尔像康德、黑格尔一样反对“自明性”,他认为所谓“自明性”表明
的不过是“不明性”,表明了不可理解而已。
一切存在者都存在(是),一切判断都可
以用“是(存在)”来铺陈、展开,无论它们的内容多么明白,这里的“是”或“存在”
仍然没有说清楚。
存在不但不是自明的,而且是一个“谜”:
“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的任何行止里面,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任何存在里面,都先天地有一个谜”。
显然,这三条成见――当然不只这三条――都不能否定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
实
际上,由上述成见可知,存在问题不仅尚未有答案,而且这个问题本身亦是有问题的:
存在是不是问题?
存在问题能否追问、以什么方式追问?
怎样回答?
如果一个问题没有
答案,我们就需要追究它是不是问题,问得合适不合适。
由此可见,“存在问题不仅尚无答案,而且甚至这个问题本身还是悔暗和茫无头绪
的。
所以,重提存在问题就意味着:
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要先进行一番充分的研讨”(P6
)。
换言之,形而上学研究存在,却从一开始就认可了这个问题的耽搁,这不仅说明存
在问题尚未得到解答,而且也说明在问题的提法上原本就存在着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首
先从问题的提法上作一番充分的研讨。
这一节主要是从学理上理论上说明存在问题并未得到解答,仍然是成问题的。
至于
其他的原因,以后海德格尔将一一道来。
下面海德格尔专门分析了存在问题的结构。
第二节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
存在曾经是一个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了。
但是存在却早已不再是
一个问题了。
显然,“存在”从一个问题变得不是问题,这其间肯定在问题的“问法”
上出现了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再将存在当做问题,或者关于存在问不出问题了。
既然如
此,现在我们要重提存在问题,在我们之所问与古人之所问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同之处。
所以我们有必要讨论“发问”本身的问题。
海德格尔首先讨论了“任何问题一般都包含
的东西”,然后说明存在问题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是如何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这一节从问题的问法入手来讨论存在问题的特殊意义。
海德格尔首先讨论了“发问”的形式结构。
在他看来,“发问”(Fragen)乃是某
种“寻求”(Suchen),“寻求”总有从它们所寻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有
什么东西吸引我们去寻求,例如我们问:
“这人是谁”时,我们总是有原因的,而这原
因其实就在这个人的身上,是他的出现他的存在他的与众不同引导我们询问他是谁的问
题。
从现象学上看,这也就是说,在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时,虽然问题之所以是问题就在
于我们有所不知,但实际上我们与这个问题已经发生关系了。
即是说,在问题成其为问
题之前,我们已经与问题相遇,与之打交道了,而且正是这一更为源始的层面决定着问
题之为问题,以及问题的提法,从而亦决定着问题的回答。
这就是海德格尔之所以专门讨论问题的发问方式和结构的原因所在。
换言之,问题
以及问题的解答决定于问题的发问方式(提法或问法)。
问题能否回答,究竟怎样回答,
都与此有关。
所以,我们有必要考查关于问题的问题。
形而上学不再把存在当作问题,
而我们现在把存在当作问题,其间的区别应该在这里有其根源。
Fragen包含三个环节:
1、“问之所问”(Gefragte)
Gefragte――fragen――gefragt(过去分词,构成被动语态,“被问”)。
ge-
作为前缀有“集合”、“归属”之义。
发问总是被引发之问,所以“发问”就是“对…
…的问”,亦是“就……问”。
海德格尔之所以使用了fragen的过去分词,其中似乎暗
含着现象学之先天性的意思在里面,以体现“发问”-“寻求”“都有从它所寻求的东
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P7)。
在这里就什么发问?
被问的是什么?
存在。
2、“被问及者”(Befragte)
befragen:
询问、向……打听、查阅(详细)。
前缀be-多表示“切入”、“密切”、
“相关”、“紧密”等。
“问之所问”是存在,通过什么来问存在?
通过存在者。
存在
者,具体说来就是我们所是的存在者,就是“被问及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怎么问”
――通过在者。
3、“问之何以问”(Erfragte)
erfragen:
er-“结果”、“过程”。
erfragen:
通过询问而得知、“问明”。
发
问是为什么而问?
问的目的是什么?
问的目标或缘由是什么?
即发问要得到的什么目的。
在这里,发问的目的就是存在的意义。
例如我们询问一个人的品质。
问之所问是这个人,被问及的是他的行为举止,问之
何以问是他的品质。
不要以为海德格尔在这里是故弄玄虚,把“问题”复杂化了。
他的目的是通过对问
题的结构分析,说明关于存在问题的问法与众不同,而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了存在,不
再把存在当作问题,乃源于在问题的“问法”上出了差错。
一般地说明了问题的发问结构之后,海德格尔现在来分析存在问题的与众不同了。
1、就问之所问而言。
问之所问的是存在。
这一问却不同于一般对存在者的追问。
如前所述,发问总有来自问之所问的事先引导,我们之所以发问,一定是有所问,
或者说问之所问对我们来说成其为问题。
所以,在我们发问之前,我们便与这问题发生
关系了。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存在,那么“事先的引导”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作为存在者总已经活动在对存在的某种领悟中了。
对存在发问,
追问存在的意义,这些都是从对存在的某种领悟中生发出来的。
换言之,在我们追问存
在之前,我们就已经存在,而且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悟了。
现在我们追问存在,其实也
就是由对存在的领悟“引导”、“生发”而来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存在’说的是什么,然而当我们问道‘存在’是什么时,我们已经
栖身在对‘是’(在)的某种领悟之中了,尽管我们还不能从概念上确定这个‘是’意
味着什么”(P8)。
“领悟”(Verst?
ndnis)――vertehen,understanding,亦译作“理解”、
“领会”。
海德格尔用这个概念来表示我们人这种在者在将存在看作认识的对象之前,
与存在之间的某种关系。
从现象学上看,我们在认识一个对象之前就已经与之打交道了
(意向性),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与一般的认识对象不同,因为存在不在我们之外,
我们无论如何都存在着。
由于我们能够对我们的存在发问,而这一问问的乃是我们自己
的存在,所以在追问存在之前,我们早已同存在在一起了,因此对存在总已经有所领悟、
领会、理解了。
这里所说的“领悟”是“前科学”、“前意识”的。
在我们问存在之前,
我们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处在与存在的关系之中,当然早已经有所领悟了。
“领悟”
在此有体验、体会的意思。
以后海德格尔将专门讨论这个概念。
显然,我们追问的是存在,而存在不同于存在者,两者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追
问或认识存在者的方式不适合于追问或认识存在。
当我们对一棵树产生疑问时,无论我
们与树有怎样的现象学的“意向性”关系,我们毕竟不是树。
然而,当我们追问存在的
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某个在者,而是在者的存在,而且我们就在存在之中,存在就在
我们之中。
这就是说,我们所追问的存在就是我们自己的存在,因而存在问题需要一种
本己的展开方式,这种展开方式当然不同于对存在者的追问。
由此可见,就问题结构而论,存在问题与存在者的问题显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问
题。
海德格尔批评形而上学遗忘了存在,并不是说形而上学忘了它是研究存在的,实际
上形而上学从来没有忘记这一任务,而是说,形而上学忘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别―
―海德格尔称之为“存在论差异”。
形而上学之所以回答不了存在问题,之所以不再把
存在看作是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2、“被问及的东西”。
我们究竟通过什么来询问存在?
问之所问是存在,被问及的东西则是存在者。
因为
虽然存在者由存在而来,因存在而在,但是一问到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我们
只有通过存在者才能追问存在问题。
所以,追问存在“就是要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它的
存在来”。
我们追问存在,追问存在必须通过存在者。
通过存在者追问存在,也就是使存在者
能够不经歪曲地给出它的存在性质,这就必须如存在者本身所是的那样通达存在者,使
之如前所是地显现自身。
然而,我们追问的毕竟是存在,而存在问题与众不同。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正确的方
式来追问存在。
换言之,虽然一切东西都存在着,我们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存在者,通
过它来解答存在问题。
由上述“发问结构”可知,存在问题不同于一般的问题:
当存在
成为问题时,这意味着存在进入了“发问”的形式之中,换言之,存在必须成为问题,
成为“问之所问”,才能被问及。
这就意味着,存在要成为问之所问,一定要有在者去
问才能成为问题。
而世间只有一种在者,也就是我们向来所是的在者,能够对存在发问,
而对在发问,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存在发问,因为我们就是因存在而在的在者――Dasein.
“彻底解答存在问题就等于说:
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
存在者透彻可见”(P10)。
这就要求我们找到一种存在者,它不仅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而且能够“发问存在”。
“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
他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我用Dasein来称呼这种存在者”。
因此,
唯有在一种能够提出存在问题的存在者那里,存在才能成为问题,存在才能以最本己的
方式得以展开。
所谓“最本己的方式”是说,我们不可能通过追问其他存在者的存在的
方式追问存在,那是问不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追问自己的存在来追问存在。
换言之,
存在必须是在“最本己的方式”中才能得到解答。
海德格尔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受到了现象学的启发,这就是存在就在我
们之中,我们就在存在之中,因而对存在发问并不是对外在的对象发问,而是对我们自
己的存在发问。
我之所以说这一思想“重要”,是因为在形而上学史上,由于认识论立
场的限制,哲学家们的基本思路是将存在当作某种客观存在的外在对象――对象、客体,
我们自己则是认识的主体,他们没有意识到,问之所问存在,我们自始就栖身于对存在
的领悟之中了。
若无此领悟,就不会存在问题。
所以存在问题只能通过“最本己的方式”
才能提出和回答。
然而由此势必引出这样的结果:
我与存在乃为一体。
我怎样理解存在,
我就怎样存在;我怎样理解存在,存在就怎样存在(显现)。
也许有人会提出责难:
必须先就存在者的存在来规定存在者,然后又根据Dasein这
种存在者才肯提出存在问题,这不是“循环论证”吗?
!
因存在而存在的存在者Dasein
追问存在,这不是“自问自答”吗?
!
海德格尔认为,就存在问题的性质而论,这里不
存在“循环论证”,因为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存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推
导的方式进行论证,而在于用展开的方式显露根据。
3、问之何以问:
存在的意义。
正如我们所说的,存在不同于存在者,存在问题――存在的意义,问的并不是存在
“是什么”的定义或概念,而是存在是如何存在的,或者说,从存在之为存在出发,说
明存在是如何“存在”(zusein)即如何显现的。
这个问题是任何存在者都不可能回
答的,只有此在有此可能性。
海德格尔在下一节回答了这个问题。
总之,我们通过对问题的提问结构的分析,说明存在问题不同于一般的问题,因而
也就需要不同一般的回答。
回答这一问题乃是此在的历史使命。
第三节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
ontology在海德格尔这里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哲学史上的意义,可译作本体论,一
种是源始的意义,也是海德格尔所主X的意义,应译作存在论。
所谓“存在问题在存在
论上的优先地位”指的是存在问题乃是存在论的基本问题,甚至严格说来,应该是在存
在论之前必须得到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海德格尔将解决存在问题的分析称为“基础存
在论”。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节是接续着第一节作文章(第二节转向了存在问题不同一般
的问题结构),即接着讲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
我们在第一节中分析了存在问题的必要性,说明这个问题至今尚无答案,而且连问
题的提法都是成问题的。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存在问题是非常古老的而且尚无答案的问
题,我们仍然有可能这样问: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用?
”如果存在问题的
确只是哲学家们所关注的纯粹的理论问题,那么他们找不到答案也没有什么,存在问题
不提也罢。
我以为,海德格尔在这一节里实际上就是在回答这样的疑问,他要证明的是存在问
题在存在论上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存在问题的解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因而研究
存在问题的存在论相对于科学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另一方面,存在论为科学奠基,
但存在论之所以可能则需要以存在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为前提,因而存在问题在存在
论上亦具有优先地位。
在这里显示出了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间的分歧:
胡塞尔要为一切科学知识确定先验
的基础,这基础就是纯粹意识或先验的自我――知识与对象两者共同的根据在意识的意
向性活动之中。
海德格尔则不同,在他看来,纯粹意识还不能算是最本源的因素,一切
存在者必须首先存在,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因而存在是真正本源的东西。
在这一节里,海德格尔讨论了存在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他关于存在的观点――科学
研究的是存在者,对于存在是不过问的,也不可能解决存在问题――很容易让人想起亚
里士多德――“有一门学问……”,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
我以为,一方面在这里或许
胡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