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寨族群意识形成与孔明信仰分析.docx
《葛亮寨族群意识形成与孔明信仰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葛亮寨族群意识形成与孔明信仰分析.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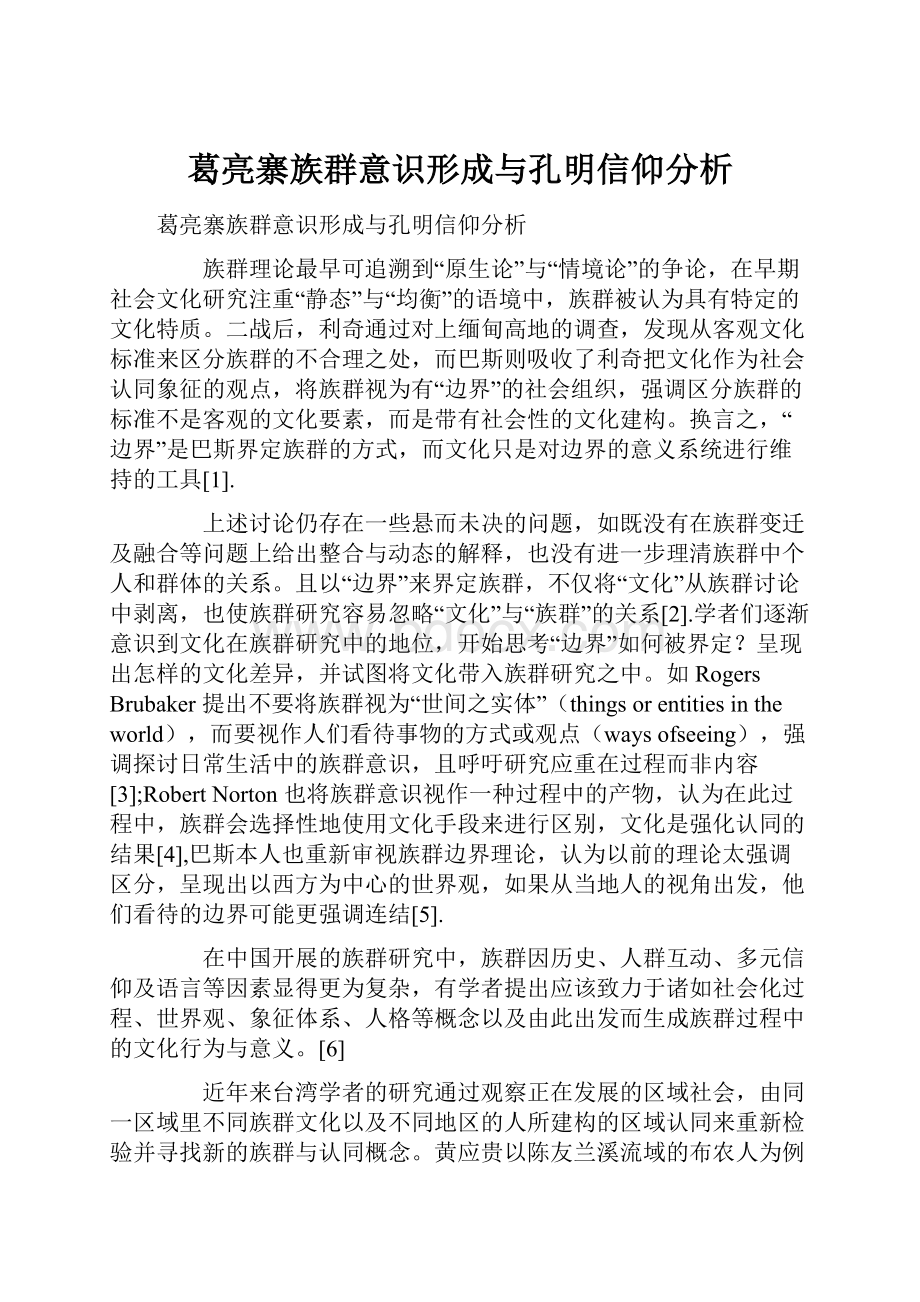
葛亮寨族群意识形成与孔明信仰分析
葛亮寨族群意识形成与孔明信仰分析
族群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原生论”与“情境论”的争论,在早期社会文化研究注重“静态”与“均衡”的语境中,族群被认为具有特定的文化特质。
二战后,利奇通过对上缅甸高地的调查,发现从客观文化标准来区分族群的不合理之处,而巴斯则吸收了利奇把文化作为社会认同象征的观点,将族群视为有“边界”的社会组织,强调区分族群的标准不是客观的文化要素,而是带有社会性的文化建构。
换言之,“边界”是巴斯界定族群的方式,而文化只是对边界的意义系统进行维持的工具[1].
上述讨论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既没有在族群变迁及融合等问题上给出整合与动态的解释,也没有进一步理清族群中个人和群体的关系。
且以“边界”来界定族群,不仅将“文化”从族群讨论中剥离,也使族群研究容易忽略“文化”与“族群”的关系[2].学者们逐渐意识到文化在族群研究中的地位,开始思考“边界”如何被界定?
呈现出怎样的文化差异,并试图将文化带入族群研究之中。
如RogersBrubaker提出不要将族群视为“世间之实体”(thingsorentitiesintheworld),而要视作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或观点(waysofseeing),强调探讨日常生活中的族群意识,且呼吁研究应重在过程而非内容[3];RobertNorton也将族群意识视作一种过程中的产物,认为在此过程中,族群会选择性地使用文化手段来进行区别,文化是强化认同的结果[4],巴斯本人也重新审视族群边界理论,认为以前的理论太强调区分,呈现出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如果从当地人的视角出发,他们看待的边界可能更强调连结[5].
在中国开展的族群研究中,族群因历史、人群互动、多元信仰及语言等因素显得更为复杂,有学者提出应该致力于诸如社会化过程、世界观、象征体系、人格等概念以及由此出发而生成族群过程中的文化行为与意义。
[6]
近年来台湾学者的研究通过观察正在发展的区域社会,由同一区域里不同族群文化以及不同地区的人所建构的区域认同来重新检验并寻找新的族群与认同概念。
黄应贵以陈友兰溪流域的布农人为例,认为当不同族群的人交错生活在一起时界线不再是清晰可辨的,他们所建构的族群认同不再以“边界”来认定[7];苏弈如、黄宣卫也注意到撒奇莱雅人如何在族群边界暧昧不清的情况下,运用文化创造维系族群意识完成正名运动[8].这些研究将重点放在族群文化边界的建构之上,且试图弱化“族群边界”概念所强调的族群间的分野,关注到复杂社会中族群相互之间连结的重要性。
本文所关注的葛亮寨位于都柳江下游,地处黔桂两省交界地带。
始于清雍正年间的航道疏浚使都柳江流域进入了王朝视野,更经由珠江水系进入到了更广阔的市场联系中。
区域的商业化发展吸引了大量移民,移民中溯江而上的闽粤商人实力最盛,占据沿河的主要市场。
还有部分移民是来自都柳江上游、支流的苗民与侗民,他们虽与生活在该流域的苗侗土着差异较小,但仍离乡背井,在沿江兴盛起来的贸易活动中,又因无资本经商,只能从事诸如放排、运输、打杂等工作,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复杂的人群关系中,他们的身份界限呈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葛亮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由上述移民汇聚发展而成的聚落,有趣之处在于,苗侗移民透过对“葛亮”这一寨名的演绎,将孔明传说与村落具体空间结合,创造了一套村落的“历史记忆”,并透过孔明庙宇的建立和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并表达了“我群”的族群意识与身份认同。
本文试图从葛亮寨当地人群观念出发,将族群问题放置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呈现苗侗移民在区域社会急剧变化的复杂联系下,如何通过文化手段协调彼此关系、建构族群意识,以及如何通过对“历史”创造性的重构与再造,型塑自身在区域中的定位,进而为族群情感的产生与族群意识的建构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村落空间与孔明叙事
葛亮寨坐落于都柳江南岸,为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乡下辖的自然寨,居住着富禄行政村第五、第六两个村民小组,共130多户,632人。
从户口登记的民族成分来看,大部分为侗族,寨中交往主要使用侗语,村民也几乎都能说桂柳话。
“葛亮”这一寨名的来历难以追溯,在清代的县志中就已出现,而侗语中称呼葛亮寨为“ban”,是一个当地人也说不出具体意义的普通名字。
葛亮寨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寨名,更在于村落中流传至今的众多孔明传说,这些孔明传说都基于这样一个“村落历史”:
相传葛亮寨曾是古夜郎国属地,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蛮期间,部将马岱所率领的部队曾在此驻扎和作战。
这一“村落历史”的表述也被志书所记载:
孔明城即诸葛垒,在富禄乡武侯村葛亮屯之下,长约五十丈,阔约三十丈,今存基址,尚有高七八尺者,相传为汉武乡侯征蛮时所建,曾埋金鼓于内,每风涛响应,如闻角声,现虽壕堑依然,第己荆榛满目,无残碑折戟可供摸索凭吊也,其右有井,俗亦称孔明井,长约八尺,约宽三尺周围均大石块所建,井深约五尺,水清凉彻骨,该屯饮料取给于此。
[9](P.106)从上文可知,与诸葛亮相关的“村落历史”也存在于葛亮寨村民对村落空间的解释中,如今村民仍能在葛亮寨东边精确地指出一片空地,认为此处即是马岱部队曾经驻扎过的“土营”.所谓“土营遗址”,实则是一段不完整的土夯矮墙,“墙”上长满了植物,已难辨认其轮廓。
此外,还有多处以孔明命名的空间,如孔明桥、诸葛亭、孔明井与孔明庙。
孔明桥原位于都柳江北岸与葛亮寨隔河相对,因山路崎岖而建,原桥为侗式建筑“风雨桥”,几次被毁后如今成为公路桥,仍命名“孔明”;诸葛亭原是孔明桥旁的一座凉亭,遮蔽一眼山泉,现虽不复存在,但山泉与地名仍沿袭至今。
当下最常被村民所提及的是孔明井,这是今天葛亮寨唯一的饮用水井,位于葛亮寨寨尾。
孔明井是葛亮孔明传说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传说当年诸葛亮派马岱率兵到达都柳江时,马岱部队的人马饮用都柳江江水后出现上吐下泻的情况,士气受挫。
诸葛亮接到消息后,亲自到都柳江探察,在葛亮寨的山坡上插下一根棍子,令士兵掘井,部队饮用井水后身体恢复了健康,最终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如今,水井的正前方还有一块因年代久远而模糊的石板雕刻,上面依稀可辨两个模糊的人形,村民们认为他们是诸葛亮与孟获,是人们为纪念诸葛亮寻井而雕刻。
这个故事充满了都柳江流域与外来征服者之间的微妙隐喻,与下文将要论及的都柳江区域开发历史不无关系。
另外,孔明除了作为一种叙事存在,同时也是葛亮寨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神灵,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孔明庙赋予诸葛亮以神圣性,被村民祭拜至今。
在都柳江流域,孔明传说不仅仅出现在葛亮寨,上游和中游地带的一些苗侗村寨中也流传着与孔明有关的故事。
这些故事的叙述模式较为类似,都将苗侗的传统娱乐活动与孔明联系起来,如认为吹芦笙和斗牛是孔明有意麻痹地方土着的方式,“目的是让我们玩物丧志,忘记要反对汉人的事”.在这些叙事里,或多或少地透露出当地人被征服的无奈。
除此以外,村民还将火药、水车等工具说成是诸葛亮带来的。
这些在西南地区较为普遍的传说叙事早已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讨论主要围绕对诸葛亮南征过程的考证以及诸葛亮南征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影响展开,或者分析诸葛亮南征叙事中所呈现出的本土反应的复杂性①.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笔者感兴趣的是这些孔明传说具体是如何在地方社会历史过程中被生产或被表述的。
实际上,孔明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由寨名衍变为传说,进而成为一套加以操演的信仰和仪式,这不仅与都柳江特殊的区域历史过程息息相关,更反映了村落社会生活中特定人群的身份诉求。
可以说,对孔明这一形象的加工与创造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历史和人群关系的互动过程。
二、区域历史与葛亮苗侗移民
葛亮寨中的孔明符号看似错综复杂,而真正的涵义和隐喻则应放置到具体的区域社会历史脉络中加以揣摩。
“葛亮”作为一个存在于“客话”中的村寨名称,本身就与清代国家对“苗疆社会”的拓殖和经营密切相关。
从雍正年间开始的一系列军事举措使都柳江流域被纳入到由水道连接的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之中,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由江河体系与陆路交织的市场网络,葛亮寨就是在这个市场网络中极为活跃的一环。
因区域商业化的发展,来自两广、闽、黔等地移民聚集于此,构成了葛亮人群的多样化,不同的人群又围绕市场贸易产生出新的联系。
在都柳江河道疏浚之初,葛亮地方曾是闽粤移民定居与经营的极佳选择,当商人移民逆流而上进入都柳江流域时,最早就在葛亮落户。
葛亮河宽滩阔,因地形之故江水在此回流,岸边江水平缓,这对于收放木材、湾船停泊来说是最理想的地理位置,至今人们还能回忆起河滩停放木排的盛况,“你可以在木排上走着,从河这边走到那一边”.在葛亮的移民中,有实力的商家主要是来自闽粤的移民,姓氏以赖姓为主,他们落脚在葛亮,从下游将盐、布匹等运至上游交易,再将上游的木材、桐油、山货等运往下游。
这些闽粤移民是市场中最为活跃的人群,同时也因其资本雄厚在地方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道光年间他们在葛亮修建了闽粤会馆和天后宫,以地域认同整合移民商家,闽粤会馆和天后宫保存至今,如今葛亮寨仍有两三户赖姓居住于此。
除闽粤籍移民商家之外,葛亮市场的兴盛还吸引了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即原本就居住在都柳江流域的苗侗人群,他们由上游或支流地带的榕江、西山、贯洞、龙图、黎平、广西大年等地迁徙而来。
今天居住在葛亮的寨民,虽民族身份被识别为侗族,但实为这些苗侗移民的后代。
最初苗侗人群迁徙葛亮多是迫于生计,来到葛亮后,依靠早到的“同乡”帮忙,为老板看铺、放排或者种田,逐渐安居下来。
这一历史也体现在葛亮多样的姓氏上,葛亮如今有石、罗、骆、梁、赖、杨、覃、潘等姓,他们总爱强调是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的,甚至同一个姓氏内部也有区分。
如葛亮的罗姓被分为两种,分别是“罗”和“箩”,村民普遍认为“罗”姓是广东籍移民,而“箩”姓则是从今贵州省从江县贯洞迁徙而来。
这些只有当地人才能区分的姓氏关系与说法,反映了葛亮区域开发后人群交错的状况,这在葛亮妇女的衣着上也有所体现。
当地女性称葛亮早已没有穿少数民族服饰的习惯,目前仅能从一些老年女性所梳的偏发髻上看出一些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
实际上,因区域社会变迁而迁徙到葛亮的苗侗移民,生存境况较为被动。
一方面,葛亮市场由闽粤籍商家主导,苗侗移民在村寨中处于相对弱势,只能“为老板打工”;另一方面,葛亮寨属于都柳江下游流域“七十兄弟寨”②之一,虽然兄弟寨相互之间有防御和帮衬的义务,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七十兄弟寨”除葛亮外均为苗寨,主要分散坐落于都柳江南岸的一条支流---大年河两岸高坡,大年河汇入都柳江的入河口就在葛亮上游约一公里处,因此大年河口以及葛亮河滩是苗寨木材交易的重要通道。
最初的“七十”兄弟寨并不包含葛亮,但葛亮这一移民村寨希望借由村落联盟寻求庇护,而苗寨则希望借助葛亮的地理优势进行木材贸易,因此同意葛亮加入“七十”.同时,高坡苗寨依靠“七十”结盟的约束力对葛亮这一移民村寨也形成了一定的控制和影响。
在同治二年(1862)的“苗乱”中,“叛苗”以葛亮为据点[10],对葛亮扰动颇深,虽然我们对“七十”苗寨在“苗乱”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得而知,然而自“苗乱”后,闽粤籍的移民商家们陆续搬往对岸下游约500米的富禄居住经商[11].如今从葛亮搬去富禄的人家回忆道,过去葛亮“土匪”猖獗,抢劫、拉羊③时有发生,因此才不得不离开,而所谓的“土匪”就包含了“七十”兄弟寨的当地人。
尽管这只是闽粤移民离开葛亮的原因之一,但足见葛亮一隅之地所交织的复杂人群关系,而此种复杂性正是与水路通道所带来的区域社会变迁深刻嵌合在一起的。
在这样的境况下,从周边地区迁徙到葛亮的苗侗移民,既无力如闽粤商人那般以会馆、市场整合移民社会,同时在“七十”兄弟寨中又呈现出被动地位。
这种“尴尬”的处境也使得葛亮苗侗移民的身份呈现出模糊性,他们既不是文化上的“陌生人”,其语言、生活习惯与沿河苗侗并无明显差异,但同时也不能完全融入“当地”,唯一可依靠的只是移民间的同姓、同乡关系。
直至民国期间孔明桥的修建与复建给葛亮苗侗移民整合提供了一个契机。
孔明桥实际为南侗建筑特色的“风雨桥”,第一次修建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
碑文记载,孔明桥的修建资金由广东木材商人莫氏提供,主持修建的是当年富禄乡乡长廖氏与副乡长赖氏,目的是方便来往富禄的行人,“孔明桥”因其位于葛亮寨的对岸而得名,可见孔明桥最初修建以富禄闽粤移民为主导,与葛亮关系并不大④.后来桥被洪水冲毁,民国三十五年(1946)葛亮苗侗移民联合富禄闽粤移民开始重建孔明桥,资金则从富禄、葛亮、青颀、匡里、拉拢、梅寨、石碑、贵州龙图、贯洞、八洛、西山等地筹措,而参与捐银的地方与葛亮苗侗移民的迁出地有很大程度的重合。
这次修建以葛亮寨为主导,所用木材和人工均由葛亮提供,并由葛亮寨民负责监工。
孔明桥的重建对葛亮苗侗移民具有多重意义:
首先,通过共同参与修桥,苗侗移民得以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其次,以诸葛亮命名的“孔明桥”,使得葛亮以空间为载体拥有了共同的象征符号,并使“孔明传说”与现实生活衔接;第三,葛亮寨作为整体参与到地方的公共事务中,为其在该区域中找到相应位置奠定基础。
孔明桥后几经损毁,于1993年修建富梅公路时,在其旧址建公路桥,仍被命名“孔明桥”.葛亮苗侗移民的身份困境与都柳江流域区域历史、商业化发展以及传统村落关系等一系列复杂因素息息相关。
在区域历史进程中,葛亮苗侗移民通过“孔明桥”的建设整合寨中的移民群体,同时强调孔明与葛亮寨的联系,用孔明传说替代了葛亮寨闽粤移民活动的痕迹,而基于葛亮地方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虽然这一过程已不可追溯具体发端于何时,但葛亮寨渐渐使用另一种“村落历史”来进行表述,如闽粤移民曾在葛亮修建“孔明井”的历史,则渐渐被诸葛亮凭借智慧选址凿井的传说掩盖了。
三、孔明信仰与仪式实践
如果说葛亮寨区域开发、人群交织的过程是村落历史的“真实”写照,那么围绕“孔明”而创造的一系列传说故事则是关于“历史”的另一种表述。
生活在葛亮的苗侗移民通过此种表述形成共同记忆和织造意义,同时通过建构神圣空间树立起孔明信仰,衍生出一套仪式与习俗,在特定的时间使用文化手段不断强化自己的族群身份与认同,并定义自身在区域社会的位置。
最初孔明只是一种说法,并不具备神性,也没有专门供奉的庙宇。
孔明庙在葛亮的建立,据称源于当地人的一个梦。
据说20世纪80年代一位梁姓侗民梦见孔明乘着一艘大船从都柳江上游漂来,漂到葛亮河滩后上岸,就不再往前走了。
侗民梦醒之后就去河滩边,看见河滩上有一根被江水推下来的大木头,于是认定这就是梦中孔明所乘坐的“船”,进而相信作为“神”的孔明又重返葛亮了。
于是,梁氏与罗、潘、吴几个姓氏一起筹措在葛亮建孔明庙。
关于这根木头葛亮村民有很多说法,有人说它被大水冲走了,也有人说它被埋在了河滩下,但是葛亮村民没人敢在此处锄地,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砍到木头了,后果是很严重的”.这个梦看似偶然,但相信梦境可以与神灵沟通,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预示作用,这是一个被生活在都柳江流域的苗侗人群所普遍接受的观念。
无论这样的梦境是否真实发生,但孔明庙的建立使孔明具备一种神圣性在村中被固定下来,这是事实。
将孔明、村寨与人群三者之间相联系的过程,对我们了解族群情感如何生成以及如何被族群中的个体所接受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可以说,葛亮族群情感的产生正是通过根植于当地人头脑中的文化观念和逻辑,再经由文化的再创造和象征性的沟通而建立。
孔明庙出现之前,闽粤籍移民已在葛亮寨修1作两个花炮并举行抢花炮仪式来祭拜神灵。
闽粤移民离开葛亮之后,这个节日在葛亮苗侗移民的操持下继续开展⑤.新中国成立后,这个节日一度停止,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恢复。
孔明庙修建后,葛亮寨决定为孔明增设一枚花炮,同时将花炮节解释为一个与孔明相关的节日,认为这是诸葛亮为了让少数民族地区寨与寨之间的关系友好、团结,才发明了抢花炮这一活动,从而为节日增添了新的话语与意义。
由此,葛亮的苗侗移民用孔明传说代替了原来花炮节与闽粤移民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且强调葛亮的花炮节比富禄的更加“灵验”.葛亮人将花炮节的习俗经过再解释,纳入到了自身的文化体系之中。
每年农历三月廿三,葛亮寨的村民乃至贵州贯洞乡、龙图乡、黎平等地侗寨和“七十”苗寨都会前往葛亮过节。
人们在河滩争抢花炮,是为了将神灵接入家中带来好运,抢到花炮的人家,必须将花炮抬入家中供奉一年,如同对待孔明一样祀奉花炮,并遵守一系列禁忌,直到次年花炮节再将“孔明”送回庙宇中。
除花炮节外,每逢春节葛亮村民也会去孔明井边烧香烧纸,并撒一把米到井水中,以求孔明保佑,而大年初一的凌晨,每一户都带着水壶到孔明井,努力争取在新年打到井中的第一桶水,以期顺利。
经过上述与孔明信仰相关的节日、习俗和仪式实践,葛亮苗侗移民形成了一套共同的观念和共同遵守的习俗与秩序,从而建立起了关于地方的知识及其对我群的看法,并在区域性的节日中加入了与孔明有关的内容,确立起身份的标识。
那些关于“过去”的“历史记忆”表述,通过仪式这样的象征方式和文化手段加以实践,转换为当下对族群的理解。
这些从节日、仪式中观察到的诸多复杂内容,正是不同时期葛亮寨苗侗移民在不同的境遇下,运用意义、象征、关系、秩序所织造出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图景。
四、结论
综上所述,葛亮寨的历史折射出的是特定的区域社会历史与人群互动过程,在都柳江下游这样一个多元人群交汇的地带,族群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一致,如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以及说“客话”的闽粤移民和真正的“土着”之间,身份呈现出暧昧的状态,他们不仅要处理现实而复杂的人群关系,而且文化的交汇也带来意义的交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并非纯粹被动地接受或调适自己与其他人群的关系,而是运用文化手段主动参与和创新。
这不仅是他们适应客观环境的动态过程,更是在自身文化逻辑中加入想象的创造过程。
表面上看,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不断对孔明这一符号进行演绎与创造,制造出碎片化的传说叙事、神圣空间以及复杂的习俗,但其背后却是族群成员通过文化手段建构自我意识与情感归属的过程。
通过将孔明与村落历史相结合,围绕孔明信仰进行仪式实践,来自四面八方的葛亮移民逐渐在心态上建立起一种对地方与“我群”的认同,进而得以联系为一个整体。
在今天的葛亮寨,我们仍能生动地观察到正在进行中的身份建立过程。
如在当下的花炮节中,原本没有穿着“民族服饰”习惯的葛亮村民开始从高坡或沿河的其他村寨中“订做”侗族服饰,女性也开始学习刺绣手艺。
从这些“恢复民族传统”的努力中,我们不能完全认定“族群”就是人们一种情境式的选择,但是当我们把“文化”带入族群的讨论中就会发现,人作为一个整体生活的行动者,在不同的社会以及文化的碰撞间,对自我有不同的认识与界定。
因此,族群意识的建构过程1会文化范畴中加以思考、分析,才能真正跳出巴斯以“边界”界定族群的限制。
标签:
上一篇:
澳大利亚足球中的族群政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