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docx
《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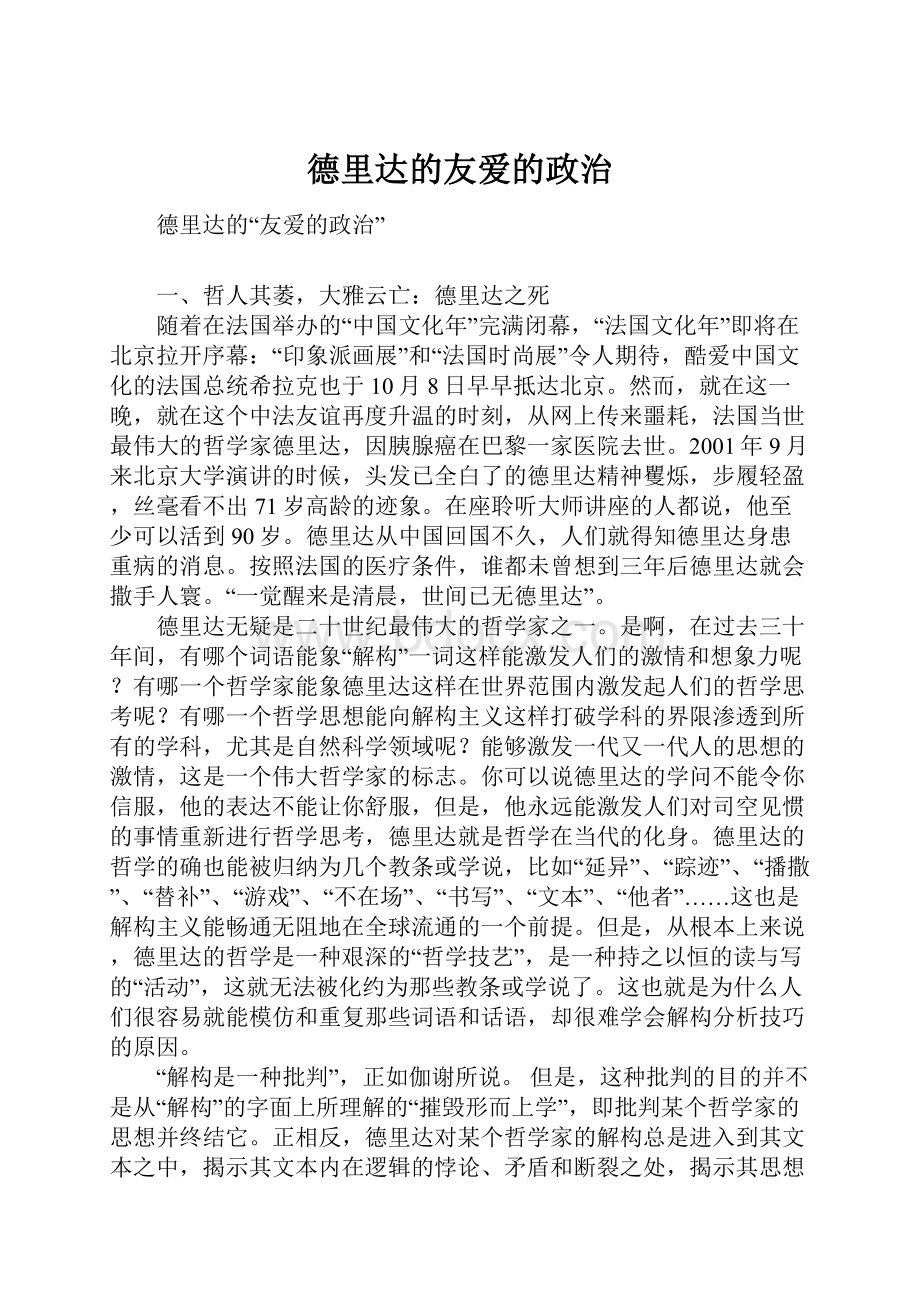
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
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
一、哲人其萎,大雅云亡:
德里达之死
随着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完满闭幕,“法国文化年”即将在北京拉开序幕:
“印象派画展”和“法国时尚展”令人期待,酷爱中国文化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也于10月8日早早抵达北京。
然而,就在这一晚,就在这个中法友谊再度升温的时刻,从网上传来噩耗,法国当世最伟大的哲学家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一家医院去世。
2001年9月来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头发已全白了的德里达精神矍烁,步履轻盈,丝毫看不出71岁高龄的迹象。
在座聆听大师讲座的人都说,他至少可以活到90岁。
德里达从中国回国不久,人们就得知德里达身患重病的消息。
按照法国的医疗条件,谁都未曾想到三年后德里达就会撒手人寰。
“一觉醒来是清晨,世间已无德里达”。
德里达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是啊,在过去三十年间,有哪个词语能象“解构”一词这样能激发人们的激情和想象力呢?
有哪一个哲学家能象德里达这样在世界范围内激发起人们的哲学思考呢?
有哪一个哲学思想能向解构主义这样打破学科的界限渗透到所有的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呢?
能够激发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的激情,这是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标志。
你可以说德里达的学问不能令你信服,他的表达不能让你舒服,但是,他永远能激发人们对司空见惯的事情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德里达就是哲学在当代的化身。
德里达的哲学的确也能被归纳为几个教条或学说,比如“延异”、“踪迹”、“播撒”、“替补”、“游戏”、“不在场”、“书写”、“文本”、“他者”……这也是解构主义能畅通无阻地在全球流通的一个前提。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德里达的哲学是一种艰深的“哲学技艺”,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读与写的“活动”,这就无法被化约为那些教条或学说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很容易就能模仿和重复那些词语和话语,却很难学会解构分析技巧的原因。
“解构是一种批判”,正如伽谢所说。
但是,这种批判的目的并不是从“解构”的字面上所理解的“摧毁形而上学”,即批判某个哲学家的思想并终结它。
正相反,德里达对某个哲学家的解构总是进入到其文本之中,揭示其文本内在逻辑的悖论、矛盾和断裂之处,揭示其思想隐秘的前提、隐含的修辞或可能性条件,揭示其陷入某种中心主义的思想困境。
因此,解构并不是简单地以“非主题”的方式在前人的哲学文本中揭示出前人所未曾见到的东西,比如说那些语言学的、精神分析的、人类学的、女性主义的新洞见,而是以一种使经典文本被激活的方式重新阅读和进入传统的经典文本。
德里达对某个经典哲学家的解构总是能激起人们以新的方式和新的视角重新阅读这些哲学家的激情,解构使那些庞然大物复活了。
“解构就是批判,而批判就是激活”,这就是德里达的伟大之处。
罗蒂愚蠢地假想他要和海德格尔、德里达去争谁是“最彻底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的皇冠。
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到,海德格尔与德里达都不是不学无术之辈,这两个引领二十世纪哲学潮流的人对哲学传统的熟悉和珍视,远非一个颠覆形而上学的尾随者和狂热分子所能理解。
与通行的印象相反,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不是为了彻底摧毁西方形而上学,而是为了激发西方哲学传统的新生。
德里达正是以这种方式扞卫着哲学传统,并将自身归之于其中。
德里达总是精心地选择自己与之对话的哲学家:
柏拉图、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索绪尔、海德格尔等。
就象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一样,德里达通过对那些经典哲学家的文本解构性的分析,激活了那些哲学家的思想,激发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进入那些经典和传统之中,激发人们在哲学之中和“哲学的边缘”重新进行哲学思考。
德里达的文本给人的那种精神的愉悦就在于,尽管你很难读懂他的文字,但是,你所读懂的和读不懂的都能激发你真正的哲学思考。
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结构主义研讨会上一举成名之后,他在法国的形象一直是作为五、六十年代鼎盛一时的结构主义运动的分裂者和终结者。
多斯在两大卷的《结构主义史》中,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词来标志“结构主义时代”之后的整个一个时代。
而费里和雷诺在《六八年的思想》中则把德里达定位于与福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拉康这些思想家同属于法国六八年学潮的那一代激进的“反人道主义”的哲学家。
他们给德里达戴上一顶“法国的海德格尔”的帽子。
到了八十年代,德里达在法国的影响已经减弱了,而在法国之外他的影响却远远要比在法国本土大得多。
耶稣说:
“先知在本地是没人尊重的”。
德里达在法国一直被学院派人士认为是一个诡辩论者,一个智者,一个怀疑一切的怀疑主义者,一个鼓励随意阅读的不严肃的人,一个不学无术的骗子,一个犬儒主义者,一个保守主义者……人们不禁会问:
难道他们竟无视德里达的思想的激进、对现实的积极关注、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和严密论证、对一种负责任的伦理和政治的扞卫吗?
他们难道从不去读德里达的书就肆意攻击他人吗?
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解构呢?
现在,大师已去,当年索邦大学和那些大学学院中保守的教授也已耆耆老矣,与大师之间的种种恩怨也该化解了。
他们应该将对后现代主义的厌恶与对德里达的尊重区分开,以重新审视德里达对于法国和我们的时代的意义。
随着福柯、阿尔都塞、巴特、拉康在八十年代初的五年间相继辞世,当年叱咤风云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大师们还剩下谁了?
到现在,他们应该发现,是谁带给人们如此多思想上的惊喜和震动?
是谁堪当法国二十世纪“哲学的辉煌”中的“最后一位大师”?
还有谁能在德里达的身后继续扞卫着法国哲学的光荣与梦想?
所以,他们应该珍惜德里达,把他视为法国的国宝。
可以预想,新的一轮对德里达思想的研究将在法国本土兴起。
这就是德里达的死亡所带来的和解。
德里达之死使他成为呼唤我们去聆听和理解他思想的允诺的“幽灵”。
他活着时候的形象带给人们“影响的焦虑”,并妨碍了人们心平气和地对待他。
现在,哲人日已远,应该还德里达一个“公正”了,不是法律上和名誉上的公正,而是向德里达的思想敞开友好的胸怀的“公正”,是给予一个死者无条件的“宽恕”的“公正”。
现在,德里达将作为一个“幽灵”而不断重新来到人们的思想之中。
因此可以说,德里达的死亡是他的生命的“替补”。
德里达在《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曾说过,“从始至终,列维纳斯的整个的思想就是沉思死亡。
”“永别”就是对他者的必死性的承认。
让我们说:
“永别了,德里达!
”
我们“重复”他思想的“踪迹”,我们接受他赠与我们的思想的礼物,我们也在“灰烬”中看到他的必死性,看到了他的思想被消抹、被覆盖的不可避免和脆弱性。
因此,保留他的死亡留下的终必消亡的思想“踪迹”,这是我们对这位再无法与之面对面交流的人的“记忆”和“哀悼”,也是我们在背叛的“可能性”之中对这位永远“不可能”在场的死者无条件的“忠诚”和“责任”。
这是他教给我们的。
把德里达思想的踪迹实体化,把作为激发人思考并纠缠于人的思考的幽灵可见化、肉身化,甚至给他披戴上“解构主义之父”的皇冠和新装,把他激进的思想彻底学院化、教条化、经典化、官方化、安全化,再把他送入哲学神圣家族的殿堂的神龛之中,这些闹剧无疑都消解了“哀悼”本身,是最糟糕的一种“哀悼”。
哀悼必须恰如其分,那就是以进入德里达思想之中的方式守护着他的思想的灰烬和踪迹。
因为死亡带来了哀悼和友谊,所以,在德里达之死之时,适宜的是与德里达一起去沉思“哀悼”与“友谊”。
二、解释德里达的三种模式:
海德格尔、德曼与列维纳斯
“德里达的幽灵”无法被划归为某个特定的学院制度或思想体系之内,其思想内部也存在着矛盾的、悖论的、异质性的甚至是自我颠覆性的成分,这些都不应该被简化为某种单一解释模式,而应该为其保留其文本的可写性和无限再解释的权利。
对德里达思想流行着三种解释模式。
第一种是在前面讲过的把德里达视为彻底地颠覆传统形而上学之人。
这种解释模式我称之为“海德格尔式解释”,比如哈贝马斯、费里和雷诺就把德里达视为“尼采-海德格尔”的解构形而上学事业的传人。
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的事业在于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它的语音中心主义,能指中心主义,阳性中心主义,在场中心主义等等。
德里达关于不在场对于在场的优先性、将来对于现在的优先性、有限性的悖论等思想无疑来源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
但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其实更依赖于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索绪尔语言学的重新解释。
此外,也很难说尼采在这方面对德里达的影响就比海德格尔要小。
第二种解释模式是把德里达视为打破文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身处文学与哲学之间的准哲学家。
这种注重文本的互文性、自我解构和自由游戏,以及意义的延异-播撒-增补-踪迹-重复-涂抹的解释模式我称之为“保罗·德曼式解释”。
在《六八年的思想》中,在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差异”的视角对德里达的“延异”和“播撒”的概念做了一番假充内行的考察之后,费里和雷诺说,德里达在解构了“主体”之后,“所有剩下的就是文学了”。
这个理解大成问题,但他们也道出了一个基本现象:
德里达在八十年代之后的影响力主要在美国而不在法国,而且主要在文学领域而不在哲学界。
德里达对“文字与声音”、书写的“踪迹”与意义的“播撒”、二元对立的替补、文学与“白色的隐喻”、文本与差异、“双重场景”的思考,对萨德、马拉美、卡夫卡、乔伊斯、塞林纳、贝克特、阿尔托、博尔赫斯、巴塔耶、布朗肖、蓬热、热奈的解读,还有德里达的写作那种决不混同于他人的鲜明的文体风格,以及着有《明信片》和《丧钟》这样的超级文本,再加上罗兰·巴特以及文学批评中的“耶鲁四人帮”、芭芭拉·约翰逊、乔纳森·卡勒、罗蒂的呼应和推波助澜,人们很容易得到与费里和雷诺相似的印象。
的确,现代文学经验更好地证成了德里达所钟爱的关于哲学、文学、语言学、文本和写作的那些主题:
语言的差异性和创造性、文本性或文本事件、文本的游戏与愉悦、写作实践或可写性、能指的自主性、踪迹和意义的播撒、文学与文学批评的交互性、修辞性与虚构性、反讽性和隐喻性、签名的独特性与自传等等。
德里达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看到了那种通过透明的、无歧义的语言,即几何学的、数学的、科学的、现象学的纯粹语言再现历史的梦想,他转而向那些现代作家以隐喻性的语言、复杂的修辞、多义与歧义、虚构和自我解构的形式去重现和包容历史的努力致敬。
德里达深深迷恋于现代文学作品及其自我意识,他从中看到了一种颠覆哲学、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禁忌、边界和制度的力量、激情和愉悦,一种文学事件的独特性与重复性、虚构性与文本性。
德里达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不仅给出了一种不同于“新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或“读者反应批评”等等的文学批评的技艺,而且还揭示了那些“写得好”的文本的“自我解构性”,正如德曼经常做的那样。
尽管如此,文学在德里达的哲学中也并不拥有什么对抗哲学的特权,因为德里达通过那些“表现的危机”、“语言的危机”和“文学的危机”中的现代派作品提出了“文学是什么?
”或“文学从哪里来?
”等等关于文学本体论、“文学建制”或“文本的法则”的问题。
德里达对文学及其建制、文学史及其同形而上学观念、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样报以解构的态度,质疑其历史性构成,追问文学事件以其独特的书写方式对历史事件的独特的责任和义务。
德里达看起来象他那些文学批评家朋友一样钟爱文学、文本和文字游戏,但是他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不过他的“哲学语法”更接近于文学和文学批评而已。
对德里达思想的这两种解释模式涵盖了德里达的早年哲学,到此为止,我们会得到“就剩下文学了”的印象。
而第三种流行的解释模式更多地把晚年德里达的思想考虑进来,这就是德里达的关于“他者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这一解释模式我称之为“列维纳斯式解释”。
这种模式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海德格尔模式和德曼模式能截然分开,而且,它也使得德里达能避免“海德格尔事件”和“德曼事件”的陷阱。
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聚拢”和同一性思想的批判就来源于他的老师列维纳斯的他者、差异、异质性、不可还原性、非关系性等思想。
在扞卫他者、差异和异质性这方面,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远远地走在了德勒兹、福柯、利奥塔、拉库拉巴尔特、南希、马里雍这些法国新潮哲学家的前面。
列维纳斯强调他者的不可还原的、不可“总体化”的原初的给予性和无限异质性:
他者的踪迹,他者的不可见的“面孔”,他者的“外在性”,他者的超越性,他者的死亡,对他者的义务,总之,“绝对的他者”。
德里达从列维纳斯及其好友布朗肖的思想中发展出他自己的“幽灵政治学”、“记忆政治学”,非关系性的“他者伦理学”以及没有肉身和精神的幽灵、“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没有本体化和目的论的末世论”、“没有宗教的正义”等思想。
从列维纳斯的思想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德里达晚年思想中的那些核心概念:
宽恕、友爱、好客、到来的民主、新国际等。
三、友爱的政治:
好客、到来的民主与新国际
德里达曾因秘密讲学而在捷克被捕入狱,他反对南非种族歧视、支持曼德拉的解放事业,他为建立国际作家议会而奔走,在七十年代他发起哲学教学研究小组运动、创立国际哲学学院,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事业失败的时候他站出来谈论马克思……尽管如此,德里达并不是一个萨特式或福柯式的知识分子。
长久以来,他的政治姿态都基于他的怀疑主义的与修辞学的解构立场。
不过,长达二十年的解构实践磨练了他的技艺,使他可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一种非政治化、非教条主义的方式面对“政治”,质疑“何谓政治”以及政治的限度,质疑“何谓法律”以及“何谓法律之外的正义”、《马克思的幽灵》、《法律的力量》)。
德里达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十多本大大小小的着作表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解构的“政治转向”或“伦理转向”。
在这些着作中,唯一带有“政治”字眼作为标题的着作是《友爱的政治》。
这本书由“噢,朋友们,没有朋友”这句被蒙田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箴言所引出千变万化的解释分析编织而成,展示出德里达高超的解释技巧和不羁的思想灵感,出版之后就成了九十年代西方哲学的一本经典。
德里达在《多义性的记忆:
为保罗·德曼而作》与《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所表现的对德曼和列维纳斯的友谊以及对这一友谊的沉思堪称《友爱的政治》所描述的友爱的典范。
然而,《友爱的政治》在思想上却与《马克思的幽灵》是姊妹篇,构成了德里达的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文本。
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路数是通过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进入到无限的他者政治之中,通过一种完全不同于整个西方传统友爱观的新型友爱来谈论一种新型的政治,通过对他者的无条件的“好客”来谈论“到来的民主”和“新国际”。
而“新国际”正是《马克思的幽灵》的主题。
在向德里达之死表达哀悼和友谊的场合,富有教益也倍增悼亡之感的是回忆他如何谈论“友爱的政治”。
在《友爱的政治》中,象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一样,德里达更多地从布朗肖那里吸取思想的灵感,以阐发他的友爱观,并解构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观。
通过解构从希腊、罗马到基督教,从法国大革命到尼采的西方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观念,德里达质疑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把友爱作为一种政治参与经验的传统民主概念,进而质疑以权力、民族、主权、合法性、代议制等为核心的政治的概念,提出了他自己的“好客”、“到来的民主”和“新国际”的新政治哲学。
对于德里达来说,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概念实际上息息相关于民主的政治修辞学,而从日常生活到国际政治中,民主政治修辞学无疑都具有的核心地位。
这就是德里达在《友爱的政治》中为什么要谈论“友爱”,为什么要谈论“政治”。
在西方传统思想史中,友爱是政治哲学中的边缘性概念,它更多地属于伦理学范畴。
亚里士多德是在《伦理学》中讨论了友爱的德性。
虽然《伦理学》中最高的友爱是基于德性的,是两个有德性人之间的友爱,是非政治的,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其政治学的一部分。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友爱是正义和城邦民主政治经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义离不开城邦中平等自由的公民间的友爱,它才是城邦的基础。
然而,德里达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友爱的德性是年轻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友爱,而非男女之间和女人之间的友爱。
而罗马的公民共和友爱就象现代的“同志”般的友爱一样,也是男人之间的“公共的友爱”。
至于基督教的友爱,同样是上帝子民之间的兄弟之爱,法国大革命的“博爱”是这一概念的世俗化形式。
通过对友爱的“解构性的谱系学”的分析,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概念是男性中心主义的。
对于德里达来说,对男性中心主义的质疑就已是一种政治行动了。
因为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概念完全基于某种政治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非常明显的是“城邦”及其“公民”的概念,在其它情况下是国家、民族、地域、主权、阶级等概念。
德里达认为,基于这些认同的政治就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纳粹和保守主义的共同起源。
因此,解构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以及象海德格尔哲学对存在的爱,是解构这些根深蒂固的政治概念的前提;而解构这种爱有差等的友爱又依赖于解构“有限数量”的友爱所依赖的政治共同体的自然根基。
德里达解构“友爱的政治”也要确立自己的“敌人”,这个敌人既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不是蒙田、尼采、海德格尔,而是书中以四章的篇幅着重讨论的德国公法学家和政治神学家施米特及其“敌人的政治”。
在德里达看来,施米特是二十世纪最顽固不化的国家主权论的倡导者和蛊惑者,其政治的概念乃是自由民主最大的敌人。
因此,要呼唤一种新的政治的概念和新的国际法的概念,就必须解构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既要解构其作为政治的标准的“敌友之分”的概念,也要解构其基于国家和主权概念的政治的概念。
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认为,“政治的”是“国家的”,“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只有国家才能“决断战争和敌人”。
德里达认为必须解构这种建立在国家主权概念之上的政治的概念。
于是,德里达以他者和将来之名跨越各种固有的自然限制,允诺和呼唤一种承认无限的异质性、尊重无限的差异的“到来的民主”:
一种无限友爱的民主,一种无限民主的友爱。
于是,“到来的民主”就成了“为无限的异质性疲于奔命的解构”。
当然,“到来的民主”并不是期待什么“未来民主”,而是指出民主是一个事件性和历史性的过程,是对超越公民概念、民族国家概念、主权概念和大国制定的国际法的概念以及对与从政制、主权、组织来理解民主全然异质的民主的允诺和呼唤,是积极承担民主的责任和紧迫感。
德里达的“到来的民主”的根据在于从本体论上来讲的对他者的无限的责任和对他者无限敞开的“好客”,这是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的“神圣的他者”政治化了。
对于施米特来说,政治中最重要的不是“绝对的他者”,不是对陌生人“好客”的“友爱”,而是政治中的“敌人”。
政治行动不能取消“敌友之分”,人类日常语言也清楚地显示了所有根本性的政治概念的敌对性,甚至基督教的“爱你的敌人”也愈加清楚地预设了“敌友之分”。
如果取消了“敌友之分”,尤其是取消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敌友之分”的话,战争与和平、内政与外交、武力和文明的区分,以及国家、主权、战争、敌人等概念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这实质上就是以“人类”、“权利”、“和平”、“秩序”、“责任”、“未来”、“正义”等名义消除了“政治”。
徳里达认为,施米特犯了自由主义的老毛病,他总把政治领域视为独立的、纯粹的、自律的、与其它领域有着根本的区分原则的“政治”本身。
正因如此,施米特才坚持“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甚至不惜为政治而“决断”出至少一个敌人。
施米特认为:
“在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上,在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世界上,将不存在敌友之分,因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
……战争作为最极端的政治手段揭示了那种支撑着所有政治观念的可能性,即敌友之分。
”在徳里达看来,施米特并没有追问战争和敌人的起源,因为不仅存在着在敌对性的概念之间无限播撒的语汇,而且也存在着大量的敌友之间无法绝对分立的延异,难道一定要将其极端化为战争状态吗?
而施米特从战争和敌人来定义政治,无非是对国家的主权的认同的极端化,它仍然建立在对祖国、大地、人民、血缘、种族以及政治共同体的其它自然属性的认同之上,从而隐含地建立在传统的友爱的概念之上。
徳里达认为,施米特用“战争的可能性”或“政治的严峻性”这一含混的哲学概念掩盖了敌友之分的复杂性。
施米特认为政治统一体区别于其它组织的特征就在于它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德里达认为,如果这样,那么“敌友之分”必须推到彼此杀死对方的可能性上才可能让敌人成为真正的、严肃的、政治上的、公共的敌人。
这种在道德上并不邪恶、经济上并不竞争、审美上并不丑陋、人性上并不缺乏尊严甚至是更有尊严的敌人,最后只能是为了生存和种族而与之斗争。
然而,这就意味着存在着超出“敌我之分”之外的政治标准,即自然的生存或种族的生存。
施米特最终仍然是诉诸作为政治统一体的民族或国家的绝对性,而这正是德里达的“新国际”政治学所要解构的首要目标。
德里达质疑了整个西方男性中心主义的友爱概念的限度,尤其是作为这种友爱概念的政治基础的城邦概念和公民概念;德里达也质疑了施米特的“敌友之分”的可能性,尤其是其决断敌人的基础和权力,即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
象哈贝马斯那样,德里达从康德的“永久和平”学说中也学到了“世界公民权利”的概念以批判施米特。
德里达特别借用了康德的“好客”概念,并将其“世界公民的政治学”的谱系一直追溯到晚期希腊的斯多亚派和圣保罗的“四海一家”的观念。
按照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学,“好客”就是无条件地接待他者,允许他者进入我的空间,无论他人是“公民同伴”,还是“非公民同伴”,甚至尤其是后者。
于是,建立在“世界公民权利”上的“好客”就颠覆了整个西方传统的友爱的伦理学和友爱的政治学。
这种无条件的“好客”的“世界公民权利的政治学”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国际”概念,这就是《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自由市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国际”概念。
“新国际”并不是说不同国籍的人以新的方式联合起来,而是说要以新的“没有政治的政治”去重新理解人权、国籍、国家、国际法和民主等司空见惯而在今天已经大成问题的观念。
这就是德里达的新的“友爱的政治”所允诺和呼唤的东西。
【注释】
1RodolpheGasché."DeconstructionasCriticism",InventionsofDifference:
OnJacquesDerrida.Cambridge,MA:
HarvardUniversityPreass,1994.p22.参见,TheTainoftheMirror:
DerridaandthePhilosophyofReflection.Harvard: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
2参见,Fran?
oisDosse.Histoiredustructuralisme(2vol).Paris:
éditionsLaDécouverte.1991.HistoryofStructuralism.Minneapolis:
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7.《从结构到解构》,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当然,没有多少人会同意多斯把德里达当做"超结构主义者"的提法。
3LucFerry&AlainRenaut.LaPensee‘68:
Essaisurl‘antihumanismcontemporaine.Paris:
Gallimard,1985.FrenchPhilosophyoftheSixties:
AnEssayonAntihumanism.trans.MaryCattani.Amheret:
The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1990.德里达十分恼火他们给他扣上的头衔。
显然,没人会喜欢"法国的尼采"、"法国的马克思","法国的弗洛伊德"这些标签。
4德里达论尼采,参见,JacquesDerrida."TheQuestionofStyle",trans.RubenBerezdivin,inTheNewNietzsche:
ContemporaryStylesofInterpretation.ed.DavidB.Alli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