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西汉的酷吏.docx
《也论西汉的酷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也论西汉的酷吏.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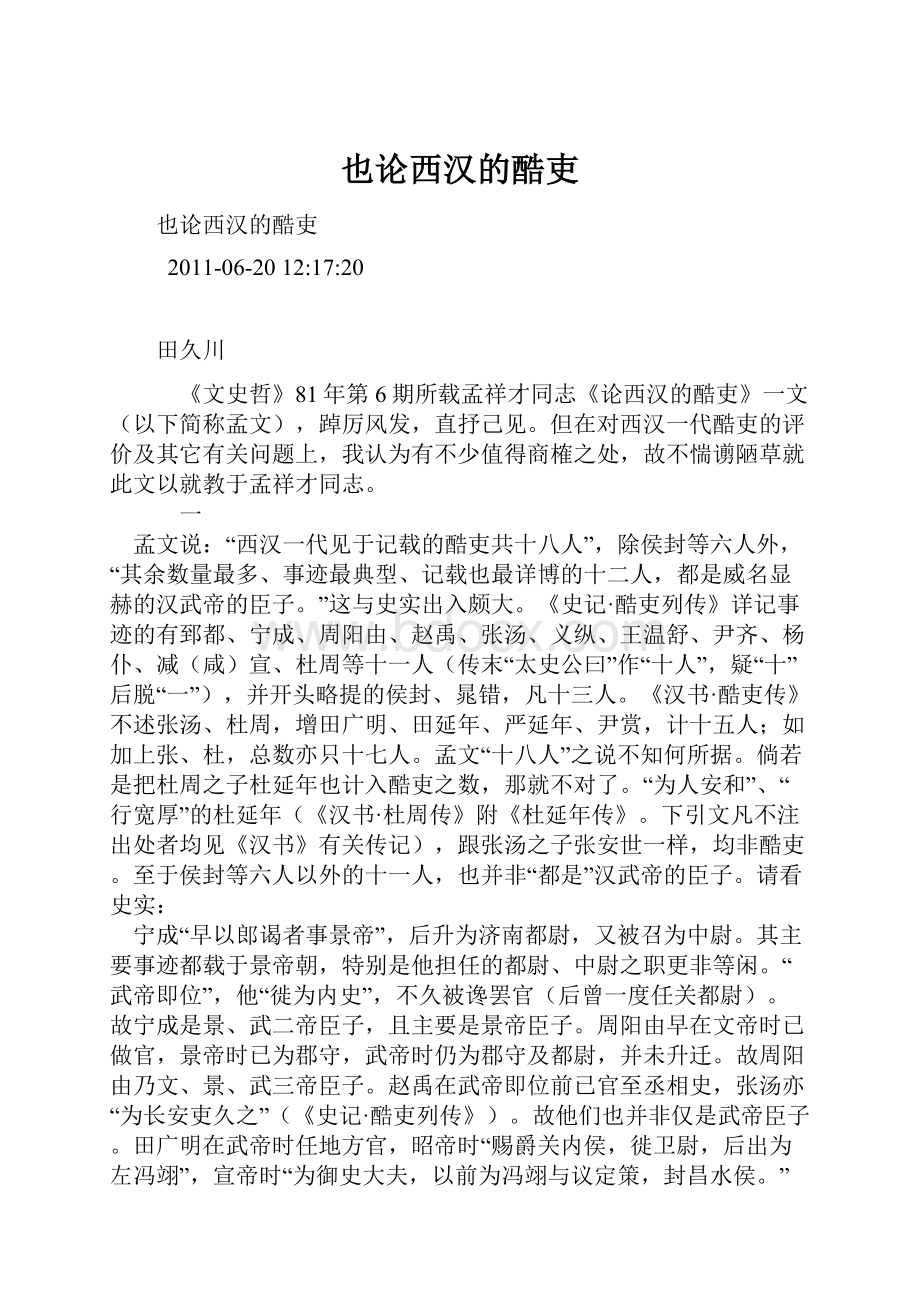
也论西汉的酷吏
也论西汉的酷吏
2011-06-2012:
17:
20
田久川
《文史哲》81年第6期所载孟祥才同志《论西汉的酷吏》一文(以下简称孟文),踔厉风发,直抒己见。
但在对西汉一代酷吏的评价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我认为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故不惴谫陋草就此文以就教于孟祥才同志。
一
孟文说:
“西汉一代见于记载的酷吏共十八人”,除侯封等六人外,“其余数量最多、事迹最典型、记载也最详博的十二人,都是威名显赫的汉武帝的臣子。
”这与史实出入颇大。
《史记·酷吏列传》详记事迹的有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咸)宣、杜周等十一人(传末“太史公曰”作“十人”,疑“十”后脱“一”),并开头略提的侯封、晁错,凡十三人。
《汉书·酷吏传》不述张汤、杜周,增田广明、田延年、严延年、尹赏,计十五人;如加上张、杜,总数亦只十七人。
孟文“十八人”之说不知何所据。
倘若是把杜周之子杜延年也计入酷吏之数,那就不对了。
“为人安和”、“行宽厚”的杜延年(《汉书·杜周传》附《杜延年传》。
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见《汉书》有关传记),跟张汤之子张安世一样,均非酷吏。
至于侯封等六人以外的十一人,也并非“都是”汉武帝的臣子。
请看史实:
宁成“早以郎谒者事景帝”,后升为济南都尉,又被召为中尉。
其主要事迹都载于景帝朝,特别是他担任的都尉、中尉之职更非等闲。
“武帝即位”,他“徙为内史”,不久被谗罢官(后曾一度任关都尉)。
故宁成是景、武二帝臣子,且主要是景帝臣子。
周阳由早在文帝时已做官,景帝时已为郡守,武帝时仍为郡守及都尉,并未升迁。
故周阳由乃文、景、武三帝臣子。
赵禹在武帝即位前已官至丞相史,张汤亦“为长安吏久之”(《史记·酷吏列传》)。
故他们也并非仅是武帝臣子。
田广明在武帝时任地方官,昭帝时“赐爵关内侯,徙卫尉,后出为左冯翊”,宣帝时“为御史大夫,以前为冯翊与议定策,封昌水侯。
”故田广明系武、昭、宣三帝臣子昭昭然。
以上宁成等五人,至少不应整个算做武帝臣子。
孟文将其统统算在武帝账上,另外再加上一个不知姓甚名谁的人,使武帝朝的酷吏总数一下子膨胀到“十二人”,这显然非一时疏忽所致。
究其原委,盖欲以武帝时酷吏特多的“数据”,来证明其结论:
只有在“汉武帝那灿烂的时代”,“酷吏那曼陀罗般的花朵”才能够“怒放”;“功业显赫的英主”汉武帝,“差不多同时也是一个暴君”。
质言之就是:
上有汉武帝式的暴君,下才有王温舒式的酷吏。
孟文断言:
“在封建专制时代,正象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意味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一样,一个功业显赫的英主差不多同时也是一个暴君,汉武帝正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汉武帝究竟是不是英主加暴君,这里暂置不论,仅就孟文的一般性结论而言,恐非确论。
贞观年间的唐朝政府亦可谓“强有力”矣,它“意味着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吗?
唐太宗也算得上“一个功业显赫的英主”了,他“差不多同时也是一个暴君”吗?
若按孟文的逻辑,是否可以说只有虚弱无力的政府才意味着轻微的赋役,尸素其位的庸主才差不多同时也是一个仁君呢?
孟文说:
“巍巍功业与苛暴酷烈是汉武帝矛盾统一体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
”我认为“功业”与“暴酷”不能构成什么人“矛盾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因为前者指的是其人的成就,后者指的是其人的政治品格(或手段),两者所属的范畴不同,怎能凑在一块儿去构成什么“矛盾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至于孟文所谓“缺了这一面,也就没有了另一面;否认这一面,另一面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云云,显然是又把“暴酷”与“功业”从“两个侧面”进而变出了“前因后果”,使二者生出了“必然的内在联系”之类。
汉武帝其人其事是否可以概括为坏手段加好效果,亦可暂置不论,仅就孟文极口称赞的汉宣帝来说吧:
他“躬亲万机,励精图治”——并不“苛暴酷烈”;而当时却呈现着“汉王朝中兴之局‘政平讼理’的穆穆气象”——却是“功业巍巍”。
由此可见,“缺了(苛暴酷烈)这一面,也就没有了(巍巍功业)另一面”之说是难以站住脚的。
“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古人这个说法倒是比较合乎汉武帝的实际情况。
“外施仁义”与“外施暴酷”当然不是一码事。
尽管武帝也有暴酷之为,但考诸史实,还是“外施仁义”即“假仁假义”者居多。
尽人皆知,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皇帝能假仁假义干出一些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就算是不错了,真正实行仁义的皇帝是没有的,就连孟文赞许的昭宣二帝亦概莫能外。
昭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汉书·元帝纪》),执政的权臣霍光也坚持“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汉书·循吏传》)。
宣帝自己承认“民多贫,盗贼不止”,他在训斥太子时更毫不掩饰地声称:
我们汉家自有法度,向来就是杂用霸(刑名)王(儒)道,怎能纯讲仁义儒术(《汉书·元帝纪》)!
如果说昭、宣是什么“仁君”而非武帝式的“暴君”,恐怕不过是多搞了点“外施仁义”罢了。
退一步说,就算是武帝朝比昭、宣朝多了两三个酷吏,那也谈不上是什么“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
武帝在位53年,比昭宣二帝在位时间总和(37年)还要长得多,而当时匈奴、诸侯王、豪强、富商等重大社会问题多而且剧,不奋力解决不行;要奋力解决,光“外施仁义”也不行,难免要多用几个“风行霜烈”的所谓“酷吏”来干事。
到他死时,这些问题有的基本解决,有的有所好转,昭宣叨其余光,麻烦自然减少,由张而弛,条件具备,理固当然。
孟文说“汉武帝时代造就了酷吏大量生长的肥沃土壤”。
“土壤”是“时代”造就的,但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
“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39页),孟文也曾说过“汉武帝那灿烂的时代”。
由这个灿烂时代造就的肥沃土壤之上,不单单生长着“大酷吏”张汤之属,也还生长着“大经学家大政治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大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和“大音乐家李延年”等“西汉一朝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上引书)。
张汤其人如果算不上一个大政治家,至少也够得上大政治家汉武帝的一个十分得力的、当之无愧的“大助手”(详后)
二
关于酷吏的本质及酷吏活动与封建法律的关系问题,孟文在作了一般性论述后,具体分析了西汉酷吏的四个“特点”。
对此我有如下看法:
第一,西汉酷吏并非仅仅是“皇帝追求习惯权力的忠实工具,因此,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受封建成文法的约束,他们敢于公然蔑视封建法律而任意胡为。
”而应该说:
他们主要是统治阶级维护法定权力的忠实工具,其活动一般还是要受封建成文法的约束,他们一般也不敢公然蔑视封建法律而任意胡为。
孟文引杜周答客问的一段话:
“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然后分析说,“你看,在酷吏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家根本大法,皇帝的任何屁话都是金科玉律,他的随心所欲也就是神圣的法令。
”首先应指出,“国家根本大法”即“国家的总章程”或“规定国家根本制度的法律”,一般即指宪法,这是一个近代法律学的概念,孟文将它用到西汉那个时代是不妥当的,因为那时确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家根本大法”。
杜周所说的“律”是指刑法典,“令”特指对刑法所做的具体规定,所谓“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是也(《旧唐书·职官志·刑部》),也就是高祖时萧何所制定的《九章律》,武帝时赵禹、张汤所条定的律令三百五十九章之类。
从杜周所言,能否得出孟文那样的结论呢?
不能!
杜周说的是:
三尺法是哪里来的?
是皇帝制定的,但它并非既定不变之物——前主著律,后主疏令,都是按自己的是非标准搞的。
究竟执行前主的还是后主的?
作为法官当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是,执行后主之法。
难道谁还能舍弃今法去执行“古之法”吗?
从理论上说,杜周的上述讲法是站得住脚的。
同时可以看出杜周一类酷吏并非“敢于公然蔑视封建法律”、“不受封建成文法的约束”而任意胡为,因为他们所遵奉的后主之“令”,并不是孟文所讥笑的“皇帝的任何屁话”,而是同前主之“律”一样,都是封建法律,而且也都是封建成文法。
实际上西汉酷吏的多数人是重视法律、通晓法律、执法不阿的。
郅都以“奉职死节官下”自励,“致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赵禹“据法守正”,“见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并奉诏与张汤“论定律令”;义纵“直法行治”;尹齐执法如郅都;咸宣“以重法”绳不法下属;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力行法治;张汤、杜周、咸宣、赵禹等皆被称为“无害”——“谓既通晓律令文而不深刻害人也”(陈直《史记新证》第188页),“言无人能胜之者”(《汉书·赵禹传》颜注);等等。
至于周阳由“挠法”活其所爱,“曲法”灭其所憎,确系破坏法律,但他毕竟不敢公然全弃法律,只是在对法律“挠”或“曲”以后售其奸宄。
法官随己意或上意挠曲法律的现象,司空见惯,周阳由不过突出一些罢了。
由此概括出西汉酷吏都具有“公然蔑视封建法律而任意胡为”的“特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孟文说:
“只要一切都是围绕着皇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本利益”,酷吏“任何丧尽天良的作为也是既合理又合法的”。
但是,封建法律的本质正是体现着“皇帝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本利益”,而“围绕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根本利益”也正是围绕着封建法律本身!
由此怎能得出“酷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法外的特殊人物”并且“带头破坏”封建法律这类结论?
再者,孟文既已肯定酷吏的任何作为是“既合理又合法”,却又马上断言酷吏的作为主要体现的是“法外的封建特权,而不是封建法律本身”,前后岂不自相矛盾?
总之,我与孟文看法相反,认为西汉酷吏的某些酷行主要是封建酷法所使然,体现着封建法律本身。
第二,“酷吏以杀伐为手段,治狱特别残酷。
”然而是否还要明确:
酷吏之酷用来镇压劳动人民,是罪恶,要谴责;而用来对付豪强恶霸、富商大贾、贪官污吏、不法权贵、野心诸侯王以及市井之内的“没毛大虫”之类,则是功劳,苛责怒斥是大可不必的。
因为这些家伙的残酷,比些许酷吏的残酷要“特别”多少倍。
以酷吏之酷对付彼等之酷,谓之“以毒攻毒”,可;谓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亦未尝不可。
为了论证酷吏“治狱特别残酷”的“特点”,孟文列举了几个酷吏的罪状以为论据。
我对此看法不尽相同,故一一提出加以讨论:
1.张汤。
他“与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深文”,使法益苛,这当然无庸讳言。
但他与赵禹为九卿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义纵传》)。
他“排富商大贾”、“{K23A40.JPG}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所治“即下户羸弱”,则必另想巧法让皇帝减免其罪。
这种“抑强扶弱”的精神,在封建官僚群中是很少有的,那些谀强凌弱的滥官庸吏无法望其项背。
“舞文巧诋”当然不好,但对象是可恶的豪强。
那些疯狂兼并而又根粗腰硬、巧诈凶狡的“大鲨鱼”们,已经是“常法不能制”了,大概不“舞文巧诋”也不能使之落入法网罢!
可见张汤之酷,也酷不到哪里去。
2.赵禹。
他初虽“酷急”,然“至晚节”,“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名为廉平。
”(并见前述)
3.宁成。
“其治如狼牧羊”——这是那位“为人意忌、外宽内深”、经常公报私仇的公孙弘说的。
“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这是“关吏税肄郡国出入关者”的相诫之语,这些人中当有不少是贪官污吏、奸商政客,怕宁成胜过怕乳虎,恐非坏事。
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犯法”,景帝闻宁成“酷”名,即召为中尉,弄得“宗室豪桀人皆惴恐”(孟文第三部分将此事移到宁成做济南都尉时,误);武帝徙成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并使其“抵罪髡钳”。
这说明宁成“酷”得好。
哀平之际,若有此等酷吏,则外戚之类或许不至于那么猖狂。
4.义纵。
他少年时“为群盗”。
照孟文第三部分把“盗贼”、“群盗”都看作起义者的观点,则义纵也是一个起义者出身的人。
初为上党郡中令,“治敢往,少温藉,县无逋事,举第一”;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连太后外孙也难逃其“酷”;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为南阳太守,法加土豪宁氏,“破碎其家”,搞得另外两土豪“孔、暴之属皆奔亡”;为定襄太守,一日杀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对最后一事,孟文亦持完全否定态度,我不敢苟同。
其一,定襄是汉匈交战前线的军事重镇,元朔四年匈奴侵定襄等三郡,当地形势紧张,此后数年间卫青、霍去病“军数出定襄”击匈奴,而“定襄吏民乱败”,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迅速解决问题,否则抗匈战争必败,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关键时刻,武帝选调义纵为定襄太守,大是。
义纵至则严惩犯罪分子,是形势之所迫,属于特殊情况。
其二,原先入狱的二百余名重犯,竟有二百余名“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义纵捕之,完全有理合法;经审讯,认定私入相视者犯有“为死罪解脱”之罪(这完全有可能),按律当斩,义纵尽杀之,并非“视法律作废纸,以人命为儿戏”的兽性大发作。
其三,义纵对四百余人是“奏请得报而论杀”的(本传颜注),并非因性酷而擅杀。
5.王温舒。
他做广平都尉,“广平声为道不拾遗”;做河内太守(孟文误作河南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
”明明是“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
”而孟文却说成“相连坐千余家”,“全部杀掉”。
6.严延年。
“为人短小精悍,敏捷于事,虽子贡、冉有通艺于政事,不能绝也。
”他对忠节之吏“厚遇之如骨肉”,“治下无隐情”。
宣帝时,涿郡先后几任太守都是窝囊废,郡中豪强猖狂至极,东、西两高氏尤甚,谁都怕他们,咸曰:
“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孟文第三部分作“勿负大豪家”)。
两高氏豢养一群盗贼,称为宾客,纵其抢掠并加窝藏,“吏不敢追”,以致强盗益多,郡人张弓拔刀才敢走路。
延年被派往任太守,至即治两高氏罪,“穷竟其奸,诛杀各数十人。
郡中震恐,道不拾遗。
”他做河南太守时,“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
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
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内之。
”“令行禁止,郡中正清。
”孟文不管这些,只把“屠伯”一类中伤者语拿出来以证明严延年为人之酷,未免失之偏颇。
7.郅都。
都为人“勇有气”,“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
”“济南{K23A41.JPG}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拜都为济南守。
至则诛{K23A41.JPG}氏首恶,余皆股栗。
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
”为中尉时,“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苍鹰”这个徽号明明是城狐社鼠们畏憎郅都执法不阿而送给他的,而孟文却偏要说成是因为他“治狱特别残忍”才得到的,既曲解史实,又不讲是非。
老实说,郅都治狱谈不上什么“特别残忍”,即使对{K23A41.JPG}氏那样的大恶霸,他也不过诛其首恶而已。
唐权德舆《酷吏传议》就曾指摘司马迁以郅都冠《酷吏列传》是缺善善恶恶之心,认为郅都不是酷吏。
其实司马迁对酷吏之酷并不一概笔伐,对酷吏基本上是肯定的(详后),他把郅都列为酷吏之冠是并不奇怪的。
还有几个酷吏之“酷”,孟文未曾提到。
如晁错之“酷”于除害兴利,尹齐、咸宣、田广明、田延年、尹赏等之“酷”于诛锄豪强和惩治恶棍,等等。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列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从一个侧面来说,酷吏之酷是作为豪强之强的对立物产生的,或者说是豪强之强逼出来的。
要对付常法不能制、二千石莫能制的大豪强,不用酷吏别无他吏,故何处豪强闹得凶,酷吏就在何处干得猛;武帝等敢于放手让酷吏去诛锄豪强,正是其“英主”之“英”的一种表现。
其二,穷凶极恶的豪强不仅是封建国家的祸害,而且更是劳动人民的死敌,酷吏风行霜烈、从重从快地惩处他们,对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保护社会生产力是有益的;特别是一些酷吏在摧折豪强的同时还能“扶助贫弱”,更是难能可贵。
酷吏锄豪强,就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其三,西汉的多数酷吏实是精明强干的干吏、能臣。
其四,因此应该说西汉的多数酷吏主要不是以“治狱特别残酷”为其特点,而是以对豪强残酷无情为其特点。
第三,西汉的多数酷吏是刚直不阿、比较清廉的,是廉吏、清官。
孟文把“胁肩谄笑、阿谀献媚、贪脏枉法”作为西汉多数酷吏的又一“特点”,并以张汤等五人为例;而尹齐、义纵、郅都“几个正直骨鲠之士”在酷吏群中“实在不过凤毛麟角而已”。
这是故意贬抑。
事实是除尹齐等三人外,还有:
“为人廉裾,为吏以来,舍无食客”,连公卿造请都“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作为法官,这是特别重要的“职业道德”和政治品格)的赵禹;敢于纠弹权臣,使“朝廷肃然敬惮”的严延年;“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为求“万世之利”而以身殉国的晁错。
张汤虽“以知(智)阿邑人主”,却能推功揽过,荐贤举才,“数称(尹齐)以为廉”,“扬人之善,解人之过”;为九卿多年,贵宠无比,权过丞相,而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它赢”。
他举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实是对他们的抬举;他对儒生“心内虽不合,然阳浮道与之”,这主要是为使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推行过程中减少某些阻力而对那班人采取的虚与周旋的手段。
这些都谈不上是什么“纵横捭闔,毫无操守。
视法律作废纸,以人命为儿戏。
把统治阶级的贪婪残暴的本性发挥到极致”云云。
此外,宁成、周阳由、咸宣等人也没有什么根据可冠之以“胁肩谄笑、阿谀献媚”的恶谥。
敢于搏击权贵豪强,甚至专务“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许多酷吏,表现的是刚直不阿、不畏强御的精神,应该赞扬。
而孟文却另有看法,大施挞伐,令人难以索解。
少数酷吏如杜周“从谀”,王温舒“多谄”,确实不足为训。
但谄媚决非西汉酷吏独具的“特点”,连孟文非常欣赏的循吏之中也多有其人。
就拿循吏之首、大名鼎鼎的黄霸来说吧,不是就曾因对犯罪大臣“阿从不举劾”而差点掉了脑袋吗?
他当丞相时,某日正在问事,恰巧京兆尹张敞家的鶡雀飞集相府屋上,他立即借题发挥,上奏曰:
“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
”这是向皇上献瑞亦即献媚,同时亦欲别人向自己献媚,颂其“感天动地之德”。
可惜谁也不买帐,都“窃笑丞相仁厚有知(智)略”(如此“智略”!
),张敞更公开弹劾他,主张“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恶”。
皇帝“嘉纳敞意”,并派人训斥黄霸,霸因拍马屁未响反挨一脚而“甚惭”(应惭!
)。
可知他在颖川任上所谓其郡多集“凤凰神雀”(盖亦鶡雀之类)云云亦属媚上钓誉的谎言。
难怪严延年“素轻霸为人”,当蝗虫飞集颖川时,延年讥笑说:
“此蝗岂凤皇食邪?
”更有甚者,霸见“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旧恩侍中贵重”,便荐史做太尉,结果又痛遭一脚,他吓得“免冠谢罪”,好歹总算免罪,他“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操守”何在?
)。
第四,孟文说西汉酷吏“绝大部分都不得寿终”,有“十三人都是死于非命的”,而循吏则“得以寿终,生荣死哀”,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酷吏不得寿终是什么皇帝有时“愤于他们不能死心塌地地绝对忠于皇权”所致,那么循吏之得好死必是由于他们能够“死心塌地地绝对忠于皇权”了,这有什么光荣?
酷吏不得好死又是什么皇帝有时“为着敷衍反对派的攻击”所致,但“反对派”是何等样人?
陷害宁成的外戚,为泄私愤而置郅都于死地的窦太后(以及惧怕郅都而暗施狡计的匈奴),等等,值得什么称道?
酷吏不得好死又是什么皇帝“在他们的效用使尽之后”加给的,但兔死狗烹的悲剧连韩信、周亚夫等并非酷吏的大功臣都难幸免,不去鞭笞封建专制皇权,不去谴责杀人者,却对被杀者之“死于非命”而幸灾乐祸,乌足道哉!
孟文所谓西汉酷吏“十三人死于非命”,也是膨胀了的“数据”。
实际只有十人,而此十人亦并非都罪该万死。
其中,晁错是被枉杀的:
他力主削藩,七国兵叛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幌子,景帝惑于错政敌袁盎之谗而斩错,后来邓公为错洗冤,景帝为自己枉杀功臣而憾恨不已,而袁盎亦未得寿终。
郅都是被逼杀的:
他案问犯罪的临江王,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弗与”(这是执法不阿),窦太后从兄子婴却私给刀笔(这是违法行为),王畏罪自杀,窦氏恼羞成怒,构害郅都,罢其官。
后景帝暗用都为雁门太守,匈奴怕得要死,“乃中都以汉法”,窦氏不顾国家利益和景帝的反对,强逼有司杀害了郅都。
宁成也因外戚之毁,险些“死于非命”。
义纵是被屈杀的:
武帝久病初愈,忽然要游甘泉,见道路不治,遂迁怒义纵(想是病人“病态心理”反应罢),后以“废格沮事”的罪名杀之。
张汤是被朱买臣等三长史合伙谋害致死的,他自杀后,武帝痛悔,“乃尽按诛三长史”,与之有牵连的丞相青翟也畏罪自杀(可见谁都可能“死于非命”,非酷吏独然)。
武帝“惜汤”,乃提拔其子安世,致张汤“子孙贵盛”,成为汉代最大的官僚世家之一。
严延年是被“年老颇悖”的无赖丞义构害,“坐怨望诽谤政治”而被杀的。
以上五人之不得寿终,非如孟文所判是什么因其“背着人主追逐一己的私利”云云,而是恰恰相反。
其余五人之死于非命,也不可一概为之拍手称快,如咸宣因属下在追捕亡吏的格斗中误射上林苑门而坐罪下狱自杀,也不能说他死得活该。
三
对于酷吏在削藩锄豪和推行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緡告緡、货币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措施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孟文予以一定肯定,我赞同。
还应指出:
许多酷吏在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中态度坚决,成绩卓著,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军事才干,比那班抱残守缺、不通时势变化、迂执祖宗旧套而又道貌岸然的腐儒滥吏要高明得多,甚至有天壤之别。
武帝时,匈奴求和亲,博士狄山在御前会议上乱弹“兵,凶器”的滥调,攻击抗匈事业,张汤当即痛斥:
“此愚儒无知。
”狄山无耻地自诩为“愚忠”,却把“诈忠”的大帽子扣到张汤头上,恶毒诋毁张汤严惩谋反诸侯王的正义之为是“别疏骨肉”。
对这种阴险的挑拨,头脑清醒的武帝看得很清楚,接连问他能否守住一郡、一县,他皆答曰“不能”(可见其无用);又问:
“守一座城堡怎么样?
”他明知连这也不行,却为避免追究而硬着头皮说“能”(可见其诈)。
武帝说到做到,即派他去守一座城堡,才过了一个多月,这位博士先生的“愚忠”之头便被匈奴砍去了(他也“死于非命”)。
孟文说“狄山当面直斥他(张汤)是‘诈忠’,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道理”大概就在这里罢。
反之,当武帝“大兴兵伐匈奴”而财政发生困难时,张汤殚思极虑赞助武帝推行种种措施,“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他更忙得废寝忘食了。
如果说这是“诈忠”,那到底何谓“真忠”?
难道对那班只会吃白饭说空话而诬人有术的“愚忠”们略施敷衍手段而不真心结交,就构成了对皇帝的“诈忠”大罪了吗?
真是岂有此理!
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素闻都节(刚直有节操),举兵(全军)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
匈奴至为偶人象都,令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
”这与连一座小城堡都守不住而“死于非命”的狄山之流确实是“形成鲜明的对比”!
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酷吏杨仆率军讨伐,冲锋陷阵,立有大功,被封为侯。
次年,东越王余善反,自立为“武帝”,封其将曰“吞汉将军”,气焰嚣张已极,杨仆“与王温舒俱破东越”。
元封二年(前109年),杨仆又率军讨伐侵扰辽东的朝鲜王右渠,朝鲜大臣暗中约降,正在联系中,而左将军苟彘却私执杨仆。
后朝鲜降,荀“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而杨亦被免官(以上见《汉书》本传及《史记》南越、东越、朝鲜传)。
其他还有昭帝时田广明讨平西南夷之乱,宣帝时严延年击败西羌,等等。
就连杜周也曾身临抗匈前线,严惩过那些无能失职的滥吏。
昭帝时,御史大夫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说武帝抗匈是“以义伐不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盐铁论》)。
宣帝即位即下诏曰:
“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氏、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岁、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
……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汉书·夏侯胜传》)。
哀帝即位,王舜、刘歆议曰:
武帝“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抚可见。
……至今累世赖之。
”(《汉书·韦贤传》)以上都是对武帝功绩,特别是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历史功绩的评价。
而在这方面的活动中,许多酷吏是立有汗马功劳的,不能抹杀。
不言而喻,同循吏一样,酷吏的主要职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