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docx
《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docx(2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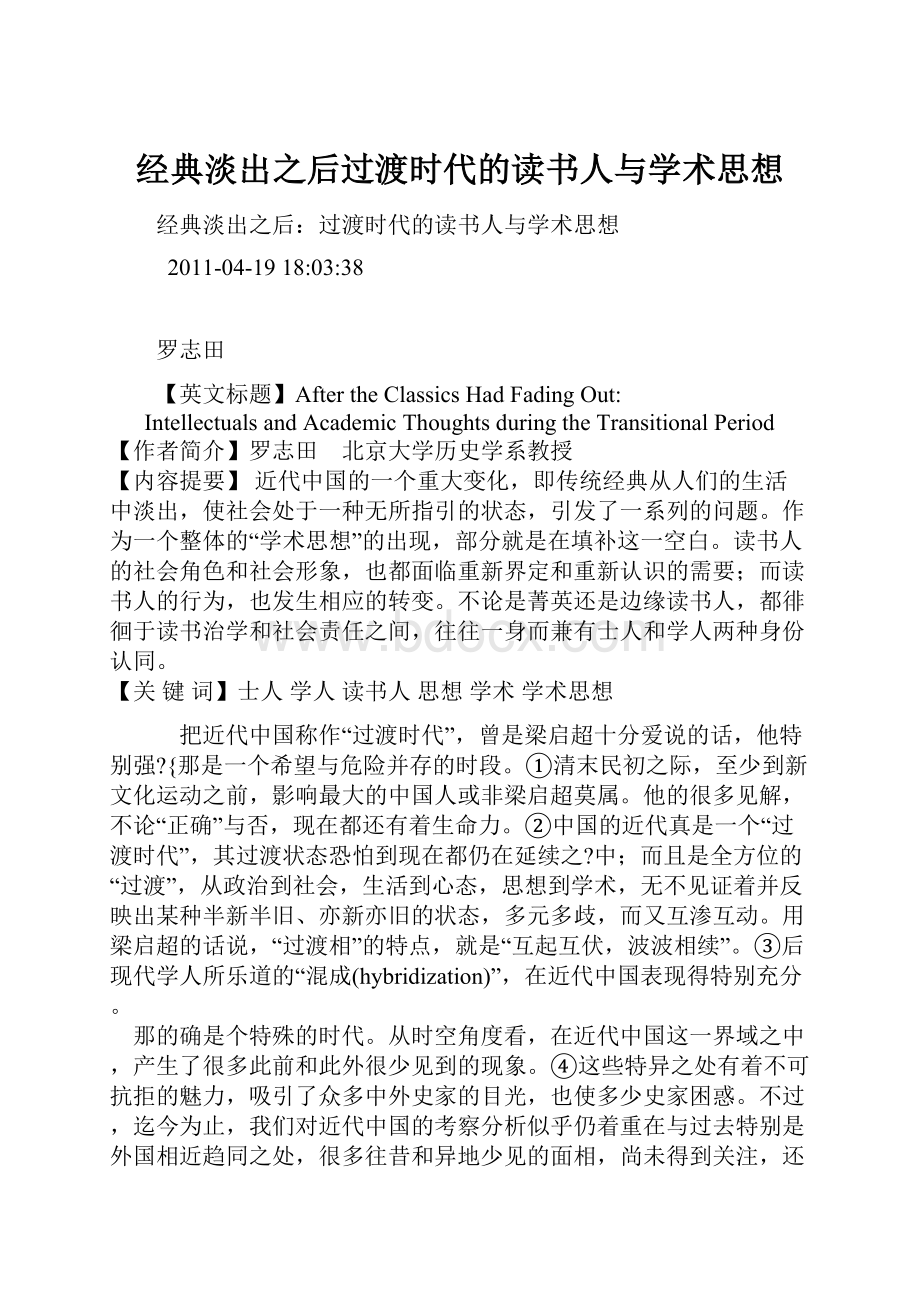
经典淡出之后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
经典淡出之后:
过渡时代的读书人与学术思想
2011-04-1918:
03:
38
罗志田
【英文标题】AftertheClassicsHadFadingOut:
IntellectualsandAcademicThoughtsduringtheTransitionalPeriod
【作者简介】罗志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近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变化,即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使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的出现,部分就是在填补这一空白。
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也都面临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读书人的行为,也发生相应的转变。
不论是菁英还是边缘读书人,都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往往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
【关键词】士人学人读书人思想学术学术思想
把近代中国称作“过渡时代”,曾是梁启超十分爱说的话,他特别强?
{那是一个希望与危险并存的时段。
①清末民初之际,至少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影响最大的中国人或非梁启超莫属。
他的很多见解,不论“正确”与否,现在都还有着生命力。
②中国的近代真是一个“过渡时代”,其过渡状态恐怕到现在都仍在延续之?
中;而且是全方位的“过渡”,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无不见证着并反映出某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的状态,多元多歧,而又互渗互动。
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互起互伏,波波相续”。
③后现代学人所乐道的“混成(hybridization)”,在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充分。
那的确是个特殊的时代。
从时空角度看,在近代中国这一界域之中,产生了很多此前和此外很少见到的现象。
④这些特异之处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了众多中外史家的目光,也使多少史家困惑。
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考察分析似乎仍着重在与过去特别是外国相近趋同之处,很多往昔和异地少见的面相,尚未得到关注,还等待着研究者更深入的挖掘,并将此绚丽多姿的奇景揭示出来,展现给对历史充满兴趣的专业和非专业读者。
例如,在此过渡时代中,近代读书人,不论是菁英还是身处边缘者,大体都有一种共同的意态,即始终徘徊于读书治学和社会责任之间。
或可以说,近代读书人往往是一身而兼有士人和学人两种身份认同;并产生一种连带的思路,常常把今日意义的学术和思想视为一体。
在这些现象背后,隐伏着近代一个重大变化,即在一些趋新士人的有意努力之下,传统经典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的出现,部分即是在填补这一空白。
与此同时,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都面临着重新界定和重新认识的需要;而读书人的行为,也在发生相应的转变。
有一点我要略作说明,⑤本文所说的“读书人”,略同于今日一般史学论著中所说的“知识分子”。
我之所以不用“知识分子”,一是因为这在近代中国是一个后出的外来词,在本文讨论的时段里,至少前一段时间,这个词汇本身尚未出现,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自己并无这样的身份认同,有些可能也不一定接受这个认同。
二是中文世界里过去和现在都有不少人是从字面意义理解和使用外来词的,我感觉把intellectuals(或其它西文里相应的词)译作“知识分子”可能有些误导,至少在用于指称中国读书人方面。
原因是:
在中国传统之中,“读书”是一种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而不仅是一种直观意义的阅读书籍或与技术性、技能性学习相关的行为;它更可能是强?
{一种不那么功利、目的性不那么具体的超技能的持续学习(所以为官者需要聘请专业化的师爷),一种追求和探寻无用之用的努力,以提高人的自主能力,至少改变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参见孟子所说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
这个问题较?
大,我会另文专论。
但有一点很明确,以前读书人所“读”之“书”,与后来日益专业化的“知识”实较少关联;换言之,“知识”不是他们学习的主要目标。
在近代这一过渡时代,这样的状态虽有断裂,仍在延续。
因此,用“知识”来界定这一羣体,会产生某种程度的误导,或者还是“读书人”更能传达其原初的涵义。
一 过渡时代的士人学人与学术思想
所谓读书人的社会责任,也包含从政议政,这在以前与读书治学本无冲突。
传统士人不论是否用世,都像躬耕陇亩的诸葛亮一样,随时为“澄清天下”作着准备。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政与教息息相关,用张之洞的话说,国家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⑥学者最好不做官也不论政的取向,是近代的新事物,到民初虽开始得到提倡,但上述传统观念仍影响着众多读书人(包括其中的趋新者)。
身处过渡时代的读书人,确常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两种身份认同之间,有时欲分,有时又感觉难以切割为二。
⑦
以前的士人是进退于江湖和庙堂之间,虽然也有所谓乡曲陋儒,但若以理想型(idealtype)的方式表述,则士人进退之际,基本保持着“天下士”的胸怀。
与之相比,徘徊于士人与学人之间,已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不过,“士”的传统之现代影响,仍处处可见。
很多读书人的确希望作一个疏离于政治和社会的专业学人,但近代又是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国家一旦有事,他们大多还是感觉到有“不得不出”的责任:
少数人直接投身于实际政治或反向的政治革命,多数人则不时参与议论“天下事”。
马克思曾说,“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⑧此即最能体现。
与前不同的是,那些参政或“议政”的读书人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仿佛离了本行,往往不免带点欲语还休的意态。
“学人”与“士人”,大体可以说是“学术”和“思想”的载体。
我们今日意义的“学术”与“思想”,恐怕都是近代纔“兴起”的概念,甚或是充满外来意味的概念。
而其在兴起之初,确曾关联密切,难以区隔。
实际上,若徘徊于士人与学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之间,也很容易产生一种连带的思路,即在思考和表述中把“学术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学术”和“思想”两者相加而成的一个混合词。
把“思想”和“学术”混为一谈,大致也以梁启超为始作俑者。
梁氏在清季所写的那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当时即广为传播,后来更有持续的影响。
正如胡适指出的,梁是那一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曾经“受了梁先生无穷恩惠”的胡适后来回忆,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⑨
那是一篇写了一两年也没完成的长文,写成部分约有八九万字。
梁启超在其中虽有几次将“学术”与“思想”分开来讨论,如“但求吾学术之进步、思想之统一”;“由思想发为学术”一类,但大多数时候,文中的“学术思想”就是一个不分的整体。
⑩胡适回忆中的用语,大体也在表述相类的意义,最能体现“学术思想”一语在当年既模糊又涵盖宽广的特征。
(11)
与此同时,张之洞所说的国家兴亡“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的观念也在发生过渡性的转变。
梁启超曾以为,“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
(12)这比较像前引张之洞表述的传统观念,但他在大约同时又说:
“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
”(13)两说之间显然有些冲突,而中国与泰西的不同,恐怕纔是其关注的重心。
梁氏似乎在暗示,中国后来之所以不那么“进步”,即因其学术思想未能影响政治,反为政治所左右。
梁启超的观念影响了很多人;或也可以说,在那前后有很多人分享着类似的思路。
杨度就认为:
“有精神而后有物质,有理论而后有事实,有学术而后有政治。
”(14)《国民日日报》一篇不署名文章则将思想与学术区分,提出“天下有思想而后有学术,有学术而后有政治,政治之不善,原于学术者也;学术之不善,原于思想者也”。
(15)该文尽管有这样更细致的区分,但整体上还是主张思想学术的优劣影响甚或决定着政治的好坏。
马君武曾专文讨论“新学术”与“羣治”的关系,认为在人类社会的生存竞争之中,所谓适者生存,就体现在“能发明最新之学术,而进化不已”。
惟“文明人种独有新学术,而野蛮及不进化之人种无之”。
世界历史上“当每一新学术发明之时,则必震撼一切旧社会,而摇动其政治经济等界之情状”。
其势力巨大,随之而变则胜,不变则不胜。
(16)邓实在大约同时也强?
{,“今日之急务”是以学术思想养成国人之政治思想。
(17)而刘师培夫妇稍后也说,“中国一切之政治,均生于学术”。
(18)刘本人更曾进而申论“学术专制与政体之专制相表里”。
(19)
而且,时人对“学”的关注,已在一种新兴的世界竞争视野之下。
《游学译编》一篇不署名的《与同志书》说:
“无学问,无教育,则无民智,无民气;无民智,无民气,则无政治,无法律;无政治,无法律,则无武备,无实业。
学问、教育者,三累而上,强国势之起点也。
”该文指出:
当时世界竞争已剧烈到生死存亡的程度,竞争方式不外兵战、商战和学战。
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
(20)《江苏》上署名“云窝”的文章也说,今日生存竞争“利害之烈莫甚于学战,胜则为全球主人翁,败者入自然淘汰之旋涡,而种族渐归澌灭”。
从表面看,“兵战、商战、农战、工战”皆“足以兴人国亡人国”,其实这些竞争的胜败“无一不以学战为总枢纽”。
(21)
“学战”说在那时非常流行,很可能受到西方文化竞争观念的影响。
(22)当年多数人都与上述诸公相类,特别强?
{“学”的决定性地位。
而章太炎则是个例外,他曾通俗地指出:
“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
何以见得呢?
你看别国的政治学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那个政治上的英雄伟人,也不见他专讲究政治学。
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书?
籍上得来的少。
就像中国现在,袁世凯不过会写几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识字,所办的事,倒比满口讲政治的人好一点儿。
”(23)章氏后来也承认“文章与风俗相”,但又强?
{:
社会风俗之根株“皆政事隆污所致”,近代中国出现“重文学而轻政事”的弊端,是受了日本人治中国史的影响。
(24)
按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与泰西的不同,即所谓“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本也接近章太炎的看法。
但太炎显然是要从根本的通例层面否定“学以致用”的取向,故强?
{这是中外皆然的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章氏似乎是在提倡某种现代意义的“学术独立”,特别是独立于政治。
然而这一思路后来却成为参与实际政治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即只有从政治上根本改变现状(即更换政权),纔能谈到其它方面的转变。
?
而另一些提倡思想改造者则希望通过改造国民性以再造中国文明。
章、梁的观念虽对立,其思路仍相近。
不论是学术影响政治还是政治决定学术,最后仍落实在具体的个人和羣体之上。
甲午后日益响亮的口号是“开民智”,但四民社会解体的结果是士人原本具有的楷模地位动摇,庚子后政府已被认为不能救亡,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来承担?
梁启超当年已感不能自圆其说,遂提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25)用今日的话说,人民可以也只能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章太炎大致分享着类似的思路,不过转而寄希望于“革命”。
他说:
“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26)
然而,人民能否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以及革命是否补泻兼备之良药,在当时仍是充满想象的未知因素。
《外交报》一篇不署名文则提出:
“宪政之能立不能立,则不系乎政府,而系乎国民。
且并不系乎今日之国民,实系乎先民之政教。
先民政教中,其犹有善因耶,则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其竟无善因耶,则宪政必不立,而吾国必亡。
”(27)此处仍隐约可见梁启超《新民说》中对“民”的强?
{。
梁氏以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28)而此文则认为当时的国民仍在“先民之政教”的影响之下,也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着国民的素质及宪政的成败。
在趋新大潮波涛汹涌的时代,如此看重传统的制约力,是相当少见的。
后来五四新文化人或反向传承了这一认知,特别强?
{以破除传统为救亡图存的要素。
当然,新文化人无疑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前引梁氏关于“学术思想为母,风俗政治皆其子孙”的观念,很可能鼓励了新文化人从“学术思想”这一根源处反传统的取向,也就是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以解?
决问题的方法”。
(29)而梁氏只要能“新民”就可以“新”一切的主张,大致也是新文化运动时借改造国民性以改变中国这一取向的思想资源。
在陈独秀看来,中国人在西潮冲击下的“觉悟”分三步,即学术,政治和伦理,后者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他认为,“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
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
照此看,他所说的“伦理”似略同于“根本思想”,而且他确实寄希望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的变更。
不过,陈独秀并不像其它人那样细致梳理学术、政治和伦理(根本思想)的递进关系,而是进而提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必须以“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态度,全面彻底地“取而代之”。
(30)
梁启超稍后总结说,时人因辛亥鼎革后“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
(31)他所谓“全人格的觉悟”,非常像陈独秀所说的“最后之最后”的伦理觉悟,多少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倾向。
(32)随着东西“文化”的对比和对立逐渐成为共同关注的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中国文化”来表述那已被负面整体化的中国传统。
前引胡适所说梁启超的文章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亦即把“四书”、“五经”作为“学术思想”的对比参照物,就很有提示意义。
在胡适说话的时代,“四书”、“五经”本身也经历着过渡——从曾经规范人伦的道义载体变为过去“学术思想”的载体,以及当时“学术思想”的对象,已经是一个充满颠覆意味的转变了。
而且这是一个有意促成的转变。
曾为晚清改革重要推手的黄遵宪,对20世纪初年全国“兴学校”的风潮甚为不满,颇感其举措“皆与吾意相左”。
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它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
(33)这一表述非常重要,表明黄遵宪等人已将推行“去经典化”落实到意识层面,要把经书从“经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或“切于日用”,或“归入专门”,而不复具有规范人伦的指导意义。
(34)
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学术思想”与“风俗政治”的关系成为一个思考的问题,恰是趋新读书人“去经典化”努力的结果。
(35)以前“风俗政治”都在“道”的指引之下,“道”的意义虽有灵活波动的一面,但大体意旨仍是明确的。
重要的是“道”以经典为载体,若对“道”的意旨有任何不明确,正可从经典中寻觅。
“去经典化”之后,“风俗政治”便处在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之下,而“学术思想”则扮演着一种身份似明确而意义不确定的角色:
它此前基本可以说并不“存在”,遑论是否能影响政治。
现在一部分人赋予它以前经典所行使的功用,(36)然其究竟是否能够承担,以及应该怎样完成,的确都还是问题。
二 经典淡出后读书人的责任与困惑
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影响极为深远,虽然其表现可能是逐步的,一开始未必那么直接和明显。
在经典淡出之后,不论新兴的“学术思想”能否承袭以前经典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读书人的社会角色可能都需要重新界定、重新认识,甚至读书人的社会形象也会发生某种转变。
伴随着“去经典化”的推行,从19世纪末年开始,近代中国可见一个日益加剧的读书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进程,造成了读书人形象的负面转化。
(37)
梁启超在主张人民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同时,就曾指责中国“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在民为蠹,在国为虱”。
(38)另一读书人林白水也代国民立言,说“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39)不久梁氏和章太炎又互相指斥对方(革命党人和戊戌党人)不道德。
(40)以梁、章二位在当时的影响力,这样的攻击性论争对读书人的形象具有相当的破坏性;盖若双方所言多少有些依据,则其在“道德”方面都有缺陷,而士人的整体形象自然也就更成问题了。
但梁氏自己对“民”和“士”的态度很快有所?
{整。
他在写《新民说》之前曾向往一种两全的境界,即以“多数之国民”的主动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以为助动者”,以获取“一国之进步”。
(41)到1907年,他已将中国宪政成立与国家兴亡的希望寄托于“中流社会之责任心”。
盖“中流社会,为?
一国之中坚;国家之大业,恒藉其手以成。
此征诸各国,莫不有然,而今日之中国为尤甚”;若“一国中有普通知识居普通地位之中流社会,能以改良一国政治为己任”,则国家前途便有希望。
(42)
到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终于回归到四民之首的士人心态,承认“无论何国,无论何时,其搘柱国家而维系其命脉者,恒不过数人或十数人而已”。
此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而“能得多数之景从者”时,国家就昌盛。
他确信,只要中国“能有百人怀此决心,更少则有十数人怀此决心”,而并力与恶政府、恶社会以及全世界之恶风潮奋战,中国就不可能亡。
他进而一面代国民立言,以为“微论吾国今日未遽亡也,就令已亡矣,而吾国民尚当有事焉”;一面更自己表态说:
“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
”(43)
这里的转变至为明晰:
此前是想以“多数之国民”来“驱役一二之代表人”,现在转而为由少数“在朝在野指导之人”来吸引“多数之景从”了。
入民国后,梁启超在讨论“多数政治”(即西方议会民主制)时继续说:
多数政治要实行得好,关键在于“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
即“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
以此中坚阶级来“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
他明言:
“理论上之多数政治,谓以多数而宰制少数也;事实上之多数政治,实仍以少数宰制多数。
”(44)
稍后梁氏仍以为“恶劣之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但又说中国“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
善良的人民却产出恶劣的政府,这一“国事败坏之大原”,实种因于恶劣的士大夫(他定义为“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
盖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
然而他又说:
“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
”故“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
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
(45)梁启超在自责的同时,又自我承担起国事的责任。
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他最终放弃了让人民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取向,但显然更强?
{读书人的责任了。
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1915年,报人黄远庸当时已感觉“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故转而思考“根本救济”之法。
他试图仿效欧洲“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拟“从提倡新文学入手”。
黄氏写信给章士钊,主张一方面“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同时更“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这大致是在梁启超的思路上发展,但章士钊的观念则近于章太炎,他虽承认提倡新文学“是根本救济之法”,然以为“文艺”只是社会事业之一,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
盖“欧洲文事之兴,无不与政事并进”,而中国并不具备“与民间事业兼容”的政治条件。
(46)
章士钊当时的政治立场是站在袁世凯政府的对立一面,他似乎感觉黄远庸“不谈政治”有逃避之意。
他以鲁索的《民约论》为依据说,既然中国人民对国家法令已不能行公民复决之权,则人民委托政府统治的契约即已解除,可以“视国家为已解散”。
解散之后,“人人既复其自由,即重谋所以建国之道”。
虽然建国之道在于人人“尽其在我”,章士钊仍着眼于“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希望这些人起而带头,负起整理民族建设新国家的责任。
用他的话说,就是“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47)这基本是复述前引梁启超所说的“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但那种想要指导人民的自我承担气概表现得更显著。
问题是当时读书人的状况不使人乐观,陈时在同一年就感觉“吾国士大夫之不悦学,莫今日若”,因此导致“思想趋于偏隘,学殖益荒”。
他接续清季《国民日日报》的观念说,“学术足以铸文明,而思想又适以母学术”。
故“思想发达一步,学术即演进一步”。
但又说:
“智力竞争,愈演愈剧,惟学术实左右之。
黄金世界,学术造之也;铁血精神,学术鼓之也;蛮族之淘汰,学术挤之也;白皙之雄长,学术拥之也。
”或许思想和学术的关系真有些类似于鸡和蛋的关系,陈时终于还是像梁启超那样将学术思想合为一体,主张“欲造成国民的国家,世界的国民,舍学术思想莫由”。
(48)
“学术思想”这样重要,而士人状况又如此不佳,国家前途还只能肩负在他们身上,这是一幅怎样令人困惑的图景!
其实不论什么时代,读书人的状况总是千差万别的。
即使儒生,也很早就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乡曲之士”和“天下士”等等区分。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本是理想型的读书人;而以“干禄”为读书目的者,也从来不少见。
同时,日益明显的新旧之分和新旧之争,也都反映和体现在读书人之间。
在近代中国,伴随着读书人边缘化进程的,还可见边缘读书人的兴起。
介于两者之间的“学生”,尤其是一股上升的力量。
在这方面,五四学生运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用李大钊的话说,正是五四运动“证实”了“知识阶级的胜利”,赋予了知识阶级作为“民众先驱”的地位。
(49)此后“读书人无用”的观念一度衰歇,代之而起的是“学生无事不管”的现象。
(50)到五四运动二周年时,瞿世英注意到,由于五四运动“成功太易,学生都变成趾高气扬,以为学生万能,无论什么事,都有‘舍我其谁’之概”。
(51)
读书人成分的转变很快引起关注,中共的瞿秋白也承认五四运动“能成一大高潮”,即因学生和知识阶级的作用。
然而“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
据他分析,在“中国式的环境里”,知识阶级已分为新旧两类,旧的是“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新的则是“欧风美雨”的产物,从学校的教职员到金融实业机构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其中“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
(52)瞿氏虽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基本还是以新旧区分。
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对“知识分子”的界定进一步学理化,(53)而其它人也基本认同了“读书人”本是一个由不同小羣体组成的大社羣。
当年“学生”一词的涵盖面常常较宽,陈独秀曾说,中国“自戊戌变法以来”,多数人基本处于睡眠状态中,“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故“学生们奔走呼号,成了社会改造的惟一动力”。
可知他所说的“学生”,还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和他自己这样的读书人。
问题是,即使到“五四”之后,“偌大的中国,只有少数青年学生是醒觉的”,这既是非常危险的,也意味着“他们的责任愈加重大”。
(54)若把“学生”广义地看作“醒觉的”读书人,便明显可见前引章士钊所说的“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的自我承担。
陈独秀稍早在探索中国政治不良的责任时,也认为是国民决定着政治的优劣:
“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
”故“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55)这里当然可见清季“新民”说的延续,但他和许多侧重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人一样,(56)似乎都更接近梁启超后来的见解,即主张由觉悟了的读书人来改造国民。
尽管新文化人在理智层面无意把社会分作“我们”与“他们”两部分,(57)但其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终成为鸡以自解的困局。
(58)
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思想”,在近代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