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docx
《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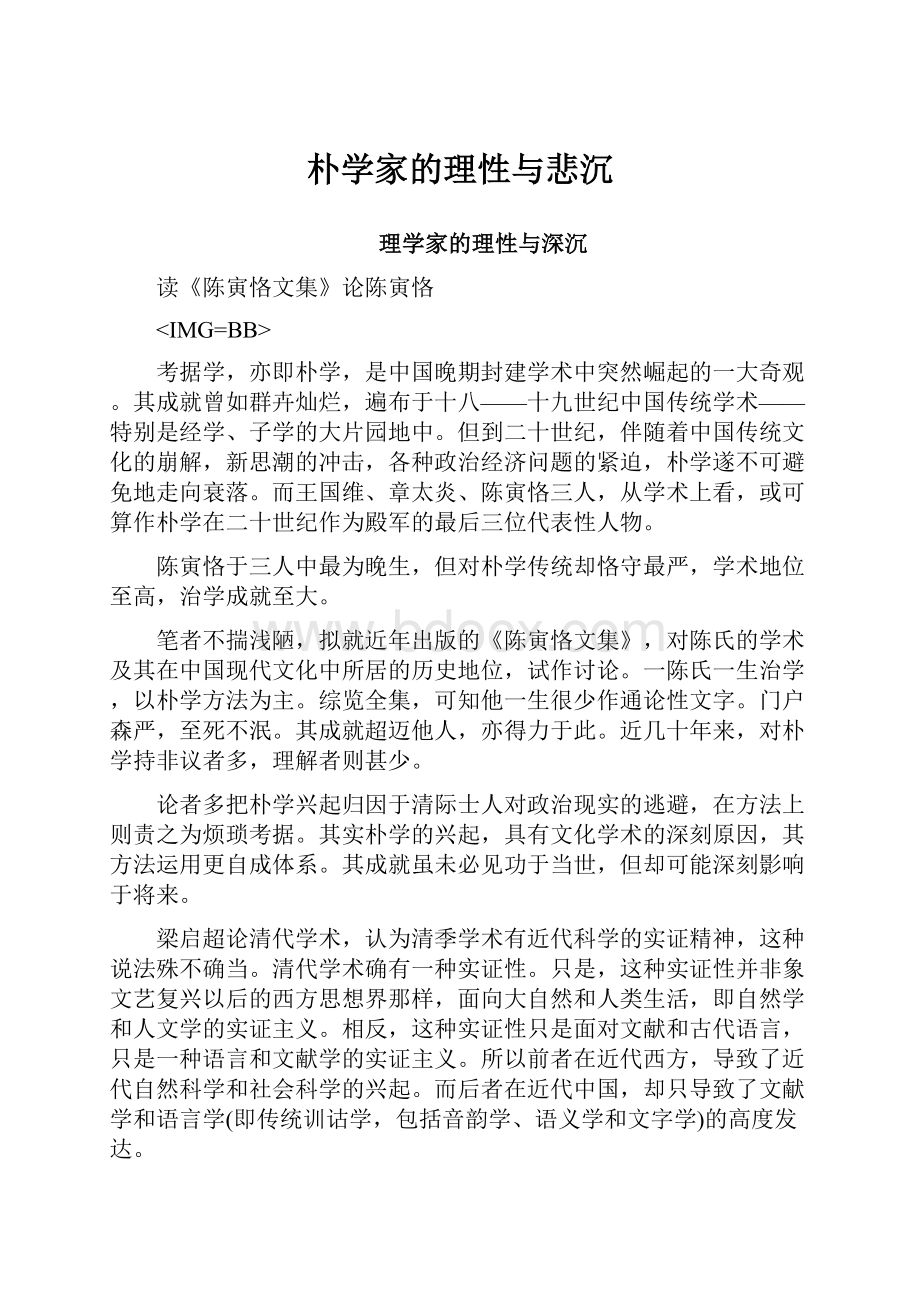
朴学家的理性与悲沉
理学家的理性与深沉
读《陈寅恪文集》论陈寅恪
考据学,亦即朴学,是中国晚期封建学术中突然崛起的一大奇观。
其成就曾如群卉灿烂,遍布于十八——十九世纪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子学的大片园地中。
但到二十世纪,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崩解,新思潮的冲击,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紧迫,朴学遂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而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三人,从学术上看,或可算作朴学在二十世纪作为殿军的最后三位代表性人物。
陈寅恪于三人中最为晚生,但对朴学传统却恪守最严,学术地位至高,治学成就至大。
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近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对陈氏的学术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所居的历史地位,试作讨论。
一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
综览全集,可知他一生很少作通论性文字。
门户森严,至死不泯。
其成就超迈他人,亦得力于此。
近几十年来,对朴学持非议者多,理解者则甚少。
论者多把朴学兴起归因于清际士人对政治现实的逃避,在方法上则责之为烦琐考据。
其实朴学的兴起,具有文化学术的深刻原因,其方法运用更自成体系。
其成就虽未必见功于当世,但却可能深刻影响于将来。
梁启超论清代学术,认为清季学术有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这种说法殊不确当。
清代学术确有一种实证性。
只是,这种实证性并非象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思想界那样,面向大自然和人类生活,即自然学和人文学的实证主义。
相反,这种实证性只是面对文献和古代语言,只是一种语言和文献学的实证主义。
所以前者在近代西方,导致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起。
而后者在近代中国,却只导致了文献学和语言学(即传统训诂学,包括音韵学、语义学和文字学)的高度发达。
我们知道,清代朴学是作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而发轫的。
梁启超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把清代的朴学运动,比拟于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对古代希腊罗马的重新发现和研究。
但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不恰当地作了一种文化的类比。
这不仅由于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与清代学者所感兴趣的汉代学术精神完全不同,而且由于清代学者的方法与近代西方学者的方法,在实质上也非常不同。
培根以后的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是归纳逻辑和实证的知识论,尤为注重知识的实效。
而清代学者所重视的却是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题,他们倡导为求知而求知,耻以急功近利为目的。
实际在这一点上,清代学者的方法倒较接近于二十世纪西方维特根斯坦以后的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反形而上学、反知识论;而朴学也反宋明理学的形而上系统,反“心、性、义、理”的知识论和价值论。
而就方法看,清季朴学对宋明理学的胜利,正是语言分析方法对形而上思辨哲学的胜利。
陈寅恪幼承家学,自八岁起研习《说文》学和高邮王氏父子的训诂学。
少年时期的这种朴学训练,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一生的学术事业。
他十三岁(一九○二年)出游日本,十七岁归国。
二十一岁(一九一○年)起游学欧美。
先后在柏林、巴黎、伦敦及美国哈佛大学就读。
在西方他所学习的主要科目是语言兼及史部。
就前一方面而论,由于陈氏天资过人,他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法文、日文,而且博通拉丁文、希腊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及突厥文、西夏文、藏文、蒙文和满文。
就语言文字知识的这种广博性而论,二十世纪的中国学者以至世界学者中,不要说在历史学界,即在语言专家中,恐怕都鲜有能与陈氏相匹者。
综陈氏一生学术发展而观,大体可以作这样的概括,由传统朴学出发,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次地深入于史学、佛教学、文艺学和文化学的广泛方面。
关于清代朴学对陈氏一生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也可以从如下一点看出。
陈氏早年的同学和姻亲俞大维(现居台湾)在《忆陈寅恪》文中说:
“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
”这正是有清一代朴学家治学的一条根本纲领。
此说首倡于戴震,而大振于二王(王念孙、王引之)。
清代朴学正是从这一点上——不识字即无资格谈经论道;不仅掀翻了宋元三百年的理学,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二千年的经学正统(戴震曾说:
“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
”)。
他们所说的“识字”,当然不是说普通的认字,而是指理解、阐释文字形、音、义的源流变化。
清代朴学家,实际都是一批最认真的文字学家,又是语义学家、语源学家和语音学家。
因此就“读书必先识字”这一朴学名言而论,其意义实可比侔于维特根斯坦用以否定西方形而上哲学传统的一句名言:
“不弄清语言的意义,即无资格讨论哲学。
”
清季朴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汉语文字和音韵;二、文献考据。
但对陈寅恪来说,前者倒并非他的专长。
在文字和音韵的领域中,他的注意力不是在汉语,而是投射于域外的语言文字上。
但是,正因为具有极其广博的中外语言知识,所以在文献的搜求阅读上,在汉语中外来语的语根求索上,以及在中外文献的比证考据上,他都大大地开拓了传统朴学的旧有天地。
从陈氏的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每立一义,必不拘烦琐地进行大量的文献举证。
逐字逐句逐义地比勘辨伪,然后作归纳和分析。
正如清季朴学家蔑视理学一样,陈寅恪一生轻视哲学的玄谈。
在治学中始终坚持以证引论,而避忌以论带证。
这种方法,也正是首倡于顾炎武而为朴学家所珍视的“实事求是”的方法。
但是,与清代朴学的传统相比,陈氏在治学的方法和范围上有两点创新:
一、突破了传统训诂学单一的汉语的研究,而广泛采用了多种语言文字的比较研究。
二、在研究的对象方面,他超越了为乾嘉朴学家所注重的经学,以及晚清朴学家所注重的子学,而开拓了清代朴学较薄弱的两个部门——史学和文学。
同时,由于陈氏游学海外多年,对域外西方史地文化具有广博的文献知识和实际了解,因此他在治文史之学时常具有一种综合的宏观文化视野。
这一点不仅为清代朴学家所不及,即使在当代的历史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中,也鲜有堪与其匹者。
二论西方现代哲学者,常忽略或低估西方学术方法在本世纪内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就是由培根、笛卡尔以来重视知识论和逻辑工具问题,转变为重视语言分析问题。
一位西方哲学家曾指出:
“语言的问题和释义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
”(P·利科尔《论解释》)这一转变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在人类所构造的文化世界中,恐怕没有任何事物比语言更重要。
不仅一切关系于人类生存或价值的知识要靠语言传播和传递,而且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事实上主要结晶或积淀在语言—文字系统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语言的秘密。
文化密码的破解,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
语言表层结构的变化,常常指示着文化形态和风气的变化,而通过对语言深层结构——语义和语源的追索,又常常可以揭示文化演变的脉络。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语言学的诸部门——符号学、语义学、语源学和语用学,正日益受到人文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且渐有发展为领先学科的趋势。
清季朴学家囿于时代文化的局限,当然不可能如此高瞻远瞩地预见现代语言学的这种意义。
他们所注重的,常常只是汉语语言现象中的微观研究(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大理论眼光,这正是清代朴学的根本弱点,也正是这种研究的琐碎性之所在)。
但就陈寅恪而论,他毕竟已是二十世纪的学者,何况又学贯中西,所以尽管他主观上极力恪守朴学正宗的传统,在客观上却不能不对传统朴学的藩篱有所突破。
即使在微观的研究中,陈氏应用他所独擅的中外各种语言知识,在学术上亦常有过人的发现和创获。
例如他根据匈奴名Huua,指出汉语中历来词源不明的“胡”族之名即此音之转化。
根据汉简中卢文的Cinstan(秦斯坦)一词,比照佛经,指出这正是印度和西方语言中称中国为震旦(Cinisthana)、支那(China)、秦斯(Chinese)的语源。
但是,陈氏虽极精于审音考证,于无把握处却并不滥用这种方法。
所谓“多闻阙疑”,是他在文章中常常言及的古训。
例如他诠释白居易《阴山道》诗,对诗中“纥逻敦肥水泉好”一句,便指出“纥逻敦”一词殊不易解。
按突厥方言固可推测“纥逻敦”为“kara-tunā”的对音,即青草地之义。
但在指出此点之后,他却表明这只是“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
表现出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前人论陈寅恪学术,在微观的知识上,多叹服其淹博。
已故复旦大学陈守实教授在早年访谒陈寅恪后便说:
“师谙各国文字。
而于旧籍亦翻检甚勤,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
”(《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又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一文中言:
“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在实际上我们要超过他。
就象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语中虽给陈氏戴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但亦不能不承认其知识广博的权威地位。
当世有一位史家曾说,史学界真正通读过二十四史者,不足十人。
其中他所服膺者,以渊博论为王国维、吕思勉。
诚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王、吕无疑是两位巨子,特别是前者。
但就某些方面而论,陈寅恪之精识则过于此二人。
但这种知识面的淹博,其实不过是陈氏学术的微观方面。
所体现者只是他的“器”,而不是“识”与“道”。
陈氏更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宏观方面,得自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
但亦应当指出,对微观问题的审辨和重视,正是朴学的一大特色。
所以赵元任在论陈寅恪的同时,批评学术界的一种风气说:
“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必是不可靠的。
”
晚近以来,国内史学界有所谓“史料”与“史论”孰重之争,有“以论带史”或“论从史出”之争。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史学中一些已纠缠数十年争不清楚的问题,常常是由于基本材料的不清或误解所致。
那么就这一方面而言,朴学重视微观研究的传统,在今天就显得更其可贵了。
三陈寅恪为王国维遗书作序时论中国现代学术,认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金明馆丛稿》)也就是说:
一、用考古实物推证认识古代文化;二、用多元比较的方法认识中国文化;三、引入新观念,再认识和再评价传统文化。
这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基本趋向。
就陈氏来说,他晚期治史学、文学的方向,则主要侧重于后两方面。
而由这种研究入手,就势必不能不扩展为较宏观的文化思考。
因之在这种研究中,除了传统的考据以外,陈氏更开辟了以诗、文、小说证史和析史的新领域。
综览陈集,其关于魏晋史的研究,已极广泛地取材于汉魏诗文、小说、佛经、内典以至五行杂书。
不仅取材于中国,而且取材于异域。
在陈氏之前,则这些材料每为治史者所忽视,或更因功力所限,难以涉猎运用。
陈寅恪在治隋唐史中,大量地搜采于唐人笔记、小说、诗歌。
陈氏所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可以看作他所独创的、以诗文为主要材料探史析史的三部代表作。
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一书,全书四十万言,是陈氏暮年双目失明后穷十年之力,完全依靠记忆口授著成。
关于此书,曾参与工作的陈氏助手黄萱曾说:
“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这部著作以明清之际的著名文人钱谦益与江南名妓柳如是的婚宦爱情为主线,考核述评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诸如复社事迹,钱谦益降清的背景与心态,郑成功复明的活动,柳如是的才志、气节、性格等等。
其中大量史实都是陈氏首次钩掘于旧籍中而鲜为人所知者。
然而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吴宓日记中有与陈氏谈话后所记云:
“寅恪之研究„红‟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
绝非消闲风趣之活动也。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记)吴宓是陈氏毕生的挚友,亦是著名历史学家。
故此则材料对于理解陈氏治史旨趣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陈氏这种宏观的历史方法时,我们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xx在忆陈寅恪文中说:
“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
他常说:
在史中求史识。
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之原因何在?
这些都是他的研究题目。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实际上,陈氏的治史方向,已远远超越了旧的政治、思想、文学史或其他单一史的范围,而开辟了广义文化史的研究境界。
陈氏有时考证的问题虽小,而关系却大,以小见大正是陈氏治史的卓识之处。
如元稹的《莺莺传》,前人多以其为一部自传体言情小说。
陈氏则从文章体裁、写作时间等方面,证明《莺莺传》不是小说,而是显示包括史才、诗笔、议论的一部考试性作品,即元稹作为求仕士子,向主考官投献的一篇“文备众体”的行卷。
陈氏不仅由此找出了中唐小说何以繁盛的社会原因,更由此篇作品的分析出发,多方面揭示了中唐时代的社会文化风气。
他指出,元稹(即小说中的张生)抛弃崔莺莺的真实原因,实在是因为崔氏出身门第太低,因而恰与小说表层关于崔氏出身旧家的描写相反。
他指出:
“若莺莺果出于高门甲族,则微之无需弃之而更婚韦氏。
唯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
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
”“元微之于莺莺传夸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而不以为愧疚,其友朋亦视为当然,而不非议,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
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少,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轻重,不必顾忌者也。
”
关于小说与历史的关系,陈氏特别指出,应注意个性与通性的问题。
小说中的个性往往是假托的,例如小说中的人物姓李,而真正的人物却未必姓李。
小说写开元年间的事,而实事却未必发生在开元。
其道理就在于,小说只是作者所构拟的一个象征性系统。
但小说既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发生,就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渗透着大量的时代内容和文化意识。
其所以可用以研究历史,原因即在于此。
只是史学家应善于从中剔除掉那些假托的象征性意象,而发掘出已被层层积埋的历史涵义和文化隐义。
陈氏认为,小说人物和作者的署名亦是值得研究的一项。
古人著书署名常常假托。
但其托名则又必有文学的、语言的或政治、社会的来历。
因此,往往并非随意假托。
再者,小说的写作总带有一定的目的。
作者对牵涉到政治上的问题,顾忌一定很多。
不得不用一些手法掩饰。
如写皇帝为宦官所杀,只能说些神怪故事,治史者要善于鉴别,努力从中探求真相。
在这里我们特别应当注意到,陈氏对中国古典文学所采用的上述研究方法一一实际上是将文学作品理解为一个负载着文化信息的“能指”(Signifier)——即符号结构。
他认为批评家应通过他的工作,将这个作品置于一个生动的文化整体中予以还原和分析,从而揭示出这个结构在功能上和意义上的各个潜隐层面。
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现代化的批评方法(既是“结构”的,又是“解构”的),这是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在国外语言和文学界发展起来的文学符号学分析方法。
还应当指出,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中所采用的方法,虽然从表面上看仍近于传统朴学的笺证方法;而在实际上,却已接近于晚近西方哲学中所谓“阐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
R·E·帕尔默就阐释方法的特点曾说:
“解释学和符号学一样,是专门研究传递到书面文字中的语言符号的解释的。
”“不论解释学的定义多么广泛,解释学一方面不同于校勘,另一方面也不同于文学批评。
校勘只是为了证实或确立原文,确认可靠的版本。
文学批评只是根据美和善的定义,对原文的价值作出价值判断。
”“解释学注意的中心是理解原文——即理解用语言写成的„作品‟。
……不管原文是一个梦,一个神话,一条法律,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份电报。
人们只靠单词或句子不能理解„作品‟,必须依靠构成作品的更大的单位作为理解的向导。
”(《解释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文学批评,多么富于现代意义。
实际上,他的这种方法已远远超过了对古典作品的分析,而同样适用于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分析,所以陈氏所留下的遗产,并不只限于一组史学和文学的微观性研究成果。
他在宏观上所常显示出的那种宏大的文化眼光,特别是他以语言学方法为主干的分析和批评方法,尚是一个有待于从现代学术观点作重新认识和探掘的矿藏。
四当我们就要结束这篇论文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就是由论文转而论人。
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陈寅恪?
陈寅恪一生跨越三个时代,他曾是世家出身的清朝贵公子(胡适在民国初年认识他时,尚感到他身上有“遗少”味道),又是早在本世纪初即已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学者,而就其学术成就和方法看,陈氏更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少有的,具有与世界学术水平对话能力和居于领先地位的优秀学者。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当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前夕,蒋介石、傅斯年曾多次电召、甚至专机接陈氏赴台湾,陈氏均坚拒不往。
但在解放以后,由于对这一社会巨变所必然造成的深刻文化断裂,特别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现代社会中一系列巨大的政治、经济、思想、价值转变的不适应、不理解,因之陈寅恪的晚年心境,从其收录在《寒柳堂集》的诗篇可以看出,是颇为压抑和郁闷的。
而他的最终结局,更是相当悲惨的。
在“文革”中,他以年届八十的老病盲翁,横遭多次抄家和人身凌辱,卧病榻上仍被批斗,书籍手稿以至文物什器被抄掠殆尽,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以心力衰竭而辞世(逝世前数日陈氏曾述一联:
“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见《编年事辑》第171页)。
这种结局不能说不具有深刻的悲剧性。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惨剧,其直接原因,当然是极左路线的罪恶。
但从个人方面说,这一悲剧结局的逐步演成,实也与陈氏本人所出身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背景具有深刻的关系。
陈氏《元白诗笺证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
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
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其故何也?
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
这一段话,很难说陈氏不是有所为而发的。
又,他在早年作的王国维挽词序中说:
“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
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
陈寅恪早年与王国维同任教授于清华研究院,思想志趣极为相投,友情甚深。
这一段话,我们亦未尝不可看作陈氏的夫子自况。
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生活在中国新旧文化交相嬗替激烈斗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
而综陈氏一生学术事业而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可以说比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任何人,都更加自觉和固执地坚守着传统儒家关于“士”的理想规范:
砥砺气节,高尚情操,渺视荣禄,淡泊自守。
正是由于这种“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陈氏一九六四年所书的一篇序文中曾这样自我剖白: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氏晚年的思想和操守,以及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热爱,对传统价值的珍视。
这种气节和操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真如凤毛麟角,实在是极为稀见的。
陈氏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中度过了他的一生,写出和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学术成果。
但是作为一个在价值观念上恪守儒家传统的人物,他的生活悲剧,并不仅仅是个人性的。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悲剧。
就其成就来说,陈寅恪是传统学术理性的化身。
而就其不幸来说,他的悲剧更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
其是非功过,由于历史距离的过近,也许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作出定评的。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于xx求是书屋
(《陈寅恪文集》:
一、《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四、《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六、《元白诗笺证稿》,七、《柳如是别传》(共三册),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均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