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docx
《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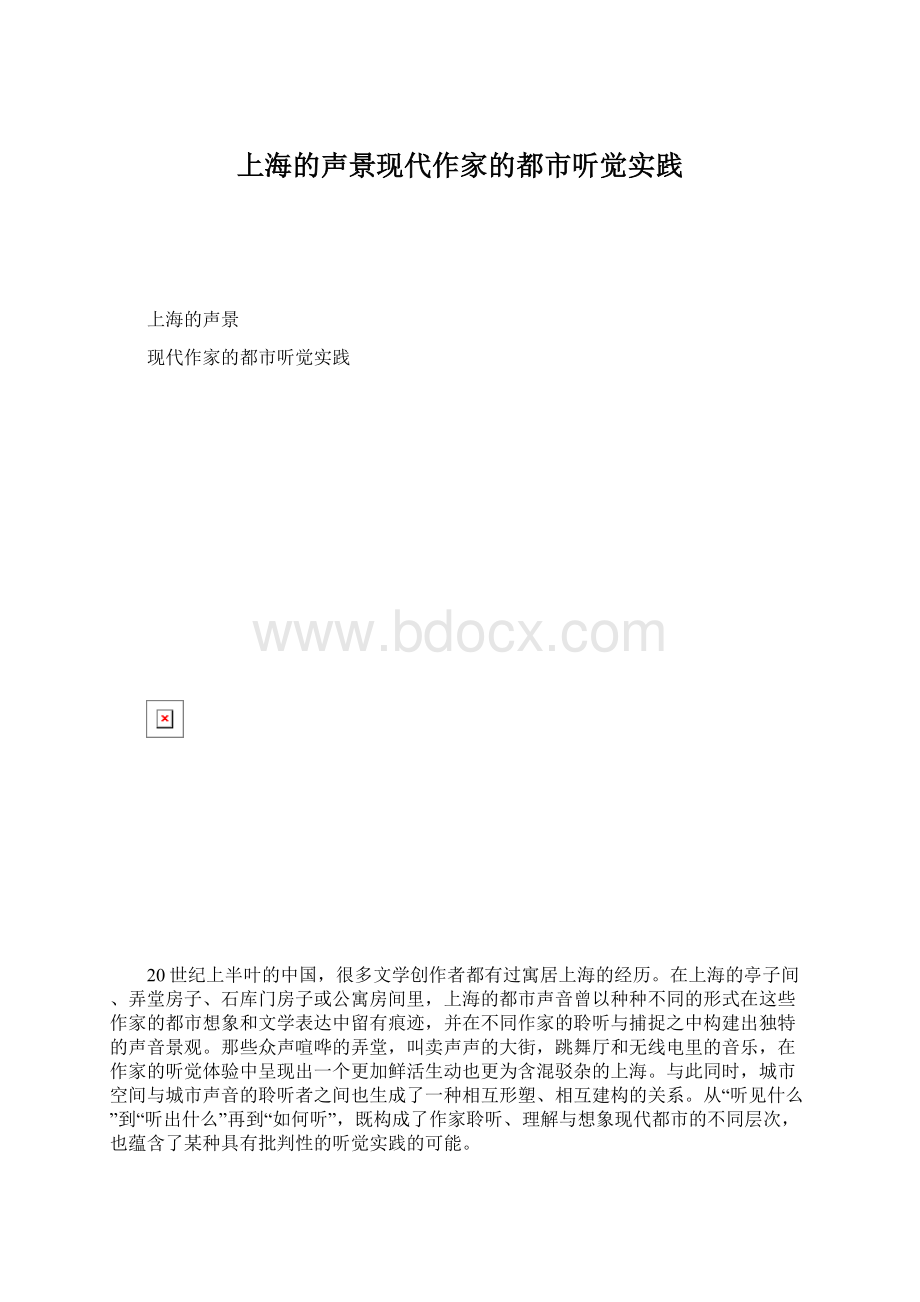
上海的声景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
上海的声景
现代作家的都市听觉实践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很多文学创作者都有过寓居上海的经历。
在上海的亭子间、弄堂房子、石库门房子或公寓房间里,上海的都市声音曾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在这些作家的都市想象和文学表达中留有痕迹,并在不同作家的聆听与捕捉之中构建出独特的声音景观。
那些众声喧哗的弄堂,叫卖声声的大街,跳舞厅和无线电里的音乐,在作家的听觉体验中呈现出一个更加鲜活生动也更为含混驳杂的上海。
与此同时,城市空间与城市声音的聆听者之间也生成了一种相互形塑、相互建构的关系。
从“听见什么”到“听出什么”再到“如何听”,既构成了作家聆听、理解与想象现代都市的不同层次,也蕴含了某种具有批判性的听觉实践的可能。
一“市声”:
听觉体验与城市声景
无论是如波德莱尔的游荡者一般在拱廊街上闲逛,还是像霍夫曼的表弟一样在街角窗户后面审视人群,视觉似乎都是作家把握都市时头等重要的感官方式。
林荫大道、拱廊街、人群、擦肩而过的妇女……那些只能发生在城市里的邂逅与瞬间似乎一旦被人们的视觉感官所捕捉,便无一例外地泄露着都市的秘密。
在都市体验的感官等级系统之中,视觉仿佛一直占据着首要的位置。
张爱玲就曾颇有兴致地提起一位朋友的母亲:
“闲下来的时候常常戴上了眼镜,立在窗前看街。
英文《大美晚报》从前有一栏叫做‘生命的橱窗’,零零碎碎的见闻,很有趣,很能代表都市的空气的,像这位老太太就可以每天写上一段。
”[1]就连张爱玲自己也喜欢在高楼上据守着一方于这城市可进可退,可介入而又可疏离的阳台,眺望着下面敝旧而惨淡的上海。
正如齐美尔所言,相对于其他感官,只有视觉具有占据和拥有的绝对权力。
[2]“视觉使人们不仅拥有他人,还拥有不同环境。
它使我们可以远距离地控制世界,将分离与掌握结合起来。
通过寻求距离得到从熙熙攘攘的日常城市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合适的视野。
”[3]看什么、如何看、在哪里看,使视觉具备了某种选择性和控制感,“看”对于城市景观拥有一种选择性接受的特权甚至“所有权”。
然而听觉则不同。
依齐美尔所言,“耳朵是个非常利己主义的器官,它只索取,但不给予”,同时“它为这种利己主义付出代价:
它不能像眼睛那样避开或者合眼,而是因为它只索取,所以凡是来到它附近的东西,它注定要统统都得接受”[4]。
与嗅觉一样,听觉不能被打开或关闭,因而声音也便和气味一样因其无形的存在和四处弥漫的状态而难以被自由地选择或绝对地管制。
与具有选择与控制特权的视觉相比,听觉与都市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直接和具体,都市的声音作为一种破碎的、易于捕获但又因其转瞬即逝而无法被长久占有的体验形式,则为感官主体与都市之间提供了一种缺乏规划与预谋的相遇。
听觉感官的直接性与具体性取消了“凝视”在采集城市景观的过程中所生成的一种感官对于刺激的宰制关系:
一方面,“听是超个体主义的”[5],声音弥散式的传播打通了不同空间之间的区隔,在某种程度上取消了感官主体进行主观选择的可能,同时也为感官环境内种种隐秘的信息提供了流通的媒质;另一方面,听觉又“传授着单一个人的丰富多彩的种种不同的情绪,传授着思想和冲动的长河和瞬间的极度高涨,传授着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的整个对立性”[6],“包含着难以计数的听众身体做出有形反应的可能性”[7]。
也正是由此,听觉得以将内含着观测距离的景观社会还原为一个亲近的可触性城市,因而与视觉体验相比,都市的声音也许更能激发感官主体对城市的直接感觉和真实体验。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个热衷于阳台俯瞰的张爱玲同样喜欢守在房间里听“市声”,她在《公寓生活记趣》那个著名的段落中说:
“我喜欢听‘市声’。
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
在香港山上,只有在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
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
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汩汩流入下意识里去。
”[8]——单把这样单调安稳的声响从一个鼎沸的上海里拣选出来放在枕边当眠歌,连思想的背景也呈现为电车声的轨迹,可见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形式甚至也是由现代都市的声音参与形塑的。
更饶有意味的是,相比于松涛、海啸这种书写“幽人应未眠”时的传统意象,张爱玲则在电车声中开掘出一种属于现代都市的诗意形式。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王娇蕊在公寓里等佟振保回来,听着电梯的声响:
每天我坐在这里等你回来,听着电梯工东工东慢慢开上来,开过我们这层楼,一直开上去了,我就像把一颗心提了上去,放不下来。
有时候,还没开到这层楼就停住了,我又像是半中间断了气。
在这里,电梯的声音几乎是对其引发的心理体验直接予以赋形,声音成了判断自我与他人、与外部空间的关联并结成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
这与古代思妇听着嗒嗒的马蹄错把过客当作归人的心理体验之间虽存在着某种同构,但在电梯声取代马蹄声的同时,人的情感形式也被赋予了机械的形式与节奏。
正是电梯上上下下机械运动的声响为这一古老的情境增添了更为细腻复杂的现代诗意体验。
在这些时刻,声音为感官主体接触现代都市提供了更为亲近的契机。
而比之于街道或广场,居住空间相对更为固定和封闭,因而与大街上的漫游者相比,处于居住空间之内的感官主体则更少受到视觉优越性与支配性的制约,声音反而成了诱发视觉感官的先在体验。
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深夜写作的鲁迅“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不由地起身“推开楼窗去看”[9],不料却撞见女仆与姘头的幽会;张爱玲听见“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也“突然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10]。
居住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将视觉放在头等位置上的感官等级关系,使听觉和嗅觉更为自觉和自治,成为一种更加鲜明、直接的感官形式。
因而对于居室之内的都市人而言,声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其把握都市体验的直观媒介。
而另一方面,现代都市也改变了人们能够听到的声音内容,甚至是人们聆听的方式。
电车声、电梯声、电话声、留声机、无线电……现代技术不仅生产出新的声音,也为声音的传播与感知提供了新的形式与空间。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米丽·汤普森在其听觉文化研究中提出了“声景”(soundscape)的概念。
她将“声景”定义为一种听觉的景观(acousticalorautallandscape),它既是物质环境又是感知这一环境的方式,不仅包括声音本身,同时还包括在听者感知声音的环境中由声音所创造或毁灭的物质对象。
因而声景既包含了有关聆听的科学与美学方式,也包含了聆听者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社会境遇。
在一个更广义的范畴内,所谓“现代性的声景”,正是在声音与都市空间的相互生产之中产生的。
[11]
在现代作家的都市书写中,城市声景的构建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想象性的。
相比于直接的声音对象或声音技术,文学文本提供的是现代作家关于都市声音的体验、感受、想象或记忆。
因此,文学想象中的“声音景观”其实是对作为建筑学或生态学范畴的“声景”概念的某种借用和引申——它既在不同的聆听者和记录者那里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又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既是城市声音与空间对于聆听者的自我意识的形塑,又是聆听者对于生产声音的城市空间的阐释性重构;它既是私人的,也是公共的,既带有情感性与想象性,又可能触发理性的思辨或批判性的实践。
二“大上海的呼声”:
现代性经验的声音形式
自20世纪20年代起,很多出身内陆的文学青年都曾在上海有过或长或短的居住经验。
许杰、王以仁、丁玲、叶灵凤、周全平、白薇、周立波、谢冰莹、艾芜、徐懋庸、萧军、萧红等众多作家都由于其外来者的边缘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困窘先后屈居于上海的亭子间,而周围弄堂的嘈杂声响也为很多作家津津乐道。
胡也频就曾在小说《往何处去》中写到一个潦倒的青年所饱受的烦扰:
亭子间的底下是厨房。
一到了早上、中午和傍晚,而其实即在普通安静的下午也是常有的,锅声就杂乱的响着,又夹着许多怪腔的男女的谑笑,这种种声音都非常分明的奔到这亭子间里面来,而且还带来了臭熏熏的茶油在炸的气味。
像坐牢一般的无异君,也正因为是孤伶伶的,真不能用一种耐心去习惯这些。
所以,只要听见了那声音和嗅见了那气味,无异君就会陡然觉得沉沉地压在心上的,差不多是苦恼和厌恶混合的情绪。
[12]
亭子间是在上海特有的民居建筑石库门房子内部临时搭建起来的居住空间,上有供人洗晒、休闲的晒台,下有炒菜做饭的灶披间,北向临街,冬冷夏热,“周年照不到阳光和受不到东南风”[13],空间逼仄阴暗,毫无隔音可言,多用来堆放杂物或居住佣人,因其简陋、低廉而成为外来文学青年租住的首选。
在这里,吵闹嘈杂的声音与恶臭污浊的气味所构成的完全是一个摩登都市之外的底层世界,而“无异君”的烦扰体验所呈现的也正是一个城市边缘人观照中的上海。
这些初到大都市闯荡的知识青年多少还抱着些理想主义的幻梦,而弄堂里弥漫着卑俗的小市民气息的喧嚣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无疑将加剧其迷惘与孤独的现实体验。
在这些声音中,清晨弄堂里伴着臭气倒马桶的声响向来是上海底层市民的“起床号”:
到第二天早晨醒过来,那您就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了。
如跑马的奔驰声音,如廊里的木鱼声动,又如在日本东京清早的乐器,接接连连地合奏着。
那足足持续到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光景。
不细细去思索,真不晓得是一些什么器乐。
您起来,您可以听见有一些山歌般地“咿语哀哑”的调子喊叫起来了。
这时,开始了弄堂中的交响乐,您就越发要觉得神秘了。
……从后门望去,家家都有一个或两个红油漆的马桶,在后门陈列着。
那种罗列成行的样子,又令人想起像是一种大阅兵式,方才的马桶合奏乐,又令人怀疑到是野战的演习了。
卖青菜的挑子,在弄堂巡游着。
家家的主妇或女佣,在后门外,同卖菜者争讲着,调情的样子,吵闹着,到处水渍,腥气,那令您不得已要在嘴里含一枝香烟。
也许您会因之就坠入沉思,想象着上海的马桶和汽车的文化来了。
[14]
穆木天对这扰人的声响不乏戏谑式的调侃,其《弄堂》通篇也是以一种向旅人介绍上海弄堂的口吻所写,然而字里行间仍流露出一种“外来者”的不解、无奈与自嘲,俨然是对其亲身遭际的叙写。
语气中虽带有一种猎奇式的谐趣,但亦不乏对混杂着“马桶和汽车的文化”这样一个新旧雅俗杂糅的上海略带排斥的微讽。
在“马桶合奏乐”之后,接着上演的则是穷人们“种种生的挣扎的叫喊声”:
当晨间被倒马桶的声音吵醒以后,再没有方法睡下去了;继续着有种种的声音在窗前叫喊着:
“……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报”。
这种的叫喊,至少有四五次;接着又有叫卖“……乳腐……乳腐……”的;有叫卖“甜酒酿……”的;有叫卖“菠菜……青菜……黄芽菜……”的……[15]
在《上海之春》中,周乐山用这些声音的碎片勾勒出了一副属于穷人们的“龌龊弄堂”的底层都市图景。
而叶圣陶则从深夜的叫卖声中听出了在都市底层谋生的辛酸与苦楚以及穷人们劳碌而疲惫、人命如蚁又不堪重负的卑微形象:
这些叫卖声大都是沙哑的;在这样的境界里传送过来,颤颤地,寂寂地,更显出这境界的凄凉与空虚。
从这些声音又可以想见发声者的形貌,枯瘦的身躯,耸起的鼻子与颧骨,失神的眼睛,全没有血色的皮肤;他们提着篮子或者挑着担子,举起一步似乎提起一块石头,背脊更显得像弓了。
总之,听了这声音就会联想到《黑籍冤魂》里的登场人物。
[16]
事实上,在这些关于底层都市的经验和想象之外,与背负着恶名的气味一样[17],声音的分殊关联着的实则是现代城市空间格局的分化与生活秩序的社会区隔。
因此,在杂乱喧闹的闸北弄堂“再不会瞅见其他任何的自然,大都市的激动的神经强烈的刺激,也更到不了您那里来”[18]。
在眼光敏锐的鲁迅那里,声音恰恰是区分都市空间等级的某种标志:
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
咿咿唉唉,唱呀唱呀。
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
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