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人与新文学文档资料.docx
《新文人与新文学文档资料.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新文人与新文学文档资料.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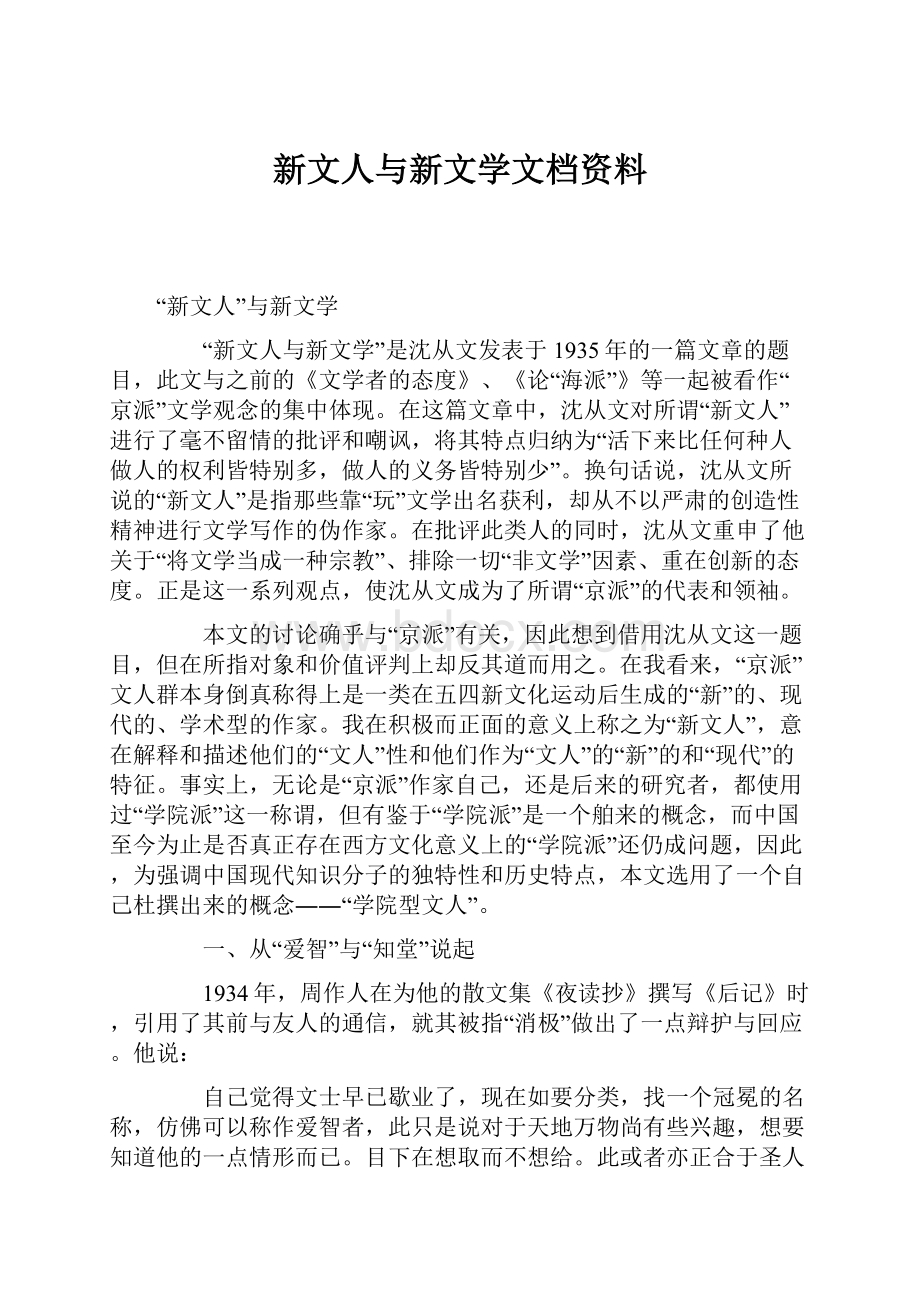
新文人与新文学文档资料
“新文人”与新文学
“新文人与新文学”是沈从文发表于1935年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此文与之前的《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等一起被看作“京派”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
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对所谓“新文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和嘲讽,将其特点归纳为“活下来比任何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别少”。
换句话说,沈从文所说的“新文人”是指那些靠“玩”文学出名获利,却从不以严肃的创造性精神进行文学写作的伪作家。
在批评此类人的同时,沈从文重申了他关于“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排除一切“非文学”因素、重在创新的态度。
正是这一系列观点,使沈从文成为了所谓“京派”的代表和领袖。
本文的讨论确乎与“京派”有关,因此想到借用沈从文这一题目,但在所指对象和价值评判上却反其道而用之。
在我看来,“京派”文人群本身倒真称得上是一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生成的“新”的、现代的、学术型的作家。
我在积极而正面的意义上称之为“新文人”,意在解释和描述他们的“文人”性和他们作为“文人”的“新”的和“现代”的特征。
事实上,无论是“京派”作家自己,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使用过“学院派”这一称谓,但有鉴于“学院派”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而中国至今为止是否真正存在西方文化意义上的“学院派”还仍成问题,因此,为强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和历史特点,本文选用了一个自己杜撰出来的概念――“学院型文人”。
一、从“爱智”与“知堂”说起
1934年,周作人在为他的散文集《夜读抄》撰写《后记》时,引用了其前与友人的通信,就其被指“消极”做出了一点辩护与回应。
他说:
自己觉得文士早已歇业了,现在如要分类,找一个冠冕的名称,仿佛可以称作爱智者,此只是说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而已。
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给。
此或者亦正合于圣人的戒之在得的一句话罢。
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
大约长沮桀溺辈亦是如此,他们仍在耕田,与孔仲尼不同者只是不讲学,其与仲尼之同为儒家盖无疑也,……
这段话透露了一个讯息,即周作人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思想变化,并受到了文坛其他人的关注。
而周作人本人并不完全否认思想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他也谨慎地表示了自己并非“消极”。
他自陈思想大致未变,仍不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中的一员,但有所不同的是,他因“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
也就是说,他白认为在“日常行动”与内心思想等方面,自己并无断然改变,只是在“说”的问题上发生了变化。
有些事看到想到了却未必说,有些事说到了却未必多说。
这种不说或少说,一方面有外部环境的限制导致的“不敢说”与“无法说”,同时也有其自身主观层面上的“无从说”或“懒得说”。
同时,对于“说什么”与“不说什么”,也有了重新的考量。
这种“想取而不想给”、多思而少说的姿态,被周作人称为“爱智”。
就在一年前即1933年,周作人自编《知堂文集》在上海出版。
他自取“知堂”一号,其背后的情绪与思想也颇值得玩味。
对此,周作人在他的短文《知堂说》里有清楚的说明: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
此言甚妙。
有研究者评论说:
“这是一个由‘知’而‘智’的过程。
不写文学批评,近似‘不知为不知’;不写社会批评,仿佛‘默而当’;至于文章新的内容和新的写法,则体现了‘知之为知之’和‘言而当’罢。
”
的确,“知堂”与“爱智”是需要联系起来看的。
一方面,周作人的致“知”就是一种“爱智”;另一方面,他的“爱智”也是一种对于人生有取有舍、有爱有不爱、有所为也有所不为的“知”。
再追溯至《夜读抄》时期,就已能看出周作人思想的转变了。
在《夜读抄》后记里,他明确表达了一种与五四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
他说:
“我们偶然写文章”,是“一不载道,二不讲统”的。
这分明是在有意撇清自己与传统士大夫以及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企图表明一种与二者不同的思想立场。
事实上,无论是对“人的文学”的提倡,还是在“自己的园地”的耕耘中,周作人潜在地都还具有一种“载道”的观念和意图,只是这个“道”与儒家之“道”所指已有不同罢了。
同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周作人,其所受到的启蒙主义的影响,也是不可能不认同文学的现实功利意义的。
因此,即便在“自己的园地”时期,他一面强调“尊重个性”,一面仍在以“文”的方式来载他自己认定的“道”,以“个人的自觉”来“言”他自己胸中的“志”。
可以说,周作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混淆了“载道”和“言志”两种说法,用来为自己的文章和想法取得一种存在的合理性。
然而,到了《夜读抄》时期,他却明确提出了“不载道”、“不讲统”的说法,能否做到先且不论,至少在姿态上,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表达。
由此贯穿起来看,不难发现周作人思想中的变化过程。
五四以后的他,在《自己的园地》时期开始了思想的转变,到了《夜读抄》和《知堂文集》时期,这种转变已基本完成。
这时的周作人,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学术清谈的方向,并由此奠定了他后期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风格的基础。
正如陈思和所说:
“五四新文学传统中,鲁迅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流脉,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
”这一“另类的传统”,“其所关注的是比较抽象层面上的奥秘,这与启蒙不一样”。
陈思和称之为“民间岗位取向”,用以与“传统士大夫的庙堂价值取向”相对照。
在陈思和看来,五四新文学所造就的鲁迅一类启蒙知识分子是一群具有“广场的价值取向”的类型,而周作人的“爱智”就是对所谓“广场”取向的背离。
事实上,周作人的选择不仅仅体现了他个人的倾向,同时也代表并影响了周围的一群人。
或者说,是这一群人因为具有相近的思想立场和文化选择,所以才聚集在周作人的周围。
正如孙郁所说:
1920年代后期,“周氏身边就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子。
……这些人大多远离激进风潮,喜欢清谈,厌恶政治,象牙塔里的特点过浓,与‘左’倾文化是多少隔膜的。
……京派文化的出现,实在说来和苦雨斋的关系是深而又深的”。
这个群体,从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上说,又多是北平城内学术机构中的人物。
这个时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大公报?
文艺副刊》上聚集,发表具有相近文学观念与立场的言论和作品。
又由于沈从文等人的提倡和声张,以及与南方不同文学观念的文人之间的颇引人瞩目的争论,一个“京派”群体已经出现了。
周作人本人虽说一直不被完全视为一个“京派”,但是谁都无法否认,“京派”文化的出现与他之间的关系可谓“深而又深”。
这就是本文“从‘爱智’与‘知堂’说起”的原因。
在我看来,“京派”与周作人的关系不仅在于人事上的亲近,更在于思想观念上的相通。
“京派”思想中最鲜明的核心莫过于对文学“纯粹性”和“庄严感”的强调,以及对于“非文学”因素的拒斥,体现了周作人所说的那种“言而当”与“默而当”的“知”和“爱智”的精神。
有意味的是,这个“爱智”群体中的很多人,对于“京派”这个称呼并不很赞同。
比如卞之琳就明确说过:
“与其说京派,不如说是学院派。
”这一来是因为不愿沾染地域色彩,二来也是为了淡化这个词源所带有的“保守”或“正统”姿态。
而与此同时,带有一定程度的西方文化色彩和模糊性的概念“学院派”,倒正贴近他们的自我期许和自我认识。
陈思和曾以“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来界定周作人的思想核心,认为他是“从人类的智慧(知识)传统里面求得一种价值取向,作为安身立命之地”。
我同意这个说法。
应该说,这个“岗位”就在高等学院或研究机构中。
因而,在已往的一些研究中,一些学者沿用了“学院派”这一称呼。
比如高恒文在其《京派文人:
学院派的风采》一书中认为:
“京派”的“学院派”特色,主要在于“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立身行事、人生道路都能自觉地作出选择,并能坚持不渝,不轻易受外力的左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因此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钱谷融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又补充谈到:
学院派精神还“与他们都在高等学校任教,是所谓的学院中人,知识、文化素养较高,懂得做一个人有他应守的信念和应尽的责任”有关,“而他们的收入也较丰,生活比较优裕,不必为柴米油盐等衣食问题烦心,可以集中精力搞他们的专业。
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很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不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业,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的情志所寄,情绪所托,也是他们这些人安身立命之本”。
钱先生认为:
所谓学院派精神“就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能够顶住一切干扰、坚持贯彻为真理是尊的精神”。
这种看法显然代表了很多学者对“学院派”这一概念加以使用的基本原因和看法。
也就是说,从身份、知识素养、经济实力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个群体有着较为突出的安定的专业意识和职业兴趣,这是建立在身份和各方面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反过来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和思想。
而这个思想的核心,就是“严肃认真的唯真理是尚”的精神。
笼统一点说,“爱智”与“唯真理是尚”的确是有一定关联的。
他们都表现了一种追求“纯粹”的立场,企图把政治(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等其它因素排除在文学和学术之外。
文学和学术对他们而言,就是“智”、是“真理”,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
当然,这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其它更为复杂的方面将在后文谈及。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人的社会存在方式、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化,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那么,在五四落潮之后直至1930年代前期,“学院型文人”群体的出现,应被看作是中国现代知识界的另一个新现象。
这个群体是五四知识分子的一个新的分支,他们继承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很多重要精神,但同时也有所变化,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对于这种继承与变化,周作人个人的思想转变就是非常好的代表与说明。
应该说,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爱智”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落潮后中国知识界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他们不同于五四时期的激进主义的立场,选择了一种退守学院或书斋的姿态,以“爱智”统领其学术思想与文学观念,期望能专注地进行着他们的“纯文学”与“纯学术”建设,尝试着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和角度。
当然,这种对“纯粹”的追求和强调,未必就是真的――也未必就真能――杜绝一切非文学和非学术因素,而这就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
这个“爱智”的群体,也许勉强算得上是正在生成的“学院派”,而且事实上,没有等他们成为真正的学院派,历史就中断了他们的进程。
因此,鉴于对其特殊性、时代性和混杂性的尊重,本文杜撰了一个“学院型文人”的概念。
之所以愿意仍沿用“文人”这样一个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概念,也就是意在看重与强调其与传统之间的复杂联系。
而所谓从“文士”到“文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
我所着意的在于给他们一个位置,一个在古今中西的文化交错中的相对确定的一个位置。
二、从旧“文士”到新“文人”
让我们先撇开“学院型”的问题,看看这种新“文人”与中国古代传统中的“文士”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
既然周作人自觉地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代知识分子与“文士”相区别,就说明他们是非常明确于二者之间的根本性的差异的。
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士”的传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余英时先生曾总结过:
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
荀子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大致点破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功能。
秦汉统一帝国以后,在比较安定的时期,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持都落在“士”的身上;在比较黑暗或混乱的时期,“士”也往往负起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
通过汉代的乡举里选和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度,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
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
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
也就是说,传统的“士”处于文化中心的位置,与政治和社会文化秩序的领导与维护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中国有数百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儒家思想也一直有着“立德立功立言”的目标,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可以说,中国文人对于“居庙堂之高”的社会地位与自我形象的认同,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想传统,即便暂时“处江湖之远”,也并不减少其随时人世从政的心理准备。
这种心态造就了士人的价值观念。
宋代王安石关于学者之“志”的说法可谓深具代表性:
为己,学者之本也。
……为人,学者之末也。
是以学者之事,必先为己,其为已有余,而天下之势可以为人矣,则不可以不为人。
故学者之学也,始不在于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
今夫始学之时,其道未足以为己,而其志己在于为人也,则亦可谓谬用其心矣。
谬用其心者,虽有志于为人,其能乎哉!
显然,周作人所说的“早已歇业”的“文士”,指的就是这样一批“志在为人”、以“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读书人。
而周氏以“爱智”和“想取而不想给”作为自别于“文士”的地方,则明显是具有针对性和反叛意识的。
应该说,从晚清开始,中国文人中有一部分人在发生着自我心理定位上的变化。
到周作人这里,态度就已经十分清晰。
所谓的“文士”既已歇业,而希望代之而起的,则是“爱智者”这一由“文士”群体分离出来的小小类型。
他们将经国治世的兴趣转而投入到具体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中,并将之作为自己事业的最高理想。
“学”与“仕”之间的密切联系被逐渐剥离开来,“学”可以成为一种单纯的职业和岗位,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方式。
而提供这样的存在方式的场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学院”――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
社会存在方式和心理上的巨大变化,同样带来了治学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
陈平原曾在其研究中指出:
“传统中国推崇的是‘通人之学’。
……读书人钻研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目的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国家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晚清开始出现专攻西学的书院(从‘方言’到‘格致’)。
而废除科举考试后,西式学堂成为大势所趋。
张之洞之创建‘存古学堂’,讲‘国学’作为‘专门’来修习,预示着世人政治立场及文化心态的大转移。
已经从‘半部《论语》治天下’,大踏步后退为‘保国粹,存书种’。
……曾经是读书人命脉的孔门学说,如今成了专修科场。
强调‘客观研究’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将其从日常生活中剥离出来”。
与所谓“文士”不同之处在于,“文士”通文,其目的在于出仕。
他们修身养性背后有一个更为宏大的目标,就是要“兼济天下”。
因此应该说,“文士”与“文人”之间的区别正在于:
“文士”的重点在“士”,也就是出于庙堂,为人谋士的意思;而“文人”之重点在“人”,相对而言,这是一个较为强调个体性的概念,从身份认知上说,淡化了他们为官出仕的前景。
如果说从晚清以降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和自我定位发生了一种转变的话,可以说,几乎就是一种从“文士”到“文人”的转变。
即便将那些启蒙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纳入观察的视野,也可以看到,传统的“文士”的确已经消失了。
现代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更看重社会责任的变成了批判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政治、文化等等领域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改革的主张,完全不再是为当政者出谋划策的谋士形象。
而另一部分像周作人等退居书斋的学者和专门家,更是珍惜自己“文人”的特立独行和清高超然的姿态,而有意与社会政治划清界限。
“爱智”成为他们的特点,同时也是一枚表明姿态和维护自我的护身符。
以现代标准来看,“文人”之于“文士”的不同最突出表现在“文人”的自由的思想特征、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他们以个体的写作等方式生活,通过近乎资本市场的方式获取个人的生存,而不依赖于某种政治或官方势力。
落实到“爱智”的京派文人身上,可以看到几个较为明显的特征:
首先,最为基本和核心的精神就是对“自由”的尊重和强调。
伴随着理性的觉醒和个性的高张,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思想界带来的第一大精神特征就是对“自由”的尊重和追求,而文学创作之自由,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可以说,五四时期最为流行的一个新文学原则就是“发挥个性,注重创造”,而在五四落潮之后,仍坚持强调这一“自由”原则,在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两个领域同时将之明确为基本原则。
周作人早在1920年代写《文艺上的宽容》时,就明确表达了对“自由”写作的尊重。
他说:
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他人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的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是研究人的便宜上的分类,不是文艺本质上判分优劣的标准。
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虽然在终极仍有相同之一点,即是人性。
)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
现在倘若拿了批评上的大道理要去强迫统一,即使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实现了,这样文艺作品已经失了他唯一的条件,其实不能成为文艺了。
因为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所以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
虽然周作人在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批评的方法和标准问题,但他对待文学的最核心的标准却已经表明,即“文艺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离不是合并”。
可以说,将“自由”视为“文艺的生命”,这是周作人最为明确的一次表态。
这个“自由”,指的就是创作主体的“自由”。
在提倡和尊重“自由”的同时,周作人也表明了对于“批评上的大道理”的反感。
这让人联想到周作人对文艺“载道”目的的反对。
宽泛一点说,这个“道”除了指儒家之道,也包括一些主义,同时,未必不涵盖了这种“批评的大道理”。
周作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置换了“载道”和“言志”的原本涵义,但一个基本思路毕竟是,他认为“言志”是自由的、伸张个性的;而“载道”则是一种以统一的思想或标准压制个人自由的方式。
因此,归根结蒂地说,在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主张“自由”是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事实上,“京派”作家中大多是尊重自由、强调个性的。
而且这种主张,贯穿了整个1930年代“京派”的活跃时期。
直到1936年,沈从文在《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中还强调说:
“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有他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责任和权利。
”他反对的是某种观念或风气对于文艺作者个性的压抑和限制,强调作家必不能“与一种流行的谐趣风气相牵相混”,而是要以“一个清明合用的脑子”和“一支能够自由运用的笔”,来进行独立的思索,甚至要“稍有冒险精神,想独辟蹊径走去”,“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
这样子来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他说,这“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如果说,周作人和沈从文是从创作者和批评者的角度上指出了“自由”是“文艺的生命”,创造个性是“创作的基本信条”;那么,朱光潜则是从理论的角度,通过文艺心理学的剖析,提出了创作自由的正当和必然。
他认为:
文艺“彼此可以各是其所是,但不必强旁人是己之所是。
文坛上许多无谓争执以起于迷信文艺只有一条正路可走,而且这条路就是自己所走的路。
要破除这般人的迷信颇不容易,除非是他们肯到心理学实验室里去,或则只睁开眼睛多观察人生,很彻底地认识作者与读者在性情,资禀,修养,趣味各方面,都有许多个别的差异,不容易勉强纳在同一个窠臼里”。
可见,“京派”的“自由”的文学观念,不止针对政治化、商业化的压制和浸染,同时也针对文艺批评上的狭隘主义。
也就是说,这个“自由”观念既落实于文学层面上,又超越于文学层面之外,成为一种根本性的思想追求。
本雅明在讨论19世纪巴黎文人的特征时强调“文人”的“自由”,就像“波希米亚人”与流浪汉一样,他们以“漫步”、“观察”、“思想”的方式,成为某种文化最深入的表现者。
同时,他们也以自由写作的方式获得社会生存的位置和方式。
本雅明的这种概括,应该是对现代社会“文人”特性的概括。
在我看来,这种特性是普遍存在于各种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文人”的现代性特征的一种体现。
“学院型文人”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学术的专业性与艺术风格的“知性”。
从思想上说,这群文人看重的是“专门”和“纯粹”。
他们厌倦了将“文”与“学”置于“经国之大业”,厌倦了以才学换取权利的人生方式。
他们回过头来,看到了在“自己的园地”里可能获得的收获。
同时,更是对这种自己的收获的尊严的看重。
因此,他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走向专门和纯粹,同时也有意强调学术、文学的庄严感。
不再将仕途作为唯一有尊严有价值的出路。
可以说,将“不从政”的姿态作为一种自我岗位的确认,这是他们思想“专门性”的最突出的表现。
知性,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智”。
即其所谓“对于天地万物尚有些兴趣,想要知道他的一点情形”。
这里就包含了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从而超出了单一对于政治文化的偏好与偏向。
他们对于知识的追求,不再仅仅因为其有利于国家社稷,而是很可能包含着的审美、求知等目的。
卞之琳曾经在述及自己的诗歌追求时表示,特别看重的是一种“智慧之美”。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算是‘心得’吧,‘道’吧,‘知’吧,‘悟’吧,或者,恕我杜撰一个名目,‘beautyofintelligence’。
”之所以把“beautyofintelligence”译为“智慧之美”,是因为这里的所谓“智慧”,既包含着“理智”、“才智”、“理性”、“智力”等层面,同时又应高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依卞之琳本人的解释,“intelligence”既包含理性的“知”,也包含感性的“悟”;同时,它既是客观的“道”,也有主观的“心得”。
因此可以说,卞之琳的诗歌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哲思与诗美的完美结合,而这种结合,又正是通过诗人的“智慧”感受并传达出来的。
卞之琳所说的“智慧”与周作人的所谓“智”之间显然有一定的相似性。
同时,又与西方现代思潮中的“知性”追求也颇有关联。
卞之琳本人就是第一个翻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的译者,对于西方文学思潮中的“知性”追求不可能不熟知,因此,在他强调自己的诗学观念时,可以说是自然而然地融会了知性与中国文人的爱智追求。
与知性相关的,还有审美趣味上的冷静、爱好玄思等特征。
这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中,也表现在他们学术研究和理论批评等方面。
比如说,京派著名的理论家朱光潜就提出含蓄敦厚的美学思想,并成为京派推崇的理论原则,应当说,这种审美趣味与“爱智”的思想不无关联。
“学院型文人”的第三个思想特征,体现在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上。
事实上,在对“京派”文人的研究中,对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态度的讨论,一直是一个重点。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史书美在《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一书中,以“反思现代”一语概括了京派的“新传统观念”,并将之与上海现代派的“炫耀现代”相比较,强调了其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以及与传统之间更主动、更密切的联系。
史书美认为:
“京派的新传统观念对中国传统重新加以了肯定,并承认中国传统作为西方文化之外的另一特殊性文化的合法性。
……他们所努力寻求的是扩展现代性构成的范围,而并不否弃现代性本身。
”她认为,京派美学是一种“受约束的、简明的、空闲的、温和的、传统主义的和抒情诗体的非功利美学”。
而代表人物周作人、朱光潜都以其各自鲜明的理论主张抵制着对于“传统”的断裂。
比如周作人对于晚明文学的推崇,以及他对于“文艺复兴”和历史循环的观念的提出,都表明了一种独特的亲近传统的态度。
朱光潜则以其特有的辩护态度为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做出了积极的诠释和发掘。
而年轻的诗人卞之琳更是第一个翻译了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借助现代主义大师对于传统的观念,表达了自己一派对此的认同。
可以说,艾略特关于一个作家的当代性是由其对待传统的态度而决定的这一著名论点,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京派作家,同时也应被看作是京派作家自身的传统观念的一种表示。
正是在这样一种重视传统的现代性姿态中,京派作家表现出了他们对“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二元的打破。
正如史书美所说:
“传统意识是对当代性进行认知的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与个人天才》成为了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