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恋风尘高三作文.docx
《恋恋风尘高三作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恋恋风尘高三作文.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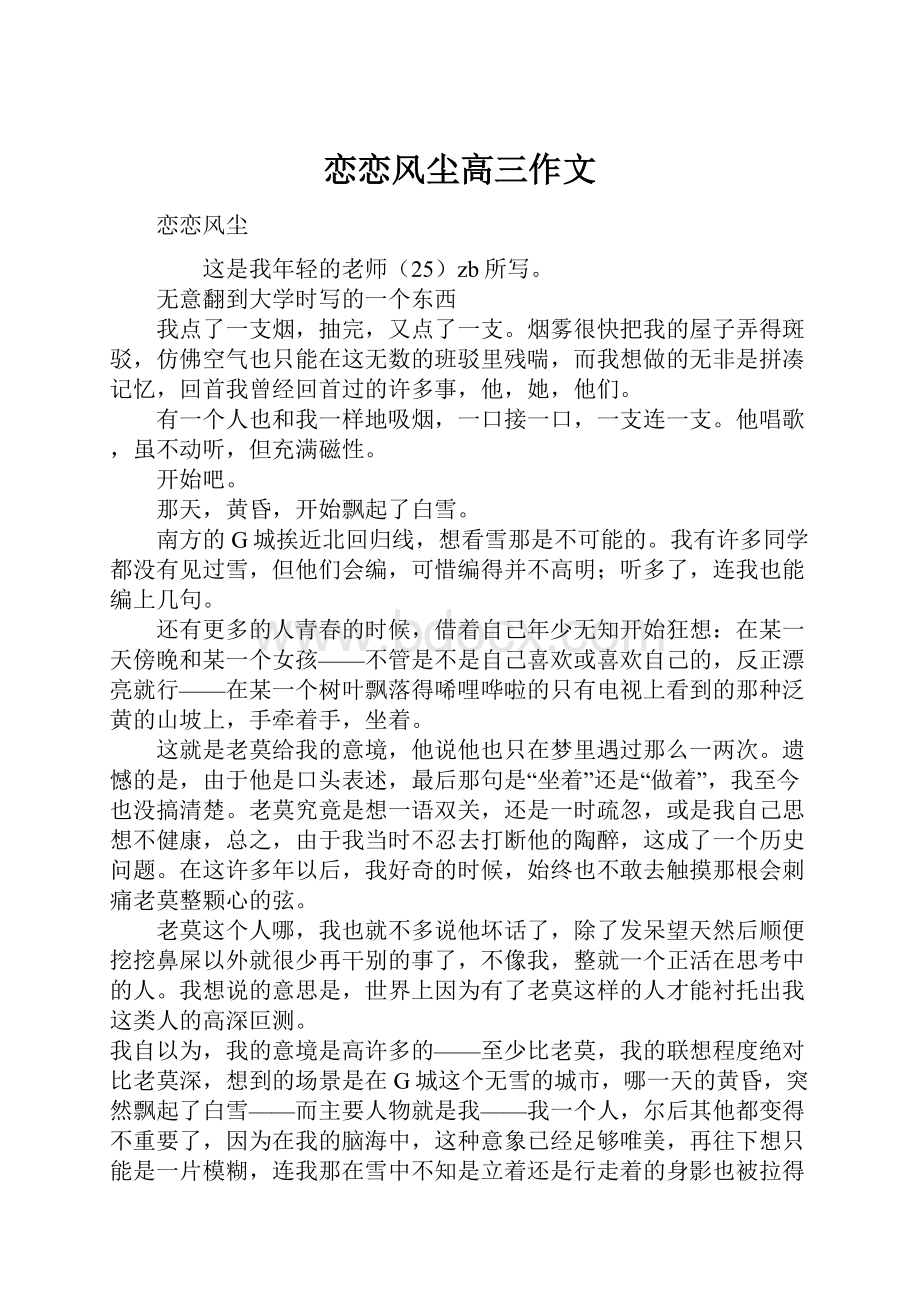
恋恋风尘高三作文
恋恋风尘
这是我年轻的老师(25)zb所写。
无意翻到大学时写的一个东西
我点了一支烟,抽完,又点了一支。
烟雾很快把我的屋子弄得斑驳,仿佛空气也只能在这无数的班驳里残喘,而我想做的无非是拼凑记忆,回首我曾经回首过的许多事,他,她,他们。
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地吸烟,一口接一口,一支连一支。
他唱歌,虽不动听,但充满磁性。
开始吧。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南方的G城挨近北回归线,想看雪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许多同学都没有见过雪,但他们会编,可惜编得并不高明;听多了,连我也能编上几句。
还有更多的人青春的时候,借着自己年少无知开始狂想:
在某一天傍晚和某一个女孩——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或喜欢自己的,反正漂亮就行——在某一个树叶飘落得唏哩哗啦的只有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泛黄的山坡上,手牵着手,坐着。
这就是老莫给我的意境,他说他也只在梦里遇过那么一两次。
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口头表述,最后那句是“坐着”还是“做着”,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老莫究竟是想一语双关,还是一时疏忽,或是我自己思想不健康,总之,由于我当时不忍去打断他的陶醉,这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在这许多年以后,我好奇的时候,始终也不敢去触摸那根会刺痛老莫整颗心的弦。
老莫这个人哪,我也就不多说他坏话了,除了发呆望天然后顺便挖挖鼻屎以外就很少再干别的事了,不像我,整就一个正活在思考中的人。
我想说的意思是,世界上因为有了老莫这样的人才能衬托出我这类人的高深叵测。
我自以为,我的意境是高许多的——至少比老莫,我的联想程度绝对比老莫深,想到的场景是在G城这个无雪的城市,哪一天的黄昏,突然飘起了白雪——而主要人物就是我——我一个人,尔后其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意象已经足够唯美,再往下想只能是一片模糊,连我那在雪中不知是立着还是行走着的身影也被拉得模糊起来。
我把我这个念头告诉老莫的时候,他很是不屑,他说G城根本就没雪,就算有,你肯定是躲在家中的棉被里;就算在外面,你肯定也是玩着堆雪人之类的猥琐游戏,而且一张嘴还笑得很灿烂……说完倒是老莫自己冽着嘴哈哈大笑,两腮的肌肉被拉扯得凹凸不平,整一张夸张且扭曲的脸。
我和老莫就是这样,从初中到现在。
我有着我的梦,他也有着他自己的梦,我们又偏偏喜欢和对方分享,然后就相互耻笑,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最有乐趣的,然后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才能静静地去延续自己的梦。
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大一的秋天。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比较迟,以至于老莫十二月了还能穿着短裤四处招摇,这在校园内就比较显眼,老莫居然引以为荣。
等到冬至的时候,凉意上来了,老莫为了突显他的崇高人品——他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是短裤一条,并且这时,他赋予了自己更深的内涵:
他说他很忧郁,长得很忧郁。
以上仅是他的观点,如果要我说,我觉得用“抽象”形容老莫的长相会更加确切。
这个问题我没有和他谈过,一旦我提出,他肯定会和我高兴地辩论一番,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既定事实的辩论,我只好闭嘴。
老莫见我不反对,于是就更加坚信自己很忧郁,还扯出了一句话形容自己:
一张无限郁闷的脸,逐渐消融在夕阳中。
有一天中午,我和老莫去参加高中的同学聚会,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还记得,那时我们见着的每个人,都有着曾经的味道,但却似乎又充满着莫名的陌生。
老莫小声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认识的只有他们的脸了。
这时班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张粗犷的脸带有点妩媚,并举着酒杯大声说,妈的,还是你们两小子幸福啊,大学还同班同宿舍,还能一起混,我们其他这些人,早已经是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了,呵呵……说罢,他高兴地唱起歌来。
我和老莫都没出声,心想傻逼一个。
后来下午的时刻,他们说去网吧,重温高中的温馨,我俩没去,跑到了以前中学的后山上,老莫说,这里这是我年轻的老师(25)zb所写。
无意翻到大学时写的一个东西
我点了一支烟,抽完,又点了一支。
烟雾很快把我的屋子弄得斑驳,仿佛空气也只能在这无数的班驳里残喘,而我想做的无非是拼凑记忆,回首我曾经回首过的许多事,他,她,他们。
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地吸烟,一口接一口,一支连一支。
他唱歌,虽不动听,但充满磁性。
开始吧。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南方的G城挨近北回归线,想看雪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许多同学都没有见过雪,但他们会编,可惜编得并不高明;听多了,连我也能编上几句。
还有更多的人青春的时候,借着自己年少无知开始狂想:
在某一天傍晚和某一个女孩——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或喜欢自己的,反正漂亮就行——在某一个树叶飘落得唏哩哗啦的只有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泛黄的山坡上,手牵着手,坐着。
这就是老莫给我的意境,他说他也只在梦里遇过那么一两次。
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口头表述,最后那句是“坐着”还是“做着”,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老莫究竟是想一语双关,还是一时疏忽,或是我自己思想不健康,总之,由于我当时不忍去打断他的陶醉,这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在这许多年以后,我好奇的时候,始终也不敢去触摸那根会刺痛老莫整颗心的弦。
老莫这个人哪,我也就不多说他坏话了,除了发呆望天然后顺便挖挖鼻屎以外就很少再干别的事了,不像我,整就一个正活在思考中的人。
我想说的意思是,世界上因为有了老莫这样的人才能衬托出我这类人的高深叵测。
我自以为,我的意境是高许多的——至少比老莫,我的联想程度绝对比老莫深,想到的场景是在G城这个无雪的城市,哪一天的黄昏,突然飘起了白雪——而主要人物就是我——我一个人,尔后其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意象已经足够唯美,再往下想只能是一片模糊,连我那在雪中不知是立着还是行走着的身影也被拉得模糊起来。
我把我这个念头告诉老莫的时候,他很是不屑,他说G城根本就没雪,就算有,你肯定是躲在家中的棉被里;就算在外面,你肯定也是玩着堆雪人之类的猥琐游戏,而且一张嘴还笑得很灿烂……说完倒是老莫自己冽着嘴哈哈大笑,两腮的肌肉被拉扯得凹凸不平,整一张夸张且扭曲的脸。
我和老莫就是这样,从初中到现在。
我有着我的梦,他也有着他自己的梦,我们又偏偏喜欢和对方分享,然后就相互耻笑,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最有乐趣的,然后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才能静静地去延续自己的梦。
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大一的秋天。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比较迟,以至于老莫十二月了还能穿着短裤四处招摇,这在校园内就比较显眼,老莫居然引以为荣。
等到冬至的时候,凉意上来了,老莫为了突显他的崇高人品——他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是短裤一条,并且这时,他赋予了自己更深的内涵:
他说他很忧郁,长得很忧郁。
以上仅是他的观点,如果要我说,我觉得用“抽象”形容老莫的长相会更加确切。
这个问题我没有和他谈过,一旦我提出,他肯定会和我高兴地辩论一番,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既定事实的辩论,我只好闭嘴。
老莫见我不反对,于是就更加坚信自己很忧郁,还扯出了一句话形容自己:
一张无限郁闷的脸,逐渐消融在夕阳中。
有一天中午,我和老莫去参加高中的同学聚会,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还记得,那时我们见着的每个人,都有着曾经的味道,但却似乎又充满着莫名的陌生。
老莫小声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认识的只有他们的脸了。
这时班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张粗犷的脸带有点妩媚,并举着酒杯大声说,妈的,还是你们两小子幸福啊,大学还同班同宿舍,还能一起混,我们其他这些人,早已经是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了,呵呵……说罢,他高兴地唱起歌来。
我和老莫都没出声,心想傻逼一个。
后来下午的时刻,他们说去网吧,重温高中的温馨,我俩没去,跑到了以前中学的后山上,老莫说,这里这是我年轻的老师(25)zb所写。
无意翻到大学时写的一个东西
我点了一支烟,抽完,又点了一支。
烟雾很快把我的屋子弄得斑驳,仿佛空气也只能在这无数的班驳里残喘,而我想做的无非是拼凑记忆,回首我曾经回首过的许多事,他,她,他们。
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地吸烟,一口接一口,一支连一支。
他唱歌,虽不动听,但充满磁性。
开始吧。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南方的G城挨近北回归线,想看雪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许多同学都没有见过雪,但他们会编,可惜编得并不高明;听多了,连我也能编上几句。
还有更多的人青春的时候,借着自己年少无知开始狂想:
在某一天傍晚和某一个女孩——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或喜欢自己的,反正漂亮就行——在某一个树叶飘落得唏哩哗啦的只有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泛黄的山坡上,手牵着手,坐着。
这就是老莫给我的意境,他说他也只在梦里遇过那么一两次。
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口头表述,最后那句是“坐着”还是“做着”,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老莫究竟是想一语双关,还是一时疏忽,或是我自己思想不健康,总之,由于我当时不忍去打断他的陶醉,这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在这许多年以后,我好奇的时候,始终也不敢去触摸那根会刺痛老莫整颗心的弦。
老莫这个人哪,我也就不多说他坏话了,除了发呆望天然后顺便挖挖鼻屎以外就很少再干别的事了,不像我,整就一个正活在思考中的人。
我想说的意思是,世界上因为有了老莫这样的人才能衬托出我这类人的高深叵测。
我自以为,我的意境是高许多的——至少比老莫,我的联想程度绝对比老莫深,想到的场景是在G城这个无雪的城市,哪一天的黄昏,突然飘起了白雪——而主要人物就是我——我一个人,尔后其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意象已经足够唯美,再往下想只能是一片模糊,连我那在雪中不知是立着还是行走着的身影也被拉得模糊起来。
我把我这个念头告诉老莫的时候,他很是不屑,他说G城根本就没雪,就算有,你肯定是躲在家中的棉被里;就算在外面,你肯定也是玩着堆雪人之类的猥琐游戏,而且一张嘴还笑得很灿烂……说完倒是老莫自己冽着嘴哈哈大笑,两腮的肌肉被拉扯得凹凸不平,整一张夸张且扭曲的脸。
我和老莫就是这样,从初中到现在。
我有着我的梦,他也有着他自己的梦,我们又偏偏喜欢和对方分享,然后就相互耻笑,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最有乐趣的,然后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才能静静地去延续自己的梦。
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大一的秋天。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比较迟,以至于老莫十二月了还能穿着短裤四处招摇,这在校园内就比较显眼,老莫居然引以为荣。
等到冬至的时候,凉意上来了,老莫为了突显他的崇高人品——他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是短裤一条,并且这时,他赋予了自己更深的内涵:
他说他很忧郁,长得很忧郁。
以上仅是他的观点,如果要我说,我觉得用“抽象”形容老莫的长相会更加确切。
这个问题我没有和他谈过,一旦我提出,他肯定会和我高兴地辩论一番,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既定事实的辩论,我只好闭嘴。
老莫见我不反对,于是就更加坚信自己很忧郁,还扯出了一句话形容自己:
一张无限郁闷的脸,逐渐消融在夕阳中。
有一天中午,我和老莫去参加高中的同学聚会,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还记得,那时我们见着的每个人,都有着曾经的味道,但却似乎又充满着莫名的陌生。
老莫小声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认识的只有他们的脸了。
这时班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张粗犷的脸带有点妩媚,并举着酒杯大声说,妈的,还是你们两小子幸福啊,大学还同班同宿舍,还能一起混,我们其他这些人,早已经是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了,呵呵……说罢,他高兴地唱起歌来。
我和老莫都没出声,心想傻逼一个。
后来下午的时刻,他们说去网吧,重温高中的温馨,我俩没去,跑到了以前中学的后山上,老莫说,这里这是我年轻的老师(25)zb所写。
无意翻到大学时写的一个东西
我点了一支烟,抽完,又点了一支。
烟雾很快把我的屋子弄得斑驳,仿佛空气也只能在这无数的班驳里残喘,而我想做的无非是拼凑记忆,回首我曾经回首过的许多事,他,她,他们。
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地吸烟,一口接一口,一支连一支。
他唱歌,虽不动听,但充满磁性。
开始吧。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南方的G城挨近北回归线,想看雪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许多同学都没有见过雪,但他们会编,可惜编得并不高明;听多了,连我也能编上几句。
还有更多的人青春的时候,借着自己年少无知开始狂想:
在某一天傍晚和某一个女孩——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或喜欢自己的,反正漂亮就行——在某一个树叶飘落得唏哩哗啦的只有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泛黄的山坡上,手牵着手,坐着。
这就是老莫给我的意境,他说他也只在梦里遇过那么一两次。
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口头表述,最后那句是“坐着”还是“做着”,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老莫究竟是想一语双关,还是一时疏忽,或是我自己思想不健康,总之,由于我当时不忍去打断他的陶醉,这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在这许多年以后,我好奇的时候,始终也不敢去触摸那根会刺痛老莫整颗心的弦。
老莫这个人哪,我也就不多说他坏话了,除了发呆望天然后顺便挖挖鼻屎以外就很少再干别的事了,不像我,整就一个正活在思考中的人。
我想说的意思是,世界上因为有了老莫这样的人才能衬托出我这类人的高深叵测。
我自以为,我的意境是高许多的——至少比老莫,我的联想程度绝对比老莫深,想到的场景是在G城这个无雪的城市,哪一天的黄昏,突然飘起了白雪——而主要人物就是我——我一个人,尔后其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意象已经足够唯美,再往下想只能是一片模糊,连我那在雪中不知是立着还是行走着的身影也被拉得模糊起来。
我把我这个念头告诉老莫的时候,他很是不屑,他说G城根本就没雪,就算有,你肯定是躲在家中的棉被里;就算在外面,你肯定也是玩着堆雪人之类的猥琐游戏,而且一张嘴还笑得很灿烂……说完倒是老莫自己冽着嘴哈哈大笑,两腮的肌肉被拉扯得凹凸不平,整一张夸张且扭曲的脸。
我和老莫就是这样,从初中到现在。
我有着我的梦,他也有着他自己的梦,我们又偏偏喜欢和对方分享,然后就相互耻笑,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最有乐趣的,然后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才能静静地去延续自己的梦。
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大一的秋天。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比较迟,以至于老莫十二月了还能穿着短裤四处招摇,这在校园内就比较显眼,老莫居然引以为荣。
等到冬至的时候,凉意上来了,老莫为了突显他的崇高人品——他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是短裤一条,并且这时,他赋予了自己更深的内涵:
他说他很忧郁,长得很忧郁。
以上仅是他的观点,如果要我说,我觉得用“抽象”形容老莫的长相会更加确切。
这个问题我没有和他谈过,一旦我提出,他肯定会和我高兴地辩论一番,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既定事实的辩论,我只好闭嘴。
老莫见我不反对,于是就更加坚信自己很忧郁,还扯出了一句话形容自己:
一张无限郁闷的脸,逐渐消融在夕阳中。
有一天中午,我和老莫去参加高中的同学聚会,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还记得,那时我们见着的每个人,都有着曾经的味道,但却似乎又充满着莫名的陌生。
老莫小声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认识的只有他们的脸了。
这时班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张粗犷的脸带有点妩媚,并举着酒杯大声说,妈的,还是你们两小子幸福啊,大学还同班同宿舍,还能一起混,我们其他这些人,早已经是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了,呵呵……说罢,他高兴地唱起歌来。
我和老莫都没出声,心想傻逼一个。
后来下午的时刻,他们说去网吧,重温高中的温馨,我俩没去,跑到了以前中学的后山上,老莫说,这里这是我年轻的老师(25)zb所写。
无意翻到大学时写的一个东西
我点了一支烟,抽完,又点了一支。
烟雾很快把我的屋子弄得斑驳,仿佛空气也只能在这无数的班驳里残喘,而我想做的无非是拼凑记忆,回首我曾经回首过的许多事,他,她,他们。
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地吸烟,一口接一口,一支连一支。
他唱歌,虽不动听,但充满磁性。
开始吧。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南方的G城挨近北回归线,想看雪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许多同学都没有见过雪,但他们会编,可惜编得并不高明;听多了,连我也能编上几句。
还有更多的人青春的时候,借着自己年少无知开始狂想:
在某一天傍晚和某一个女孩——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或喜欢自己的,反正漂亮就行——在某一个树叶飘落得唏哩哗啦的只有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泛黄的山坡上,手牵着手,坐着。
这就是老莫给我的意境,他说他也只在梦里遇过那么一两次。
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口头表述,最后那句是“坐着”还是“做着”,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老莫究竟是想一语双关,还是一时疏忽,或是我自己思想不健康,总之,由于我当时不忍去打断他的陶醉,这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在这许多年以后,我好奇的时候,始终也不敢去触摸那根会刺痛老莫整颗心的弦。
老莫这个人哪,我也就不多说他坏话了,除了发呆望天然后顺便挖挖鼻屎以外就很少再干别的事了,不像我,整就一个正活在思考中的人。
我想说的意思是,世界上因为有了老莫这样的人才能衬托出我这类人的高深叵测。
我自以为,我的意境是高许多的——至少比老莫,我的联想程度绝对比老莫深,想到的场景是在G城这个无雪的城市,哪一天的黄昏,突然飘起了白雪——而主要人物就是我——我一个人,尔后其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意象已经足够唯美,再往下想只能是一片模糊,连我那在雪中不知是立着还是行走着的身影也被拉得模糊起来。
我把我这个念头告诉老莫的时候,他很是不屑,他说G城根本就没雪,就算有,你肯定是躲在家中的棉被里;就算在外面,你肯定也是玩着堆雪人之类的猥琐游戏,而且一张嘴还笑得很灿烂……说完倒是老莫自己冽着嘴哈哈大笑,两腮的肌肉被拉扯得凹凸不平,整一张夸张且扭曲的脸。
我和老莫就是这样,从初中到现在。
我有着我的梦,他也有着他自己的梦,我们又偏偏喜欢和对方分享,然后就相互耻笑,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最有乐趣的,然后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才能静静地去延续自己的梦。
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大一的秋天。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比较迟,以至于老莫十二月了还能穿着短裤四处招摇,这在校园内就比较显眼,老莫居然引以为荣。
等到冬至的时候,凉意上来了,老莫为了突显他的崇高人品——他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是短裤一条,并且这时,他赋予了自己更深的内涵:
他说他很忧郁,长得很忧郁。
以上仅是他的观点,如果要我说,我觉得用“抽象”形容老莫的长相会更加确切。
这个问题我没有和他谈过,一旦我提出,他肯定会和我高兴地辩论一番,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既定事实的辩论,我只好闭嘴。
老莫见我不反对,于是就更加坚信自己很忧郁,还扯出了一句话形容自己:
一张无限郁闷的脸,逐渐消融在夕阳中。
有一天中午,我和老莫去参加高中的同学聚会,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还记得,那时我们见着的每个人,都有着曾经的味道,但却似乎又充满着莫名的陌生。
老莫小声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认识的只有他们的脸了。
这时班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张粗犷的脸带有点妩媚,并举着酒杯大声说,妈的,还是你们两小子幸福啊,大学还同班同宿舍,还能一起混,我们其他这些人,早已经是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了,呵呵……说罢,他高兴地唱起歌来。
我把我这个念头告诉老莫的时候,他很是不屑,他说G城根本就没雪,就算有,你肯定是躲在家中的棉被里;就算在外面,你肯定也是玩着堆雪人之类的猥琐游戏,而且一张嘴还笑得很灿烂……说完倒是老莫自己冽着嘴哈哈大笑,两腮的肌肉被拉扯得凹凸不平,整一张夸张且扭曲的脸。
我和老莫就是这样,从初中到现在。
我有着我的梦,他也有着他自己的梦,我们又偏偏喜欢和对方分享,然后就相互耻笑,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最有乐趣的,然后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才能静静地去延续自己的梦。
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大一的秋天。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比较迟,以至于老莫十二月了还能穿着短裤四处招摇,这在校园内就比较显眼,老莫居然引以为荣。
等到冬至的时候,凉意上来了,老莫为了突显他的崇高人品——他是这样告诉我的——还是短裤一条,并且这时,他赋予了自己更深的内涵:
他说他很忧郁,长得很忧郁。
以上仅是他的观点,如果要我说,我觉得用“抽象”形容老莫的长相会更加确切。
这个问题我没有和他谈过,一旦我提出,他肯定会和我高兴地辩论一番,为了避免这种无聊的既定事实的辩论,我只好闭嘴。
老莫见我不反对,于是就更加坚信自己很忧郁,还扯出了一句话形容自己:
一张无限郁闷的脸,逐渐消融在夕阳中。
有一天中午,我和老莫去参加高中的同学聚会,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还记得,那时我们见着的每个人,都有着曾经的味道,但却似乎又充满着莫名的陌生。
老莫小声地对我说,现在我们认识的只有他们的脸了。
这时班长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一张粗犷的脸带有点妩媚,并举着酒杯大声说,妈的,还是你们两小子幸福啊,大学还同班同宿舍,还能一起混,我们其他这些人,早已经是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了,呵呵……说罢,他高兴地唱起歌来。
我和老莫都没出声,心想傻逼一个。
后来下午的时刻,他们说去网吧,重温高中的温馨,我俩没去,跑到了以前中学的后山上,老莫说,这里
我和老莫都没出声,心想傻逼一个。
后来下午的时刻,他们说去网吧,重温高中的温馨,我俩没去,跑到了以前中学的后山上,老莫说,这里这是我年轻的老师(25)zb所写。
无意翻到大学时写的一个东西
我点了一支烟,抽完,又点了一支。
烟雾很快把我的屋子弄得斑驳,仿佛空气也只能在这无数的班驳里残喘,而我想做的无非是拼凑记忆,回首我曾经回首过的许多事,他,她,他们。
有一个人也和我一样地吸烟,一口接一口,一支连一支。
他唱歌,虽不动听,但充满磁性。
开始吧。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
南方的G城挨近北回归线,想看雪那是不可能的。
我有许多同学都没有见过雪,但他们会编,可惜编得并不高明;听多了,连我也能编上几句。
还有更多的人青春的时候,借着自己年少无知开始狂想:
在某一天傍晚和某一个女孩——不管是不是自己喜欢或喜欢自己的,反正漂亮就行——在某一个树叶飘落得唏哩哗啦的只有电视上看到的那种泛黄的山坡上,手牵着手,坐着。
这就是老莫给我的意境,他说他也只在梦里遇过那么一两次。
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口头表述,最后那句是“坐着”还是“做着”,我至今也没搞清楚。
老莫究竟是想一语双关,还是一时疏忽,或是我自己思想不健康,总之,由于我当时不忍去打断他的陶醉,这成了一个历史问题。
在这许多年以后,我好奇的时候,始终也不敢去触摸那根会刺痛老莫整颗心的弦。
老莫这个人哪,我也就不多说他坏话了,除了发呆望天然后顺便挖挖鼻屎以外就很少再干别的事了,不像我,整就一个正活在思考中的人。
我想说的意思是,世界上因为有了老莫这样的人才能衬托出我这类人的高深叵测。
我自以为,我的意境是高许多的——至少比老莫,我的联想程度绝对比老莫深,想到的场景是在G城这个无雪的城市,哪一天的黄昏,突然飘起了白雪——而主要人物就是我——我一个人,尔后其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在我的脑海中,这种意象已经足够唯美,再往下想只能是一片模糊,连我那在雪中不知是立着还是行走着的身影也被拉得模糊起来。
我把我这个念头告诉老莫的时候,他很是不屑,他说G城根本就没雪,就算有,你肯定是躲在家中的棉被里;就算在外面,你肯定也是玩着堆雪人之类的猥琐游戏,而且一张嘴还笑得很灿烂……说完倒是老莫自己冽着嘴哈哈大笑,两腮的肌肉被拉扯得凹凸不平,整一张夸张且扭曲的脸。
我和老莫就是这样,从初中到现在。
我有着我的梦,他也有着他自己的梦,我们又偏偏喜欢和对方分享,然后就相互耻笑,仿佛这样的生活就是最有乐趣的,然后一到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们才能静静地去延续自己的梦。
这样的生活,贯穿了整个大一的秋天。
忧伤,开满山冈,等青春散场。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比较迟,以至于老莫十二月了还能穿着短裤四处招摇,这在校园内就比较显眼,老莫居然引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