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二三事外1章Word格式.docx
《母亲二三事外1章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母亲二三事外1章Word格式.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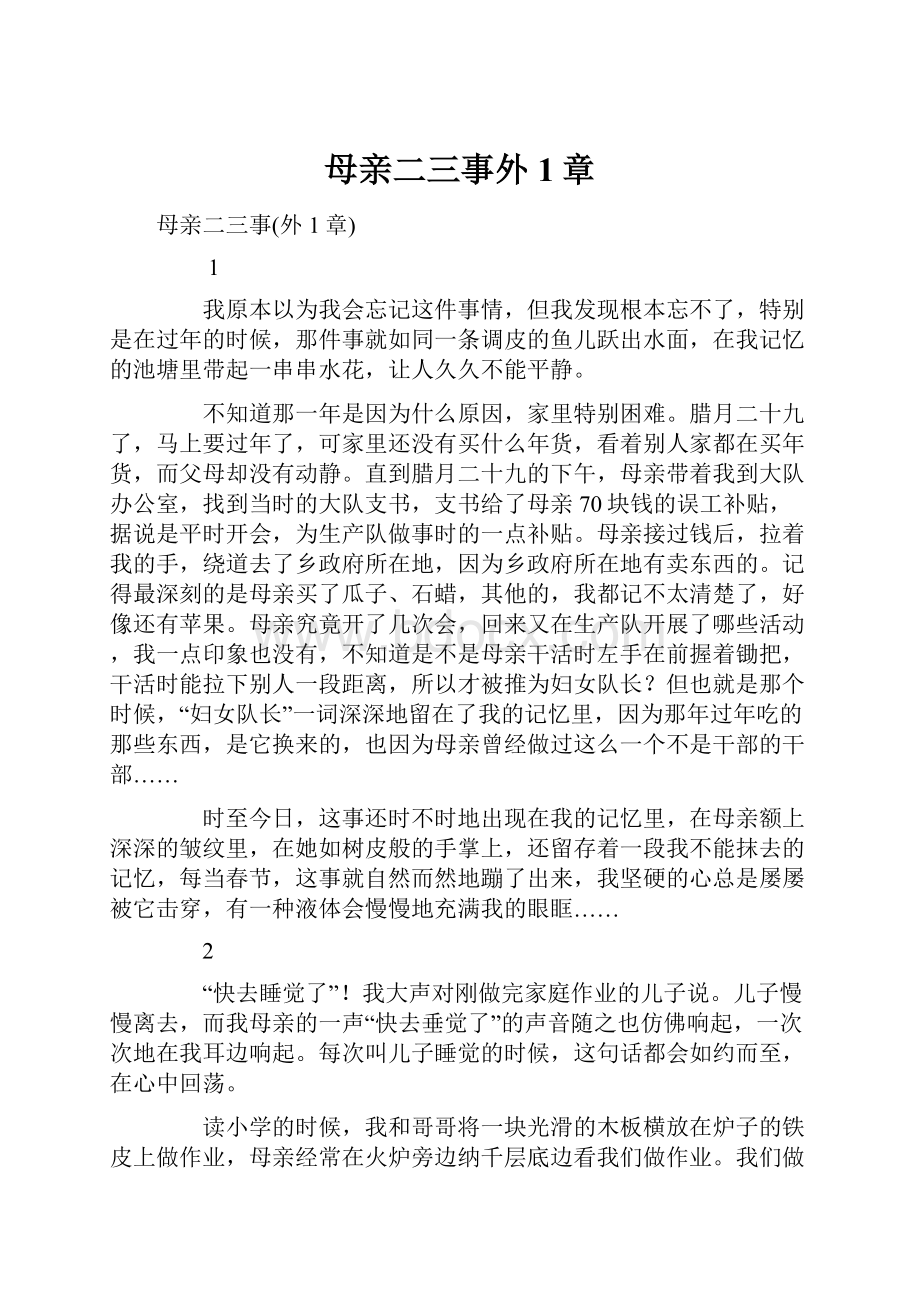
“原来是我读错了,对不起你们啊……”
母亲在家里排行老二,我的第一个外婆死于难产,留下了一个男孩子。
所以在她的上面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母亲称他为大哥,我们称他为大舅。
我外公续弦后又生了五个子女,母亲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兄弟。
在这样的家庭里,重男轻女是必然的,所以我的姨妈从未进过学校,到现在也是仅能写自己的名字;
而母亲受到的教育也极为有限,通过她在家里绝食两天的抗争,外公同意母亲去上学。
先是从一年级上起,他与我三舅同读一年级,那年,她已经13岁了。
一年级读完后,母亲觉得这么大了还读一年级,颇有点丢脸,她自作主张,直接到乡中学读了初一。
很奇怪,她是怎么说服那些老师让她读初一的。
初一还没有读完,外公就坚决把母亲叫回家了,因为我四舅出生了,家里实在忙不开,所以她也就极不情愿地告别了教室,回家做农活了。
她的一生就读了两年书,都是读的一年级,只不过是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现在想来,像她那样连跳这么多级的学生也算是少见吧。
从学校回来后,母亲便再也没有进过教室读书了。
母亲对我和哥哥读书的支持是竭尽全力的。
从我们读书开始,只要是说要做作业,不管家里的农活有多忙,她都会让我们先把作业做了;
只要我们捧着书在读,她也绝对不会叫我们做其他的事情。
那时候为了逃避劳动,我常常谎称要做作业,却偷偷地看些与课本毫无关系的课外书,而母亲也是轻易地相信了,现在想来,真是愧疚。
我和与哥哥都读师范的时候,家里四个人的田土,多数是她一个人在耕耘,只是遇到重活,父亲才会抽出时间来帮忙。
那时烤烟是家里主要的经济作物,有一天晚上,月亮很明,天气格外的凉爽,她决定将一块烤烟地里的草锄了再回家。
正当她忘我劳作的时候,发觉小腿上有些痒,感觉有什么东西爬了上去,她以为是棵草,顺手往外一抓,东西倒是从腿上扒开了,但发现不对劲,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草,而是一条筷子长的雷公虫,雷公虫是我们方言中对蜈蚣的称谓,据说毒性居五毒之首。
在我们这里,筷子长的雷公虫很是少见,母亲看着那雷公虫飞快地游走了,她站在那里全身发软,哆嗦了好一会后,咬着牙坚持把那块地锄完了才回家。
后来我们问她:
“怕那雷公虫吗?
”她肯定地告诉我们:
“不怕!
”她告诉我们,如果那条雷公虫咬了她,她就不治了,家里的钱是给我和哥哥读书的,不是给她治病的。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毅然决然,很是坚决。
后来我们还教母亲查过字典,无奈,她老是将“b-d、p-q、f-t”等搞错,边鼻音也不分,教到后来,她自己也失去兴趣,不愿意学了,总说也不出门,就算学来也没有什么用处。
她不积极,我们自然也就不再坚持了,遇到需要记某人的电话号码时,我在家时,她也会问我们某个字是怎样写的,我们不在,她就会用同音字或想当然地造个字来替代,尽管是错的,但于她而言,对与错都不重要,自己能看懂就行了。
所以母亲在砂石场干活,她会记上一天打了多少方砂石;
她与寨子上的人一起出去做杂工,她会记自己劳作的工天;
我修房子的时候,她会记哪位师傅拉了多少砖和砂石,虽然那些字歪歪扭扭,且错字连连,但却没有记错的,就连那些老板对她也是刮目相看。
她在学校里学的东西、认识的文字极为有限,但她现在还能记账、出门能认些简单的字,也算是奇迹。
最近几年来,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前几次回去时才发现:
她的视力已大不如前,记账时必先取出老花镜;
低下头来时,花白的头发一览无余。
每次回老家时,她都很高兴,夜深时也叫儿去睡觉;
是的,是“睡觉”,而不是“垂觉”。
唉!
她再也不会大声地叫我们“快去垂觉”了……
3
母亲在一家木材加工厂打工,每天工作的时间是12小时,她与另一个人轮流上着白班和夜班。
那天晚上,我们决定回家睡觉,门锁换后,我没有家的钥匙。
于是我到母亲那里去取钥匙。
到木材加工厂后,我不知道她在哪里,因为我从未去看过她劳作的环境。
还好,儿子知道奶奶在哪里劳作,他领着我循着灯光找到了母亲。
母亲的工作是烧锅炉,在轰鸣的机器声中,我看到了瘦小的母亲正弯着腰、挥舞着铁铲将锯木面、废弃的木料铲入炉中。
那些木材加工厂自己制造的燃料堆积如山,正常情况下,母亲每隔二十秒就要铲上一铲。
总共是两个排在一起的锅炉,她刚铲完一边,盖上炉盖,马上又去铲另一边,如此循环往复12小时。
看到我们,她很是意外和高兴,一个劲地怪我取钥匙打电话就行,不用跑到厂里来。
我没有告诉她我打过她电话了,但她没有接,现在看来,如此嘈杂的环境,她怎么会听得见电话响呢?
我走上前去,站在那锅炉旁,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我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太热了!
“这几天还好多了,天凉爽了。
前段时间更热!
“我来铲几铲,你休息一下!
“这活路你干不来,我习惯了的,不怕!
她的手机在一旁放着那年代久远的歌曲,我拿过手机,这应该是部新买的手机,翻盖的,有3个未接电话,全是我打的;
我除去了未接的记录。
她告诉我手机是新买的,花了300元,以前那个实在不能用了。
她还说新手机电池超级好,整晚上放音乐可以放两三个晚上呢。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不停地劳作,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我只要大门的钥匙,可母亲把一串钥匙全给了我,她说她下班回来的时候我们肯定还在睡觉呢。
母亲送我出来,我催促她回去,她却坚持又送了一截;
我再次催促,她才往回走,我掏出手机,打开电筒给她照亮,她摆摆手说:
“看得见,我习惯了的!
”我拉着儿子返身往回走,不经意间回过身去,母亲却又返身站到了原地,正目送我们离去。
我转过身去,冲母亲挥了挥手;
儿子也转过身去,冲奶奶挥了挥手。
她向我们挥了挥手,这才转身。
早上醒来,一看时间,已经是七点过了,按理,母亲应该到家了。
我掏出电话,给她打电话。
她说她已经到农贸市场了,正准备打电话叫我煮饭。
我告诉她昨天已经同儿子的姨妈说好了,到她家吃早饭。
我让母亲把买的东西退了。
她说菜已经买好了,怎么可能退呢?
我告诉妻子,让她打电话给儿子的姨妈,不去她那里吃早饭了。
我煮好饭。
在打扫卫生时,我发现桌子上有一个空的方便面箱子,再一看,旁边的条几上还有两箱,一箱已经空了一半,另一箱还没有开封……
母亲回来了,她买了肥肠、烤鸡、瘦肉、蘑菇、豆芽、鸡蛋。
母亲一边做菜一边吩咐我烧水卤鸡蛋吃,我这才发现她还买了卤水。
她一遍又一遍耐心地洗着那肥肠,细心地切着瘦肉。
我把卤水放到锅里,屋里顿时有了浓浓的五香味,母亲开心地笑了:
“这卤水还可以!
”儿子打开电视,看起了动画片。
熊大和熊二的对话在屋里飘荡,儿子的笑声在屋里响起。
母亲把手机交给我,让我帮她把手机上的“手写”功能调出来。
按着超大的数字键,我这才发现,这是部老年人专用手机,调出“手写”功能后,我发现手机里我的电话号码只有一个,我赶紧把自己的另一个号码存了进去。
我抬头准备问母亲卤蛋是否可以了,阴沉的天气里,昏暗的光线透过窗户洒向了她,她的银发在闪光,笑容溢满早已沟壑遍布的脸上。
饭菜上桌,母亲往孙子碗里挟鸡腿,往我和妻子碗里挟鸡肉、瘦肉。
不断地催促我们赶紧吃菜、多吃菜,不然仅那肥肠已足够她吃一天了。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聊着些童年的往事、老家的亲戚。
我问她那些方便面,她说24包,35元钱,是熟悉的老板给的批发价呢,她半夜里或者是天亮时泡来吃的,她解释说,也不全吃方便面,有时也吃点水果。
吃完饭,我看时间,已是十点过了。
我催促她赶快去睡觉,她没有坚持要洗碗了。
等我洗好碗时,悄悄透过门缝,母亲早已熟睡!
昨天下午,母亲同岳母聊天,说起我们:
“要不是住在街上,我们怕是一年到头也看不了他们一眼哦!
今天早上,母亲打电话问我们是否回去了,没有回去她好做早饭。
我告诉她,我们正在回家的路上,她说如此便泡方便面对付一下;
她嘱咐我开车时不要喝酒、开慢点等等;
我说晓得了。
她“哦”了一声,隔着青山白云,手机里传来了重重的失落……
哥哥
我们出生的时候,父母会给子女起个乳名。
那乳名也颇有时代感,我堂哥的乳名叫做治国;
我哥哥比堂哥晚两年出生,他的乳名叫做爱国。
在我记忆中,父母在田间地头劳作,哥哥就在一边逗我玩。
母亲总对他说:
“爱国,好好带弟弟,你是哥哥哦”。
我听见父母叫“爱国”,我也跟着叫。
时间一长,我就叫顺了嘴,后来也就一直这么叫他。
在我家里有张一寸大的黑白照片里,我和哥哥并排站立,他略比我高,我们穿着黑白两色带碎花的衣服,想来是母亲把自己的衣服拆了为我们缝制的。
哥哥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我们两人的另一只手里都抓着一把油炸的薯片。
在那青石镶边的院坝边,我们站立的条石旁指甲花开得异常灿烂,但看不出绚丽的颜色,因为只有黑白两色。
那年,哥哥四岁,我两岁。
哥哥读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学。
他上学去了,自然就没有人和我一起玩泥巴、捉蚂蚁了。
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屋檐下无聊地走来走去,先是和家里喂的大白狗玩了一会,然后就看着麻雀空中成群结队,一会儿飞过来,一会儿飞过去,永远不知道疲倦;
看蜻蜓在秧苗上歇息,在稻田上舞蹈,蜜蜂带着花香飞进蜂房,然后又精神抖擞地飞出来,嗡嗡嗡地唱着我听不懂的歌曲……
放学了,哥哥在家对面的小路上冲我嚷:
“华二、华二,我给你带麻糖来了,是幺爸用包谷兑的!
”哥哥说的麻糖就是麦芽糖,哥哥说的幺爸是我们这里对最小的叔叔的称呼。
幺爸仅比哥哥大几岁,他在读书时,哥哥也在读书。
时常有卖麦芽糖的到学校里来,没有钱的就用包谷兑换,四斤包谷兑换一斤麦芽糖。
哥哥这么一喊,在坝子上劳作的人都听见了,我爷爷也在坝子上犁田,自然也是听见了,据说当时就骂了声:
“狗日的,又偷包谷了,回家去老子收拾你!
” 哥哥回到家,从帆布书包里取出用练习本包好的麦芽糖递给我。
我迫不及待地在一边美美地吃去了。
幺爸随后到了我家,看着我正努力地撕扯着粘在麦芽糖上的纸……他用手指了指哥哥:
“叫你不要和人说,你还没有到家就开始吼,这下子,到处都听到了,你公(爷爷)晓得了,肯定要打我,下次不给你吃了!
哥哥挠了挠头,说:
“哎呀,我一激动就搞忘记了,我下次一定不和人家说!
但没有了下次了,因为幺爸是个记性极好、小肚鸡肠的人。
过了那次,他真的没有再给哥哥吃过麦芽糖,就算他后来又偷着兑换了几次麦芽糖,还故意在哥哥面前炫耀,却再也不给哥哥了。
那年,哥哥七岁,我五岁。
葫芦寨挨着岩宁寨,说挨着,其实也隔了好几个山头。
因此虽然同属于一个大队,但小孩子们上学后却也是分了团体的,陶家湾算一伙、葫芦寨算一伙、岩宁寨算一伙、高山组算一伙……反正一个生产队算作一个团体。
我们上学时必须从岩宁寨的一户人家门口经过,记得那家姓许,家里喂着一黑一白两条恶狗。
每次从许家门前过,那狗都会在他家的猪圈边狂吠,准备随时向我们扑来。
而那家的大人则好像很少在家一样,偶尔在家听到狗叫时就象征性地出来吼几声,那狗倒也应声而退。
但许家大人不在家的日子,葫芦寨的孩子却没少被吓,有一次一个伙伴还在躲避之中摔下了土坎,满身是泥。
哥哥曾经多次请求许家大儿子许进把狗看好、不能吓人,更不能咬到大家。
但许进说喂狗就是看家护院咬坏人的,并且自家那狗有狼狗血统,即使我们被咬了也是一种光荣。
葫芦寨的孩子受到多次惊吓,无奈之中自发地组建了“打狗队”,大家结伴而行、一致对狗。
十来个孩子被迫“迎接”了一场又一场的自卫反狗战,一起捡起石头像抗战剧里扔手榴弹一样向那两条狗砸去,趁那狗躲闪的时候,年纪小的赶紧冲过去,年纪大一点的在后面“掩护”。
那狗也拿我们没有办法的,但也少不得被砸中后更加狂怒。
许进对我们砸他家的狗大有意见,多次对我们严正声明、强烈抗议,说他家的狗被我们给砸到了,有次白狗的后腿都给砸瘸了,要求我们停止这种“暴力”行径,否则他要叫我们付给狗治伤的医药费。
大家不以为然,从他家门口走过时,只要那狗敢出来,大家照样用石头狠狠地砸。
有一次,我的拼音没有过关,被老师留了,哥哥就一直在教室外等我回家。
留我的老师是位女老师,姓陶。
她留我下来单独训练,叫我抄了好几十遍,读了好几十遍,见我勉强会了才放过了我。
我和哥哥出了学校很远,望着学校,一边走一边唱:
“陶老师,尖尖脚,太阳落坡不放学!
我们饿得轻叫唤,她也饿成空壳壳。
”走到许家门前时,那两条狗狂叫着准备扑过来。
我胆战心惊地望着哥哥说:
“爱国,我害怕,我害怕!
”哥哥赶紧把我拉到身后,飞快地从旁边的土坎上抠出块石头,朝前面的黑狗砸去,一击得手,正好砸中了黑狗的头,黑狗“嗷”的一声,逃了回去。
哥哥蹲下身子,作捡石头状,那白狗见状已无心恋战,掉头就走。
第二天,我们去上学时,白狗出来看了我们几眼,黑狗却在地上趴着,全当我们没有存在。
那两条狗虽然对我们选择了忽略,但许进却特意跑到教室里去找了哥哥。
他指责哥哥把黑狗的眼睛砸瞎了,要求哥哥出医药费,如果不出医药费,他就要收拾我哥。
我哥当然不同意,当即说那狗吓到我了,并且经常出来吓人,每天见葫芦寨的人从门前过,都要咬,它们的眼睛早就是瞎的了;
并且自己早就给许进打过招呼,让他看好狗的。
许进自然不服,他看着比自己矮了不少的哥哥,便和哥哥约好了在放学后进行“决斗”,用武力解决争端。
放学后,我和哥哥来到约定的地点。
许进早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比哥哥高了很多,站在他面前,哥哥显得确实很矮小。
我怯怯地拉了拉他的衣角:
“爱国,我们回家算了,不和他打了。
”哥哥取下帆布书包递给我:
“拿好,看我收拾他!
我抱着书包闪到一旁,看着许进把书包扔进旁边的白菜地里,正好砸到了一棵异常漂亮的大白菜上,那棵白菜顿时就遭受了灭顶之灾,被砸散开了,犹如披头散发、落魄不堪的乞丐。
他冲地上使劲地吐了口痰,然后又吐了些口水在手心,两手搓了搓,接着像他家养的恶狗那样朝哥哥扑来,口里叫着“呀!
呀!
”哥哥往旁边轻轻一闪,许进就扑了个空。
他再扑过来,哥哥又轻轻地闪开了。
许进一把抓住哥哥的头发不放,哥哥也一把抓住了许进的头发,他们僵持了一会。
突然许进咬着牙齿使劲一抓,哥哥用力把头一甩,许进的手里就有了一绺哥哥的头发。
哥哥痛得用力一扯,手却从许进的头上没有扯下头发,他顺手操起田边用来拦牲畜的红籽刺,劈头盖脸地向着许进抽去。
许进招架不住,蹲在地上用双手护住头:
“怎么可以用红籽刺呢?
我要告你,打架用红籽刺!
”哥哥还踢了他一脚:
“看你家狗下次还敢咬我们不,看你下次不把狗拴好!
告诉你,我们不是坏人,你家狗咬到我们是要付医药费的,下次你再不看好你家狗,我还用红籽刺打你!
“决斗”的结果是哥哥大获全胜,我们离开“战场”的时候,许进还在田坎边嚎叫:
“我要告你,我要给你家爸爸告你!
”哥哥拉着我头也不回地说:
“只要你家狗敢吓我们、咬我们,我就打你!
没想到,许进真把哥哥给告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他直接到我家来告到了我父亲那里。
告的理由是哥哥欺负他。
他露出了头上、身上、胳膊上被红籽刺划出的口子、血痕……许进告状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说得声泪俱下,如果说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点也没有夸张。
父亲一边听一边狠狠地瞪着哥哥,哥哥一边听一边准备反驳,我也准备争辩,却被一贯武断的父亲打住了,不让我们说。
许进前脚刚离开我家,父亲就操起了扫帚,劈头盖脸地向哥哥抽来,一边抽一边吼:
“看你欺负人,看你欺负人!
”他打了一会,停了下来:
“错没有,错没有?
”哥哥站在那里,倔强地抬着头:
“没有,我没有错!
父亲又捡起扫帚,冲哥哥狠命地抽来:
“没有错,老子叫你欺负人,还说没有错。
”我站在旁边吓得瑟瑟发抖,想要再次分辩,但被吓得哆嗦着、手脚冰凉,嘴里说不出半个字来。
父亲直把那把扫帚打散了,才停了下来。
哥哥的脸上也被扫帚抽出了丝丝血痕,但始终没有哼一声!
晚上睡觉的时候,哥哥还把他的屁股和背露给我看,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打那以后,许进家的狗似乎有了记性,看到哥哥和我,不敢再狂吠了;
许进家也买了两条铁链子把狗拴起来了,听说是许进哭着叫他爸爸买的,不买他就不去上学了,许家就许进一个男孩子,家里很是宠爱,自然是百依百顺,葫芦寨的孩子这才解散了“打狗队”。
但哥哥的伤痕过了半个月才总算不那么疼痛、看不到明显的痕迹了。
记得那时电视上正播放着一部我已经忘记名字的电视剧,只记得其中的主人公戴着一顶鸭舌帽,按现在的说法是帅呆了、酷毙了。
我向往着能有一顶那样的帽子,拉低帽檐,腰里别着玩具木枪,再把两手插在裤兜里,往同学们面前夸张地走几步,那该是多么拉风啊。
有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和他抵足而眠,不知道怎么就说到了我的这个愿望,他似乎睡着了,没有接我的话。
过了一会他用脚蹬了蹬我的屁股:
“我有钱了给你买个鸭舌帽!
那年,哥哥十岁,我八岁。
哥哥上中学了,我读五年级。
他每周走路到离家四十里远的区中学上五天半的课,星期六中午再走路回家来取生活费。
父亲每个星期给他两元钱做生活费。
有个星期六,他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因为鞋子底磨破了,他的脚上起了个水泡,所以走得慢。
趁他吃饭的工夫,母亲打开檐灯,在院坝边给他洗衣服,从他的口袋里翻出了一元钱。
第二天,他要走的时候,母亲悄悄问他怎么还有一元钱,他说存着给华二买鸭舌帽的,他去问了,要一块二一顶。
他已经存了好几个星期了,下个周就可以给我把帽子带回来。
他把我拉到一边,兴冲冲地给我描述了那鸭舌帽,还说自己戴过,我戴刚好合适。
我一听太兴奋了,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记得曾经承诺过要送我一顶鸭舌帽。
于是,我就天天盼望着周六快点到来,我甚至在睡觉前已经想了不知道多少次在同学们面前怎样显摆显摆了。
周六,直到天黑,哥哥都没有出现。
母亲坐不住了,叫父亲打着葵花杆火把去接一下他。
父亲刚走出门,哥哥就回来了,满脸沮丧,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哭过的。
母亲一边给他做饭,一边听他叙述事情的经过。
他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那鸭舌帽,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帆布书包里,因为要去买鸭舌帽,他也就没有与寨子上的其他同学一起走。
走到半路,他还拿出来戴了一下。
走到乡政府的时候,他觉得快要到家了,有点小激动,准备再拿出来戴一下,那鸭舌帽却不见了。
再一翻那书包,才发现帆布书包的扣子掉了,肯定是在过小路的时候,被树枝给划掉的。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有根树枝使劲地“拉”住了书包,他使劲才挣脱,但却没有回头检查书包。
于是他又回去找那鸭舌帽,一边走一边回忆,一边走一边问后面来的人有没有看到。
他回到树枝“拉”他书包的那个地方,跳到高高的土坎下,仔细扒拉了那些荒草和荆棘丛,但一无所获。
他仍不死心,又沿路仔细寻找,来到半路上取帽子戴的那个地方,结果依然没有帽子的踪影。
他这才垂头丧气、一路小跑往回走,一边跑,一边抹眼泪。
母亲又找了颗扣子给他的帆布书包钉上。
他一边吃饭,又一边掉下了眼泪!
后来,哥哥始终觉得欠了我一顶鸭舌帽。
在我表示心甘情愿放弃鸭舌帽之后,他仍然觉得内疚,后来终于在那年寒假时给我买了本童话故事。
我清楚地记得书名是《365个童话故事》,我兴奋地用毛笔蘸着蓝墨水在书的前扉和书口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遗憾的是那本书后来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其中的一些故事我到现在还有一些印象,有个故事就说的是比目鱼。
那年,哥哥十三岁,我十一岁。
哥哥先于我一年上了师范,第二年,我也上了同一所师范学校。
那一年的暑假,他决定出面去包一辆中巴车运送老乡回家,从中赚取点差价解决我和他回家的车费问题。
经过放假前与老乡的联系,已经有很多人决定坐我们的车了,算下来,差不多可以免除我和他的车费了。
放假那天,中巴车开到了学校门口。
哥哥一边照着名单点人,一边嘱咐我给大家看好行李,因为行李很多,地上堆了一堆,还有些得绑在中巴车的车顶,所以需要人专门照看行李。
等行李绑好后,我决定上个厕所,等我上完厕所回来,车已经开走了。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到几百里外的地方读书,我甚至搞不太清楚我应该往哪条路上回家。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小学生都用上了手机。
无奈之中,我焦急地回到了熟识的老师那里,老师建议我坐黄包车到郊外必经之路去等。
我便依着他的话,坐着黄包车到郊区去等。
还好,黄包车跑到了前面,哥哥在车上发现了正在路边等候的我。
他不等车停稳,就从车上一下子跳了下来,然后对我招手说道:
“快上来,快上来,吓死我了,要是把你搞丢了怎么办?
”他的脸色有点苍白,声音也带着哭腔,看得出非常的焦急。
那年,哥哥十九岁,我十七岁。
我与哥哥决定建房,我们夜里去小山村里买木料。
他早骑着摩托车经过崎岖的山路,经过一路颠簸后与山里的村民谈好了价格。
村民砍好木材后,我们只需要叫上农用车去运输。
那时,他在村小工作,我在小镇上。
当地人帮我们往农用车上装好木料后,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过。
当我们把木料运到工地上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过了。
皓月当空,夜风徐徐。
司机停好车,到驾驶室睡觉去了。
我和他开始从车上搬卸木料,母亲在车上帮我们把木料从车上推下来,他站在车下接着。
等木料快要完全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们一人扛一头,他总是先于我一步扛上大的那一头,我这头都是小的。
那年,哥哥二十九岁,我二十七岁。
后来,我去了交通运输局工作。
一天阴沉沉的,我坐在办公室开着空调,仍然觉得热得不行,感觉大雨将至,而我的眼皮也一直跳个不停,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下午,我就接到了哥哥打来的电话。
原来,哥哥买的新车在开回来的路上出了意外。
要命的是卖车的老板骗了他,没有给他办临时牌照,车子被外地的交警扣留了,说没有临时牌照是非法上路。
他认为我在交通运输局工作,应该和交警的工作有交集,便打电话给我让我找人补个临时牌照。
其实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员,和交警有交集的时候很少,况且到新单位工作的时候也不长。
我不忍拒绝他,硬着头皮到处打电话,结果还是没有办成,他的焦急写在脸上,在眼睛里闪烁,但却故作轻松地挥着手对我说没有关系,他再想办法。
他回去的时候天上大雨如注,我心里也下着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