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Word格式.docx
《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感知与洞察研究实践中的现象学社会学Word格式.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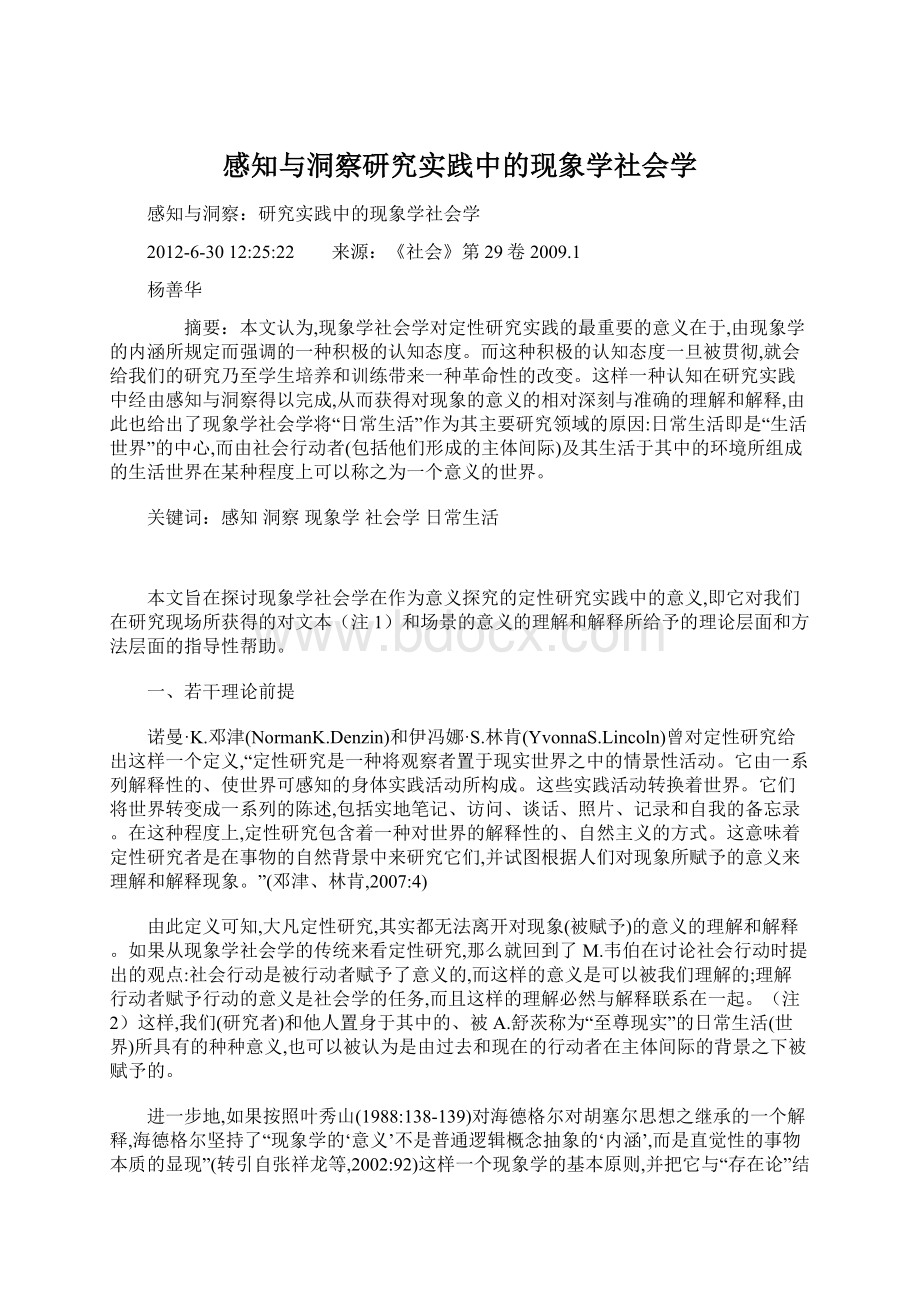
它由一系列解释性的、使世界可感知的身体实践活动所构成。
这些实践活动转换着世界。
它们将世界转变成一系列的陈述,包括实地笔记、访问、谈话、照片、记录和自我的备忘录。
在这种程度上,定性研究包含着一种对世界的解释性的、自然主义的方式。
这意味着定性研究者是在事物的自然背景中来研究它们,并试图根据人们对现象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和解释现象。
”(邓津、林肯,2007:
4)
由此定义可知,大凡定性研究,其实都无法离开对现象(被赋予)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如果从现象学社会学的传统来看定性研究,那么就回到了M.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
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
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
(注2)这样,我们(研究者)和他人置身于其中的、被A.舒茨称为“至尊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所具有的种种意义,也可以被认为是由过去和现在的行动者在主体间际的背景之下被赋予的。
进一步地,如果按照叶秀山(1988:
138-139)对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思想之继承的一个解释,海德格尔坚持了“现象学的‘意义’不是普通逻辑概念抽象的‘内涵’,而是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显现”(转引自张祥龙等,2002:
92)这样一个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并把它与“存在论”结合起来。
“‘存在’、‘有’就是‘让’(Lassen)事物‘呈现’出来,自己让自己呈现出来。
于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最精髓的概念‘显现’被保存了下来。
”
这一论断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作为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自我呈现的意义的显现是一种“存在”,是“有”,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感知它或者发现它。
因此,只要我们去感知或者去发现,我们就能获得对这样的意义的认知。
具体到定性研究来说,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研究现场听到的被访人的讲述、观察到的被访人的生活环境,以及我们和被访人正在互动的访谈场景都是被被访人赋予意义的。
或许也能说,这样的意义是肯定存在的。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这样的意义,那只是说我们没有去感知或没有去发现。
所以,按照这样的理路,现象学社会学将研究从一开始就带入经验调查的现场的同时,也倡导了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也就是说它强调一种主动投入到田野研究的场景中去感受和认知的精神。
二、感知:
悬置、意义的辨析与区分、意义的逻辑
(一)被访人的日常生活:
感知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
A.赫勒(1990:
3)曾将日常生活定义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并且强调“日常生活存在于每一社会之中”,“每个人无论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的地位如何,都有自己的日常生活”。
这是因为日常生活首先就是个体为保证自己生存而进行的种种活动(对个体来说从事这样的活动必然会有时间的耗费和空间的转换),在这样的活动中,社会制度对个体的规范、限制与约束,以及观念层面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也得以展现。
并且,因为它与每个个体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以生老病死为表现形态的生命过程相联系而呈现出一种“常态”,即具有重复性和稳定性。
但是,在社会出现纵向的分化形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之后,这些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不同位置的社会集团会对自己面对的“常态”赋予不同的意涵,他们的生、老、病、死因此也获得了各自的意义。
所以,日常生活是被打上社会的烙印的,它被赋予的意涵因此也具有鲜明和浓重的社会性。
因为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都有时间的耗费和空间的转换,因此,从经验的层面上看,我们可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时间分成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两个部分。
“事件”时间是指当生活中出现各类对个体及其从属的群体(比如家庭)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时,被访人及其所属的群体在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它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在总量上则可长可短;
日常生活时间通常是指个体为了生存和满足自己生理需要所耗费的时间,它的特点是具有重复性与稳定性,如做饭、吃饭、生产(工作)、交往和休息等。
但是,日常生活时间和“事件”时间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个体之所以能被动员起来是因为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具有了对自己从属的群体的认同,看到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和在事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这样一种意识和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了解显然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日常生活之所以能成为我们考察个体活动(行动)的主要领域,是因为这些活动是被作为行动者的个体赋予了一种意义的(比如虽然每天都要吃饭,但是外面的饭局和家里全家人一起吃的家常饭就会具有不同的意义),而且一个社会在没有发生战乱与灾害等波及全社会的重大事件的时候,它所呈现的常态就是这样一种日常生活。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就成了现象学社会学家A.舒茨的“生活世界”(那坦森,1982:
159)(注3)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用A.舒茨的话来说,它是生活世界的中心,是“至尊现实”(转引自李猛,1999,20)。
他认为,社会行动只能具有一种主观意义,即行动者本人的主观意义(但意义的产生除了主体外,还需要主体在其中生存并与之互动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参见霍桂恒,1996:
337)。
而生活世界则是人们在其中度过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经验的主体间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体,和他人共同构成生活世界)的文化世界。
其特征是预先给定性,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
A.舒茨对研究对象所作的“现象学分析”是指将研究对象视为“现象”并还原成最初赋予意义的经验,只不过他所针对的不是认识主体的主观意识,而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力求从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出发阐明其意义结构(杨善华、刘小京,2000)。
由上所述可知,作为某一特定社会群体一员的被访人的日常生活之所以会成为我们感受的对象和研究的重心,是因为日常生活是他(她)生存的主要表征,并且这样的表征充满了社会学的意义。
而上文中A.舒茨对“现象学分析”的阐述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基础,即我们要认识、把握并在理解基础上给出解释的是“处于生活世界之中、具有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而不是我们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所以一定不要用我们的主观意识来代替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
(二)悬置
从认识和把握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识这一点出发,胡塞尔所强调的“悬置”就构成了感知的前提和必经的步骤。
所谓悬置,在胡塞尔那里,简单地说,就是中止自然态度(注4)下的判断,“我们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并由此,“我排除了一切与自然世界相关的科学”(胡塞尔,1992,97-98),尽管它们依然有效,但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不再使用与之相关的任何命题、概念,包括真理。
只有经过悬置,才有可能去讨论作为“世界消除之剩余的绝对意识”(同上,133)。
我们可以运用同样的方法,来对研究者自身的日常生活知识体系,以及社会科学的体系、知识以至判断进行悬置,也就是暂时中止研究者原有的自然态度以及科学态度的判断。
悬置的意思是悬置我们自己(研究者)原来持有的“成见”,即我们(研究者)以前所有的理论预设,它包括我们(研究者)对于某些东西的习惯性信仰,以及对传统的割裂个别与一般的理论框架的悬置。
当我们进入田野调查现场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抛掉前述“成见”的前提下,全神贯注地去感受被访人的各个侧面(包括外貌、衣着、神情和语言,也包括访谈进行中的环境。
如前所述,所有这些都是被访谈对象赋予了一定意义的),(注5)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就好像是用一张尽量素白的纸去“印”田野调查时的场景和被访人的各个侧面,从而获得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
当然,这样的感知和认识是要经由沟通性的理解才能得以实现的(杨善华、孙飞宇,2005)。
(三)意义的辨析与区分
“悬置”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在排除了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和观念之后的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注6)和认识。
应该说,它与研究者感受被访人、访谈内容和访谈现场这样的“材料”是基本同步的。
所以,悬置是感知的前提条件。
但是这样的感知肯定会有一个结果,即获得“相关材料”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样的田野调查与访谈中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未必都有社会学的意义。
然而从我们研究的学科特征来说,我们应该获得的是具有社会学的意义的素材。
所以,意义的辨析与区分就是在感知的同时,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材料从所有的材料中分离出来,并争取完成研究层面的提升——争取由经验层面提升到理论层面,作出一个经验层面上的生动和鲜活的理论概括。
杨善华、孙飞宇(2005)在《作为意义探究的深度访谈》一文中曾提出三层次的文本分析一说,认为在第二层次开始于对文本蕴涵的意义的价值的认识,要做的就是发现被访人的叙述中的精彩之处和闪光点,同时也可以对被访人做一个“类”意义上的认识(被访人的个性中有哪些特征具有“类”的意义或具有某种共性)。
我们还认为,在这个时候,研究者的社会学视野开始显现,因为精彩点的发现和“类”的特征的把握都是以某种普遍性为前提的,而研究者只有具备一种社会学的全局观和理论意识才能对这种普遍性有相对准确的把握。
显然,这样一种分辨和区分是在对材料的选择及对材料意义的解释中体现出来的。
因此,这一步解决的是感知什么、如何感知,以及对研究者的社会学素养的要求等问题。
而这样的感知,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本质直观”的一部分,是本质直观的内在基础;
所以说到底,本质直观并不外在于原初感知(不是对于感知加以抽象、概括的结果),而只是通过观察目光的调整而改变统握感知材料的方式罢了,也就是从感觉直观的方式转变为概念直观或范畴直观,发现更高层的关系结构。
我们要选择的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普遍性的材料,而这样的普遍性显然是具有“类本质”的属性的,但又是浸润在原初的感知场之中的。
(四)意义的逻辑的把握
在访谈的现场,我们可以通过感知发现一种意义的一致性,即被访人赋予自己访谈的内容与他的外貌、穿着打扮,以及他赋予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意义(如果是在被访人家里进行访谈)是一致的(这就是“意义的逻辑”)。
这是因为这样的意义赋予是与被访人的生命过程紧密相连的,在这样的生命过程中形成了被访人(社会分层中)的自我定位、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的行为与个性特征。
而在访谈过程中,被访人的访谈内容和他的外貌神态和行为举止会隐约或清楚地体现这一切,以至到最后可以浓缩或突显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类的判断。
这时我们就获得了解读被访人赋予其话语和行为意义的钥匙,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获得了探索被访人内心世界并完成对被访人的理解和解释的可能。
这样的意义逻辑,也是加芬克尔所言的用于理解表达与行动的“索引性”(indexity)(李猛,1999:
57-58)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由此去追溯被访人在访谈中未予明确言说的言外之意。
这就为下文的洞察提供了一种可能。
三、洞察:
感知的目标和结果
根据叶秀山对海德格尔对胡塞尔思想之继承的一个解释,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的‘意义’不是普通逻辑概念抽象的‘内涵’,而是直觉性的事物本质的显现”。
因此,作为感知的目标和结果的洞察,就是在直观式的感知中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这样的事物本质是“显现”在那里的,是只要你去感知就一定能认识它的。
上面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阐述的另一个意思是,这样的本质就是事物自身所显现的意义(参见倪梁康,1994:
81),所以就是这样的意义与事物(现象)一起同时呈现在那里,等候着我们的感知和发现。
从我们的实践来看,作为感知的目标和结果的洞察,它可以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第一,对被访人言外之意的洞察。
这构成了对被访人贯穿在访谈中的主观意图的判断的一个重要环节。
该讲的被访人没有讲,该答的被访人回避了,这都反映出被访人的意图和价值观,或者这件事情与被访人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有的时候被访人也会用曲笔,即非常含蓄地表示他(她)对一件事情的态度,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可能涉及他们的家庭关系中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或者是因为存在着感情方面的伤痛。
除此之外,对被访人在社会结构和社区利益格局中的位置的了解也有助于这样的洞察。
比如,当一个领取最低社会保障的城市贫民自豪地称自己家里从不欠债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就是他的人格尊严之所在。
(注7)当然,这样的洞察仍然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发生的,或者说它是经由直观式的感知获得的,因为这是我们在访谈的现场听取被访人讲述时得到的。
一个训练有素的访谈者几乎可在被访人叙述这一内容的同时感知被访人叙述背后的意义。
第二,对现象“本质”的洞察。
上文曾提及对田野调查现场意义的逻辑的感知和把握,由对意义的逻辑的阐述可知,一旦我们实现了这样的感知与把握,其实已经完成了对现象本质的洞察。
但是,由对“本质”的界定可知,其实这种对“本质”的洞察最重要的是对现象所呈现的意义的普遍性的洞察。
而当进到这一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提炼和关系统握已经出现,只是这种提炼和关系统握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的“萃取”,而并非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当然,这样的“萃取”的背后一定会有社会学理论与视野的构成作用。
比如,当我们根据西部农村几户村民在生产与生活中的长期互助,进而提出“道德共同体”这样的概念,来回应地形为山区与半山区的农村社区在分田到户后出现的、差不多是一盘散沙的社区整合状态时,我们的问题意识与社会学视野就得到了清楚的显现。
此外,我们考察现象所呈现的意义的普遍性,其最终目的还是要落在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这一点上。
因此,当我们发现苏南和浙东农村社区的老实本分、奉公守法的民风,并以它来回应社区秩序的形成机制这样的问题时,其实我们是在跟以往关于“社会何以是可能的”的研究作理论对话,但是,诚如大家所知道的,“社会何以是可能的”恰恰是社会学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第三,对现实社会生活与制度安排中“盲点”与悖论的洞察。
(注8)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A.舒茨认为,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其基本特点就是自然态度(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转引自李猛,1999)。
它使人们认为生活世界是不言自明的现实,这些抱有自然态度的普通人都会想当然地接受它。
其原因则是因为生活世界具有预先给定性的特征,即它存在于社会个体对它进行任何理论反思和理论研究之前。
因此,在每个个体开始社会化的时候,他(她)所要学习的有关社会的知识和规范都是已经存在的,而且大量是常识性的(比如婚丧嫁娶的风俗)。
这种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接受,这是因为个体会发现别人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知识和规范,他(她)若不接受就会变成异类而被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群体所排斥。
但是,恰恰因为这是未经反思的、想当然的“自然态度”,这种态度以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就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悖谬的。
福柯(1997:
3)曾揭示“自由”的悖谬。
他指出,某些自由对人同样具有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因为“那些约定俗成的制约”“并不写在法律条文里”,“而是隐含在普遍的行为方式中”。
福柯这段话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当“自由”从价值层面降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的时候,其实就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而自由的要义恰恰在于它是个人所具有的选择的权利。
所以,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不会将自由看作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从而只是在制约和自由之间去寻求一种平衡。
而我们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多是未经反思的(尤其是像风俗这样的不成文的制度),甚至有些过去看似合理的制度,因为形势和体制的改变,也会失去它的合理性,但是却仍被我们继承下来,成为制约我们前进的因素。
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即我们想推行的制度因为脱离实际而出现悖谬。
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就有一个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的悖论,即当追求男女平等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要求(就业)机会平等的时候,会因为男性和女性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她们又拒绝特殊照顾导致结果的不平等,但是当她们要求结果平等的时候,也会因为上述原因而需要社会作出某种政策倾斜来保证,但这恰恰是追求无条件的男女平等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
(注9)而有的时候,人们也会在贯彻执行某项制度的时候忽视了该制度的执行前提,从而将此变成一个盲点。
比如“村民自治”,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一般都认为这是一项推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同时又可以在党的组织作用健全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用它来履行政府机构的行政职能而又不增加自己的财政负担的好制度。
但是当研究揭示出村庄政治精英和能人的大量流失导致村落社会的解体这一事实的时候,村民自治需要村庄政治精英与能人的参与这一前提条件就会显现,同时也会使人们意识到这恰恰是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执行中的盲点。
四、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首先,托马斯·
A.施瓦特在《定性研究的三种认识论取向:
解释主义、诠释学和社会建构论》(注10)一文中认为,解释主义传统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它们将人类行动视为有意义的;
第二,它们以对生活世界的尊重和忠实的形式表明了一种伦理承诺;
第三,从认识论的观点看,它们共有着新康德主义强调人类主体性(如意图)对知识的贡献,而同时又并未因此而牺牲知识的客观性这样一种偏好。
(注11)应该说,这确实体现了现象学社会学的特征。
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从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根源现象学的层面来看的话,那么,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现象学社会学在强调了“在社会世界中个人主体间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动的客观意义的根源”(Outhwaite,1975:
91)的同时,也必然会倡导一种积极的认知态度。
从我们的研究实践来看,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认知态度使我们对材料的感受变得日益敏锐。
其次,虽然本文对感知和洞察作了区分,但是在此笔者要申明的是,根据解释主义的传统,当理解被视为一种“认识者(作为主体的研究者)获取关于某一对象的知识(人类行动的意义)的智识过程”(同上)的时候,那么在认知的层面,其实我们是无法将感知和洞察明确分开的,因为感知和洞察就意味着理解的发生与解释的给出,因此,感知到就意味着洞察的发生。
再者,这样的感知和洞察,在实践过程中最后会表现为一种直觉,或者说研究者对材料的一种即时反应。
当研究者作出这样的反应时,其实已经省略了感知与洞察发生的一系列中间过程,而只是将材料的意义(本质)以直观的形式显现在自己的脑中,因此它类似于禅宗的“顿悟”,有点“直指本性”的意味。
而这样的灵气也是认知现象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纯粹西方的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释道两家有了相通之处。
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现象学社会学的训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直觉的培养。
最后,归根结底,现象学与现象学社会学并不是要提供一种对世界或者对社会的终极认识或者终极理论。
按其本意,它提供的只是我们认识胡塞尔与A.舒茨都将其看作是研究的重心的生活世界的原则与通路(当然也可以包括我们研究与分析生活世界不可或缺的某些方法论与方法方面的启示)。
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社会学是开放的,就像现象学是开放的一样。
我们要完成的只是按照多姿多态的生活本身来认识生活这样一项任务,而这可以借用现象学的一句话来概括——朝向事情本身。
作者简介: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本文是我们课题组多年实践的一个总结。
我要感谢所有参与这一实践的课题组的同事和同学,感谢他们在田野调查的讨论与总结中闪现的思想的灵光,使本文的轮廓日益清晰,内涵日益丰厚。
因此,这是集体的创造,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我还要感谢张祥龙教授,他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注1:
这里的文本首先是指被访人在接受访谈时的叙述,这样的口头叙述若被记录就会形成一个书面文本。
注2:
虽然后来A.舒茨对M.韦伯的说法有很多批评(详见Schutz,1972),比如认为M.韦伯没有注意到文化客体制造者的意义与被制造客体的意义,意义在自我、他人那里的构成、修改,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自我理解与理解他人的重要性等,但是从我们的经验研究的实践看,M.韦伯对社会行动所蕴涵的意义作出的判断,仍然可以成为我们讨论现象学社会学传统的定性研究的实质的出发点。
注3:
A.舒茨的学生那坦森(1982)曾简明地将生活世界概括为“包括人所牵连的种种日常事务的总和”。
注4:
这种自然态度是每个人在其自身的日常生活中所具备的,即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
其间,首先是将这个世界,包括自己的世界视为理所当然(takeitforgranted)的存在;
其次是如上所说,将自己与他人的沟通视为理所当然。
而按A.舒茨的说法,这也就是人们对生活所持的最初的、朴素的、未经批判反思的态度。
注5:
对于研究者与被访人的互动过程中意义的理解的问题,孙飞宇在《论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上)(《社会理论学报》第7卷第2期,2004年秋季卷)中亦有深入的分析。
注6:
感知”在胡塞尔认知现象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按胡塞尔的说法,感知是原本意识,因为感知所统握的是感觉材料,即体现性的、自身展示性的内容。
因此,作为直观行为的感知与同样作为直观行为的想象相比,是最原本的,是一种“当下行为”(呈现行为),而想象是“当下化行为”(再现行为)。
(参见张祥龙,2002)
注7:
当然,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对意义的逻辑的感知与把握使我们获得了感知被访人言外之意的一种索引性,这也有助于获得对被访人言外之意的洞察。
注8:
盲点的一个最通俗的解释就是熟视无睹,即对某种现象可能天天看见,但却没有想过这个现象可能是不合理的,甚或是悖谬的。
注9:
这一部分论述可参见杨善华的《关注常态生活的意义——家庭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初探》,《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注10:
托马斯·
A·
施瓦特将A.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归入解释主义的范围。
注11:
此段施瓦特的引文载诺曼·
K·
邓津和伊冯娜·
S·
林肯主编的《定性研究:
方法论基础》第209页,风笑天等译,2007年1月,重庆大学出版社。
参考文献:
邓津,诺曼·
K.、伊冯娜·
S.林肯,主编.2007.定性研究:
方法论基础[M].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福柯,米歇尔.1997.权力的眼睛——福柯访探录[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赫勒,阿格妮丝.1990.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
胡塞尔.1992.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