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词汇研究传统的人文阐释Word文档格式.docx
《古代词汇研究传统的人文阐释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代词汇研究传统的人文阐释Word文档格式.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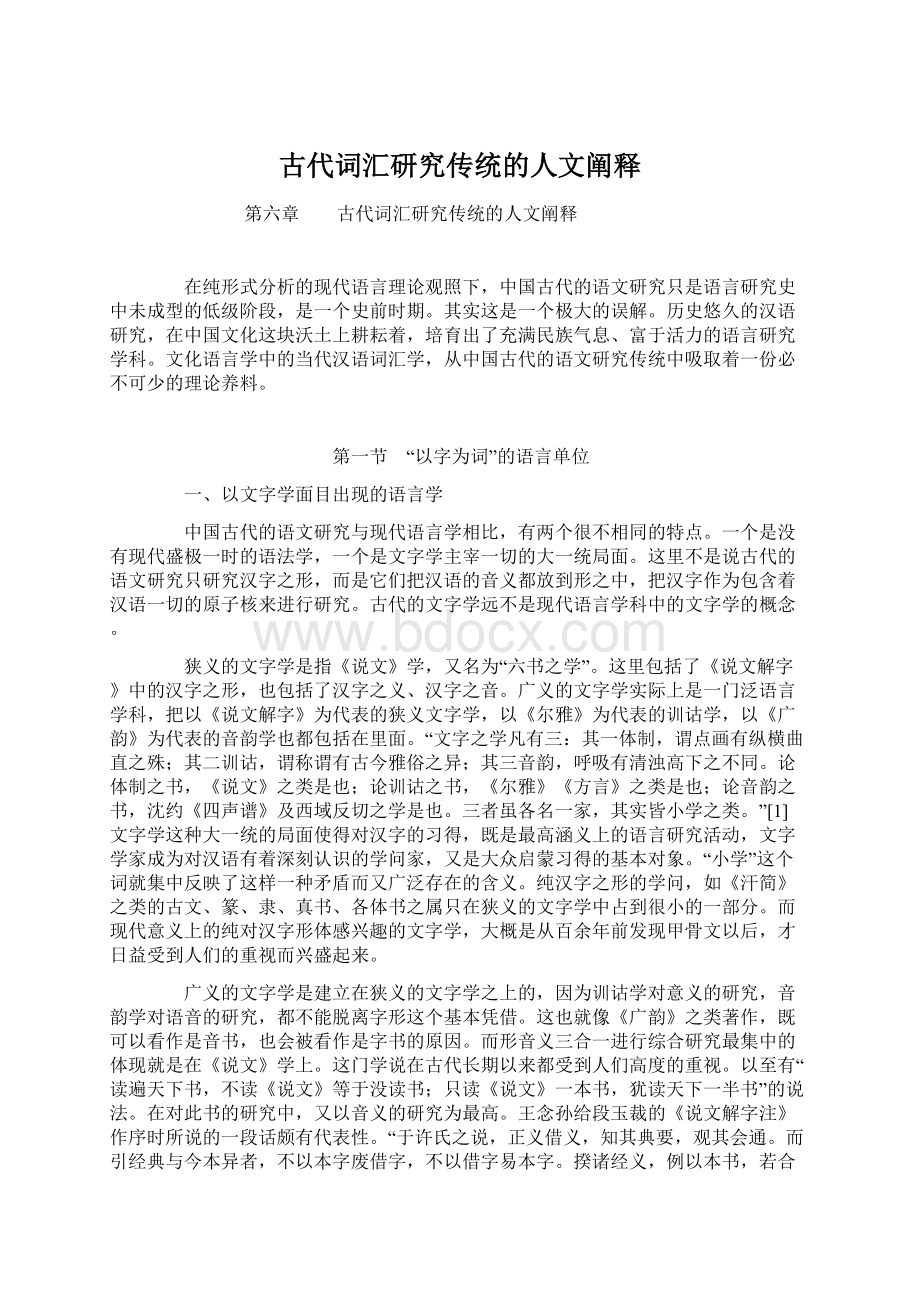
王念孙给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作序时所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于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
而引经典与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
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
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
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若夫辨点画之正俗,察篆隶之繁省。
沾沾自谓得之。
而于转注假借之通例,茫乎未之有闻。
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声音训诂也。
其视若膺之学浅深相去为何如邪。
”在传统的文字学中,将形音义转辗对应起来进行研究的,才是最高境界。
单纯的笔划竖直的字形研究则一直受到人们的鄙薄。
这就是因为“《说文》之学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
这当然是因为此书太重要了,而更底层的原因则是汉字本身就是形音义合一的语言单位。
只不过是许慎首先看到了这一点并把它赋之于实践而写出了这部千古不朽的伟大著作。
这样,就使得后来的语音之学一直与文字学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凡许氏形声谓若,皆与古音相准。
或为古之正音,或为古之合音。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循而考之,各有条理,不得其远近分合之故,则或执今音以疑古音,或执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
”段玉裁所以在研究《说文》上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也就在于他就是从语音的联系上来爬梳整理,创构出古音十七部。
二、以字为词的语言单位观
曾有人说古代的语文研究只重视书面语,轻视口语,其实这是很肤浅的看法。
固然前代能够传来下的只有用文字记载了的文献,但就是当代的语言哪里又不是用汉字来记载的呢?
中国古代文字学大一统的局面之所以形成,更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以字为词”的基本语言单位观在支配着人们。
人们已经看到,汉字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笔划构成体,而是语言信息满负荷反映的自足的语言基本实体。
汉字不是单纯作为一个视觉符号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是它本身就是语言的最基本的一级单位。
在它身上,意义、语音都融合为一体,都能够从字形上予以清楚准确地反映。
在语音上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是音节,而一个音节正好与一个汉字相配。
在意义上,词以载义,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而汉字正好以它自身的结构或以象形显之,或以会意示之,或以形声类之。
在形态上,汉语词不具备这方面足够的信息,没有首尾的词缀变化,也没有足以别义的内部语音屈折,因此在汉字字形上也就是完整一个,一旦结构凝固,它就是一个示意整体。
汉字是以“结构”而不是以“笔画”来表意的。
这样,汉字与汉语中的单音词发生着神韵相合的关系。
字也就是词,认识汉字也就是认识汉语,古来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能不能说这就错了呢?
持肯定说法的人大都是以西方的文字语言关系观作为立论的基本落脚点。
其实,西方的文字也是与它们的语言相合拍的。
它们的词充满着形态变化,词的语音屈折比较丰富,它们的语音变化直接揭示着许多的语言信息。
如词性的诸多语法属性,时、人称、数、格、语气、态,都会通过一定的语音差异显示出来。
它们的语音基本组合是一个有机的弹性体,可以随时在一个词的语音载体上作出适度的变移。
在这里,一个稳定、凝固、不可再分割或再迭加的文字结构都会成为不可取的表达形式。
问题不是西方的语言文字与中国的语言文字孰优孰劣,它们都各自很好地发生着契合的关系。
问题在于以一方之规矩律另一方之梁木,就会出现方枘圆凿的尴尬局面。
假如不是像现在这样以西方文字来律东方的汉字,而是将汉字在西方语言世界强行推广,试想这里面的闹剧一定也是非常可笑的。
古人长期以来在对汉字的认识中,他们确实是体会到,通过汉字是完全可以认识汉语的,通过汉字是可以真切地体会到汉语口语词所表达的一切的。
固然在汉字与汉语的音节中会出现交叉表达的情况,一个字表示几个音,一个音用几个字来表示。
但如果不是停留在这种机械地、静止地看法上,而是还进一步地看到,许多汉字拥有一个形,同时也就是拥有了这个形的音,那么,汉字同构字、同旁字的建立,不也就是语音上声母或韵母同类字的建立吗?
这就是汉字谐声系统形成的原因。
前人正是依据它对早已湮没了的先秦语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同声(旁)必同(韵)部”,实在是道出了形与音之间的密切关系。
三、以汉字形式为依据的释义方法
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有着释义的三大方法:
义训、形训、声训。
这里面就有两大方法是建立在汉字之上的。
所谓的形训就是根据汉字的字形对意义作出解释。
所谓的声训就是根据汉字的字音对意义作出解释。
它们的目标都是对字义的揭示,对字义与单音词词义之间基本合一的对等关系是不用怀疑的。
但对字义的揭示却凭借的都是汉字的形式部分。
这只能说明汉字的形音义确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这三大释义方法中,最具民族特色,也最起直接作用的就是形训。
形训是古代运用最广、历史悠久的一种释义方法。
“止戈为武”,“自环为厶,背厶为公”,就是在先秦已经出现了的形训。
而大规模运用形训的是《说文解字》。
如果说《说文解字》最大的贡献只有两个,那么除了首次建立汉字部首以外,最具影响的也就是总结并大规模地运用了据形释义的形训方法。
它对9353个汉字都释了义与形,有的还释了音。
它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它在汉字的义与形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又自然的联系。
如“牛”字是象形字,“像角头三、封、尾之形也”。
在指称与牛有关的大小、雄雌、毛色之义时当然是用以“牛”为偏旁的字,如“牡”“牝”“犊”“牲”等。
而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通用义上也用了“牛”来作偏旁。
“牢,闲,养牛马圈也。
”“牵,引而前也。
”“物,万物也,牛为大物。
”牢、牵、物表示的都是通用义,如果说前两个是先用于确指再扩大开去的,那么第三个“物”字显然是为了指称这样一种有普遍性的词义才用上了“牛”的字形。
“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
”这就清楚地说明古人在要表达一个意义时,总是千方百计在汉字的字形上赋予一些有特征性的东西,总是尽量在字形与字义上建立直接的联系。
这也就给形训方法的运用奠定了异常牢固的基础。
有人说《说文解字》中的释义“十之八九”是声训。
如果这点能成立的话,那么这首先也是建立在形训基础之上的。
如“政,正也”,“示,神也”,“帝,谛也”,都有字形的相叠夹杂在里面。
据形释义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
第一,对字本义的揭示。
汉字起源悠久和汉字长期稳定决定了它所反映的词义也就久远,不曾中断。
因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对许许多多的汉字字形上窥出、猜出,或直接度出意义所在。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试看当今世界上哪里还有像汉字这样具有悠久表义能力的文字系统。
第二,对类化义的揭示。
汉字对本义的反映,会通过汉字的繁衍而保留下来。
汉字是孤立的,一个一个分别存在的。
但汉字又是一个有联系的大系统,它们并不是几千个几万个互不关连的象形字的组合群体。
象形字只有200多个,其它都是在这些象形字之上组合搭建构架起来的。
在象形字身上建立了指事字,在象形字指事字身上建立了会意字,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身上建立了形声字。
这样一层层地叠加,字形组合到一起去了,字义也组合到一起去了。
寻到了一个汉字之根,就可以寻找到一个汉字之群。
寻到了一个汉字字根的意义,也就寻找到了一个汉字之群的意义范围。
为什么人们一直对《说文解字》部首表示了特别的钟情,就是因为一个部首总是揭示着一个大的意类。
“凡山必言山,凡水必言水”,古人确实是看到了汉字偏旁对义类揭示的重要作用。
“秀才识字识半边”,它嘲笑了半通不通的浅学文人。
其实如果它指的这个秀才是面对从未识过的汉字的话,那么这种“识半边”又是一种简便无比的方法,它依靠的正是汉字表达类义的功能。
第三,对词义引申方式的确定。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词语绝大多数都由单音词走向了多义词。
在一个多义词中间,具有回转往复的词义引申关系。
它复杂,会令人不得头绪,它幽秘,会令人感到突兀,这时依靠形训的方法往往会使人豁然得解。
如“间”字之义甚多,有“中间”义、“嫌隙”义、“间隔”义、“空闲”义、“隔阂”义、“侦伺”义、“离间”义、“间谍”义、“隔离”义、“更迭”义。
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它还有许多灵活生出的临时义,如“肉食者间焉”中的间是“参与”义。
要对这么多的词义进行整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抓住本义。
从“间”的字形上可以判断出来,它最早指的是两扇门中透过日月之光。
同样是着眼于两扇门之间的距离,它可以就这一静止的状态引申出“空隙”“隔阂”方面的一串词义,也可以引发出动作性的词义“离间”等一串词义,还可以将它运用到不同的具体场景、不同环境中产生“空闲”“更迭”等诸多意义。
汉字字形可以在这方面给人以展开丰富联想的空间。
声训就是依靠语音,主要也就是依靠字音来解释意义的方法。
“古无韵书,训诂即韵书也。
古无训诂书,声音即训诂也。
故古代经典文字多用音相借,训诂多声近相授。
详考吾国文字,多以声音相训,其不以声音相训者,百不及五六。
故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反是,即非真正之训诂。
”[2]经过清代学者的总结,声训之法在释义方法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声训在两个方面突破了形训的局限,一是在深层义的了解上,声训具有特别的功用。
二是对同源词的认识上,语音的相同或相近成为同源词构成的外部形式之一。
它突破了一个个具体字形的限制。
但如果不是落实在每一个具体字形,而是在整个汉字体系上来看,特别是在排除掉具体文字运用过程中临时产生的通假字,那么就可以看到,汉字声音的联系其牢固的根基之一就是汉字的字形,声训方法与形训方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清代有成就的训诂学家就是从汉字的文字体系与汉语的语音体系结合起来,探讨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六书之有谐声,文字之所以日滋也。
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
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
……谐声者必同部也。
三百篇及周秦之文备矣。
”[3]
形、声、义三者相依相存的情况,在下面两类情况中表现尤为突出。
一是声旁含义。
声旁是汉字结构中的一个部件,声旁表示了相同相近或相类的语音,而声旁相同的字往往意义又有相通之处。
这样在训释词义中通过对“声旁含义”现象的分析,就把汉字的形、音、义三者连在一起了。
下面是《广雅疏证》中的一些例子:
“曙,明也。
”(《卷四上》)疏:
“曙、署、著三字声相近,皆明著之意。
”“椁,廓也。
”(《卷五下》)疏:
“椁字亦作 ,郑注《檀弓》:
椁,大也。
言椁大于棺也。
……《释名》云:
郭,廓也。
廓落在表之言也。
又云廓,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廓与椁亦同义。
”
随着声旁在更多的汉字中出现,声旁的声、义也就一起进入了新的汉字。
结果是造成了凡是有相同声旁的字也就有了相近的意义。
“甾,业也。
“是凡言甾者,皆始立基业之意。
”“启,踞也。
疏云:
居、踞、跽、启、跪,一声之转,其义并相近。
”(《卷三下》)在《说文解字注》中,这样明断凡从某之字皆有某之义随处可见。
如“埤,增也”(《说文·
土部》),段注:
“凡从曾之字皆取加高之意。
……凡从卑之字皆取自卑加高之意。
”又如“娠,女妊身动也”(《说文·
女部》),段注:
“凡从辰之字皆有动意。
二是同源字。
人们在谈到同源字时,一般用的概念都是“音同义近”、“声近义近”,其中同源字中字形的联系也相当普遍,这里有的是以形旁出现,有的是以声旁出现。
如王力的《同源字典》“之部”中有49组同源字,其中有字形联系的是30组。
“支部”中有27组同源字,其中有字形联系的是26组。
正是由于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三者扭结在一起,因此古代有成就的语言学家,特别是词汇研究家,都是充分利用了汉字形音义之间的这种联系,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诠释,深入地揭示出了汉字的义蕴,从而也就深入地剖析了汉语词语的意义。
因此,突破单纯的形训、声训,将它们串连起来运用也就成为一种更高的境界。
这就是前人常谈到的三者互求,六者互求。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
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
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
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
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也正是因为能三者互求、六者互求,因而在训释古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
”[4]
在古代汉语言学的研究中,在汉语词义的训释方面普遍运用的方法都是建立在汉字基础之上的。
这些释义方法立足于汉字之上,有效地寻找到了汉字形音义之间的固有联系,而释义方法本身又进一步把汉字形音义的联系牢牢地固定了下来。
四、向以字显义的单音词靠拢的规范化趋势
在古代的汉语言学研究中,确实是把字与词合为一体的。
汉字成为单音词的化身。
汉字的字音字义也就是单音词的词音词义,汉字的字形也就是单音词的词形。
这样汉字可视性强的外观强化了单音词的外形,使得单音词成为独立性更强,在表意上清晰度更高的语言单位。
汉字字形成为人们在认知词语时遇到的第一个认识对象。
人们在长期接触汉字的历史中,对它的形象性、表意性有了强烈的下意识反应。
这种反应会在汉民族认知文字时产生明显的类化作用,会把其它不具备表意功能的汉字、长于单音词的多音节词语,向表意的汉字和单音词看齐靠拢。
这就是为什么在长期的古代语言研究中,会对以下几种现象格外重视的语言原因。
1.假借字。
假借字就是从字形上看不出为什么会具有这个意义的字。
本来汉字都是据义造形的,但在假借字却并没有做到这一步,却是借了别的字形来作为自己的表达形式。
所谓的假借字就是借用了别的字形罩在自己的脸上,遮住了自己的真实面孔。
假借字才是真正的符号,没有以形表义功能的符号。
假借字是有违于汉字基本性质的变异现象,因此,假借字也就成为阅读理解古籍中最大的一个难点。
人们用以克服假借字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声辨词。
“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 为病矣。
”[5]以声求义是对真正学者的要求,能做到这一点的学者并不多。
而在读书过程中“强为之解”的却不少,这就是由汉民族由字观义的认知习惯造成的。
2.联绵词。
联绵词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是由两个音节,也就是两个汉字组成的,但在意义上又不可以拆开来分别作单独的解释。
二是这两个音节之间往往有双声、叠韵或二者间有的关系。
联绵词就是现代所说的复音单纯词中的一种。
联绵词是口语中词语语音形式的一种变化,它的意义是独立的,两个音节合起来成为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
它表达的意义大都是形容性词义,这与音节上的迭合,声韵响亮、和谐有关。
但由于联绵词仍是用汉字记载,一个汉字只与一个音节对应,并不与联绵词的意义发生对应。
这是有违于汉字基本性质和表意功能的又一种文字现象。
但由于人们对汉字的使用习惯太强烈,他们对联绵词中的汉字也往往会按汉字通常具有的表意内容来理解,以致出现不应有却经常可见的讹误。
因此,联绵词又成为阅读古籍中的另一个难点。
如对“犹豫”两字,古人多以《说文解字》认为它们是动物的说解来释义,认为这两种动物进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与此相似而得言。
段玉裁批评这是“郢书燕说”,因为一个汉字为何具有这个意义“古有以声不以义者”。
绝大多数用来记载联绵词的汉字都是“以声不以义”而连结在一起的。
为什么前人在联绵词上的说解上会这么经常地出现“以字说义”而不是“以声说义”,主要就是人们仍然习惯一个汉字对一个单音词的语言单位,不习惯没有形体作依据的字义,不习惯几个汉字对应一个词语的语言单位,所以总是会出现将联绵词分开解说的现象。
3.复合词。
复合词是汉语单音词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单音词基础上出现的另一种内部结构复杂化、内涵丰富化、表义功能进步的词语单位。
构成复合词的都是实词素,都有独立的意义。
这些实词素大都曾经或仍在作为单音词使用。
它们的意义有的基本不动地进入了复合词,有的是稍作变动,有时则已经是改头换面了。
即使是后者,人们仍然可以从词素义联想到复合词词义,或从复合词词义猜度到词紀义。
这就使得词素义与复合词义之间有着相当外露的演化关系。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一个词素是用一个汉字记载,一个汉字反映着一个词素的意义,它使得融合了词素义而成的复合词词义并不能在单独的汉字身上完整地反映出来。
复合词词义是靠几个汉字来共同反映,是在具体上下文的语境中突出出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又可以说只记载词素的汉字对复合词的词义起着离异的作用。
因此,古代对复合词的认定往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并经过多次的反复。
从古代的词义训释实践中不难看到,人们总是会把复合词拆开来作单音词理解,把词素义当作两个并列的词义看待。
古代用辨异法分析的“同义词”,其实中间有不少已经是一个复合词,是一个词内部的同义词素的关系,但人们往往仍会由单个的汉字入手把它们看作是一个个单音词。
如“恭”与“敬”,段玉裁在对《说文》中“恭,肃也”进行训释时说道:
“此以肃释恭者,析言则分别,浑言则互明也。
《论语》每‘恭’‘敬’析言,如居处恭执事敬,貌思恭事思敬,皆是”。
显然这里的“恭”与“敬”是两个同义词。
但《左传》中的“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这句话,里面的“恭敬”又应该是一个复合词。
汉语复合词的定型往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许多次的反复。
4.意化字。
所谓的意化字是指一个原本用来译音的音译字会演化成能够表意的汉字。
如“师子狮子”,据《汉》等古籍记载,狮子是波斯国王进贡而来的,它曾写成“师子”,但最后的定名是“狮子”,因为前者只是根据声音写成的,人们还不能从字形看出它是何物。
后来写成“狮子”,因为加上了“犬”旁,人们能够轻松地把它与走兽类动物连在一起。
意化字的产生就是因为它将声音与意义的单方面联系发展成了声音和字形都与意义发生联系的复式联系。
它符合汉民族的认知特点和认知需要。
与意化字有点相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有这么两种现象。
一种是汉字繁衍中的繁化字。
繁化字往往是指在原字中表意的形符已经变得不清晰甚至湮灭,而另加上一个新的表意字符来显示它的会意指向。
如“厶私”。
广义的繁化字还可以包括那些有分化关系的古今字,如“顷倾”、“奉捧”、“受授”、“要腰”。
而意化字却是把本来只是单纯用来表音的字变成既能表音,又能表意的字,它不是产生于汉字的意义繁衍分化过程中的,而是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上纯粹为了增加它在视觉上的区别度而作出的一种变化。
另一种就是意译词。
意译词是指在翻译外来词时,不用音译而用意译的词。
音译词据音写字,意译词则重新寻找造词理据,重新选用新的词形。
而意字化则是在纯音译字的基础上,将原字由纯表声音的符号,添加上形符以增加汉字的表意功能。
意化字出现的潜在动机还是具有表意性质的汉字在起作用。
汉民族在认知一个汉字时,在潜意识中仍希望从这个汉字的形体就能够直接感知到它所表示的意义。
只要在有汉字的地方,它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将自己的表意功能显示出来,恢复它的视觉传递信息的特性,而将纯粹的表音功能尽量地降低到最小程度。
在对外来词进行翻译时,现在已经流行出一种比重造式的意译词更具效率的“美义音译词”,即在语音上尽量与原来的外语词接近,但在所选用的汉字字形上,又尽量与它原有的意义发生联系。
如以“乌托邦”译“Utopia”,以“邦”暗示出某种社会建制义,以“乌”暗示没有义。
以“奔驰”译“Benz”,显示这种高级轿车的快速便捷的特性,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第二节 “随文释义”的实用精神
在古代的著述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说法:
“因文诂义”“缘事生训”“随事为文”“随文释义”。
看起来,它们指的是古代词汇研究中的一条释义原则。
其实,把“释文释义”放到整个语言研究的活动中来看,它就已经不再仅仅是一条释义原则了,而是古代词汇研究中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
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注重随文生义的语用现象,注重词义灵活的变通性,注重传笺注疏式的著述形式。
也正是它,使得整个古代的词汇研究活动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充盈着人文精神。
一、以词的变通义、具体义为研究对象
我国的古代语言研究历史悠久,其中最为源远流长的应该说是词汇研究。
从先秦一直到晚清,词汇的研究自始至终在里面占据着主流的位置。
但假如试图对古代的词汇研究稍作一次分类,就会发现那时的词汇研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它们重视的是词义而不是词形的研究,二是它们重视的是对词的具体义、语境义,而不是稳固的语言结构义的研究。
这些具体的语境义大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极易消失,成为不太为人知晓的古义。
因此对古义的解释也就成为词义诠释的主要对象之一。
如《诗·
邶风·
泉水》:
“遄臻于卫,不瑕有害。
”注云:
“遄:
疾,臻:
至,瑕:
远也。
”笺云“瑕:
犹过也。
害:
何也。
”对原文两句8个字,注笺就对其中的4个字作了解释。
对“瑕”字《注》与《笺》还作出了不同的诠释。
这些字主要就是因时代相隔久远而引起词义变化太大,后人已经不易读懂它们。
《尔雅》收录了“业”字的五个义项:
“大也”。
郝疏:
“《说文》云:
大版也,《诗传》同,俱本《释器》为说也。
‘四牡业业’,毛云:
业业然,壮也。
又云:
业业言高大也。
高壮亦皆为大矣。
“叙也”。
“大版又篇卷也,版作锯齿,捷业相承。
篇有部居,后先有次,皆有叙义。
“绪也”。
“舒业顺皆可以义求。
“事也”。
“上文云叙也、绪也,端绪次叙皆与事近,故《鲁语》云:
非故业也。
《史记·
项羽纪》云:
业已讲解。
韦昭及索隐并云:
业,事也。
”
“危也”。
“《释诂》云:
大也。
物高大则近危。
故《诗·
云汉·
召》传笺并云:
业业,危也。
《长发》传:
业,危也。
《常武》传:
业业然,动也。
震动亦危惧之意。
这五个义项中有的就属于具体的文义。
在后来的辞书中,它们只是在对故训无所不收、缺乏有条理概括的《中华大字典》中才能全部见到。
《康熙字典》着重收了在其中的“事也”义演派出来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