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冲疼痛的边地文档格式.docx
《腾冲疼痛的边地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腾冲疼痛的边地文档格式.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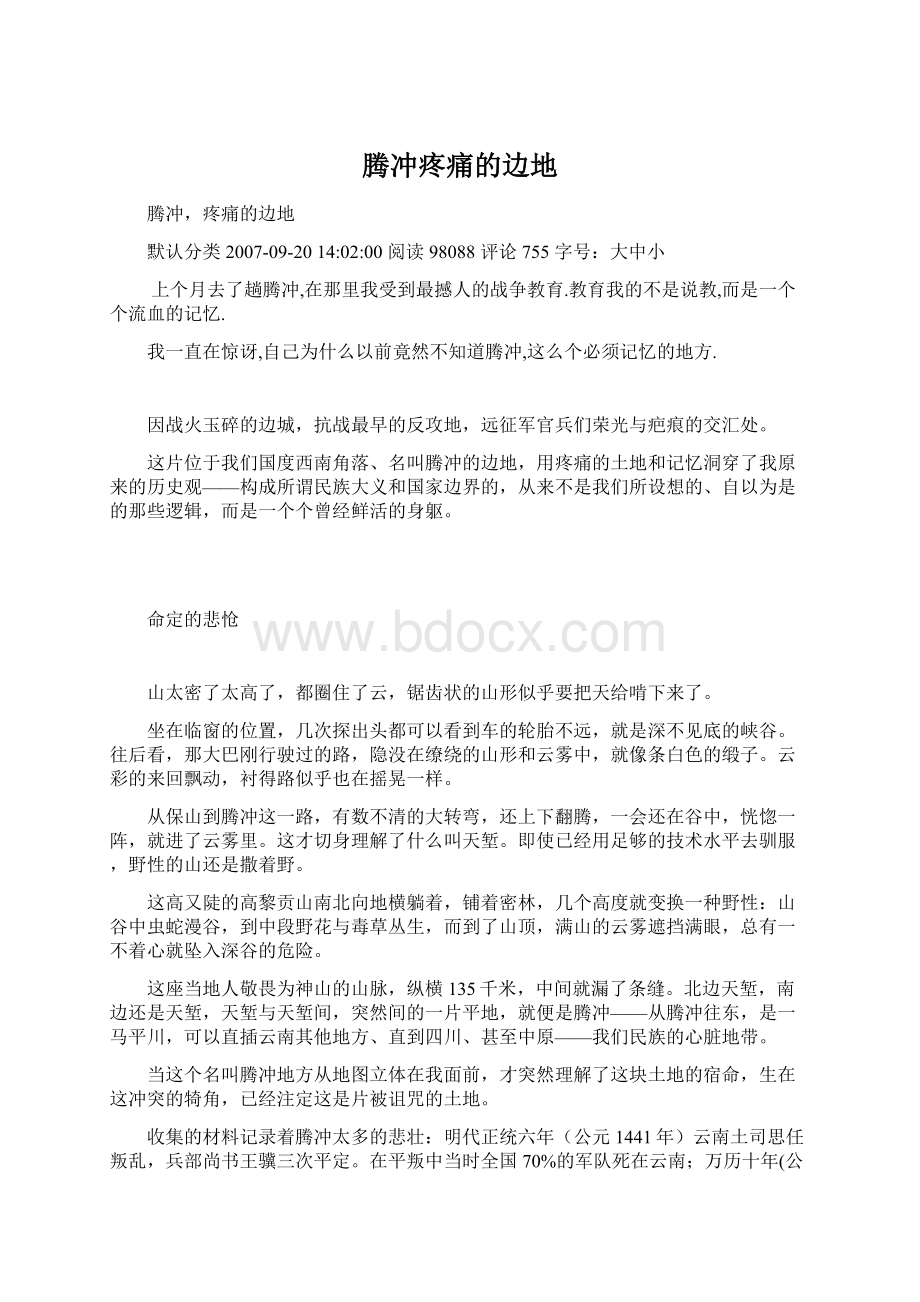
”朝廷急调邓子龙携部日夜兼程,于万历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到达永昌,最终三战三捷,但因此尸横遍野;
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滇缅间诸土司屡与缅人冲突,缅兵进攻,朝廷派遣云贵总督杨应琚率兵攻缅,缅甸之役从此开始。
但杨应琚攻缅失败,致使缅兵长驱直入,并围攻永昌(今保山)、腾越(今腾冲)各边防营地。
乾隆皇帝得知此消息后,召还杨应琚,赐死。
之后,另派遣明瑞为将军兼云贵总督,并增调满兵赴滇,以几万的肉躯横生生挡住了进攻……
最近的却也是最悲壮的一次,1944年,中国远征军和入侵的日本军在这个边城里开始了民族的第一次反攻,腾冲成了中国第一个收复的地方,付出的代价是,那座用火山石筑起“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周长七里二分的石头城”完全成了一片焦土。
“据说,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
”
怀揣着这样的记忆往这座城走,越近越发觉得有些慌张。
天光巧合得有些刻意,当大巴从高黎贡山往下,车窗外已经是一片夕阳,周围的山脉被夕阳涂得殷红的,而山脉中间展开的腾冲城却灰黯成一片,看着,仿佛像个火山口,又或者像是凹陷的巨大的伤口。
不过,我想即使没有那血一样夕阳,这血色的土地以及历史,已经足以让我无论在何时抵达,都会觉得心惊。
死过的城
“我在这里挖出过三具尸体。
”这个激动的司机叫刘天章。
我在城外的长途车站搭上他的车的,目的是那座在原地上新建好的腾冲城。
我也只是无意间提到那个传说:
”他就突然刹下车,把我领到路旁,指着一排绿化带说,“这里曾经是一座民宅倒塌的墙根,我那次帮忙清理的时候,就挖到过,他们其中一个还握着枪,尸体早已僵硬,那枪始终拿不下来,他们的眼睛都睁得老大老大的,像是在拼命看什么。
后来,我在文庙就看到他描述的那种眼睛,那是木柱子上的一个个弹孔,许多子弹还嵌里面,像是瞳孔一样。
当我在腾冲文管所前所长李正的指引下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闪着黯哑的光,看上去那么似乎很恐慌,也很悲伤。
这座文庙是那次战争后仅存的、为数不多的建筑物之一了。
进门前李正给我说过一个让我慌张的数据,他就指着我站着的地方,用一个严谨的学者的口吻冷静地说:
“这里发生过悲壮的枪战,日本兵以这些建筑为天然屏障,还挖了相互贯通的战壕,我们的中国远征军是以每米牺牲7个人的方式推进的,所以你每跨过一步,就跨过多少个爱国将士的身躯。
关于那场战争,仅仅梳里数据就很骇人:
从1944年5月11日强渡怒江到9月14日攻克腾冲,127天,中国军队伤亡1.8万,民夫伤亡相近,全歼守敌6000,日军无一生还。
三四万人就阵亡在这极边小城,难怪“随便一个地方挖下去都是人尸。
”而城也早已经是焦土一片,遗留下来的描绘显得悲怆:
“战斗结束后,腾冲城里没有一间站立的房子,没有一片树叶上没有弹孔。
我后来收集到当时对阵双方将领的日记,他们的描述甚于我的想象:
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敌人突然在黑暗中怒涛般地涌了过来,一场军刃和刺刀的混战。
敌人被击溃,遁入灌木丛用
机枪反击。
这时我们推出一门大队炮,小队长命令:
“零距离射击,放!
”敌丛里飞溅起巨
大的火花,五六发以后,敌丛哑然无声,微微传来敌兵的呻吟声。
……敌人并没有就此败退,新手一个个地接替上来继续对我实施轮番进攻,阵地上的树木几
乎全被击毁,痛苦中死去的战友尸体还紧紧地抱着枪身。
从凹洼处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
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堆积。
但我们的子弹已所剩无几。
敌人立即在层层堆积的他们同伴
的尸体上架起机枪开始扫射。
……我们退回腾冲城内,3000多日军,受到6万多中国军进攻。
……我穿过到处爆炸的城内
去寻找粮食,两旁重叠着被炸死的友军尸体,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有没死的二三名日
本士兵,表情痛苦地伸出满是血污的手向我求救。
九月十日,敌人在蒋介石总统的愤怒激励下,实施最后总攻。
我们剩下的守备队兵有350多名,他们像狂涛一样席卷而来,奋战、奋战,殊死奋战。
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
9月12日太田大尉发给师团司令部诀别电报:
“我们已弹尽粮绝,突入城内优势之敌自昨日以来即与我混乱战斗中。
我决定将军旗及密码烧掉后,实行最后的冲锋和突围,敬祝全军胜利。
一个军曹嘶叫起来:
“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
冲!
”
陶达纲《滇西抗日血战写实》
在进攻高黎贡山的灰坡时,日寇的速射炮、机关枪如一阵狂风暴雨般……第二天清晨,本人
清查官兵伤亡情况、第一、第三两营官兵,已经有85人伤亡。
师长叶佩高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到团指挥所,真是与部下同生共死的好长官啊!
第二次再攻,本人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二百余人。
这些都是他们父母所心爱的好儿子啊!
5月30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皇军的悲惨下场。
也感到很奇怪。
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原日寇据点),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
6月1日这天,高黎贡山上很冷。
我眼看着两位战士在我面前冻死去了。
592团之官兵,在滇西大捷一役中,自5月11日起至9月25日止,有不幸负伤一次两次三次者,又再上战场,又再阵亡者。
呜呼!
能不令人悲伤,他们此种牺牲精神,无愧对中华民族之先烈在天之灵,凡有良知的人,能不同声一哭!
1944年5月发生了两个民族生存本能的戮血交锋。
日本希冀占下腾冲,割断英美从西南角落给正在抗日的中国部队的补给线,他们觉得守着这里,就守住他们民族所谓宏大的伟业,而我们民族知道惟有贯通这条线,方能有借助外力的可能,避免整个国家被覆没的危险,这两支部队的人,用的是肉体去攻防。
对双方来说,一个是民族的底线,一个则是扩张的边界点。
其实,这样的描述已经算克制,一个当时参与攻城的老兵写过进入那“玉碎”腾冲见到的场景,“腾冲城里到处是枪声、喊杀声,一眼望去是烈火和硝烟。
残垣断壁下,一堆堆的尸体,一股股焦臭味死尸味直呛得恶心。
进攻的路上,为隐蔽身体,拔开敌人腐烂的尸体,从一堆堆蛆上爬过去……,用死尸堆起的工事,流淌着恶臭的血水,一梭子机枪射来或手榴弹爆炸,溅得一头一脸的死人肉。
我是在书店读到这些材料的,夜晚当我揣着这些材料搭车回宾馆时,见到的,是那空荡荡的马路,虽然盛夏,但高原的风冰冷成一片。
车过景换,几乎每个路过的地方都能找到材料当中描绘惨状的章节,文庙、文星阁……,那句话,就不断在我耳畔萦绕——“能不同声一哭!
盛开的伤口
终于无法成行,突然的大雨带来的泥石流,截断了我去高黎贡山界头村的念头。
产生这个冲动,来自于中午吃饭时,听那小菜馆的老板娘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就是高黎贡山南北斋公房这一段,每到下雨天就可以听到,千军万马的奔腾声、号角声,哭声。
她说她就来自那段山底下的界头村,她曾在某个雨天的晚上,突然听到一声嘶哑而凌厉的“冲啊,杀啊!
”。
“他们说是因为高黎贡山是磁山,能吸收声音。
”她描述完当时她的恐惧后,这么引用当地政府的解释,不过她有另外的理解,“我妈说,是因为太惨了,连高黎贡山都忘不掉。
但遗憾的是,路上拦住了几辆车,司机都说,现在雨季,山上到处泥石流,不敢走。
不敢走的或许不只这个原因,后来才听李正说,即使没有泥石流,估计也不会有司机会想带我去那个地方。
李正是那种心直口快的人,身强体壮,皮肤和这边的阳光差不多灿烂,这个专业考古的学者,虽然是50多岁了,却常一个人带着帐篷到处去考察。
像他这样的人不多,特别在腾冲,原因是,这里太多人相信鬼魂。
事实上,这里聚集的,几乎是整个中国最会讲鬼故事的司机了。
在腾冲一周,我碰见八个给我讲鬼故事的司机,而且他们都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方式说的。
下午我搭着车出城去,一路上那个女司机一直交待,一定要八点前回来。
我不太理解她反复的叮嘱,最后她才支支吾吾地说:
“这里阴气重,晚了难免碰到不干净的。
”她还补充了句:
“如果碰到远征军那还运气好,碰到日本鬼子那就糟糕了。
这样的忌讳有时候让这个不信鬼魂的李正有些恼火——他有几次到了高黎贡山界头村,想去据说死伤最多的一段名叫“灰坡”的路,山密路隐,他需要当地人的向导,结果找了周围一个又一个村子,大家都说不知道,后来才有人偷偷告诉他:
“其实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敢去。
我更愿意把这种情绪看成是,世袭记忆的伤口——它还没停住流血。
城里的弹坑都抹平了,但可以感觉到,伤口还在到处盛开着,以传说或者鬼故事的方式,在这个高原的天空如那些触手可及的星尘那般若隐若现。
但在腾冲一周,让我明白不能轻视或者嘲笑这种情绪,没有亲历过的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恐惧或者说敬畏。
李正后来到过那条当地人不敢去的路,即使这个让人感觉顶天立地的汉子,都说“除非是亲历,否则没有人能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艰险的战场。
”他回忆说。
一米多高的石磴数不胜数,每一步都得手脚并用。
很多石蹬窄得刚好放下脚掌。
旁边就是悬崖,但凡失足,人掉下去连个回声都不会有。
而且“山高天冷雨多,打仗当时正是雨季,光冻死的就许多。
我在美国记者的文章里看到那种旁观者的惊讶,战时美国新闻处编的《最高海拔的战斗》中这样描述:
高黎贡山战斗,是二战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次战斗,山上每天都是云遮雾罩,厮杀声枪炮声始终回响在云层之上。
当地老百姓说,那是天兵天将在干仗。
听起来极富诗情画意。
但诗情画意只是表象,当年的高黎贡山其实是生命的炼狱。
这话一点不夸张。
后来据守高黎贡山的日本老兵写过回忆录,他们说,那时他们的炮筒根本无须瞄准,每一发炮弹落下,都会溅起一堆血肉。
光秃秃的山坡上潮水般汹涌而来的远征军官兵根本就来不及隐蔽,也无从隐蔽。
远征军完全是用血肉来消耗日军的弹药。
“旺子从山上往下流,像河一样的一直流到山脚。
吓死人啦。
李正曾在山下听到一个老村民描绘的恐怖情景:
战斗结束时,阵地上的死人密密麻麻。
在他们的家门口,美军运输机空投下来的炮弹、子弹箱,像码柴火一样堆满了整个山凹。
他说着,叫孙子到柴房里找出一颗引信还在的六零炮炮弹,只是已经锈蚀了。
战后几年里,像他一般大的孩子全靠捡子弹壳捡破枪烂炮买书上学。
不止是灰坡下的村庄,整个高黎贡山两侧,只要打过仗的地方,那千千万万的子弹壳,几乎养大了山下整整一代孩子,有人还靠子弹壳换回老黄牛。
这悲怆竟然如此强大,以致一代代的遗传。
也难怪他们会说,“是因为太惨了,连高黎贡山都忘不掉。
活着的鬼
到底要如何同这样的记忆相处?
段生馗说,正视它,看清楚它。
那个下着雨的午后,他开车领着我来到他建立的滇缅抗战纪念馆。
一路上,天气冷得让已经加了一件长衣的我还是有些发颤。
我说,你们这真奇怪,正值盛夏,这却冷成这样。
他笑着随口就答:
“可能阴气重吧。
他和他的这个馆,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报道,一个流行的宣传语是:
“中国民间第一座也是最大的抗战纪念馆。
”我不是被这个耸动的宣传语吸引来的,而是因为在采访中听到段生馗的一个段子:
“段生馗在我们当地是出名的怪人,学生时期就收集那些战后遗物,有日本人拿来煮中国人的汽油桶,有日本人骨灰,满满地塞满整个宿舍。
”这个段子的高潮在于,那些他收集来的日本人的骨灰和灵位全部塞在他的床底下,据说有些日本鬼不服气一到晚上就在床下不安分地发出声音,段生馗晚上都要气氛地用脚跺跺床板,才能让它们安分。
我曾把这个段子说给李正听,问他,那段生馗看来也不信鬼,李正纠正了我的用语,“他不是不信,是不怕。
确信这点是在段生馗的纪念馆里,他指着一个汽油桶问我,你感觉到了“冤气”了吗?
你感觉到了那不肯闭眼的冤魂了吗?
那是个有着奇怪色滓的桶。
段生馗告诉我,那是人肉被煮烂后风干的痕迹。
那个汽油桶是他从一个村子里的祠堂收来的。
日本兵打进来的时候,全村的人带着能吃的东西全逃了,这让负责来找食物的日本兵特别恼火,而当时村里派三个村民去打探日本兵的消息,结果却被日本兵活捉了,就把这三个人绑在汽油桶里慢慢煮,直到把整个人煮熟、煮烂。
后来村民就把这三个汽油桶供在村里的祠堂里,段生馗几次去收,他们都不答应。
段生馗后来也不催了,自己默默帮村里做些事情,拉自来水管,关心当地的孩子教育,村里人自动来找到段生馗,问他,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些桶,我们要把它们摆在村里,世代供着。
段生馗说了句:
“我就是想让它展览在更多人眼里,碍着他们的眼,让他们不会忘记历史。
”桶于是被运到了馆里,据他说,运的时候全村人夹道相送,许多老人眼眶含泪。
段生馗的几乎每件藏品都有段这样的故事,它们各自记载着历史的某些碎片,让观者心惊。
显然,这是段生馗的目的,他把在野人山收集来的头盔一个个排好,对映一张张照片,告诉我,“他们为了我们民族曾深入野人山结果被吃了,只留下这头盔,但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竟然忘记他,我们凭什么忘记他。
他不愿意搽去一把日本长刀上血迹,是因为他想指着它告诉我,这把刀曾捅进多少女人的阴户,刺杀过多少个人。
他是个太过激动的讲述者,以至几次讲得自己都有些哽咽。
也让我几次感到难以遏制的悲哀。
终于坐下来喝茶的时候我不得不问:
你为什么要花一生做这些事情,而且要自己掏腰包,又要经受许多误解。
他当时有点自嘲地笑,“因为我内心不安,为许多人不安。
我们这个地方,许多村里都有那种鬼屋,就是因为有人在那时侯掺死在里面,众人就不敢去,甚至不敢提了,久而久之就淹没在荒草里了。
你不觉得,这种刻意遗忘对死者是那么残酷,对后人来说,永远无法了解到真相,前人的逃避,让他们失去了健康地去面对历史的可能,而是在传说中,变成了一种莫名恐惧或者愤怒,那无助于一切。
“难道你不怕这些东西吗?
你不相信鬼吗?
“我信,但我不怕,我们这里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就是远征军的投胎,我们是命定要来守这个边城的,我也是命定要来守住这些记忆的!
”那一瞬间,我抬起头看他的眼睛,还真觉得,自己见到了那些保家卫国的远征军。
生者之伤,亡者之殇
李正一直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不断采访那些老兵,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留住记忆。
他答应带我去寻找那些亲历的老兵。
但他执意,先带我去那些没能活下去的兵,他们在离城5公里地,一座名叫国殇的墓园里。
我原本更在意一路上他提到的那些老兵。
他说,有个老兵战争结束后,怕了战争了,就在这里自己找个地方活了下来,没有结婚没有儿女,老兵年纪越大因而生活越发困难,但一直没有得到救助。
七八十岁了还下田,冬天一双凉鞋子。
有个看到报道的北京女孩子看到报道了,自己寄钱给他,有次李正去了,帮忙拨通了捐款的那个女孩子的电话,老人抢过电话就喊,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
还有个远征军老兵,1950年保山地委书记让他做秘书,派克笔都给他用了,但在填表时他如实写了抗日经历,生活全变了,几十年里每逢政治运动就挨整。
这几年他奔忙着想为打日军而阵亡的同队八百多兄弟弄个墓、立个碑,因为他听说黄土坡上那些军人坟被平了,种地的还犁出骨骸来。
他还为一位孤寡的远征军老兵写申请向政府求助,可县民政科说无政策,那战友到死也未拿到一分钱。
他最后说了个老人,叫蒋绍福,今年92岁了,当时他是警卫队——就是负责保护一些重要长官的,本不应该上战场的,后来打到没兵了,他们被组成各敢死队,就负责攻克我去过的那个文庙,结果进去一队出来就一个人。
这个老人后来在当地当了倒插门女婿。
却因为曾经的国民党军的身份给孩子带来过麻烦,和孩子一直亲不上。
后来一些企业家弄了个慈善基金会,老人就靠每个月两百的救济款生活。
那个老人许多媒体采访过,还照了许多照片,但从没有寄来给他过。
有次李正带深圳的一个记者去采访,他拉住李正说这个事情。
李正回去后马上送了一张他给老人拍的照片过来,而那深圳的记者当即说要帮老人拍一张,并守诺地寄过来了。
李正约着我,“我们看完国殇墓园就去送照片。
到了国殇墓园,我才明白李正的执意。
这墓园是建在一座山上。
山顶立着一个纪念碑,从纪念碑开始,每个阵亡的士兵墓碑按照生前的编队,一列列从山顶直直往山底排。
我从山底拾级而上,每一级台阶,上下左右全都是这些士兵的墓碑,他们似乎还活着,依然守着军人的秩序排着队。
李正曾主管过这里,他告诉我国殇墓园从一开始就是个遗憾。
1945年,阵亡官兵被集体火化后骨灰成车拉来,开始怕罐不够,压得很满;
后来罐又多了,又匀出些装半罐,墓碑并不对应骨灰,三千多名字也不能包括反攻牺牲的九千多阵亡官兵。
远征军死亡的故事太多,立碑的太少。
保山博物馆李枝彩先生讲了父亲亲历过的场景。
61年前一个营的远征军在山神庙峡谷乘夜埋伏,计划凌晨偷袭日军,没想到被发现,日军集中火力一阵狂轰,只逃生了一个拉肚子的士兵。
战后多天,尸体腐臭,一拖就会掉腿和胳膊,只好就地掩埋。
沟底因此垫高一尺,乡民不再走此路,斜坡上又辟一径。
60多年了,像冷水沟、灰坡、象达一样,渐渐再无人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
而时间越往后推,越遗憾。
清明的公祭在五十年代初取消了,大约同期,民政部停发了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的抚恤金。
国殇墓园沉寂了十多年,甚至长满了荒草。
再喧闹时是文革,墓碑上所纪念的二十集团军中的54军,在内战中曾被蒋介石调到东北与林彪属下的解放军54军对垒过。
文革中解放军54军支左恰好驻扎在腾冲。
正是革命有理的年代,解放军54军就在远征军54军的纪念塔下埋了炸药。
红卫兵们也将坟山上的三千多块刻有远征军官兵的墓碑尽数砸毁。
(惟有腾冲另一处纪念54军198师的阵亡将士塔,得以原物保存,只因很早该塔被人用泥糊上后大写了“毛主席万岁”等红色标语)
文革最热闹时,城关镇小学有一位老师带着小学生们来砸墓,他还爬上主建筑“忠烈祠”把四角的飞檐斗拱的木雕锯了,如今仍满檐断茬。
墓园被底朝天毁了一遍,只有一块于右任手书的“忠烈祠”匾额保了全身。
当时粮食局职工田复明悄悄拿回家,作了10年床板,1984年墓园重修时他扛回来并捐上10元钱。
他还说,年前去庙宇祭母,发现地下一块碑上有字,他慢慢用手抠,发现竟是他研究过的战死于腾冲的名将李颐少将墓碑,他赶紧让人送到国殇墓园。
这次陪我们来拍摄,他问起李颐的碑,没想到被搁在院草丛中,翻过正面,已有虫爬。
但他想告诉我的还不止这些,他特意带我去到同在一个墓园里的修缮一新的美国飞虎队的纪念墓群。
配合远征军的美国顾问团共亡19人,他们都在当时或战斗后几天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梅姆瑞少校在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大洋的上好棺木。
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装了回国迁葬,并写出上报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
前几年美国国内还不断有人来寻找这些英雄,政府为此专门组织了许多活动。
而即使日军在中国的阵亡者,也似乎来得幸运。
战争之初祭典规格高,死的多了,只好从简。
一部分横尸缅甸的日军遗骸,几十年间在其遗属、企业财团、政府的大量资金人力关注下,或被迁回或在当地大修墓地,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或民居,日人皆重金买下而祭祀,甚至犬马也有立碑。
一位旅居缅甸的远征军老兵提起当年葬缅的战友墓地,哽咽难语。
而日本人也在盘算着将死在滇西的日军骨骸及文物迁回国,自然遭到拒绝。
至今还能看到日本人到国殇墓园里的倭冢或日军战死地悄悄鞠躬、洒酒、焚香。
由此美国国内还寻找这些美军的遗骸时,李正带着一些作家摄影师随行报道,当时政府特意组织少先队扫墓,
那时大约下午五六点钟,斜斜的阳光照在墓碑上,那个摄像师和同行的一个作家突然伏在层层叠叠的墓碑丛中,泣不成声。
李正急忙走上前问原因,他们说:
“我们是来拍寻找美国老兵的故事的。
可是怒江战役中阵亡的数万中国军人,有谁找有谁问?
”李正当即也哭出了声。
笑话
一路上,李正像个孩子一样不断拿出蒋绍福老人的照片端详。
每看一次他都要激动地说:
“老人估计要乐坏了。
老人住在离县城30多分钟车程的村里。
大概在李正第5次拿出照片端详的时候,我们的车到了那个村。
进到李正熟悉的那个村口,李正却看不到老人的身影。
他自己纳闷地嘀咕:
“老人平时都坐在这个地方,怎么今天不见了。
”他边说边下车问,我在车里,就看到他和周边的人打探了几声,就突然闷声闷气地走回了车里。
他拼命呼吸,脸转了过去,不让我们看到。
他的举动吓到了我,连忙问:
怎么了,李老师?
他再回答时,声音已经完全哽咽:
老人死了,就在前几天。
我当时自以为沉稳地安慰:
“老人92岁了,生老病死说不准。
李正不答话,过了许久才说:
“老人是自杀的。
我当即蒙了。
李正稳住情绪接着说:
“老人前几天上县城领救助款,但城里告诉他,没钱了,从此以后没钱了,慈善捐款都没了。
老人回来就傻了,听邻居说,老人从县城回来特意到山上的温泉洗了个澡,穿上他唯一的一套正装,沿着村子走了一遍,然后晚上,就自杀了。
同行的李正的朋友张先生深深叹了口气:
“枪林弹雨的没死,却被这逼死了。
”李正再也控制不住,抱着那照片痛哭出声……
要离开腾冲前,李正特意和我聚了一下。
他问我:
“你准备怎么写腾冲呢,还想探讨这个地方为什么发生这么多战争,以及,我们民族是靠什么守住这个地方的吗?
我提供些我的研究成果给你说不定有用。
这个地方的人大部分都说自己是明朝戍边将士的后代,都来自中原南京大柳湾,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这些将士的投胎,所以他们前仆后继地用肉躯去守这个边界,但,实际上我考察过,他们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这听起来像个笑话吧?
我点了点头:
是个笑话。
一阵悲哀,瞬时,又涌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