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发展史Word格式.docx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发展史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日本发展史Word格式.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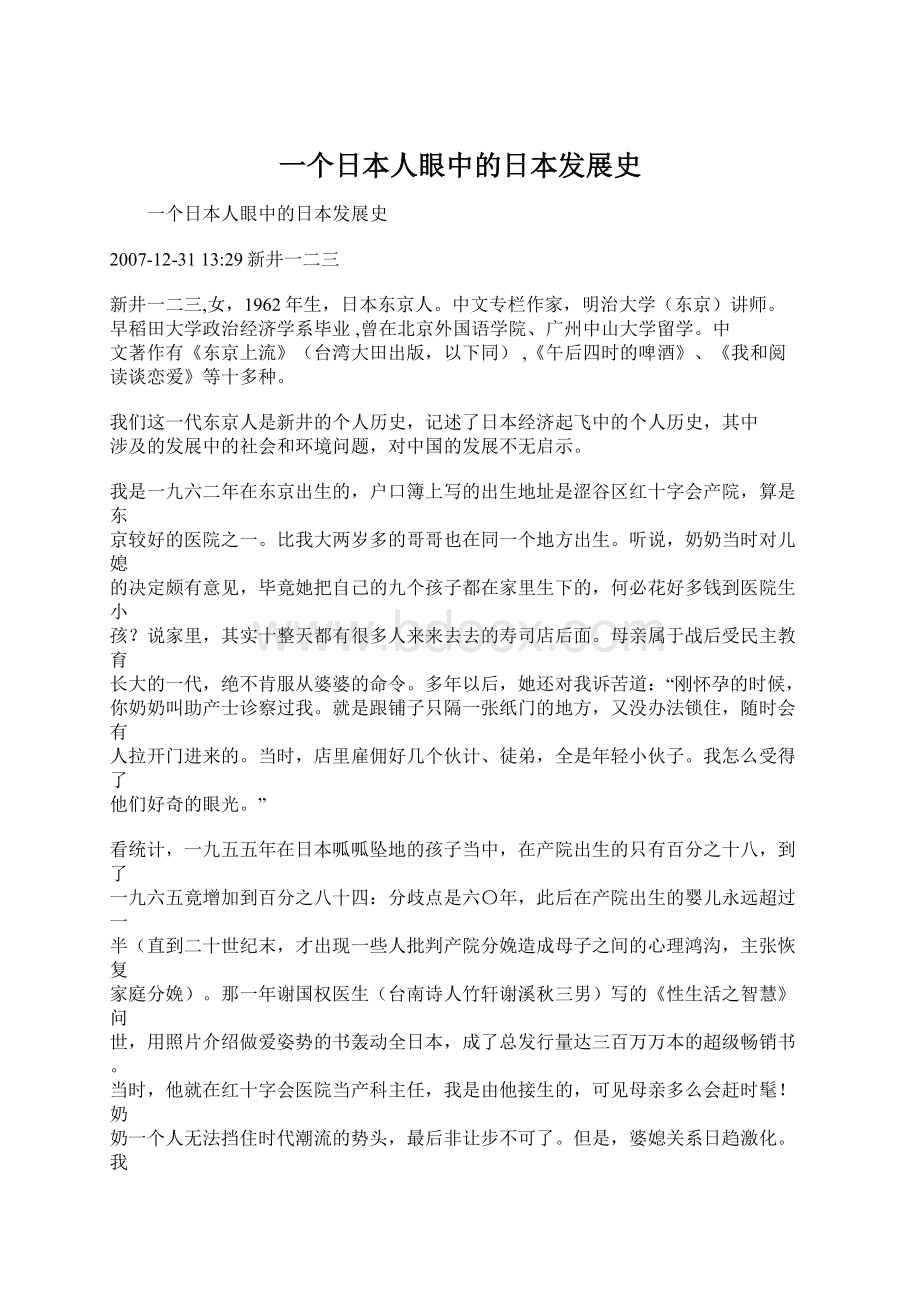
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
东京奥运
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
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
为了迎接外国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
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
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
跟日本多
数家庭一样,我家也是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许多人都说,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
如今回顾“美好昨日”
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〇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
末,东京室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
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
煤炭炉,和服,塌塌米。
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
我小时候,家里每年增
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
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
、微波炉。
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
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
生活同时被破坏。
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跟美国人过一样的日子,祖先留
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
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
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
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
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
家一同富起来的。
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
饭碗。
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
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
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
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
说是最后一代。
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
她懂
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全有
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
本性的调整。
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
旧水路上的。
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
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
看江户时代的浮世
绘,很多都画着水景。
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
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
路的一批工程师,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
起来了。
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作用,即确保东京
湾刮来的海风经过的路。
果然,四十年以后的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
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
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上升。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推到工程师的身上去。
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境是进步
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
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
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
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之极。
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过,他小时
候(一九四O左右)曾经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
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
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干脆把旧货推下河中去
。
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
到了世纪末,市政府才通过景观条例
企图恢复水边生态。
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
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年前。
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到了世界第三位的水准。
同时国内纷纷发
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
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
“全共斗”学运达到高潮,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
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
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
(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
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总体
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
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
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
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
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
,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了。
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留着长发,穿喇叭裤和高跟
靴,弹吉他唱反战歌曲,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进自卫队基地
,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
他享年四十五
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
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
相片。
周围的大人包括父亲和学校老师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
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
长大以后开始看各种评
论才开始理解其所以然。
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
治方向不可。
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O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
社会上
基本认为三岛之死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
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
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
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
场面使他兴奋。
(二OO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
书》里探讨:
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者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
结论还是否定
的。
)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沸腾过一回。
“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
各地来的朋友们!
你们好,你们好,来樱花国的宾客们!
”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
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
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
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
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要出生的小弟。
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
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
小轿车
后座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
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定了某公司休养
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
酷热的夏
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
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
球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
模糊地记得我和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
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
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
不扣的异国风味。
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
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
有个同学因父亲工作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
至极的。
在博览会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
他主
张:
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
农民
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
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
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
出版社都推出了首相的半生记。
我从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
他是左派教员工
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
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
上台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
跟矮个田
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
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
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
我和一批同学们去上野动物园隔
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
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
推土机首相本人。
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推出售大熊猫花样的
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部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
记得有一天,卫生纸
卷开始从超市货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
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
了卫生纸卷可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去抢购,没半天真的卖光了。
当时六
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
没有了卫生纸卷可以用新闻纸吧。
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
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
的只是市中心而已。
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
大黑洞)。
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起以前贵多了。
莫名其妙的卫生纸卷事件
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
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
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
段时间饭桌的情境特豪华起来,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详
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
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
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账。
父
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
幸
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
有失去窝。
当年日本有个规则:
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
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
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
下降的滋味。
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喱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
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
父母拼
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
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的主意,她不
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
我高
中三年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
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
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
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培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
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让他放
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
东京教育大学(现筑
波大学)附属高中。
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
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
我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
人。
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
一
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和老师
同学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
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
父母亲告诉我:
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
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
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
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读过大学的。
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
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
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
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
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以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
,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
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
“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是中上、中中、或
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这十
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的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
同
时,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
穿着西装
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了,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
人觉得奇怪了。
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厢情愿把自己划为“
中层”;
我们家也不是例外。
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
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
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
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
,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
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
厚压倒了我们的。
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
有什么藏书可说;
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聊家常
时候的话题。
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
戚朋友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
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
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
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深刻的阶级震撼。
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
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
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
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
到底从哪里来的区别?
恐怕
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
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
同时
,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
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
松弛;
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
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
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区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
生的特权。
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
了好大学。
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
少爷们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
、商社、制造业公司。
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
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很快被迫辞
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
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
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
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是直
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
当中,女生只有七十多人,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
果然,政
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
选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中,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
(也就是百分之一整)。
九十年代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
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
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
但是,
八十年代初期,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以后,只有少数
人在学习汉语的。
作为惟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
学习不可了。
好在我对这门课,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士著名的音韵学者滕堂明保老师;
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
,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
来当客座教授。
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滕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
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
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
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
“北风那个吹……”
接着
,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
“妈、麻、马、骂”。
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
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
汉语美丽极了!
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钟情
,一点儿也不夸张。
滕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
“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
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
去日中学院吧。
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
,而且我当院长。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
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
,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
自
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
小时候,接触到外国文
化的机会少之又少;
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
好热闹的大街小
巷边,挤满着大餐厅笑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
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扁制过的。
哇,多么特别!
可以说,横滨中华街食一
九六O,一九七O年代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
进入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
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
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
十六岁,在高中上
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了也嫌语音不悦耳。
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
中生必修课之一;
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
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
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
月亮而不幸溺死等。
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
们的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
在远处的老朋友。
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于
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
两个相互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
魅力”。
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憾。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
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
风气正在成气候。
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
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
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着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
她们打
扮得跟最新一起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
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
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
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
高中同学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
上日中学院的课了。
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
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
有些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个多人纯粹出于
个人兴趣。
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认真得不知多少倍。
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
岁,曾经经历过“火红的年代”的一代人。
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
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
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
开过三中全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
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
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
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
他在文中指出:
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
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
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
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
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
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
地来奋斗的新居民;
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
这是经过明
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就开始的现象;
连天皇家都是那时候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
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
相对而言,大阪、名
古屋等其他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
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
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
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老东京作家谷崎润
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
蹋到底了;
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
外地人可以“上”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
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
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
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
魅力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
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
“下”去的;
作为
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
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
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暑假汉
语进修班。
中国民航班级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
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
坐了一个多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