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王小王选在《人民文学》第四期Word文档格式.docx
《《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王小王选在《人民文学》第四期Word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邂逅是一件天大的事》王小王选在《人民文学》第四期Word文档格式.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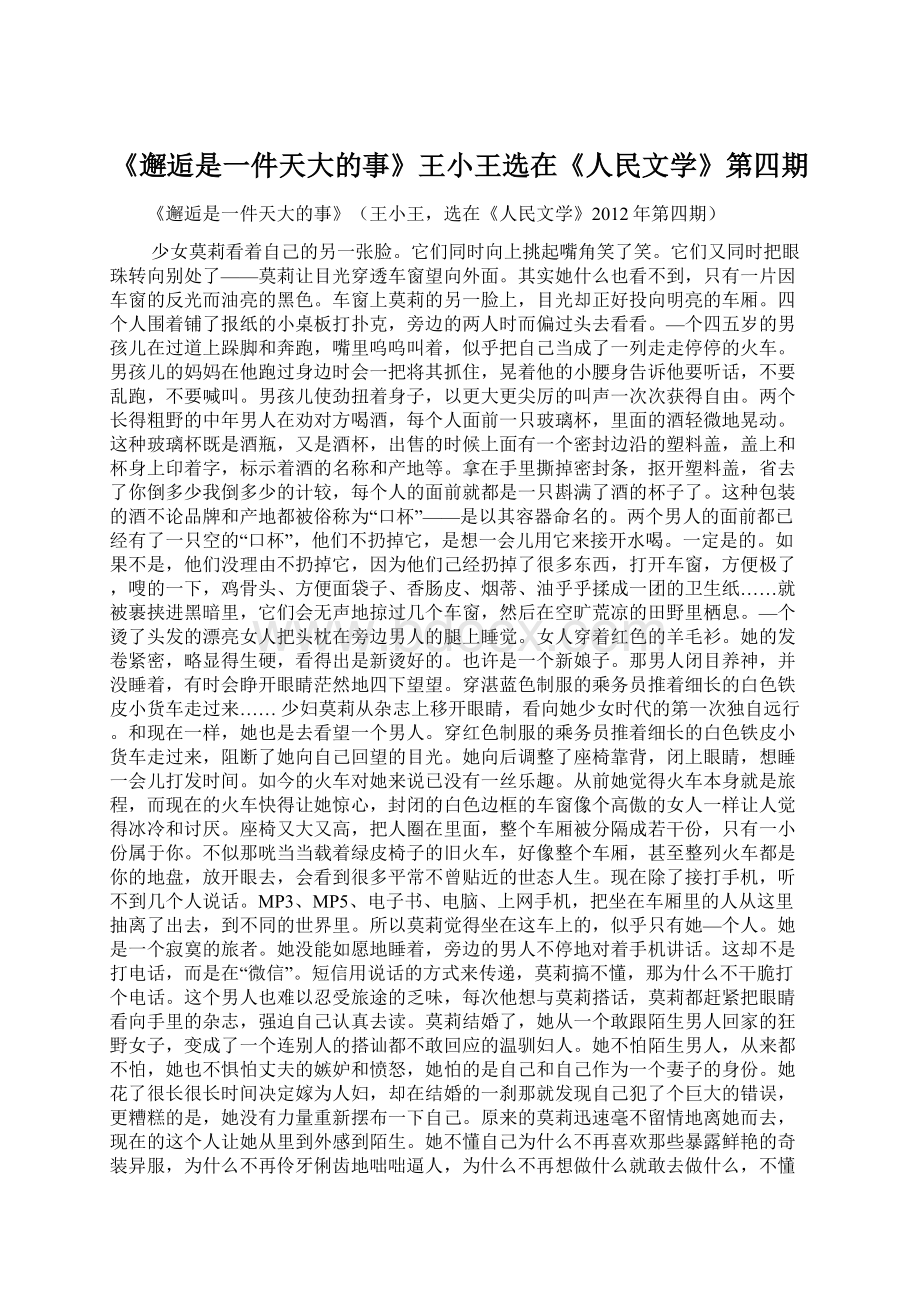
座椅又大又高,把人圈在里面,整个车厢被分隔成若干份,只有一小份属于你。
不似那咣当当载着绿皮椅子的旧火车,好像整个车厢,甚至整列火车都是你的地盘,放开眼去,会看到很多平常不曾贴近的世态人生。
现在除了接打手机,听不到几个人说话。
MP3、MP5、电子书、电脑、上网手机,把坐在车厢里的人从这里抽离了出去,到不同的世界里。
所以莫莉觉得坐在这车上的,似乎只有她—个人。
她是一个寂寞的旅者。
她没能如愿地睡着,旁边的男人不停地对着手机讲话。
这却不是打电话,而是在“微信”。
短信用说话的方式来传递,莫莉搞不懂,那为什么不干脆打个电话。
这个男人也难以忍受旅途的乏味,每次他想与莫莉搭话,莫莉都赶紧把眼睛看向手里的杂志,强迫自己认真去读。
莫莉结婚了,她从一个敢跟陌生男人回家的狂野女子,变成了一个连别人的搭讪都不敢回应的温驯妇人。
她不怕陌生男人,从来都不怕,她也不惧怕丈夫的嫉妒和愤怒,她怕的是自己和自己作为一个妻子的身份。
她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决定嫁为人妇,却在结婚的一刹那就发现自己犯了个巨大的错误,更糟糕的是,她没有力量重新摆布一下自己。
原来的莫莉迅速毫不留情地离她而去,现在的这个人让她从里到外感到陌生。
她不懂自己为什么不再喜欢那些暴露鲜艳的奇装异服,为什么不再伶牙俐齿地咄咄逼人,为什么不再想做什么就敢去做什么,不懂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就失去了与众不同的魅力,变得像满街庸常妇人的孪生姐妹。
她抬起手臂,看着做工精细的真丝袖口,和袖口中伸出来的那只做了保养和美甲的塑料模特一样的手,发起了呆。
余娜娜坐在莫莉斜前方靠窗的位置,她和莫莉素不相识。
她也不知道莫莉正在看她。
当然,莫莉此刻看不到余娜娜,高而厚实的座椅靠背把她的身体遮得严严实实,莫莉能听到的只是她的声音。
余娜娜正在打电话。
她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区域销售代理。
这个公司刚刚起步不久,正在疯狂揽市场的阶段,只要完成销售任务,可以免除代理费。
也就是说,余娜娜可以“空手套白狼”。
但她也并不那么轻松,她是可以不交代理费,但她也不能不挣钱。
不挣钱她拿什么交房贷、买漂亮衣服和做美容呢?
她在高档饭店请人吃饭的时候常常有错觉,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女强人、女富商了。
回到家里,酒劲儿散去,她的沮丧便更深一层,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正在费力打拼的可怜的单身女人,很心疼在饭店里付出去的大把钞票。
攒起这些积蓄不容易,如果这个代理做得不顺畅,拿不到能完成任务的订单,那么花出去的钱就真的是覆水难收了。
所以实际上,所谓区域销售代理,只不过是不用付工资的销售员。
余娜娜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威严,她在跟公司交涉,希望获得一些免费的样品。
只靠一本图片,谁敢跟你签合同呢?
余娜娜反复强调自己已经打开了局面,她解释说之所以她到现在还没有签下一张订单,就是因为公司答应给她提供的样品一直没有到位。
对方是公司的一个副总经理,也是—个女人。
余娜娜不喜欢她,女人对女人总是很严苛,她坚决地要求余娜娜必须按出厂价自己出资购买样品。
她的理由让余娜娜很生气,她说如果你拿了免费样品就跑了呢,不做了呢,我们又没有收你的代理费,没有办法约束你。
这个理由很充分,但余娜娜依然理直气壮,她不想跟女人打交道,于是要求得到老总的手机号码。
余娜娜没见过他,可她相信只要给她机会,她就能把他搞定。
可女副总虚伪地向她道歉,说老总有家事要处理,特意交代这一周任何事情都不要打扰他。
余娜娜并没被女副总打击,她与公司的另—位男副总关系很好,就是他曾经允诺过可以特批给余娜娜一些免费样品。
但当余娜娜指出这一点时,女副总终于掩饰不住骄傲,用带着些讥笑的口吻告诉余娜娜,那位怜香惜玉的男副总已经辞职了。
莫莉不知道前面那个打电话的女人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她听到女人的声音很有活力,很润朗,有时还很高亢,听得出年龄不大,或许比自己还要小儿岁。
莫莉很羡慕她,莫莉羡慕一切有手腕的年轻女人,青春加上手腕,她们能让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
莫莉反省过,她发现自己只有对虚无发狠的能耐,即使在我行我素的年纪,她做出的那些自以为惊天动地的事也仅仅是些对现实无用的疯狂。
莫莉坐直身体,揉着僵硬酸痛的脖颈,耳朵里依然灌进那个女人的声音。
“我认为,他辞职与否跟这件事无关。
我只知道一个曾经主管公司销售的人答应过我可以提供一批样品。
如果你们公司可以用主管人员辞职来解释这种出尔反尔,那我就只能认为你们是个不守信不正规的企业。
有的是公司跟我联系,我可以随时撤出。
”莫莉觉得很振奋,她觉得女人的话切进要害,真理在握。
她再次瞥向那个座椅,期待那女人能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身,让她看看这个有着好听嗓音的年轻女强人有着怎样的面庞。
“……这不是我的损失,恰恰相反,这是你们的损失。
我在这方面有很广的人脉,现在我已经在大区的几个城市都打通了关节,合作意向都有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知道吗?
只要样品一到,他们对质量和样式都满意,马上就可以签合同。
他们是我的朋友,不是你们公司的朋友。
你不明白吗,我可以随时转做其他公司的代理,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时把这些你们公司的潜在客户变成别的公司的。
”莫莉又一次打开杂志,眼睛扫过一页一页的奢侈品广告,心里微微替女人着急起来。
她希望那个不知是干什么的混账公司赶紧同意女人的要求。
“……咱们虽然接触不多,但是我很敬重您。
”莫莉听到女人的声音突然变得软煦起来,好像由谈生意变成了拉家常。
“哪里哟,您才是真正的女强人啊,我还差得远呢。
您也别太累啊,女人嘛,得多为自己着想。
我们不为自己想,男人就不想着我们啦。
哎,对了,我一个朋友从美国给我寄来一些葡萄籽粉,听说能抗衰老的,特别好,美国人现在都吃,我寄给您几瓶您先试试效果……没关系的,也是朋友送的。
我有很多的。
”莫莉看到周围的几个人似乎都在倾听女人的话。
邻座闭目养神的男人这时候也睁开眼睛,看向斜前方女人的方向。
莫莉不满意女人突然的转变,不喜欢女人这种讨好的声音。
她觉得她应该据理力争地获得一次光明正大的胜利。
烦躁感又回到她心里,莫莉刷刷翻过几页炫目的彩页,看到一篇介绍野生动物摄影师的文章。
配发的图片里有一幅名叫“与美洲豹对视”。
莫莉把杂志捧起来,举到眼前,跟变成照片的美洲豹对视。
照片上那双眼睛虽然只是由彩色油墨合成,但莫莉还是在里面看到了凶狠和狡黠。
莫莉想,每个生物体都有一套个体哲学,用以让自己的生存和强大变得磊落和充满道理。
回过头来细看文章,里面写到的这个叫张愿的摄影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哲学系,后专职研究和拍摄野生动物。
记者问他为什么会改行。
张愿说,他其实并没有改行,最广阔和最真实的哲学就在大自然中。
莫莉想到自己刚才的想法竟与文章中提到的不谋而合,她认为那是她奇怪的预感又一次现身。
莫莉相信,人人都对自己的人生有着神奇的预知,只是没有人能分辨巧合和预感的差异。
于是,当事实发生时,先前的预感只能作为后悔或者感慨的依据,别无他用。
余娜娜疲惫地挂掉电话,嗓子干涩,说话的惯性却让她还有些兴奋。
她拧开矿泉水瓶盖,喝下一大口,又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她需要把刚才的事情向人讲一讲,她需要有个人倾听一下她对这件事的处理,夸赞一下她的先兵后礼,处事圆通,需要再顺便被关心几句,享受一下做女人的甜蜜。
电话通了,他的声音传过来了,余娜娜心里涌上调皮和喜悦,却还没等说话,就听见电话里低声而焦急地说道:
“我现在有事情,你有事吗?
”有事吗?
余娜娜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自己有事还是没事,她支吾着说:
“噢,也没什么事吧。
但是想跟你说说话。
”电话中说:
“那等—会儿我忙完了打给你啊。
”余娜娜说:
“好吧,那你忙吧。
”可是,这句话说出的时候,电话已经挂掉了。
虽然并没有人知道她说出的只是句无的放矢的废话,但她依然觉得很尴尬,心跳加速,脸上突地热了起来。
她不自然地换了—个姿势,看向窗外,可是天已经黑透,车窗上映出的只是她自己。
她看到自己,更觉得不好意思,马上又低下头来翻找手机上的电话簿。
如果你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只是想向人毫无理由地讲述一下自己的经历,那么对象真是少得可怜,只有这时候,你才发现,你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友谊和爱情。
这个想法让釗那娜很恐惧,她急于证明自己并不孤独,手指加快了速度,电话簿上的名字伴着“嘀嘀”的按键音一个个闪过,终于有一个名字让余娜娜停了下来,她舒了一口气,愉快地按了拨号键。
彩铃是一个叫“凤凰传奇”的组合的那首成名曲《月亮之上》,欢快高昂,让余娜娜对即将开始的通话充满动力。
然而,电话响了很久也没有人接听。
断掉之后,她又执拗地重拨了几遍。
《月亮之上》一遍一遍地重复演唱,每一次都被“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接听”毫无感情地切断。
余娜娜把手机拿在手上摩挲了一会儿,然后用力按了关机键,把它塞到皮包里。
《月亮之上》还是缭绕在耳边,那旋律在她身体里灌得满满的,马上要从嘴里溢出来。
她再一次打开皮包,取出笔记本电脑,打开,点击播放软件,找到电脑里专门存放歌曲的文件夹,插上耳机,按下鼠标—一就从那首《月亮之上》开始。
莫莉惊讶地听到了一阵似有若无的歌声,声音尖细,似乎在尽力抑制着不得施展,她以为是火车上的广播,仔细听了听,发现并不是。
歌声不顺畅,偶尔落掉几个字的歌词儿,又接上,还有些走调。
莫莉已经听出,是那首曾经满街传唱的《月亮之上》。
她不喜欢这种歌,觉得没有什么品位,尽管在某种时间和场合,它也显得有些动听。
现在,这歌声可并不动听,莫莉终于发现,它竟然来自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她原本以为,女人哼两句就会停下来,谁知道不仅没有停下.而且唱完了女声的部分,连男声部分的RAP那个女人也没有放过。
莫莉听到女人粗着嗓子学着男声,哼哼哟哟地念叨着。
她忍不住笑了出来。
不仅是她,周围几乎半个车厢的乘客也都同时明白了歌声的来源,不约而同地看向女人的方向,进发出一阵轻笑。
这种笑带着戏谑与嘲讽,与看马戏团的小丑表演时还不太一样,舞台上的小丑带给人的笑只是表达简单的欢乐,生活中的小丑带给人的笑还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满足。
莫莉此刻的笑与其他人并无不同,她觉得这女人突然尽失身份,形象骤然低落,成了漫长乏味的旅途中半个车厢的笑料。
莫莉合上杂志,专心听女人走调的歌声,用猜测她唱的是哪首歌的方式打发时间。
这对被旅途折磨着的莫莉来说真是行之有效。
感到轻松了许多的莫莉几次坐直身体,试图看到那个女人,但只看到小桌板上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半边屏幕,还有女人连着耳机的半头卷发。
女人唱的歌儿都是过时的流行歌曲,这类歌大多没有重量,不会让你内心深沉,只有简单的欢愉。
莫莉这才发现了这种歌曲的好处,她甚至有些感激。
坐在唱歌女人身边的男孩子已经把半个身子侧了过来,毫无用处地与女人的歌声拉开距离。
莫莉能看到他的侧脸,还长着几颗青春痘。
男孩儿正用手机玩游戏,女人的歌声对他来说显然已经从乐趣变成了干扰。
但他从没转过头去看他的邻居,除了偶尔用手不着痕迹地抚一下额头表达无奈,没有别的举动,莫莉便觉得,这是个礼貌的、心存温柔的男孩儿。
那么自己呢?
如果自己坐在女人身边,会不会表示出明显的嘲笑或厌烦,要么,会不会善意地轻声提醒女人她的失态?
莫莉不确定自己在特定时刻能否克制歹毒或驱除冷漠。
余娜娜的电脑上存了几百首歌,她几乎都会唱,如果生活全然顺遂自己的意愿,那么她会让自己去当一个歌星。
她的嗓子好:
乐感好,从小学到中专,都是文艺委员,学校里有演出,还经常是站在前面领唱的。
但余娜娜是一个现实的人,她做完了梦就会醒,最看不起那种头脑发热的傻瓜。
她只是把当歌星的愿望像一个宝贝样揣在怀里,时而拿出来看看。
在各个公司跳来跳去之后,余娜娜获得了一些资本,包括金钱、经验、心机、人脉,最重要的是她发现了自己的潜力——她要创业。
可对她这样一个缺少背景的女孩子,创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苦的时候,余娜娜感到好像自己全身都长出了味蕾,都能品到那苦的滋味。
好在有卡拉OK这种东西,她由此得到了不少补偿和安慰。
长大了的文艺委员余娜娜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拿起麦克风,她就会像曾在学校里对男同学构成吸引一样,瞬间风采怡人,令那些她尽心讨好的男领导男客户双眼发亮,心旌荡漾,看上去能为她去做任何事情。
所以唱歌渐渐在余娜娜生命中有了更丰富的意义,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武器,她用这种武器对付男人、时间和忧伤。
余娜娜将自己塞在座椅的一角,觉得刚刚的几个电话在恶狠狠地逼迫着她,她想重整旗鼓,马上想到了她还有件最称手的武器。
戴上耳机,歌声响起,余娜娜就进入了一个无敌的境界,屈辱感和失败感土崩瓦解,她开始膨胀,涨开逼仄的座位空间,冲破密罐样的火车车厢,变成顶天立地的一位女神。
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她自己。
余娜娜为自己涌起崇拜,这时候怎么也抑制不住想唱的欲望。
她跟着耳机里的旋律忘情哼唱的时候,根本没有顾及她会因为塞住了耳朵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而走调,也没有想到在噪音很小、乘客安静的高速列车上,她的歌声听起来会是那么嘹亮。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当听到女人嗲着嗓子唱出这句欢快得实在不合时宜的歌词时,莫莉发现周围的乘客们再次集体哑然失笑。
坐在女人后面一排的老年夫妇笑得靠在了一起。
老太太是那种穿着时髦、举止欢快的人,更年期的忧郁症状在她那个年龄早已一扫而光,脸上泛着孩子样的红润光泽。
莫莉有些羡慕这样的老年人,也许内心的怡美只有这样的年纪才会踏踏实实地跟在一个女人的身边。
老太太向她前面女人的座位伸出手去,被老伴一把将那只手攥住,握回放在腿上。
富态的老先生笑着摇了摇头,说了句:
“由她去唱嘛。
”莫莉听不出这句话的语气和情感倾向,可是莫莉发现,女人已经不再唱了。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唱完了这一句,歌声就戛然停止了。
莫莉在心里默默复唱了一句,突然感到了一阵酸楚,她闭上眼睛。
睫毛湿莹莹的,弄得她眼角有点儿痒。
车厢里霎时显得极为安静,除了火车行进的声音,莫莉只能听到自己因克制情绪而粗重的喘息。
她猜想,唱歌的女人跟她一样,被这句歌词引发了感伤,此刻,她们同样因为流逝的美好或者还有迷惘的余生产生了哭一场的欲望。
莫莉终于把泪水忍了回去,睁开眼睛望向女人的方向——深灰色的座椅靠背把女人完全遮挡,仿佛那座位上根本就没有人,仿佛刚才的歌声压根儿就只是在莫莉的心里。
合上电脑,余娜娜深深吸了一口气,再慢慢地,一点一点吁出来。
她并不知道,她的心境被另—个女人轻轻地、毫无预谋也毫无道理地猜中了。
嗓子感觉干燥,空调抽走了她身上仅有的那点滋润感。
可是余娜娜只是将矿泉水瓶紧紧搂在怀里,并没有拧开瓶盖喝上一口,好像那是一个什么珍贵的物品。
她跟自己的干渴对峙着,品味着自虐感带来的忧伤。
耳边没了音乐,一下子显得特别空静。
余娜娜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她很少有这样的思考——假如人一直身处天堂样的宁静和安稳,心中是会常喜悦,还是会更焦灼?
直到到站,莫莉一直靠在调斜的椅背上,瞪着眼睛看着苍白的车厢顶棚。
乘务员从车厢的一端走过来,逐个座位收拾垃圾,并提醒乘客整理好自己的物品。
莫莉邻座的那个男人如释重负地坐直身体,自言自语地叹道:
“终于到站喽。
”然后麻利地从自己的前前后后收拾出七八个空的饮料瓶,一股脑儿扔到乘务员推着的垃圾车里。
莫莉没注意他什么时候喝了这么多水,而且惊讶他竟然这几个小时都没有起身去厕所。
莫莉因此对他笑了一下,这笑容让他获得了机会似的眼睛一亮,凑过脸来问莫莉:
“你是来出差吗?
”莫莉慌忙收了笑,答非所问说:
“我老公来接我。
”听到自己莫名其妙的回答,莫莉马上羞愧起来,低下头收拾东西,没有敢去看那男人。
男人穿上大衣,站起来。
莫莉仍旧只是低着头向外侧了一下身,看到他粗壮的两条腿从身边挤过去,在过道上停留了片刻,向车门的方向走去。
乘客们陆陆续续地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东西。
很多人都迫不及待地先到车门旁边排起队来。
莫莉没有动,她想看到坐在斜前方窗口座位的那个女人站起来,转过身,从身旁经过,诚恳地向自己展示容貌、身材、体味、服装的品位和目光中的内容。
她想了解那女人,想得到—个适当的时机跟她说说话,想体贴她的心思,分享她的苦乐,听她讲讲她生活中最细小的那些事,或许还可以向自己传授一下她与这世界周旋的办法。
但是,那个女人跟莫莉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座位上,似乎是在与她抗衡。
等到火车停稳,车门打开,人流从车厢里转移到熙熙攘攘的站台上,等到有人从外面叩响莫莉这一侧的车窗,那个女人还没如莫莉所愿地站起来。
莫莉看到车窗外丈夫向她微笑的脸,只好起身,穿上貂皮大衣。
大衣是丈夫送的,莫莉不喜欢,她厌恶甚至蔑视把动物毛皮穿在身上的人。
可她还是穿上了,并且竟然说了喜欢和感谢,说了你真好和我爱你。
豹纹图案的大衣让她想起杂志图片上那只与她对视的美洲豹。
裹在大衣里的她觉得自己是一只被美洲豹吞到腹中的猎物。
那个女人还没动,站起来的莫莉可以看到她静止的头发和摆在扶手上的一只胳膊。
莫莉本想从前面的车门下去,尽管远一些,但是她可以回头看一眼那女人。
可是她透过车窗看到丈夫已朝她背向的那个车门走过去,只好拎起手包,转身,与那个女人越来越远,还原成最初那种彻底的陌生。
余娜娜觉得自己累极了,尽管明天约见的人对她的所谓事业来说很重要,她也不想明天到来。
她得知那人有些好色,这对—个急需他帮助的女孩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也是一件坏事情。
余娜娜有的是对付这种男人的经验,要动用那种似有若无的勾引,让他觉得有希望又不明确,还得展现能力与才华,让他心怀渴慕又不敢冒进。
如此才能牵动男人心,让他帮你做事又无法控制你。
但是这是一场很艰难的斗争,弄不好便会事也办不成,还要将自己赔进去,劳神着呢。
余娜娜早就厌倦了这种周旋,她真想某个能上天人地的男人会死心塌地爱上她,听从她的指示,扶她上青云。
她就是这样想的,她需要依靠男人,但不是把自己完全塞给他的那种依附。
对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的余娜娜来说,男人应该是台阶,而不是屋子。
然而,她遇到的男人都虚情假意,她也只得让自己虚情假意。
她自认为是—个心存真诚的人,对一个心存真诚的人来说,虚情假意是一件特别累的事情.余娜娜觉得几小时坐着不动的旅程让她胸中积郁,她重重地叹出一口长气。
这是终点站,车厢中渐渐空了下来,乘务员带着疑问的表情向唯一一个还坐着不动的旅客走过来。
余娜娜赶紧站起来,匆匆忙忙地套上大衣,从行李架上取下像个红灯笼一样孤零零悬在头上的红色旅行箱,拉开拉杆,拖着沉重的脚步和箱子向车门走去。
莫莉回应了丈夫的亲吻和询问,乖乖地跟随着他。
她被带到一辆在停车场的灯光下闪闪发亮的宝马车前。
丈夫拉开车门,满脸得意地看着她,等她评价。
莫莉只好说:
“真漂亮。
”“不光是漂亮。
”丈夫显然对这句没有切入要害的赞美不太满意。
“最新款的顶配,给你买的。
我就知道你喜欢。
”莫莉笑了笑,坐上车。
她很想纠正一下丈夫的话,首先这是他的车,莫莉与他两地分居,分享的次数有限得很,还有便是她根本就不喜欢。
但是她说不出口。
她所有那些难以言说的感觉都不会被丈夫理解,即便是说出来的心思也会被他毫不犹豫地忽略。
而且这个男人有本事将所有自利的行为都说成是为别人好,莫莉曾多次想辩驳,但最后都以绝对的失败告终,还会鬼使神差地对他产生愧疚和感激。
现在莫莉早已放弃了抵抗,沉默起码还能让她保持清醒,一旦发言她就越说越糊涂。
所以莫莉此时只得笑笑。
坐下来,透过车窗,莫莉才发现原来正在下雪。
细小的雪花在无数路灯和车灯中飞旋,被照耀得像一只只莽撞的萤火虫。
停车场里汽笛声乱作一团,宝马和不是宝马的车辆们接到了亲人和不是亲人的人,都急着要驶离这个没情趣的地方,回家或者去往不是家的其他好地方。
丈夫不着急,他发动汽车,把暖风开大,不由分说地就把莫莉搂了过来。
莫莉的大衣没有系扣子,里面只是一件丝质衬衫,这让丈夫的手极为顺利地长驱直人,一把握住了她的一只乳房。
莫莉被这只冰凉的手惊吓,一把推开丈夫。
“别摸我!
”她大声说。
丈夫马上皱紧了眉头。
莫莉像外国人那样耸耸肩,拍拍椅座,“B,M,W——别摸我。
”她说,随即尴尬地笑了两声。
丈夫脸上再次展现出昂扬的笑,这让他看起来似乎完全相信了这只是莫莉临时进发的幽默。
莫莉不得不承认,自己害怕这个男人。
她无奈地看到自己的右手正将丈夫的左手拽过来,焐在大衣里暖了一会儿,便任由它再次突破衬衫和胸罩,抚上自己起伏的胸。
那只手还是很凉,莫莉觉得全身由一只乳房开始刚的一下便冷透了。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手很凉?
”莫莉搞不清楚自己该因丈夫不管不顾的激情感到欣慰还是伤心。
余娜娜拖着箱子站在车站广场上,没有人接她。
尽管她已经打电话预订好了酒店,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没有归处,不知道该去哪儿。
出租车等候站拥满了人,地铁售票处前的队伍也排得曲曲折折,甩了几道弯还嫌不够长。
人们行色匆匆,每张脸都像冰雕,让余娜娜突然感到了某种诡异的恐惧。
心尖锐地疼了一下,很具体的疼。
她想,“心痛”真是一个高明的词,是心理和生理状态的胶合。
余娜娜抚着自己的头发,有点儿湿,这才发现下雪了。
灯光里旋落的雪花和灯光里笼罩着的人一样多,雪中和人潮中的余娜娜更觉茫然,她呆呆地站了很久,才决定不管怎样,先要让自己看起来是个有奔头的人。
于是,蹬着高跟短靴的余娜娜迈出了弹性十足的那种步伐。
拖在地上的红色拉杆箱碾过广场上的方砖,一颤一颤,显得跟余娜娜的靴子一样快活。
地上有些湿滑,余娜娜绷紧小腿,让脚步没有一丝的犹疑。
连她自己也被这坚定的姿态骗过,心中仿若真的充满方向。
莫莉很想阻止丈夫不断按响喇叭的手,可这似乎比阻止他那只攥住她乳房的手还缺乏理由。
她于是转过头看向窗外。
汽车的车窗外与火车的车窗外有全然不同的景色,一个繁华过盛,一个寂寥太深。
她忽然又想起火车上那个自顾听着耳机唱歌的女人,希望自己此刻能重演她的举动。
作为丈夫的男人终于将那辆让他自信倍增的宝马车隆重地驶出了停车场,一路汽笛长鸣。
莫莉深埋着头,羞耻感将她的脸蒸得发烫。
丈夫只会为了没有钱而羞耻,他认为—个人被别人瞧不起只是因为缺乏地位和金钱,他只对这两样东西谦和有礼,对其他所有的都显出不可一世的傲慢。
从小职工到小商人,从小商人到大老板,他迅速地扩张业务,没有原则,什么赚钱做什么,最近又刚刚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
莫莉想,与其说他是在积累财富,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积累傲慢的资格。
圆滑和强硬,虚伪和无情,自大和狡猾,这些莫莉最恐惧和最缺少的东西却聚集在这个离她最近的男人身上。
可能正因为恐惧,莫莉在面对它们的时候毫无抵挡的能力,被利落地打成败寇,而也许也正因为缺少,在虚无里骄傲而在现实中却现出彻头彻尾的可怜的莫莉才不由自主地需要它们的保护。
所以与其说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