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均田制下产权制度变迁分析Word下载.docx
《北魏均田制下产权制度变迁分析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北魏均田制下产权制度变迁分析Word下载.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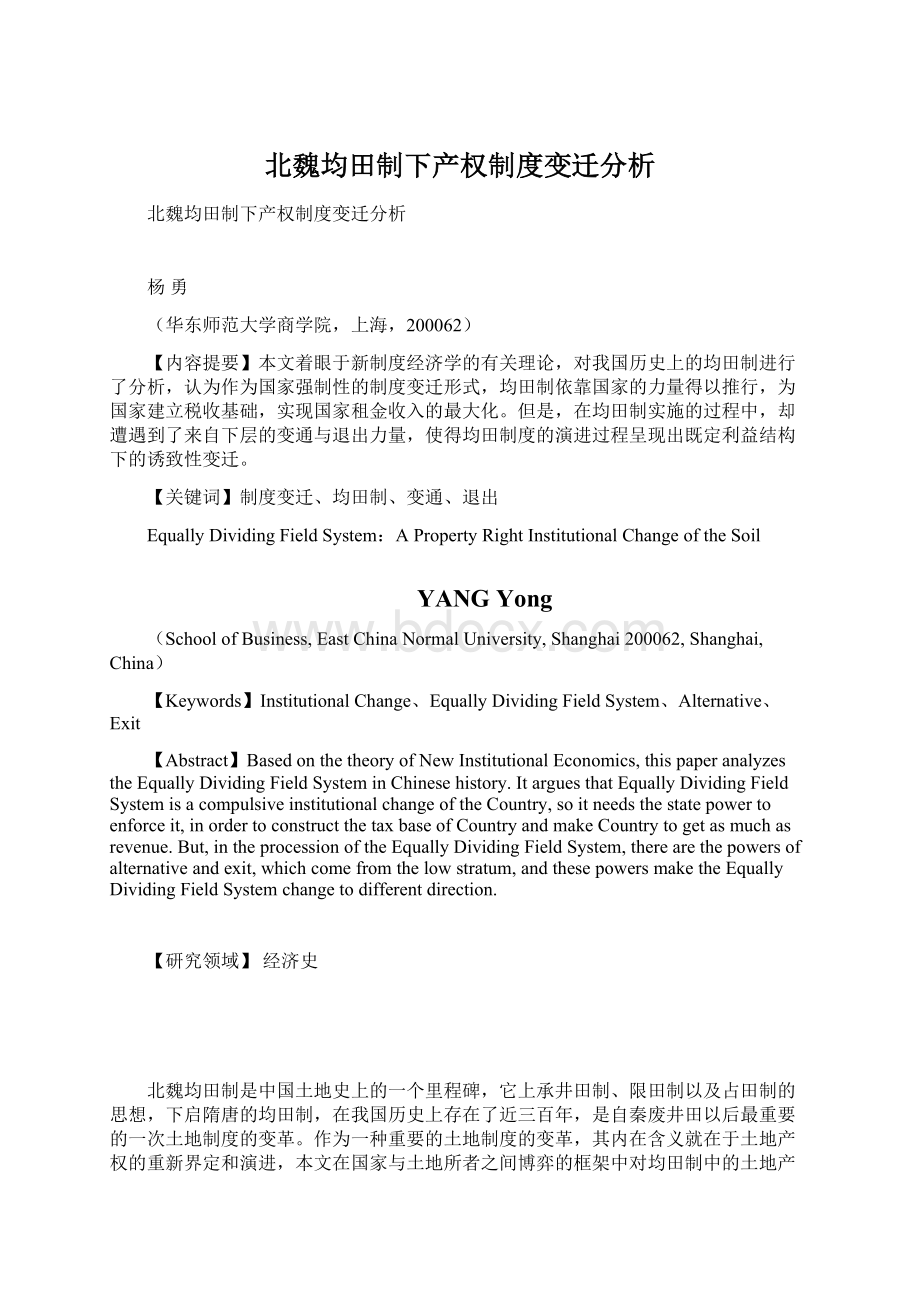
不过诺斯注意到,国家上述两个目的并不总是完一致,因为“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有效率的产权安排只是国家与私人努力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众多结果中的可能的一种。
但是,国家作为在“暴力潜能”方面具有优势的组织,一方面可以为现有的产权结构提供有效的保护;
另一方面还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租金最大化的目标而实施强制的产权制度变迁。
特定的制度决定特定的产权结构,如果产权纯粹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契约,并且可以通过个人信用得以履行,国家就不再构成产权安排中的一个必要成分。
然而,当产权经济学家阐述产权的实施时,通常都要强调产权的被保护和实施。
这就要求超越个人之间平等权力的强制权力的存在,国家由于其特有的“暴力潜能”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这个角色。
所以,当现有的制度结构不能适应国家租金最大化的要求的时候,国家就可能通过强制的力量来实现制度变迁,形成新的产权结构。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1989)在其经典论文中对制度变迁的形式进行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区分,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清晰可辨的,二者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影响和交叉;
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
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性变迁更多的是对现有制度下不能实现的利益的自发响应,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目标函数和需求。
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易于形成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和产权结构,这又会成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起点和背景。
由国家界定和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目的同经济社会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目的一样,即都是为了重新安排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不均衡的利益机会。
在经济增长出现利益机会的不均衡的时候,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有关利益的各方之间自发进行协调和谈判的结果,而强制性制度变迁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方式,更多地是取决于国家租金收入目标的实现和对产权的保护。
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大的利益集团的有时决定了实际的制度演进方向。
奥尔森通过对利益集团行为的研究表明:
“不存在这样的国家:
其中所有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都可能组成平等的集团并通过全面协商而获得最优的结果。
”大的利益集团的行为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作用力,这可能纠正政府所制定和执行的新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形式,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所以,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某些制度变迁的路径是国家与社会经济个体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博弈的结果。
简言之,就是一种制度的变迁既不全是自发力量实现的诱致性变革,也不全是国家力量强制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各界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也就决定了产权变革的方向和内容。
以上的讨论可能稍嫌粗浅,但是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大致的理论框架。
下面我们以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为例来进行分析,以验证以上的理论框架。
二、国家控制和推进的土地制度变革
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是我国古代土地史上重要的一种制度形式。
一、均田制的基本思想
大约在太和8年(484年),李安世向孝文帝上疏提出了均田主张,认为:
“今虽井田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
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
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
……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
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
”该思想上承限田、占田思想,成为北魏均田制的主要指导思想。
均田制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力业相称”,创造一个稳定的小农经济单位,使“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黄仁宇在研究均田制的过程中认为:
“(均田制)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基层组织,使大多数的小自耕农纳税当兵”,也就是说,均田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为国家提供一个广大的税收基础,通过政权的力量减少豪强地主占有的耕地以及“荫庇”的劳动力,增加国家的“编户齐民”,使“豪右靡余地之盈”,使国家获得更大的租金收入。
二、三长制度和新租调制度
新的户籍制度及赋税制度是均田制实施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制度,均田制和清理隐户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把隐户清理出来,才能落实均田制;
只有实施均田制,也才能妥善安置清理出的隐户。
为此,太和十年(486年),北魏政府颁布了三长制,即五家为邻,设一邻长;
五邻为里,设一里长;
五里为党,设一党长。
其主要任务就是校订户籍,查实田地数量,协助政府检括隐户以及收敛租调,差派徭役,从而,使“课有常准,赋有恒分,包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
”为国家收入提供可靠保证。
随着三长制的施行,北魏政府施行了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税制度,即新的租调制: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
民年十五以上未娶着,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
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
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新的租调制以小农户为征收单位和基础,稳定的税收来自稳定的税基,稳定的税基来自稳定的基层经济组织。
因此,国家最大化租金目标的实现需要均田制、三长制以及租调制的相互配合,均田是核心,租调是目的,三长制则是实现前两者的前提。
三、均田法下的土地产权类型
根据均田法规定的受田、还田的规则,国家发授的土地产权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有受有还型,一是有受无还型,这两种土地发授类型体现了不同的土地产权。
1、有受有还型的土地产权
均田制的重点就在于土地的“还受”,“均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
”北魏均田制根据国家规定的土地的使用用途将国家发授的土地分为露田、桑田、麻田、宅地以及菜地等类型,露田和麻田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类田地,规定: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从良。
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
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受还之盈缩。
”并且,“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
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
“诸麻布之土,男女及课,别给麻田四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
皆从还受之法。
按照《通典》的解释,“不栽树者谓之露田。
”露田就是种植大田作物的土地,而麻田则是种植桑麻的土地,国家发授的这两类土地均“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
”是有受有还的土地,国家拥有这两类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农户得到的仅仅是该土地的使用权,并且是不完全的使用权。
新的租调制度是一种征收实物的税收制度,主要以征收粟米以及布匹为主,国家通过保留土地最终所有权以及部分处置权可以获得稳定的赋税收入,使得当时的土地制度更多地体现了国家的利益。
2、有受无还型的土地产权
有受无还型的土地主要有桑田、宅地,这部分土地体现了农户对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农户名义上以“世业田”的形式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国家仍然保留了对土地的部分权力。
“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即通入倍田分。
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
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
奴各依良。
限三年种毕,不毕,夺不毕之地。
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
“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诸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
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
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其不足。
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这里不但规定了露田、倍田以及桑田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规定了桑田的性质以及相关的权利。
作为世业田,农户对桑田拥有所有权,不进行还受,老免身没不还,并且可以有子孙世袭,成为农户长久占有的田土部分,也成为农户相对固定的产业。
农户对其拥有使用权、继承权以及足额的占有权,但是对其使用权却再一次受到国家权力的干扰,即只能在这种土地上种植国家规定的作物,并且“限三年种毕,不毕,夺不毕之地。
”并规定“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此外,世业田的买卖权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买卖都不能超过各人应得之数,否则就是违法的。
四、国家制造的、残缺的土地产权
“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可能渴望进行调整的回应。
”这里面含有力量不对等的不同人群或权利之间就新的产权进行的协调和谈判,国家权力有时就成为这些谈判中的重要力量。
当现有的产权结构不利于国家租金收入的取得乃至影响到国家政权稳定的时候,国家就有可能采取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以形成有利于国家租金收入的制度(产权)结构。
在均田制的施行过程中,国家保留了大量的土地所有权,而农户得到的仅仅是一种残缺的土地产权,如规定田地的用途以及使用期限;
就桑田等世业田来说,虽然国家承认农户对其的所有权,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土地的买卖,但是,国家不但限制了土地买卖的范围(“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其不足。
”),而且就使用用途也作了限制,并要求必须完成,“限三年种毕,”否则,“不毕,夺其不毕之地。
”国家要收回不能完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土地。
在北魏新的租调制度下,租(“粟”)调(“布”)是国家租金收入的主要部分,国家对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限制也就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保证露田的“租”以及麻田的“调”的来源(“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
”),并对土地的还受根据劳动力“可课”与“不可课”(“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
”)为时间期限进行配给。
也就是说,国家利用国家权力侵入了农民的土地产权,对农户土地使用、收益以及转让给予了限制、管制和干预。
按照产权经济学家的分析,国家造成了农民所有制的“残缺”。
这部分集中在国家手中的残缺的土地产权是与国家的租调收入结构相适应的,正是国家控制的这部分残缺的土地产权构成了国家获取租金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
农户虽然获得了土地及其部分的使用、收益和转让权,但是其经营行为却被国家强制地纳入到国家的收入结构之中,国家通过收回土地等有力的威胁将农户的土地产权结构纳入国家的利益框架之中。
三、变通和退出
经济制度变革的结果只能在事后加以评估,但是,当一种制度,尤其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形成的时候,政策的制定者总是假设制度与制度设计者的目标之间存在对应的关系。
然而,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却可能因为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改变以及既定利益结构的存在,造成原有利益集团对新制度抵制,或者造成制度的演进方向脱离制度创始者的意愿轨道,或者导致新制度的破产,社会不得不重新进行利益的安排。
一、大地主集团的谈判力量:
变通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均田制无疑是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得以推行的。
然而,在我国古代的“中央—地方—宗族—农户”的社会统治结构中,大地主作为国家政权统治的一环是具有相当的谈判力量的。
一方面他们的利益要求可以比较容易地反映到国家政权的高层统治者,一方面他们作为当时社会上巨大的利益集团,可以“增加法律的繁文缛节,强化政府的作用,造成协议的复杂性,并改变社会的演化方向。
”在均田制施行之初,对三长制的反应就有部分的抵抗:
“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
”虽然《食货志》上称:
“书奏,诸官通议,称善者众。
”对李冲的三长制,那些代表豪富并兼者利益的诸官是坚决反对的。
“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
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
‘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
言似可用,事实难行。
’羲又曰:
‘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
’……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
……著作郎傅思益进曰:
‘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
’”可见当时的反对意见是很激烈的。
面对百官的反对,“太后曰:
‘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群议虽有乖异,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
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仅就三长制的施行而言,以豪强百官代表反对派的意见与朝廷意见是不一致的,只是在文明太后的驳斥之下,朝廷才力排众议,使得三长制得以实施。
所以,均田制在实施之初就显示出国家作为一个拥有暴力潜能的垄断组织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
但是,在均田制的具体执行环节中,国家做强制制定的产权制度结构却受到了来自下层变通方法的挑战,使政策在执行中发生了扭曲。
变通的方法,或者是无视均田制的存在,有令不行或缓行;
或者是在均田制规定的框架内就有关内容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加以调整。
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均田制通过国家的力量得以施行,但是并没有全面的推行,至少在若干地方并没有实行。
北魏重臣韩麒麟,官居冠军将军、给事黄门侍郎、齐州刺史、假魏昌侯,他在太和十一年(487年)即均田令颁布二年后,给皇帝的表陈时务疏中提到: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
”并提出与均田制相似的“制天下男女,计口授田。
”可以看出,韩麒麟对早已于两年前就颁布的均田法是不知情的,否则,就不至于重提“计口授田”之事了。
另外,一般情况下,任何新制度的推行,政府总会先以京师一带试验,取得经验后加以推广,边远地区通常不会走在前面。
而韩麒麟所称则是京师“不田者多”,而且“游食之口,三分居二。
”其后太和十六年(492年)的一个劝农诏书中说:
“京师之民,游食者众。
”证明韩麒麟的话是不错的。
并且,这些为数众多的“不田者”或“游食者”不可能都是工商业者,因为此时的工商业也不发达,从“魏初至太和,钱货无所周流。
”工商业是很不发达的,容纳的人口必然很少。
另外,即使有些地方表面上遵照法令,实行授田,但是豪门权贵每每凭借权势,上下其手,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使土地的分配有利于自己。
把瘠土荒畴分给百姓,而良田沃壤则尽归权门,这样,名为均田,实系兼并,这种情况在边远地区尤为严重。
“(怀)表曰:
‘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葘亩。
然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凋敝,日滋月甚。
……’时细民为豪强凌压,积年枉滞,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
”景明时是在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以后十五年以后,边缘地方虽然按照均田令进行分田,但是丰腴肥沃的土地都为主将参僚所独擅,百姓分到的都是贫瘠的土地,使当地的百姓苦不堪言,及至有了申诉的机会,“一朝见申者,日有百数。
”象这样的事例在北魏实行均田法以后并不鲜见,这就完全与均田制的精神相左了。
二、小农的谈判力量:
退出
均田制将租税的交纳与否同土地的还受完全结合起来,确定了土地使用者和国家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以劳动者与土地相结合为前提的新的租调制度确立并固定了农户应缴国家租赋的数额,固定的租赋负担对农户具有良好的激励效应,因此,农户与土地的长期结合似乎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假设。
国家租赋数额的确定更多地包含了国家的意志,体现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环节中国家却缺乏有力的控制,这无疑会导致执行过程中对该政策的扭曲。
更加致命的是,北魏均田制实行之初,对土地的分配是按照当时人口进行分配的(“仅从见口”),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与人口之间的原有比例关系必然会面临严重的威胁,从而就会威胁到均田制实行的前提条件。
此外,农户在缴纳租调制所规定的赋税以外,还要为国家承担繁重的徭役劳动,这也是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对农户进行征收的另一种形式的赋税。
被征调的劳动力为国家无偿地服役,从事各项公家劳务,比如营造或修建皇家的各项建筑工程,政府各机关的公用建筑或政府举办的公共工程以及政府指定派遣的各项劳役,如此等等,成为农户的繁重负担。
比如:
“[天平二年(558年)八月]甲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
”也就是说,农户实际承担的各种形式的国家赋税还是相当重的,在国家赋税的负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农户就必然会通过各种方法甚至是极端的农民起义的方法来对抗国家的权力或推翻现有的国家政权。
北魏均田制虽然建立了农户与国家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但是农户在与国家的关系中,仅仅是一种单向度的管理与统治关系,广大小农户的需求和呼声通过正常途径“上达天听”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因此,通过其他的方式实现与国家之间的协商和博弈就成为农户所能使用的手段。
均田制限制了农户在“狭乡”和“宽乡”之间移动的条件,但是,劳动力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农户自己的手中,农户可以通过对自己劳动力的处置权来实现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协调。
在与国家博弈的过程中,农户对劳动力的处置权主要是通过从国家的赋税体系中退出而实现,一是从国家的编户体系中退出,寻求大地主的荫护,利用当时士族的免役特权,再次成为大地主的荫庇之民,或“穿避山湖,”去做“浮浪人”;
一是毁坏自身的劳动力,甚至自残身体,使自身不再成为国家征收或徭役征调的对象。
更有甚者,当佛教兴起的时候很多人皈依佛门,以逃避征调,这种情况到北魏时达到极盛,僧尼大众多达二百余万人:
“正光以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募沙门,实避调役,猥滥至极。
自中国之有佛法,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余万矣,其寺三万有余,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四、结论性评论
本文把均田制看作是围绕土地产权的重建所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个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权力对全国的土地实行了全面的进入,以形成国家与农户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重建国家的税收收入基础——小农土地所有制。
均田制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据《魏书•地理志》记载:
“正光(520年)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余矣。
”西晋太康(280年)平吴以后,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
今云倍而余者,是其盛时,则户有五百余万矣。
”也就是说,均田制实行以来,国家编户户口大量增加,这虽然有社会安定人口自然增殖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大地主的荫庇下脱离出来受田自耕的户口。
另外,均田制的实行增加了北魏的国库收入,通过编户与均田,使“隐口漏丁,即听附实”,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于时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
及太后赐百官负绢,任意自取,朝臣莫不称力而去。
但是,在均田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传统社会组织中的各种力量形成了对国家推行制度的抵制,使得北魏政府执行的均田制不是得不到真实的贯彻,就是被扭曲,使得制度的演进重新复归到原有的大地主的利益路径上来。
所以,北魏均田制同样面临“诺斯难题”,即拥有暴力潜能的国家如何保护有利于国家租金最大化的产权问题。
当国家的目标与执行者以及农户的激励不相容的时候,国家的政策就必然会受到来自他们的抵制和扭曲,使国家强制规定的产权结构在自发交易的基础上得以重新构建,并逐渐脱离国家意愿中既定的方向。
均田制自北魏实施以来,到唐朝“两税法”,绵亘近三百年,其间经过了种种变动,但是最主要的变动就是土地处置权范围的扩大。
北齐、北周时期,麻田也成为永业田,“不在还受之列”,私有制范围得到了扩大。
唐朝则对土地买卖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北朝买卖土地仅限于永业田,并仅仅是“得卖其盈,”“买所不足”,到了唐朝,在好几种情况下,口分田都可以买卖。
就北魏均田制著名学者黄仁宇做了如下的归纳,可谓一语中的:
“魏之‘三长’、‘均田’以及(其后)各朝的‘府兵’,都系用‘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Design)作基础,也就是先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广泛的推行于各地区,行不通时,互相折衷迁就,只顾大体上在某种程度上的可行,无意以条文作主,凡事认真。
这种办法施行至公元775年安禄山叛变时,已不能继续。
”经济制度的变革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无疑内含着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在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中的利益主体必然会利用各种力量来修正经济制度的变迁,以至于使新的经济制度流于破产和失败,使得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整个国家当作一个多数农村拼成的大集团,缺乏中层经济上的组织与交流,迫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单线条数量上的扩充,缺乏质量上的突破。
”这或许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低水平发展而不能进入的新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原因吧。
参考书目:
1、[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美]曼库尔·
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