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民的诠释Word文件下载.docx
《民法中民的诠释Word文件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民法中民的诠释Word文件下载.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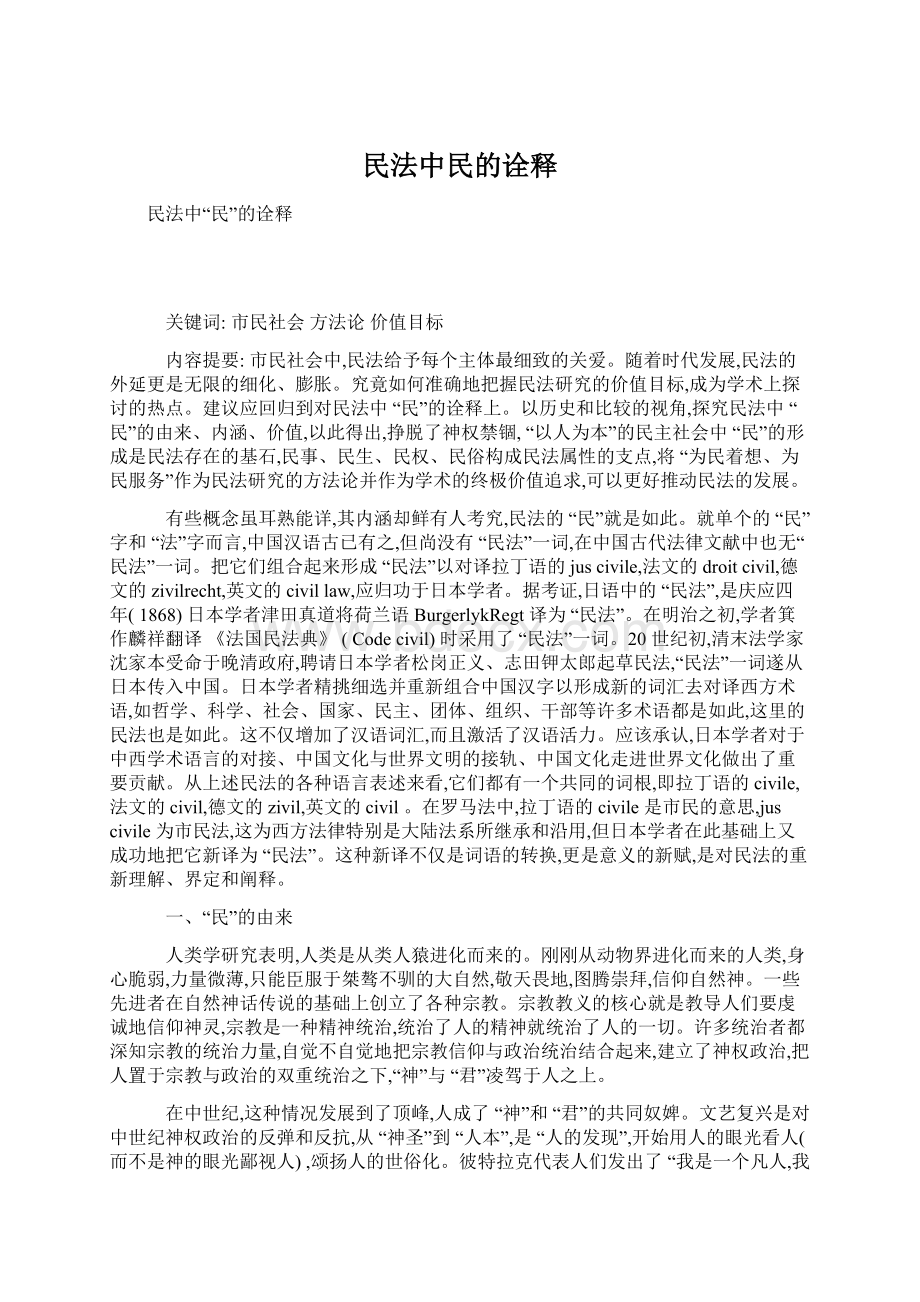
以历史和比较的视角,探究民法中“民”的由来、内涵、价值,以此得出,挣脱了神权禁锢,“以人为本”的民主社会中“民”的形成是民法存在的基石,民事、民生、民权、民俗构成民法属性的支点,将“为民着想、为民服务”作为民法研究的方法论并作为学术的终极价值追求,可以更好推动民法的发展。
有些概念虽耳熟能详,其内涵却鲜有人考究,民法的“民”就是如此。
就单个的“民”字和“法”字而言,中国汉语古已有之,但尚没有“民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也无“民法”一词。
把它们组合起来形成“民法”以对译拉丁语的juscivile,法文的droitcivil,德文的zivilrecht,英文的civillaw,应归功于日本学者。
据考证,日语中的“民法”,是庆应四年(1868)日本学者津田真道将荷兰语BurgerlykRegt译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学者箕作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Codecivil)时采用了“民法”一词。
20世纪初,清末法学家沈家本受命于晚清政府,聘请日本学者松岗正义、志田钾太郎起草民法,“民法”一词遂从日本传入中国。
日本学者精挑细选并重新组合中国汉字以形成新的词汇去对译西方术语,如哲学、科学、社会、国家、民主、团体、组织、干部等许多术语都是如此,这里的民法也是如此。
这不仅增加了汉语词汇,而且激活了汉语活力。
应该承认,日本学者对于中西学术语言的对接、中国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接轨、中国文化走进世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上述民法的各种语言表述来看,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根,即拉丁语的civile,法文的civil,德文的zivil,英文的civil。
在罗马法中,拉丁语的civile是市民的意思,juscivile为市民法,这为西方法律特别是大陆法系所继承和沿用,但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又成功地把它新译为“民法”。
这种新译不仅是词语的转换,更是意义的新赋,是对民法的重新理解、界定和阐释。
一、“民”的由来
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是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
刚刚从动物界进化而来的人类,身心脆弱,力量微薄,只能臣服于桀骜不驯的大自然,敬天畏地,图腾崇拜,信仰自然神。
一些先进者在自然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创立了各种宗教。
宗教教义的核心就是教导人们要虔诚地信仰神灵,宗教是一种精神统治,统治了人的精神就统治了人的一切。
许多统治者都深知宗教的统治力量,自觉不自觉地把宗教信仰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建立了神权政治,把人置于宗教与政治的双重统治之下,“神”与“君”凌驾于人之上。
在中世纪,这种情况发展到了顶峰,人成了“神”和“君”的共同奴婢。
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反弹和反抗,从“神圣”到“人本”,是“人的发现”,开始用人的眼光看人(而不是神的眼光鄙视人),颂扬人的世俗化。
彼特拉克代表人们发出了“我是一个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呐喊,唤醒人们不再痴迷那美轮美奂但遥不可及的天国美梦,人自此从神话的说教中和威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后来,路德进行了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对教义的垄断和教会对世人的束缚,人们可以直接与上帝单独交流,可以自己想象上帝,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经文。
宗教改革进一步将人从教会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催生了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人开始了精神独立。
紧接着启蒙运动的开展,开启人的心智,运用人的理性,认识到人本身的尊严和力量。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促使近代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
“我”的存在归因于“我思”,是“我”自己的“思考”“思维”“思想”“理性”,而不是归功于“神灵”和“君主”,更不是别人,后面这些东西只能使“我”为“他们”而存在,甚至使“我”不存在,而无法从根本上使“我”存在——“为我的存在”,“自我的存在”。
这就为人的存在、独立和自由奠定了理性的基础。
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不仅开创了主客体的二元论传统,更重要的是突出了哲学中的主体性要素——人的因素。
至17世纪,康德认为“人是目的”[1]、黑格尔认为“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是法的绝对命令”。
[2]至此,人的理性和尊严确立起来了。
哲学转向是政治变革的前奏,哲学思潮是政治革命的指导思想。
法国大革命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集大成和总结果。
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革命的主要成就之一是颁布了《人和公民权利宣言》以及《法国民法典》。
至此,人不再仅仅是哲学探究和政治议论的主题,而且成为了法律权利的主体和制度保障的对象,人在法律制度中确立起来了,人也因此真正站立起来了。
由上可见,人的成长经历了从神到君,再从君到人的发展历程,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民法是基于人的成长而制定出来的,有了独立、平等、自由的人之后,才有民法和民法典。
民法关于人的规定,自罗马法开始就有。
罗马法“或是关于人的法律,或是关于物的权利,或是关于诉讼的法律”。
罗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法”。
不过,与近现代以来的民法不同的是,罗马法的“人法”依据等级观念把人分为若干等,“关于人的法律地位主要区分如下:
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3]因此在罗马法上,并不是人人皆为主体,也不是人人平等,生物学上的“人”(Homo)与法律上的“人”(Persona)并不一致。
罗马法中表达“人”的另外一个词——“Caput”,其含义之一是市民名册一章。
[4]这种登记是甄别人口的一种治理技术,还不是赋予人主体地位的一种资格规定。
近现代民法中,人本身就足以获得法律主体地位,作为法律主体的人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完全同一的,所有的人、只要是人都享有法律主体资格。
如《法国民法典》第3条规定:
“关于个人身份与法律上能力的法律,适用于全体法国人,即使其居住于国外时亦同。
”第8条规定:
“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
[5]《德国民法典》第1条“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的完成”;
第2条“满十八周岁为成年”。
近现代民法接纳人人,没有限制,人皆主体,无人能外。
民法中的所有规范既以人为起点,也以人为目的,是典型的“人法”,离开了人,民法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这是民法秉承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和表现。
近代民法担当着反封建专制、限制君主权力和消灭社会等级的历史重任,所以它们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就是把人抽象化,规定一般的人,在人身上再也看不出身份等级差别,民法确认和保障人人平等,这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但这种抽象的人太一般、太笼统,连人的固有差别都抹杀了,以至于体现不出民法应有的属性和特征。
其实,只要社会存在,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必然存在两类人,即官与民,因此必须对人作这种区分,把人区分为官与民。
此两类人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处于不同的法域,适用不同的规则,因而才有官法与民法(比叫公法与私法更好)的划分。
民法是民之行为准则,是民自然自发、自由自治形成的法律规则,与官法在形成、属性和宗旨等方面都大不相同。
如果没有官与民的区分,由于官与民的不同,官优于民,官大于民,必然是官高于民,官侵害民,甚至有官无民,而没有民就没有民法。
在历史上,妨碍民法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官民不分,以官代民,官本民末,民不自立。
因此,要发展民法,根本前提是民区分于官,民独立于官,以民为本,民可自治。
民法作为“民”之法,一切都因“民”而来,抓住了“民”,才能抓住民法的根本,理解了“民”才能真正理解民法,不理解“民”就不理解民法。
所以,在民法中必须要有民本意识,民法思想仅仅停留在人的阶段或高喊“以人为本”是不够的,还要实现从人到民的进化。
近代民法如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的产生,是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然,是市场化、城市化使然,“民”已经在向市民方向发展,其中一部分民已经发展成为市民。
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存在社会分工和社会交易,存在独立的商品携带者,存在自由的交易主体;
同时,资本主义得以存在,也需要摆脱官僚支配的资本家和独立的雇佣劳动者,需要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以上都从经济基础上促进了官与民的分立。
政府对民众的统治方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文明化、自由化了,民众开始独立于政府,可以意思自治了。
这不仅减轻了政府管理的负担,而且有利于政府的统治。
孟德斯鸠在考察贸易史后认为:
“人们开始医治马基雅弗里主义,并一天天好起来。
劝说诘戒时,要更加适中温厚了,过去所谓的政治的妙计在今天除了产生恐怖而外,只是轻举妄动而已。
”[6]市场贸易使政府越来越予民独立、自治,民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市场贸易也促使民众独立自治,在很大程度上,民众的独立、自治能力是在市场贸易中练就和习得的。
亚当.斯密认为:
“一般来说,从商业和制造业所赚的工资,比从任何其他方面赚得的工资高,结果人们就变得更诚实。
人们如有可能从正当的、勤劳的途径赚得更好的衣食,谁愿意冒险干拦路抢劫等勾当呢?
”[7]市场贸易使民众勤劳、富裕、诚实、自立和文明,这正是民法所需要的民,是民法的基础。
所以,是市场交易真正造就了合格的民——市民,一个能够独立于官、自治于己的市民,在市民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市民法。
所以,过去把民法叫做市民法是合理而准确的。
而资本主义国家与时俱进,通过制定民法典对市场经济予以进一步的制度化确认。
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民众的主体地位日益明确。
文艺复兴打破了神话思维,人们由关注外在于人的神灵转而关注自己本人,神灵并不能使人幸福,人也不祈求天国的幸福,而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即使是凡人的幸福也不能诉诸神灵而只能依靠自己,自己是其幸福与否的终极决定者。
宗教改革打破了教皇、教士和教会对教义的垄断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对话,也有能力与上帝单独交流,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是人平等的重要基础。
启蒙运动是祛除愚昧,特别是祛除各种形形色色的愚民政策,它启发理性、尊重理性、运用理性,认为人人皆有理性,能够理性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为己操心,替己理事。
所有这些归结起来,就充分地奠定了“民”的主体地位。
民事行为的正当性,不再像过去那样由社会权威
来裁判,这些社会权威曾分别是家长、教士和君主,而现在是民自己,民的独立、平等、理性和自由,使民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体,也可以成为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担当者,一个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归根结底由其自由意志和外在行为来决定。
这样,人就从对上帝、家长和君主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了。
民主体化了以后才会有民法。
有了主体化的民以后,民与民之间、民众之间自然会形成一个共同体,即民间社会。
在这个共同体中,会形成一套民间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交往规则,这正是民法的渊源,也是民法异质于公法的根源。
民间社会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协商性和民约性,它区别于政治社会和政治权力,与之划清了界线,并且与政治社会、政治权力分庭抗礼,有力地制约了政治权力对民间社会的介入、干涉和侵犯,以及政治社会对民间社会的僭越、扭曲和侵吞,它坚定而自信地告诫政府和官僚,民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为自己谋利、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需要他们指手画脚、包办代替。
《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正是民法得以运行的社会基础,也是社会民主自由的基础。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只有“民”才是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也只有当“民”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时,才是一个民本、民主的社会,也才是一个正常、正当的社会。
全民皆“民”是最理想的社会,也是民法所追求的最好社会。
“民”是人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