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P认证现场检查与药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监督协同性的思考Word下载.docx
《GMP认证现场检查与药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监督协同性的思考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GMP认证现场检查与药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监督协同性的思考Word下载.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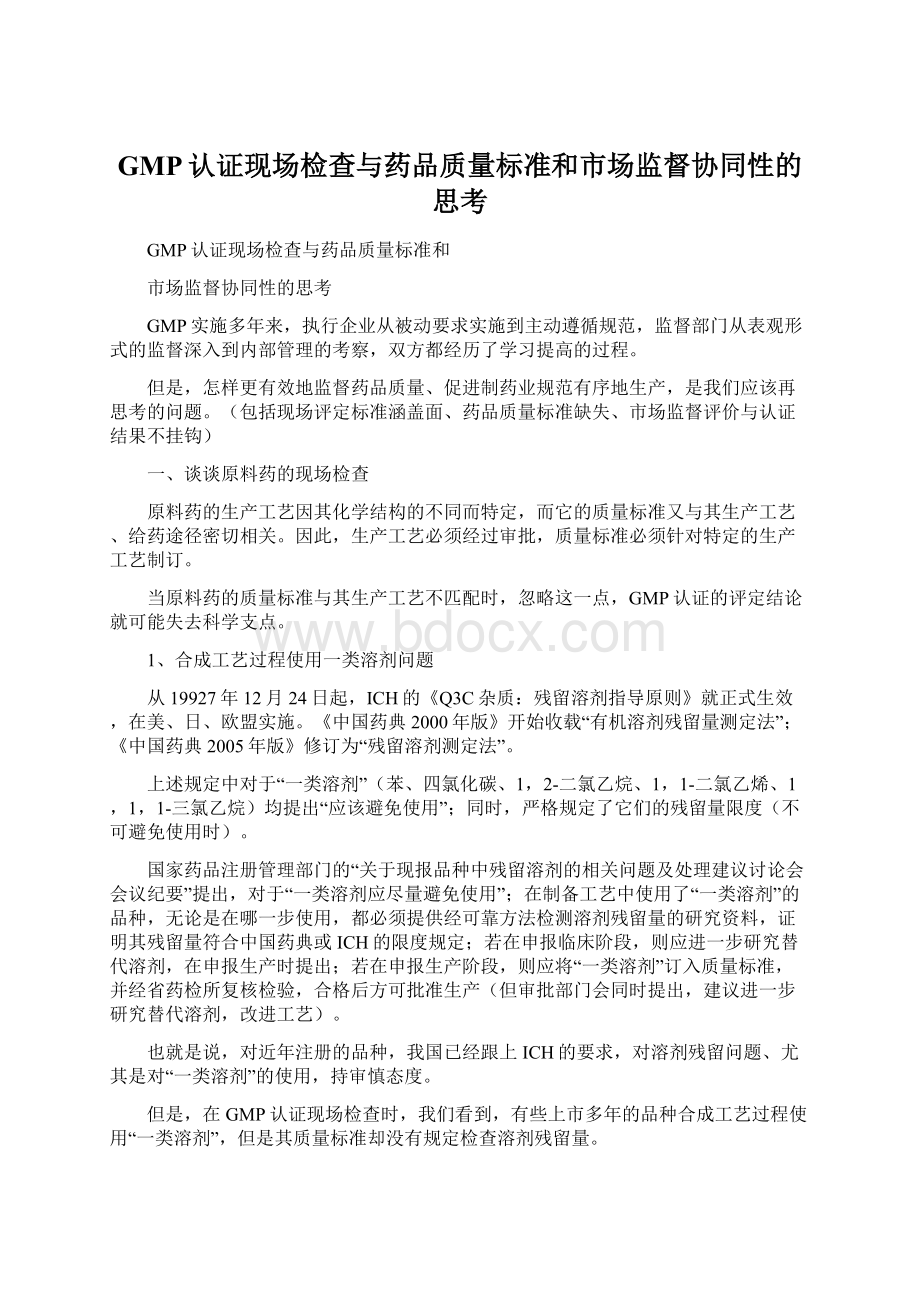
残留溶剂指导原则》就正式生效,在美、日、欧盟实施。
《中国药典2000年版》开始收载“有机溶剂残留量测定法”;
《中国药典2005年版》修订为“残留溶剂测定法”。
上述规定中对于“一类溶剂”(苯、四氯化碳、1,2-二氯乙烷、1,1-二氯乙烯、1,1,1-三氯乙烷)均提出“应该避免使用”;
同时,严格规定了它们的残留量限度(不可避免使用时)。
国家药品注册管理部门的“关于现报品种中残留溶剂的相关问题及处理建议讨论会会议纪要”提出,对于“一类溶剂应尽量避免使用”;
在制备工艺中使用了“一类溶剂”的品种,无论是在哪一步使用,都必须提供经可靠方法检测溶剂残留量的研究资料,证明其残留量符合中国药典或ICH的限度规定;
若在申报临床阶段,则应进一步研究替代溶剂,在申报生产时提出;
若在申报生产阶段,则应将“一类溶剂”订入质量标准,并经省药检所复核检验,合格后方可批准生产(但审批部门会同时提出,建议进一步研究替代溶剂,改进工艺)。
也就是说,对近年注册的品种,我国已经跟上ICH的要求,对溶剂残留问题、尤其是对“一类溶剂”的使用,持审慎态度。
但是,在GMP认证现场检查时,我们看到,有些上市多年的品种合成工艺过程使用“一类溶剂”,但是其质量标准却没有规定检查溶剂残留量。
例如,《中国药典》收载的品种“桂利嗪”(血管扩张药),现场检查发现合成时使用强致癌物“苯”,属于“一类溶剂”,但是其质量标准中没有规定“苯”的残留量检测。
这是“药品质量标准缺失”的突出例子。
严格地说,该品种的质量标准已经不足于监控药品的安全性,而安全性却是我们监管部门追求的最起码要求。
问题是,象这样的品种,GMP认证现场检查,即使发现存在“质量标准关键项目缺失”,又能怎么办?
不通过认证?
那怎样评定?
照样通过认证?
那么这样执行“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是不是忽略了“安全有效”这个宗旨?
2、改变起始原料问题
随着化工产业的兴旺,药物合成的部分工序(尤其是多步反应品种)被转移到化工厂,其结果是,在原料药厂缩短了合成路线、减少了硬件投入和减排压力。
但是,对于监管部门而言,看到这些实际上“改变了原料药合成起始原料”的动作,应该做何反应?
默认?
允许?
还是不允许?
如果允许,那么前期(中间体)合成的工艺如何保证按照经批准的工艺进行?
怎样监督?
如果对原料药前期合成的工艺不关注,那么最后的药品质量保证怎样落到实处(工艺改变了质量标准不变则形同虚设)?
3、改变化合物纯化、结晶的溶媒问题
有些上市多年的品种,原料药生产厂家或者为了提高收得率、或者为了提高临床疗效(改变晶型)等原因,改变了原料药的纯化工艺、或改变了重结晶的溶媒。
但是,这些改变,厂家不申报,监管部门不关注,最后就直接影响制剂的安全性。
假如在制剂监测时发现,扳子打在制剂厂家,人家还不服。
例如,阿奇霉素,厂家申报的质量标准中规定监测残留溶剂是“乙醇”,而实际用于最后析晶工序的溶媒是“丙酮”,结果药检所按照质量标准检验“乙醇”,必然是“符合规定”,但其“丙酮残留量”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此,即使原料药的合成路线没有改变,最后改变了重结晶的溶媒,也不能忽视。
二、药物制剂的认证
1、原料药等级问题
注射剂的原料药必须符合其制剂的质量要求。
但是,这些年来,有不少品种由于其原料药的国家标准没有注射级(用)的,而注册审批部门照样批准其注射剂的生产,结果造成厂家们使用口服级原料药生产注射剂。
虽然这当中一些厂家申报了原料药“精制工艺”(自制成注射用级)、以内控标准控制精制后原料药的质量,但我们发现许多厂家实际生产时没有经过原料药精制,就直接投入注射剂的生产。
典型的品种是“注射用盐酸克林霉素”、“注射用阿奇霉素”等。
现场检查时我们曾提问这个“精制”问题,有的厂家声称制剂生产过程的“活性炭吸附”,就是等同于“精制”。
显然,这是混淆视听、偷梁换柱的陈词。
我们知道,药品制剂生产过程使用“药用炭”目的主要是脱色、除去热原;
而原料药的“精制”工序,通常是利用合成目标物在两相(溶媒)中溶解度不同或目标物在某种溶剂中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有明显差异进行的重结晶,在此过程除去水溶性杂质、脂溶性杂质,同时,去除水分和残留有机溶剂,收集目标物的理想晶型。
因此,制剂生产过程“活性炭吸附”根本不能等同于“原料药的精制”。
另外,还有些原料药虽收载于国家标准,但不是“无菌粉”,而注射用粉针剂却需要该原料药的无菌粉,结果又是有“料”却没有国家标准。
例如“碳酸氢钠”。
问题是,认证现场检查,发现这些问题如何定论?
如何认定这些原料药的合法性?
对没有国家标准、没有文号的品种却允许其生产(精制),怎样实施监督?
怎样保证质量可控?
2、注射用粉复方制剂工艺的无菌混粉问题
对于注射用粉复方制剂而言,工艺过程有个“混粉”工序。
众所周知,这个“混粉”工序必须保证无菌,因为是2种无菌粉的混合,之后是无菌分装制成注射用粉复方针剂。
现在的普遍情况是,由于无菌粉混合工艺要求较高(环境和设备),制剂厂家干脆买进“混粉”。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混粉”(原料药混合体)没有国家标准、没有批准文号,假如我们可以忽略“混粉”的质量标准问题(参照成品制剂标准控制),那么允许原料药厂家生产和出售它没有批准文号的“混粉品种”,是不是与法规相悖呢?
甚至有的原料药厂家只能生产“混粉”中的一种原料药,却另外买入另一种原料药,专门生产“混粉”,供应制剂厂家。
我认为,此种情况应该不仅质疑它的质量可靠性,还要质疑它的生产及销售的合法性。
国家局2006年9月“国食药监安2006-514号”文(关于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原料药混合粉有关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使用该原料药混合粉的制剂生产企业,应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应提出变更申请……。
这个文件给出的信息是,东瑞虽然只有混粉中两种原料药各自的文号,但它可以生产并出售这两种原料药混合粉(即混粉不需要文号,混粉也不需要有国家标准)。
另一方面,这个文件没有明确,所谓“制剂生产厂家应提出变更申请”,是申请变更生产工艺,还是申请变更原料药来源?
按照现行法规,前者的批准部门是国家局,后者的批准部门是省局。
或可以认为,对于制剂厂家,省略了“混粉”过程,只做“无菌分装”,在线工艺过程是不同了。
对不对?
若认为对,则需申报改变工艺。
已上市的注射用复方粉针剂并不只有“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一个品种。
因此,我们应当还要关注其他类似品种。
3、剂型相同但给药途径不同的药品安全性问题
在以往的认证现场检查中,我们比较注意的是整个生产线的状况,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同一条生产线上的不同品种由于给药途径的不同,安全性的要求会不同;
但这时药品质量标准的常规监控一般无法及时发现问题;
而“清洗验证”往往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现场检查时我们时而看到,在同一条生产线生产的、同样是注射剂,但是,有的是“仅供肌内注射”、有的是“静脉注射”,而无论是生产厂家、还是我们的某些检查员都忽略了“给药途径不同”这个关键点。
这是一个明显的安全隐患。
上海华联制药厂的“注射用甲氨喋呤”、“注射用阿糖胞苷”、“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都是抗肿瘤药,在同一车间生产,给药途径都有“静脉注射”。
容易被忽略的是:
“注射用甲氨喋呤”、“注射用阿糖胞苷”既可以“静脉注射”也可以“鞘内注射”;
而“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虽然可以“静脉注射”却因其周围神经系统毒性大而“仅用于静脉注射”。
这起由于不同给药途径的2种药物交叉污染导致的严重药害事件,应该给我们每一个检查员、给我们监管部门敲响警钟,提醒我们高度关注类似的药品生产状况,提醒我们高度关注类似生产线上的微量残留、甚至痕量残留药物导致的安全性风险的评估。
这样的品种,建议考虑,应该避免使用同一设备接触药物,以保证安全性。
尤其是,我们的药品质量标准、GMP认证评定标准中对这种安全隐患都没有明确的限制项目。
所以,必须在生产设备硬件上消除交叉污染的机会。
三、辅料问题与内包材问题
1、辅料问题
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
《中国药典2005年版二部》专门收载了73种药用辅料,并在凡例中规定的“制剂中使用的原料药和辅料,均应符合本版药典的规定,本版药典未收载者,必须制定符合药用要求的标准,并需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但是,由于目前还有许多辅料尚未纳入批准文号管理,以致于药典的上述规定往往无法得以落实。
甚至,有的辅料虽然我们监管部门已经纳入批准文号管理,而它同时可用于食品行业,因此不少药品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就购买食品级的辅料,放弃选用价格高的药用级辅料。
例如,乳糖、蔗糖等。
现场检查时我们还发现,有的品种使用国家药典已经收载的辅料“十二烷基硫酸钠”,是上海牙膏厂生产。
还有,与上述原料药等级问题类似的是,已上市的注射剂中也存在使用非注射用级辅料的问题。
例如,冻干注射剂使用口服辅料作为冻干支架,这也是与《中国药典》的规定不符的,存在明显的安全隐患。
尤其不能忽略的是,作为冻干支架的辅料的处方用量往往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主药,因此,辅料的安全性明显影响制剂安全性。
《中国药典2005年版二部》中的药用辅料标明“供注射用”的,只有“甘油”。
2、内包材管理问题
国家局自2002年以来分期分批组织制定发布了113项药包材标准,又于2006年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包材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国食药注2006-306号),提出“特别要加强监督用于注射剂的药包材(如塑料输液瓶、多层共挤膜输液袋、药用丁基胶塞等)”。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与药品原料药的质量标准相比,药(内)包材的质量标准和管理要求比较低,而药(内)包材处方组成又相当复杂。
内包材的质量控制缺位的话,同样严重影响药品质量。
例如,中检所胡昌勤主任等的研究报告指出,“药用丁基胶塞中检出21种挥发性成分”,这些组分若是未被完全化学键合的反应剩余物,经制剂生产过程的清洗、灭菌,就可能迁移到胶塞表面,造成药粉(液)的污染(抗生素注射用粉针剂多个品种的澄清度问题就是证明)。
再有,药包材(主要指注射剂的内包材)的生产批号的确定也还比较随意,不能符合“药品制剂质量溯源”的需要。
我们在现场检查时发现,药用玻瓶的生产批号(或称编码)各式各样,多是与生产时间没有明显相关,制剂厂家经常把同时进货的玻瓶作为一批。
但是,这样的“抽样检验”结果有多少科学性?
样本的代表性科学吗?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问题。
四、与市场监督的协同之必要
国家监管部门对药品流通领域的监督常用方法是“评价性抽验”和“日常监督抽验”,国家抽验计划由省级以上药检所承担检验任务,检出不合格的品种就列入国家药品质量公报,定期公布。
GMP认证现场检查要求的是生产线在动态下实施检查,以往关注较多的是厂内管理状态。
但是,我们的GMP认证与国家药品公报所公示的药品质量信息似乎没有协同性。
我们发现,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认证现场检查某厂评定结论为“通过”后不久(不足一月),国家药品质量公报上就公示其产品抽验不合格,可是这个企业却照样被认定通过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