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忆谈林徽因的《记忆》与李商隐的《锦瑟》二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此情可待成追忆谈林徽因的《记忆》与李商隐的《锦瑟》二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此情可待成追忆谈林徽因的《记忆》与李商隐的《锦瑟》二诗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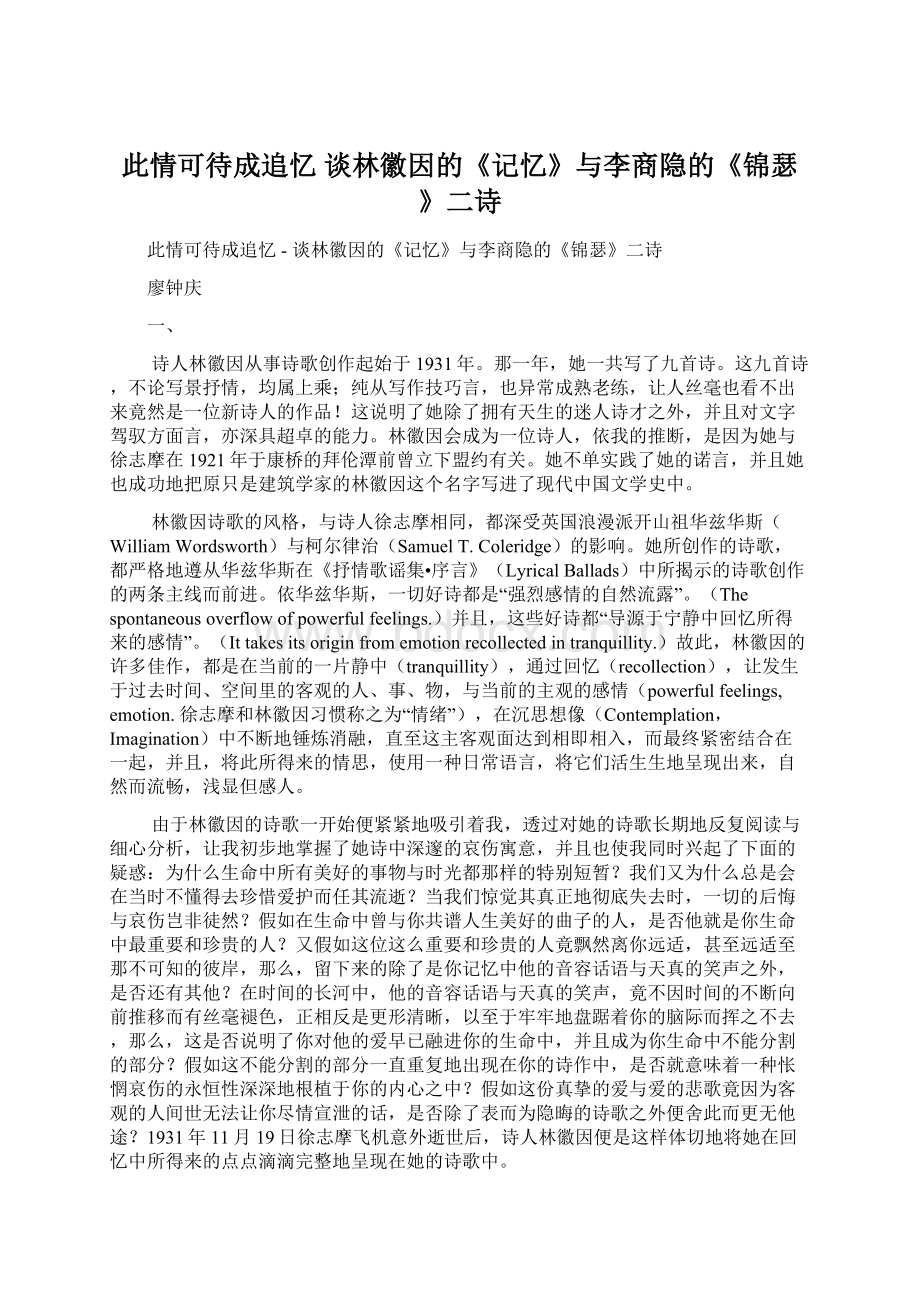
她不单实践了她的诺言,并且她也成功地把原只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这个名字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中。
林徽因诗歌的风格,与诗人徐志摩相同,都深受英国浪漫派开山祖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与柯尔律治(SamuelT.Coleridge)的影响。
她所创作的诗歌,都严格地遵从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LyricalBallads)中所揭示的诗歌创作的两条主线而前进。
依华兹华斯,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Thespontaneousoverflowofpowerfulfeelings.)并且,这些好诗都“导源于宁静中回忆所得来的感情”。
(Ittakesitsoriginfromemotionrecollectedintranquillity.)故此,林徽因的许多佳作,都是在当前的一片静中(tranquillity),通过回忆(recollection),让发生于过去时间、空间里的客观的人、事、物,与当前的主观的感情(powerfulfeelings,emotion.徐志摩和林徽因习惯称之为“情绪”),在沉思想像(Contemplation,Imagination)中不断地锤炼消融,直至这主客观面达到相即相入,而最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将此所得来的情思,使用一种日常语言,将它们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自然而流畅,浅显但感人。
由于林徽因的诗歌一开始便紧紧地吸引着我,透过对她的诗歌长期地反复阅读与细心分析,让我初步地掌握了她诗中深邃的哀伤寓意,并且也使我同时兴起了下面的疑惑:
为什么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与时光都那样的特别短暂?
我们又为什么总是会在当时不懂得去珍惜爱护而任其流逝?
当我们惊觉其真正地彻底失去时,一切的后悔与哀伤岂非徒然?
假如在生命中曾与你共谱人生美好的曲子的人,是否他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和珍贵的人?
又假如这位这么重要和珍贵的人竟飘然离你远适,甚至远适至那不可知的彼岸,那么,留下来的除了是你记忆中他的音容话语与天真的笑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
在时间的长河中,他的音容话语与天真的笑声,竟不因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而有丝毫褪色,正相反是更形清晰,以至于牢牢地盘踞着你的脑际而挥之不去,那么,这是否说明了你对他的爱早已融进你的生命中,并且成为你生命中不能分割的部分?
假如这不能分割的部分一直重复地出现在你的诗作中,是否就意味着一种怅惘哀伤的永恒性深深地根植于你的内心之中?
假如这份真挚的爱与爱的悲歌竟因为客观的人间世无法让你尽情宣泄的话,是否除了表而为隐晦的诗歌之外便舍此而更无他途?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飞机意外逝世后,诗人林徽因便是这样体切地将她在回忆中所得来的点点滴滴完整地呈现在她的诗歌中。
无独有偶,在1931年的一千零八十年之前,唐宣宗大中五年(西元851年),诗人李商隐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逝世,这位与他结发十四年的妻子王晏媄,再也不能尽力地给予他为事业而奋斗的精神上继续支持而离他远适,远适至更隔蓬山一万重还要更遥远的彼岸!
从851年到李商隐逝世的858年这八年之中,是否李商隐就与现代诗人林徽因一样,只是异时异地但境遇完全相同的两个孤独哀伤的诗魂?
李商隐留下来的许多无解的隐晦无题诗与准无题诗究竟能否找到一丝可理解的线索?
1936年2月林徽因写出了她的《记忆》一诗,这首诗究竟与李商隐逝世前所写的《锦瑟》一诗是否有某些神秘的关联?
时间跨越了整整超过一千年以上的这两首诗,是否不约而同地共同彰显了人性中的普遍性与其绝对的孤独与悲伤?
在诠释这两首诗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这两首好诗。
《记忆》
林徽因
断续的曲子,最美或最温柔的
夜,带着一天的星。
记忆的梗上,谁不有
两三朵娉婷,披着情绪的花
无名的展开
野荷的香馥,
每一瓣静处的月明。
湖上风吹过,头发乱了,或是
水面皱起象鱼鳞的锦。
四面里的辽阔,如同梦
荡漾着中心彷徨的过往
不着痕迹,谁都
认识那图画,
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
《锦瑟》
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二、《记忆》一诗写于1936年2月。
这是一首歌颂自然的诗歌,充分地透显出人与自然圆融地相即相入的和谐性。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述,诗人林徽因的许多佳作,都是在当前的一片静中(tranquillity),通过回忆(recollection),让发生于过去时间、空间里的客观的人、事、物,与当前的主观的感情(powerfulfeelings,emotion徐志摩和林徽因习惯称之为“情绪”),在沉思想像中不断地锤炼消融,直至这主客观面达到相即相入,而最终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将此所得来的情思,使用一种日常语言,将它们活生生地呈现出来,自然而流畅,浅显但感人。
这首《记忆》一诗是她所有诗作里最明确表达出,她就是紧依着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所揭示的诗歌创作的两条主线而前进!
诗中明确地点出“回忆”(recollection)、“情绪”(emotion)和“静”(tranquillity),而出现在诗中的“曲子”、“夜”、“星”、“花”、“野荷”、“月明”、“湖”、“头发”、“水面”、“鱼鳞的锦”、“梦”、“痕迹”、“图画”、“水底”、“倒影”等意象与景象莫非都是我们经常使用到和接触到的,为什么这些如此浅显的语言与如此熟稔的自然景致会让我们直接就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清新与惊羡?
英国浪漫派诗歌另一位开山祖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Literaria)一书的第14章里,对他与华兹华斯当初相交的第一年,如何热切地讨论浪漫派诗歌的基本课题与创作的分工,作出了详尽的追述,他说:
在华兹华斯先生与我成为邻居的第一年间,我们的谈论,常常交集在诗歌的两个基本课题上,那就是:
藉着一种对自然之真理的坚决忠诚,以激起读者的同情的力量;
与藉着对想象力之缤纷的修饰,以促成对新奇产生兴致的感觉的力量。
突然变化的光与影,或来自月光,或来自夕阳,散发在已知与熟稔的景致上,这种偶现的迷人魅力,似乎正表示着两者之间之结合的实用性。
这些都是自然的诗歌。
……《抒情歌谣集》的计划,便源于这种观点。
在这本诗集中,我们彼此同意,我致力于集中在人物与角色的超自然上,或者说,这至少也是浪漫的;
不过,尚须从我们的内在的本性中,移植出人性的情趣,与真理的投影,从而为想象力所形构的这些影像,充分获致当前的怀疑态度之自愿搁置,这便形成了诗意的信仰(poeticfaith)。
另一方面,华兹华斯先生的创作目标是:
从习焉不察的昏慵中,以唤醒心灵的注意力,并将这心灵的注意力导向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之美好与惊羡,从而给与日常的事物一种新奇的迷人魅力,并激起一种类似于超自然的情思。
(注1)
明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诗人徐志摩与诗人林徽因在中国开创的就是中国浪漫派诗歌,与英国浪漫派诗歌一脉相承!
都是以歌颂自然为主的抒情诗歌。
但是,我们仍然好奇,究竟林徽因诗里说的“湖”是什么地方?
她在诗中最后一个诗行“沉在水底记忆的倒影!
”这一哀叹的实指为何?
让我们诵读一下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的“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便能对照出来,林徽因哀叹的就是她与徐志摩当年的盟约之毁弃,以至于原先的美梦之破碎,并且这个美梦之永恒地沉淀在拜伦潭潭底的悲伤!
(注2)所以,她在诗里所说的“湖”就是拜伦潭!
林徽因《记忆》这一首诗写于1936年2月,它的写作时间距离徐志摩的逝世已五年多,距离她到剑桥访问已经整整十五年!
这首诗,就是如此地在当前的一片“静”中,透过“回忆”、“想象”,一下子便回到那时空睽隔的康桥与康桥的拜伦潭。
“断续的曲子”,是不是就是徐志摩在《再会吧康桥》一诗中所说的“自然音乐”?
在该诗中,徐志摩自述他之所以能接触到这种“音乐”以及睁开双眼窥探文艺学术的殿堂,是因为:
“不昧的明星,赖你和悦宁静/的环境,和圣洁欢乐的光阴,/我心我智,方始经爬梳洗涤,/灵苗随春草怒生,沐日月光辉,/听自然音乐,哺啜古今不朽,/”。
假如徐志摩从未到过康桥学习,是否他心灵的耳朵将无法聆听到康桥这美妙的自然音乐?
又假如林徽因从未伴随徐志摩来到过康桥的拜伦潭,是否这种具体美妙的自然音乐对她来说只能算是空洞的抽象音符而无实质意义?
她,不只去了,也听到了,在一个宁静的朗月月色下,在一个繁星满天的点点光辉中,在一个最美最温柔的夜里。
是否只要你不沾滞丝屑的俗念,是否只要你审美的本能未曾泯灭,是否只要你仍保有那完全诗意的信仰,那么,披着情绪的花(诗本身!
)便会长在记忆的梗上?
那么,诗人林徽因问:
在记忆中,谁不有两三朵如此娉婷的花?
事实上真的这样简单吗?
我们都知道,诗歌宜雅忌俗,俗念绝不可能化为美好的诗行,而生活忙碌的人,常常在指顾之间泯灭其审美的本能,试问又如何能把那种一闪而过的诗歌意念化为缤纷的诗行?
更何况现实人生里,谁又能长期地坚持诗意的信仰?
那么,这样说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闪现在记忆的梗上之诗歌意念让它真实地化为朵朵鲜花(指诗)是明显不过的。
这些歌颂自然与人性的五彩缤纷的诗行,正像瓣瓣荷花在明月的静夜里无名的展开並且散发出迷人的香馥一样。
但是,这毕竟只是少数的专业诗人才能真正做得到,而诗人林徽因所说的“谁不有”云云,也许视作她对我们的鼓舞激励可能更加恰当吧!
让我们重新回到拜伦潭。
正如我在诠释林徽因的《藤花前》与徐志摩《偶然》二诗时已经指出,“云”是林徽因,“水”是徐志摩。
天空中的云,自在轻盈明艳,她随着风到处飘荡,不经意地与地面上的水偶尔相遇,这短暂的交会,于是便形成了倒影。
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一诗中所说的“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正是这种投影关系。
那发生在转瞬间的交会,具体地言,就是一见钟情。
林徽因在这首诗里,把这种投影关系轻轻地化约为“湖”(水)、风、与“头发”(她自己)的关系,而“水面皱起象鱼鳞的锦”,正是指在徐志摩“心头荡漾”着的“波光里的艳影”的这种投影现象。
拜伦潭的水面,皱起了象织锦般美的鳞漾,伴随着康桥的天籁,在这最温柔、最美的月夜里,星光下,向着四面扩散,寂静辽阔,漫无边际,在诗人林徽因的脑海中回忆里渐次消逝,如静夜中之夜曲的fadedout,最后是似有还无,不着痕迹。
当年一对年青人的盟誓,所追求的“敬仰,希望与爱”这一单纯信仰的理想,(“WelivebyAdmiration,HopeandLove.”见华兹华斯《远游》一诗WilliamWordsworth,TheExcursion,1814,BookIV)如诗如梦,如梦如诗。
他们不经意地深陷情网,陶醉于初恋的甜美中,他们向往百年多前两位英国浪漫派的创始者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所创作的诗歌,他们更希望能出版一本诗歌合集–中文版的“抒情歌谣集”!
但是,这个“创作诗歌”与“落实感情”的美梦最后竟因为盟约的崩解,誓言的毁弃而彻底地破灭。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是徐志摩在1928年初秋重访剑桥这伤心地时的话,而对林徽因来说,那一个彩虹似的梦,只是永远处在她人生旅途的过往的中间之记忆里,美丽而遥远。
这个仿佛彷徨荡漾在拜伦潭如诗一样的梦,以及这个沉在拜伦潭潭底下破碎的梦,最后只演变成为一幅永恒的图画,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首度揭橥,在林徽因的《记忆》这首诗里再被重提,尤其在林诗中,以一个感叹号来结束全诗,更显示出人生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