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家笔下陶渊明形象的常与变.docx
《中古史家笔下陶渊明形象的常与变.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古史家笔下陶渊明形象的常与变.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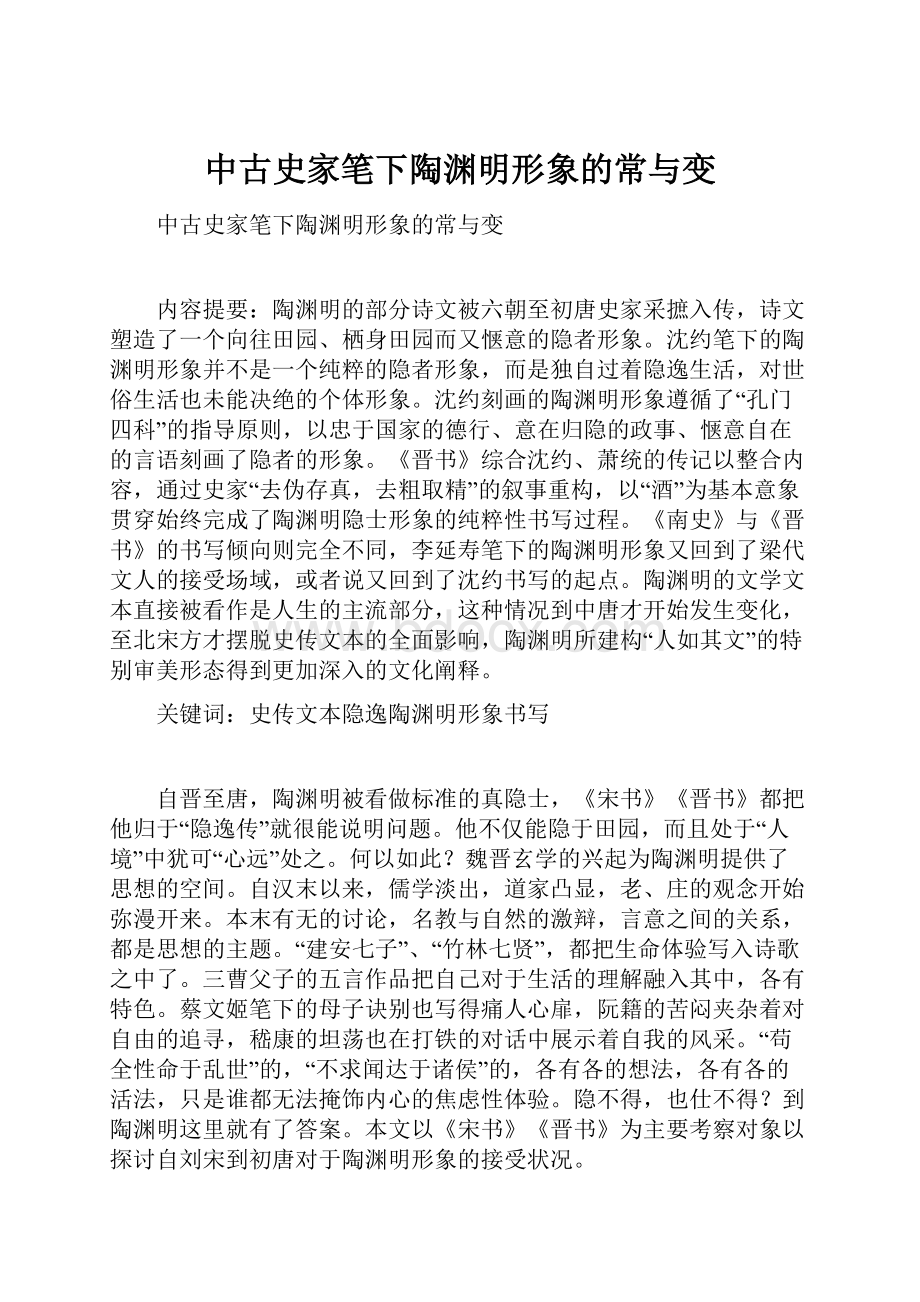
中古史家笔下陶渊明形象的常与变
中古史家笔下陶渊明形象的常与变
内容提要:
陶渊明的部分诗文被六朝至初唐史家采摭入传,诗文塑造了一个向往田园、栖身田园而又惬意的隐者形象。
沈约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隐者形象,而是独自过着隐逸生活,对世俗生活也未能决绝的个体形象。
沈约刻画的陶渊明形象遵循了“孔门四科”的指导原则,以忠于国家的德行、意在归隐的政事、惬意自在的言语刻画了隐者的形象。
《晋书》综合沈约、萧统的传记以整合内容,通过史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叙事重构,以“酒”为基本意象贯穿始终完成了陶渊明隐士形象的纯粹性书写过程。
《南史》与《晋书》的书写倾向则完全不同,李延寿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又回到了梁代文人的接受场域,或者说又回到了沈约书写的起点。
陶渊明的文学文本直接被看作是人生的主流部分,这种情况到中唐才开始发生变化,至北宋方才摆脱史传文本的全面影响,陶渊明所建构“人如其文”的特别审美形态得到更加深入的文化阐释。
关键词:
史传文本隐逸陶渊明形象书写
自晋至唐,陶渊明被看做标准的真隐士,《宋书》《晋书》都把他归于“隐逸传”就很能说明问题。
他不仅能隐于田园,而且处于“人境”中犹可“心远”处之。
何以如此?
魏晋玄学的兴起为陶渊明提供了思想的空间。
自汉末以来,儒学淡出,道家凸显,老、庄的观念开始弥漫开来。
本末有无的讨论,名教与自然的激辩,言意之间的关系,都是思想的主题。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都把生命体验写入诗歌之中了。
三曹父子的五言作品把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融入其中,各有特色。
蔡文姬笔下的母子诀别也写得痛人心扉,阮籍的苦闷夹杂着对自由的追寻,嵇康的坦荡也在打铁的对话中展示着自我的风采。
“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活法,只是谁都无法掩饰内心的焦虑性体验。
隐不得,也仕不得?
到陶渊明这里就有了答案。
本文以《宋书》《晋书》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探讨自刘宋到初唐对于陶渊明形象的接受状况。
一、陶渊明的自我形象书写
对于陶渊明的理解,大家往往突出他隐逸的一面,古今都有不一致的时候。
鲁迅就认为陶渊明也“并非浑身静穆”,可是也不会是一个汲汲于富贵功名的人。
冈村繁有本著作《陶渊明新论》就认为陶渊明有以安贫的姿态扬名之心理,他突出了陶渊明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对世俗名声的追求欲望”[1]。
冈村繁反其道而行之的研究方式虽然刻意挖掘资料来追求新意,确实存有因对中国文化理解不深而造成的误解。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人与自然同在,神与物游的审美主潮,回归田园是很正常而又极不寻常的选择。
陶渊明经历了从入仕到出世的过程,“尘网”里的很多事务让他苦不堪言,“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这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
”[2]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于是终于“羁鸟返旧林,池鱼思故渊”。
《归去来兮》就是他的表白,这篇文章屡屡被史家采摭入传正说明其已成为陶渊明形象书写的组成部分。
文曰: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携幼入室,有酒盈罇。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因“耕植不足以自给”采取解决生计问题,“遂见用于小邑”,在彭泽饮酒赋诗的生活也没能遏制“眷然有归与之情”,“质性自然”的陶渊明又逢程氏妹的死,于是“去职”了。
《归去来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
迷途知返是陶渊明对自己所选择生活的认识,于是,快乐感油然而生。
“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
”如此的惬意;“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何等的温暖;“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自然也养神。
山水清音,自然使日常生活染上了诗意。
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他接着写道: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乎西畴。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
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不必说肯定是惬意的,也是最简单质朴的生活。
正是这样水流花放的大自然消解了误落尘网的伤神,生活的自在程度是不能以贫富贵贱来相论的,安贫乐道是很高的境界。
《五柳先生传》活画了一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世外高人形象。
不知何许人,也不详其姓字,实在是没啥可束缚自己的了。
不经意的放眼一看,宅边有五棵柳树,就叫自己五柳先生吧。
这位先生不爱说话,不慕名利,爱读书也不求深意,读高兴了,连吃饭都忘了。
爱喝酒,家穷有时候喝不起,亲旧就招待他,一喝就醉,醉了就走。
家徒四壁,穿用简单,经常写写文章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陶渊明把自己写成这样一个人,一个“忘怀得失”,自娱自乐的人。
这样的人才会想出世间会有桃花源,不是谁都能找到的,只有“心远地自偏”的高人才能找到“真意”。
从这个角度来说,陶渊明的文字是以明隐逸之志为主,算不上审美文本。
因之钟嵘《诗品》中将他列为中品,并说他是“古今隐逸之宗也”。
自刘宋至唐代,史家采摭此文入传也正在于《五柳先生传》成为陶渊明隐者形象的主体内容。
陶渊明说: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杂诗》),他没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焦虑感,珍惜时光是要过自己选择的生活,尽管这样的生活时常不免孤独和寂寞,让他觉得“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读书的时候,也会写出“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读山海经》)这样的句子。
人生有限,陶渊明非常关注死亡现象,他给自己写了《自祭文》,还写了三首《拟挽歌辞》,他想象自己离世的情景: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
鸿雁于征,草木黄落。
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
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
于是,“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可惜从此不能尽兴喝酒了,面对祭拜的情景,“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这是谁也不能改变的命运。
《拟挽歌辞》的第三首是对送别和别后的描写: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诗人把目光放在了送葬的场面上,凄凉的布景,大家的反应,自己的淡然都写出来了。
鲁迅的《孤独者》、萧红的《呼兰河传》也很善于写这样的场面,在这一点上,叙事文本与抒情文本异曲同工。
英国诗人史蒂文森有一首《安魂曲》:
“在这寥廓的星空下面/掘一座坟墓让我安眠/我活得快乐,死也无怨/躺下的时候,心甘情愿//请把下面的诗句给我刻上/他躺在自己的心之向往的地方/好像水手离开大海归故乡/又像猎人下山回到了家园。
”中英诗歌同样书写生死主题,同样寄托了人与物游的情思。
擅长写这类作品的诗人为数不少,中国的陆机、鲍照、傅玄,俄罗斯的普希金、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这样的作品。
生乐于隐,死安于隐,陶渊明在诗文中塑造了一个向往田园、栖身田园而又惬意的隐者形象。
通观这类作品,自然让阅读者认定其生活在“隐逸”的范畴之中。
生活图景往往取代了诗歌书写者的身份。
在隐者与诗人之间,陶渊明的隐者身份更容易被接受,而他所生活的时代,诗人是需要在词语和措意这两个方面都要具备审美的价值。
所以他在文学创作上并未显示出超人的一面,他在叙事性诗文中的自我书写更容易被读者接受,文本里面隐含的人生出处的向往符合怀才不遇者的共通元素。
总而言之,陶渊明本人的诗文中已经具有自传的性质,正因如此川合康三在所撰《中国的自传文学》中就以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为中心讨论以陶渊明、王绩、白居易所形成的自我书写谱系。
刘宋时代,颜延之有《陶征士誄》一文,“序”中描绘了陶渊明“道不偶物,弃官从好”的选择过程,从此过着“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的隐逸生活。
陶渊明的隐者身份至此已定。
鲍照《学陶彭泽体》虽开效陶诗之先河,其诗在意而不在文,定位在“但使樽酒满,朋旧数相过”的隐趣之中。
两位同朝代诗人的作品给陶渊明身份定了主基调,即他的诗是隐逸生活的直接反映。
可见,《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拟挽歌辞》等文本成为陶渊明自我认定的经典文本,同样也得到了史家的认可,这些文字重在隐逸,确认了陶渊明的隐者身份。
相对于文学家身份而言,这要直接得多,而对文学家身份的确认需要时代、环境、文化等因素发生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作品构成了史家将陶渊明入传的前提条件。
二、《宋书》中的陶渊明形象
一览史传文本,陶渊明竟然都是归入“隐逸”之中,尽管传记文本也列了他的作品,基本不离《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归去来辞》这三篇。
隐士身份的陶渊明压倒了文学家的陶渊明,直到苏东坡,才开始改变。
陶诗的朴素和精致是两位一体的,因其朴素而在当时声名不显,因其精致而在身后名声大噪。
追求华彩的社会,朴素便被淹没了,也过于奢侈。
史家入传带有盖棺论定的意味,史家如何将笔下的人物合理归类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沈约对陶渊明的归类从未引起过争议,甚至后修的《晋书》《南史》也延续了这样的归类方式,陶渊明自刘宋至李唐并没有发生身份归属的变化[3]。
梁代是陶渊明研究的一个高峰时期。
昭明太子萧统、江淹、钟嵘、沈约等人都留下了关键性评价文字。
萧统《陶渊明传》承袭沈约的文字,与沈约《宋书》中的传记并行,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钟嵘《诗品》对陶渊明的评价也是后来学人讨论的热点话题,曰: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每观其诗,又想其人德。
世叹其质直。
至如“欢言酌春酒”、“ 日暮无天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每观其诗,又想其人德。
”的原因正在“质直”之风格,这是互为关联也极为关键的一句话,诗与人很好的融合在一起[4]。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这句断语下的精准,《诗品》重在品诗,陶渊明作为诗人,也是隐逸诗人,虽有地位,却在“隐逸”一类。
钟嵘与沈约算是同时代人,评价的趋同性自不可免,钟嵘的论断也有自己的参照标准[5]。
江淹《拟陶征君田居》与鲍照诗相类,不外乎饮酒躬耕的隐者书写。
稍后萧统《陶渊明传》承袭沈约之传文,基本是在讲故事,陶渊明与檀道济的对话、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饮酒抚无弦琴等种种情景展现的正是一心向隐的情怀[6]。
萧统充分注意到了陶渊明诗文的文学价值,不仅在《陶渊明传》中写上“善属文”这样的文人身份认可,而且整理了陶集,并将陶渊明及与其相关的文章收入《文选》,这次编撰活动对陶渊明诗文及形象的传播影响极大。
《陶渊明集序》中专门论及陶渊明之文章: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荡昭彰,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
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评语还在“笃意真古”一面,与后面所叙“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结合起来,虽并未出钟嵘议论之范围,却高扬了陶渊明的文学地位。
以上的简要分析可见梁代对陶渊明的评价还在突出他的隐者情怀,与刘宋时代之描述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上升到品评范畴以内,有了相对准确的定位。
沈约《宋书》将陶渊明纳入“隐逸”类中自然是顺从时评了。
从众声喧哗到写入正史,正是趋于为之定评的过程。
《宋书》并无文学之专传类别,文学家中荦荦大者获得了单独立传的资格,当然仅有文学的成就还不够,政事之成就也要到达一定地位。
细读传记文本,沈约笔下的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完整如一的隐者,而是存在着书写的矛盾定位。
传记文本有三点值得关注[7]。
第一是重在描绘仕隐之间的选择过程,以此展示传主的一生行事。
“少有高趣”却为生存为官,为官却又不愿屈己,无法容忍而后终于归隐田园。
第二是纪事以写人。
不为五斗米而折腰、与王弘等人饮酒,俱是向隐之故事,符合人物的身份。
第三是采摭诗文入传。
陶渊明既然入“隐逸”,采摭诗文入传自然要追求特色,采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疏》等三篇文章,还有《命子》诗。
可分两类:
隐逸之志和训诫之言。
两部分结合起来,可见矛盾之处。
陶渊明有《责子》诗,责诸子懒惰,《与子俨等疏》是“勉诸子和谐相处”[8],《命子》诗花费很大的篇幅述及家族的显赫荣耀[9],“追述祖德”难免要反观自身,“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也并非一时之感慨。
采摭文章入传前后的语境书写值得重视,如采摭《五柳先生传》先说: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将作品设置在“年少”这个年龄段,说明作品是自我形象书写;采摭文章后,说:
“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旨在说明陶渊明的自我形象书写得到了同时人的认可,这样就从自我认同到了公共认同。
既非陶渊明的个案认识,也非史家的片面书写,更加符合客观事实。
《归去来兮辞》是因事入传,是对“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诠释。
因此传记文本先是讲故事,仕宦与饮酒有干系,一旦与政务联系起来,就与饮酒相距甚远,反而不能惬意。
于是,《归去来兮辞》在陶渊明的人生历程中就具有了转折意义。
采摭此文后并无评论,而是接着叙事,所叙的故事沿袭《归去来兮辞》的命意。
传记文本中有一段值得注意: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世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这一段话是叙述陶渊明仕隐态度变化之因由,与家世家风颇有关联。
于是,采摭文章为之一变,晚年的诗文得以采摭入传,这些“训诫之言”皆是有临终遗言性质的作品。
综合这些采摭文字来看,沈约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隐者形象,而是独自过着隐逸生活,对世俗生活也未能决绝的个体形象。
沈约根据时流的观念,以纪事、采文的方式结构了一篇隐者陶渊明的传记,传文中陶渊明写给儿子的诗文占据了不小的篇幅,对于隐者身份并无增益之处,反倒映衬出荣耀身份下的自得与自责的矛盾状态。
传主到底是要逍遥身外还是觉得愧对祖先呢?
这恐怕要取决于阅读者的主观倾向了。
有一点不可否认,沈约刻画的陶渊明形象遵循了“孔门四科”的指导原则,以忠于国家的德行、意在归隐的政事、惬意自在的言语刻画了隐者的形象,而关于文学则没有专门述及,仅以采摭诗文入传无意识地表现出来。
作为第一篇陶渊明的传记,沈约的文字影响深远。
而后陶渊明的形象就朝着愈加符合隐者身份的方向发展下来了。
三、《晋书》中的“袭”与“变”
梁代之后,评论陶渊明的并不多。
阳休之《陶集序录》认为陶渊明的文章,“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
”[10]议论的范围并未出《宋书》之外。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陶渊明,却并无论述。
王通《中说》有云:
“或问陶元亮,子曰:
‘放人也。
《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也’。
”[11]提及的篇目也并未超过沈约传记文本的范围。
修于贞观时期的《晋书》与《宋书》相比是后出的,《晋书》有“文苑”类,却未提到陶渊明的名字,这部新修的“正史”依然把陶渊明归入“隐逸”,传记文本则多多少少发生了一些文字上的变化[12]。
首先,《晋书》综合沈约、萧统的传记以整合内容。
重构是在《宋书》的基础上结合萧统《陶渊明传》完成的,虽然并不是遵循简单的加法规则。
与《宋书》相比,关于陶渊明的姓、名、字有所不同,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增加了“善属文”,不能小瞧了这三个字,“善属文”虽然袭自萧统,与“所有文集并行于世”联系起来,却为陶渊明增加了文士或者文学家的一重身份。
纪事的变化很少,故事性有所增强。
萧统笔下的檀道济并没有被引入进来,沈约讲述的颜延之与陶渊明的关系也被省略了,虽然《晋书》减少了许多与酒有关的故事,关于“酒”的叙事份额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其他元素的被删削而更加突出了。
田晓菲认为:
“他(陶渊明)对酒的爱好不像其他传记那里得到强调,主要是因为送钱给酒店、重阳节酣醉、‘我醉欲眠’以及葛巾漉酒的故事全部被省略了。
”[13]从传记文本的字面上看确是如此,但是从通篇布局来看,又不尽如此。
其次,主题集中而明确了。
《晋书》的陶渊明传记不论写陶渊明的仕宦生活,还是写其隐居生活,都结合一个“酒”字。
传记文本介绍了陶渊明的家族背景之后,直接引入《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传》成为传记文本的书写导向。
政事活动写其饮酒之事,隐居生活亦写其饮酒之事。
政事活动“令吾常醉于酒足矣。
”隐居生活则“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宠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
传记文本写到王弘其人,陶渊明也是见酒不见人,有酒不厌人。
末一段,酒与琴联系起来,更见隐者本色。
传云:
“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
每一醉,则大适融然。
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兒仆。
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则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
”至此一位安于隐的高人形象已经形成了。
为了烘云托月,让传主的“高趣”更上层楼,便藉以铺排叙事。
传云:
“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
‘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无弦琴”意象中表现隐趣的一面也突出出来了[14]。
再者,传记文本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在采摭诗文入传方面。
《晋书》使用的是减法规则。
《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依然全文采摭入传,采摭文本的前后句子都没有变化。
而《与子俨等疏》《命子》等文本被删去了,陶渊明“以言其志”的一面消失了,“耻复屈身后代”的一面也消失了。
《晋书》通过史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叙事重构,以“酒”为基本意象贯穿始终完成了陶渊明隐士形象的纯粹性书写过程。
我们继续向后延伸,看看李延寿《南史》中是如何存录了陶渊明的隐者形象。
在“隐逸”的序中,陶渊明被突出出来,成为被提名的唯一人物。
如田菱所论:
“在一百七十年内,陶渊明已经被从《宋书》中的众多隐士当中提拔出来,成为《南史》中当代隐士的缩影。
”[15]《南史.隐逸传》之陶渊明传记几乎完全取自沈约的传文,稍有改动,改动之处借鉴了萧统的传记。
如“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武帝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所着文章,皆题其年月。
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正是沈约、萧统传记文本的相加而形成的。
“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
”是后加的,形成了陶渊明形象的两面性,他的隐居生活似乎是为了消解痛苦,家族荣耀、“以言其志”的内容反而突出了。
由此可见,《南史》与《晋书》的书写倾向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说李延寿笔下的陶渊明形象又回到了梁代文人的接受场境,或者说又回到了书写的起点。
陶渊明“对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16]的一面再度被发掘出来。
采摭诗文入传方面仅仅提及《命子》,并未采入传文。
《晋书》的广泛流传确定了陶渊明作为隐者的文学家地位,虽然隐者依然是他最终被确立的形象。
正如田晓菲所说:
“我们甚至会忘记,陶渊明首先是一位诗人—无论我们多么颂扬他的‘人格’,如果没有他的诗,陶渊明首先是一个诗人,陶渊明不过是《宋书》《晋书》《南史》所记载下来的众多隐士中的一员。
”[17]田晓菲的这段话只是针对陶渊明入“隐逸”来论定的,三篇传记比较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盛唐时期,一方面陶渊明成为诸多文学家企慕的对象,另一方面却也成为他们无法企慕的对象。
高适、李白、王维等人都在作品中提到陶渊明,向往陶渊明栖身田园的生存状态,却又无法为之。
王维前后期人生态度的变化,也体现在对陶渊明形象的书写中,从《偶然作》到《与魏居士书》演示了从企慕到质疑的过程。
这是由于所处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
陶渊明诗人的身份并未得到认可,文人关注的依然是陶诗中体现的隐逸情怀,立足点还在“隐逸”范围之内。
对于本文来说,这些都是后话了。
对陶渊明的理解和研究至北宋方蔚为大观,陶诗才会获得关注,陶渊明才渐次被认可,终成为古今一流的大诗人。
总之,传记的用意在于写人,陶渊明文如其人,其人反而代替其文了。
各种传记文本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同内容,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陶渊明的文学文本直接被看作是人生的主流部分,而非审美文本。
这种情况到中唐开始发生变化,如白居易成规模的拟作即是一个例子。
至北宋方才摆脱史传文本的全面影响,陶渊明所建构“人如其文”的特别审美形态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文学阐释。
注:
[1]冈村繁认为如果仅仅以《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饮酒》等作品来书写陶渊明形象,“那么渊明就成为一个远超俗尘,在田园中悠闲自在与世无争地生活的隐逸诗人了”。
《陶渊明李白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戴建业《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戴建业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3]冈村繁分析了史书中陶渊明形象的一致性,认为:
“我认为《宋书》以后的诸传记之所以仅仅赋予渊明以高洁无欲的隐者性格,主要原因在于构成他传记的前提。
这种前提具有不得不赋予那种形象的强制力。
它制约并驱使着作者如此写。
这种限制力首先表现在《宋书》、《晋书》、《南史》中。
为了把当时有名的隐者全部收录入《隐逸传》中,作者竭力使其中有关隐者的每篇传记都具有符合隐者风貌的内容。
”《陶渊明李白新论》,第15页。
这种分析有其道理,有为书写人物形象的以偏概全之嫌,但是应不仅如此。
陶渊明形象的稳定性还源于作品的被接受效应。
田菱《解读陶渊明:
历史接受的变化形式(427—1900)》一书中也对上述史传文本进行了细节分析,从故事性的演变分析陶渊明如何成为“超然不群的隐士形象”。
参见吴伏生《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177页。
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一书中也专列“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一章探讨四篇陶渊明传记的源流与文本变化。
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3—82页。
作者撰写《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参该书第18页。
[4]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4页。
[5]范子烨《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中认为陶渊明的诗歌与曹植的风格有相承之处,其《拟古》是对曹植人生的叙写。
参范子烨《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按:
《诗品》是以曹植为核心人物确定品第之高下的,钟嵘将曹植定位文学中的孔子,“文圣”的称号呼之欲出,论评诗人不免以之为标准权衡人物品次定位。
[6]萧统《陶渊明传》采摭陶渊明诗文多是仅有题目。
采摭文本入传的只有《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的部分句子。
文中还提及陶渊明的妻子“与其同志”,亦是沈约传记文本中所无者。
[7]冈村繁认为沈约《宋书》里的陶渊明传记收到颜延之《陶徵士诔》的影响。
《陶渊明李白新论》,第14页。
[8]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1页。
[9]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将《命子》诗系于太元十四年(389年),陶渊明是年三十八岁。
《五柳先生传》系于义熙十一年(415年),陶渊明六十四岁。
则《宋书》以《五柳先生传》证陶“少有高趣”则不通也。
魏耕原认为《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六十岁以后的作品,参魏耕原《陶渊明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邓安生将《命子》诗系于太元二十一年(396),陶渊明二十八岁。
参邓安生《陶渊明年谱》,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龚斌《陶渊明传论》认为:
“《命子》诗反映了陶渊明青年时代的政治热情和光宗耀祖的思想”。
参《陶渊明传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10]北大中文系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页。
[11]北大中文系编《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