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君礼物的思想.docx
《夏可君礼物的思想.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夏可君礼物的思想.docx(3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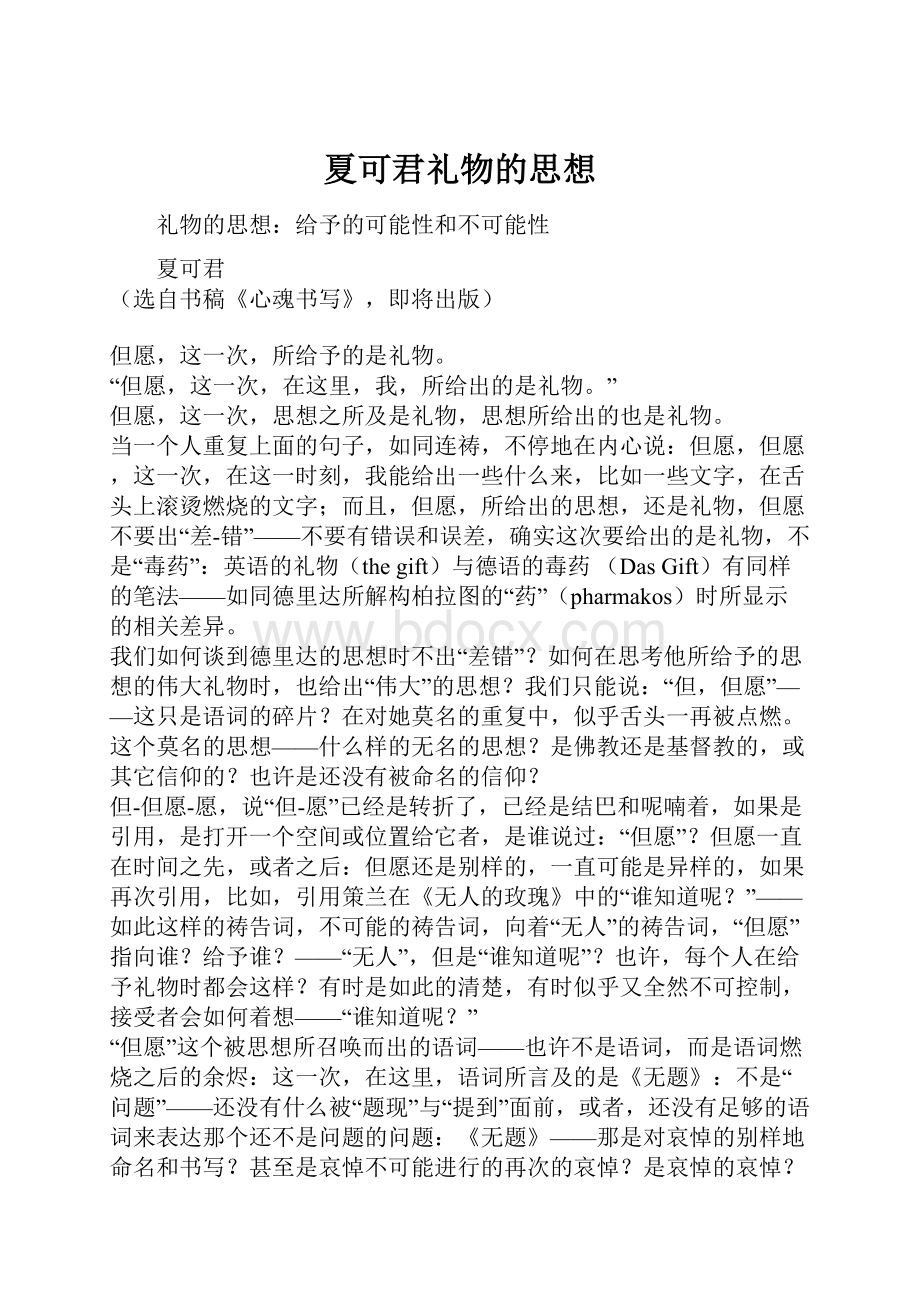
夏可君礼物的思想
礼物的思想:
给予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夏可君
(选自书稿《心魂书写》,即将出版)
但愿,这一次,所给予的是礼物。
“但愿,这一次,在这里,我,所给出的是礼物。
”
但愿,这一次,思想之所及是礼物,思想所给出的也是礼物。
当一个人重复上面的句子,如同连祷,不停地在内心说:
但愿,但愿,这一次,在这一时刻,我能给出一些什么来,比如一些文字,在舌头上滚烫燃烧的文字;而且,但愿,所给出的思想,还是礼物,但愿不要出“差-错”——不要有错误和误差,确实这次要给出的是礼物,不是“毒药”:
英语的礼物(thegift)与德语的毒药(DasGift)有同样的笔法——如同德里达所解构柏拉图的“药”(pharmakos)时所显示的相关差异。
我们如何谈到德里达的思想时不出“差错”?
如何在思考他所给予的思想的伟大礼物时,也给出“伟大”的思想?
我们只能说:
“但,但愿”——这只是语词的碎片?
在对她莫名的重复中,似乎舌头一再被点燃。
这个莫名的思想——什么样的无名的思想?
是佛教还是基督教的,或其它信仰的?
也许是还没有被命名的信仰?
但-但愿-愿,说“但-愿”已经是转折了,已经是结巴和呢喃着,如果是引用,是打开一个空间或位置给它者,是谁说过:
“但愿”?
但愿一直在时间之先,或者之后:
但愿还是别样的,一直可能是异样的,如果再次引用,比如,引用策兰在《无人的玫瑰》中的“谁知道呢?
”——如此这样的祷告词,不可能的祷告词,向着“无人”的祷告词,“但愿”指向谁?
给予谁?
——“无人”,但是“谁知道呢”?
也许,每个人在给予礼物时都会这样?
有时是如此的清楚,有时似乎又全然不可控制,接受者会如何着想——“谁知道呢?
”
“但愿”这个被思想所召唤而出的语词——也许不是语词,而是语词燃烧之后的余烬:
这一次,在这里,语词所言及的是《无题》:
不是“问题”——还没有什么被“题现”与“提到”面前,或者,还没有足够的语词来表达那个还不是问题的问题:
《无题》——那是对哀悼的别样地命名和书写?
甚至是哀悼不可能进行的再次的哀悼?
是哀悼的哀悼?
“谁知道呢?
”
但是,当一首诗的题目题为“无题”时,标题本身已经在否定自身了,已经是哀悼的言辞,已经在矛盾与曲折之间为咏叹定下了忧伤与怅然,茫然与空茫的基调。
我们定然会想到李商隐歌咏过的那首最为传颂的《无题》哀悼诗: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作为标题是否正是语词在歌咏后留下的余烬?
要不然,为什么,诗人在无奈之际,在没有语词可以使用的情形下,只得使用这样的标题?
一个不是词的词,一个一无所指,空空茫然的词?
“但愿”这个词,与作为“无题”的标题一样,也不是词,而是“无奈”之后的叹息?
或许,“也许”,所有的语词也只是叹息——使徒保罗说过那是圣灵,神圣鬼魂的叹息!
“但愿”这个词是我们对德里达与布朗肖以及尼采的“也许”(peut-être,perhaps,viel-leicht:
一点点,“也”还有剩余的,“也”总是很有多余的或剩下的,或者,还多出一点点,还是很多的-很轻易的事情?
)的对应的翻译与重写,甚至是在汉语中的“改写”?
“也许”是例外的逻辑,是对要到来的事件的召唤,永远有着不可能性的例外。
同时,她也是我们在汉语中所要给出的思想?
但给予谁?
她如何被翻译回去——回到西语中?
是先有“也许”,还是先有“但愿”?
她们如何交叉与交错?
这是思想的秘密?
我,在这里书写的“我”,如何知道?
依然是“无题”。
说“但愿”,但,为什么要说“但愿”呢?
是担心所给予的不仅不是礼物,而且担心所给出的还不是最好的。
似乎如果是礼物,如何能不是最好的呢?
从而礼物就总是要求着更多与更好?
!
甚至是“更多的更多”与“更好的更好”——于是,礼物就总是要激发一个过分的要求:
礼物的要求总是过分的?
是神圣的与宗教层面上的,而且是超越一切法则,乃至伦理之规范的?
这是否也挑起一个无尽的乞求:
礼物只能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那就没有谁能给出礼物了?
那也就没有礼物了?
这样,礼物不就被取消了?
礼物如何能成为一个讨论的“题目”?
除非有一个已经敞开的空间,才有“名目”可以去填补。
于是,在言说礼物之前,在谈及礼物之初,我们就“应该”先在地请求“宽恕”(for-giving,为了纯然的给予而给予?
)?
请求它者宽恕我们,总是没有给出最好的礼物,总是带有我们自己的意志与心意,总是在要求回报,总是会“给-错”,给的不恰当,不合时宜,更不能做到“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事”。
是否没有宽恕就没有礼物?
那么,礼物就是思考宗教的一条道路?
也许是思考所有宗教的前提?
每一种宗教不都是在一次“献祭”的“死亡给予”的仪式行为中奠基起来的?
这一次,我们将反复念叨“但愿,但愿”,但愿的转折与呼求,既是否定又是肯定,而且“也许”还在这肯定和否定之前。
“但愿”的言说事件在召唤一个例外的事件,尽管还不确定,于是,德里达说:
“如果有这样的一件事——我不能确信,一个人从不能确信有礼物,礼物被给予”,也许我们只能说:
也许,有礼物;或者不得不采用虚拟的限定式:
“礼物可能存在着,如果有的话”,它将不得不与可能性的条件和可计算相关并与之并存;但愿,有过礼物,但愿,礼物在到来着,到来之中。
是的,有谁在给予礼物时“志在必得”,而内心不在颤栗?
“谁知道呢?
”
1,礼物作为问题
当一个人开始思想,当一个人被思想所召唤进入思想的进程时,并思想那思想本身时,就已经在接受来自思想的礼物了!
只有当思想和思想的激情已经在那里,或者已经被唤醒,我们才可能去思想。
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已经是礼物,已经先在地被给予我们了!
思想的礼物与礼物的思想就相互牵引着,任何对礼物的思想都伴随着对思想本身的思考,即对那给予我们,为我们所承继的来自思想的礼物与接受方式的思考,也即是说,“对礼物的思想”要求我们同时思考思想的可能性——即“接受”思想,“保存”思想与“给出”或“给还”思想的可能性。
但礼物能成为我们所思考的“对象”吗?
礼物作为给予之物是一种什么样的物?
甚至“有礼物”吗?
我们能够说礼物“存在”吗?
如果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存在也只是被给出的礼物之一(esgibtSein:
itgivesBeing)?
这给出的事件(Ereignis)甚至比存在论差异还要根本。
但存在作为天命馈赠的礼物(DasGeschenk)在发送(schicken)中就一定能到达它的目的地?
甚至,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中对重来的祈祷与呼求时,也是在书写中,在引用的叙述中,在多重的声音中,在书信开始的传递系列中发送(envois)的,如何保证传递的通道不被打断?
从而不扰乱福音的传递?
如何能避免给予中“交-错”的可能?
在所谓哲学的终结之处,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循环体系终结之后,尼采在他严肃又戏仿的第五福音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馈赠的德行》中写道:
“现在我吩咐你们失去我,并且寻找你们自己;当你们已经全盘否定我,我将重来到你们处”。
即只有在失去(verlieren)思想的教导者或思想的给予者之后,这“得己或成己(Er-eignis)”与“去己或失己(Ent-eignen)”的游戏——海德格尔对尼采和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判决标尺(在《什么召唤思》的前半部讨论尼采的著作中),它既是尼采离开形而上学的尝试,也是礼物给予是否成功的秘密。
尼采的超人的教导者要求我们成为孤寂者与被排斥者(Ausscheidenden)——或许也是去成为一个被弃者——瞧,这个人!
这个被世界和神一起所抛弃与离弃,遗弃在十字架上的人子:
一个多余之物,比死亡还要小——上帝的死使死不再有意义?
又还要多——那在流血,将要腐烂,却又可能复活的肉体使死不允许被神圣化与替罪羊化?
成为“药”?
而尼采还希望这些“被弃者”成为一个新的被拣选的民族(又一个被摹仿和戏仿的犹太民族,或某种超越犹太教的犹太性?
),这是对重临的圣灵或神圣鬼魂的重写?
但他在《爱邻人》中却反讽地提醒我们,应该爱远方之人而不是邻人,爱幽灵(与基督教的精神有什么差别)与“危险的也许”,尼采的哀悼与遗言是对基督的思想的重新激活,还是别样地改写?
这些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还有待成为讨论的“课题”。
但在尼采对一种新的馈赠方式的召唤与倡导中,是否一种新的思想,以及伴随着新的给予的德行,一种新人,即,未来的哲学家将被给予出来?
甚至,在这个馈赠的德行中将产生伟大的政治?
这是一种消除战争或重新规范与约束战争的可能的方式?
如同我们的儒家在一个战乱时代所要给出的礼乐教化的政治原则?
于是,“礼物”的思想对哲学与神学都将性命攸关了,它关涉思想的未来与它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一直还可能的不可能性,如何还能是无题呢?
而礼物的思想还离不开那个时代的思想的转折,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韦伯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对商品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剖析已经提供了对礼物思考的可能。
如果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共同体(/共通体)和“共产主义/共同体主义”的思想,我们将发现礼物和商品内在的交错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的思考依然是提纲式的):
1,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开头写道:
Communism——是一个幽灵:
dasGespenstdesKommunismus,“犹太人”马克思这样用他的母语“德语”书写着。
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之后,我们必须追问马克思他如何梦想这个幽灵的?
——一个幽灵总是与梦想,幻觉(Phantasie),幻象(Phantom)有关——这个derKommunismusdesGespenst?
我们的这个颠倒,这个语词位置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一个梦想是否总是大于这个梦想者的?
犹太人的耶和华这样的唯一神,与一个基督教化了的德意志的现象学精神,和一个未来的到来中的Kommunismus幽灵——这之间会没有区别?
或者我们根本上就没有能力来区分这些幽灵们?
而现在,在汉语中,已经将近一百年了,我们一直在实现这个词,有意无意地使用着这个组合词,但是,我们汉语的鬼神如何与这个异域的幽灵,幽灵们相遇?
相混合和结合?
马克思的英文和法文都很好,他能够说也能够写它们,当他在伦敦和其他人隆重聚集,当《宣言》发表时,他是否会用英语说他们正在形成一个CommunityofSpecters吗?
Community这个词显然与Communism相通,它们词根相同,这个轻微的变异书写改变了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他是如何思想这两个词的?
2,Communism应该是由Communi-st(共产?
党-员:
这里根本没有财产这个字义,虽然有“共有某物”的含义)还是Communi-ti-st(共同-体-员)组成?
也许,在马克思那里,这二者并没有差别?
或者,这个差别是隐而未显的?
或者,这个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个差别的思想,思想自身所产生的差别,伟大的差别和差别的伟大——大过了马克思本人自己的思想?
由无产阶级组成的党或由某种“文学性”(/书文:
并非狭义的文学艺术,而是文字阅读与书写意义上的)组成的共同体(/共通体),其性质有何不同?
革命的主体或行动者必须一直是革命的,那么作为运动,一直运动着的革命者也是未定的,是一群幽灵们?
那就成了:
幽灵们的幽灵!
这个重言式是否消解了革命的现实性?
但离开了幽灵性的革命还是革命吗?
在汉语古代思想中,离开了天命的革新还是其命维新吗?
如果文学性的真正本质或其本性就是创造和革新,那么,是否后者更能承担革命的使命?
那么这个共同体——幽灵性的共同体(/共通体)如何书写和阅读它自己?
如何不断地改变它自己?
是否最初的无产阶级——承担着扬弃着哲学的使命,成为自为的解放的心脏——就必须在书写中,在头脑中书写一种新的哲学而形成的?
而且马克思的手稿就是片断性的,《资本论》还一直没有完成!
3,这个发端于对“所有制”(DasEigentum)和“私有财产”之历史形成——即私有制之“成其事”(/成己:
Er-eignis)的思考,是否也同时在渴望剥夺或去除(Ent-eignis:
去己)它自身?
但是,如果这个Communism发端的思考不仅仅是对这个居有(成事、成己)和非居有(去己、剥夺)——集中于Eigen(自己,自身,专己,专有),Eigentlich(本己的,本真的)意义上的相互关联的思考,而且也是——甚至更是在一个与它者(otheness)共在着的和一起生活的,而且,可能这个“共在”(Mitsein)的共生存还是“同时”或“先于”这个本己的思想的思考(参看南希对共在的本体论的思考),甚至,如果实际业造性的(Faktizitaet),被给与的(vor-gegeben),如果被抛的生活或“实际性(/业造性)的生活经验”比存在问题的发生更为根本的话(如同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的情形),这个共同生活(Mitleben),在生活和生命的意义上比存在的思考还要根本:
因为从没有独自一个人的生活,实际的生活一直是在共同生活之中发生的。
那么,重新思考这个生存和生活的共同性(Being-in-Commom?
Life-in-Common,Co-existence),将意味着什么?
4,马克思研究的是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
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谓的生产关系,但关系在先。
马克思本人,在他的时代也是如此,是如此着迷于这个词,用它来区别国家,以前的共同体(Gemeinschaft,Community),于是:
Communism(共产主义)又被称为社会主义——注意在德语中也是与英文词society相关的。
但社会与共同体有什么差异?
如果我们前此已经把Communism和Community内在关联起来,是否马克思对社会的思考一直被这个共同体的幽灵所陪伴着?
事实上也是如此,在1844年国民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当他区分动物与人类的共同生存特性时,认为人类在共同体中可以通过交换彼此使用对方在劳动分工后的产品,而“动物不能为它的共同体的利益和种族的舒适做出贡献”,在这里,马克思同时在人类和动物“社会”或组织的一般意义上使用“共同体”,但显然认为二者有别。
这个区别在进一步界定人类的类本质时,把社会性和共同体区别开,如果人类的男女配偶关系是一个自然的共同体,他还甚至提到“妇女的共同体”,认为私有财产的关系一直保持为共同体与物品世界的关系,来比较和思考妇女作为共同体的共有财产,如同普遍的妓女,认为配偶关系只是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类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人成为人之自然的关系,即,还不是社会的关系,那是人的类本质,那是社会自身把人作为人来生产,这要通过社会化的活动和精神,这有这样人才能成为社会化的人。
马克思认为共同体只是一个劳动的共同体,作为支付薪水和普遍资本的共同体,显然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资本的共同体相重叠了。
进一步,如果“共产主义(/共同体主义)”或者Communism是一个不停息的运动,那么当国家消亡,是否“社会”也将不存在?
马克思为什么不去用英语和法语来思考Communism与Community的关系?
而却偏偏偏爱“社会”这个词,而不是共同或共通这个词?
5,当马克思讨论犹太人问题时,他说“金钱是以色列的勤奋的神”,却又只是在幻想中交换(又是一个幽灵),而犹太人作为一个最为独特的阅读和书写塔木德的“共同体”(显然不是社会),却被马克思当作基督教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来处理,而且把犹太人的解放和社会从犹太人的解放,即从虚假的金钱关系中解放——但犹太人认为自己的劳动并不是为了社会和国家,而是为了其民族性和神圣的律法,也不是自我主义的——而是他者性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的批判中是以《圣经》文本的结构展开的,其中提到了“旧约的经济”和“新约的经济”,如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馈赠的德性”隐含的经济。
而且,马克思所面对的“犹太人问题”还一直是问题,成问题的。
在二战之后,必须被再度反思的问题。
这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那个可见的神性的金钱货币有什么差异?
资本主义的资本的幽灵就是犹太人的唯一神?
基督教的的世俗化就是神的货币化?
如同黑格尔的逻辑?
耶稣的宝血的给出和供奉呢?
如果犹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神学问题,这个解放的问题与犹太人自身的出埃及的源初的解放是什么关系?
那么,中国人问题呢?
鸦片作为“药”的问题呢?
“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呢?
6,马克思发现了“商品”以及商品上所凝结的社会关系,剩余价值,甚至是历史。
这个发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上展开:
在历史,文化人类学层面上,他谱系式地追踪了商品与社会分工,阶级形成之间的关系;然后,在社会与人的本质结构层面,即社会学层面上,他还原出凝结在商品上的人与人的本质关系;而这都是在对人的本性与社会关系,即人与劳动的关系中来考察的,使剩余价值的发现可能,从而为人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提供了可能——这是在哲学层面上的揭示和解释了;对劳动和异化关系的思考,已经隐含了批判的标准:
即所有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也由此确立起解放的许诺,在对资本“精神”的驱魔中形成了所谓马克思的弥赛亚主义的终末论——显然,这是宗教神学,甚至是“解神学”意义上的了。
德里达已经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中重演了这个精神纠缠的奇异场景。
而第四个层面其实与第一个层面是相通的,即,从根本上说,这几个层面的思考只是思考方式和结构上的方便说法。
但是,马克思•韦伯却为资本主义作了宗教上的辩护:
他从比较宗教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出现的原因,在问题的提出上结合了人类学和宗教层面,其解决也落实在这个层面。
首先他强调了商品交换所要求的薄记与计算的重要性——这是经济社会学层面上的考察;而计算可以推动理性与逻辑的形成,这是在哲学上辩护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而为什么资本主义只在西方兴起,其最核心的原因还在于所谓的新教伦理,即基督教的天职劳动观念的影响,这当然与圣子的献祭(基督的宝血)及其人在亏欠中的回报(来抵偿罪过)分不开。
正是在这里:
这个圣子的献祭的给出与供奉(offering),无疑也是礼物(gift)。
离开了礼物的回报的德行和行为,资本主义,或者说,整个西方社会是不可能被理解的。
而对礼物的思想,从人类学,哲学等等各方面的全方位思考,恰好就处于这个时代思想的转折上。
于是:
礼物如何在商品的形成中起作用呢?
礼物与商品的差异何在?
是并行的还是在所谓的进化论上商品扬弃了礼物?
礼物可以被交换吗?
礼物是否从消费的另一端不同于商品的生产?
对礼物的遗忘是否是西方主义的命运?
更“要命”的礼物是“鸦片”:
是宗教的,还是殖民化的商品?
还是战争的象征符号?
而马克思是讨论过鸦片贸易和战争之间关系的。
只是囿于人类学的视野与历史事件的限制,马克思对东方文明的思考还只是在萌芽阶段,而且西方自身传统与哲学的思考方式的限度还有待显明——如奥斯威辛与西方文化的命运;而韦伯虽然努力发现其它文明的独异性,但他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时,仍然是从西方的资本主义出发的,主要还只是在说明东方,比如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总是喜欢用否定的说法来展开比较)出现资本主义,却不去问中国文化自身有什么,是如何形成为这个样子的。
如果,汉语思想能够对礼物提出独特的思想,是否意味着“卡夫丁峡谷”的通道可以打开?
这与Communism的传播,在中国现实历史上的作用将会重新被审查?
在所谓的“共产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垮台之后,一种新的共同体或“共通体”如何形成?
是否,应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话语实践中,在汉语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交往中来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共同体”和“共同体主义”的思想?
如何激活汉语经典思想的感通性和生发性,以及革命的思想?
其间的关联在哪里?
如何形成政治上新的可能性?
在“一党”的现实政治统治和未来“共同体主义”的可能政治行动之间,如何蓄势待发?
同时,在回到我们自身传统的创见,即孔夫子那里,在一个德位不当的时代,通过师生的阅读共通体的方式传递着天命,但在后来却完全被政治帝王统治代替了学统和道统,如何避免这个覆辙?
如何保持政治共同体和学习共通体之间的张力?
犹太人的它者性命运和现实的双重身份是否给我们以启发?
而这又回到了共通体的共在上了。
这里我们还不讨论个体理论和原子的偏斜说,个体与自由(及其主义)的关系,革命与共和、保守之间的关系,以及民主的未来的问题。
因此,把礼物馈赠作为经济模式来理解已经狭隘化了,礼物馈赠作为一种“元伦理”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势必也影响政治和政治本身。
如果考虑到马克思对商品和资本的批判,如果在商品中已经有礼物的要素,如果在东方社会中,比如中国礼物“交换”占据主导,那么儒家的礼乐传统如何与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
这无疑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而不再只是亚洲四小龙的儒家资本主义了?
同时,它是否可以消解当前宪法改革的困难和中国资本积累的“贪污受贿”的道德焦虑和所谓的“原罪感”?
如果中国的资本已经凝结了礼物彼此给与和回报的交往原则的话情形将如何?
!
是否这可以激发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思考的可能性?
阅读此处
而以“礼乐文明”著称的中国文化难道不正好可以为“礼物的发现”提供契机——而这正是本文在汉语中写作的动机?
但是,在汉语思想中,“礼物”似乎一直是“无题”的:
在无法投递的信物中,在礼仪扭曲的身姿中,在帝王内宫的火焰中,礼物或者“礼”本身从没有成为本体的至高的问题——当然,在孔子那里是一个例外,可那是天命在给予中的发生。
虽然这已经经过了一个思想的迂回运动,是西方对礼物的思想唤醒了我们重新来面对我们自身的思想,因此,对礼物的思想总是带来思想的礼物。
只是这一次的接受与转换,转变,都在礼物的思想的流动中进行,“生生之易”是礼物“往来”的原则?
但是,如果这“生-生”之间出现了断裂呢?
“易”停顿了呢?
靠生殖来传递与保证的“香火”——那火焰不会成为灰烬?
那家谱中死者们,鬼魂们的名字如果不再被冥币的火焰在节日所点燃,不再被哀悼,是否讲述的历史会中绝?
还是通过尼采,在其《论道德的谱系》中,大胆揭明了道德发生的暴力与权力机制,认为道德与宗教上的内疚与罪孽的责任观念,实际上,“起源于最古老的最原始的人际关系,起源于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
不管是否是德语本身(dieSchuld:
有着“债务和过失”的双重含意)为尼采提供了反思馈赠方式的便利,尼采的发现起码为重新全方位解释历史提供了可能。
随后,在1925年在法国出现了莫斯的《论馈赠》(或译为《论礼物》)一书,在该书中,莫斯力求通过对北美原始部落之间相互馈赠礼物或交换礼物,直至在交换中比试着回报更多更好的礼物,以至于挥霍礼物(如夸富宴),甚至毁灭礼物的分析,来说明礼物交换与商品交换的差异,强调礼物交换比商品交换对社会的人际关系与道德感的形成更有影响,礼物是价值的价值,是信贷经济理性的基础,赋予了礼物在传统社会整合中最为重要的功能,而且还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所谓“礼物的精神”)来讨论。
然而,正如德里达后来所尖刻地指出的,在该书中,莫斯除了没有说到礼物,说了一切,因为莫斯既然要区分礼物与商品,却又随意地使用“交换”一词,但是,礼物是能够被交换的吗?
德里达的提问实际上使礼物与馈赠行为本身发生了致命的分裂,使日常的礼物概念和哲学意义上的礼物范畴发生了断裂。
当然,德里达的思想已经受到了巴塔耶的激发。
正是巴塔耶比其他的人类学家更为彻底与坚决地把礼物作为其思想的核心,并以礼物为核心来考察宗教的神圣社会学,尤其是宗教的牺牲与献祭仪式,法西斯主义的暴力机制,以及寻求一种“非知识”的可能性。
进而,他区分了资本主义的“有限的经济学”与尊重绝对主权的“一般的经济学”,而后者对耗尽,消费,挥霍的强调,不同于资本主义对生产与交换循环的推崇——显然这与马克思对生产力,韦伯对合理性的推崇有重大差别,当然并不就意味着巴塔耶是所谓的非理性主义的。
他还力求在思想礼物馈赠的可能性时为新的共同体的形成提供准备条件,以便走出西方传统的封闭体系,为批判资本主义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中则从两种书写形式中揭示了巴塔耶对“在场”的自我保存意志的依赖性书写的藐视,而强调对另一种让绝对主权将自己分配的书写:
“这另一种书写就将痕迹当作痕迹去生产的书写”,只有当痕迹也抹去自身时,并把书写当作某种绝对抹去的可能性来建构时才是痕迹。
即绝对主权的“主体”要走到底,就必须抹去自身,拒绝被承认(打破主奴相互承认的辩证法),成为不在场的,无意志,无希望地忍受一切,生活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