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新疆茶务探微.docx
《清代新疆茶务探微.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清代新疆茶务探微.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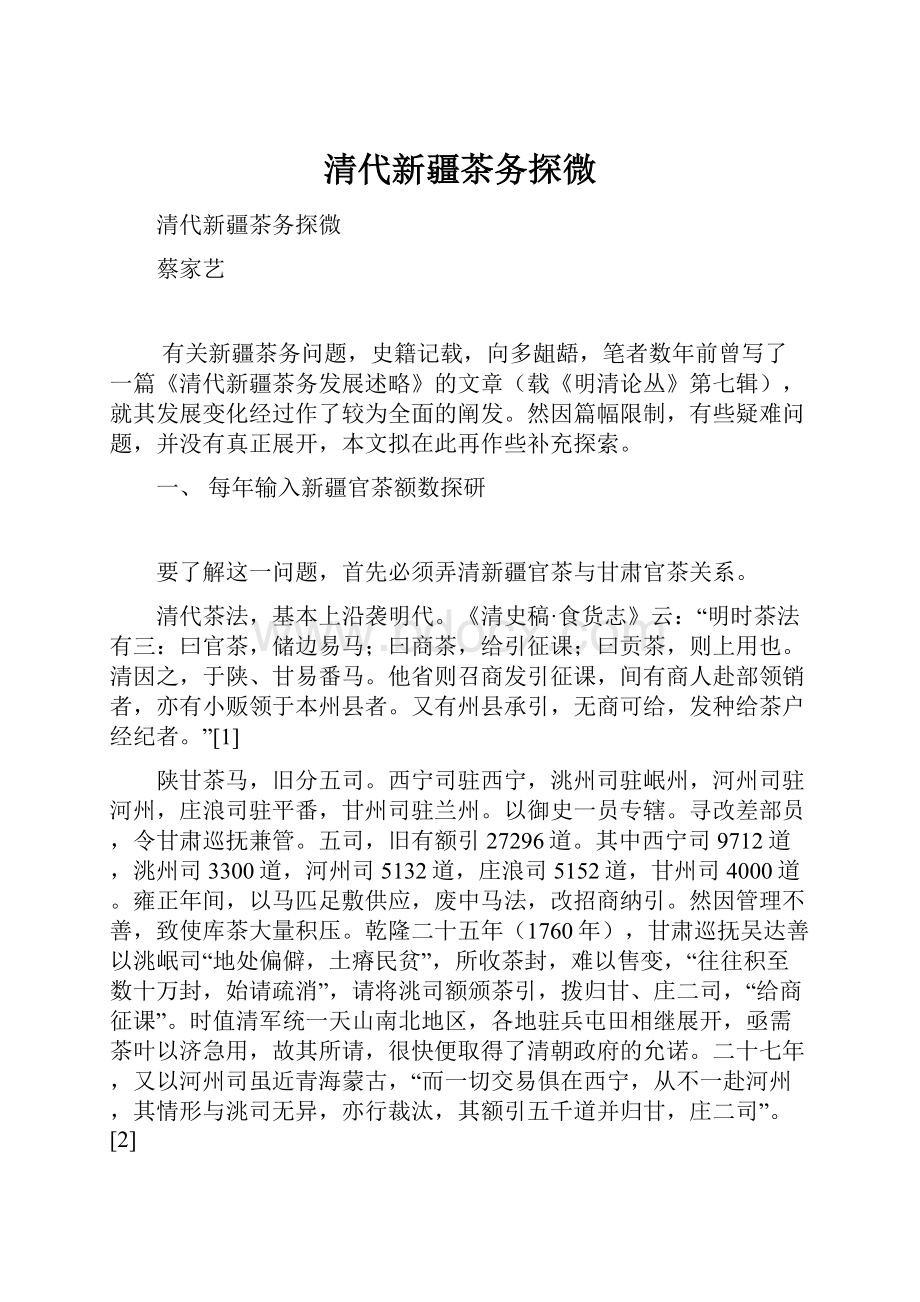
清代新疆茶务探微
清代新疆茶务探微
蔡家艺
有关新疆茶务问题,史籍记载,向多龃龉,笔者数年前曾写了一篇《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的文章(载《明清论丛》第七辑),就其发展变化经过作了较为全面的阐发。
然因篇幅限制,有些疑难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本文拟在此再作些补充探索。
一、每年输入新疆官茶额数探研
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新疆官茶与甘肃官茶关系。
清代茶法,基本上沿袭明代。
《清史稿·食货志》云:
“明时茶法有三:
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
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
他省则召商发引征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州县者。
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给茶户经纪者。
”[1]
陕甘茶马,旧分五司。
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
以御史一员专辖。
寻改差部员,令甘肃巡抚兼管。
五司,旧有额引27296道。
其中西宁司9712道,洮州司3300道,河州司5132道,庄浪司5152道,甘州司4000道。
雍正年间,以马匹足敷供应,废中马法,改招商纳引。
然因管理不善,致使库茶大量积压。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甘肃巡抚吴达善以洮岷司“地处偏僻,土瘠民贫”,所收茶封,难以售变,“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消”,请将洮司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给商征课”。
时值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各地驻兵屯田相继展开,亟需茶叶以济急用,故其所请,很快便取得了清朝政府的允诺。
二十七年,又以河州司虽近青海蒙古,“而一切交易俱在西宁,从不一赴河州,其情形与洮司无异,亦行裁汰,其额引五千道并归甘,庄二司”。
[2]
从有关记载看,所谓“将洮、河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一事,实际上则是全归甘司所有。
因为在上述二司中,只有甘司之茶,才能直接灌输于新疆南北两路。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光二年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中得到证实。
他说:
“新疆为甘司行引之区,久已有定界,难容私贩充斥,以致官引滞销,亏短国课。
”[3]这就是说,新疆所有官茶,皆来之于甘州司所颁之额引。
清楚了这一点,那末,当时新疆官茶额引数,则可不言自明,这就是甘司原有的4000引与洮、河二司额引数之和。
换句话说,其时输入新疆之官茶,应当是12432引。
甘肃茶法,“每引纳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
又云:
“定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
”[4]意思是说,商人每运茶100斤,除交官茶50斤外,余50斤包括附茶共64斤,商人可自行销售。
何谓“附茶”?
“附茶”原是官方为提供茶商作酬劳和损耗之茶,因许其与自售作本的“正茶”一起运销,故称之。
考其来源,明时已有所见。
例如《明史·食货志》载:
“五年(隆庆)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开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踰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
”[5]《甘肃通志》说:
“明陕西置茶马司四。
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
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
官茶易马,商茶给卖。
每上引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
”[6]
新疆官茶与附茶原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搭放兵饷”之茶,而后者则是指商人即官商自卖之茶。
但在有关记载中,有时是将其加以严格区别的,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陕甘总督杨应琚说:
“新疆虽需官茶二万七百余封,应陆续运贮,令官兵领买,稍加运费,较买自商人,尚属减省,将来遇有换班兵,更可酌为携带。
现在巴里坤、哈密先行拨运,再由内地运往。
”[7]但将二者视为一体的也屡见不鲜。
例如纪昀《乌鲁木齐杂诗》:
“闽海迢迢道路难,西人谁识小龙团。
向来只说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
”诗中所说的“官茶”,实际上就是指附茶而言,这可以从作者在其诗注中得到佐证。
“佳茗颇不易致,土人惟饮附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
商为官制,易马之茶,因而附运者也。
”[8]清代甘商所运正茶、附茶,向皆“湖南安化所产之湖茶”。
[9]之所以将附茶也称为“官茶”,目的是为与从北路输入的晋茶即私茶相区别而已。
道光初年,那彦成以甘肃“官茶壅滞”,奏请制定“新疆行茶章程”,其所说之“官茶”,也是这一意思。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起,清廷因榆林府官引壅滞,即将其所引1000道中拨出500道归甘州司行销。
嘉庆二年(1797年),又以其“原留额引五百道仍属壅滞”,拨出400道归甘州司。
“十年(1805),复以甘州茶引不敷行销”,“增引八百道”。
[10]经过数次调整,促使甘肃官茶额引由原来的27296道跃升至28996道。
这些新增引数,实际上都归属于甘州司所有。
这就是说,甘州司额引已从原先12432引上升为14132引了。
根据甘州司所持额引计算,则大体可知,自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其每年输入官茶(包括“搭放兵饷”11万余斤)约为18万余封,90万余斤。
而自嘉庆十年(1805)起至道光年间,其每年输入官茶则为20万余封,100余万斤。
以上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基本上是可信赖的。
道光八年(1828),钦差大臣那彦成在其“禁奸商私贩并设局稽查”的奏折中说:
“臣那彦成出关时,沿途探访,并行查兰州、凉州等及口外各城。
据兰州道奏称,南北两路,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向食北路商茶。
伊犁、塔尔巴哈台、乌什三城,向例兵饷搭放茶封外,其余十二城,均系自其引地,岁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加以带销带引及拨运官茶,约计二十余万封,向系官商运至凉州发庄,听往来客贩转运出关,随地销售。
”[11]那彦成所说,值得注意地方有二:
一是“岁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
一是“加以带销带引及拨运官茶二十余万封”。
这两个问题,前者较为费解,尚不知其所自出。
后者则可一目了然,是甘司额引数与拨运官兵搭饷数之和。
新疆规复后,官茶行销实施以票代引。
然其每年额销茶又有多少呢?
《新疆图志》记载,“旧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南商改办晋茶,续发茶票一百五十张。
伊犁创办公司,请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常年销数”。
[12]以上记载,因说的很含糊,乍看起来实令人莫名其妙。
但细为观察,它其实是包含着三个不同历史时段的输入数在内。
首先,是“旧发茶票三百五十张”。
这里的“旧”字是指何时?
文中没有明确交代。
从已有资料看,当是指建省前后的一段时期。
倘推断无误的话,按以票代引法每票给茶5000斤,外给损耗700斤推算,其时每年输入之砖茶,当为39万余块,合199万余斤。
但据《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记载,官茶的行销并未因新法的实行使滞销现象有所改变,相反是“私茶充斥”日见严重。
自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发行第一案茶票后,中隔近十年,至光绪八年始发行第二案茶票。
时“每岁约销一百余票”,到光绪十二年(1886)尚没有完全销完。
当年又续发第三案茶票,共409张。
此后每隔两三年左右便续发一案。
截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发第十一案茶票。
[13]倘从光绪八年起,其茶票数按第三案发行数计算,则其每年的发行数量实际上只有194票左右,折合茶叶仅为22万余块,110万余斤。
这与《新疆图志》所说,显然有很大的出入。
个人看法,似以《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所说较接近于事实。
其二、“南商改办晋茶,续发茶票一百五十张”。
这当是指光绪三十年(1904)之后数年。
《清德宗实录》记载,松蕃奏:
“新疆伊塔一带,本系南商官茶引地,近因晋商私茶充斥,官运滞销,现南商另请新票,赴湖北羊楼峝采办茶砖,送至关外各处行销,应准其试办,下部知之。
”[14]据此计算,则自次年起,其每年输入之官茶,只约相当于39万余块,196万余斤。
其三、是“伊犁创办公司,请发茶票三百五十张”。
伊犁茶务公司建置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为官商合办。
后因“用人行事,利权不一,东鳞西爪,使不相闻,虽在同谋,亦怀疑二经手者掉动不灵。
又值湖商不服,甘督力争”,加以协饷奇缺,“以致奏准三年,尚难开办”。
[15]及至宣统二年(1910)改归商办后,始请遵章发给第一案茶票。
似此看来,其正式运行已是宣统三年了。
这就是说,及至清末民初时,其每年输入之官茶应当是79万余块,395万余斤。
二、新疆晋茶非甘肃官茶考辨
《新疆图志》说:
“昔承平之时,官茶引课咸属晋商,谓之晋茶。
乱后流离,湘人遂专其利。
”[16]按其所说,新疆晋茶,其最初也是来自甘肃官茶。
因其为山西商人所贩运,故称晋茶。
依据上述论断,此后有的学者便进一步引申说:
“这种晋茶,实在也是从湖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
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
”[17]一句话,两者来源,均为甘茶引课,其所运皆湖茶。
这种说法对吗?
在笔者看来,这纯粹是一种误解。
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早在甘肃官茶输入新疆以前,山西商人就已将茶叶及其它各种日用必需品,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归化城等地输入新疆了。
《清高宗实录》记载,大小和卓木叛乱平定后,清朝政府为鼓励内地商民到新疆贸易,即下令规定,北路蒙古等愿以牲只到巴里坤、哈密、辟展等处贸易者,俱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给予执照。
其从归化城、张家口等地前往商民,亦照此办理。
时上述两地商民,以领照纡回,往者寥寥。
乾隆皇帝得知情况后,便立即对前述规定作了相应调整,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著传谕直隶、山西督抚及驻扎将军、扎萨克等,旗民愿往新疆等处贸易,除在乌里雅苏台行走之人仍照前办理外,其张家口、归化城等处,由鄂尔多斯、阿拉善出口,或由推河、阿济行走,著各该地方官及扎萨克等,按其道里,给予印照”。
[18]此外,又饬令乌里雅苏台将军,使“贩卖杂货、布匹、茶封之商民等,前赴乌鲁木齐贸易”;“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北路商民销剩余茶,准赴乌鲁木齐等处易换粮食”。
[19]由于新规定的推行,前述地区商人便纷纷涌入新疆。
因最先进入新疆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山西商人,便称其所运之茶为晋茶。
罗迪楚《新疆政见》云:
“新疆自准部用兵,分南北两道,南军由关陇,北军由蒙古及草地,而商路亦遂因之。
南商川、湖、江、豫、晋、陕,由甘肃出嘉峪关至新疆古城;北商奉、直、晋由张家口、归化城,专行草地,所谓山后买卖路,亦至新疆古城”。
“南商运销湖南安化之茶”,故称“湖茶”;“北道运销湖北羊楼峝之茶,在羊楼峝、汉口制造,改称晋茶”。
[20]以上记载,有力地表明,晋茶的来源与甘肃官茶引课,根本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其二、甘肃官茶,基本上都是官商在甘肃官茶局领引后,到湖南安化一带采办,“以散茶装筐,由湖北襄河运上陕西,在泾阳制造成块”,[21]然后经湖南、湖北以达陕甘各省,行销北口、西口。
“行北口者,陕西由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由宁夏府、中卫、平罗等县。
其销西口者,由肃州、西宁等府州各属承引纳课。
”[22]晋茶则不同,其茶大都是山西商人采自湖北、福建等地,在当地自行收购加工,经由河南、山西以达张家口、归化,请领理藩院印票,贩运至新疆各地,《清朝续文献通考》云:
“乾隆五十二年题准:
陕西榆林府每年领引一千道,官商赴湖广买茶,在所属之榆林、怀远各县并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
嗣因蒙古各旗与晋省、归化城壌地相接,该省民人制茶出口,蒙古人等就近买茶,榆林官引壅滞。
自乾隆五十一年为始,将榆林引张内拨出五百道归甘省甘州司入额行销。
”[23]据说著名旅蒙商大盛魁投资设立的“三玉川”茶庄,其据点就设于湖北蒲圻县羊楼洞。
“三玉川”,又名“大玉川”,故址至今还保留着一块乾隆皇帝赐给的双龙石碑,上面镌有该号在贸易中的重要业绩与贡献。
[24]据《旅蒙商大盛魁》一书载,“三玉川”采茶的地方有三处:
湖北蒲圻羊楼洞,蒲圻县与湖南临湘交界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市。
采茶的人小暑去,冬天回来,汉口常住两人,办理运茶和收款等项,主要为大盛魁进货。
[25]从张家口和归化城贩运前往新疆各地的茶叶,部分是由蒙古的骆驼队运输,部分则由归化城商人自养的骆驼队运输。
其中规模最大的骆驼队是元德魁和天聚德。
元德魁商队拥有500峰骆驼,天聚德拥有400峰骆驼。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拥有三四十峰骆驼的商队承担。
[26]方士凎《东归日记》云:
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
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
”“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
茶叶又运至回疆南路八城,获利尤重。
”[27]晋茶与甘肃官茶之不同,此又可资一证。
其三、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官茶多被称为“附茶”,而晋茶则多被称为“杂茶”。
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佐证。
道光二年(1822)冬,陕甘总督那彦成以甘肃官茶积滞,奏请严禁私贩。
时伊犁将军庆祥得知后,随即表示反对。
声言“回疆各城,向准商民贸易,以茶易粮,历久称便”。
今概请严禁,“茶商不能运往该处售卖,以致兵民、回众均形竭蹶,实属格碍难行”。
清廷饬令户部议复。
户部在复文中表示,“著照陕西、甘肃设有茶商、由引之例,即添在新疆地方,令该商承领输课”。
[28]但庆祥非但没有被说服,反而再次上疏表示:
“新疆回夷口食,茶粮最关重要。
自乾隆年间通商以后,历久相安,未便率更成例。
且各城并无殷实土著之户,遽令承充官商,必至运课两误”。
“茶粮既不流通,商货因而滞塞,殊于夷民日用有碍。
”[29]由于他的一再坚持,清廷最后答应“著照所请,准令北路运售杂茶之商民照旧运售,严禁夹带附茶”。
[30]这里所说之“附茶”,显然即是官茶之别称、而“杂茶”则是“晋茶”的别称。
彼此之间,名称不同,号亦各异。
倘若晋茶原属甘茶引课,何以又要如此加以严格区分。
三、史籍上说的“杂茶”是指哪些茶
前已指出,在有关清代新疆茶务记载中,官茶大都被称为“附茶”,而晋茶则多被称为“杂茶”,但究竟哪些茶属于“杂茶”?
史籍说法多不一致。
经初步了解,主要有二说:
一说“杂茶”是指:
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块砖茶等名目。
持其说者为《新疆图志·食货志》。
书中说:
“查甘省官茶,向行西、甘、庄三司,而甘司则直达新疆南北两路,是新疆本官茶引地。
承平时,晋商由蒙古草地兴贩各色杂茶,有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块砖茶等名目,自伊犁地方,官为设局抽税,由将军监督抽税。
”以上所述“各色茶”,实际上又分为“细茶”和“粗茶”两类。
“细茶有红梅、米心、建其等名目,粗茶有砖块、帽盒、桶子等名目。
”[31]
一说“杂茶”是指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等诸色茶。
主其说者为左宗棠的《甘肃茶务久废请变通办理折》。
他在该折中说:
“奸商所领理藩院印票至新疆等处销售”,“原止运销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皆产自闽滇,并非湖南所产,亦非藩服所尚”。
但他又指出:
“该商因茶少价贵,难于销售,潜用湖茶,改名千两、百两、红分、蓝分、帽盒、桶子、大小砖茶出售,以欺藩服而取厚利。
”[32]
左宗棠所说之“六色杂茶”,有的文献则又称为“细茶”,而其所说“潜用湖茶”的千两、百两等,则被称为“杂茶”。
有关这一点,道光八年伊犁将军德英阿在其《稽查北路茶叶大黄章程》中说得最为清楚。
他说:
“查私贩出卡之茶,多系细茶,而杂茶居其少半,如大叶、武彝、六片、白毫、珠兰等项,名为细茶,味最馨而价最贵,每斤值八九钱。
以其性寒,伊犁、塔尔巴哈台兵民、蒙古、回子,向不买食。
至广匣子、千两、百两等项,名为杂茶,价与副(附)茶相等,而贵于大茶、斤茶。
因其捆缚成束,不肯零星挂卖,是以兵民、蒙古、回子,忌不买食。
以上杂茶、细茶,并非兰商官引,运销皆系北商自归化城私贩,运至古城,再由古城搀于杂货,转运伊犁等处。
”又云:
“大茶、斤茶,统名砖茶,每斤价值二钱一二分不等,兵民买食最为便利,虽非兰商引运,但久经北商运卖,应准嗣后专卖。
”[33]
德英阿与左宗棠的说法,表面上看虽然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其差别完全是由于两人着眼点不同造成的。
因为前者是从官茶与晋茶关系说的,后者则是从茶叶原料及加工工序上看问题。
这就是说,左氏所说之“晋茶”,实际上也包括粗、细两种茶在内。
何谓“细茶”?
所谓“细茶”,其实包含着两重含义:
一是叶料细嫩,二是加工精细。
宗景藩《种茶说十条》云:
“凡细茶,当茶芽初出极嫩时采摘。
清明前采者曰明前,谷雨前采者曰雨前,即《茶谱》所谓旗枪、雀舌等类。
此茶之最细最嫩者,采成后用手揉软,以铁锅微火轻轻搅炒,待半干时取出,用炭火焙干,拣去粗梗,用纸包固,以石炭贮缸内”,“可以久藏”。
“三月为头茶,可做青茶。
四月底五月初为二茶。
六月初为荷花,七月初为秋露,均做红茶。
”[34]从以上记载中不难看出,凡是炒青茶及红茶类茶,大体上都属于细茶之列。
粗茶则相反,一般是指叶料老、加工粗糙之茶。
凡属黑茶类茶,大都是粗茶。
粗茶多数都是砖茶。
说起砖茶,学术界大都断言始于同光年间。
在笔者看来,其说颇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当道光初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时,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便在其给清廷的奏折中说:
“请准商民,仍循旧规,驮载砖茶,前赴古城兑换米面。
”清廷敕令户部议覆。
户部在覆文中称: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准侵越新疆各城。
”果勒丰阿接到咨文后立刻又奏:
“此项砖茶,系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交纳关税,贩运来营贸易,迄今六十余年,均系以货兑货,向不使用银两,今一旦全行禁止,该处数万蒙古民人,糊口无资,必致失所,均系实在情形。
”清廷接奏后,考虑到“若照旧规,尽数运往,究恐充斥官引”。
但若不令行销,又恐于蒙古、民人生计有碍,于是饬令“著照所请,准其商民等每年驮运砖茶七千余箱,前赴古城兑换米面”,“以资接济”。
[35]据果勒丰阿所奏内容,我国砖茶至少在乾隆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了。
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一书指出,嘉道时期,在湖北蒲圻县羊楼洞地方已发现有山西商人在当地自制砖茶记载:
茶“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
[36]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推定砖茶始于同光年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史料记载,白毫是我国的重要特产,在茶叶分类学上隶属白茶类,是一种轻微发酵茶。
其茶分芽茶与叶茶两种。
典型的芽茶外形色白如银,挺直如针,十分名贵。
叶茶是以一芽二三叶或单叶制成,外表白色茸毛密布,极为素雅,向以福建所产最为著名,颇受中亚各族及俄罗斯人所喜爱。
[37]
武彝,又作武夷,以产于福建崇安县武夷山一带著名。
其茶萌芽于宋,著于清,是一种半发酵茶,俗称“乌龙茶”。
以外形色泽乌褐,世又称为“青茶”。
因制作工艺独特而驰名海内外。
其清香颇似绿茶,而浓醇则又很像红茶。
珠兰,清代主要花茶类之一。
以其入花之茶称“珠兰”,故名。
珠兰属金粟兰科,常绿小乔木,叶对生,初夏开花,极芳香。
用以入茶,茶味芬芳旭郁,隽永持久,很受人们的青睐。
主要产于安徽歙县、福建漳州等地。
香片,与德英阿所说之“六片”,似属同一类。
亦为花茶类之一。
入茶之花除珠兰外,还有茉莉、米兰、桂花和玫瑰等多种,向“以福州附近出产为最多”。
[38]此前所说之“红梅”,当亦为其中之一。
大叶,又称叶茶,以摘二三叶而加工较粗之茶,大都为炒青绿茶。
普洱,因产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县得名。
以制茶工艺独特,味道浓郁,向为清朝统治阶级所珍爱。
茶农每年都要将春天最好的茶芽、蕊茶加工后入贡,然后再将其余之茶叶经杀青后制成毛茶,加工成型。
以上所述各茶,就是左宗棠称为“杂茶”而德英阿则称为“细茶”之茶。
米心,又称米砖,是以红茶末加工制成,主要产于湖北蒲圻一带。
旧分“72米砖”和“48米砖”。
砖模棱角分明,纹面图案清晰秀丽,色泽乌亮,汤色红浓,味道醇厚,[39]深受哈萨克族人的垂青。
米心虽是砖茶,但因其原料为红茶末,是以《新疆图志》将其列为细茶。
“千两”“百两”,又称“花卷”。
之所以称其为“千两”“百两”,是因其一卷茶合老秤六十二斤半,恰为1000两或100两。
该茶原是以优质黑毛茶为原料,用棍锤筑制在长筒形的篦篓中,以外形酷似木墩,故又有“木墩茶”之称呼。
[40]后因将卷型改为砖型,四面又有显形花纹,因而又称为“花砖”茶。
主要产于湖南及安徽等地。
晋商所贩运之千两、百两,大都来自安徽建德一带。
《筹办夷务始末》云:
“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走西疆之商人,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
”[41]
帽盒茶,是指外形酷似圆柱状之茶。
据说该茶产生于明代中叶,是湖北青砖茶的前身。
[42]乾隆年间湖北蒲圻县羊楼洞一带,每年已可生产10万盒。
桶子茶,又作“筒子茶”或“洞砖茶”,是指其造型酷似桶子状之茶,大都为湖北蒲圻县羊楼洞等地所产。
因砖茶外面常印有“川”字商标,故又有“川”字茶之称,向有“二七”“三九”(每片2公斤)、“二四”“三六”(每片1.5公斤)四种规格。
光绪五年,左宗棠在其《覆陈边务折》中说:
“惟南疆吐鲁番八城缠回,见砖茶则喜,谓承平时湖茶非私贩筒子茶可比,惟地方新复,销数尚未能畅。
”[43]
大小块砖茶,又称大茶、斤茶。
而蓝分、红分,目前尚不知其所自出。
以上所列,即是前述所说之粗茶。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晋商所贩运之茶叶,不但种类繁多,而且质量大都比较精细。
这就不难看出,晋茶的销路之所以一直比官茶好,除笔者以前所述诸因素外,与其茶叶种类繁多显然也有着重要关系。
因为人们居地不同,族别各异,其嗜好往往亦会有所不同。
种类多,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伊犁产茶说揭秘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雨水稀少,气候干燥,高山终年积雪,从不产茶。
其所需茶叶,向皆取之于内地各省。
然而在咸丰朝时期,却在不少史籍中出现了伊犁产茶记载,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连清朝政府亦信以为真,一再下令要求新疆地方官府将产茶情况上报,令其每年交纳茶税,从而成为新疆茶务发展史上的一大要闻。
其实,这纯粹是一场闹剧。
伊犁产茶之说最早见于咸丰六年(1856)。
倡其说者为当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
《清文宗实录》咸丰六年条载:
谕军机大臣等,“札拉芬泰奏,伊犁地方出产茶斤,商民人等采取售卖,拟酌征商税一折,自系为裨补经费起见,向来何以并未议收税。
其每年计产茶若干,约收税课若干,该将军尚未能知其数,现拟试行收税,务须详加体察。
如果舆情称便,并无窒碍,再行妥议章程具奏。
伊犁地处边陲,民间贸易,与外夷交涉,倘行之或有流弊,不可规目前之小利而贻患于后日也。
将此谕令知之”。
[44]
从以上谕示看,清廷最初并不完全相信所奏是实情,故特令其慎重从事,不可贸然采取行动。
但札拉芬泰并不以为意,当接到谕示后又上书称:
“伊犁地方辽阔,此种茶斤产自山沟,商民采取,实自近年始行查出”。
“伊犁商民于附近采造,尚不甚费工本,虽制造成色不等,均堪饮用。
兹据按成征收茶斤,一经报税,即系官茶,商人既乐于费少,小民亦乐于费廉,察之舆情,无不同声称便。
”又云:
此项茶斤,“今拟因地制宜,仅按成抽征茶斤,即在奴才衙署之旁,设立税局,遴委妥员常经理,令商民随时赴局报明茶斤数目,其成色约分上、中、下三等。
请自咸丰七年为始,每茶十分,抽茶一分半,以期立法简便,不至扰累商民”。
[45]
据记载,税局为了征收税课,还制木戳一颗,上刻“官茶图记”四字,印于茶票之上。
票内编列号码,以备查验。
票面有满、汉字体,其文曰:
“为茶票事,照得伊犁近产茶斤,业经奏明按成抽税在案,合行给发茶票,以杜偷漏假冒之弊。
嗣后贩茶商民,慿此查验,其无印票者,以私茶论。
倘敢伪造,严拿从重治罪。
”[46]
税课的征收,前后实施了四年。
第一年(咸丰六年),抽茶17100斤;第二年(咸丰七年),抽茶15500斤;第三年(咸丰八年),抽茶8800余斤。
第四年(咸丰九年),抽茶1800余斤。
第五年因产茶种绝,无人入山采茶,被迫停其税课。
[47]不久由于各地农民起义蜂起,政局动荡不安,其事无人过问。
及新疆置省,为解决新疆茶叶的输入与供应问题,户部饬令于当地植茶,设局抽税,始又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
时刘锦堂任职新疆巡抚,他接到咨文后,立刻派人到伊犁调查,其事遂大白于天下。
光绪十一年(1885),刘氏在有关新疆情形折中说:
“至种茶一节,前准部咨,饬属查复,佥称南北两路,从未种过茶树。
缘茶性喜暖,关外雪地冰天,寒冷倍于关内,种植本不相宜。
”“又部咨,内称伊犁地方出产茶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