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易卜维在狱中易如玉.docx
《我的哥哥易卜维在狱中易如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我的哥哥易卜维在狱中易如玉.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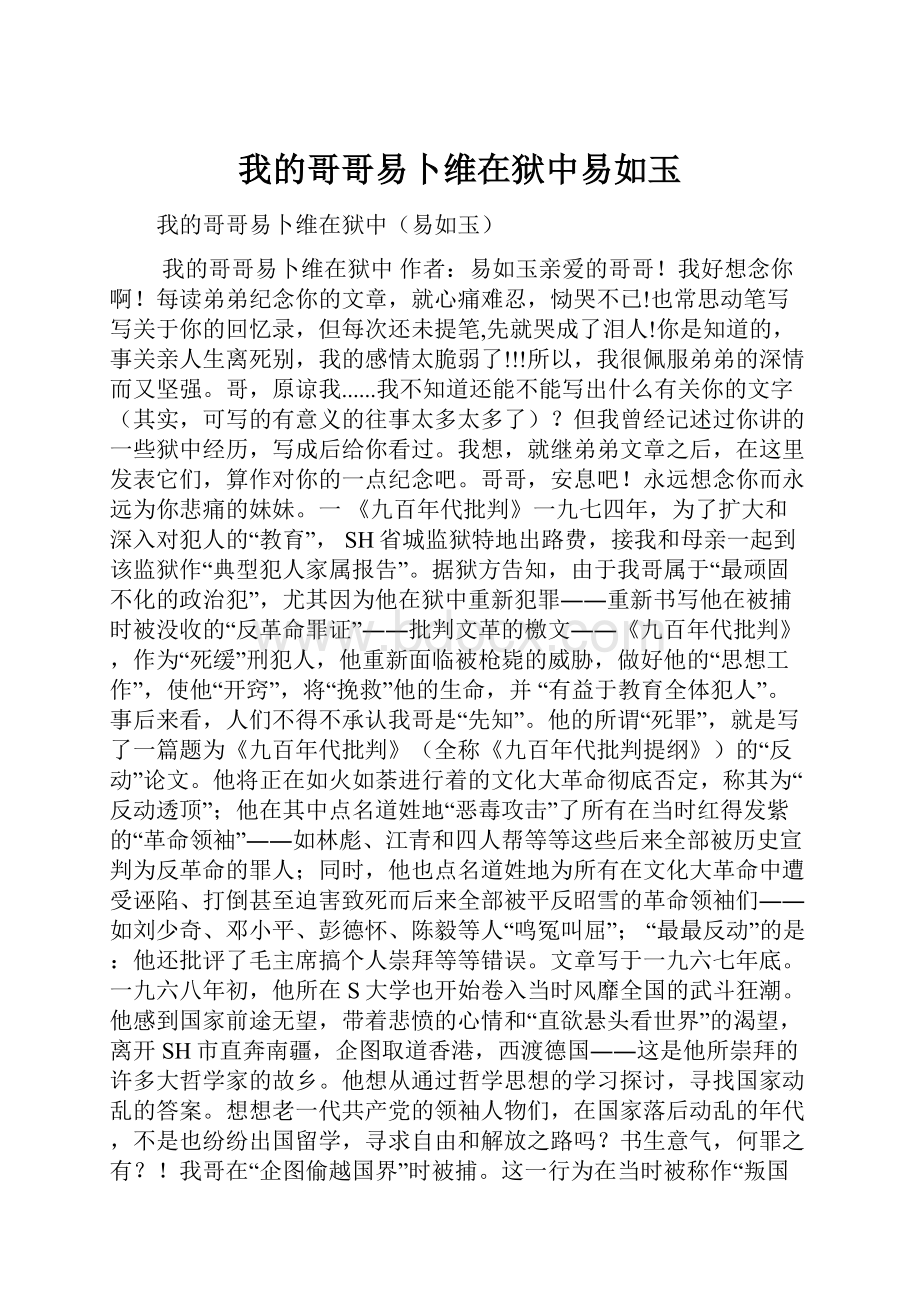
我的哥哥易卜维在狱中易如玉
我的哥哥易卜维在狱中(易如玉)
我的哥哥易卜维在狱中作者:
易如玉亲爱的哥哥!
我好想念你啊!
每读弟弟纪念你的文章,就心痛难忍,恸哭不已!
也常思动笔写写关于你的回忆录,但每次还未提笔,先就哭成了泪人!
你是知道的,事关亲人生离死别,我的感情太脆弱了!
!
!
所以,我很佩服弟弟的深情而又坚强。
哥,原谅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写出什么有关你的文字(其实,可写的有意义的往事太多太多了)?
但我曾经记述过你讲的一些狱中经历,写成后给你看过。
我想,就继弟弟文章之后,在这里发表它们,算作对你的一点纪念吧。
哥哥,安息吧!
永远想念你而永远为你悲痛的妹妹。
一《九百年代批判》一九七四年,为了扩大和深入对犯人的“教育”,SH省城监狱特地出路费,接我和母亲一起到该监狱作“典型犯人家属报告”。
据狱方告知,由于我哥属于“最顽固不化的政治犯”,尤其因为他在狱中重新犯罪――重新书写他在被捕时被没收的“反革命罪证”――批判文革的檄文――《九百年代批判》,作为“死缓”刑犯人,他重新面临被枪毙的威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使他“开窍”,将“挽救”他的生命,并“有益于教育全体犯人”。
事后来看,人们不得不承认我哥是“先知”。
他的所谓“死罪”,就是写了一篇题为《九百年代批判》(全称《九百年代批判提纲》)的“反动”论文。
他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称其为“反动透顶”;他在其中点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了所有在当时红得发紫的“革命领袖”――如林彪、江青和四人帮等等这些后来全部被历史宣判为反革命的罪人;同时,他也点名道姓地为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诬陷、打倒甚至迫害致死而后来全部被平反昭雪的革命领袖们――如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人“鸣冤叫屈”;“最最反动”的是:
他还批评了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等等错误。
文章写于一九六七年底。
一九六八年初,他所在S大学也开始卷入当时风靡全国的武斗狂潮。
他感到国家前途无望,带着悲愤的心情和“直欲悬头看世界”的渴望,离开SH市直奔南疆,企图取道香港,西渡德国――这是他所崇拜的许多大哲学家的故乡。
他想从通过哲学思想的学习探讨,寻找国家动乱的答案。
想想老一代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们,在国家落后动乱的年代,不是也纷纷出国留学,寻求自由和解放之路吗?
书生意气,何罪之有?
!
我哥在“企图偷越国界”时被捕。
这一行为在当时被称作“叛国投敌”,何况还从他身上搜出了那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九百年代批判》,真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一九七O年,在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上,我哥被判“死缓”(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他仍然深信自己观点正确,在狱中服刑第二年期间,居然置死刑于脑后,决心重写他那被没收的《九百年代批判》!
他把床单一次撕下一小块,然后伺机用蚂蚁般的小字,将自己烂熟于心的观点密密麻麻写在上面。
每写完一片布,他就借“整理内务”的机会把它缝进被褥。
就这样,他视时刻处于生死边缘的危险境地于不顾,不到一年时间,他竟然再次写出了十万字全面透彻批判文革的檄文!
在其“反动”文章即将重写完毕时,一次,他把写完的布片收进内衣上兜,准备等机会缝进被褥。
但是,没想到那块布片掉在了地上并被人拾起,而我哥却没有察觉!
又由于他总是不拆洗褥子而被人怀疑和告密,于是狱监强行拆开其褥子,“罪行”终于暴露了――褥子里居然铺满了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布片!
他死在临头竟然还敢大肆“重新犯罪”,这使狱方和所有人都十分震惊――我以为这是一种大无畏英雄气概的惊天动地!
!
!
从世俗的现实角度来看,我哥当时的行为有点儿像张志新,未免过分书呆子气――纯粹是鸡蛋碰石头——傻呆了。
但是,正是这种书呆子气,使中国人在每一次与专制邪恶进行斗争的黑暗时刻,多少还能听到一点儿出自真理和正义的声音!
他面临着死刑的执行。
然而,对是否立即将其处死,狱方颇为犹豫和矛盾。
因为我哥平时外表上“服刑态度较好”,而且在各方面都有持续而突出的“带罪立功”表现。
我哥在大学是数学系的“尖子”,聪明过人,才华横溢。
他不仅数、理、化好,对电学和机械原理颇有研究,其文学和哲学造诣也相当高――他会作诗填词,精读过许多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列著作。
平反出狱后,一开始他被学校分配在图书馆打杂儿。
后来,校内各科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课竟无人能教,所有被请来讲课的老师都被研究生嘘走了。
当时哲学系的系主任忽然想起一个人,就是我哥。
他知道我哥数理化好,又懂哲学,也许……于是他就去请我哥。
我哥说,试试看吧。
这一试,就使他在二十多年中成为各系硕士(当时该校部还不能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课的唯一导师。
由于“自然辩证法”课的自身特点,需要其教师懂得数理化等多种科学学科的知识,并需要其教师不断关注现代最新和尖端科学成果,才能使各科学生对其讲授感到满意。
所以,该科教师仅有哲学功底是不够的。
学生这样评价我哥的讲课水平:
数学系研究生说我哥原来是学数学的;物理系研究生说我哥原来是学物理的;化学系研究生说我哥原来是学化学的……恐怕这就是对一个“自然辩证法”教师讲课水平的最高赞誉。
二文武双全在狱中,我哥不仅负责犯人的文化学习,并负责管理其所在中队的电工和汽车维修。
在其指导和组织下,有关班组的工作有条不紊,不但没有发生过事故,维修质量也大大提高。
监狱的管理人员视其“人才难得”,就尽量利用他的多种专长。
他们曾请他辅导监狱管理人员的准备考大学的孩子学习数理化,而经他辅导过的孩子多能顺利考取,使他更得人心。
最令人感到赞叹的是:
在狱中关了多年的他,在与世隔绝、没有任何信息和参考书的情况下,这个曾经的数学高材生,竟在狱中展开了对一道世界级数学难题――“Cantor连续统猜想”的研究、解析,并得到某些结果。
他要求狱方将其结果拿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去认证。
对我哥的学问十分信服的狱领导毫不犹疑,立刻派人“出差”北京。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专家审查后告知:
这一著名的“数学猜想”已在1964年被国外的数学家解决了。
由于我国一直闭关自守,国外的科学信息阻滞,又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所以我哥无法知道他所做的研究已毫无意义。
但是,数学研究所的专家对这个狱中学子仍表钦佩。
他们认为在监狱那样闭塞而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任何参考书和信息来源,仅凭个人能力,完全独立地进行这种高难度的数学逻辑推理解析,其思路虽不完全准确,却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其聪明才智和勇敢精神已属少有和难能可贵。
他们的夸奖使狱方对我哥更加刮目相看。
所以,无论是犯人还是管理人员,对这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有种特殊好感。
尤其是犯人,他们不仅在懵懂中毫不含糊地知道这人的学问令他们望尘莫及,而且,他们也曾在倒抽冷气中毫不含糊地领教过这个戴眼镜儿知识分子的蛮勇和厉害――他被逼急了时比谁都更玩儿命。
他入狱不久,尚在另一监狱关押时,曾遇到一些专爱寻隙闹事欺负人的流氓刑事犯的不断挑衅,不得不经常和他们打架斗殴,因此受到连续多次“批斗”。
我哥知道这是他们故意陷害。
他忍无可忍,决心孤注一掷,狠狠反击。
一天,他在工作时藏起一把斧子并设法带到宿舍,偷偷放到被褥下面。
当这伙流氓中的一个打头向他挑衅并示意其他人一起动手打他时,他突然跳到床前,抽出磨得锋利的斧子,高举过头,用平时从未有过的凶狠腔调咬牙切齿地说:
“告诉你们这些兔崽子,今天谁要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就立刻让他见血!
我豁出这条命了,谁不信就试试看!
”看着那把高高举起的利斧、那寒光流闪的刃口,还有谁敢不信?
我哥从小注重锻炼身体,体格健美,浑身肌肉坚硬结实,胳膊和手劲儿特大,能一口气做五六十个俯卧撑。
掰腕子也很少有人能掰过他。
我能想象他那肌肉隆起的两只胳膊举着闪亮利斧的样子――肯定让那些欺软怕硬的痞子们印象深刻。
那伙流氓立刻呆住了,宿舍里几十口人鸦雀无声。
有向着我哥的人早就偷偷跑去报告事发经过,强调我哥是被迫自卫。
来了好几个狱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场可怕的恶斗。
他们早就知道那帮流氓阴坏,讨厌透了这号人。
他们表面上严厉批评我哥,并给予处分,实际上同情他。
当然他们也狠狠数落了那伙流氓一顿,说他们挑起事端,故意寻隙闹事等。
后来有好心的狱管劝我哥:
“像你这样的知识人,不值得为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毁了自己。
”我哥的厉害名声在犯人中传开了,从此没人再敢惹他,反而有更多人佩服他,凡事都来向他求教。
狱方交给我哥管理的活儿,也被他调教下的犯人完成得更加顺利而出色。
在SH市监狱,我哥非同寻常的文化知识更加受到狱方重视和利用。
有些文化水平低的刑事犯,在我哥的细心调教下,甚至精通了电工或汽车修理,我哥还经常给他们灌输一些今后应如何自食其力、正经做人的道理。
那些原本粗野鲁莽、桀骜不驯、很少服理的汉子们,却能多少听进我哥的话。
一些人出狱后确实就开始凭着这些本事挣饭吃了。
其中有人甚至自己当老板开了汽车修理铺,并因此大发了。
我哥平反出狱后,这些人经常怀着感激和崇拜的心情,提拉着大包小包去看我哥――拜见“恩师”。
我哥虽已在大学任教,却仍视他们为好友宾客,继续勉励他们不断上进……三单独禁闭――征服人间炼狱狱方确实不忍杀死这个真正的才子。
我见过他们的F副狱长,一个中年人,大学毕业生,谈吐中见出修养不凡。
我深信:
只要有点儿文化水平的人,看过我哥写的《九百年代批判》,无论他们表面怎样称其“反动透顶”,内心里都会对这篇富有深刻哲理、高度逻辑思维和非同凡响的见解的论文暗暗称奇甚至赞赏――凡真理之光,即使在黑暗时代,仍能穿透人心。
起码,他们对他在劳动管理中的出色表现十分满意。
他们决定努力“挽救”他。
于是没有对他“立即处死”,而是给了他整整一年“单独禁闭”的处罚。
我哥说,这种禁闭处罚仍然极其可怕。
首先,他被戴上脚镣手铐。
手铐戴了半年。
开始是两手后铐,不久后改为前铐。
可能要表示对重新犯罪的严厉惩罚,后铐时,他戴的烤是小号的,紧紧箍在手腕上,很快就把手腕勒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疼痛难忍!
但我哥就是忍住了,没有哀求换烤。
一个人单独禁闭时,后铐,意味着什么?
首先,洗漱就全免了;解手,你就自己想法儿磨蹭吧;吃饭,只能跪着或侧卧着,用嘴去抅饭盆儿,舔着吃!
你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吗?
那你就受用去吧!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胆敢反对它的人,都活得不像人样儿!
生不如死,你还反对个啥?
!
连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勋彭大将军胆敢“反对”它时,都照样如此专政!
你易卜维算老几?
无产阶级专政对待其敌人,绝对没商量。
脚镣在我哥脚上戴了整整一年。
一开始,冰冷坚硬的脚镣不断把我哥的脚踝磨得血肉模糊,痛彻心骨,而双手后铐的他却无可奈何。
其次,这间“10号”禁闭室高高的屋顶上有一圈铁窗,但铁窗上没玻璃也没纱窗,冬天北风夹雪花呼啸着灌进来,冷如冰窖;夏天太阳直晒,热气腾腾,犹如蒸笼;从毫无遮蔽的铁窗间自由飞进的蚊虫如麻,在周围铺天盖地嗡嗡乱叫,尤其晚上,咬得人根本无法入睡。
他说,他只能白天睡觉,从傍晚开始,就得彻夜进行人蚊大战,不断拍打蚊子,或者两手举在头顶转圈儿抡衣服哄蚊子――他就当这是“锻炼身体”。
他说,在这里关禁闭的人只给一床薄被,一条布床单,没有褥子和枕头,就这样睡在冰冷的水门汀地上。
几乎所有在这里被关禁闭一年的人,都是“走着进来,抬着出去”――不是得风湿病、肾炎,就是其他各种怪病,甚至全身瘫痪。
只有他,一年以后照样自己夹着铺盖卷儿、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所有人都不得不佩服他!
他说,他的办法就是坚持锻炼,如原地跑步、做俯卧撑等。
我哥说,当后铐改为前铐时,似乎是那个狱管人员看不过去他手腕上的伤口,有意给他戴了个大号手铐。
在给我哥戴手铐时,他曾将手铐在我哥手腕上来回捋了好几下,似乎暗示“手铐很松”。
因此,只要在手腕上吐些唾沫,以使润滑,很轻易就能把手铐退下来。
所以,每到夜里我哥就退下手铐,以便“自由活动”,到早晨再戴上。
我哥对那个好心的狱管人员深怀感激。
可见,在任何地方都有人性的闪光。
至于脚镣,我哥也设法把它打开了:
他在院子里“放风”时,偷偷捡了一块碎瓷片,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就用这块瓷片将一只脚镣上的铆钉头磨秃了,退下一只脚镣,他就可以活动自如。
白天,他用破布条系住这只脚镣,不使人发现破绽。
因为犯人用布条包缠脚镣,以免磨破脚腕是常有的事。
更妙的是,他在监狱劳动时,曾做过“长远”打算:
他趁工作之便,把自己的塑料鞋底整个儿剖开,把一根短钢锯条夹在里面,然后用电焊加热塑料鞋底,使之重新粘合,但留了一个小缝,以便不时之需。
现在,他把锯条抽出来,准备爬到铁窗上进行一项具有极大危险性的活动――锯断窗口的铁条!
一开始,他更多的还是出于“好玩儿”心理――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和诱惑性,因而具有娱乐性,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在漫长而无聊的岁月中,何乐而不为呢?
他把唯一的床单撕成一条条,搓成长而结实的“绳子”,把一头打结成疙瘩。
利用疙瘩的重力,他不断把绳子甩向高高的铁窗,练习能用绳子准确地穿过其中一条铁栏杆,恰好铁窗外面斜支着一块铁片挡板,只要准确用力一甩,绳子就从两条铁栏杆中飞出去,击中挡板并反弹回来,并恰好穿过一条铁栏杆,再从另一个空裆中穿回来,绳子有疙瘩的一头就坠落下来,再抓住它系一个活扣并拉动绳子,使活扣上升并系牢在铁窗上。
他就可以沿着绳子爬上去。
反正晚上无法睡觉,他就反复练习。
后来,他终于技巧熟练,三下两下就能让绳子按照自己的设想准确回落下来。
在铁窗上系牢绳子,他就轻易地爬到窗口。
爬绳运动本是他的体育课强项,他能双脚悬空、一口气爬到顶。
然后,他拿出还是崭新的钢锯条,开始锯窗户上的一条铁栏杆。
除了白天两次送饭,根本没人光顾这个铁笼般的禁闭室。
他每晚锯一点儿,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就把它锯断了,然后又如法炮制锯断另一根。
最后,当他被放出禁闭室、直到被释放出狱时,也没有人发现那里有两条铁窗栏杆是被锯断的。
至于那条床单,他把它从绳子还原为布条,并有意撕得更碎――一年只用一条被单儿,用烂了不足为奇。
脚镣、手铐都打开了,铁窗也锯断了,他开始打算逃跑。
虽然他清醒地知道,成功的概率极小。
一旦失败,他就必死无疑。
但是,对于一个时刻与死亡摩肩接踵、极其渴望自由的人,极小的成功率仍有巨大诱惑。
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就在他竭力精确地谋划如何逃跑时,一天,狱管人员带他到办公室并对他说,由于他“表现不错”,决定给他去除脚镣!
我哥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急中生智,马上“坦白交待”说,他自己早就把脚镣打开了,因为曾想逃跑。
但是后来觉悟到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所以决定不逃跑了。
狱管人员竟然又以“坦白从宽”饶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处罚。
不久后的一天,他“放风”回来,没听见号子上锁的声音。
他过去轻轻推了推门,果然,门没有锁!
难道是狱管人员“忘了”上锁?
我哥本来聪明过人,此时他立刻敏感到:
似乎有种预谋的危险正在等待他――他可能面临一个恶意的死亡陷阱――只要他向“自由”跨出一步,他的生命就可能完结!
一瞬间,面对着自由的召唤和死亡的恐怖,他下意识地浑身战抖,沁出一身冷汗。
他竭力使自己在理智中平静,然后对着门外大声喊道:
“报告,10号门没上锁!
”他听见狱管人员在洋灰地上“呲啦、呲啦”走过来,随后“咣当”一声,门被锁上了。
狱管人员一声儿没吭――这显然是个阴谋!
后来,这想法被证实了。
他出狱后,SH市监狱的T股长曾告诉他:
当时监狱也和全国一样,分为两派。
以F副狱长为代表的一派坚持宽大政策,反对处死我哥,要求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另一派则执意要求处死我哥,以示对“重新严重犯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那个“死亡陷阱”正是他们布置的。
如果当时我哥迈出狱门,他就死定了。
四重见天日当他从禁闭室放出来后,狱方就派人到北京我母亲家中找到母亲和我,说明来意。
我和母亲听说我哥“重新犯罪”的“事实”后,不禁一身冷汗,为他感到后怕。
我们千恩万谢地表示一定支持狱方对他所进行的“挽救生命”的工作……于是我和母亲就马不停蹄打点行装(主要是采购准备了很多给哥哥的日用品和比较解馋又有营养的食品),坐火车赶往石家庄。
F副狱长、T股长和其他领导亲切接见了母亲和我,并叫我在全体犯人面前作“家属报告”。
因为他们知道我也因“反革命罪”住过监狱,而现在“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成为一名大学教师。
这说明:
“只要好好改造”,“反革命”也“前途光明”。
按照其意图,我当夜挥笔疾书,立马写就一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家属规劝政治犯之典型讲演稿――这对饱经运动历练、已深谙文革本质的我来说,实乃“小菜一碟儿”。
讲演稿上交后,即受到狱领导高度赞扬。
副狱长情不自禁地对我母亲说:
“你的孩子个个儿都有学问哪!
”母亲听了非常得意,以致冲淡了此行内涵的悲剧色彩。
当然,“报告”极为成功。
我“声泪俱下”,表演出色。
后来我哥说,当时他就听明白也想明白了,为了亲人,他要保全自己。
于是,此后他“番然悔悟”,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他的表现令有心保护他的狱领导大感欣慰--其实,他们心里准跟明镜儿似的,不管真假,他们就希望我哥别钻牛犄角儿,以便他们有可能给他留条活路。
互相默契配合,戏才能演得逼真!
在那个年代,善良人性必须以化妆的形式表现之。
加之国内形式的不断演变,我母亲的不断上书申述和狱领导的积极配合,我哥终于从“死缓”改判18年监禁。
邓小平上台执政后,政治形式又有明显变化,中国人开始感到有了希望。
我母亲怀抱这一线希望,继续夜以继日地为我哥再写申诉信。
当时我们兄弟姊妹学习工作都很忙,她就独自承担解救大儿子的重任。
她怀着深厚而执拗的母爱,殚精竭虑。
由于不断熬夜书写,删改誊抄,她几乎双目失明。
她集中自己一生的聪颍才智和文采,凭着在文革的悲惨经历中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以严密的逻辑、简洁的语言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写就了一篇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感人至深的申诉信。
这封申诉信终于打动了一颗伟人的心,从而使我哥在监禁十一年后,“提前获释”。
当时我妹妹宓正在北京师大历史系读书,恰好刘少奇的一个儿子与她同班。
他毫不犹豫地帮我妹将这封申诉信交到“邓小平办公室”。
我哥出狱后,T股长告诉我哥说,邓小平曾亲自在我母亲写的申诉信上签署了“着高检查办”五个字。
当时的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立刻派了两人前往SH市监狱,查看了有关我哥的“犯罪记录”并进行了详细调查。
邓小平的批示使那些曾经努力保住我哥生命的狱管人员深受鼓舞,感到非常欣慰。
在SH市监狱领导善意而积极地配合下,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哥――被关了整整十一年的“罪大恶极”的“政治囚犯”,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
他的无罪释放曾在SH市监狱造成轰动--典型的蒙冤政治犯啊!
我们家族的“反革命历程”,终于画上最后的句号。
有趣的是:
他所在S大学派来接他出狱的那辆破吉普车,正是十一年前送他入狱的那辆,连开车的司机都是原版!
应该说是“人是物非”啦!
他的“平反”工作也与众不同,进行了两次:
第一次只给他“大部分平反”,留了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尾巴”,因为他在预言书般的《九百年代批判》中,不仅全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批评了毛主席的一系列错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有关方面又给予他第二次“彻底平反”――因为他对毛主席和“文革”的所有批判,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批评奇迹般地吻合!
国内有位著名作家,听了我哥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啧啧称奇,想为他写一篇纪实小说,但我哥拒绝了。
他准备自己写。
我想那一定非常精彩。
不过这将是后话了......尾声我在狱中演讲结束后,回到狱方给我安排的贵宾席时--正好面对着黑压压一片规规矩矩坐在各自小马扎上的犯人--我漫不经心极其随意地扫了一眼这些可怜见的犯人--刹那间,我的心脏几乎停跳--我看见:
在穿着一律的犯人堆儿中,在最后一排,竟然坐着我的大学同学--曾经的好朋友、我心目中一缕阳光般才华横溢的诗人郎郎!
六年前,即那个红色风暴遮天避日如火如荼席卷全国的一九六八年,我以“郎郎反革命集团”同伙罪入狱仨月,出狱后即听说他被判死刑。
兔死狐悲,心常戚戚。
分手六年、生死两茫然之际,竟然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情景中不期而遇--实在太富戏剧性了!
监狱领导当然对我们的“反革命关系”了如指掌。
为了不让我看见他(也许是怕影响我的情绪从而影响演讲效果吧),曾煞费苦心地做了种种安排(见郎郎著《我和易先生的故事》)。
可是,他们低估了画家的眼睛和艺术家的敏感值……由于这属监狱演讲之戏中又一齼戏了,就请看官且听下回分解吧。
1999年11月,写于北京双榆树杨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