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下.docx
《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下.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下.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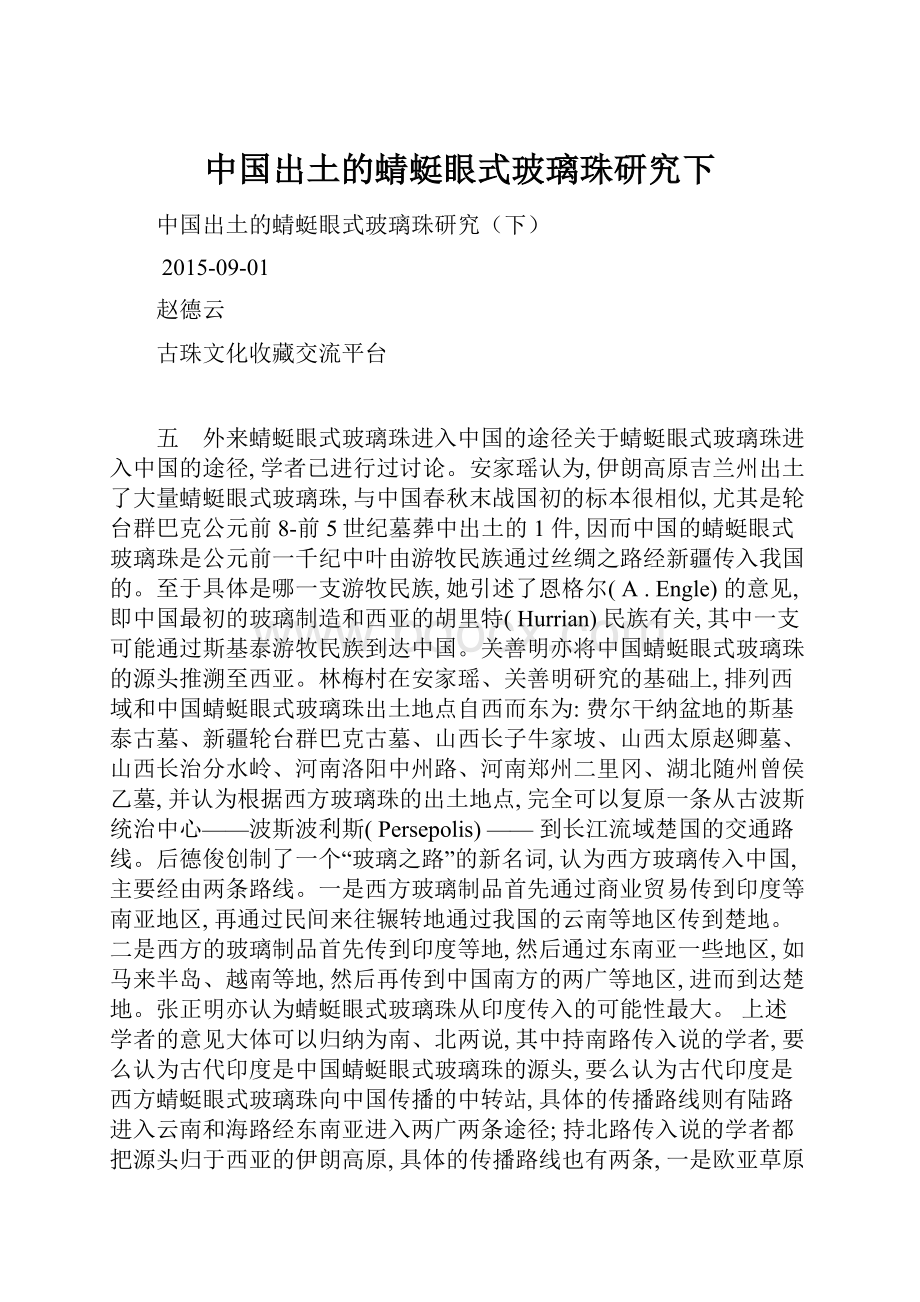
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下
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研究(下)
2015-09-01
赵德云
古珠文化收藏交流平台
五 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的途径关于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的途径,学者已进行过讨论。
安家瑶认为,伊朗高原吉兰州出土了大量蜻蜓眼式玻璃珠,与中国春秋末战国初的标本很相似,尤其是轮台群巴克公元前8-前5世纪墓葬中出土的1件,因而中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是公元前一千纪中叶由游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经新疆传入我国的。
至于具体是哪一支游牧民族,她引述了恩格尔(A.Engle)的意见,即中国最初的玻璃制造和西亚的胡里特(Hurrian)民族有关,其中一支可能通过斯基泰游牧民族到达中国。
关善明亦将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源头推溯至西亚。
林梅村在安家瑶、关善明研究的基础上,排列西域和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出土地点自西而东为:
费尔干纳盆地的斯基泰古墓、新疆轮台群巴克古墓、山西长子牛家坡、山西太原赵卿墓、山西长治分水岭、河南洛阳中州路、河南郑州二里冈、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并认为根据西方玻璃珠的出土地点,完全可以复原一条从古波斯统治中心——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到长江流域楚国的交通路线。
后德俊创制了一个“玻璃之路”的新名词,认为西方玻璃传入中国,主要经由两条路线。
一是西方玻璃制品首先通过商业贸易传到印度等南亚地区,再通过民间来往辗转地通过我国的云南等地区传到楚地。
二是西方的玻璃制品首先传到印度等地,然后通过东南亚一些地区,如马来半岛、越南等地,然后再传到中国南方的两广等地区,进而到达楚地。
张正明亦认为蜻蜓眼式玻璃珠从印度传入的可能性最大。
上述学者的意见大体可以归纳为南、北两说,其中持南路传入说的学者,要么认为古代印度是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源头,要么认为古代印度是西方蜻蜓眼式玻璃珠向中国传播的中转站,具体的传播路线则有陆路进入云南和海路经东南亚进入两广两条途径;持北路传入说的学者都把源头归于西亚的伊朗高原,具体的传播路线也有两条,一是欧亚草原路,二是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
首先看南路传入说。
古代印度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拉吉哈特(Rajghat)、乌贾因·阿希切等遗址均有发现,但数量不多,其中年代最早的出土于塔克西拉,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因此有学者指出,这些数量不多的发现是从远方输入,并非本土生产,其来源地更有可能是波斯而非地中海沿岸。
印度学者大多接受这个观点,并认为阿育王(Asoka)时代(公元前3世纪)与波斯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印度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极有可能是此时才从波斯大规模输入。
中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出现的年代远早于塔克西拉的标本,更不用说阿育王时代,因此认为古代印度是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源头的意见不攻自破。
从印度到南方沿海海路沿线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非常少。
根据弗朗西斯(PeterFrancisJr)的研究,可以举出的例子都是马赛克蜻蜓眼式珠(MosaicEyeBead),如曼泰(Mantai)遗址出土的一件被确认为是罗马产品。
另外在东南亚的一些玻璃制造中心,如马来西亚的桑给玛斯(SungaiMas)、泰国的竹古巴(TakuaPa)还可能生产过蜻蜓眼式玻璃珠。
前者的年代可早至4-5世纪,但兴盛时期在10-11世纪(图一九,2-4);后者的产品被弗朗西斯称为“竹古巴蜻蜓眼式珠”(TakuaPaEyeBead)。
马赛克玻璃制造技术虽然历史悠久,但其大规模出现是源于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亚历山大城的某种复杂玻璃制造工艺,并在其后,尤其是伊斯兰时期才得到较大的发展。
竹古巴遗址的年代更晚至9世纪早期(图一九,1)。
因此,海路的发现品种不同,数量少,年代晚,与中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云南发现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正式公布的仅有晋宁石寨山西汉中期M6出土的二件。
两广的发现,肇庆北岭松山古墓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出土标本属于本文划分的Ab型离心圆纹层状眼珠,是铅钡玻璃;其余南越王墓等出土品均晚至西汉早期。
可见云南和广东的发现数量很少,年代晚至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已是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日趋式微的阶段。
由此看来,它们的来源应是楚地或巴蜀地区,而绝不可能追溯至印度。
综上所述,无论是将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源头归于印度,还是将印度作为西方蜻蜓眼式玻璃珠传入中国的中转站,无论认为具体的传入途径是经东南亚的海路还是经云南的陆路,都是错误的,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途径不应是南路。
再看北路传入说。
我们不能同意持这种意见的学者将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源头完全归于西亚波斯,甚至具体到伊朗里海沿岸吉兰州的看法。
伊朗高原的玻璃生产早至公元前二千纪的埃兰王国(KingdomofElam),但当时主要用于生产模仿青金石制品的圆柱形印章以及其他小件器物。
尽管吉兰州的发现有少数略早一些,但蜻蜓眼式玻璃珠在整个西亚的出现和流行年代多在公元前6-前4世纪。
中国出土最早的一批蜻蜓眼式玻璃珠,年代在西周至春秋,比伊朗开始制造的年代有可能还要稍早一些,至少属于同一时代。
尽管我们承认,中国最早的一批蜻蜓眼式玻璃珠都是Aa型同心圆纹层状眼珠,整体而言,在造型上的确与伊朗的产品比较接近,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Aa型标本都是伊朗的产品,其中必定还有地中海地区、埃及等地的产品,只是限于目前的认识,还无法准确区分。
Aa型之外,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还有C型嵌环眼珠和E型套圈眼珠,其余类型的源头,根据我们在第四节中的论述,B型、D型、F型蜻蜓眼式玻璃珠可能原产于埃及以及地中海北岸等地,中国出土的某些Aa型标本,也可能是这些地方的产品;G型则最有可能是印度的创制。
因此,将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源头完全归于伊朗,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要更好地讨论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路线,首先要考虑其不同的类型可能具有不同的来源;然后结合相关类型在中国的分布来考虑其可能的输入路线,并且要注意,即使同一类型的输入品,不同的时代输入路线也可能会有不同;最后,再根据国外的发现,进一步勾勒、复原其传入途径。
这样的工作相较于笼统的比对而言,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对问题的最终澄清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从当时的欧亚大陆格局考虑,无论是埃及、地中海沿岸还是伊朗,都似乎无法和东方进行直接的交往。
从考古发现看,这些地区这一时期或更早传播至东方的若干文化因素,如马车、一人双兽母题、纺织品等,或是东方传播至西方的一些文化因素,如较早的丝绸、较晚的马镫等,都是通过欧亚草原路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伊朗,都和欧亚草原路起点——黑海沿岸存在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这里成为不同类型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汇聚之地。
根据德国学者的统计和研究,在这一地区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种类丰富,数量多,仅在黑海北岸就达到九百多颗,另有四百多颗发现于邻近的库班(Kurban)地区。
另外,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还可以补充位于黑海沿岸的乌克兰刻赤(Kerch)水神殿(Nymphaeum)墓地的多座墓葬出土的包括蜻蜓眼式玻璃珠、琥珀珠、釉砂珠在内的珠饰,墓地年代大概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在乌克兰美利托波尔斯基(Melitopol’s’kyi)石堆墓群(Kurgan)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的一号墓中,出土有数十件蜻蜓眼式玻璃珠,种类主要为Aa型同心圆纹眼珠,另有数件I型组合型眼珠系采用层状眼珠和突出圆斑眼珠共同装饰。
这些珠子和一件腓尼基鸟形玻璃坠子装在一个盒子里,置于女性墓主头部附近。
依欧亚草原路从黑海沿岸东行,沿线均有蜻蜓眼式玻璃珠发现。
位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交境处波克罗夫卡(Pokrovka)的早期萨尔马提亚墓葬中出土有蜻蜓眼式玻璃珠,经检测应是从黑海或者东地中海地区引进的。
著名的菲力波夫卡(Filippovka)古墓位于欧亚交界处,在公元前4世纪的14号石堆墓1号墓室中出土有蜻蜓眼式玻璃珠。
据称,在中亚费尔干那盆地的斯基泰古墓中也出有蜻蜓眼式玻璃珠。
有研究者认为,蜻蜓眼式玻璃珠被认为具有抵御邪恶的力量,斯基泰女性显然接受了这种观念,因此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的斯基泰墓葬中经常可以发现。
可见,蜻蜓眼式玻璃珠向斯基泰等游牧民族的流传及其在欧亚草原的流行不仅是物品的流动,而且伴随着观念的传播。
根据孙培良先生复原自黑海沿岸到蒙古高原的“斯基泰贸易之路”,由斯基泰别部前行,经哈萨克北部的丘陵和荒漠东南行,到达阿尔泰山脉的西缘,即阿尔吉帕人的居地。
商路在阿尔吉帕分两支:
东北行,经阿尔泰边区至巴泽雷克(Pazyryk)和米努辛斯克(Minusinsk);东南行,经阿尔泰山麓至准格尔。
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新疆亦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向东南绕过阿尔泰山,并继续向南传播到达拜城、轮台等地,甚至塔里木盆地东南缘的且末;二是并未直接进入新疆,而是从阿尔泰山东北行,经阿尔泰边区至米努辛斯克和蒙古高原等地。
由于这些地区,尤其是米努辛斯克盆地古文化很早以来就和新疆存在密切的交往,再辗转进入新疆。
从现有的发现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新疆后并未通过河西走廊继续向内地推进,仅在新疆流行。
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进入中国内地的途径,最有可能是经阿尔泰边区至米努辛斯克和蒙古高原等地,再折而南下的道路。
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塔什提克文化(TashticCulture)出土有蜻蜓眼式玻璃珠。
1972-1973年,苏蒙历史文化考察队研究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小分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北乌兰固木市郊外昌德曼山下一处早期铁器时代墓地发掘出“带圆斑的串珠”,从报道所附不太清晰的线图观察,应为蜻蜓眼式玻璃珠无疑。
报道者认为,这类遗存在古埃及遗存和高加索地区有发现,但在东哈萨克斯坦尚未发现,如何来到昌德曼,或者是本地生产的,还不清楚。
这处墓地被命名为“昌德曼文化”,年代上限至公元前7世纪,晚可到前3世纪。
两处地点相距不远,米努辛斯克盆地更偏北一些,大概是欧亚草原地带公元前一千纪蜻蜓眼式玻璃珠传播的东缘。
随着与中国北方地区的交往,蜻蜓眼式玻璃珠一路南下,进入中国的内蒙古、山西等地。
从目前的发现看,内蒙古凉城毛庆沟M39、山西太原晋国赵卿墓、长子牛家坡M1、长治分水岭M270、侯马乔村墓地等年代都比较早,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属于中国最早的一批。
可能反映的历史事实是,蜻蜓眼式玻璃珠是从这条道路进入中国内地的。
以上关于蜻蜓眼式玻璃珠的传入途径是针对最初进入中国的情况而言。
蜻蜓眼式玻璃珠初传中国以后,在中国的延续时间很长,其中既有中国自产的模仿品,也存在外来输入品,后者的数量随着更多理化分析数据的公布将日益增加。
可以肯定的是,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格局的变化,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的传入途径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勾勒的传入途径还较粗疏,沿线的缺环较多,一些具体的路径还无法进行准确的判定。
另外,沿线材料的年代从一般情理上说都应当比中国的发现更早,但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我们掌握的国外资料有限,有的适合材料可能没能运用进来;另一方面,欧亚草原地带包括新疆地区的早期墓葬,由于缺乏文字材料或地区年代学框架尚未很好地建立,发掘者断定的年代一般幅度较大,因此我们只能进行大体的联系比较。
我们相信,随着更多材料的发现和介绍,以及今后相关认识的进一步深入,在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正,庶几可以获得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
六 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在中国引发的模仿与变异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是一种新奇的事物,进入中国之后,与本土文化产生共鸣,激起了人们模仿的热情。
这种模仿不仅仅局限于玻璃制造,在其他的手工业部门也可找到踪影,并产生一些在外来文化因素起源地并不具备的新的装饰意匠。
模仿的过程中,除了忠实地仿制外来品,有的也会发生一些变异,这种变异,一部分是由于模仿者不了解某些装饰意匠的原有文化情境,一部分实际可能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反映着外来文化因素进入中国调适以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
另外,即便外来珠饰进入中国后形制上未发生变化,但其功能、内涵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本土文化的影响。
对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模仿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铅钡玻璃生产;二是在其他质地珠饰或器物的制作中模仿其眼纹的装饰。
第一种情况,中国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有相当部分进行过成分测试,一部分属于西方传入的钠钙玻璃,另一部分确属本土自制的铅钡玻璃,包括亳州柴家沟M16、青川赫家坪M13(H型)、广东肇庆北岭松山古墓(Ab型)、辉县固围M1(Aa型)、巴县冬笋坝M49(Aa型)、开县余家坝M132(H型)、广州南越王墓(H型)、和田阿克斯皮里古城等标本。
上述确认为铅钡玻璃的蜻蜓眼式玻璃珠,除亳州柴家沟M16出土品我们没有见到清晰的图片资料,和田阿克斯皮里古城出土品残损过甚而无法划分类型外,其余的标本均属于A型层状眼珠和H型几何线间隔眼珠两种类型。
它们的渊源前文已有分析,Aa型应当源自西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蜻蜓眼式玻璃珠,也是最为常见、普遍的,对其进行模仿是很自然的事情。
Ab型则比较集中地分布于楚文化及其相邻区域,而不见于西方古代,很可能是楚地工匠在不了解蜻蜓眼式玻璃珠原有寓意的情况下,在伊朗传来的同心圆纹层状眼珠造型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创造发挥。
H型几何线间隔眼珠也仅见于中国,情况和Ab型标本相同。
可见,类型划分、渊源分析和成分测试结果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属于铅钡玻璃者,多为中国本土在模仿基础上的新创制。
第二种情况,即用玻璃之外的其他材料仿制蜻蜓眼式珠,在国外很少见,而中国的发现质地众多,发现数量也颇不少,独具特色,在讨论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时是不能不提及的。
与玻璃最接近的材料釉砂制作的蜻蜓眼式珠,在战国时期是最为常见的,这些珠子仅表面玻璃化,从其穿孔或破裂之处可以观察到,珠体内部依然为未烧结的石英砂。
此类标本多集中于楚地及相邻地区,大概都是楚地生产的。
楚地还流行用陶土制作的蜻蜓眼式珠。
湖北松滋M32出土一件“彩绘泥球”,外表着黄色陶衣,有许多深红色圈纹,红圈内凸起,凸起处涂有翠绿色大圆点,明显模仿A型层状眼珠。
墓葬年代上限可到春秋末叶,是否蜻蜓眼式玻璃珠初传楚地即用陶土进行模仿?
因相关资料尚少,不能遽下断语。
战国中期,这类标本在楚地越发常见,如江陵望山M1出土4件,形体较大,三件呈十一面体,一件呈二十七面体,每面都用不同的颜色绘出圆圈纹或点纹(图二○,1-3)。
荆门罗坡岗M59出土五件“多色彩绘陶珠”,以乳白色为底色,绘天蓝色圆点,圆点外绘其他尚有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1件,圆形,有穿孔,表面有红、蓝、白三色彩绘。
直至东汉末期,楚地尚有陶制蜻蜓眼式珠的孑遗,如郧县砖瓦厂M3出土的1件,灰白色,圆球形,中间有一个对向小穿孔,阴饰卷云纹,在局部纹饰内残存浅蓝色、浅绿色的低温釉彩。
在楚地周边与楚文化关系密切的地区也发现陶制蜻蜓眼式珠,如陕西汉中石英沙厂战国中期M3出土小泥球2件,圆球状,有穿孔,通体饰凸点纹,底色为蓝色,外涂白衣。
河南辉县赵固战国晚期M1出土一件“假琉璃珠”,直径4.6厘,中间有穿孔,但未穿透,粉红胎,嵌白点。
报告描述很有意思,“初看甚大,认为琉璃珠之王,细察实非琉璃质,乃陶质之仿琉璃做法而烧制者”。
成都光荣小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墓出土“陶球”3件,两件橄榄形,表面涂青绿色颜料,上饰圆圈纹,内饰圆点纹;一件球形,表面涂白色陶衣,饰几何纹及褐色圆点纹(图二○,9)。
广州汉墓西汉后期M3005出土1件,饰圆圈纹。
比较特殊的陶制蜻蜓眼式珠,山西榆次王湖岭西汉初年M4共出土4件,形制相同,圆球状,直径5.5厘米,器身有一轴孔,球面通体施黑底,彩绘红、白二色的圆点纹,出土时色彩鲜艳。
一件陶珠在出土时恰在一件陶璧的“好”内(图二一,1)。
年代略晚,出土地点远离楚地,看来与楚文化制作陶制眼珠的传统关系不大。
我们注意到,将蜻蜓眼式玻璃珠置于玉璧“好”内的做法,在中原地区亦有发现,如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1件(图二一,2)。
榆次出土的陶珠和陶璧,显然是仿制品,可能是专为随葬制作的明器。
除陶珠外,楚地及其周边还出土有其他质地的仿制品,如江陵九店战国中期晚段M26(图二二,1)、荆门罗坡岗战国中期晚段M88(图二二,2)、重庆开县余家坝战国中期偏晚M15出土石珠,前者黑色,器表光洁,有若干嵌饰花纹的圆形凹窝,但嵌饰物均脱落无存。
最惊人的发现是新蔡葛陵战国中期前后楚墓出土象牙珠,数量达2298枚,都是在圆球面上用微小的圆形铜饰装饰出个数不等的“蜻蜓眼”。
战国早期以后,楚地成为中国蜻蜓眼式玻璃珠最为流行的地区,上述用各种材料仿制的蜻蜓眼式珠,与此是密不可分的。
在全国范围内,仿制蜻蜓眼式玻璃珠所用的材料尚有骨、玉石、煤精、木等。
骨珠如新疆轮台群巴克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IM7出土骨管1件,通体阴刻许多圆圈,圈内又刻一圆点(图二二,3)。
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早期M16出土662件,圆形,两端磨平,中间有系孔,灰色(似经火烧过),珠身刻有圆圈纹饰(图二二,4)。
山东长岛王沟战国早期M10出土18件,正圆体,表面旋刻六至八个圆圈纹(图二二,5)。
河南陕县战国中期前后M2507出4件,扁球形,珠体上刻同心圆纹,似料珠的蜻蜓眼,可能和其他质地的珠子组成佩饰(图二二,6)。
玉石珠如洛阳西郊战国中期四号墓出土一件“石环”,正、反面均等距阴刻三个涡纹。
河南巩义仓西墓地战国晚期M47出土石珠1件,鼓形,周面布满乳突。
安徽天长县三角圩西汉中晚期M1出土玛瑙珠1件,黑色中间夹淡红色眼球。
洛阳中州路战国初期M2717出土绿松石珠1件,“饰乳突纹”。
煤精如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末魏晋初乙M8出土1件,两面刻有三个等距圆形(图二二,7)。
木如内蒙古扎赉诺尔盟汉代M3002出土2件,大小形制一样,皆作算珠状,通体镶嵌米粒大小的白色饰物,但俱已朽成粉状(图二二,8)。
除了釉砂材料的特性接近玻璃,模仿品的特征接近玻璃制作的原型外,由于与玻璃材质的区别,用其他材料制作的仿蜻蜓眼式玻璃珠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特性的制约,带有与摹拟对象不同的一些特征。
如陶珠,一般是在珠体施加彩绘,由于原料廉价易得,可以制作得很大,山西榆次王湖岭M4出土的4件,直径5.5厘米;辉县赵固M1出土的1件,直径4.6厘米,在玻璃珠中是不见的。
骨珠、煤精珠一般是在珠体上刻划似眼珠的圆圈纹饰,有的还在圆圈中间刻一点,摹拟瞳孔。
玉石珠则除了刻划的方法外,有的在其上加工出凹窝,以便镶嵌其他材料摹拟眼珠,但由于粘接不易,容易脱落,这种方式并不常见。
更常见的是利用材料的一些具体特征量材加工,如表面本身凹凸不平的,可以加工成玻璃标本中Bb型突出圆斑状眼珠的样式,玛瑙珠本身具有不同的色泽,利用其上的色泽,可以自然地形成眼珠。
象牙珠和木珠质地较疏松,适合采用镶嵌其他材料来象征眼珠的方式。
这些模仿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标本,材质之多样,形式之丰富,不见于西方古代世界,应当是本土制造的。
它们的存在表明,蜻蜓眼式玻璃珠传入之后,得到了本土文化的强烈共鸣。
蜻蜓眼式玻璃珠传入中国之初,如果没有中介者的参与,并不能主动阐释自身的文化内涵。
因此其原有的与“恶眼意识”相关联的护符功能被大大削弱,甚至发生根本性的变异。
目前发现中,由出土情境可以反映其具有护符功能的仅有新疆尼雅东汉中晚期MN1M3出土的一例,标本中穿圆孔,内穿皮带,带长130厘米,男尸贴身斜背。
发掘者认为,这一出土情况不仅表明蜻蜓眼料珠特别珍贵,而且显示着一种求安祈福的辟邪作用。
其他大多数的发现,都是被作为珍奇之物,用以彰显拥有者的身份地位,或是其他器物的装饰,甚至进入礼制的范畴。
以下分别略加阐述。
战国时期的文献常提到所谓“随侯之珠”。
如《庄子·让王》、《韩非子·解老》等。
其与“和氏之璧”并列,是当时统治者所谓的“良宝”。
“随侯之珠”所指为何,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
一是“珍珠说”,依据主要在于《太平御览》引《墨子》佚文云:
“隋之明月,出于蚌蜃。
”此说影响不大。
二是金刚石说。
地质工作者郝用威在钟祥市九花寨的山中发现大量的金伯利岩,即基质不含长石的偏碱性超基性岩,是原生金刚石矿的主要母岩,结合文献记载关于随珠的描述,推测其有可能是一颗具曲面晶形的宝石级金刚石。
此说影响较大,但由于金刚石是自然界中硬度最高的宝石矿物,天然搬运很难磨蚀成珠,且在随州目前未发现金刚石矿,此说即使在地质工作者中也存在反对意见。
三是随珠即是蜻蜓眼式玻璃珠。
后德俊指出曾侯乙墓出土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很可能是我国自己生产的,与文献中关于随侯之珠的记载十分吻合。
这批标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属于钠钙玻璃,但样品中的Na2O含量明显低于西方同类玻璃中的含量,而且含有一定的PbO,所以李青会支持后德俊的意见,认为这种成分类型的蜻蜓眼式玻璃珠是本地的产品,但同时也承认,由于对曾侯乙墓出土的174件标本进行的检测太少,不能排除部分是西方传入的可能性。
林梅村即认为,这批玻璃珠皆为西方的钠钙玻璃,根本不是中国本土制造的,而所谓随侯之珠应是中国自产玻璃,即以铅钡玻璃、钾玻璃和釉砂仿制的蜻蜓眼式玻璃珠。
看来,曾侯乙墓出土的标本,其产地还存在争议,一时难有明确的结论,我们姑置不论。
但后德俊、林梅村皆以蜻蜓眼式玻璃珠为“随侯之珠”,这个意见是极有见地的。
《论衡·率性》云:
“隋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
”明确指出所谓“随侯之珠”,应当是人工合成制品,而不是珍珠、金刚石等自然之物。
从考古发现来看,曾侯乙墓出土多达174颗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远远多于同时期其他单一墓葬出土的数量,正符合其拥有者的身份。
如果随珠即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推论能够成立,那么其得名是由于随侯拥有获得外来蜻蜓眼式玻璃珠的贸易渠道,还是由于其治下的随国工匠掌握模仿的生产技术,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根据当时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格局,随国不太可能独家拥有直通域外的贸易渠道,以获得源源不断的蜻蜓眼式玻璃珠货物资源,并进而垄断市场。
更有可能的是,随国可能最早掌握用国产原料模仿生产的技术,“以药作珠”,来满足市场需求。
从考古发现来看,战国早、中期蜻蜓眼式玻璃珠集中分布于两湖和略北的区域,除了直接从域外传入的少量标本之外,相当部分都可能是随国生产的模仿品。
楚灭随后,技术相应地为楚人掌握,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楚地的发现最为集中的现象。
即使是中国掌握蜻蜓眼式玻璃珠的模仿技术以后,它仍然是一种珍奇之物,生产量应该不是很大,供应的对象乃是上层阶级,这从其出土单位一般为等级较高墓葬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
蜻蜓眼式玻璃珠作为其他器物的装饰,则见于剑、带钩、铜镜、牌饰、栉袋等。
剑饰的例子有荆州天星观战国中期二号墓出土二件蜻蜓眼式玻璃珠,大小形制相同,饰八眼,属于本文划分的Aa型同心圆纹眼珠。
报告称,两件珠子是木剑M2∶51的剑首。
木剑应是明器,但以蜻蜓眼式玻璃珠为剑首,应当有现实参照。
在带钩上镶嵌则见于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
出土的错金嵌玉铜带钩呈变体鳖形,前足伸出,口微张,头中央和背部都嵌有薄玉片。
与带钩同时出土的一件“椭圆球形料珠”,宝蓝色,周身为九朵团花开片镶嵌。
从所附带钩线图观察,其前部有一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