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清对六朝碑的研究doc.docx
《李瑞清对六朝碑的研究doc.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李瑞清对六朝碑的研究doc.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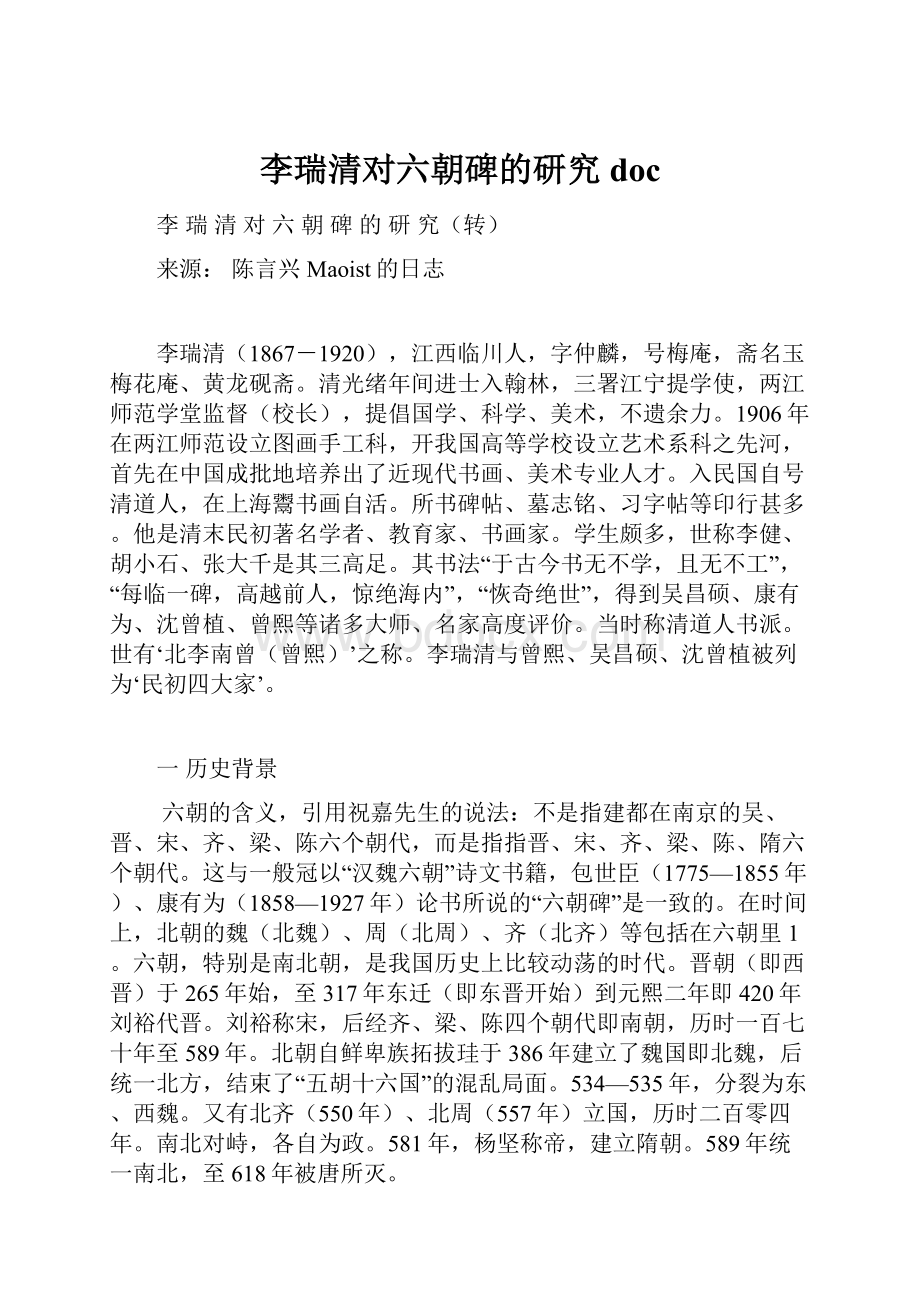
李瑞清对六朝碑的研究doc
李瑞清对六朝碑的研究(转)
来源:
陈言兴Maoist的日志
李瑞清(1867-1920),江西临川人,字仲麟,号梅庵,斋名玉梅花庵、黄龙砚斋。
清光绪年间进士入翰林,三署江宁提学使,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提倡国学、科学、美术,不遗余力。
1906年在两江师范设立图画手工科,开我国高等学校设立艺术系科之先河,首先在中国成批地培养出了近现代书画、美术专业人才。
入民国自号清道人,在上海鬻书画自活。
所书碑帖、墓志铭、习字帖等印行甚多。
他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教育家、书画家。
学生颇多,世称李健、胡小石、张大千是其三高足。
其书法“于古今书无不学,且无不工”,“每临一碑,高越前人,惊绝海内”,“恢奇绝世”,得到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曾熙等诸多大师、名家高度评价。
当时称清道人书派。
世有‘北李南曾(曾熙)’之称。
李瑞清与曾熙、吴昌硕、沈曾植被列为‘民初四大家’。
一历史背景
六朝的含义,引用祝嘉先生的说法:
不是指建都在南京的吴、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而是指指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
这与一般冠以“汉魏六朝”诗文书籍,包世臣(1775—1855年)、康有为(1858—1927年)论书所说的“六朝碑”是一致的。
在时间上,北朝的魏(北魏)、周(北周)、齐(北齐)等包括在六朝里1。
六朝,特别是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动荡的时代。
晋朝(即西晋)于265年始,至317年东迁(即东晋开始)到元熙二年即420年刘裕代晋。
刘裕称宋,后经齐、梁、陈四个朝代即南朝,历时一百七十年至589年。
北朝自鲜卑族拓拔珪于386年建立了魏国即北魏,后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
534—535年,分裂为东、西魏。
又有北齐(550年)、北周(557年)立国,历时二百零四年。
南北对峙,各自为政。
581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
589年统一南北,至618年被唐所灭。
南朝受晋朝“禁碑”的影响,官民立碑者少,著名的碑刻不多。
但也有像“二爨”、《瘗鹤铭》等著名碑刻流传下来。
南朝书法主要受魏、晋影响,书者多师锺(繇)、王(羲之),以柔美俊逸的书风见长,属魏、晋遗风,创新性不大。
书家多留迹于文牍手札,后来摹刻成帖(南帖)以传。
北朝到魏孝文帝元宏即拓拔宏,改革政治和鲜卑风俗,迁都洛阳,大兴文治,采用同化政策,接受中原文化,使北魏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书艺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
北朝书艺不仅未受“禁碑”影响,可能还远受树碑立传盛行的东汉之影响,又流行佛教,立碑造像刻石之风颇有秦汉“坚碑立榜”之势,甚至超过秦汉。
还有北方民族固有的强悍的个性影响,其书风大别于南朝,不仅刚劲有力,也有风韵,不单拘守于纸帛,已脱离了魏、晋行草书,上溯周秦两汉,产生了独树一帜的“魏碑”,即“魏体”、“北碑体”。
这是书体的重大创新。
众多的北碑与“二爨”、《瘗鹤铭》等著名南碑都是碑学乃至书学史上的辉煌成就。
六朝碑包括碑碣、摩崖、造像、墓志等,特别是北朝时期,数量之多,难以计数。
书者各显其能,尽展其才,无拘无束,自由发展,书风特色,异彩纷呈,涌现了众多未留名的书法高手,出现了书法史上的奇观。
隋朝虽短,因南北统一,又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这对书学的发展是很有益的。
李瑞清先生曾概括隋碑,“以南北合流,上承六朝,下开李唐,为千古楷书极盛之时”。
唐代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经济繁荣的局面。
唐代帝王爱好书法的颇多,书家不乏其人。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人们所熟悉的。
他专宠王羲之书法,大力创导并身体力行。
所以,唐代学王书成风。
朝廷鼓励书法学习、研究,科举取士,兼重书法。
唐之国学有书学,设书学博士。
即使不专门学书的儒生,也须学书。
书学受到朝廷的空前重视,无疑促进了书学的大发展,出现了群星灿烂,书学盛行的时代。
但由于统治者的干预,要附和统治者的意识,不可能真正自由发展。
这对日后书学发展有深远影响,使书法最终走向“馆阁体”起到了负面作用。
李瑞清分析了历史上碑学与帖学的情况后,认为“大约汉、魏至唐,无不重视碑。
南朝士大夫雅尚清谈,挥尘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
“简书尚妍雅,碑志尚古朴。
”“宋以来,帖学大行而碑学微”,能书碑者屈指可数,“碑学之中兴,自阮相国(清阮元,1764—1849年)始”。
后有包世臣、康有为等著书立说,宣传倡导,人们渴望书法突破“馆阁体”的束缚,变革求新。
“三尺之童,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碑学发展之势己不可挡。
作为碑学家的李瑞清,对“六朝诸碑,靡不备究”,“学北碑二十年”的体会是“南北虽云殊途,碑帖理应并就”。
这与重碑轻帖、重帖轻碑的书家不同,其对六朝碑的研究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
二对有关六朝碑的分行布白,结字章法的研究
在研究著名的摩崖石刻《瘗鹤铭》时,有书记载明末张力臣(即张弨,1624—?
)雅好金石文字,尤其对《瘗鹤铭》感兴趣,嘗登焦山考察研究,乘江潮归壑,往山岩下,坐地仰读。
“聚四石(当时他见到的是出水前的《瘗鹤铭》原石,可能见到的是四石)绘为图联,以宋人补刻字”。
李瑞清认为“张力臣依原石作图,依空补文,今金石家以为定式,不知摩崖书,随字体、石势高下,不得以长短定文之多寡”。
这就是书家从书学的角度对《瘗鹤铭》的研究不同于金石家的地方。
依石之空,补刻文字,但摩崖石上之空处,可能原来就没有刻字。
开始补字成文的人提出一家之说。
从实际情况看,后人再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有新意者不多,人云亦云者多。
是五石还是六石?
为何石上的字是直行从左到右,不同于汉字书写最通用的从右到左的定式呢?
五石现在的摆放怎么能说明原摩崖上书写的内容?
等等,连张氏自己也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说明这种方法依据不充分,科学性不强。
而张氏所见的《瘗鹤铭》,是出水前原石上的书迹,应远胜于拓本。
石不全,字不全,但可作为研究其书艺的范本。
所以,李瑞清先生曾不避江风,昼夜坐卧碑下,仔细研读过《瘗鹤铭》。
摩崖之石不同于碑石,是自然之石,有石质、地势、地形等方面的差别。
在摩崖上书写一要看书写的字体,二要看摩崖之石质、石势,不可能将字迹书写得比较匀称。
实际情况表明,在不同的摩崖石上,书写不同的字体也是有区别的。
李瑞清认为《瘗鹤铭》还有源于金文的“其上下相衔之妙”的特点。
这一特点在六朝碑中“均得其秘”。
“《瘗鹤铭》书势亦带行押体”。
《瘗鹤铭》通常来讲是楷书。
(图一)是《瘗鹤铭》保留下来的原摩崖石刻2。
由(图一)可见,很多字不是“端端正正”的楷书,还有带有行书书体的字。
九十余字中,两个“于”字,上面的“之”字,“表”字,“亭”字等,很有行书的意思。
李瑞清先生还认为唐太宗赞王羲之“字似欹而实正”之妙,还有《兰亭序》中同一字的多样式,其实是从金文中得来的。
(图一)中的“旌”“胎”“表”“后”“侣”“掩”“丹”等字,看似斜,而实正。
从字与字,行与行的关联来分析,不仅不难看,反而有其特有的韵味。
这样的妙秘在《瘗鹤铭》、《爨龙颜碑》、《张黑女志》(北魏普泰元年即531年)、《匡喆刻经颂》(北周大象元年即579年,摩崖刻经)及郑道昭所书诸碑等六朝碑中传承下来。
正如他所说“其要在得书之重心点也”即“力学所谓重心点也”,以科学的原理解释了“字似欹而实正”之妙。
从用笔结字分析,《匡喆刻经颂》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六朝摩崖刻经,无年月)相同,不同之处是字形大小异势,当为一人所书。
他还认为“写碑与摩崖不同,其布白章法亦异,一有横格(碑刻),一无横格(摩崖石刻)。
包慎翁(包世臣)深悟此理。
但以无横格为古人之高妙,又以九宫法求之,谬矣。
”“然不论有格无格,皆融成一片。
此学者不可不留心也。
”仍以(图一)《瘗鹤铭》分析,大字“势”、“瘗”、“禽”等比小字“上”、“表”、“留”、“(右边的)山”等大很多,剪裱的拓本字迹,必然大小不等,参差不齐。
“故古碑剪裱,则觉大小参差,而整张拓片视之,不见大小,浑然一体。
大约下笔时须胸有全纸,目无全字。
”日本菅野智明评:
“这种论述,使人耳目一新,一看便知此及李氏独创也”3。
对李瑞清有深入研究的菊南山先生早在1994年撰文《百年难得一见的书学大家》说,李瑞清提出的“胸有全纸,目无全字”箴则,传诵一时4。
深知金文书法的李瑞清发现“姬周以来彝鼎(金文),无论数十百文,其气体皆联属如一字,故有同文而异体,异位而更形,其长短、大小、损益,皆视其位以为变化,一字之妙用,全器之布也。
”篆书发展到汉代,有重大的变化,“两京(即西汉、东汉)篆势已各自为态”,金文布白章法的特点、妙秘在汉篆中已难见到了。
这种变化是一般研究者、书法家没有看出来的。
金文书法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已经结束,如同不会再现唐诗的时代一样。
但在《开通褒斜道刻石》(简称《大开通》,东汉永平六年即63年,摩崖石刻)、《石门杨君颂》(东汉建和二年即148年,摩崖石刻)等几种隶书中,《瘗鹤铭》等六朝碑中这样的布白章法妙秘得到了传承,此外“鲜有能窥斯秘者”。
三六朝碑的源流演变与特色
书法源流一直是书学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书法源流与汉字源流密切相关但不相同。
不论是论书法源流还是论书体源流,一般多是按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出现的先后论述,或篆——隶——楷——行——草,或按历史朝代的先后论述等等,与汉字字形源流(演变)没有大的区别。
但不同书体,不同流派怎样演变,上承下启关系没有解决。
李瑞清一生注重书体、书派源流演变内容的学习、研究,认为六朝诸碑的源流演变、特色与不同的汉碑(隶、分书)、金文(篆书)有相关的联系。
其研究结果举要:
《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使君(宝子)之墓碑》,东晋义熙元年即405年),南碑中的名品,与《爨龙颜碑》(全称《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龙颜)之碑》,刘宋大明二年,即458年)并称“二爨”。
因《爨宝子碑》小于《爨龙颜碑》,所以宝子称“小爨”,龙颜称“大爨”,都在云南,是云南之二宝。
《爨宝子碑》源流:
金文《(大)盂鼎》(西周康王即公元前1020年—公元前996年的青铜器)铭文。
《张迁碑》(全称《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东汉中平三年即186年)也是源于《(大)盂鼎》铭文的汉隶之一。
《张迁碑》上承《(大)盂鼎》铭文书法,下启《爨宝子碑》,方笔笔法一脉相传。
但字形字势有变化,由金文《(大)盂鼎》铭文的长形纵势演变成《张迁碑》的方形橫势,有隶变的一般性,直笔方形,又有不同于其它隶书的个性。
《张迁碑》与《(大)盂鼎》铭文不如《爨宝子碑》与《张迁碑》更近。
《爨宝子碑》是晋碑,处在向成熟的楷书发展演变过程中,书写的自由度较大。
《爨宝子碑》与其后的六朝碑楷书比较,带有隶(分)之意。
年代较早的六朝碑,如《(中岳)嵩高灵庙碑》等,也带有隶(分)意,但《爨宝子碑》隶意比《(中岳)嵩高灵庙碑》更浓。
如运笔,横划右端有向右上方波挑的笔势,与隶(分)横划的“雁尾”相近,说明隶意还未完全“蜕变”。
但同样一横划,在隶书中却见不到横划左端向左上、同时右端向右上波挑之势。
而这样的笔势,特别是横划左端向左上波挑的笔势在方笔魏碑中大量出现。
因此,李瑞清认为许多方笔魏碑是源于《爨宝子碑》。
由此也可证明,“北碑南帖”论的不科学性。
上述所举南碑《爨宝子碑》运笔之势的一个例子,居然能在其后的北碑中出现了。
可见碑与帖的艺术特色是不能以南北地理位置来划分的。
《(中岳)嵩高灵庙碑》(有关的书法辞书和《(中岳)嵩高灵庙碑》单行本几乎都说太安二年即456年。
此处引用殷宪先生之说5,北魏太延二年即436年),是北魏早期的碑刻,由隶(分)变楷的早期楷书,楷书还未最后定型。
从总体上看,楷法的规范还未固定下来,曹工化先生称《(中岳)嵩高灵庙碑》为“前规范”的楷书6,兼有隶楷,非隶非楷。
所以,书写的自由度较大,易于展现书者的面貌特色,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
这也是李瑞清喜爱《(中岳)嵩高灵庙碑》的原因。
他认为其源于金文的《(大)盂鼎》铭文的书风。
《(大)盂鼎》铭文书法再上,承殷商(即李瑞清所说的殷派)书法的余绪,其笔法有进化,成为方笔书法之祖。
汉代的《景君碑》(亦称《景君铭》,全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东汉汉安二年即143年,)是直接受金文《(大)盂鼎》铭文书风影响的汉隶之一。
一般讲汉隶字势多橫势,而《景君碑》为纵势。
再由《景君碑》到《(中岳)嵩高灵庙碑》。
从笔法、字势分析,《(大)盂鼎》铭文的方笔、纵势等特点在《景君碑》、《(中岳)嵩高灵庙碑》中传承下来。
所以,是“祖《(大)盂鼎》而祢《景君碑》”,还要由“景君、衡方(《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东汉建宁元年即168年)二碑得笔法,而以谷朗(《谷朗碑》,吴凤凰元年即272年)为面貌”。
这样才能达到《(中岳)嵩高灵庙碑》那样好的艺术效果。
李瑞清用《(中岳)嵩高灵庙碑》的精神书写的碑文见(图二)。
《爨龙颜碑》是南碑中的名品,旧拓很少。
清道光年间阮元(时任云贵总督)访拓后,大力宣扬,始显于世。
康有为更是将其列为神品第一。
所以,引起书法爱好者,特别是碑学爱好者的兴趣,研究、仿习者日多。
但因很多人不知其源流,又无较好的篆、隶基础,难以深入进去,难以达到较高的水平。
对学习、研究北碑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共性问题。
所以,李瑞清认为“不通篆隶而高谈北碑者妄也”。
他认为《爨龙颜碑》源于金文的《鲁公伐䣄鼎》(西周武王时期即公元前1046—1043年的青铜器;最晚是西周成王时期即公元前1044—1021年)铭文。
该鼎铭文拓字所见较少,对其研究的不多。
按李瑞清篆书分类法,《鲁公伐䣄鼎》属鲁书(鲁派),用笔方折,特点是“峬峭冷隽,无一笔不险绝,无一笔不平正,所以大难。
”“《爨龙颜碑》用笔取势实出此”。
不论是《鲁公伐䣄鼎》还是《爨龙颜碑》都是“纳险绝入平正”,要处理好险绝与平正的统一,所以大难。
不能以形貌求之,否则,“愈近则愈远”,“此非深知书者不知也”。
其书艺水平极高,书写的难度很大,所以,李瑞清将《爨龙颜碑》评为南碑第一。
李瑞清节临的《爨龙颜碑》见(图三)。
《石门铭》(摩崖石刻,王远书,北魏永平二年即509年)北碑中之名品,其书超逸,运笔熟练,变化多端。
康有为先生极力推崇,评其为最高等级——神品,扩大了《石门铭》的影响和传播。
李瑞清认为《石门铭》源于金文的齐书(齐派)之一的《齐侯罍》(亦名《齐侯壶》7,春秋时期之齐器,公元前772—481年)铭文。
齐书按笔法分,有两派:
一派的笔法是方笔,继承了殷书之遗风,因为“殷派亦有流入齐者”;一派为园笔。
园笔齐书的形成与齐国的情况和齐俗有关。
《齐侯罍》铭文属园笔齐书之一,“此派如龙如螭,如铁如藤,其变化不可测,”“笔长而曲,篆书之变化此为极轨,能作此,则随笔颠倒,皆成佳趣矣。
”艺术水平很高。
《石门铭》上通汉隶的《石门颂》(摩崖石刻,全称《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即148年)。
《石门铭》——《石门颂》——《齐侯罍》这一脉,《齐侯罍》铭文的书艺特色得到传承。
对《石门铭》、《石门颂》书艺的评价很高是与其源于金文《齐侯罍》铭文的特色密切相关的。
李瑞清节临的《石门铭》见(图四)。
《郑文公碑》等(郑道昭书,郑道昭生年不详,有说455年?
8,卒于北魏熙平元年即516年)与其它六朝碑一样,是在清代乾嘉以后,碑学兴起而受到重视的。
郑氏留下了《郑文公碑》等三、四十余种摩崖书迹,《郑文公下碑》(北魏永平四年即511年)最有名。
与汉碑一样,六朝碑很少见书者姓名。
郑氏是很少的署名者之一。
李瑞清认为《郑文公下碑》源于金文的《散氏盘》(亦称《散盘》、《夨人盘》,西周厉王即公元前九世纪的青铜器)铭文。
一般篆书字势为纵势,而《散氏盘》铭文为橫势,园笔大篆,其在金文中的地位极为重要。
所以,评论很多,如金文中的神品、金文中的草书等等。
吴大澂(1835—1902年)考定青铜器《散氏盘》为楚器。
按李瑞清的篆书分类,《散氏盘》铭文为楚书(楚派)。
“其气磅礴,其势横衍”在金文中独具风格。
字形向右倾斜,所谓“横斜险倾”,但字之重心很稳,“倾而不倒”,从书法艺术上讲,明显地具备了“似欹而实正”的特色。
其结字变化无穷,如散、表、于、田等字多次、十多次出现,无一同者,屡易字之形势,以求变化。
这些古篆之奥秘都蕴藏在《散氏盘》铭文中(详见9)。
这些甚至可以说是书法艺术史上具有“开先河”意义的创造。
所以,说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二十余之字各不相同;王书“似欹而实正”之妙等都来自金文书法的道理。
《郑文公碑》还与西汉《五凤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公元前56年)相通,能取西周古篆和西汉古隶之醇古,遒丽渊穆。
其笔法、字势等《郑文公碑》乃承西周《散氏盘》铭文书法的余绪。
其书艺能独步北朝,无人可比。
所以,有人尊郑道昭为“北方书圣”。
若无篆隶基础,不知源流,是学不好的,写不出《郑文公碑》那种“淡雅雍容,不激不厉之妙”。
李瑞清深有体会的说“余每用散氏盘笔法临之,觉中岳风流去人不远”。
他节临的《郑文公碑》见(图五)。
《张猛龙碑》(全称《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碑》,北魏正光三年即522年)是北碑中的名品,其“笔法险峭,文章亦尔雅,学士大夫多喜之”。
也源于方笔之祖的金文《(大)盂鼎》铭文,师法汉代的《景君碑》,得《景君碑》之法,如执笔结字。
其突出的特点“用笔坚实可屈铁,景君(即《景君碑》)之遗也,下开率更(欧阳询)。
”即影响唐代欧阳询的书法。
著名的欧书如《化度寺碑》(631年)、《九成宫醴泉铭》(632年)等名迹,字势还保留着从《(大)盂鼎》铭文到《张猛龙碑》一脉相承的纵势。
有论欧书学王献之(如唐张怀权《书断》)、学王羲之(如宋《宣和书谱》)、学二王及北齐三公郎中刘珉(如《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等等说法。
李瑞清认为欧书源于金文,远师汉之《景君碑》,直接受《张猛龙碑》的影响,能变王羲之的面貌,书艺水平极高,自成一体。
如欧阳询先生不师篆、隶,只学到二王,怎么能唐代对他就有“八体尽能,篆体尤精”的评价呢?
《张黑女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亦称《张玄墓志》,清代因避康熙帝名讳,通称《张黑女(墓)志》,简称《黑女志》,北魏普泰元年即531年)北碑中之名品。
原石早已不存,仅有墨拓剪裱孤本传世。
经包世臣、何绍基(1799—1873年)等清代名家的研习、宣传,其影响很大。
特别是何绍基,从《黑女志》获益最深。
清末民初书坛南派宗师曾熙(1861—1930年)也是喜爱《黑女志》并从中深受其益的书家。
李瑞清的研究认为:
《黑女志》遒厚精古,北碑中之全以神味胜者,由汉隶《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即185年)一派出也。
讲《黑女志》的艺术水平高,特别是有何绍基、曾熙等名家大师能得其神韵的例证,认识易于统一。
说《曹全碑》的高妙,认识的统一可能就不太容易了。
《曹全碑》的字形,除极少数上下结构的字外,总体看,字取横势;结体略取侧势,但字的重心很稳,“似斜而实正”等在《黑女志》中得到传承。
所以,《黑女志》由《曹全碑》出也。
《黑女志》与时间稍晚的《敬史君碑》(亦称《禅静寺刹前铭》、《敬显隽(或儁)修禅静寺碑》,东魏兴和二年—540年)绝相似,遒古胜之。
二者同宗,但《敬史君碑》绵邈不逮耳。
何绍基得《黑女志》之益最深的原因是“能得其化实为虚处,故能纳篆分入真行也。
”另外,李瑞清在研究、临习《黑女志》过程中还发现:
碑中《三河》与《巛塸》并举,《三》即乾卦,《巛》即坤卦,此石外,无同之者。
在李氏之前,书学研究,或六朝碑研究,或专门对《黑女志》的研究中,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李瑞清用《黑女志》的神韵和笔法题写的何绍基所藏《张黑女墓志》孤本和影印本签见(图六,1、2)。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是位于泰山东南麓龙泉山谷石坪上的特大字体(字径约2-3尺)的摩崖刻经。
无年月,也未署书者姓名。
其书艺“浑朴渊穆,冠绝古今。
”特别是学习、书写榜书大字极好的范本。
因此对其源流派别的研究、论述很多,众说纷纭,没有一致意见。
李瑞清认为是“齐经生书”,“其源于(金文的)《虢季子白盘》(西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公元前827—782年)铭文,转使顿挫则夏承(全称《汉北海淳於长夏君(承)碑》,亦称《夏仲兖碑》,东汉建宁三年—170年的)之遗,与《匡喆刻经颂》、《般若文殊》(北齐刻经)、《唐邕写经》(摩崖刻经,北齐武平三年—572年)为一体。
著名书学家王学仲先生的研究认为只有李瑞清味透了石刻的脉络10。
六朝人的大字,当以《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与《匡喆刻经颂》为极轨,与郑道昭《论经书诗》(北魏永平四年—511年,摩崖石刻)可以并读,必能于古人大字外,独辟蹊径。
但这一脉的字势有所变化: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源于《虢季子白盘》铭文。
金文《虢季子白盘》铭文字取纵势,到汉之《夏承碑》已能看出字势有了变化。
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字势又有进一步的演变,字已是方形或带橫势;不少字如刚、闻、时、众、世等都是明显的横势;由结构是左中右三部分组成的字如树、衛,甚至两部分组成的左右结构的字如谛、起等字还有特横之势。
而园笔的笔法特点从《虢季子白盘》铭文到《夏承碑》,再到《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一脉相承,没有变化。
李瑞清所书金刚经见(图七)。
四六朝碑的书写者
可能是受汉朝碑刻不署书写者的影响,六朝碑一般没有书写者的署名。
其实,甲骨文、金文都未署书写者之名。
大概越是古人,越不重署名。
不像今人,很看重书名。
在六朝碑中只有极少数碑是署名的。
其中最有名的可能要算写《郑文公碑》的郑道昭,史书上也有他的传,做过秘书监、将军、刺史等官,为官时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死后谥“文恭”,是个好官。
再一位署名者是王远,名不见经传,可能因书《石门铭》而被书法爱好者所知。
还有如《孙秋生造像》等的书写者萧显庆,生平事迹无考,就更鲜为人们所知了。
可见,署名者也多无名分。
再说《瘗鹤铭》吧,撰写者、书写者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共识,学术争鸣从唐、宋时代就有了,发表意见的不乏名家、大家。
即使认为陶宏景的道号“华阳隐居”与根据残石空缺补写出的“华阳真逸”相同,数百年前就有人明确指出:
只能拟为陶宏景之文,不当为陶宏景书(因依残石空缺补出的是“上皇山樵”书)。
说明这样的研究方法缺乏科学依据,主观臆断多,不像用同位素碳14测定年代,根据考古新发现的实物资料来证经补史等方法那样可靠可信。
除这样的情况外,能否有新的视角来研究六朝碑的书写者呢?
李瑞清曾经研究过六朝碑的书写者,将其分为两类:
士大夫书和经生书。
士大夫书写的如:
《云峰山刻石》,广义讲是指郑道昭的摩崖石刻书迹;狭义讲是指郑氏在云峰山(在山东掖县)的摩崖石刻书迹,因云峰山之外如天柱山(在山东平度县)也有郑氏的摩崖石刻书迹,《郑文公上碑》就在平度县天柱山。
这里指的是郑道昭的书迹属士大夫书一类。
还有《张猛龙碑》、《张黑女志》等都归士大夫书。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匡喆刻经颂》属经生书。
造像诸体最多,一般为经生书,然其中有士大夫书的,如《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川刺史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即498年。
朱义章书,生平事迹无考)、《李洪演造像(题记)》(全称《邑子李洪演造像颂》,东魏武定二年即544年)等就属士大夫书。
六朝碑中“道经多出士大夫之手”,而“佛经皆出经生”之手。
六朝碑中经生所书的可分二种:
《般若文殊》与《唐邕写经》等为一种。
前者“自隋以来无继轨者”,其书艺没有传承下来。
《唐邕写经》影响到唐碑,如褚遂良书《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唐贞观十六年即642年)等。
《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实出《唐邕写经》。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与《匡喆刻经颂》等为另一种。
此二刻经的用笔、结字实际上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字形之大小异势耳”。
此处所举二种,四刻经都属经生书一类。
有人提出:
关于六朝碑中的方笔笔法的碑刻,特别是有些碑刻的笔画像刀切一样方折,到底是书家写的还是石匠刻的?
是笔的功夫还是刀的功夫?
实际上是认为笔写不出来,而是刀凿出来的。
对石刻书迹来讲,这是早就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只是在十九世纪以后,大量的六朝碑得到高度评价和空前重视的情况下突显起来。
从李瑞清所处的时代到现在都存在这个问题。
举两位大名家的论述为例:
(1)启功先生认为镌刻的作用程度有两种:
一种是注意石面上刻出的效果,例如方梭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