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docx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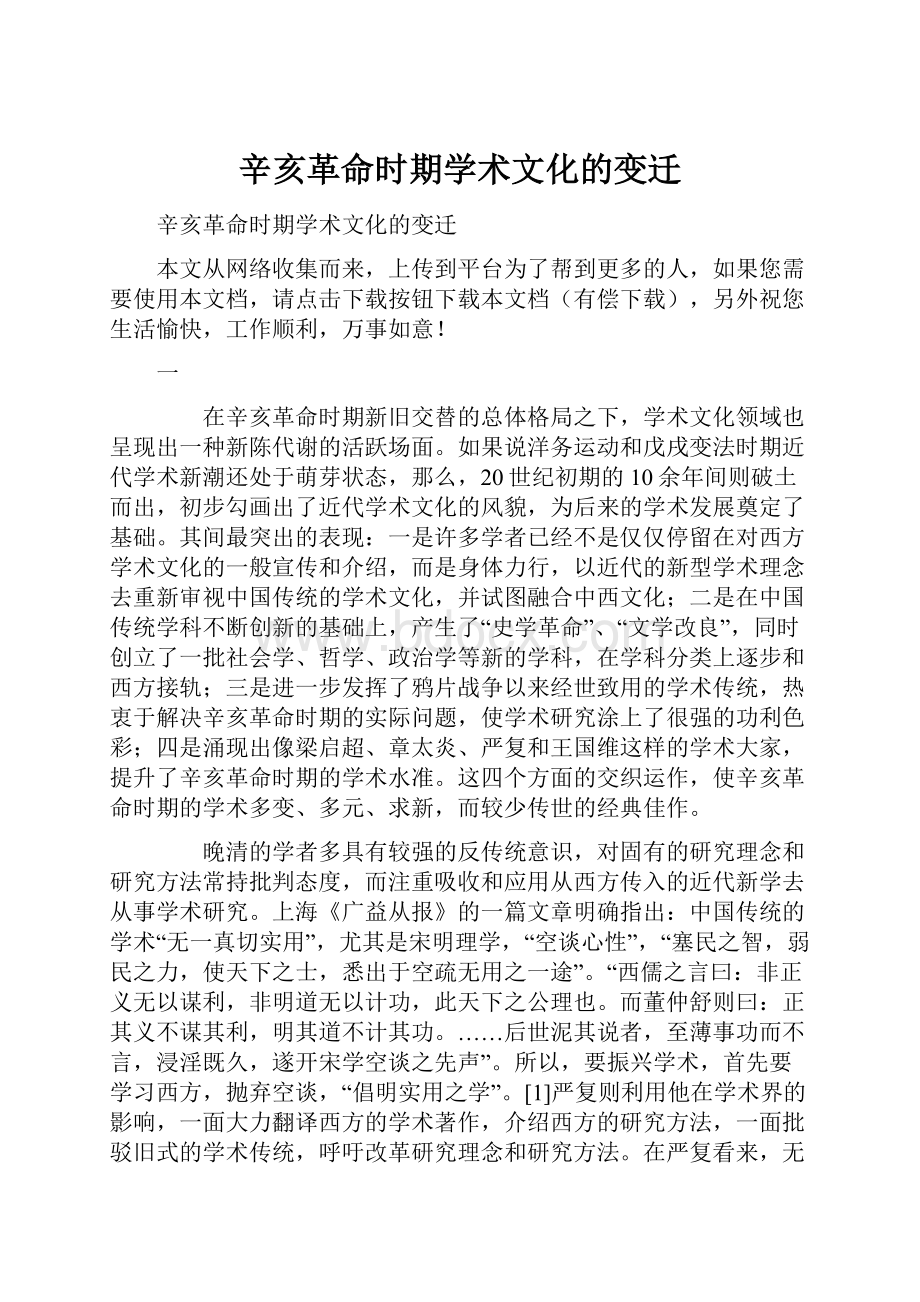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
在辛亥革命时期新旧交替的总体格局之下,学术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一种新陈代谢的活跃场面。
如果说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近代学术新潮还处于萌芽状态,那么,20世纪初期的10余年间则破土而出,初步勾画出了近代学术文化的风貌,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间最突出的表现:
一是许多学者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一般宣传和介绍,而是身体力行,以近代的新型学术理念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并试图融合中西文化;二是在中国传统学科不断创新的基础上,产生了“史学革命”、“文学改良”,同时创立了一批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新的学科,在学科分类上逐步和西方接轨;三是进一步发挥了鸦片战争以来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热衷于解决辛亥革命时期的实际问题,使学术研究涂上了很强的功利色彩;四是涌现出像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家,提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水准。
这四个方面的交织运作,使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多变、多元、求新,而较少传世的经典佳作。
晚清的学者多具有较强的反传统意识,对固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常持批判态度,而注重吸收和应用从西方传入的近代新学去从事学术研究。
上海《广益从报》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
中国传统的学术“无一真切实用”,尤其是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塞民之智,弱民之力,使天下之士,悉出于空疏无用之一途”。
“西儒之言曰:
非正义无以谋利,非明道无以计功,此天下之公理也。
而董仲舒则曰: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后世泥其说者,至薄事功而不言,浸淫既久,遂开宋学空谈之先声”。
所以,要振兴学术,首先要学习西方,抛弃空谈,“倡明实用之学”。
[1]严复则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大力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介绍西方的研究方法,一面批驳旧式的学术传统,呼吁改革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
在严复看来,无论是讲义理的宋学还是重考据的汉学,都缺少科学性,于事无补。
他尖锐地批评中国学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
他认为,“西学格致,则其道与是适相反。
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
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
[2]为了传播西方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严复在辛亥革命时期翻译了8部欧美学术名著。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则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更新自己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
他讲他在日本所汲取的新知,如临山荫道上,“应接不暇”,甚至不得不“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
1902年后,梁启超在思想和学术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开始以近代学术大家的姿态驰骋于中国学术界了。
章太炎和王国维同样深受西学的影响,而且善于创造性地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中国化,并实际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去。
总之,历史推进到20世纪初年,有头脑的学者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更新自己的学理。
鸦片战争后60年间那种关于是否应引进西学的激烈论争已经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怎样引进西学以及如何在融合中西学术的过程当中创造新的学术。
对此,王国维在1911年《国学丛刊》的发刊词中有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言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未尝知学者也。
……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讲授之西学也”。
[3](P72-73)
王国维在这时强调的是,中西、新旧之争已经毫无意义,中国学术只有在中西贯通和融合中才能有新的发展。
这表明,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学术界,只有学贯中西的学者才可能是时代的弄潮儿。
王国维等人正是看到了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西学素养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深厚的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优势,以西方新理论和新方法诠释中国古典文化,从而使中国传统学术具备了近代气息,焕发出新的生机。
梁启超关于中国学术变迁大趋势的思考以及对先秦诸子和古代学术的研究,成为20世纪初年学术界中一大亮点。
章太炎以近代理念重新研究古代经学,对《春秋》、《左传》、《易经》、先秦诸子学以及汉学、玄学、宋明理学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他在日本办国学讲习班,新论迭出,使鲁迅等一批热血青年为之倾倒。
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等西方学人的哲学观点和新的治学方法后,在哲学、红楼梦、教育学、古代诗词等领域的研究中成果卓著。
严复虽然较少有关于古典文化的学术专著,但他在翻译西方学术经典时所写的许多按语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
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这种以新观点、新方法重新考察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新动向,不仅使当时的学术研究面貌一新,而且影响久远。
五四时期胡适等人的学术研究以及30年代的新儒家等,基本是沿袭着这个套路走过来的。
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是经、史、子、集,基本服务于传统的文史研究。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仅单纯的历史和文学研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史子集的分类也遇到了挑战。
随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一批新学堂的涌现,一些新的课程如物理、化学、西医、外语等首先出现在教学当中。
到了20世纪初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和扩建新学堂的情况下,传统的文史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也涌现出不少近代的新学科,从面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格局。
洋务时期的“格致学”逐渐演进为自然科学,在学界的地位不断提升;西方社会学也传入中国,为人侧目;西方哲学被引入,逐渐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经济学也问鼎中华,被学者看好;其他如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地理、天文学等也渐渐萌发了。
辛亥革命催生出一批近代新型学科,这不仅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根基,而且对中国传统的学术起了较大的分解作用。
这应该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变迁的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研究基本是为了“匡国济世”,服务于社会变革的大局。
上海的《新世界学报》鲜明地提出学术要为政治服务,为国家尽“匹夫之责”的观点。
其《序例》明确指出:
“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
曰政曰学。
学者,所以学政也,虽然吾不敢言政。
顾亭林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学,其尽匹夫之责欤!
”[4]这样的认识,在清末民初带有普遍性,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主张从学术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那时的史学、文学、政治学等,无一不是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即使像章太炎、邓实等人关于“国粹”的研究,也是为了“激动种性”,服务于“反清革命”的政治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小说,如《老残游记》、《孽海花》等,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直观写照,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现实中对应地找到,个别人物的名字还使用了谐音。
这种立竿见影式的学术创作,确实对改革现实、发动革命具有促进作用,但却限制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学术研究在较低的水准上徘徊,难以产生传世精品。
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学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从道咸时期的“经世致用”,到办洋务,再到变法维新,基本都是“急用先学”,将学术研究变成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式的政治任务,也就是将学术和政治等同起来。
所以,近代以来的学术大家,多数是政治家或思想家。
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泰斗,除了王国维是真正的学者之外,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基本都是政治家或思想家。
这就使学术上的功利倾向无法逆转了。
事实上,只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由精深的学术文化转化成服务社会的应用性的学术研究才会水涨船高,功效显著。
近代学术忽视高深的纯学术研究,总是在功利的左右下在浅层次上重复,这不仅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也使中国向西方文化的学习问题百出,难以摆脱困境。
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和王国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学术界的领袖,其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学术个性,自然影响巨大。
从总的倾向来看,梁启超善于宏观研究,具有很好的整体把握和提炼能力,而且观点新颖、宣传有力、情感丰富,能够将高深的学术问题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加上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的市场效应,其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
相对来讲,章太炎的学术风格则古典厚重,善于以典雅的文字论述古代学术,在深奥中体现近代精神和时代意义,其治学精神主要影响于上层知识界。
他很自信,乃至目空一切,曾扬言: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5](P474)不过,平心而论,在中国古典文化的近代转型方面,章太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严复虽然是公认的翻译家,但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发展功不可没。
他在翻译西方经典名著过程中不仅介绍了新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等,而且传播了近代的研究方法,如大胆的怀疑精神和归纳法,严复称之为“内籀之术”,[2]也就是西方十分流行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这种科学的实证方法,从辛亥革命时期起步,后逐步发扬光大,一直影响了几代人。
王国维热衷于纯学术研究,尤其是武昌起义后前往日本京都留学,完全醉心于学术殿堂而不可自拔。
他政治上虽然日渐后退,但做学问总是运用新理论和新方法。
他总是“由疑而得信”,“由博以反约”,在大量的证据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论点。
[3](P38)对于做学问时的境界,王国维更视之为成败与否的生命线。
他写道: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XX,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栅处,此第三境也”。
[3](P67)
王国维虽然是在评论古诗时以词人的名句讲这段话的,但他强调的是学术创作时境界的极端重要性。
这既包括心境、意境,也涉及及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方法。
诚然,这里着重讲的是高屋建瓴的新角度、精力集中的刻苦精神和经过深思熟虑后所得出的新结论。
王国维认为,只有有大境界,才会成大学问家。
总而言之,王国维等四大名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推进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更新。
他们虽然切入点不同,学术风格存异,但在突破旧传统的束缚、传播近代学术研究理念、推广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上是完全一致的。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更新,也集中反映在这里。
二
“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是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更新的两朵金花。
“史学革命”对传统的旧史学加以揭露和批判,用进化的理念、综合和演绎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从历史的叙述中获取新意义,求得新观念。
“文学改良”充分肯定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和文学价值,使小说成了时代的“宠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与之相配合,对文言文的批评以及白话杂志的崛起,昭示着文学的语言工具必将有一场变革;而话剧、西方音乐、绘画等的输入和传统戏曲的更新,则有力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近代化。
“史学革命”和“文学改良”,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时期的变异和新生。
扛起“史学革命”大旗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其中尤以梁影响最大。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揭开了《史学革命》的序幕。
梁批评中国传统的史学陈陈相因,缺少生机,至少有四大问题:
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实际变成了24姓的家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置之不理;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历史成了少数英雄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物的兴衰史,百姓和群体完全被排除在外;三是知有陈迹不知有今务,所有的史书只是为死人作“纪念碑”,不能察古而知今;四是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旧史书只注重于单纯的叙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智,益国民。
这四大问题又引申出两大弊端,即写史“能叙述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6](P1)于是,中国古代的史书难懂、难选择、无启发、少情感,不能起到开启民智、教育国民、服务国家的目的。
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变革的需求,必须改革。
梁启超具体提出三项革新:
第一,历史学必须叙述进化之现象;第二,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第三,历史学必须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研究其“公理公例”。
总而言之,梁启超是以进化论为理论指导,试图对传统史学进行彻底改革。
章太炎对“史学革命”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
在《qiú@①书》所收录的《哀清史》、《哀焚书》、《征七略》、《别录甲》、《别录乙》、《尊史》和《杂志》等论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史学观点。
他认为传统的旧史学,一是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一般记事有余,深入分析不足,更缺少对典章制度的理论概括和演绎,至于史学批评,则基本没有涉及;二是内容单一,缺乏对科技、物质生产、文化变迁的叙述和评论,不能够反映人类文化史的演进过程;三是官修史学为主,无端歌颂太过分,浮夸习气盛而不衰,历史的真实性可疑。
为此,必须对旧史学进行全方位的改造。
章太炎提出的具体办法是:
一、加强理性思考和理论抽象,增加史学著作的思想性和理论色彩,“熔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
[7]二、将历史研究和现实沟通,古为今用,既讲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又“鼓舞民气”,面向未来。
[8]三、扩大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讲清楚人类文明史的全貌,应把科技、风俗、宗教、文字、心理等等都加以叙述和研究。
四、要适应史学发展的需要,变革传统的史学体例,增强现实感和方便性,同时吸收西方史学的表现手法,“鉴古知来”。
概而观之,章太炎的主观愿望是要扭转旧史学死气沉沉的局面,增加新内容,改革旧写法,使历史和现实结合,让人们在“朝后看”的过程中“朝前看”,察古而知今。
在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批判旧史、呼吁史学革新的潮流。
当时的许多杂志,都发表专文,讨论“史学革命”。
《新世界学报》发表数篇文章,揭露旧史学的问题,呼吁写人民的历史,讲社会的变化,学西方的史学方法,提高“史官”的社会地位和参政机会。
马叙伦在《史学总论》一文中批评旧史学“实一家一姓之谱牒也”。
要将这种个人“谱牒”的历史学变为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学,就要像西方史学那样“莫不以保国伸民为宗旨,简册所垂,动关全族,故其史为全国之史,非一姓一家所得据为私有,此文化之所以日进也”。
[4]有人还提出广修方志,以实现“史者民之史也”,因为“方志者,纯乎其为民史也”。
[4]陈天华还著有《中国革命史论》,以新的革命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演变,大胆提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颇有新意。
不过,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难免有偏激和不完善的地方。
即使如梁启超、章太炎的言论,也并非绝对正确。
这里只是从总的倾向来看问题,着重肯定的是他们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向往。
因为,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已经到了危机和新生的转折关头,不除旧布新就难以前进,梁启超、章太炎为代表的革新派,恰好充当了催生的“产婆”,使传统的中国史学发生了新的飞跃。
在批判旧史学的过程中,梁启超和章太炎互致信函,商讨按照新的理念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
章太炎的具体设想大致为:
通史必须通,要上下千古,浑然一体,从中提炼新理论、新思想,不要一朝一代地罗列;将典章制度的研究作为重心,“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帝王和人物不作为中心,要有所选择,只讲其中最重要者;要阐明社会的进化和政治变迁的原因及其走向;通史体裁要创新,要自成体系,特色鲜明;“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表记、记传亦居其半”。
[5](P139-140)梁启超基本赞同章太炎的看法,立刻身体力行,在办《新民丛报》之余给青年才俊讲授中国历史,并将讲稿草写为《国史稿》,到1904年已达20余万言。
遗憾的是,梁、章因政治活动频繁,社会交往太多,兴趣太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构想终未实现。
但是,夏曾佑从1904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编写了全新的《中国古代史》。
该书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仅完成从上古到隋朝的写作,但由于理论新、内容新、体裁新,被看作“史学革命”的标志性成果。
该书突破了传统旧史的束缚,以进化的观念、社会变迁的理论,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
它将中国历史分为传说到周初的上古之世、秦汉至隋唐的中古之世、宋至清末的近古之世等几个时期,同时特别注重社会转变时期的研究,对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用墨甚多,见解也新颖独特。
该书还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会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递进、风俗习惯的变异等的评说,在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
在体例上,该书首次使用篇、章、节来编排,前后连贯,又相对独立。
即使在文字叙述上,也革新求变,和旧史书大相迥异,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文体。
总之,《中国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学的拓荒之作,昭示着中国新史学的开始。
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时期寥寥无几。
实事求是地讲,辛亥时期的史学界是学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时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学繁荣期。
“文学改良”和“史学革命”大体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广泛一些。
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文学改良”的开始。
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将小说归为文学的“末流”及认为小说“诲淫诲盗”、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正确看法,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
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
[9]
梁启超此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有影响的学界名流纷纷著文赞同和发挥梁的论点。
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原理》,把欧美、日本的强盛都归之为小说的发达。
其中说: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
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颜。
察天下之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
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
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
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
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
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
说书唱歌,感化尤易。
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
[10]
正是认识到了小说如此强大社会功能,学界许多有识之士才开始大办小说杂志,全力投身小说创作,同时大量翻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作品,一时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小说大繁荣。
那时有影响的小说杂志就有近20种,而且涌现了公认的《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和《绣像小说》四大权威杂志。
小说的种类也层出不穷,什么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等应有尽有。
1908年后鸳鸯蝴蝶派的出现,进一步将言情小说推向了高潮。
据权威人士统计,辛亥革命时期的单行本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
[11](P197)在小说潮的带动下,产生了公认的《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这标志着那时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显示出新的特点:
一、在创作思想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贴近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揭露官场及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提倡社会改革,向往美好生活;二、在创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现手法,以短篇凑长篇,用许多相对独立但内容相近的故事合为一本大书;三、在艺术成就上显现出急就章的倾向,多数作品艺术性不高。
急速变化的动荡社会,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炼,难以产生学术精品。
但是,从中国小说历史长河去观察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时期,由此才进入了新小说的腾飞期。
与小说繁荣互为表里的是诗歌、戏曲、音乐的新飞跃。
戊戌维新时期突起的“诗界革命”,在辛亥时期又进一步发展,诗歌的爱国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昂扬。
黄遵宪、丘逢甲为代表的“新学诗”十分流行。
设立于苏州的南社兴旺发达,还在各地设立了越社、辽社、淮南社等分社,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新知识分子,所创作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
而戏剧的繁荣,又促进了诗歌及文艺创作的发展。
1904年出现了近代第一个戏剧专业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此为阵地,努力宣传戏曲的社会功能,大力呼吁组织“梨园革命军”。
陈独秀著文指出:
戏曲是“社会改良的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
[9]在陈去病、汪笑侬、李叔同等一批戏曲改革者的积极推进下,不仅传统的京剧和地方戏在清末民初有较大发展,而且在1907年,随着“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等话剧社团的涌现,话剧被从日本引入了中国,给中国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
与此同时,西洋音乐、绘画等也涌入中国。
尤其是1907年音乐课正式进入新式学堂之后,伴随着学堂歌曲的发展,音乐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虽然那时的学术界还来不及对这些新生事物加以深刻的学理上的探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并没有出现,但这毕竟给文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改良”新潮的冲击下,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也应运而生了。
1904年,20多岁的北大教授林传甲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
几乎与此同时,黄人用了7年的时间,在1910年完成了内容新颖的《中国文学史》,被学界视作研究文学史的奠基之作。
该书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改变了不少传统的观点,给小说以一定的地位,同时吸收了西方的美学理论,提出文学的真谤就是追求真、善、美,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求真明善”。
[12]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论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部文学史的影响。
比黄人取得更显著成果的是王国维。
他应用西洋哲学重新研究《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认为该书的主旨是“写人生男女之欲”,“及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
[3](P33)在王国维看来,人生即欲望;欲望即生活;人的欢乐痛苦皆由于欲望所致。
而一切欲望之中,男女之欲压倒一切。
《红楼梦》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将此高深的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论一出,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新视角,为许多人所赞许。
1910年,王国维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人间词话》,以其独特的美学思维,按照“意境”的基本思路,从“自然境”、“心境”、“心物境”等多个侧面轻松自如地评说了中国诗词的演变历程。
1913年,王国维写就了《宋元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在追述了宋以前的戏曲渊源之后,对宋代的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以及元杂剧、元剧的结构等作了全方位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之作。
时人评论此书是前无古人,“虽不敢云后无来者”,但想超越极为困难。
[13]平心而论,王国维这些学术成就,不仅初步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也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界增加了新的亮点。
三
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初步确立的,例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
即使像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虽然出现较早,但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才起步的。
这些新学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
1.社会学。
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一些维新志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并零星地有所介绍。
严复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
但此书1903年才由文明编译局出版。
而章太炎所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则在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较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来讲,章氏的社会学影响面要广得多,并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
章太炎对社会学情有独钟,认为找到了一个研究社会的新的途径,他和梁启超讨论编中国通史时,曾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他在《社会学自序》中称:
“社会学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