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概要.docx
《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概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概要.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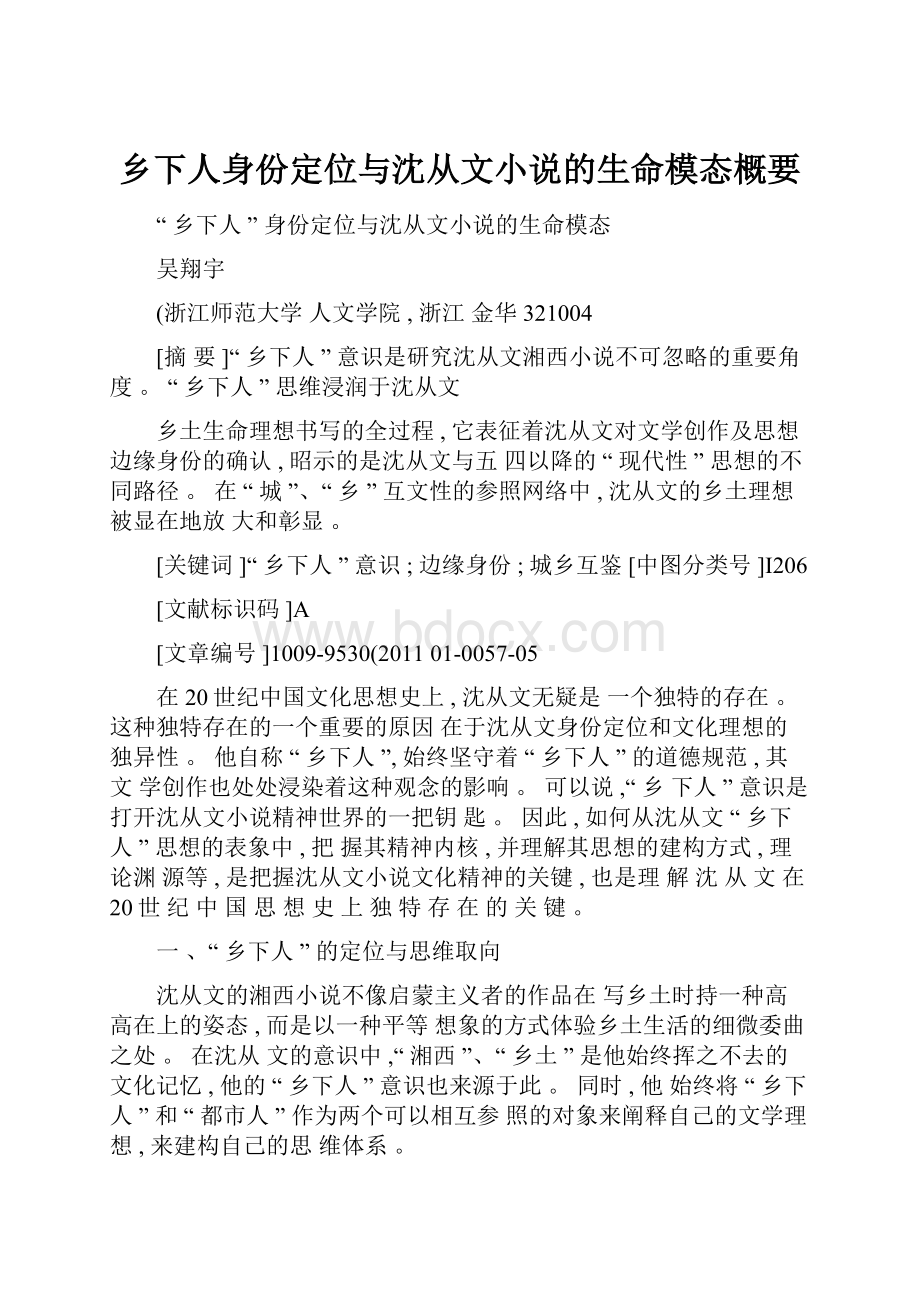
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概要
“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
吴翔宇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乡下人”意识是研究沈从文湘西小说不可忽略的重要角度。
“乡下人”思维浸润于沈从文
乡土生命理想书写的全过程,它表征着沈从文对文学创作及思想边缘身份的确认,昭示的是沈从文与五四以降的“现代性”思想的不同路径。
在“城”、“乡”互文性的参照网络中,沈从文的乡土理想被显在地放大和彰显。
[关键词]“乡下人”意识;边缘身份;城乡互鉴[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101-0057-05
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这种独特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沈从文身份定位和文化理想的独异性。
他自称“乡下人”,始终坚守着“乡下人”的道德规范,其文学创作也处处浸染着这种观念的影响。
可以说,“乡下人”意识是打开沈从文小说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因此,如何从沈从文“乡下人”思想的表象中,把握其精神内核,并理解其思想的建构方式,理论渊源等,是把握沈从文小说文化精神的关键,也是理解沈从文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独特存在的关键。
一、“乡下人”的定位与思维取向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不像启蒙主义者的作品在写乡土时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以一种平等想象的方式体验乡土生活的细微委曲之处。
在沈从文的意识中,“湘西”、“乡土”是他始终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他的“乡下人”意识也来源于此。
同时,他始终将“乡下人”和“都市人”作为两个可以相互参照的对象来阐释自己的文学理想,来建构自己的思维体系。
我们可以通过三篇文章来认识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是如何形成的?
其内涵是什么?
这体现了他怎样的价值取向?
沈从文第一次使用“乡下人”一词,源于1934年12月发表的《萧乾小说集题记》一文。
他说: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
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
快。
”[1]在这里,沈从文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侨寓于都市多年的知识分子,沈从文在都市现代文明的淘洗下,并未褪去其乡土本色,尽管“乡下人”所学的、宗教信仰与“我”的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依然尊敬他们,把他们当朋友。
文所指称的“乡下人”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上而言,进而延伸到个体存在状态及生命价值体系之中。
而“都市人”的生命状态是“我”所不取的,都市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
仿佛和平,其实阴险。
仿佛清高,其实鬼祟。
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
自然是他们的世界。
”“乡下人”的“尺寸和分量”是与“伪思想家为扭曲压
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大相径庭的。
由此,“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对立思维也因此确立了,成为沈从文小说中始终存在的“张力”性存在力量。
1936年1月发表的《习作选集代序》,以“乡下
人”对“你们”、“先生”的谈话为叙事方式,呈现出了两类人不同的创作标准、思维形态、道德评判:
“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
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诡诈……”[2]与《题记》相比较,《代序》中的“乡下人”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主体的思想方法上。
“乡下人”思想的获致除了来自“湘西”这一地域空间的影响,还来自于其特殊民族思想文化的淘洗。
基于此,沈
[收稿日期]2010-12-16
[](
[作者简介]吴翔宇(1980-,男,湖南平江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OFHUAINANNORMALUNIVERSITY
2011年第1期第13卷(总第65期
No.1,2011
GeneralNo.65,Vol.13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3卷
从文进一步提出了“乡下人”的理想生命形态———造“希腊神庙”,供奉“人性”。
在这里,“希腊神庙”
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蕴的“能指”,其“所指”是生命自然舒展不受压抑束缚的古代希腊。
而这种文学理想的确定也成为沈从文小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要提到的一篇文章是《水云》。
在其中,沈从文将“乡下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叙述得非常深刻。
“乡下人”定位已经不再局促于文学层面,更侧重其在思想上的特殊表现。
沈从文六次以“乡下人”自称,这一时期的“乡下人”定位,明显具有思想上的边缘性和作为思想主体的孤独性特征:
“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
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
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
这种思想算是什么?
……一般社会把这种人叫作思想家,只因为一般人都不习惯思想,不惯检讨思想家的思想。
”[3]沈从文创作的都市题材的小说不能定义为纯粹意义的都市小说,因为他并没有从都市的立场、眼光出发来体验都市,而是作为其湘西小说并立而在的一个参照系统,重点是为了突出和彰显他的乡土文化理想。
因此,作为一个思想者的“乡下人”的边缘性也就明确地体现出来了。
“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西方话语”与“本土语言”构成了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始终存在着的一组悖反的两难命题。
一方面,社会的前进发展需要现代的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充裕,另一方面,人的精神更需要人性和自然的庇护。
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人的价值判断和立场是不同的,常常是一个矛盾掩盖另一个矛盾。
我们经常会发问:
在乡土与都市之间,哪里才是我们的“生命之根”?
在西方现代话语与本土传统语言之间哪里是我们的文化之根?
沈从文立足于“乡下人”的立场,批判现代文明,赞美原始淳朴的乡土生命,对“过去”和“常性”生命的倡导,容易给人一种“向后看”的感觉,似乎着力想回到过去那个社会中去,与社会破“旧”立“新”,变化向前的时代精神不一致。
但我们也应肯定的是,他用前瞻性的“历史”眼光冷静地看待“现代性”,并且找到了“现代性”潜在的另一面———对人性、生命的“异化”。
这种反“异化”的头脑正体现了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正如孔范今在关于价值重建与历史观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
“文学视野中的历史观应该有别于政治家乃至史学家的历
实则另有担承,为其尤为关注的应是人性生存的现实状态,在历史中所起的也应是对那些哪怕是历史中心性进步行为的撑拒与张力的作用。
”[4]沈从文在面对“现代文明”、“现代性”这一些社会历史事物时恰恰是一种“对视”的姿态,把政治家、历史家认定是有“历史中心性进步”的“现代科技”、“物质文明”中的弊端毫不掩饰地指出,为此对“现代性”提出质疑。
这“并不是取其反”,而是对“正”(“历史中心性进步”的一种更“现代”、更“历史”的思考。
二、“边缘”身份的心理图示
“边缘”是相对“中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各自有一套自足的话语系统。
这两套话语形成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彼此所处的“位置心理”。
沈从文的“边缘身份”是由“地域边缘”与“文化边缘”两方面相加潜移完成的。
“边缘身份”在与“中心身份”的对照和关系中不断地强化着他的“边缘记忆”和“边缘心态”。
在《多义的记忆》中,德里达将个人的主体记忆看作“对现在之所谓先前在场的引证”[2],这道出了记忆的核心意义,其中的“引”和“证”可视为对习得知识和经验的重复和沉潜。
“湘西”作为一个独特的空间生态,有着自己的生活规律、风俗人情、思维习惯,这些都是当地人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
这种记忆具有社会性,是该社会群体的生活样式,并直接表现为社会心态;还具有继承性和朴素性:
一方面蕴涵悠久的时间积淀,是当地人世代的生存方式的淤积,另一方面又是一种近乎日常的朴素社会意识,在当地人的饮食、起居、生老、病死中反映这种意识。
沈从文出生在湖南边地湘西凤凰县,地处湘、川、黔三省交界,是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地势偏僻,经济文化落后,用沈从文的话来说,该地是“被地图遗忘的角落”。
湖南自古从属“荆蛮之地”,这是相对于北方汉儒文化、中原文化主流系统而言的。
古书早有记载:
“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矛决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予盟。
”(《国语·晋语》周天子认为楚是荆蛮,连参加盟会的资格也没有。
楚人也认同这种言说,楚武王就说过: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5]。
正因为远离中心地域,“乡下人”的意识中也自然打上了一种心理空间的边缘印记:
“湘西虽属湖南,因为地方比较偏僻,人口苗族占比例极大,过去一般接近省会的长沙、湘潭,以至沅水下游的常德人,常叫我们作‘乡巴佬’。
加深轻视,即叫‘苗子’(直到现在,还不易改变,表示轻贱,以为不讲礼貌,不懂道理意思。
”[6]地域的边缘以及少数民族的身份都是沈从文文学创作中难以忽略的文化基因,这些都沉积于作者的内心,成为其建构自己文学理想的思维定式和心理动因。
这个“乡下人”以“边缘地域”的身份步入异质文化
58
第1期
领域(都市“中心地域”时,异质文化的排斥性使沈从文出现种种“文化过敏”,“地域边缘”潜移到“文化边缘”。
1923年,刚从湘西到达北京的沈从文,无疑是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
但这一时期的文本中并没出现明确的“乡下人”自称。
开始以“乡下人”自称,是始于沈从文1928年转入上海后。
身处十里洋场,“乡下人”定位很容易让人想到是在城乡生存经验的对立中得以确立的。
由此,乡村题材的小说获得了现代都市的参照,而使自己的乡土——
—湘西获得了新的意义与价值,湘西宁静自然的生命和美好的诗化记忆被激活和唤醒。
湘西这片边地也成了沈从文割舍不断的“桃花源”。
作家流连忘返地游弋其中,欣赏着田园美景,醉心于和谐自然的人事之中。
湘西世界构成了作家批判都市道德文化的基础和资源。
湘西构建的“生命乐园”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力量来平衡和疏导自己在都市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和焦虑。
他不是闭起眼睛把“湘西桃园”当作避难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保护起来,他还希冀湘西这片“桃园圣地”里健康、和谐、淳朴、自然的生命形态能为治愈都市病态生命提供良方。
同时,沈从文作为都市的“乡土过客”,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修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都市现代物的不了解、现代生存习惯与规则的陌生……使他在大都市中有强烈的自卑心理,不是社会将他推到“边缘”的位置,而是自身文化心理将自己送到了一个远离“中心”的位置。
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本土之子,他对乡土的爱是沉浸于身心的一种近乎宗教的感情。
在现代都市、现代文明新的刺激物的重压下,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落差感和自卑感。
自己像处于都市的“边缘”。
这种“边缘”的尴尬境地使沈从文对自己的乡土、生命、人事有了更体己的眷恋。
他痛苦地感受着湘西社会与“现代文明”所发生的历史“错位”。
以一个“乡下人”的姿态去凸现和放大潜意识中“文化边缘”的心理图示。
对此,有论者认为:
“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
”“在世界性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与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
”[7]沈从文创作的“边缘心理”与“文化边缘”使他脱离了30年代主流文学的话语体系,走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
“文化边缘”反映在创作中的表现主要有:
它有别于正统文化、主流意识规范、主导声音,反映的是一种略带原始、神秘色彩,人物性格趋向野性的奔放,心理意识中有古老习俗、情感、道德准则的积淀。
与此同时,沈从文“侨寓”在都市,面对着都市中种种病态生命,乡土健康和谐的生命成了他理想的“
情地批判和揭露都市生命,思考理想生命的形态、精神以及发展的动向。
那么,“乡下人”理想的生命形态是怎样的?
或者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是如何的?
沈从文的回答是: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
常有山灵,秀腰百齿,往来期间。
遇之者喑哑。
”[8]自然生命与人的生命和谐同一,生命从日常的生活形态中升华出来,具有了庄严的“神性”。
这种境界让人不忍破坏、喑哑难言。
沈从文对湘西生命的“原始性”、“自然性”、“神性”大写特写。
目的是为了:
“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熠熠照人,如烛如金。
”[9]他期望的“生命”是健康向上,充盈生命力的,富于生命之光的。
但他并不一味地耽溺其中,而是以一种理性的眼光观照“生命”的“常”和“变”。
在痛失理想“家园”后,有了“经典重造”(重建“精神家园”的想法。
三、城乡互参共鉴的人生模态
“都市世界”与“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小说一对显在的对照世界,这两种题材占了他小说的一半以上。
沈从文用两套笔墨模式表明了自己的“爱”与“憎”、“褒”与“贬”、“美”与“丑”:
“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来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10]沈从文对“城”与“乡”这个相互存在又相互对立的异质文化领域不仅仅是孤立地叙述其好坏,而且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实验,进而证出优劣和好坏。
“乡下人”的生命形态主要是通过两个层面表现的,一是其具体存在形态,二是通过与“城里人”的参照,即城乡对照,反向揭示并凸显乡下人的特殊存在。
沈从文在很多文章中,将“乡下人”和“都市人”放在一起来评定,其目的恰如他在《绅士的太太》中所说的那样:
“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作为都市的“边缘人”,沈从文很不满都市的现代弊病,在都市里“营养不良”,他说过:
“我发现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
正如一个荒凉的原野,一切在社会上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种子,或道德意义的观念种子,都不能生根发芽。
”[9]所以他把期待的目光撤离了都市,而转向了自己心向往之的故土——
—湘西。
“经过多年的教育,末了还是只能在目前情况中进行工作,可以证明我过去总把自己说成是‘乡下人’的称呼,还有点道理。
因为尽管在大都市里混了半世纪,悲剧性的气质总不易排除。
”[11]在这里,沈从文以湘西健康自然的生命世界作为他的理想基点和评判标准,很显然,都市虚伪龌龊的生命系统是与沈从文自持的尺度不相协
湘西世界的“参照物”。
在城/乡张力场中优劣自现、
吴翔宇:
“乡下人”身份定位与沈从文小说的生命模态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3卷
好坏自明。
“张力”作为诗学概念,是20世纪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对康德“二律背反”命题在文学批评中的一次创造性运用。
作为一种艺术思维与批评手段,它主要地得益于辩证性思维方法的运用。
“城/乡二元互参互证”是作家将两类异质生命(城市生命与湘西生命混杂,相互体验进而价值自明的一种尝试。
即将城里的生命置身于乡下的生活环境中,或者是乡下生命到城里去体验生命。
因此某一元文化的“他者”的命运体现了两种文化的性质和优劣。
各自生命的体悟和命运的沉浮表明城乡异质生命的“水火难容”。
作家的价值判断在这种参照的结局中互证和自明。
《虎雏》写的是一个在大都市生活的“我”很想留住“生长在边壤,年龄只有十四岁,小豹子一样的乡下人”虎雏,对他施以现代的教育方式(音乐、数学、诗歌、工程学等,“希望他在我的教育下成为一个知识界伟人”。
然而,优越的条件、精良的教育方案不能脱去虎雏身上土生土长的雄蛮,最终虎雏在外滩打死一个城里人,只身逃回了湘西。
其实在“我”想留下虎雏并试图改造他时,“我”的六弟已经点破了这种尝试的不可能性:
“那你简直在毁他!
”“……可是你试当真把他关到一个什么学校里去看看,你就可以明白一个作了三年勤务兵在我们那个野蛮地方长大的人,是不是还可以读书了。
”这种“改造”尝试的失败使沈从文对城乡共生互融设想产生怀疑:
“至于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的盒子里,在我的故乡是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情,我还不大知道;我所知道的,是那些山同水,使地方草木虫蛇皆非常厉害。
我的性格算是最无用的一种型,可是同你们大都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比较起来,你们已经就觉得我太粗糙了。
”在散文《虎雏再遇记》中沈从文续写了逃离都市回到湘西的虎雏如虎归山,在自己的生存文化领域里如鱼得水,在与作者一起乘船漂行中又显示了他的勇敢与野性:
一个人在岸上码头将挑衅骂人的士兵痛打一顿。
作者写道:
“我心想,幸好我那荒唐打算有了岔儿,既不曾把他的身体用学校锢定。
这人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
他目前的一切,比起住在城里的大学校的大学生,……派头可来的大多了。
”乡下长大的虎雏,有着乡下人的野性,在异质城市文明的规范和培养下,不能得到改造,并最终逃离城市,回到乡下,在属于和适合自己的文化领域里,自然健康地成长。
《三三》显现出乡下人对都市人最终的恐惧与绝望,三三偶遇来乡下砦子里养病的城里少爷,一度对城里生活有了几丝向往,“她这时忖想……什么时候我一定也不让谁知道,就要流到城里了去,一到城里就不,
鱼,那些鸭子,以及那一匹花猫,同她在一处流去。
”不出一个月,城里人终因三期痨病而死,刚刚滋生的对城里生活的想象笼罩上一层阴影。
三三的“自然生命”与城市青年在乡村社会的“死亡”形成对照。
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
异文化(城市与乡村的水火难容。
《凤子》通过一个文化青年离开京城,返回乡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为线索,传达乡野生命如何救治这位“都市逃亡者”的主题。
把乡野的狩猎、酗酒、决斗、情歌求偶、祭祀仪式都如诗如画地表现出来。
最后沈从文分别借总爷、城里人的话表达城乡的看法。
“我以为城里人要礼节不要真实的,要常识不要智慧的,要婚姻不要爱情的。
”“对生命的解释,生活的意义,比起我们哲学家来,似乎也更明慧一点。
”
虎雏的“逃走”向我们表明:
都市世界不能改造乡下人野蛮的本性,都市生命不能“同化”、“扭曲”乡村生命。
城里青年在乡村的“死亡”昭示:
乡村人对城市生活向往的不切实际,城市不是理想生命所在。
在《凤子》中,城里人在乡村如梦如画的神境中,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生命。
沈从文也曾因“乡下人太少了”,而感到“孤独”,也昭示了自己与“普通社会”的不合。
他于是使用另一词自称,即“疯子”或“痴汉”。
如《主妇》中就有:
“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我的生命价值观即越转近一个疯子。
”之所以自称“痴汉”则因为:
“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
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
”[12]西方学者瓦尔特·F·法伊特认为:
“理解有两个基本方面:
理解他者和疏者。
”[13]他的意思是如果读者与他者命名的话语完全一致,那么读者就失去理解的条件,结果也只有误读;读者如果跳出他者命名的框架,才能获得理解真实本质的权利。
显然,“疯子”、“痴汉”来源于与“都市人”认定的生命形态相异的视角,是最适合用“疏者”化角度来解读的。
在“疯子”、“乡巴佬”似乎偏离“都市人”生命模态的言行中,洞悉到了被普遍社会意识盲视和遮蔽的社会本质。
其独特的“疏者”世界都是冷静和理智精神的交汇。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