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docx
《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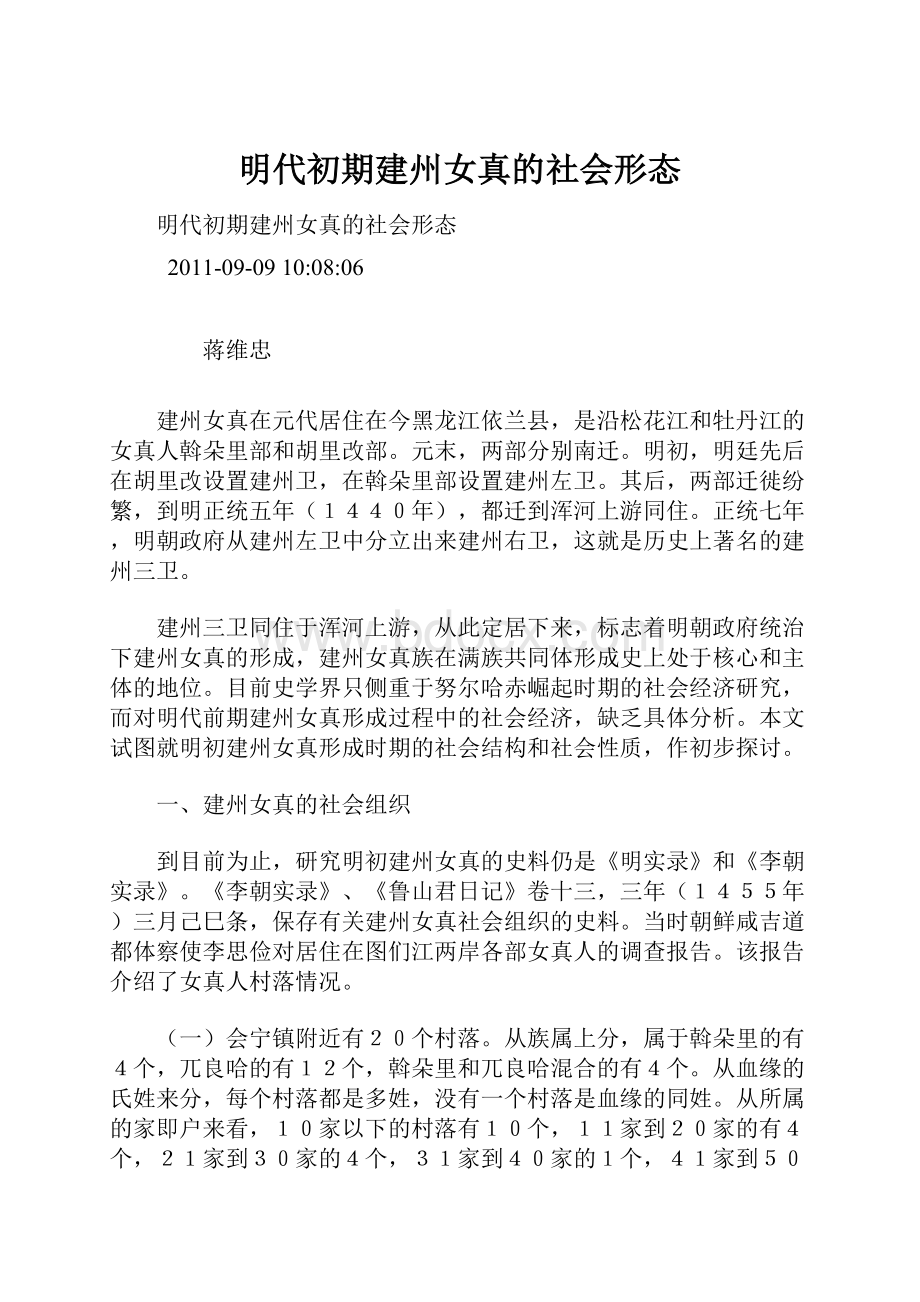
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
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
2011-09-0910:
08:
06
蒋维忠
建州女真在元代居住在今黑龙江依兰县,是沿松花江和牡丹江的女真人斡朵里部和胡里改部。
元末,两部分别南迁。
明初,明廷先后在胡里改设置建州卫,在斡朵里部设置建州左卫。
其后,两部迁徙纷繁,到明正统五年(1440年),都迁到浑河上游同住。
正统七年,明朝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立出来建州右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建州三卫。
建州三卫同住于浑河上游,从此定居下来,标志着明朝政府统治下建州女真的形成,建州女真族在满族共同体形成史上处于核心和主体的地位。
目前史学界只侧重于努尔哈赤崛起时期的社会经济研究,而对明代前期建州女真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缺乏具体分析。
本文试图就明初建州女真形成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作初步探讨。
一、建州女真的社会组织
到目前为止,研究明初建州女真的史料仍是《明实录》和《李朝实录》。
《李朝实录》、《鲁山君日记》卷十三,三年(1455年)三月己巳条,保存有关建州女真社会组织的史料。
当时朝鲜咸吉道都体察使李思俭对居住在图们江两岸各部女真人的调查报告。
该报告介绍了女真人村落情况。
(一)会宁镇附近有20个村落。
从族属上分,属于斡朵里的有4个,兀良哈的有12个,斡朵里和兀良哈混合的有4个。
从血缘的氏姓来分,每个村落都是多姓,没有一个村落是血缘的同姓。
从所属的家即户来看,10家以下的村落有10个,11家到20家的有4个,21家到30家的4个,31家到40家的1个,41家到50家的3个,50家以上的1个。
(二)锺城附近有8个村落,从族属上分,都属于兀良哈,从血缘的氏姓上分,单一姓的血缘村落有1个,其余7个是多姓。
从所属的家来看,伊应巨地方的血缘村落,没有记载家数,只记“右人族类三十余名”,可能仍保持氏族组织,所以只记“族类”。
其余7个村落中,10家以下的有3个,11家到20家的有2个,另外2个村落都是20家以上。
(三)稳城镇附近有5个村落。
从族属上分,属于兀良哈的有4个,属于女真的有1个。
从血缘上分,没有单一姓的血缘村落,都是多姓。
10家以下的3个,11家到20家的2个。
(四)庆源镇附近有10个村落。
从族属上分,属于兀良哈的4个村落,属于女真的6个。
下训春1处同住3个村落。
2个是女真人的,1个是兀良哈的。
从血缘上看,都是多姓。
10家以下的5个,21家到30家的3个,40多家的1个,还有1个村落达61家之多。
(五)庆兴镇附近有7个村落。
从族属上分,属于骨看兀狄哈的有5个,其中2个是同一姓的血缘村落。
属于女真的有2个。
另外,庆兴45里江内阿乙阿毛丹地方有1户女真人单独居住,没有记载所属村落。
除了骨看兀狄哈2个血缘村落外,其余5个,都是多姓。
10家以下的5个,11家到20家的2个。
上述女真村落共50个。
其中斡朵里部4个,胡里改部即兀良哈的28个,两者混合的4个,共计36个,属于建州女真,其余14个村落不属于建州女真。
女真和骨看兀狄哈是建州左卫迁走后,乘虚迁入图们江左,即《李朝实录》上的“江外”,和斡朵里、兀良哈的村落交错在一起的。
从上述女真村落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建州女真社会组织状况:
一、建州女真的部落,是地缘集团,已经形成为村落。
基本上是一个部落在一个村庄,上述50个部落中,有45个部落是各自居住在一个村庄里。
只有2个兀良哈部落同住一个村庄。
2个女真部落和一个兀良哈部落同住一个村庄。
没有一个部落分住两地的。
这50个部落中只有3个是单姓的血缘部落,其余全是多姓即非血缘团体。
不仅大部落是多姓,就是10家以下的村落,也多为三、四姓。
如上甫乙下村落,7家竟是两族4姓。
多家舍仅住2家,还不同姓。
凡察一姓,竟分散在5个不同的村落中。
父子、兄弟分居于不同的村落,可见已失去了氏族的血缘纽带,早已不是血缘氏姓部落,而是地缘的部落,即村落。
由此可知,就姓而论其血缘关系,是已经从“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1)]。
——但是“其成员间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2)]。
部落在发展过程中的两重性,地缘性已经居于主要的地位。
血缘性的组织仍跨村落的长期保留着。
二、建州女真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是家,即户。
那么建州女真的“家”是怎样分法?
有何特点?
下面仅举三条材料加以剖析。
被掳逃出的汉人奴隶阿家化说:
“建州贼松古老家是“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3)]。
建州卫首领李达罕(即光者秃,李满住之孙)的第三子沙乙豆(即撒鲁都)向朝鲜国王李xiē@①请赐鞍马说:
“父达罕关我云:
前者,子包“罗大(即弗喇达,长子),李多乙之介(即多之哈,次子)受大国鞍马而来,不胜感戴。
然皆别居,无益于我。
汝则同居一家,幸蒙上恩,又受鞍马而来,则我得而资之矣”[(4)]。
建州一酋长金主成可的女婿童尚时说:
“主成可率二子同居,长子、次子及我则各居”[(5)]。
这三家都是建州女真的酋长,而且李达罕是建州卫的首领,可是他们的家庭成员都不多。
首先,建州女真的家是小家庭。
是一家一户,小家小户。
其次,建州女真的分家是先长后幼,结婚则分居。
再次,家和“个体经济”是同一个意思。
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经济单位。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建州女真的小家小户的个体经济家庭,已经超越了氏族制度末期野蛮阶段的家长制的家庭公社,超越了“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6)]的家庭公社。
但是这种小家庭和现代意义的小家庭根本不同。
其本质性的差别,一是它是村落组成的单位,对部落和部落联盟承担参加狩猎和战争的义务,有分得狩猎和战争所获的权力。
从这一点来说,建州女真的家庭个体经济,受着部落的制约,它还没有超出“野蛮阶段”的家庭。
三、部落或部落联盟,基本上是族缘性的,但是已经出现了破坏和超出族缘关系的因素,部落联盟酋长也超出了部落联盟的界限。
《李朝实录》中有下列一段记载:
永乐二十二年(1124年)“婆猪江住野人李都巨等5名,指挥童凡察等41名,……各月到闾延郡小甫里口子……皆欲乞粮为生”[(7)]。
凡察是建州左卫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建州左卫指挥使,也是部落的首领之一。
前年,随其兄自辉发河上流迁到图们江下游会宁一带,迁徙时第三批的领队。
此时,却到婆猪江(佟家江)建州卫胡里改部李满住管下任指挥。
其后,正统初年(1436年),凡察又回到建州左卫斡朵里部,猛哥帖木儿死后,又代替其成为斡朵里部首领,职掌建州左卫事。
凡察出入于斡朵里部落联盟和胡里改部落联盟,更说明两个部落联盟的界限处于被突破的过程。
这对建州女真族的形成上,有着历史性的意义,它标志着建州女真的形成。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说过: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的团结起来。
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
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了”[(8)]。
十五世纪中叶的建州女真正处于这种状态。
关于建州女真的村落密集情况,《李朝实录》记载颇多。
密集的村落,排除了“彼此由广大边境地带隔离开来”[(9)]的状态。
建州女真社会氏族制度的三级组织,更处于悄悄地但又是激烈的变革之中,一方面保存着氏族制度的外壳,另一方面,血缘关系的姓和族的联系在瓦解、消失着。
建州女真的这一变革过程,也正是由“野蛮”进入“文明”的过程。
二、建州女真的奴隶占有形态
“生产关系的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10)]。
在已经产生阶级对立的社会里,生产关系中起着决定性质作用的是阶级关系,即不同阶级的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联系,对立着的具体特点是什么。
这种特殊性规定着其社会的特殊性。
明代初期,在建州女真的社会里,存在着大量的掳掠来的汉人奴隶和朝鲜人奴隶。
《李朝实录》中记载:
斡木河,婆猪江等外地面散住野人等类,与叛人杨木答兀结为群党,掳掠辽东开元等处军民男妇及本国边民为奴使唤,前头被掠人口等,不胜艰苦[(11)]。
建州女真掳掠汉人(或称唐人)和朝鲜人为奴隶的情况,是十分惊人的。
据《李朝实录》记载,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十年间,汉人奴隶自建州女真逃来朝鲜,被朝鲜政府送还辽东都司的有“五百六十六名”[(12)]。
至景泰三年(1452年)20年间“在先人口陆续逃来转解辽东共该八百三十四名,又于近年辽东等处被掠人口,或逃来小国边邑,或野人带来遂为边将收夺,节次解送共计一百六十九名”[(13)]一千零三人。
此外,明朝政府派遣官员直接从建州左卫讨还被掳为奴的汉人为566人[(14)],总计1500多人。
此后,这种从建州女真逃来朝鲜的汉人奴隶,在《李朝实录》上,一直不绝于书。
建州女真当时的人口,估计约为一万五、六千人[(15)],逃亡的汉人奴隶和建州女真人口的比例是1∶10,而得以逃脱的只能是少数,绝大部分仍处于被奴役地位。
由此可知,建州女真社会中,仅掳来的奴隶,就占有很大的数量。
建州女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奴隶来源,是买卖奴隶[(16)]。
猛哥帖木儿曾对朝鲜官员说:
“管下人将牛马衣服买得人物,逋入庆源、镜城之境,则以杨木答兀管下人例论,专不送还,管下人痛心欲掳掠庆源龙城人物,以偿所亡”[(17)]。
凡察曾多次向朝鲜政府提出“抗议”,抗议将其逃跑的买来的汉人奴隶解送辽东,杨言“将掠庆源、城镜、甲山、闾延之人为奴使唤”[(18)]。
对待这件事朝鲜政府十分为难,曾准备“实属凡察所买者,勿受,送还”[(19)]。
凡是女真奴主持有买卖文书(“文券”)为证据的”[(20)],都还给女真奴主,可是怕明朝政府谴责。
如果照例解送辽东,又怕引起边衅。
如果给以偿价,收买下来再送辽东,还怕“野人若见我买被掳汉人,谋利之徒,争来买(卖)之……援例求偿”,“必将所掳,不论老幼,事必卖之,则边将难支矣”[(21)],朝鲜政府受不了。
建州女真社会不仅有汉人奴隶和朝鲜人奴隶,其本族人也有沦为奴隶的。
正统七年(1442年)朝鲜政府给明朝政府的报告说:
“凡遇中国军民,自辽东逃来人,不拣汉人、女真人……随到随解”[(22)]。
《李朝实录》上从来是记载逃来的奴隶的族别的、如汉人、唐人、本国民、本国边民。
建州女真社会大量奴隶,是用于农业生产。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23)]。
建州女真社会也是如此,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之有无,关系到女真奴隶主的生存。
《李朝实录》记载:
凡察与土官金得渊说道:
我的使唤人口,虽系上国人民,既已作妾为奴,如今农忙月被夺转解,深以为闷[(24)]。
江界满浦口子相对:
彼土皇城(今集安县附近)住兀良哈张三甫,与镇抚安有谦说:
我等奴婢,汝节制使节送京师,使我等不得存接。
故……乘隙渡江,剽掠江边农民,可以偿吾所亡[(25)]……”唐女三之,莫只,被掳野人,转卖于柳尚冬哈,逃来锺城。
尚冬哈来言曰:
我以牛马购奴婢,若不及还,亲操耒耜必矣。
乞还之[(26)]。
不仅建州女真使用奴隶耕作,海西女真也是如此。
《明实录》有所记载:
锦州卫指挥佥事吴良奏:
臣奉命使海西,此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掳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窜者,久陷胡地,无不怀乡[(27)]。
从上面史料可知,所谓“使唤人口”“奴婢”等,不可误认为不事耕耘,仅供家内使用的家用奴隶。
恰恰相反,主要是“驱使耕作”,“操耒耜”的农业生产奴隶。
综上所述,可知建州女真在明代前期,是以奴隶来从事农业生产的。
这种奴隶,在其社会总人口的比例,是相当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承担者。
那么建州女真社会的奴隶占有是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呢?
《李朝实录》记载汉人奴隶阿加化说:
“俺年十四岁时,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
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28)]。
据此可知松古老的一家,是由“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29)]。
它的特点,“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是父权”[(30)]。
父权体现了个体家庭私有,奴隶、牛、马和其它财物,都是家长的财产。
这种家庭形式,恩格斯称之为“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31)]的家庭,这种奴隶是“家内奴隶”,“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了成文历史的领域”[(32)]。
即进入了奴隶制时代,这种家长制家庭占有的家内奴隶,是早期奴隶的占有形态。
但是,建州女真社会的家长制家庭和恩格斯所说的“完善的典型”的家长制家庭不同,已经超越了“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
“住在一起”[(33)]的阶段,而是,分为小家小户的小家庭的家庭奴隶占有。
具有了“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34)]之一种形式,“古代的劳动奴隶制”[(35)]的性质。
这种奴隶占有形态的特点,在于奴隶没有个人经济,他的生活一切,全包括在奴隶主家庭内,从事生产劳动。
这种奴隶,有的是单身奴隶,有的是有妻的。
如:
1426年被掳逃来(朝鲜的)汉人李善辈(冀?
)妻奴奴、子拘子、女唆儿等[(36)]。
1436年(徐)庆守将有小三口,自野人逃来。
有野人指挥佟木哈追来,请还日……吾买于辽东,为奴使唤已有年矣。
偷予世传指挥诰命及杂物而逃”[(37)]。
上述两例说明这种奴隶是有妻小的,但是奴隶的配偶,“只被看作简单的同居”[(38)]。
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庭,即没有自己的经济。
这是一种占有形态:
家内奴隶。
另一种形态是奴隶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可以称之为“家庭奴隶制”这一类型的特点是不仅奴隶有妻小,而且有自己的家庭经济。
《李朝实录》记载:
薰春地面,移接十户,夜春地面移接二户,共十二家。
本非猛哥帖木儿管下,乃杨木答兀所虏开阳(开原)人也。
权豆父子(即猛哥帖木儿和权豆)被杀后,或乃居斡木河或移夜春,或移薰春。
前此凡察率兵与薰春兀良哈争十二家[(39)]。
这12家可以迁移,不属于某女真人家庭所占有、而属于部落酋长管辖,凡察和薰春兀良哈动用兵力,争夺这12家,正说明这一点。
又有:
“自骨看处逃来唐人金吾将等3人,……其妻曰野人之女,因有从夫之道,且其子亦是唐人之子。
”朝鲜政府决定送还辽东,为防止发生“边衅”,“人各计正布十二匹,绵布四匹,盐三石,以给骨看。
因抚之曰:
“国家怜恤汝等,有是赐”[(40)]。
这个和“骨看”女真人结婚的汉人奴隶金吾将一家,不属于骨看人某一家,而属于骨看部落,所以朝鲜政府的赏赐是给骨看“汝等”的。
这种家庭奴隶制,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奴隶形式”[(41)]。
马克思在论述罗马奴隶制社会农业时指出过:
“另一方面则把地产划分成许多小块租地,租给隶农耕种,也就是建立起了依附小农——后来的农奴的先驱——的佃小农户,确立了一种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的生产方式”[(42)]。
这也是一种奴隶占有形态。
其根据是因为他们的人身被酋长所占有。
它和中世纪封建农奴根本不同,“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43)]。
这种被掳来的有家庭经济的奴隶,并不是由于占有土地离不开,才随土地而依附,沦为农奴的;恰恰相反,是由于被掳来造成人身被占有,才被建州女真酋长驱使在指定的土地上耕作。
所以,尽管以徭役或产品的形式交纳给主人,它也不是封建制生产关系,仍是奴隶制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44)]。
建州女真的奴隶制是完全符合马克思揭示的这一普遍规律的。
奴隶制正是从现代家庭的萌芽时开始的。
它包含着隶属于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内奴隶,也包含着被酋长以部落名义占有的家庭的奴隶。
这种有家庭的向部落提供徭役或产品的奴隶,其隶属形式很类似农奴,所以马克思用了农奴制一词,它是和中世纪的农奴制不同的。
这种依附的小农,它在建州女真社会中即是早期的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又是“后来的农奴的先驱”“孕育着中世纪生产方式的萌芽”。
“建州女真社会的这两种奴隶占有形态,就是建州女真奴隶制社会的阶级对立的具体形式。
三、建州女真生产方式及其社会性质
原始社会的部族,一般是在征服的过程中进入奴隶社会的。
当然,征服是不会创造出新的社会制度来,因为暴力不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和改变的根源。
只有在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前提下,征服做为一个必要条件,才能促进从原始公社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转化。
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
建州女真人进入阶级社会,尽管有些具体的特殊性的一面,但是,基本上仍是符合这一规律的。
仍然是其社会内部,在向奴隶制过渡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的前提下,掳掠邻人的过程中,才促使其发展成为奴隶制社会的。
女真人在中国东北地区东部长白山脉的山地之中,他是生长繁衍在“高山峻岭,带江连排”,所活动的地方都是“山路险恶,骑不并行”[(45)]。
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女真人世世代代“以射猎为生”,渔猎经济,从来是其谋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
[(46)]“畜牧的形式,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47)]。
女真人从来没有从森林区域走出,来到水草丰盛的草原,所以也就不可能分离出来游牧部落。
女真出名马,历史上早已著称,建州女真的部落都养马。
如李满住直辖部落,“率三十余户居焉,常养马十二匹”其岳家蒋家(李张家)在婆猪江南岸,“率三十户居焉,常养马十四匹”,马是建州女真的生产工具。
马对于女真人来说,和牛、羊对契丹、蒙古等族来说,是不同的。
不是其生活资料。
30余家仅12匹或14匹,每家不足1匹。
这和鄂伦春人的狩猎经济相验证便可证明了。
鄂伦春人也养马,以马为狩猎的工具,但不能因有马,就认为是游牧民族,而仍是狩猎民族。
建州女真也是如此。
建州女真不能分离出畜牧经济,其社会内部也没有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因之也不可能在女真社会内部“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48)]。
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下,自然条件的单一性,长期地决定了建州女真的生产方式的单一性。
明代前期,建州女真受汉族和朝鲜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其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
这在建州女真的生产工具上表现特别明显。
“往时野人屈木为镫,削鹿角为镞,今镫镞皆用铁”,“野人处亦有炉工冶匠”[(50)]。
建州女真社会也出现了农耕,明朝对建州女真的供应物品中就有铁铧一项[(51)]。
明朝政府准许建州女真“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52)],允许“建州女真等卫野人头目”由北京返回本卫时“沿途买牛带回耕种”[(53)]。
宣德八年(1433)朝鲜的边将崔阎德进攻建州卫,在其缴获中,有铠甲、角弓、铁镞、环刀、枪刀、鼓、马鞍、弓袋、以及牛马等。
其中大量是铁制兵器[(54)]。
建州女真人在婚娶聘礼中“婿家先以甲胄弓矢为币”[(55)]。
上面所列举的材料,都说明建州女真社会到明初其生产力已发展到铁器时代,并且有了很精锐的农具和军械,耕作是铁铧牛耕,战争是弓矢枪刀,但是,渔猎仍是主要的经济部门。
《李朝实录》记载建州女真狩猎的情形是:
“其渔猎之时,则自三月至五月,又自七月至十月,人数多不过三十,少则不下十余。
……或曰:
野人渔猎,率以二十余人为群,皆于郁密处结幕,每一幕三、四共处,昼则游猎,夜则困睡”[(56)]。
一个酋长,率领所属部落各家的“壮丁”,分为若干幕,进行狩猎。
后来满族的农幕,应该是从这种猎幕演变而来的。
上述史料足以说明建州女真人的狩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
建州女真社会的狩猎经济,尽管其生产工具已经不是kǔ@②弓石@③,而是角弓铁镞、钢枪钢刀,甚至和汉人、朝鲜人的先进的封建文化的生产工具一样,而且手工业有了高度发展,成为各村落里个别家户的专业,如和松古老“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炉匠弓人焉”[(57)]。
但是,这种炉匠弓人,是为狩猎和战争服务,制造弓箭刀枪。
建州女真社会狩猎经济的单一性,其内部交换即商品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整个社会长期的保持部族的集体狩猎经济的生产组织或武装组织。
各家各户的“丁”即劳动力,都被组织到这一生产组织中来。
生产工具和武器都属于私人的,狩猎的收获,战争的缴获,都通过分配,转为家庭的财富。
如杨木答兀虏来的人口“为猛哥帖木儿、弟凡察、于沙哈、子权豆等分执为奴使唤”[(58)]。
这种狩猎经济的生产组织,是不容易贫富分化的。
可是,建州女真的部族显贵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集团。
如猛哥帖木儿、李满住都是世袭的酋长,部族内强和弱、贫和富的差别,已经很明显。
李满住说:
“予之奴婢十口曾逃入江界”[(59)],逃跑的奴隶就有十人,被朝鲜政府礼宾寺收容使唤,可见其奴隶之多。
明初,女真的朝贡和互市,更促进建州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
自永乐元年(1403年)女真贡马以来,明对朝贡和互市来的女真酋长,给予优厚的抚赏和回赐,抚赏是政治性的,是对朝贡人的赏赐,回赐是给所贡献品的价值。
此外还有街市交易。
女真酋长是十分愿意来北京的,自洪熙元年(1425年)十二月到宣德元年一月一日间,《明实录》记载女真朝贡24次,其中9次记有人数为1480人,可见人数之多。
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改变无限制的自由来京情况,正统四年(1439年)规定一年一贡及三年一贡,人数也有规定,但当年来京进贡的女真人仍不少。
酋长得到抚赏和回赐,使之远比一般成员富裕的多起来,贫富差别、阶级分化更为迅速的发展。
朝鲜政府方面对属其管下的女真各村落的人户也分等区别对待。
各村落酋长都定为一等,“虽非酋长,部落族类强盛亦以一等施行,其余个人以强弱分为二、三、四等”[(60)]。
朝鲜政府以强弱分等,根据“族类强盛”和“麾下名数”多寡,并不按父祖之血统,同一家庭之父子、兄弟之间地位也很悬殊。
剩余劳动产品和贫富差别的出现,就是建州女真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的条件。
在这种社会情况下,狩猎经济和战争掠夺,自然是相通的。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
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61)]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富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62)]。
建州女真正是如此。
《李朝实录》记载:
彼贼等退计四、五十年间,自永安道移来,居住两卫间,别成一落,八十余户,自号歧州卫,一年十一名一朝中国而已。
不事农业,以作贼为事,所虏人马,转卖深处,以生为利”[(63)]。
这个歧州卫居住建州卫和建州左卫之间,是建州女真的一个村落,一年一度有11人到北京朝贡,显然属于中国明朝政府管辖。
这个部落正是“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富而不断进行的抢劫”的部落。
其实,不仅歧州卫,建州卫、建州左卫莫不如此,《李朝实录》上记载这种虏掠、抢劫是不绝于书的。
问题在于不是“部落对部落的战争”,而是对具有先进的封建文化的明朝或朝鲜政府的人民、财富的抢劫。
建州女真隶属明朝政府管辖,是中国明朝的少数民族,可是建州女真又不断地抢掠明朝人民和朝鲜人民为奴隶来发展农业。
所以就出现了“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64)]的状态。
建州女真本来已产生了农耕,猛哥帖木儿早在第一次居住在图们江下游时已经“耕农”[(65)]。
吸收了汉族和朝鲜族的先进农业技术,更促进了建州女真虏掠汉人和朝鲜人为奴隶来发展农业,农业成为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时,奴隶制度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毕恭在《辽东志》卷七中引《东戍见闻记》:
“建州、毛怜,乐住种”,“诸夷(包括建州女真)皆善驰猎,建州女真多喜治生”的记载是正确的。
《李朝实录》记载所见到的建州卫所居的婆猪江“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或“兀剌山南麓婆猪江之东音闲之平,见人家二户,有男妇十六,或耕更耘,放养牛马”,正是这种家内奴隶,当然也包括女真人主子在内的生产情况。
因为女真人是小家庭,二老加上未婚子女,是不会有很多人的。
二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