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docx
《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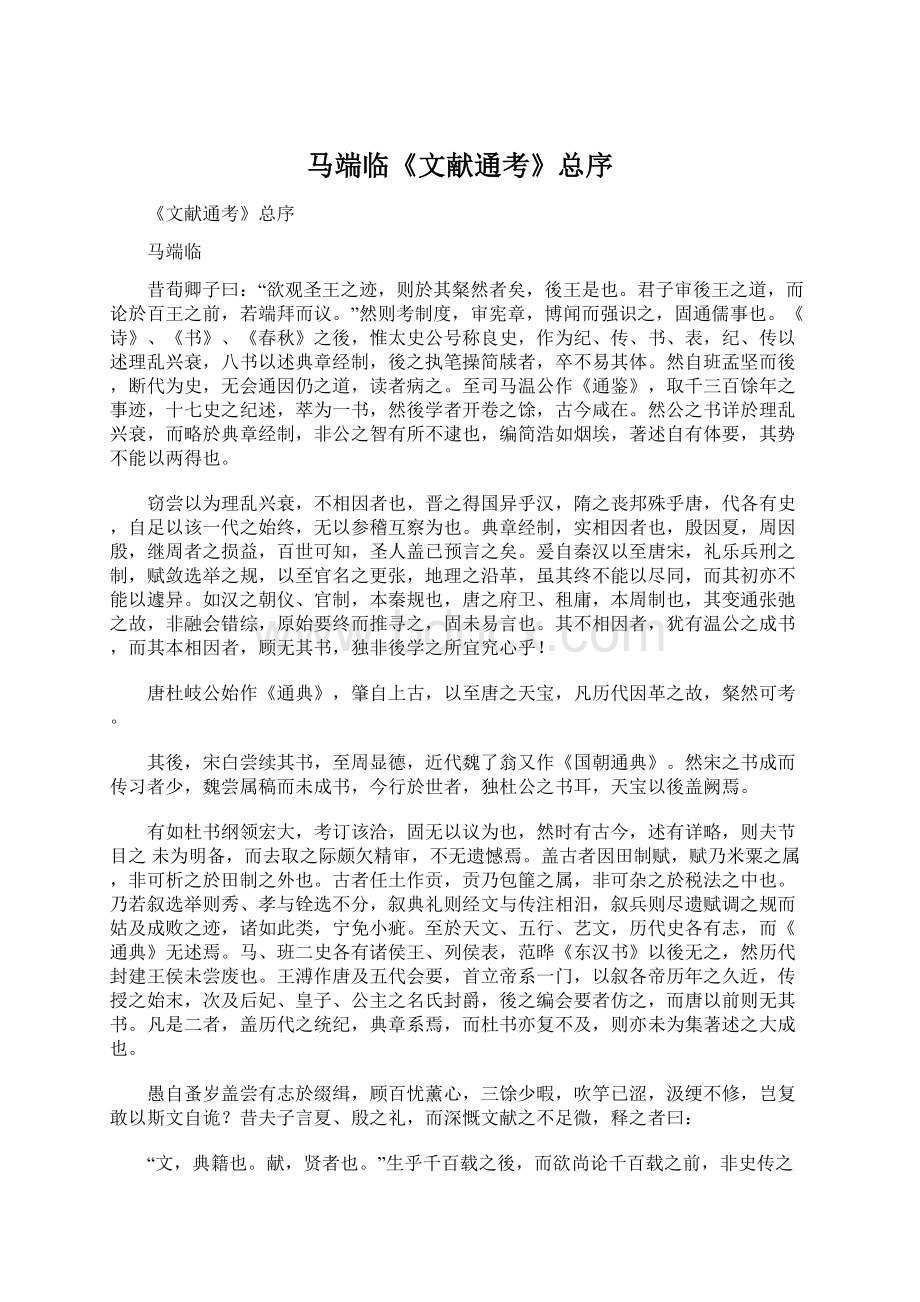
马端临《文献通考》总序
《文献通考》总序
马端临
昔荀卿子曰:
“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君子审後王之道,而论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
”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
《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
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後学者开卷之馀,古今咸在。
然公之书详於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
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
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
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本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後学之所宜究心乎!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
其後,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
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於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後盖阙焉。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
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
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於税法之中也。
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
至於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
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後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
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
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於缀缉,顾百忧薰心,三馀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
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微,释之者曰:
“文,典籍也。
献,贤者也。
”生乎千百载之後,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
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
窃伏自念:
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於文献盖庶几焉。
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
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
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
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後焉。
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於志。
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为也。
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
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钅术心,亦何所发明?
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
後之君子,傥能芟削繁芜,增广阙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车之愧,庶有志於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
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於官。
民仰给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
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
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
虽其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
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
秦於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
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ゥ。
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
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於商鞅。
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於杨炎。
三代井田之良法坏於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於炎。
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後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於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
凡七卷。
生民所资,曰衣与食;物之无关於衣食而实於用者,曰珠、玉、五金。
先王以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用之物,作为货币以权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刀、布即古钱之名)。
然珠、玉、黄金为世难得之货,至若权轻重,通贫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铜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来,未之有改也。
然古者俗朴而用简,故钱有馀;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钱不足。
於是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
数多而直轻,则其致远也难,自唐以来,始创为飞券、钞引之属,以通商贾之厚赍贸易者。
其法盖执券、引以取钱,而非以券、引为钱也。
宋庆历以来,蜀始有交子;建炎以来,东南始有会子。
自交、会既行,而始直以楮为钱矣。
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用之物也。
以其可贵且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
至於以楮为币,则始以无用为用矣。
举方尺腐败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饥藉以食,贫藉以富,盖未之有。
然铜重而楮轻,鼓铸繁难而印造简易,今舍其重且难者,而用其轻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铜之禁,上无搜铜之苛,亦一便也。
作《钱币考》第二。
凡二卷。
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
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
投之所向,无不如意。
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才益乏而智益劣。
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则惭;农安於犁锄,而问之刀笔则废。
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满隅者,总总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
官既无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只以身为累矣。
作《户口考》第三,叙历代户口之数与其赋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
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
郡有守,县有令,乡有长,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在军旅则执干戈,兴土木则亲畚锸,调征行则负羁绁,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
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劳,其理则然。
然则乡长、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户役矣。
唐、宋而後,下之任户役者,其费日重;上之议户役者,其制日详。
於是曰差,曰雇,曰义,纷纭杂袭,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
噫!
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三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後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至此极乎!
作《职役考》第四,叙历代役法之详,而以复除附焉。
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
一曰山泽,茶、盐、坑冶是也;二曰关市,酒酤、征商是也。
羞言利者,则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而欲与民庶争货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
善言利者,则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强擅之,关市货物之聚,而商贾擅之,取之於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於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
自是说立,而後之加详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则并其利源夺之,官自煮盐、酤酒、采茶、铸铁,以至市易之属。
利源日广,利额日重,官既不能自办,而豪强商贾之徒又不可复擅,然既以立为课额,则有司者不任其亏减,於是又为均派之法。
或计口而课盐钱,或望户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计其顷亩,令於赋税之时带纳,以求及额,而征榷遍於天下矣。
盖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强、商贾之徒,以优农民,及其久也,则农民不获豪强、商贾之利,而代受豪强、商贾之榷。
有识者知其苛横,而国计所需,不可止也。
作《征榷考》第五,首叙历代征商之法,盐铁始於齐,则次之;榷酤始於汉,榷茶始於唐,则又次之;杂征敛者,若津渡、架之属,以至汉之告缗,唐之率贷,宋之经、总制钱,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
凡六卷。
市者,商贾之事也。
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所贡而有馀,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
而市之说则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输,曰市易,曰和买,皆以泉府藉口者也。
籴者,民庶之事。
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馀,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
而籴之说则於齐桓公、魏文侯之平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义仓,曰和籴,皆以平籴藉口者也。
然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
方其滞於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於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
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
然沿袭既久,古意浸失。
其市物也,亦诿曰榷蓄贾居货待价之谋;及其久也,则官自效商贾之为,而指为富国之术矣。
其籴粟也,亦诿曰救贫民贱钱荒之弊;及其久也,则官未尝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积粟之入矣。
至其极弊,则名曰和买、和籴,而强配数目,不给价直,鞭笞取足,视同常赋。
盖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
作《市籴考》第六。
凡二卷。
《禹贡》,八州皆有贡物,而冀州独无之;甸服有米粟之输,而馀四服俱无之。
说者以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赋所当供者市易所贡之物,故不输粟,然则土贡即租税也。
汉唐以来,任土所贡,无代无之,著之令甲,犹曰当其租入。
然叔季之世,务为苛横,往往租自租而贡自贡矣。
至於珍禽、奇兽、袤服、异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谄之臣希意创贡,往往有出於经常之外者。
甚至留官赋,阴增民输,而命之曰“羡馀”,以供贡奉,上下相蒙,苟悦其名,而於百姓则重困矣。
作《土贡考》第七。
凡一卷。
贾山《至言》曰:
“昔者,周盖千八百国,以九州之民养千八百国之君,君有馀财,民有馀力,而颂声作。
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而不能胜其求。
一君之身耳,所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
”然则国之废兴非财也,财少而国延,财多而国促,其效可睹矣。
然自《周官。
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内府,且有“惟王不会”之说,後之为国者因之。
两汉财赋曰大农者,国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
唐既有转运、度支,而复有琼林、大盈;宋既有户部、三司,而复有封桩、内藏。
於是天下之财,其归於上者,复有公私。
恭俭贤主,常捐内帑以济军国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娱,故财匮而其民怨。
此又历代制国用者龟鉴也。
作《国用考》第八,叙历代财计首末,而以漕运、赈恤、蠲贷附焉。
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为首,才能次之。
虞朝载采,亦有九德,周家宾兴,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
两汉以来,刺史、守、相得以专辟召之权;魏晋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
皆考之以里之毁誉,而试之以曹掾之职业,然後俾之入备王官,以阶清显。
盖其为法,虽有愧於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也。
至於隋而州郡僚属皆命於铨曹,绅发轫悉由於科目。
自以铨曹署官,而所按者资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权;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试者词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阶荣进之路。
夫其始进也,试之以操觚末技,而专主於词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专校其资格,於是选贤与能之意,无复存者矣。
然此二法者,历数百年而不可以复更,一或更之则荡无法度,而侥滥者愈不可澄汰,亦独何哉?
又古人之取士,盖将以官之。
三代之时,法制虽简,而考核本明,毁誉既公,而贤愚自判。
往往当时士之被举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
降及後世,巧伪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为取士之途,铨选为举官之途,二者各自为防闲检尼之法。
至唐则以试士属之礼部,试吏属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铨选之法,日新月异,不相为谋。
盖有举於礼部而不得官者,不举於礼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进身之涂辙亦复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举士、举官两门以该之。
作《选举考》第九。
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所谓学校,至不一也。
然惟国学有司乐、司成,专主教事,而州、闾、乡、党之学,则未闻有司职教之任者。
及考《周礼。
地官》:
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孟月属民而读法,祭祀则以礼属民;州长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艺,纠其过恶而劝戒之。
然後知党正即一党之师也,州长即一州之师也,以至下之为比长、闾胥,上之为乡、遂大夫,莫不皆然。
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故发政施令,无非教也。
以至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
盖役之则为民,教之则为士,官之则为吏,钧是人也。
秦汉以来,儒与吏始异趋,政与教始殊途。
於是曰郡守,曰县令,则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学掾,则师所以教其弟子。
二者漠然不相为谋,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
士方其从学也,曰习读;及进而登仕版,则弃其诗书礼乐之旧习,而从事乎簿书期会之新规。
古人有言曰:
“吾闻学而後入政,未闻以政学者。
”後之为吏者,皆以政学者也。
自其以政学,则儒者之学术皆筌蹄也,国家之学宫皆刍狗也,民何由而见先王之治哉?
又况荣途捷径,旁午杂出,盖未尝由学而升者滔滔也。
於是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於兴衰理乱之故矣。
作《学校考》第十,叙历代学校之制,及祠祭褒赠先圣先师之首末,幸学养老之仪,而郡国乡党之学附见焉。
凡七卷。
古者因事设官,量能授职,无清浊之殊,无内外之别,无文武之异,何也?
唐虞之时,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礼,羲和掌历,夔典乐,益作虞,垂共工。
盖精而论道经邦,粗而饬财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圣贤也。
後之居位临民者,则自诡以清高,而下视曲艺多能之流;其执技事上者,则自安於鄙俗,而难语以辅世长民之事。
於是审音,治历、医、祝之流,特设其官以处之,谓之杂流,摈不得与绅伍,而官之清浊始分矣。
昔在成周,设官分职,缀衣、趣马,俱俊之流,宫伯、内宰、尽兴贤之侣。
逮夫汉代,此意犹存,故以儒者为侍中,以贤士备郎署。
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国之徒,得以出入宫禁,陪侍晏私,陈谊格非,拾遗补过。
其才能卓异者,至为公卿将相,为国家任大事,霍光、张安世是也。
中汉以来,此意不存,於是,非阉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宫庭,而贤能绅,特以之备员表著。
汉有宫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党,职掌不相为谋,品流亦复殊异,而官之内外始分矣。
古者文以经邦,武以拨乱,其在大臣,则出可以将,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则簪笔可以待问,荷戈可以前驱。
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战阵,被介胄者不复识简编,於是官人者制为左右两选,而官之文武始分矣。
至於有侍中、给事中之官,而未尝司宫禁之事,是名内而实外也(唐以来以侍中为三公官,以处勋臣,又以给事中为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为之,并不预宫中之事;)有太尉、司马之官,而未尝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实文也(太尉,汉承秦以为三公,然犹掌武事也。
唐以後亦为三公。
宋时,吕夷简、王旦、韩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
大司马,周官掌兵,至汉元成以後为三公,亚於司徒,乃後来执政之任,亦非武臣也。
)太常有卿佐而未尝审音乐,将作有监贰而未尝谙营缮,不过为儒臣养望之官,是名浊而实清也。
尚书令在汉为司牍小吏,而後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穹官;校尉在汉为兵师要职,而後世则为武弁所不齿之冗秩(尚书令,汉初其秩至卑,铜章青绶,主宫禁文书而已,至唐则为三省长官。
高祖入长安时,太宗以秦王为之,後郭子仪以勋位当拜,以太宗曾为之,辞不敢受,自後至宋,无敢拜此官者。
汉入校尉领禁卫诸军,皆尊显之官,宰相之罢政者,至为城门校尉。
又司隶校尉督察三辅,弹劾公卿,其权至雄尊。
护羌校尉、护鸟桓校尉皆领重兵镇方面,乃大帅之职。
至宋时,校尉、副尉为武职初阶,不入品从,至为冗盛。
)盖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悬绝如此。
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
作《职官考》第十一,首叙官制次序、官数,内官则自公师宰相而下,外官则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禄秩、品从之详。
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
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
”荀卿子曰:
“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父子相传,以持王公。
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
”
然则义者,祭之理也;数者,祭之仪也。
古者人习於礼,故家国之祭祀,其品节仪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义则非儒宗讲师不能明也。
周衰礼废,而其仪亡矣。
秦汉以来,诸儒口耳所授、简册所载,特能言其义理而已,《戴记》是也。
《仪礼》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礼;《六典》所载,特以其有关於职掌者则言之,而国之大祀,盖未有能知其品节仪文者。
汉郑康成深於礼学,作为传注,颇能补经之所未备,然以谶纬之言而释经,以秦汉之事而拟三代,此其所以舛也。
盖古者郊与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汉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礼礼之,盖出於方士不经之说。
而郑注《礼经》二祭,曰天,曰帝,或以为灵威仰,或以为耀灵宝,袭方士纬书之荒诞,而不知其非。
夫礼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义且乖异如此,则其他节目注释虽复博赡,不知其果得《礼经》之意否乎。
王肃诸儒虽引正论以力排之,然魏晋以来祀天之礼,尝参酌王、郑二说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废也。
至於、之节,宗祧之数,《礼经》之明文无所稽据,而注家之聚讼莫折衷,其丛杂牾,与郊祀之说无以异也。
近世三山信斋杨氏得考亭、勉斋之遗文奥义,著为《祭礼》一书,词义正大,考订精核,足为千载不刊之典。
然其所述一本经文,不复以注疏之说搀补,故经之所不及者,则阔略不接续。
杜氏《通典》之书,有祭礼则参用经注之文,两存王、郑之说,虽通畅易晓,而不如杨氏之纯正。
今并录其说,次及历代祭祀礼仪本末,而唐开元、宋政和二礼书中所载诸祀仪注并详著焉。
作《郊祀考》第十二,以叙古今天神地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禅,次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农,次亲蚕、祭先蚕,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杂祠、淫祠终焉。
凡二十三卷。
作《宗庙考》第十三,以叙古今人鬼之祀,首国家宗庙,次时享,次、,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诸侯宗庙,而以大夫、士庶宗庙时享终焉。
凡十五卷。
古者经礼、礼仪,皆曰三百,盖无有能知其节目之详者矣。
然总其凡有五,曰吉、凶、军、宾、嘉;举其大有六,曰冠、昏、丧、祭、乡、相见。
此先王制礼之略也。
秦汉而後,因革不同:
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是也;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若臣庶以下冠、昏、丧、祭是也。
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之国恤耳。
今除国祀、学校、选举已有专门外,朝仪已下则总谓之“王礼”,而备著历代之事迹焉。
盖本晦庵《仪礼经传通解》,所谓王朝之礼也。
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毋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
作《王礼考》第十四。
凡二十二卷。
《记》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故审乐以知政。
”盖言乐之正哇,有关於时之理乱也。
然自三代以後,号为历年多、施泽久,而民安乐之者,汉唐与宋。
汉莫盛於文景之时,然至孝武时,河献王始献雅乐,天子下太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哀帝时始罢郑声,用雅乐,而汉之运祚且移於王莽矣。
唐莫盛於贞观、开元之时,然所用者多教坊俗乐,太常阅工人常隶习之,其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然则其所谓乐者可知矣。
宋莫盛於天圣、景之时,然当时胡瑗、李照、阮逸、范镇之徒,拳拳以律吕未谐,声音未正为忧,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时始制《大晟乐》,自谓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
盖古者因乐以观政,而後世则方其发政施仁之时,未暇制乐,及其承平之後,纲纪法度皆已具举,敌国外患皆已销亡,君相他无所施为,学士大夫他无所论说,然後始及制乐,乐既成而政已秕,国已衰矣。
昔隋开皇中制乐,用何妥之说,而摈万宝常之议。
及乐成,宝常听之,泫然曰:
“乐声淫厉而哀,不久天下将尽。
”噫!
使当时一用宝常之议,能救隋之亡乎?
然宝常虽不能制乐以保隋之长存,而犹能听乐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过人者。
窃尝以为世之兴衰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
其自得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
而後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於黍之纵横,求正哇於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刻舟、覆蕉、叩、扪烛之为?
愚固不知其说也。
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
凡十五卷。
按《周官。
小司徒》:
“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
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此教练之数也。
《司马法》:
“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
”此调发之数也。
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
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其出一人也。
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也。
教练必多,则人皆习於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於征战。
此古者用兵制胜之道也。
後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
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是弃民也。
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於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於平时而驱用於一旦。
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
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
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
“为人议法,当依於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
”盖汉承秦法。
过於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淫刑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