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黄时雨》程青.docx
《《梅子黄时雨》程青.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梅子黄时雨》程青.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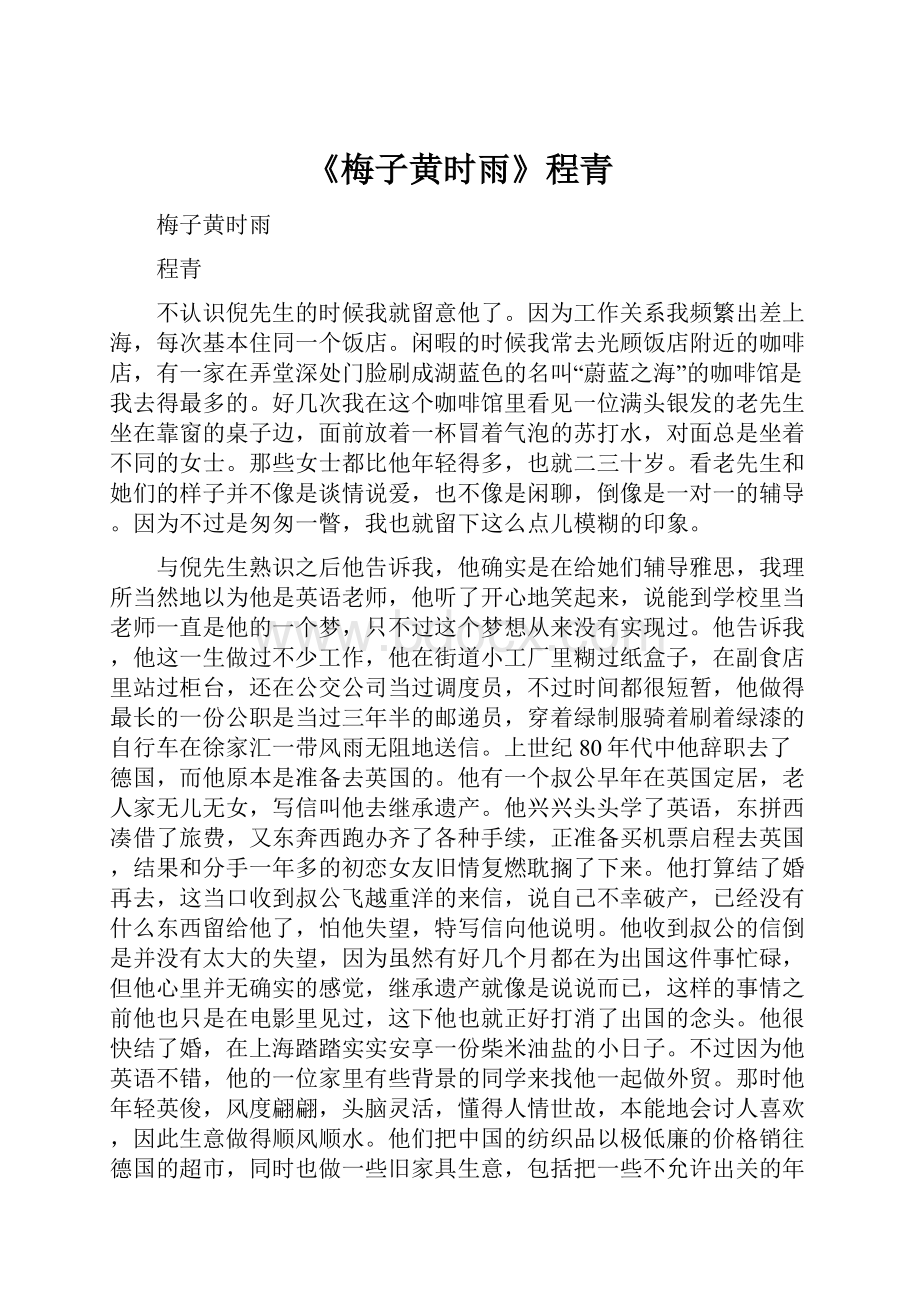
《梅子黄时雨》程青
梅子黄时雨
程青
不认识倪先生的时候我就留意他了。
因为工作关系我频繁出差上海,每次基本住同一个饭店。
闲暇的时候我常去光顾饭店附近的咖啡店,有一家在弄堂深处门脸刷成湖蓝色的名叫“蔚蓝之海”的咖啡馆是我去得最多的。
好几次我在这个咖啡馆里看见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坐在靠窗的桌子边,面前放着一杯冒着气泡的苏打水,对面总是坐着不同的女士。
那些女士都比他年轻得多,也就二三十岁。
看老先生和她们的样子并不像是谈情说爱,也不像是闲聊,倒像是一对一的辅导。
因为不过是匆匆一瞥,我也就留下这么点儿模糊的印象。
与倪先生熟识之后他告诉我,他确实是在给她们辅导雅思,我理所当然地以为他是英语老师,他听了开心地笑起来,说能到学校里当老师一直是他的一个梦,只不过这个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
他告诉我,他这一生做过不少工作,他在街道小工厂里糊过纸盒子,在副食店里站过柜台,还在公交公司当过调度员,不过时间都很短暂,他做得最长的一份公职是当过三年半的邮递员,穿着绿制服骑着刷着绿漆的自行车在徐家汇一带风雨无阻地送信。
上世纪80年代中他辞职去了德国,而他原本是准备去英国的。
他有一个叔公早年在英国定居,老人家无儿无女,写信叫他去继承遗产。
他兴兴头头学了英语,东拼西凑借了旅费,又东奔西跑办齐了各种手续,正准备买机票启程去英国,结果和分手一年多的初恋女友旧情复燃耽搁了下来。
他打算结了婚再去,这当口收到叔公飞越重洋的来信,说自己不幸破产,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他了,怕他失望,特写信向他说明。
他收到叔公的信倒是并没有太大的失望,因为虽然有好几个月都在为出国这件事忙碌,但他心里并无确实的感觉,继承遗产就像是说说而已,这样的事情之前他也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这下他也就正好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他很快结了婚,在上海踏踏实实安享一份柴米油盐的小日子。
不过因为他英语不错,他的一位家里有些背景的同学来找他一起做外贸。
那时他年轻英俊,风度翩翩,头脑灵活,懂得人情世故,本能地会讨人喜欢,因此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他们把中国的纺织品以极低廉的价格销往德国的超市,同时也做一些旧家具生意,包括把一些不允许出关的年头久远的旧屏风和旧家具拆开来夹在三夹板里运出去,几年下来就发了大财。
倪先生说起这一段是欣悦和欢快的,他脸上泛起红光,整个人就像一只亮堂堂的灯盏。
也许是因为曾经有不少时间生活在欧洲,他举止文雅,气度雍容,绅士派头十足。
虽说上了年纪,但依然是很有魅力。
尤其是他笑容里的那份真挚和友善,让他看上去略显矜持和清冷的外表变得十分生动和亲切。
有几次他的学生因故迟到,我看见他一次次走到咖啡馆外面迎候,就像在车站等待晚点的亲人。
而当她们来到,他又若无其事,谈笑风生,没有一丝一毫责怪的神色。
和他闲聊我也觉得相当有意思,他坦率诚恳,言谈之中渗透着一种自我调侃和苦中作乐的幽默感,这与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尽相同。
五六月间我又去上海出差,在江南梅雨季节闷热潮湿的下午和冗长无聊的晚上,我习惯性地去冷气开得很足的“蔚蓝之海”闲坐消磨时光。
倪先生上完课之后总会笑眯眯地走过来和我闲聊会儿。
有天,他说他在网上XX到我是一个作家,他笑得就像孩子似的对我说:
“那我就可以毫无障碍地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啦。
”
不出所料,他给我讲了他的感情故事,或许可以这么说,他对我讲了很多他的隐私。
倪先生的妻子就是他那位旧情复燃的初恋女友,名叫苏瑞雪,她有先天性心脏病,因此他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他本人也不是没有犹豫,但两个人还是结了婚。
他们从中学时代就开始谈恋爱,从拉拉小手算起前后处了有十五年。
倪先生说,那会儿的爱情非常单纯也非常纯洁,两个人在一起说过太多海誓山盟的话,不结婚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他们去白云照相馆拍了结婚照,花了一块钱领了两本红彤彤的结婚证。
那是1980年,倪先生三十岁,妻子比他大两岁。
因为妻子有心脏病他们不能要孩子,倪先生觉得这没有什么,没有孩子至少清静。
结婚之初他很照顾苏瑞雪,家务不要她做,都是他自己动手。
后来有钱了,家里常年请保姆。
苏瑞雪因为身体不好没有下放,她顶替父亲在百货公司上班。
他下海挣了钱之后她便辞职了,就在家里织织毛线看看电视。
婚后她身体依然不好,脸色越来越苍白,瘦得就像影子一般。
他叫她出去走走,她不肯。
她不爱动,见人也怕。
他一有空就陪她出去,还带她去邻居家里串门。
后来她总算跟街坊四邻走得熟了,再后来她每天睡过午觉起来出去跟他们打八圈麻将。
结婚三年多,倪先生和金小娥好上了。
金小娥是和他一起做生意的同学小霍的小姨娘,他第一次见到她还跟着小霍一起叫她“小阿姨”呢。
金小娥比他小五岁,刚刚离婚不久,搬到她大姐家来住。
金小娥长得胖乎乎的,一笑嘴角边两个小酒窝,既娇憨又明媚。
他第一次见到她就非常喜欢她,得知她离婚了,他一边为她叹息,一边又暗自高兴。
在她身上他看不出一点离过婚的痕迹,尤其是听她发出脆爽的银铃般的笑声,他感觉她就是一朵硕大的在阳光下随心所欲盛开的花朵。
他原本不喜欢胖人,但唯独金小娥例外,他觉得她胖得好看,胖得有风韵,胖得令他心软。
他觉得她性感十足,而且因为是离婚独居,这份性感越发撩人。
金小娥没有工作,她下过放,后来回城了,考了两次大学都没有考上,也就不考了。
平常她上午在家帮大姐家做做饭,下午没事去隔着两条街的内衣店里找小姐妹聊聊天,顺便帮着看看店。
倪先生常常在晌午时分过来看她,他从来不空着手来,有时带点应季水果,有时带几块奶油蛋糕,有时带一包专门去南京路买的卤菜,足够中饭时一家人吃的。
他来了就是坐在客厅里看《解放日报》,或者倚在厨房门边看金小娥切菜烧饭,偶尔也帮她剥剥毛豆,择择韭菜。
到饭快好他就走了,从不留下来吃饭。
下午等家里人上班走了他会再来,他们关上门,家里是安安静静的两人世界。
他们吃茶谈笑,自然少不了拉上窗帘做点恩爱缠绵的事情。
天长日久,难免要被撞到。
有两次大姐回家早,还有一次小霍回家拿东西,他们正在床上翻滚,听见敲门声只好穿衣起来,大家也就是笑一笑。
他们的关系在这个家里似乎被默认了,不过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说破。
可是他和金小娥的事情在他自己家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两个女人都想讨好,对苏瑞雪,对金小娥,他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
比如他给苏瑞雪买新衣服,也给金小娥买新衣服,反过来也是一样,给金小娥买金首饰,也给苏瑞雪买金首饰,甚至给她们买的衣服首饰款式和价钱都是差不多的。
然而实际上这碗水是难以端平的,他自己心里是一清二楚。
比如在金小娥这里尽了兴,回到家里他只想倒头便睡,和苏瑞雪连话都懒得多说。
有时候他在家里被苏瑞雪哕哕唆唆烦得坏了情绪,到了金小娥这里也要好半天才缓得过神来。
不过在苏瑞雪不知道有金小娥存在的时候还是好办的,不管是好情绪还是坏情绪他自己消化就是了,而当苏瑞雪知道了有金小娥这么个人存在,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具体苏瑞雪怎么知道金小娥的他不得而知。
有一天他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苏瑞雪黑着脸坐在饭桌边,脸上挂着泪痕,水门汀地板上是一片摔得粉碎的玻璃片,他一眼就看出是玻璃杯的残骸,而且显然不止一两只。
他一惊非同小可,因为苏瑞雪从来没跟他发过脾气,而且她特别痛惜东西,最关键的是她发这么大火很容易直接送命,这是医生一再警告过的。
他不敢跟她发急,赶紧好言安慰,但苏瑞雪根本无动于衷。
有三天时间她倒在床上闷睡,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只有上厕所才起来一下。
他吓坏了,强行把她送到医院里去打点滴。
很快苏瑞雪娘家也知道了这件事。
她的父母并没有就这事说什么,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平常话就不多,遇到事情也没什么主张,他们见了他没说一句埋怨的话,只是跟他更加无话可说了,不过对他的态度倒似乎比从前更好。
他们面带讪讪的笑容,小心翼翼地听他说话,似乎生怕做错什么。
只要他上门,他们会准备比以前更加丰盛的饭菜招待他。
这让他心里更加过意不去,因此也更加难得上门。
苏瑞雪的大哥作为娘家代表专门来找他谈过。
但他们见了面只是闷头吸烟,涉及实质性问题的话很少。
苏瑞雪大哥的意思是怕他要离婚,他说妹妹这个身体,辞了职也没有公费医疗,再找人结婚也会被人家挑剔,要是离了婚是不大好办的。
他赶紧表态说自己没有这个意思——他确实是没想过要跟老婆离婚,从结婚那天起他就没想要离婚。
苏瑞雪出院之后回娘家住了几天,他觉得这样过渡一下也好,正好她妈妈可以给她做些她爱吃的东西调养一下身体,她家里人或许还可以开导开导她。
一礼拜之后她回来了,气色略微好了一点,人看上去很平静,只是好像太平静了,有点心如止水的意味。
他很满意,心里感激她娘家的工作做得到位,至少是没有挑拨和挑唆什么。
他主动去给丈人家换了冰箱、彩电和洗衣机,又给他们装了空调,还给了一笔钱让他们装修房子。
他给大舅哥同样送了一套崭新的电器。
那时他很有钱,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他是个成功人士。
这件事能摆得如此四平八稳,他心里明白,苏瑞雪家那边其实也是看在他混得比绝大部分人都要好的份上。
再之后他的母亲也知道了这件事。
他问妈妈是怎么晓得的,妈妈说是去菜市场买菜听从前的一个老邻居说的。
那个时候通讯还不太发达,装个固定电话需要好几千块钱的初装费,手机叫大哥大,个头像板砖那么大,又贵又不好买,打电话接电话都要钱,用得起的都是很有钱的人。
普通人传播资讯的方式除了写信、拍电报、打公用电话之外基本就是口耳相传。
他不知道有关他的消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的,但他母亲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对苏瑞雪娘家的反应都了如指掌。
倪先生的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前头四个都是女儿,他是唯一的儿子。
在那个物质匮乏、重男轻女的时代,他在家里享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优厚待遇。
母亲对他一向宠溺,不过他心里还是十分惧怕她,从来不敢对她稍有违拗,因此一直有孝子的好名声。
母亲和他说起这件事,他心中忐忑,不过母亲倒没说他什么,只是说:
“一个不够烦,还弄两个?
”他听了羞惭地笑,不说什么。
母亲便像是自言自语一般说:
“有什么用呢?
”这句话倒是刺痛了他的心,他认为母亲话里的意思是说,他弄了两个女人却没有一个能给他生孩子的。
母亲不到四十岁就守寡,无论是按照风俗还是按照心愿,她都是要跟小儿子相依为命的,因为儿媳不中意,她打消了这个念头,自己一直单独住着。
原先礼拜天他会和苏瑞雪一道来看望母亲,陪母亲吃顿中午饭,自从有了这件事之后苏瑞雪就再没有上过母亲的家。
他知道她是怨他母亲不出来为她伸张正义,他也知道母亲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她是个非常传统的女人,识字不多,从骨子里认同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她是绝不会为任何人得罪自己儿子的,哪怕是儿媳也不例外。
苏瑞雪不和他母亲走动,对他母亲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损失,充其量就是少听她软绵绵嗲兮兮地叫几声妈,也算是眼不见心不烦。
然而苏瑞雪不来,金小娥便来了。
金小娥怀着要取代苏瑞雪登堂入室的强烈意愿,对他母亲十分恭敬和讨好。
她像一只邀宠的猫一样围着他母亲妈长妈短,进门就帮他母亲做事,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子样样都做。
母亲对她客客气气,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偏向。
时间一长,金小娥来还是来,做事也还是做事,但巴结的态度明显淡了。
倪先生和苏瑞雪的婚姻经受住了冲击并没有破裂,金小娥无法再往前一步,只得还处在那个不尴不尬的地位。
倪先生仍然对两个女人都好,因为他觉得两头亏欠,因此两头都尽力补偿。
他虽然生意很忙,但总是尽量抽出时间陪她们。
为了补偿金小娥,他把她常去串门的那个内衣店盘下来送给了她。
金小娥有了自己的店,专心地打理起来,对他也不像之前那样缠得紧了。
他就在这个时候迷上了跑步,每天一大清早马路上还没有人就出去跑,跑得大汗淋漓回家。
跑步让他精力充沛,心情舒畅。
他身体健壮,在两个女人之间穿梭,合理地分配时间和精力,他自认为足以让她们满意。
两个女人相安无事,他的生活达到了新的平衡与和谐。
这样过了两年多,金小娥意外怀孕了,在要不要生下孩子的事情上他们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抉择。
如果要生,他们就必须结婚,如此,倪先生和苏瑞雪就得离婚——这是违背他初衷的,而且他清楚,这样一来家里不可避免会引发强烈地震,他没有勇气迎刃而上,也害怕自己承担不起后果。
他觉得这个意外等于是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金小娥在刚得知自己怀孕时还十分高兴,她惊喜地看到怀孕等于把一次翻盘的机会摆在了她的眼前。
可是她看他却远不像她这样高兴,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
再后来她看他迟迟不表态,也沉不住气了,变得焦躁不安。
她不敢直接问他,怕他把决定说出来不好转弯。
她去他母亲那里探口风,当然也是希望他母亲能帮她说话。
她还是老策略,去他母亲家里做事,买菜烧饭洗衣服扫地样样都做,而且做得尽心尽意。
他母亲自然是明白她的意思的,但并不开口替她说话。
金小娥也清楚她知道自己的心思,看她到了这个地步都不肯替自己说句话,心中只是气苦。
有两次她把话头引过去,他母亲也不接话。
转眼她怀孕满三个月了,倪先生去了德国,走前也没有明确的交代,而且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无奈之下她只得把话挑明了问他母亲怎么办。
他母亲叹了两口气,说了一句话:
“阿姐,我哪能好讲啥?
”
金小娥无可奈何,流着眼泪去医院把孩子做了。
四个月之后倪先生从德国回来,家里又是风平浪静。
他仍然享受着拥有两个女人的生活,家里人习以为常,连亲戚朋友也都习以为常,没有人说他什么,顶多是有人会拿他开几句玩笑。
苏瑞雪自从知道他出轨之后对他冷淡了不少,不过这个冷淡是相对于之前的浓情蜜意而言的,再说她还要靠他,她晓得利害,所以也就是少了亲密而已,并没有到日子过不下去的地步。
有时候她也要吃醋,她会无缘无故拉长了脸,好几天不跟他说话;或者是无名火起,冲他大发脾气。
不过他哄哄她就好了,他知道她就是跟他瞎胡闹呢,孙猴子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因此心里是笃笃定定的。
金小娥自从打掉了孩子,对他也冷了不少,她的冷倒不是做在脸上,而是表现在床上。
以前她上了床热情似火,而且很有服务精神,叫她做啥就做啥,听话得很,这是苏瑞雪远远不及的,也是让他最称心快意的。
他跟金小娥开玩笑说,她是把床上的生活当作事业的。
现在她不那样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热情,却多少有点半推半就,而她的半推半就也不是装出来的,真的就是打不起精神。
有时候做得时间久点,她会中途熄火,本来是小溪潺潺,两岸青葱,忽然干得就像一根木桩,让他颇为扫兴。
从前连续作战所向披靡的干劲已经再难见到。
他忽然觉得就像季节更迭,他跟金小娥显然已经走过了春天,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总是在春天里徜徉,现在大约是秋天了,他不敢去想是不是很快就会走进严寒的冬天。
他依然生意做得很好,钱赚得很多,但他内心里觉得命运之神并不总对他露出微笑了。
他年幼的时候深得母亲和四个姐姐的宠爱,从小习惯了女性的柔情,而现在无论是苏瑞雪还是金小娥,对他都不再是百分之百爱慕和依恋,这让他心里很落寞。
他本来贪恋苏瑞雪的情和金小娥的色,现在这两样都大大地打了折扣。
他心里也有懊悔和忧伤,却说不出来,而且也无处可说。
他慢慢对她们心劲也松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两个都挂在心上。
他花更多的时间忙自己的事,外出也更加频繁,在欧洲一住就是好长时间。
这个阶段他开始有了外遇——他心里从来没有把金小娥当外遇,他当她是自己的女人,另一个老婆。
他的那些外遇用他的话说不过是“露水夫妻”,多数连露水夫妻都称不上,就是露水关系。
长的也有相交两三年的,短的就是见个两三次,甚至也有一夜情的。
他已经过了四十岁,因为常年坚持跑步,依然肌肉结实,容光焕发。
他毫不费力就能交往到新的女人,那些女人还真不是因为钱跟他搞到一起的,当然他跟她们一起时也是很舍得为她们花钱的。
这一点上他认为自己和长辈很不一样,他不再以节俭为美德,懂得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出去,原本他就生性大方,这下更加是花钱如流水。
而且他认为钱花到女人身上是值得的,因为这世界上男女之间最好的润滑剂就是金钱,当然若是再能把钱花得贴心贴意,效果自然更佳。
他跟那些外遇也是有过不少美好和美妙的时光的,然而更多的却是空虚感。
他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别人是否跟他一样,但空虚就是空虚,他骗不了自己。
如此一混就混到了五十岁。
五十岁对他来说就像一下子进入了多事之秋。
他的一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和他闹翻,那人卷了他很大一笔钱跑到澳大利亚去了。
时隔不久,苏瑞雪查出患了癌症,他带她四处寻医问药,找最好的医生替她治疗。
那一段他不再在外面寻花问柳,连金小娥那里都去得极少,他就像一个好丈夫一样对老婆尽心尽责。
苏瑞雪的手术很成功,术后恢复得很好,暂时没有生命之虞。
为了给苏瑞雪看病,他拿出了本来答应给金小娥买房子的钱。
金小娥当时没有意见,她明白救命比买房重要——这么多年一块儿过下来,她知道他们三个其实是一家人,真的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可是,苏瑞雪病情稳定后,金小娥也就理所当然地跟他重提买房子的事。
他没有给她买房子,而是把手上的余钱投进了股市。
2000年那会儿股市正走牛,他每天听到的都是周围的朋友买股票挣了大把的钞票,实在心痒难忍,决定一试身手。
他打的如意算盘是从股市里把金小娥要的房子给她挣出来。
他以前也买过股票,知道股市里挣钱是很快的。
可是他忘了股市涨起来快,跌下来比涨起来更快.尽管还没到熊市,他刚刚建仓便满仓被套,亏损很大。
那时他没有止损和止盈的概念,听信了别人说的价值投资,以为拿得时间越长越好。
的确有人因为持股时间长而发了大财,比如巴菲特老先生,而到他这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前半辈子挣来的钱除了花出去的,竞有一大半亏在了股市里。
他原本是想给金小娥从股市里捞套房子出来的,没想到进了这口热气腾腾的大锅一滚资金严重缩水。
这时候他如果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不在乎亏损,有多少拿出多少还是足够买两三套房子的,只是他实在舍不得割肉。
他看着每天上上下下的指数和红红绿绿的盘面,离他解套获利总是差着一大截距离。
他心灰意冷,任由那一大把深套的股票在股市里涨涨跌跌。
偶尔打开账户看一眼,还是绿肥红瘦,而房价却蹿了起来,而且就像吃了春药一样金枪不倒。
他答应给金小娥买房子的诺言也就一直没有兑现。
为了补偿金小娥,他拿出自己以前买的一套房子给她住,金小娥自己的房子出租,每月能收两千多块钱的房租。
他让给金小娥住的这套房子的房本上也写着苏瑞雪的名字,因此他和她说了一声。
苏瑞雪对这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时没说话。
隔了些日子借题发作,拉着脸说了几句气话,不过并没有跟他吵架。
她精神不好,有点自顾不暇。
为了调养身体,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娘家。
苏瑞雪不在家住的时候他就和金小娥住到一起,渐渐地金小娥这边似乎成了他主要的家——一方面是为了相互有个照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省钱。
从做生意挣到第一桶金开始,他从来没有想过要省钱,现在他已经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他母亲连续两次大腿骨折,让他意识到她真是老了,他得负起为她养老的责任。
他母亲骨折之前身体一向不错,她帮别人看小孩,中午在家里摆一张小饭桌,照应几个父母没空做饭的小学生吃中饭,挣来的钱足够她自己花销。
现在她卧床不起,自己的生活都需要雇人照顾。
一里一外,钱上就紧张了。
照理母亲的养老应该由五个子女分担,但是她对四个女儿向来很无所谓,她们小的时候她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很少给她们好脸色看。
她眼里只有儿子,她也只对儿子言听计从。
四个女儿早已经伤透了心,除了逢年过节礼节性的拜访,平日很少上她老人家的门。
她们都是工薪阶层,挣得不多,混得远不如弟弟好,平常都是精打细算过日子,对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贴补母亲都很畏难。
他同情姐姐们,也替母亲难过。
他决定独自承担起这个责任,并且认为自己责无旁贷。
他征求了母亲的意见,把她送进了养老院。
他给母亲选的养老院在青浦,刚开始每个星期天他都去看她,后来改成两个星期去一次,再后来是一个月去一次。
苏瑞雪身体不好,正好有理由不去看他母亲。
金小娥也不去看他母亲,主要是因为她跟他母亲感情疏淡。
至今她还对自己怀孕时她不肯站出来替她说话耿耿于怀。
她说起他母亲老是挖苦说“当初你妈骑在墙上……”他对她把“骑墙”说成“骑在墙上”十分恼火,却不好跟她发作,因为这里面是埋着雷的——他没娶她,没让她生下孩子,也没给她买房子,跟她不明不白过了半辈子也没个交代,细究起来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他只好忍气吞声,随她去说。
他自以为有两个老婆,但这两个老婆没一个跟他去看他母亲,每次他都是独自一个人去,好在母亲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问。
每次他去看母亲都给她带一些吃的:
水果、点心还有卤菜,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人人爱吃的,母亲自然也爱吃。
他从来没有问过母亲想吃什么,母亲也从来没有跟他提过任何要求。
在他面前,母亲永远是一副非常知足的样子。
后来想想,他似乎被她满足的样子给迷惑了。
有一天母亲对他说,做梦梦见吃烧鸡。
自此以后他每次去看望她都会给她带一只烧鸡。
他仍然坚持跑步,但他发现好像连跑步都变了味儿了。
以前他跑步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风华正茂,步履轻捷,有一种血气方刚犹如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感觉。
现在他跑步脚后跟会不自觉地拖在地上,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点苟延残喘。
他已经感觉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明显在走下坡路。
他已经不在外面猎艳了,一是闲钱不多,二是没有这个兴头。
过完五十五岁生日,他处理了外面的生意,除了留下一点银行股的底仓,清掉了别的股票,他甚至要回了从前不好意思张口要的别人的欠款,他算了算,这点钱并不够用到老。
从三十来岁手头阔绰了开始,他一向是挥霍成性的,后来收敛了不少,尤其是近几年已经是十分节约,再缩减开支,就要到节衣缩食的程度了。
他想想害怕,决定节流之外还要开源。
到了这个年纪他已经没法出去找工作了。
但凡能看见的招聘广告写的都是需要年轻人,尺度最宽的也是要四十五岁以下的人,他已经被彻底排除在招聘的人选之外了。
再说他自己心里也过不去这个坎,他曾经是有钱人,自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精英,如今他没有办法豁出脸去求职,即便是朋友的公司,他也放不下架子,再说越是朋友他越是张不开口。
到了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一无所能。
他没有学历,没有专业技术职称,也没有职务,甚至没有能够开列出来证明自己能力的唬人的工作经历。
他有的只是搭同学便车的投机经验和顺风顺水挣些容易钱的经历,再就是一些历年积累下来的知道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能碰的教训。
他没有办法凭自己这个年龄经历过的挫折和失败去找工作,更不可能找到一份能达到内心要求的工作。
他忽然对自己很灰心,觉得此生完了,已经被这个时代和社会抛弃了。
他再出去跑步,脚后跟更加拖在地上,嚓嚓嚓的,就像一只垂死的刺猬。
不过他没有因此消沉,他毕竟是有年纪有阅历的人,也是风风雨雨过来的,知道凡事要靠自己想办法,也知道办法总比困难多。
有一天他在跑步的时候,看到一张被雨淋湿已经脱落了一半的街头小广告,心里立马有了主意。
他记下了广告上的电话,去报了一个雅思班,学完之后同样贴出小广告,开始招收学生教授英语。
他不开班,只是一对一辅导学生。
刚开始他心里是有点忐忑的,生怕自己水平不够。
他确实水平不高,不过就是依葫芦画瓢,怎么贩来的怎么卖出去。
他的优势是时间灵活,全由对方说了算,价钱也公道,比报班上雅思的学费要便宜三分之一,而且态度好,永远是笑呵呵的。
他一边教英语一边讲笑话,或者反过来说,一边讲笑话一边教英语,所以他开张不久来的学生就相当多。
他清楚像他这样靠教雅思是发不了财的,不过就是挣点茶饭钱而已。
而放在从前,这样的小钱他是不屑去挣的。
他渐渐在教雅思中找到了乐趣,不是钱上的乐趣,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另一番乐趣。
除了一开始,他没再打过广告,他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偶尔也有个把男生来找他,通常在听完他的免费试听课之后就再不露脸了。
他觉得也算是两相便宜。
他自嘲是一个“专教女生的雅思老师”,不过他很满意自己的这个状态。
杨莲是他学生中的一个,刚开始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的印象,在他眼里她除了容貌不错,其他都很普通。
她的英语水平在他的学生当中属于基础差的,所以他还同时给她补习语法。
一开始杨莲每星期来他这里上两次课,一次课时一小时。
每次她都来去匆匆,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本来就只有一个小时,纠正完预留的作业,也讲不了太多新内容。
出于好心,他建议她把课时延长一小时,这样也不枉赶路辛苦。
她似乎有些为难,他怕她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实际上他收的学费已经是很低了,他半开玩笑说增加的这个小时算是买一送一,不额外收费。
她听了露出笑意,但却口气坚决地说:
“谢谢,不用。
”
杨莲的断然拒绝让他有些莫名的震动,可以说是从那一刻起他对这个外柔内刚的姑娘有了特别的关注。
他不知道人跟人是如何产生微妙的联系的,对他来说这是生活中的一个秘密。
他觉得自己和杨莲之间就是从她的断然拒绝开启了某种微妙的关系,至少在他是这样体会的。
自从他意识到自己方方面面在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