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之水.docx
《循环之水.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循环之水.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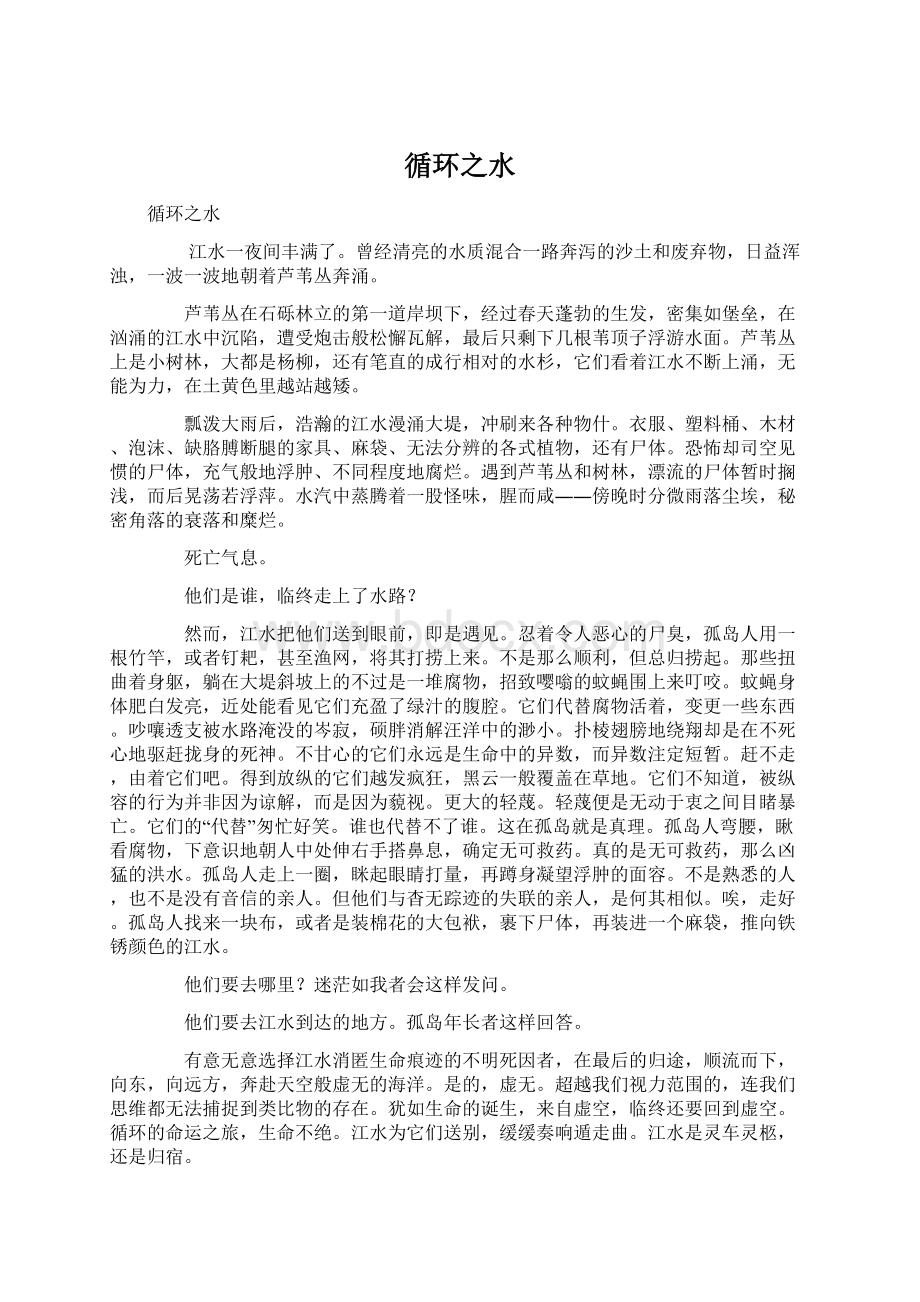
循环之水
循环之水
江水一夜间丰满了。
曾经清亮的水质混合一路奔泻的沙土和废弃物,日益浑浊,一波一波地朝着芦苇丛奔涌。
芦苇丛在石砾林立的第一道岸坝下,经过春天蓬勃的生发,密集如堡垒,在汹涌的江水中沉陷,遭受炮击般松懈瓦解,最后只剩下几根苇顶子浮游水面。
芦苇丛上是小树林,大都是杨柳,还有笔直的成行相对的水杉,它们看着江水不断上涌,无能为力,在土黄色里越站越矮。
瓢泼大雨后,浩瀚的江水漫涌大堤,冲刷来各种物什。
衣服、塑料桶、木材、泡沫、缺胳膊断腿的家具、麻袋、无法分辨的各式植物,还有尸体。
恐怖却司空见惯的尸体,充气般地浮肿、不同程度地腐烂。
遇到芦苇丛和树林,漂流的尸体暂时搁浅,而后晃荡若浮萍。
水汽中蒸腾着一股怪味,腥而咸――傍晚时分微雨落尘埃,秘密角落的衰落和糜烂。
死亡气息。
他们是谁,临终走上了水路?
然而,江水把他们送到眼前,即是遇见。
忍着令人恶心的尸臭,孤岛人用一根竹竿,或者钉耙,甚至渔网,将其打捞上来。
不是那么顺利,但总归捞起。
那些扭曲着身躯,躺在大堤斜坡上的不过是一堆腐物,招致嘤嗡的蚊蝇围上来叮咬。
蚊蝇身体肥白发亮,近处能看见它们充盈了绿汁的腹腔。
它们代替腐物活着,变更一些东西。
吵嚷透支被水路淹没的岑寂,硕胖消解汪洋中的渺小。
扑棱翅膀地绕翔却是在不死心地驱赶拢身的死神。
不甘心的它们永远是生命中的异数,而异数注定短暂。
赶不走,由着它们吧。
得到放纵的它们越发疯狂,黑云一般覆盖在草地。
它们不知道,被纵容的行为并非因为谅解,而是因为藐视。
更大的轻蔑。
轻蔑便是无动于衷之间目睹暴亡。
它们的“代替”匆忙好笑。
谁也代替不了谁。
这在孤岛就是真理。
孤岛人弯腰,瞅看腐物,下意识地朝人中处伸右手搭鼻息,确定无可救药。
真的是无可救药,那么凶猛的洪水。
孤岛人走上一圈,眯起眼睛打量,再蹲身凝望浮肿的面容。
不是熟悉的人,也不是没有音信的亲人。
但他们与杳无踪迹的失联的亲人,是何其相似。
唉,走好。
孤岛人找来一块布,或者是装棉花的大包袱,裹下尸体,再装进一个麻袋,推向铁锈颜色的江水。
他们要去哪里?
迷茫如我者会这样发问。
他们要去江水到达的地方。
孤岛年长者这样回答。
有意无意选择江水消匿生命痕迹的不明死因者,在最后的归途,顺流而下,向东,向远方,奔赴天空般虚无的海洋。
是的,虚无。
超越我们视力范围的,连我们思维都无法捕捉到类比物的存在。
犹如生命的诞生,来自虚空,临终还要回到虚空。
循环的命运之旅,生命不绝。
江水为它们送别,缓缓奏响遁走曲。
江水是灵车灵柩,还是归宿。
我童年时,堤岸不过是垒起的高高土坡。
土坡上长满棒头草。
这些草不仅根系相连,连叶片也紧贴泥土,犹如焊在泥土中。
可想而知,棒头草护堤防洪,并不比水泥逊色。
长满棒头草的堤岸沿着江水画了个圆圈,把孤岛圈在其中。
在水中央的孤岛,被水孤绝,却又与水流相依。
生与死,存在与消亡,逼仄与深豁,拘囿与飞翔。
这种悖论的生存矛盾下的火花与流水,恰如真理的产生,其间的过程,伸展着叙述与传奇的枝叶,深扎着隐喻寓言的根茎。
堤岸是堡垒,却并非唯一的屏障。
堤岸下江水以上的芦苇、树林和牢固扎根泥土的花草、灌木,沿着一长溜的堤坡铺陈,葳蕤、蓬勃,简直到了气焰嚣张的地步。
我儿时的记忆中,它们犹如秘密花园,既充满了声色的诱惑,又无时不给入迷宫般的警示。
我心灵的第一次惊恐,是迷失在堤坡下这片繁密的植物里。
荆条花、刺花、金银花绽放得汪洋恣肆,矢车菊、婆婆纳、蒲公英星星点点铺满堤坡,蜜蜂蝴蝶蜻蜓满天飞。
埋首啃吃的牛羊偶尔抬头,嘴角还叼着青草,却忍不住哞哞咩咩地前后应和。
春汛里涨潮的不只是江水,还有植物花朵,还有混合了各式声响与颜色的气息。
它们彼此交融,在阵阵江风中发酵,醇酒一般,令人酩酊大醉。
我醉了。
跟在华表姐全胜哥他们后面,在秘密花园游荡。
漂亮的华表姐在上初中,她有清亮的歌喉,反复吟唱影片《知音》里的插曲:
山青青,水碧碧……唱到“啊”音时,她胸脯起伏,脸色涂抹胭脂似的绯红,嗓门一波三折,眼睛流转出水波。
全胜哥在对岸城市一所重点高中读书,正好放假。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白色衬衣被江风鼓胀,如同风帆。
在华表姐的吟唱声中,他踟蹰在刺花和金银花缠绞的花丛前,眼睛越过花丛,越过花丛那边的芦苇和芦苇下的长江。
对面的城市高楼矗立,隐约有白色的烟蛇般扭行。
他仿佛思索,仿佛眺望,仿佛聆听,还仿佛陶醉,也仿佛心神出窍。
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凝视着。
我姐姐刚上学,痴迷他们,亦步亦趋。
三四岁的我,更容易被穿行花丛的斑斓蝴蝶吸引,它们一次次点亮我的眼睛,牵引我的脚步。
穿过树林,绕过一方芦苇,经过一丛荆条花,刚瞄准的蝴蝶又飞到团团簇簇的黄色菊花上。
跑跑停停,再跑,蝴蝶与我展开游戏。
我气喘吁吁也无法捕捉到一只。
我满头大汗,决定放弃时,已经找不到华表姐他们。
我左右打转,朝前走,觉得不对,又退后,再右行,还是不对,再左拐。
没有他们。
我扯破喉咙呼喊,仍然无济于事。
植物丛林中分岔的小路,犹如刺猬身上的芒针,根本不是路,而是荆条花、刺花、芦苇丛、树林、牛羊,雷同场景布下的迷魂阵。
我一颗心咚咚乱跳,快要蹦出胸膛。
右手压在胸口上,却随着心跳忐忑不安地颤抖。
疲软,混沌,迷蒙。
汗水黏糊的潮湿不爽让我呼吸急促。
我感觉一阵尿意。
然而,排泄并没有缓解不适。
我提起裤子起身时,芦苇丛边闪现一具白色的骷髅,狰狞、阴森,分泌出破坏毁灭的暗示。
被剔除血肉的骨头,生命最后的凭证。
我被白色骷髅抽空了力气,跌倒在地无法站起来,只好双手撑地朝前逃行。
夕?
在地上漏下万千余晖。
向晚的江风跑出响马呼哨,繁枝茂叶鞠躬让行。
咩咩――羊叫的声音打破岑寂。
我寻着咩咩声爬,回家的欲望陡然给我勇气,我站起来,扯着喉咙哭喊“姐姐,姐姐”。
放羊人甩着细长的杨柳枝条朝我走来。
这是一个邋遢的老头。
他用细长的杨柳赶着羊,羊跑一阵停一阵。
他偶尔吆喝,回家呵。
我双腿无力,再次瘫软在地。
放羊人拉起我,惊诧不已。
你一个小孩家,走了那么远?
已经过了两个村庄。
此后三天我一直昏迷,噩梦连连。
白色的骷髅,长出蝴蝶的翅膀,在我梦里翻飞,而抖动的翅膀却扇起血液,如江水朝我劈头浇来。
我伸手捂住脑袋,却发现脚底下涌出血水,血水积蓄成溪流,慢慢淹没我的脚踝、小腿……一个头上长出角的男人,披着一身羊毛,呵呵发笑,又伸手给我,说,我带你回家。
我一次次哭泣着惊醒,冷汗不断。
祖母认为我中了邪,拿个掏了内瓤已被风干的葫芦,在月光下挑起银针,嘴巴念念有词,左右画圈,朝凸起的葫芦中心扎去,左一圈右一圈。
两天后,我奇迹般地病愈。
也说不上奇异,这归功于我祖母的巫术。
拿银针对着月光扎葫芦瓢,是在驱鬼。
祖母解释,我到江边玩,被小鬼迷了魂,小鬼总在晚上寻来,只好对着月光用针扎,扎得小鬼害怕,打了退堂鼓,我自然就好了。
她不解释我也清楚。
我祖母的能耐不是葫芦瓢,而是对着人的经脉铺蛇皮扎银针。
这有什么讲究?
说不清楚。
只有结果。
我表姐曾经半夜抽搐打摆子,在祖母的蛇皮银针下,身体康复且不再复发。
我自然也好了,但异常胆小,常常惊叫,耽于冥想。
在乡村,冥想是可耻的。
至少,我的亲人不允许我冥想,他们在言行上极力修正。
我母亲要强而自信,说话做事干脆果断。
她批评我娇弱、自己惯养自己。
什么事不好做,又发呆了,痴呆啊,就是胆小嘛……我满脸羞愧。
母亲现身说法:
怕什么怕,都是这样长大的――我在你这个年龄时,母亲早过世了,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人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甚至我比他们做得还好。
到了初中,要过江到对面的江口镇上学,每天早上坐一个渔划子去上学,晚上再坐渔划子回来,要是怕就不读书了。
你真不怕?
我满是惊讶。
母亲不回答我,继续她的回忆。
平常晴天,没多大问题,要是遇到暴雨,也真危险,渔划子左右摇晃,没个定准,我狠命抓住船舷――有一次,渔划子快要翻了,雨水和江水噼里啪啦地摔在我身上,我眼睛难得睁开,不小心掉进水里,船老板伸一根竹篙,我抱住竹篙跟着渔划子走,人倒好好地,断断续续地读完了初中。
你真的――不怕?
我再次询问,并放慢语速。
母亲终于回答了。
要说不怕也是假话,可怕不好的,我们孤岛人就是站在长江里,除了承受,怕能解决什么?
怎么承受?
很多年,我不理解母亲的话,认为她不过是讨了机遇的好。
成年后,我与母亲闲聊,讲起十岁那年夏天,与几个老表带妹妹到长江游泳。
已是三伏天了,江水暴涨,混浊臃肿,朝着堤岸翻涌。
我们站在堤下的芦苇丛边。
芦苇丛的根部已被江水淹没。
芦苇丛的下坡是石头,然后是沙滩。
我伸脚朝江水里探了探,双手不由抓住芦苇。
幸亏有芦苇。
无法落脚的水下,松懈、秘密,似乎藏着无底洞穴。
洞穴上的漫漶潮水,拍打翻卷,它雄心壮志地堆满我的眼睛。
仿佛在宣告不可知的世界有多大,它就有多大。
五岁的妹妹探脚站在江水里,一步一步地朝前移,突然被波浪掀到深水区。
妹妹慌忙伸手,却闭紧了嘴巴呜呜地呼喊求救。
几乎刹那间,波澜起伏的昏黄水面,只剩下妹妹几摞头发,左右晃荡。
我手足无措,一颗心跳到嗓门上。
妹妹不见了。
她被那个无底洞穴带走了。
我伸手乱抓。
然而,这根本无用。
刚从江水里爬回的平表哥,叫了声“我的天”,再次踏进江水,伸手去拽,果然拽住妹妹,把妹妹拉出江水。
妹妹固执地抿紧嘴唇,而眼眶全是水液,也许还有泪水。
被平表哥拽住的瞬间,妹妹嘴巴张开,鼻子喷出水线。
我再次伸手,拉住妹妹。
那一刻,我们拥抱一起,放声大哭。
平表哥警告我们,谁也不能把这事讲出去,否则死定了。
平表哥异常调皮,那个夏天偷偷到涨水的江边游泳,正是他的主意。
而那时,我们都不会游泳,陷进深水区的妹妹都看不见了,已经滑到无底洞穴边,平表哥居然伸手就把妹妹拉出江水。
果然,没有谁再提起。
但成年后的我说起时,心脏怦怦乱跳,充满了后怕。
我讲完,声喉莫名嘶哑。
母亲怔了怔,脸色发白,嘴唇抖颤,随即,脸庞又浮现一片红晕。
她吐出一口长气,右手拍打胸口道,还有这回事情啊……到底逢凶化吉了,当然,只能说这是福气,江水总是赐福于我们的。
她肯定被吓住了。
然后,又为妹妹死里逃生倍感幸运。
我明白了母亲,她以敬畏破解江水的魔力,并因此获得胆识。
这是有趣的事情,孤岛人的坟墓大都选择在堤岸下。
一条长堤把坟墓和长江隔绝开来。
坟墓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棉田,春天种植麦子、油菜,夏秋是密集如子弹的棉花。
堤岸另一边的树林里也有坟墓。
我舅爷、祖母还有祖母的族人,他们的坟墓都在江水之上的树林里。
我祖母七十岁后病入膏肓,吃不下任何东西,身体枯瘦若柴,每天靠输葡萄糖维持能量。
她没有力气下床了,背倚床架,吁吁叹息。
一向寡言的祖母,某天清晨说道,我要走路了。
看上去,她形容憔悴,眼神却有着一股淡定从容。
她望向蚊帐某个地方,从冬天望到春天,再望到夏天来临。
初夏,江水又开始涨潮,拍打堤岸。
松动的土堤有些地方开始裂缝。
一个叫作五四的地方,在一场暴雨后溃口。
洪水汩汩地穿越堤岸,淹没了农田。
五四这个地名有来历,是为了纪念1954年特大洪涝中,我们孤岛为沙市武汉分解压力挖堤泄洪的事迹。
1954年多不平常啊。
破堤后,洪水汹涌地奔泻,漫漶孤岛,农田和房屋被淹没。
牲畜疲于奔命,卷进旋涡,抽搐几下,就没了踪影,它们的存在被洪水消解。
在这点上,洪水几乎等同于烈火。
牲畜如此,人呢?
孤岛上的人被转移到对面的城镇去,直至洪水消退。
人比牲畜要幸运。
洪水过后,孤岛一片狼藉,充斥着腐烂的臭味。
苍蝇蟑螂跳蚤类的虫豸到处飞行,它们身体肥厚,全都长着贪婪的大嘴。
它是洪水的后?
z症,却比洪水更加凶恶,见谁逮谁,填充血肉,日益膨胀它们的欲望。
我父亲最小的弟弟、祖母娘家的几个兄弟和一个侄子都在那年洪涝中得病死去。
生老病死的人生终极,几乎无解,简直无可奈何。
它赋予命运的莫测况味,除了承受还能怎样?
而承受的心境总是不平常的。
淡看,澹行。
我成年后,对“承受的心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尘埃落定似的醍醐灌顶,举重若轻,一步步走向尽头,实则是“悟生”。
我祖母就是一个“悟生”的女人。
她一直很坚强。
但“走路”那年的初夏,她却孩子般软弱,长吁短叹,动不动就哭。
特别是在听说五四溃口后,她双水捶打床铺,呜咽却没有泪水。
那不能证明她不伤心,只能说她的眼泪早流干了。
祖母一天清早又一次说道,我要走路了。
我们愕然,没有作声。
她再次咕哝,我要走路了。
重复枯索无味,却增加寡言祖母的伤心。
我父亲听出她的伤心,请假一天专门伺候。
他觉得,他母亲的话不再是牢骚,而是……果真,傍晚时,祖母气若游丝,上气不接下气,她右手抖颤,在空中被父亲接住。
我祖母交代,死后把她埋葬在她娘家的冢群里。
父亲小声提醒,下面就是江水。
祖母右手摇摆,又做了个水流姿势。
父亲回头翻译祖母的手势意思。
那有什么,冲走就冲走,江水要来,堤岸能挡得住吗?
反正都给了长江,由它不好?
我们给祖母修了一个石墓,石墓里种植芦苇。
年三十晚上,我们给祖母上坟送灯时,就在枯槁的芦苇上挂起鞭炮。
啪啦啪啦的鞭炮声里,芦苇稀里哗啦地烧出熊熊大火。
浩荡的江风不仅无法对垒冲天火柱,反而推波助澜。
噼啪噼啪――比鞭炮持久的祭奠,在红色大火中绵延不绝。
父亲说,祖母一生懦弱,身体多病,每年点火,她会感到温暖的。
第二年清明时,坟墓上的芦苇密匝得如同铜墙铁壁,只不过是绿色的墙壁,隔绝出能够听见心跳的静谧。
祖父却与祖母相反,生前强悍,对死亡却异常畏惧。
他有高血压、支气管炎,常年咳嗽。
冬天时,他泡上浓酽的茶水,加进红糖,放在火炉上煨烤,屋子里弥漫着茶叶的醇香。
他喂羊养牛很在行,打纸牌更在行。
祖父还烧得一手好菜,他的拿手菜是炖肥鱼。
那年头,春天的长江里有许多肥鱼。
肥鱼无鳞,浑身都是嫩肉,没有一根刺,但滑?
,警惕性高,难得捕捉。
祖父洞悉肥鱼藏身之所。
陡峭的石壁下,石头缝里长着芦苇丛,芦苇丛蔓延到江水里,这个水域里肥鱼一定活跃。
水域下面藏匿陡峭的石头,且有较大坡度,属于深水区域.危险系数也大。
尽管肥鱼多,但捞上来的屈指可数。
祖父每周到江水捕捉一次。
他不贪心,一条足够,大部分卖掉,尾部带回家打牙祭。
他会好好炫耀他的厨技,用腊肉熬出的肥鱼汤,鲜美无比。
无疑,他是一个享受在上的男人。
但他却血性,正是血性,才使他选择四围环水的孤岛生活。
我祖母生育十三个儿女,大都天折,存活下来三个。
父亲上面有一个小哥,感染了肺炎,没有钱医治,祖父找当地一家富裕的地主借钱,遭到奚落,便愤而出手,打残了地主,祖母劝祖父逃跑。
祖父带我伯伯去医院治病,私下却安排祖母带着两个儿女(我小姑还没有出生)离开荆州,从松滋那边过长江,迁居到孤岛。
就在医院里,祖父遭到仇家的报复。
一生不求人的他,跪下来求他们姑且放他几天,儿子命在旦夕,等儿子过了难关再清算。
仇家恶毒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儿子怎么在你手中死去。
贫寒成为所有病痛的不治之症,我伯伯死在他父亲眼皮底下,仇家在一旁冷笑。
祖父在揪心的疼痛和耻辱中,失魂落魄地寻到孤岛,找到祖母他们。
一家人开始异乡人的讨生。
我父亲、两个姑姑能够活下来,正是依靠长江,当然,也离不开祖父捕鱼的能耐。
祖父却对死亡充满了恐惧。
他因何恐惧,我无从探询,也不曾探询。
生命的极限,是每个人的心病。
祖父自然不例外。
从六十岁开始,祖父迷恋上花牌,不分日夜地玩花牌。
也许,相对于病痛或者灾难,娱乐至死更符合恐惧死亡的生命。
祖父死在玩牌上。
孤岛流行一种纸牌,即花牌,无论多么贫寒,人人都玩得一手好纸牌,这是习俗。
农闲时,家家在门前摆上牌桌,三四人围成一桌摸牌。
1983年深冬的一个晚上,据说一夜没有火气的祖父在天亮时摸了一个大和,三个花精都统上了顶,摸最后一张,祖父和牌了,一下反败为胜,得意忘形,下了牌桌回家,刚走到家门前的榆树下,就歪倒在地。
母亲早上起来开门,看见祖父靠着榆树睡着了。
雪花把他的头发眉毛和衣服全都裹上白色。
母亲惊叫一声,祖母颠着小脚跑出来,伸手摸祖父鼻子,说,睡去了。
祖母在祖父棺材里放了三样东西,菜刀、捕鱼的网兜和花牌。
为何放菜刀?
祖母解释,你爷爷是胆小的人,给他菜刀,他就不怕了。
也许,在棺材里放菜刀,是祖父自己的主意。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不能说“死亡”这个词,否则,祖父的长烟锅准会敲到我们脑门上。
祖父生前血性,却恐惧死亡,祖母生前懦弱,却对死亡无所谓,这样的悖论究竟被怎样的生死观统帅成生命的美学,值得我一生思考。
孤岛躺在长江里,孤岛人就是站在江水中。
孤岛是怎样的一个岛呢?
称它为岛,实际是长江在漫长岁月中遗落的泥沙冲积出的沙洲,土壤肥沃,气候四季分明,具备亚热带农作物生长的得天独厚条件,而相邻荆州的水域,河港沟汊、星罗棋布,又是典型的江南水乡。
稻谷、麦子、棉花、食油、各类鱼虾,一切经济作物,种啥收啥。
富庶的环境仍然留不住孤岛人。
走出去历来是孤岛人的愿望,只有躲逃天灾人祸才选择走进来。
譬如,我祖父从荆州来到孤岛,是因为眼睁睁地看着儿子病死,又受到仇家的奚落,按照父亲的话说,是消隐。
祖父他们移居孤岛,没有固定的房屋,靠着一尤姓大户搭建了一个偏屋,房顶是用油毡盖的。
到了夏天,偏屋里除了床和灶台,剩下的全是包裹,准备随时奔命。
1954年,长江涨水,严重威胁沙市和武汉,孤岛为缓解对面城市的压力,挖堤分洪。
这是祖父他们到孤岛后遇到最严重的一次水灾。
祖母就是在那一年的疲于奔命中,恨上了祖父,一辈子也不能原谅祖父的选择。
她本是孤岛人,嫁到荆州,就是想逃出孤岛。
生儿育女后,还是回到孤岛,这是命运的错乱还是宿命的安排?
就在那一年,祖母右眼瞎了,她很少说话,只是弓着身子拼命做事。
祖母个子很高,从我记事起,她的上身就直不起来了。
身在异乡,一家人遭受过许多凌辱,而祖母一律谦让、忍受。
有一年,我小姑捡远边花(即田主摘完棉花,剩下不要的棉花),捡了一满包袱,却被一个男人污蔑是他家的,我小姑争辩,男人朝小姑当众挥舞拳头,刚好打在小姑左眼上,留下永久的残疾。
小姑左眼视力总是模糊。
强悍的祖父到孤岛后一改以前脾性,他沉默,视而不见。
我祖母当场把包袱给了男人,只简单说了句:
说是你的,拿走吧。
在常年的忍辱负重中,祖母悟出――走出错乱或者宿命的安排,必须读书,她把所有精力放在培养父亲上。
父亲果然不负祖母期望,成为很有名气的外科医生,被我们县市誉为“一把刀”。
但是,祖母怎么也想不到,父亲多次放弃进城的机会,留在孤岛医院里。
亲朋好友有的埋怨父亲没有眼光,有的表示遗憾叹息,连母亲也为这事与父亲争吵过几次。
我却从没有听到祖母埋怨父亲一句。
母亲跟祖母说这事,祖母一言不发。
祖母本来寡言(她在我十四岁时过世,我几乎不记得她的声音),但她对父亲固守孤岛仅仅是因为寡言?
她不是一直渴望走出宿命般的孤岛?
现在,我写着她时,我认定――祖母已经知道了命数。
对她来讲,孤岛安排了一个人的命,但环围孤岛的长江却给了孤岛人命数。
走出与不走出,恰如离开与返回,究竟几何区别?
我肯定,祖母一定设想过不返回孤岛的生活,而恰恰是?
O想又让她安于现状。
多年后,我和我的姐妹那么厌烦周围的一切,没完没了的风沙和江水,逼仄的环境下频繁的灾难,我们满心都是渴望,渴望走出孤岛,以为离开孤岛就会摆脱冥冥中的宿命。
后来,我们如愿了,一个个远离孤岛,姐姐和妹妹走得更远,奔走异国他乡,可是命运的大手还是卡在我们脖子上,生老病死在我们身边如同灰尘,走过游来,构成我们的生活。
我承认,我很脆弱,一点点打击就让我灰心绝望,可是,我还在灰尘的缝隙里呼吸,还万分努力地靠近生活,在现在的我看来,正是孤岛和江水给我最早最永久的试炼。
循环之水留下的密语,岂止脚步丈量那样简单?
它是生命的密码,是生活档案。
我们注定要为它穷尽一生。
当祖母拉着父亲的手,说:
那有什么,冲走就冲走,江水要来,堤岸能挡得住吗?
反正都给了长江,由它不好?
这是她在我记忆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可是,我还是不能记起她的声音,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我母亲也是地道的孤岛人。
在母亲娘家人身上,最能体现孤岛人的性格,尤其是大舅舅。
外公家本不富裕,但三外公异常聪慧,率先在孤岛上千起船舶运输,并收购孤岛上所有的酒作坊,在四十年代,笼络了长江中下游漳河一带的漕运,是当时有名望的民营资本家。
母亲七个兄妹,除了大姨没有读书,其余个个进了学堂,这都是三外公的功劳。
念书最有成效的是大舅,读到大学时,接触许多新思潮,并多次领导学生运动。
在他即将毕业时,大舅被外公召回来结婚,是儿时的娃娃亲。
对方是三外公他们捡回来的孤女,一直侍奉着体弱多病、性格古怪的三外婆。
三外婆多年不孕,膝下无儿无女。
孤女成为他们唯一的孩子,很小就与大舅定下娃娃亲。
眼看大舅将要完成学业,有可能远走高飞,三外公他们逼着外公兑现诺言,要大舅赶快回家成婚。
外公召回舅舅,正是履行诺言。
怎么可能?
包办婚姻是违法的。
舅舅本能地反抗,还是被外公骗回孤岛。
洞房花烛夜,舅舅趁上厕所的机会,溜出家门,一路向南,跑到长江边,此时是冬季,江水干枯,在孤岛南边,只不过涓涓细流。
舅舅淌过长江,一直下落不明。
此后,舅舅回家一趟,要求离婚,舅妈上吊威胁,舅舅再次离家,踏上北上鸭绿江的火车,抗美援朝去了。
身为团长的舅舅,在朝鲜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三次战斗功,一次工作功,但在入党时,舅舅的问题暴露出来――三外公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抄家,抄出了金条送进了监狱,定上反革命罪名。
舅舅只要与三外公划清界限,他不仅能解决入党问题,还能平步青云。
但舅舅拒绝了,很暴躁又果敢地拒绝。
他说――人不能忘本。
舅舅的执拗成为他以后道路上铲除不断的荆棘,回国后,在昆明一家汽车厂当了一辈子技术员。
舅舅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离了近半个世纪的婚。
在他六十多岁时,我那个有名无实的舅妈同意离婚,舅舅独身一人生活。
然而,他们已步入老年。
青春、理想、爱情……流水般的岁月,于他们有着如何的面目?
一路冲刷来的时光洪流,“离”或者“拒离”筑构澎湃的热潮,纷纷击败任何一次“猜想”与“假设”的目光。
这未尝不是尊严的胜利。
一次搬家时,我们从一张照片和一封来自朝鲜的信笺中,知道了舅舅的爱情在朝鲜,他的金达莱已经不在人世,留下了一个儿子。
照片上的男子有舅舅的浓眉大眼。
生死茫茫,舅舅的岁月在他走出孤岛的那刻已经注定,他把他的一生都押注在他的硬气上,如同奔涌东流的江水,无法改写。
是的,如同长江般的男人,就是舅舅,孤独而华丽、执拗而悲壮、硬气而辽阔。
面对舅舅白花花的头发和眉毛,我一次次想起朝鲜的冰天雪地,它们在舅舅的心灵里,是如何解冻出传奇式的绚丽春天?
而一个人在岁月的洪流下,需要怎样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奔涌出宽阔的江河?
舅舅退休后,曾有一段时间住在孤岛,在我外公的孙女燕表姐家,离我曾经的舅妈只有一两里路。
舅舅散步时,遇到已经成为老妪的曾经是名义上的妻子,他会停下来,与她唠叨棉花、猪羊,老妪说着说着,会突然发怔,然后泪流满面地跑开。
舅舅久久伫立,燕表姐寻来,拉舅舅回家,舅舅嘟哝:
不是我的错,我有错吗?
这是一个充满内疚的男人。
他完全老了,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走不出家门一步。
现在,他对我说:
他过后,把他的骨灰撒在环绕孤岛的江水里。
我们哄他,还没有咧,你身子骨硬朗,阎王爷不收。
舅舅会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笑过后,又一遍遍嘱咐,过世后,把他的骨灰撒在环绕孤岛的江水里。
每次,我都哽咽着嗓子点头。
舅舅颤抖着双手捧起茶杯。
茶水从嘴角溢出,连绵成一条雨线,朦胧了我的双眼。
我懂得,只有把他的血液、骨头都交还给孤岛和江水,他的生命才拥有亲人的欣慰。
他害怕孤独,又不愿意屈服孤独,一生踽踽独行.生命的密语只有循环的江水才可以解密。
那一刻,我悲怆,倍感凄凉。
孤岛最美丽的时刻,是月光洒满江水的夜晚。
水波潋滟,银色的光芒被轻柔的江风抽丝剥茧,留下筋骨,一层层地镀进水流的心脏,清凉、静谧和光洁,环绕着耸立在江水中心的孤岛周围,它们耐心而诚挚地缝合裂痕,不动声色地抚平沧桑,孤岛如同一座逍遥岛随着江水漂流,它抱紧自己,切近逐渐睡眠的心脏。
我说得多么表象啊。
可是,这表象的文字没有一句虚妄之语。
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一个流传下来的传说,使孤岛散发出神性的光芒。
我多次在散文中叙述这个传说,简直不厌其烦。
可说到孤岛,孤岛外循环的江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