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民工的游民电影.docx
《电影民工的游民电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电影民工的游民电影.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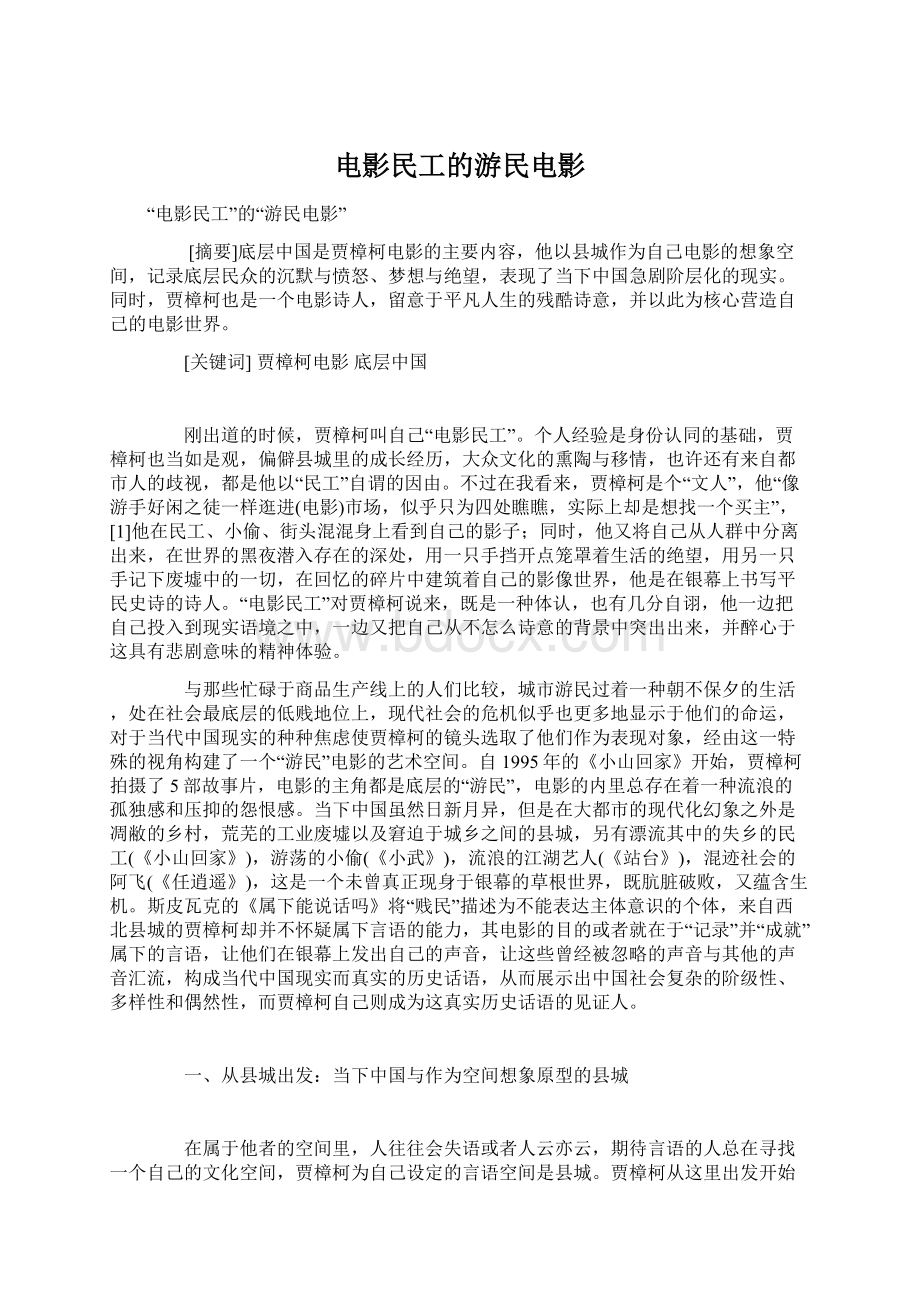
电影民工的游民电影
“电影民工”的“游民电影”
[摘要]底层中国是贾樟柯电影的主要内容,他以县城作为自己电影的想象空间,记录底层民众的沉默与愤怒、梦想与绝望,表现了当下中国急剧阶层化的现实。
同时,贾樟柯也是一个电影诗人,留意于平凡人生的残酷诗意,并以此为核心营造自己的电影世界。
[关键词]贾樟柯电影底层中国
刚出道的时候,贾樟柯叫自己“电影民工”。
个人经验是身份认同的基础,贾樟柯也当如是观,偏僻县城里的成长经历,大众文化的熏陶与移情,也许还有来自都市人的歧视,都是他以“民工”自谓的因由。
不过在我看来,贾樟柯是个“文人”,他“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电影)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一个买主”,[1]他在民工、小偷、街头混混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同时,他又将自己从人群中分离出来,在世界的黑夜潜入存在的深处,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生活的绝望,用另一只手记下废墟中的一切,在回忆的碎片中建筑着自己的影像世界,他是在银幕上书写平民史诗的诗人。
“电影民工”对贾樟柯说来,既是一种体认,也有几分自诩,他一边把自己投入到现实语境之中,一边又把自己从不怎么诗意的背景中突出出来,并醉心于这具有悲剧意味的精神体验。
与那些忙碌于商品生产线上的人们比较,城市游民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低贱地位上,现代社会的危机似乎也更多地显示于他们的命运,对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种种焦虑使贾樟柯的镜头选取了他们作为表现对象,经由这一特殊的视角构建了一个“游民”电影的艺术空间。
自1995年的《小山回家》开始,贾樟柯拍摄了5部故事片,电影的主角都是底层的“游民”,电影的内里总存在着一种流浪的孤独感和压抑的怨恨感。
当下中国虽然日新月异,但是在大都市的现代化幻象之外是凋敝的乡村,荒芜的工业废墟以及窘迫于城乡之间的县城,另有漂流其中的失乡的民工(《小山回家》),游荡的小偷(《小武》),流浪的江湖艺人(《站台》),混迹社会的阿飞(《任逍遥》),这是一个未曾真正现身于银幕的草根世界,既肮脏破败,又蕴含生机。
斯皮瓦克的《属下能说话吗》将“贱民”描述为不能表达主体意识的个体,来自西北县城的贾樟柯却并不怀疑属下言语的能力,其电影的目的或者就在于“记录”并“成就”属下的言语,让他们在银幕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这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与其他的声音汇流,构成当代中国现实而真实的历史话语,从而展示出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性、多样性和偶然性,而贾樟柯自己则成为这真实历史话语的见证人。
一、从县城出发:
当下中国与作为空间想象原型的县城
在属于他者的空间里,人往往会失语或者人云亦云,期待言语的人总在寻找一个自己的文化空间,贾樟柯为自己设定的言语空间是县城。
贾樟柯从这里出发开始了他与世界的对话,县城――汾阳是他电影的想象起点和空间原型。
县城在《小山回家》里是小山欲还的家乡,《小武》、《站台》粹是关于汾阳的小城故事,《任逍遥》虽然拍摄于大同,可是大同宛然是个廓大的县城,《世界》大则大矣,却不过是位于县城――“大兴”的微缩景观。
在贾樟柯看来:
“世界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假的,不存在世界,只存在角落。
世界不过是一个想象,使我们把各种各样的生活状况集中在一起的一个假象空间,而我们本身并不生活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只生活在角落里。
”[2]照我的理解,世界固然是个广大的实体,却浩然无边、玄机莫测,对它的认识始于虚构,贾樟柯所谓的角落就是汾阳――他畅想世界的起点。
在汾阳,中国,世界构成的空间同心圆里,汾阳是位于中心的一个,由此辐射出贾樟柯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想象。
汾阳在贾樟柯心底是关于世界的世界――元世界:
使电影的虚构空间产生的空间原型,并以此为基础构筑关于整个世界的阐释。
汾阳,远在山西的偏僻县城,由于贾樟柯生长于斯,或者还有去乡的想象,便被蒙上了一层或真或幻的历史感和神秘感,县城的客观空间物是:
街道、城墙、房屋、天空、市场……甚至还有落寞的行人,弥漫于空中的灰尘,食物的味道、或者其他莫名的气息,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诗学意义的空间结构。
在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里,县城的街道是人物主要的活动场所,是人物获得自我认识和价值认同的社会空间,而家庭是父权的领地,个体的压抑而寂寞,只有在街道、舞厅、录像厅、或者其他公共空间,人物才焕发出内在的活力。
譬如小武,街道是他唯一合适的栖身之地,在家庭,他沉默不语,在歌厅,他局促窘迫,而在街头,他似乎是一个王者,整个街道都是他的天下。
《站台》是浪迹江湖的青春故事,不过电影并没有将汾阳之外的空间表现得如何异样,外在世界的空气一如汾阳的空气,颜色、气味和声音尽皆相同,仿佛一干人的漂流不过从汾阳的一端踱到另一端,不曾丝毫跑到城墙之外。
至于《世界》,其实也就是汾阳城里的“梦巴黎”和“大上海”,封闭子一个“仿像”世界里的赵小桃们,就像偶然迈进“大上海”歌厅的小武一样,不过为县城的生活添了几分幻想,似乎并不能生出其他特别的意义。
贾樟柯将一个县城搬演于不同的故事里,不同的故事于是也就成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县城的故事,县城里的人们或者会离开县城,游走于外在的世界,可是却不停地失陷于“角落”之中,一梦醒来,世界不过米寸之间,也不比县城大多少。
县城之于中国便如中国之于世界,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县城,不如说贾樟柯在县城里发现了中国。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地理中,县城具有特殊的地位,是都市和乡村间的过渡空间,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在这里抵牾、冲突并融合,此地的人生具有矛盾又协调的悖反特征:
乡土性与现代性对立同一。
特别是在急剧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这种对立同一的悖反特征表现得分外明显,县城的人们在拥抱现代性;中击的同时,也在同样忍受着失去一些东西的痛苦,譬如传统的伦理关系、人际格局和道德体系,都市中也有如此情形,只是不及县城这般突出和尖锐。
《小武》就是一个不停的失落的电影,小武在电影中经历了数次的失落,友情的失落,亲情的失落,爱情的失落,还有自己的失落。
所有的失落无不与金钱关联,当小武在药店里称钱的时候,也许是在称量友情、爱情和亲情在当下中国的重量。
金钱的重量决定了县城里的空间分化,显示了当代中国以经济为衡量标准的重新阶层化的现实。
小武特殊的混杂身份――一个来自农村、活动在县城里的小偷,使电影的视野中又包含了关于城乡差别的内容,乡村也不是小武栖身的田园世界,其间的酷烈甚至可以淹没亲情,当父亲因金钱驱赶小武的时候,乡土中国的田园幻梦由是也彻底破灭。
来自乡村的小偷出没于县城的街道,也许是在无声地讨要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于乡村的盘剥。
县城的历史结构就最大程度地反映了这个现实:
一方面否认与乡村的同一性,通过与乡村的疏离而获得现代性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否定的痛苦和危险,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时刻带来伦理的压力。
贾樟柯的县城是一个含蕴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之痛的空间,城乡之间的日益强化的差别和对立在此间膨胀。
实际上,县城正在逐渐地成为飘浮于乡土海洋中城市飞地,虽也“现代”了,却成了无根之地,当下中国何遑不是如此。
贾樟柯的汾阳是一个微缩的中国镜像,远比他的《世界》现实而生动,大兴的世界公园如果是一个梦想,汾阳就是做梦的土地,它托起梦想,却与梦想无关。
总之,县城是一个含混的边缘地带,介于乡土中国与都市中国、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其双重被看――都市眼里的乡村,乡村目中的城市――镜像效应,成为县城指认自我文化身份的困境,造成县城不断地自我边缘化,同样这也是县城人生的境遇――含糊的身份、边缘的处境以及无望的空虚。
在贾樟柯电影里,县城含混的身份还表现于其中声音的驳杂:
高音喇叭的声音,是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它无远弗及却又辄起辄落;流行音乐的声音,是商业文化感性的诱惑,它无所不在却往往随风而逝;民众个体自己的声音,它微弱的盘绕于心底,却是这个县城中国最坚强的声音;当然还有其它物质性的声音,车声、脚步声、叫卖声……则构咸县城嘈杂的底色,其他的声音无不以此为衬底。
高音喇叭和大众文化的声音来来往往,此起彼伏的间隙却是人们自己的歌声从未停息,每一时代的高音喇叭和流行音乐不过是舞台的背景,时间的驿站,而平凡的人生则是这个舞台上日夜不息的梦与戏。
二、站台与舞台:
江湖――世界里的戏梦人生
《站台》的序幕由四个静止镜头构成:
等候入场的观众;尹瑞娟报幕及台下观众;舞台剧表演《火车向着韶山跑》第四个镜头是演员们在车内等候、点名、嬉闹,灯熄,车子开动,人声模仿的火车汽笛、轮轨声响起,灯光渐黑,车厢隐入黑暗,字幕打出。
字幕显示的过程中,火车的声音不曾断绝,渐徐渐远。
舞台是1979年冬天的舞台,舞台上戏谑般的歌声是一个时代行将结束的尾音,曾经庄严的舞台剧在观众的哄笑里获得别样的意味:
革命时代的政治说教成为群众娱乐的笑料。
这是1970年代的最后一场演出,然后人们聚集站台,赶往下一个时代。
持续的黑暗不过说明,当一个时代谢幕的时,夜晚如期而至,人们匆忙地登上一列不知所往的火车。
舞台和站台由此构成了贾樟柯对于人生、历史和现代性的看法,站台是线性历史时间流程上的时代标识,个体的生命经由它而获得人生的感觉和节律,而舞台则是人在自己的时代所获得表演空间,个人的表演时刻在时代的背景里闪光,得以点燃这漆黑的现代之夜,不过霎那的光亮之后依然是寂寞无尽的长夜。
站台的短暂停留带来人生的戏剧,而漫长的旅途依赖梦境打发时光,戏与梦的界限并不分明,人生如梦如戏,是所谓戏梦人生。
人生无论如何戏梦,总是个时间的旅程,“在路上”是其中首要的生命形态,而在站台“等待上路”则是另外一个形态,人生也许除了在站台无所事事的等待,就是无有目的的漫游。
不过世界广大,江湖路遥,出走的人生上下求索,却好像总是在原地徘徊,人们只有等待,等待一列开往远方的列车,站台上的等待成为人生最常见的风景。
“在路上”和“在站台”是贾樟柯着力表现的人生状态:
《小山回家》昱回家的路途永远在脚下又永远没有开始;《小武》的序幕就是站台上的等待,然后小武登上一辆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站台》的序幕也有等待,等待人齐,然后前往不知名的未来;《任逍遥》的伊始就是小济驾驶摩托,呼啸在大同的马路上;至于《世界》,赵小桃总是独自一人在公园的游览车上漫游,到达一个又一个的站台。
其实,“在路上”与站台并不矛盾,就像《等待戈多》一样,等待是路上的等待,“在路上”也是等待,等待充满了理由也没有任何理由,等待上帝,等待救赎,等待死亡,等待“等待”……等待使站台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味,它是等待的位置甚至就是等待本身。
崔明亮1980年代的江湖行是个等待青春流逝的旅行,他在等待尹瑞娟的爱,而尹瑞娟却在汾阳城里等待别的,当尹瑞娟也在等待的过程中年华尽逝,告别大棚生涯的崔明亮重返汾阳,尹瑞娟就把过期的爱情又还给了他。
岁月逝尽之后,昔日的恋人没有理由地坐上了同一辆车,驶往下一个站台。
电影以流行文化作为某个时代的精神站台,这是大众感知时代变迁的文化印迹,居于汾阳县城的崔明亮和尹瑞娟在时间的河中老去,能留存于他们记忆里的或者只有几首关于岁月的老歌。
在《站台》里不时响彻空间的广播喇叭中当然还有别的声音,一个宏大的历史之音:
刘少奇的平反;1984年的阅兵;1989年的通缉令。
以这些宏大的声音的为背景的凡人生活是如许的内容:
崔明亮、钟萍车站送张军去广州;张军、崔明亮陪钟萍堕胎:
崔明亮、张军们在车站等车,赶往下一个车站。
那些宏大庄严的声音似乎无处不在,却与凡人的世界无甚关联,人们在这些声音里等待和生活。
个体欲求,大众文化,主流历史是贾樟柯《站台》的里三个隐形角色,也是等待在站台上的人的历史文化结构,人生所向不过是这三者的合力而为,而其中贾樟柯最为在意的是个体的自由与体验,这才是人等待于站台的初衷。
站台是天地岁月的时间结点,也是人生的驿站,对于《车站》里的崔明亮们来说,下了站台就走上舞台,或者站台就是舞台。
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舞台是人情物事汇聚之地,人生天地的缩影,而世界亦是人生的舞台,或大或小,天天上演喜怒哀乐的人间百戏,舞台与天地同构而生,舞台的霎那堪比天地的永恒。
在贾樟柯的电影里,舞台有虚拟与现实两种,虚拟的舞台是戏剧的舞台,上演人生抽象的戏剧,是《站台》和《世界》里所呈现的那个舞台:
乡间戏台,排练舞台,江湖大棚……,而舞台的表演却为现实的生存,演戏亦是人生戏剧的一个段落,现实的舞台就是人生的舞台,演绎具体的生活,是电影营造的银幕空间:
汾阳,大同,江湖,世界……,虚构戏剧的生活源头。
其实人并不能分辨清楚现实人生和虚拟戏剧的界限,舞台上的戏剧是人的梦想和寄托,常常混淆于现实的生活,关于舞台的幻想就是关于别处之生活的幻想,当尹瑞娟在税务局的办公室独自起舞的时候,似乎现实的人生与梦幻的舞台已经二位一体。
贾樟柯关于舞台的思考似乎并不止于此,他还把观看他电影的人们也裹挟其中,在《小武》的片尾,我们被贾樟柯绑架进电影,摄影机使我们的目光与小武的目光重叠,在黑暗中的每个个体都变成了小武:
我们在看电影,电影里人们在看我们。
此身何身?
我们是在戏剧之外?
抑或在戏剧之中?
其实没有分别,生命的岁月哪天缺乏戏剧?
贾樟柯洞悉于此,将舞台搬演成人生的站台。
汾阳虽小,却是一隅江湖,《世界》却大,不过蝇头之地,无论大小,只是人生暂寄的站台,彼此并无差别。
岁月蹉跎,生命载沉载浮,惘然不知所向,即有灿烂的浪花,不过昙花一现,上台日亦是下台时,舞台的风光转瞬即逝,空留了许多的无奈与怅惘。
人道戏如人生,又说人生如梦,其实台下的期盼,梦醒的时分,何尝不是伫立站台的岁月?
汽笛声的响起,若何不是舞台召唤的声音?
戏与梦也许不差毫厘。
《站台》的尾声,崔明亮恬然安梦,手中烟蒂尚燃,温馨的镜头让人诧异,不知今夕何夕。
忽然炉水沸溢,哨声如火车汽笛,经久不息,崔明亮酣睡如斯,仿佛汽笛声彻响于梦中,崔明亮在梦里或者又上了舞台。
三、另一种现实:
底层生命的沉默与愤怒
贾樟柯有一个DV作品《狗的状况》,片子只有5分钟,拍摄了大同郊外的一只狗,它忧郁而疯狂,无休止的怒吠表达了来自底层的愤怒。
我觉得在这5分钟之前,它也许孤独而寂寞,而5分钟之后或者就是死亡,愤怒是沉默的绝望之声。
这部作品完成于2001年。
同年,贾樟柯开始拍摄《任逍遥》。
如果此前的《小武》和《站台》尚存些许的浪漫和暖意,那么《任逍遥》就表达了彻底的空虚和绝望。
《任逍遥》里,人物依然游荡街头,但是无助、无根的状态取消了游荡的青春意义,少年们冷漠而沉闷,面色暗淡而茫然。
其实,这种绝望的状态同样存在于《小山回家》,民工小山落魄而困窘的寻伴――回家之路何尝不是摆脱这空乏状态的尝试?
陷于空洞的社会现实中的底层生命从来不缺乏绝望的体验。
《小武》和《站台》也没有独立于这绝望和疏离的体验之外,县城里的小偷和大棚的艺人一样是被抛掷于社会底层的生命,当微薄的梦想一点点的破碎,剩下的便只是沉默的贱民生涯。
《狗的状况》大概就是贾樟柯所有电影的底层寓言,大同郊区的狗的痛与恨也许就是中国郊区的贾樟柯的痛与恨。
贾樟柯电影的主角大多是些沉默的人,这些沉默的人让电影也变得仿佛无话可说,只能一味的沉闷下去,消极的沉默成了贾樟柯电影的一个特点。
沉默并非决口不言,只是一种相对少言的生命状态,这种相对沉默的状态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底层难以表述自己困境。
人们一直以为,在现代社会以及人类历史中,底层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既缺乏表述的能力,也缺乏表述的权力,虽然人人都认可底层的表述的必要,可是阶层隔离使底层的言语发生在社会视野之外,几乎所有底层的言语都在被扭曲中传播。
从另一个方面看,面对媒体的沉默,包括在电影镜头前的沉默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表述,如果沟通和交流不可能达成或者只能被动的达成,沉默就是最好的言语。
贾樟柯因为知道沉默对于底层的意义,所以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的演员喋喋不休,人物只是无声地浪荡于喧闹的街道和嘈杂的市井,高音喇叭、流行音乐,以及各种噪声衬托出主体的沉默,沉默也许就是对于各种话语暴力的轻蔑和抵制,因此而具有了反抗的意义。
沉默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表现为如下几种:
一是压抑性的沉默,为主流原理所挤压造成的突然性失语,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小武》里,小武的徒弟面对街头突然采访时的茫然无措,一个小偷如何回答对于严打的看法?
二是内在化的心照不宣的沉默,譬如小武在小勇家与小勇的相顾无言,阶层化造成的新伦理壁垒让双方对于过去的友谊无从言语三是疏离性的沉默,被弃于主流社会轨道之外的底层民众对于主流叙事的隔膜与置若罔闻,《任逍遥》里的小济冷漠的置身于欢呼人群的背后,此时的人们因为听闻中国申奥成功而雀跃,他的沉默就是底层民众关于主流叙事的背书;四是对于痛苦经验的沉默,当没有人在乎你的痛苦时,沉默是避免进一步羞辱的最好措施;五是对难言之隐的沉默,表现为集体记忆的丧失,这个在《世界》里表现得最为显著,世界里的人们都对自己的农业背景讳莫如深,这是城乡差别和乡村歧视造成的沉默:
最后是抗拒性的沉默,也许前面所罗列的几个沉默都可以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拒绝言语不是不能或者不会言语,而是一旦说话就会在转述或者演绎中丧失意义。
其实这也可以理解贾樟柯为什么在所有的电影里坚持方言,对于方言的坚持其实就是对一同性话语的形式性拒绝,这也是一种沉默。
贾樟柯虽然执着于表现底层生民的缄默,但并不是制造了一个无声的底层世界。
当小武赤身摇晃于澡堂里,贾樟柯发现了小武喉咙里热情而饱满的声音。
也许在从某种文化分析的视角看,小武高歌的《心雨》除非他自己的言语,而是被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改造后的嗓音。
但是那一个阶层的言语是纯粹独立的言语呢?
知识阶层就能够完全的言传心声吗?
在我看来,小武的《心雨》倒真的是言传心声,辞堪达意,更具有人性的本质和力量。
世俗生活中的大众文化是底层民众的精神食粮,它或者真的会导致麻木与驯服,但也的确会激发幻想与反抗,其中涵蕴着世俗人生朴素的愿望和朴素本身的悲剧力量。
这种悲剧的力量在贾樟柯电影里表达为一种深沉的缄默,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表达形态:
无力的愤怒。
贾樟柯最愤怒的电影莫过于《任逍遥》,沉闷、冰冷的影像透露出一种近乎亢奋的残酷,所有的一切都在绝望的情绪中挣扎,但是没戏,一切皆是徒劳。
“任逍遥”大概代表了终极的自由,或者还有快乐,可是电影恰恰与逍遥无关,触目所及,都是禁锢与牢笼,人人不能挣脱。
贾樟柯的绝望与愤怒造就了《任逍遥》的绝望与愤怒,而这种绝望与愤怒或者就是当下中国最普遍的情绪,贾樟柯触及了当下中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任逍遥》中有一个镜头是小济模仿《邦妮与克莱德》中饭店打劫的一幕,其实这部电影就是一部中国版《邦妮与克莱德》,抢劫的初衷似乎是为了金钱,但实际上是为了摆脱绝望,可是行动之后,绝望更甚于前。
贾樟柯的《任逍遥》没有《邦德与布莱尼》那样张肆,让主人公一路枪林弹雨中狂奔,最后遍体弹孔告终,而是让彬彬和小济抢劫银行的行为在一声大吼中遽然完结,荒诞的失败使绝望的愤怒立时沦为绝望的空虚。
在电影的结尾,沉默寡言的小济在派出所里忽然唱起了歌曲《任逍遥》,慷慨激昂、宣扬乱世英雄主义的草根气质溢于言表,朴素而简单的情绪里包含的依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草莽精神,只不过江湖梦远、逍遥无地,愤怒、绝望还有梦想终成空虚,化作几句潦草的歌声。
其实不必对于底层的暴力情结太过苛责,当阶层分化日甚,几有天堂地狱之别时,谁还奢望让地狱里生出天使?
大同郊外的那只狗也许还活着吧,据说“贱种”的命都挺抗“造”。
贾樟柯的电影透露出强烈的底层气质和草根精神,他“在这个时代找不到什么他喜欢的事情,”[3]所以他说“自己不快乐,拍不快乐的电影,”[4]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电影缺乏诗意,诗意跟快乐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认为贾樟柯是第六代电影人中、或者说大陆中国影人中最具诗人气质的一个,我倾向于以诗来形容他的电影格调,而他自己则是一个用光影书写人生的电影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