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1.docx
《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1.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1.docx(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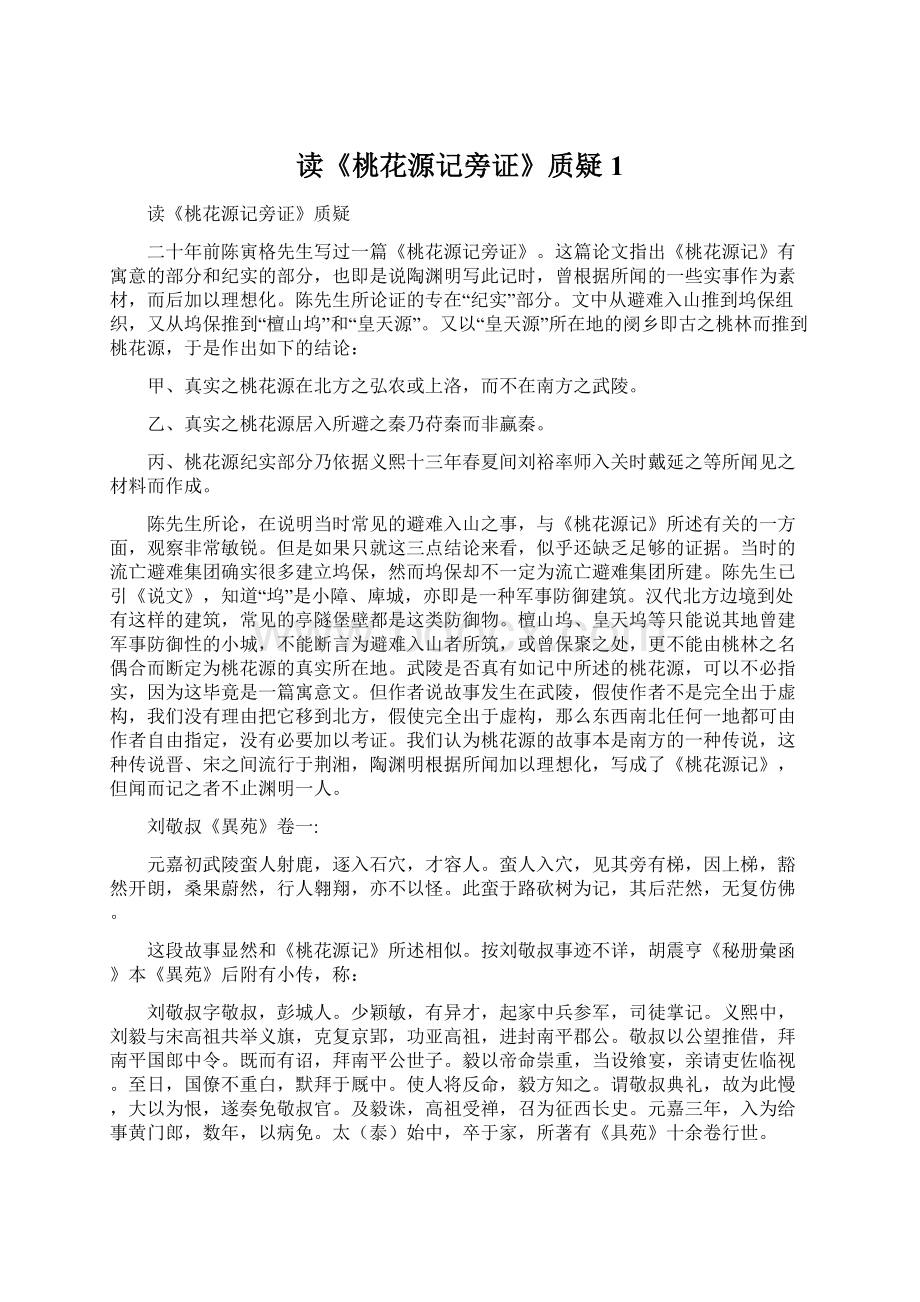
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1
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
二十年前陈寅格先生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旁证》。
这篇论文指出《桃花源记》有寓意的部分和纪实的部分,也即是说陶渊明写此记时,曾根据所闻的一些实事作为素材,而后加以理想化。
陈先生所论证的专在“纪实”部分。
文中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源”。
又以“皇天源”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于是作出如下的结论: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入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赢秦。
丙、桃花源纪实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陈先生所论,在说明当时常见的避难入山之事,与《桃花源记》所述有关的一方面,观察非常敏锐。
但是如果只就这三点结论来看,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当时的流亡避难集团确实很多建立坞保,然而坞保却不一定为流亡避难集团所建。
陈先生已引《说文》,知道“坞”是小障、庳城,亦即是一种军事防御建筑。
汉代北方边境到处有这样的建筑,常见的亭隧堡壁都是这类防御物。
檀山坞、皇天坞等只能说其地曾建军事防御性的小城,不能断言为避难入山者所筑,或曾保聚之处,更不能由桃林之名偶合而断定为桃花源的真实所在地。
武陵是否真有如记中所述的桃花源,可以不必指实,因为这毕竟是一篇寓意文。
但作者说故事发生在武陵,假使作者不是完全出于虚构,我们没有理由把它移到北方,假使完全出于虚构,那么东西南北任何一地都可由作者自由指定,没有必要加以考证。
我们认为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但闻而记之者不止渊明一人。
刘敬叔《異苑》卷一:
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
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
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这段故事显然和《桃花源记》所述相似。
按刘敬叔事迹不详,胡震亨《秘册彙函》本《異苑》后附有小传,称:
刘敬叔字敬叔,彭城人。
少颖敏,有异才,起家中兵参军,司徒掌记。
义熙中,刘毅与宋高祖共举义旗,克复京郢,功亚高祖,进封南平郡公。
敬叔以公望推借,拜南平国郎中令。
既而有诏,拜南平公世子。
毅以帝命崇重,当设飨宴,亲请吏佐临视。
至日,国僚不重白,默拜于厩中。
使人将反命,毅方知之。
谓敬叔典礼,故为此慢,大以为恨,遂奏免敬叔官。
及毅诛,高祖受禅,召为征西长史。
元嘉三年,入为给事黄门郎,数年,以病免。
太(泰)始中,卒于家,所著有《具苑》十余卷行世。
这篇小传我们述不能找到其来源。
其中为刘毅郎中令,因事免官一段见于《宋书》卷三〇《五行志》一,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已经指出。
小传只说义熙中,《五行志》是义熙七年(四一一年)事。
《四库提要》卷一百四十二以本书自述知道敬叔于义熙十三年为长沙王道怜的骠骑府参军。
按本书卷七吴兴沈庆之条,述废帝杀庆之事,这一年末即是泰始元年(四六五年),大概即小传卒于泰始中所本。
考敬叔于义熙七年为南平国郎中令,下距泰始元年已五十五年,假定他为郎中令时为二十五岁至三十岁,那末死时当在八十岁以上。
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四二七年),大约五十余岁。
刘敬叔与渊明同时而略晚。
他当然能够看到陶渊明的作品,然而这一段却不像是《桃花源记》的复写或改写,倒象更原始的传说。
我们认为陶、刘二人各据所闻的故事而写述,其中心内容相同,而传闻异辞,也可以有出入。
敬叔似乎没有添上什么,而渊明却以之寄托自己的理想,并加以艺术上的加工,其作品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这里我们还应该提出《異苑》的蛮人也是在武陵发现这个石穴的。
《異苑》所载的故事又见于《太平御览》卷五十四引《武陵记》,内容几乎与《異苑》完全相同。
《御览》卷四十九引《武陵记》云:
“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
”另外一条又说:
“昔有临沅黄道真在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
陶潜有《桃花源记》。
今山下有潭名黄闻。
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
”《武陵记》据章宗源《隋书经籍考证》,以为黄闵撰不知为何时入。
但《后汉书注》既引其书,应亦是南朝后期著作。
这本书中是渔人和射鹿蛮人的两种传说并列的。
桃花源故事说明本之陶氏之记,射鹿蛮人虽无说明,观其文字,应即本之《異苑》。
在其他书中,也还有类似的记载。
《云笈七籖》卷一百十二《神仙感遇传》蜀氏条:
蜀氏遇晋氏饥,辈三五人挟木弓竹夫入白鹿山捕猎以自给.因值群鹿骇走,分路格之。
一人见鹿入两崖间,才通人过,随而逐之。
行十余步,但见城市栉比,闾井繁盛,了不见鹿。
徐行市中,以问人曰:
“此何处也?
”人曰:
“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
”遂出穴,密志归路,以告大守刘悛,悛使人随往失其旧所矣。
庾仲冲《雍荆记》曰:
“武陵西(酉)阳县南数里,有孤山,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垅,拜而乞之,辄自拔,食之甚美。
山顶有池,鱼鼈(鳖)至七月七日皆出而游。
半岩室中有书千余卷,昔道士所遗经也。
元嘉中有蛮人入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蛮人逐之。
穴旁有梯,因上,即豁然开朗,别有天日。
行数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蛮人惊遽而出,旋削树记路,却结伴寻之,无复处所。
”
按《神仙感遇传》见于《宋史·艺文志》,无撰人名,上面为杜光庭的著作,或亦光庭所撰,总之应为唐末五代时书。
这一条记载其实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白鹿山小成都故事,当在后面再说。
第二部分是引庾仲冲《雍荆记》所述,故事内容完全与《異苑》相同,但更确指石穴在武陵西(酉)阳县南数里。
所谓庾仲冲《雍荆记》当是庚仲雍《荆州记》、《湘州记》之误。
《隋书·经籍志》有庚仲雍《湘州记》二卷,《汉水记》五卷。
《旧唐书·经籍志》有仲雍的《江记》五卷,《汉水记》五卷,《寻江源记》五卷,又一卷。
这一卷的《寻江源记》,亦见《隋·志》,但不著撰人名。
《新书·艺文志》同《旧·志》而无一卷之《寻江源记》。
《新·志》有《湘州记》四卷、《湘州图副记》,《旧·志》则仅有《湘州图记》一卷,都没有说庾仲雍撰。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宋晃载之《续谈助钞》殷芸《小说》引庾穆之《湘中记》,姚氏以为“似庾穆之即仲雍也”。
按雍、穆名字相应,姚氏的推测可信。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称《艺文类聚》山部所引正作庾仲雍《湘中记》,似庚氏所撰《湘州记》和《湘中记》本是一书之异称。
仲雍又有《荆州记》,见于《文选》注,《艺文类聚》所引。
庚仲雍是一个专精荆、湘地理的专家,他的事迹一无可考,亦不知何时人,但殷芸、郦道元都引他的著作,当是梁以前人。
他所记蛮人入石穴事大致本之《異苑》。
但他指定石穴所在或亦本之传说。
《神仙感遇传》另外一段蜀民入白鹿山事地点便不在武陵了。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三彭州九陇县白鹿山条引《周地图记》:
宋元嘉九年有樵人于山左见群鹿,引弓将射之。
有一鹿所趋险绝。
进入石穴,行数十步,则豁然平博,邑屋连接,叶陌周通。
问是何所?
有人答曰:
“小成都。
”后更往寻之,不知所在。
此当即《神仙感遇传》所本。
但《神仙感遇传》更加煊染为一个闹市,以求合于小成都之名。
地点是在彭州九陇县,移到了四川,但射鹿入穴的内容和《異苑》,《荆州记》或《湘州记》相同。
《周地图记》,公隋·志》著录一百九卷,不著撰人名,疑当是北周官书。
如上所述,我们一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见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则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见。
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着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传来的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结合,才构成《周地图记》所载的故事内容。
我们知道,陶渊明是曾在江陵住过一个时期的,他有“辛丑(晋隆安二年,三九八年)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诗题,其祭程氏妹文亦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罚”,皆可为证。
刘敬叔于义熙七年(四一一年)为南平国郎中令,南平即在江陵之南。
但刘毅是时方为荆州刺史,南平僚佐应亦随任江陵。
以后他又作长沙王道怜骠骑参军,自云“在西州”,西州亦即荆州,道怜于义熙十一年(四一五年)以骠骑将军为荆州刺史,至义熙十四年(四一八年)征还。
敬叔在江陵两次任职,居住时期较长。
至于庾仲雍应是新野庾氏,这个家族自南渡后长期住在江陵。
江陵距武陵不远,我们可以推想陶、刘都在江陵听到这个故事,庚仲雍所述虽本之《異苑》也可能他原来听到过,而在写作时参考了《异苑》。
《桃花源记》还提到南阳刘子骥。
《晋书》卷九十四《隐逸·刘驎之传》:
“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居于阳岐。
”戴校本《水经·江水注》“江水又右径阳岐山北”下注云:
“今考阳岐
即今石首县西山,在江之南岸”,刘子骥所居应即在此,距武陵更近一些。
我们应该注意《異苑》所记发见异境者是一位蛮人。
具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卷一所载的《桃花源记》有注云:
“渔人姓黄名道真。
”传世《陶渊明集》李公焕本《桃花源记》亦有此注,陶澎笺注认为李氏据《搜神后记》注是有理由的。
不管《搜神后记》是否为渊明所著,总述是南朝前期的书。
还有稍后的《武陵记》也采取黄道真为渔人姓名之说,并且指出是明沅人。
这里送给渔人的黄姓就颇有蛮族嫌疑。
《风俗通》卷九“世间多有蛇作怪者”条称“武陵蛮吏黄高攻烧南郡”。
《魏书》卷六十一《田益宗传》:
“萧衍建宁太守黄天赐筑城赤亭,又遣其将黄公赏屯于漴城。
”按《宋书·州郡志》郢州西阳太守属有建宁左县长称:
“孝武大明八年(四六四年)省建宁左郡为县,属西阳。
”《徐志》有建宁县,当是此后为郡。
又蕲水左县长条称:
“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四八年)以豫部蛮民立建昌、南昌、长风、赤亭……十八县属西阳。
”按照当时通例,左郡县的守令都以蛮族首领充当,所以黄天赐、黄公赏都应该是西阳蛮。
因此《桃花源记》中的渔人有姓黄的传说并不偶然。
武陵本是蛮族所居之地,这段故事发生在武陵,发见异境者是蛮人或具有蛮族氏姓的渔人,很可能本来是蛮族的传说。
《水经·沅水注》:
沅南县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险四绝,昔有蛮民避寇居之,故谓之夷望也。
南有夷望溪。
我们当然不想证明夷望山就是于此射鹿入穴的山,更不想把夷望溪当作《桃花源记》中的溪。
只是用以说明蛮民避寇进入深山在武陵是有传说的。
蛮民所避之寇是什么呢?
不言而喻,那就是历朝统治者政治上的乃至军事上的压迫,其目的在于掠夺蛮民财富。
这种事例在历史上经常看到,史籍中的蛮传都有较详细的纪载,这里没有必要加以引证。
本来山居的蛮族人民当遭受压迫之后,通常总是退入更深险的山中。
我们知道深险地区一般不适宜于农耕,因而希望获得如故事所传的那样一块乐土是很自然的。
此外,蛮族的社会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知道得不多,大致还逗留在氏族公社末期,他们内部已经出现了世袭的氏族贵族,但没有显著的奴隶生产制,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是不显著的。
蛮族人民当然要受自己贵族的剥削与压迫,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压迫来自外部的各皇朝统治者。
《宋书》卷九十七《蛮传》:
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
分建部落,布在诸郡县。
……变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
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
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所在多深险。
居武陵者有雄溪、满溪、辰溪、酉溪,舞淡,谓之五溪蛮。
这一段纪载,说明所谓“顺附”的蛮民,是要向政府缴纳租谷的,虽然史籍上认为无杂调、徭役,较之“宋民”为轻,但仍然是一种苛重的负担,以致常常引起反抗。
而且当政府进行军事镇压时,大量的蛮族人民及其财富便被掠夺。
在这段纪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饱受压迫的汉族人民“逃亡入蛮”,他们并没有被当作奴隶,而是被接纳下来,和蛮族入民共同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生产,也共同反抗封建统治者的进攻。
蛮族人民渴望摆脱外来的封建羁绊,以便保持其分隔的、狭隘的但是比较平静的公社生活。
这一点也是很自然的。
我们认为《桃花源记》和《異苑》所述故事是根据武陵蛮族的传说,这种传说恰好反映了蛮族人民的要求。
然而陶渊明在写作时并不是单纯复述了所闻的传说。
他也可能结合了当时常见的逃亡入山事。
记中称桃花源居民的来历乃是“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境,不复出焉。
”他所说的“秦时乱”既不像后来的御用史学家以农民起义为“乱”,也不指刘、项纷争。
在他的诗中开头就是“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显然是承用汉代以来“过秦”的议论,下面特别提到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是“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通篇没有一句说到逃避兵乱的话。
由此可见,他所说的“乱”是指繁重的赋役压迫。
我们知道三国时江南的宗部、山越中不少都是逃避赋役的农民。
东晋时期仍然如此,“逃亡”是当时最普遍的一种斗争形式,而其中一部分是亡入山林川泽,深险之区。
他们一般都在困苦的环境下坚持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
我们知道,山林川泽一直被认为是王有的,那里不发生土地私有的问题,特别是深险之处,人迹罕到,除了空洞的王有之外更谈不上归谁所有。
因而当逃亡人民迁入山中时,不难设想,在土地方面只能是作为公有的土地,计口配给份地。
我们也不难设想,按照当时条件,在山林湖沼地带垦荒是一种极端艰苦的工作。
逃亡人民很难有足够的农具和牛马,生产配备非常薄弱,剩余生产品必然也不会多。
为了保证生存,就只有最大限度地采取通力合作,彼此互助的办法。
既然如此,公社形式的组织自然给恢复起来,而且,恢复公社也正是农民的要求。
陶渊明的祖先原是鄱阳人,后来迁居浔阳。
我们知道汉末孙吴时期鄱阳以至南城一带是宗部势力相当强大的地区。
这种宗部是以宗族为核心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带着氏族残余。
原始性氏族残余当集体避难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曾经暂时延缓其成员的进一步封建化。
《三国·吴志》卷十九《诸葛恪传》:
众议咸以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
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
逋亡、宿恶咸共逃窜。
这里虽然是说丹阳山越,但山越是和宗部本有密切关系,鄱阳宗部的情况大致也相同。
由此可见,这些“幽邃民人”长期以来处于深山,几乎和外界隔绝,他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似乎还没有显著的封建剥削关系。
陶渊明既然祖籍鄱阳,迁居的浔阳亦距离不远,故老流传,应熟知旧事,而且东晋以来逃避赋役而入山的事仍然在继续。
因此当他听到武陵的蛮族传说后就会很自然地与他自己的见闻结合起来,写成《桃花源记》。
陈先生曾经举出若干史例证明宗族、乡里组成集团避难入山为当时习见之事,《桃花源记》所述即以此为背景。
这一点和我们的说法部分相似。
但是陈先生似乎把所有避难集团一般化了。
我们认为避兵和避赋役二者应有区别。
陈先生所举之例都是避兵。
我们知道当时避兵不管入山或是流移他乡通常都是由宗族乡里中的首领统率的,集团中间一开始就包含着两个对立的阶级。
而逃避赋役却除了个别例子以外,一般很少可能有封建统治者参加,因为他们无需逃避。
逃亡人民的集团是在封建统治者的围攻下建立起来的。
如上所述,由于所处环境的艰困和生产配备的薄弱,他们必须在较长期间保持通力合作,彼此互助的办法。
至于在豪强统率下的避兵集团就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纵有之,也立刻就会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承认豪强统率下的集团既然是以宗族、乡里组成,所以也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公社色彩。
我们也承认他们入山或者流移之始原来的豪强和所有成员一样丧失了他的土地,而眼前的土地由于本来是山险之地或由于经常迁徙,一时还说不上归谁所有。
加上生产的艰苦,合作互助的必要因而在一个短期内也可能使原有的公社因素滋长。
陈先生所引《晋书》卷八十八《庾袞传》所述大致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庾袞和同族、庶姓“保于禹山”时是彼此间“均劳逸,通有无”,而他后来避兵大头山当饥荒时,也是“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
显然,这种情况下很难有剩余生产品可供剥削,庾袞自己参加收获,似乎没有脱离劳动,他之作为首领是一种氏族家长式的。
可是我们必须指出存在于这种集团中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宗族、乡里组织纵然带有残余的公社性质,但是既然为其中的豪强(通常是官僚)所统率,这个豪强就必然要利用现存的组织为自己服务,庾袞入山之后,第一件事就要立主。
所有的“主”不管是保聚的坞主、营主,流移的行主总是把自己和所有成员间的关系变成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关系。
纵使在短期间公社残余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终于要走回原来发展的道路,即是成员的封建化。
陈先生曾经提出苏峻和祖逖的例子,我想这两个例子恰好说明这个间题。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说他“纠合得千余家,结垒于本县”,以后苏峻又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到了广陵。
这所部之数百家当然就是原先纠合的千余家中之一部分。
当他们随苏峻南渡时,业已成为他的部曲了。
同书卷六十四《祖逖传》称西晋乱时,“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被推为行主。
以后祖逖北伐除了召募了一批以外,“仍将本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
所谓本流徙部曲自然是指自太原南渡的亲党。
关于部曲这个名辞所包涵的内容可能是异常广泛的,我们在这里不拟讨论,但可以明确部曲对于将领具有私属的关系。
而且在此时部曲和客有时很难以分别。
我们还可以看出,那些坞主、营主在他们所屯据的土地上就是封建主,他们常常招徕流民。
这些流民被安置在上地上进行生产,缴租服役。
在坞主、营主的势力范围内分配土地的权力就操在坞主、营主的手中。
不管这些土地名义上是否有主。
实质上是由坞主、营主等占有的。
分配到一块耕地的人民在坞主、营主的统治下承担着耕战义务,这种义务是属于封建性质的。
由此可见,不管避兵入山或是流移,豪强统率下的宗族、乡里集团纵使在短期内带有公社残余因素,但立刻就会发生变化。
庾袞在最艰困的时候死了。
如果他所在的地区获得暂时安定,如果有更多的流民来归附,而以他为主的势力扩大了,很难想象如本传所述的那种太古之风会保持下去。
因此,如《桃花源记》所述的那种没有剥削的生活,那种“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秩序是和那时常见的避兵集团的坞壁生活很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