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阅读111之三总1169白马湖畔的小屋档.docx
《星期一阅读111之三总1169白马湖畔的小屋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星期一阅读111之三总1169白马湖畔的小屋档.docx(1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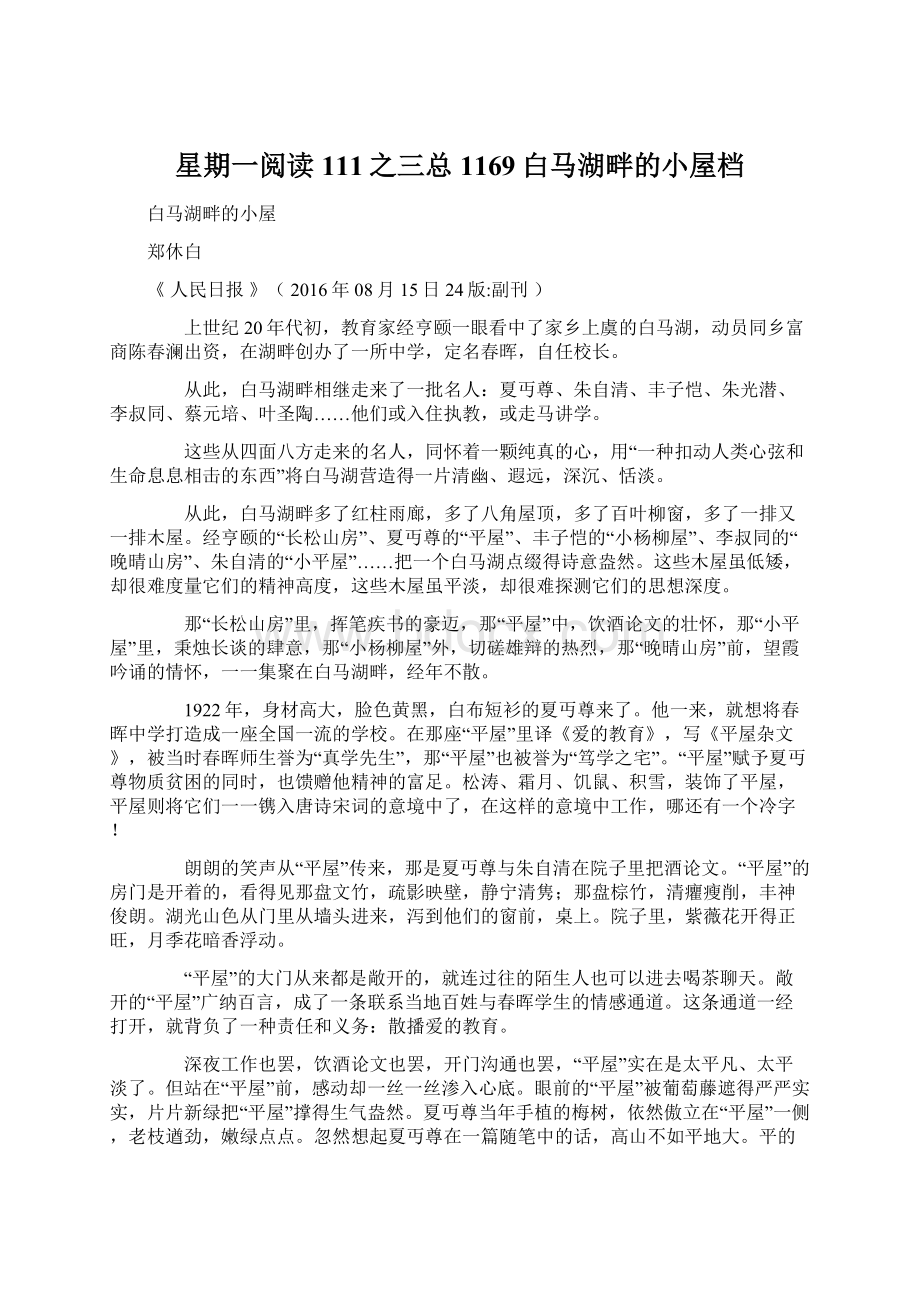
星期一阅读111之三总1169白马湖畔的小屋档
白马湖畔的小屋
郑休白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5日24版:
副刊)
上世纪20年代初,教育家经亨颐一眼看中了家乡上虞的白马湖,动员同乡富商陈春澜出资,在湖畔创办了一所中学,定名春晖,自任校长。
从此,白马湖畔相继走来了一批名人:
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李叔同、蔡元培、叶圣陶……他们或入住执教,或走马讲学。
这些从四面八方走来的名人,同怀着一颗纯真的心,用“一种扣动人类心弦和生命息息相击的东西”将白马湖营造得一片清幽、遐远,深沉、恬淡。
从此,白马湖畔多了红柱雨廊,多了八角屋顶,多了百叶柳窗,多了一排又一排木屋。
经亨颐的“长松山房”、夏丏尊的“平屋”、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李叔同的“晚晴山房”、朱自清的“小平屋”……把一个白马湖点缀得诗意盎然。
这些木屋虽低矮,却很难度量它们的精神高度,这些木屋虽平淡,却很难探测它们的思想深度。
那“长松山房”里,挥笔疾书的豪迈,那“平屋”中,饮酒论文的壮怀,那“小平屋”里,秉烛长谈的肆意,那“小杨柳屋”外,切磋雄辩的热烈,那“晚晴山房”前,望霞吟诵的情怀,一一集聚在白马湖畔,经年不散。
1922年,身材高大,脸色黄黑,白布短衫的夏丏尊来了。
他一来,就想将春晖中学打造成一座全国一流的学校。
在那座“平屋”里译《爱的教育》,写《平屋杂文》,被当时春晖师生誉为“真学先生”,那“平屋”也被誉为“笃学之宅”。
“平屋”赋予夏丏尊物质贫困的同时,也馈赠他精神的富足。
松涛、霜月、饥鼠、积雪,装饰了平屋,平屋则将它们一一镌入唐诗宋词的意境中了,在这样的意境中工作,哪还有一个冷字!
朗朗的笑声从“平屋”传来,那是夏丏尊与朱自清在院子里把酒论文。
“平屋”的房门是开着的,看得见那盘文竹,疏影映壁,静宁清隽;那盘棕竹,清癯瘦削,丰神俊朗。
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泻到他们的窗前,桌上。
院子里,紫薇花开得正旺,月季花暗香浮动。
“平屋”的大门从来都是敞开的,就连过往的陌生人也可以进去喝茶聊天。
敞开的“平屋”广纳百言,成了一条联系当地百姓与春晖学生的情感通道。
这条通道一经打开,就背负了一种责任和义务:
散播爱的教育。
深夜工作也罢,饮酒论文也罢,开门沟通也罢,“平屋”实在是太平凡、太平淡了。
但站在“平屋”前,感动却一丝一丝渗入心底。
眼前的“平屋”被葡萄藤遮得严严实实,片片新绿把“平屋”撑得生气盎然。
夏丏尊当年手植的梅树,依然傲立在“平屋”一侧,老枝遒劲,嫩绿点点。
忽然想起夏丏尊在一篇随笔中的话,高山不如平地大。
平的东西都有大的涵义。
是的,“平屋”没有幽州台的高峻,没有岳阳楼的雄伟,但谁又能说它不高峻,不雄伟呢?
今年,刚好是夏丏尊诞辰一百三十周年,逝世七十周年。
遥望“平屋”后通往象山腰的那条小道,夏丏尊与他夫人的墓隐约可见,这个低平的墓,从1946年到现在,整整七十年,一直对望着“平屋”书房的窗轩。
叶圣陶的碑文,马叙伦的墓志铭在苍松掩映下,闪闪烁烁。
于是就有诗句跳上心头:
“江南祭酒今属谁?
域外名贤苦见寻。
东莞高风留梵宇,香山雅望重鸡林。
翻经事业推能手?
疾世襟怀见素心。
留取艰贞傲岁晚,松姿未许雪霜侵。
”
1922年,丰子恺从上海来了。
他一到白马湖,就向人讨了一小株柳,种在寓屋的墙角里。
从此那间被朱自清称为“一颗骰子似的客厅”,成了文化沙龙中心。
油灯下,他们切磋宏论。
朗月高照,微风吹拂的晚上,住在白马湖的一批“布衣先生”总喜欢到“小杨柳屋”院内的那株柳树下,摆上一张八仙桌,打开一个老酒甏,端一碗炒螺蛳,边吃边谈。
“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
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他们个个才气横溢,彼此意气相投,共同追求真善美。
中国现代散文中的一脉——白马湖派,就在这样的气氛下诞生了。
一个美好的月夜,丰子恺一人漫步白马湖边。
一钩初夏的新月高挂中天,近看,白马湖微风细波,万木扶疏,远望,“小杨柳屋”帘卷西风,高朋雅坐。
他一下来了灵感,快步回到“小杨柳屋”,嗖嗖几笔就画出了那幅传世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用疏朗简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有木桌茶具,画面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
清幽的夜色,清雅的房舍,清静的心境,如泠泠的古琴声在画幅间流淌。
很有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
从此,那间“小杨柳屋”的客厅互相垂直的两壁上,常常贴满了丰子恺的漫画稿,微风过处,可以听见飒飒的声响,很有一种诗意和韵味。
丰子恺早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小杨柳散文》犹在,他的《小杨柳书法》还在,他的《白马湖春天》还在,他的《子恺漫画》还在,它们一一挂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长廊上,与“小杨柳屋”与白马湖一起,熠熠生辉。
如今,“小杨柳屋”东边的居室已辟为纪念室,纪念室的一角放着一架钢琴,掀开琴盖,高高低低的琴键已是破损不堪,用力击键,敲出几个音符来,不成调,但回旋在“小杨柳屋”上空,自有一种清幽高远的余音。
那是《游子吟》校歌,还是《城南旧事》插曲,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
1924年,潇洒倜傥的朱自清从宁波来了。
三天前,他还在宁波第四中学书房枯坐,独对孤灯,听屋外淅沥苦雨,想国事家事,风声、雨声、心声交汇一起,“万千风雨逼人来,世事都成劫里灰。
秋老干戈人老病,中天皓月几时回?
”三天后,他便接到夏丏尊的来信,要他立即到白马湖春晖中学执教。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微风飘萧的春日”“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
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人多少清新的趣味……这是一个阴天。
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
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
”朱自清走着,“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水很满,仿佛要漫到他的脚下。
“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
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
山水之美,真诚之美,闲适之美。
这是白马湖给朱自清的三件礼物。
他常常聚三五知己,烫一壶老酒,看月缺月圆,听潮起潮落。
或发思古之幽情,或作邈远之遐想。
朱自清十分喜欢白马湖,说,那里春天也好,夏天也好,黄昏也好,始终氤氲着一种诗意。
“青山绿水为伴,良朋益友为邻”,白马湖畔的幽远,小平屋的温馨,把多愁善感的朱自清从茕独凄苦中解脱出来。
他的灵魂在白马湖畔欢悦地高叫着,他的思想在小平屋里自由地驰骋着。
《春晖的一月》《白马湖》等一篇篇佳作呱呱坠地了。
中国现代散文的璀璨一页就要揭开,传世名作《荷塘月色》正在孕育之中。
一种柔情一旦被真善美所激发,就有不可阻挡的力量。
难以想象,当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后,这位柔弱的文人在那小平屋中拍案而起,一口气写下那急雨战鼓式的长诗《血歌》和《给死者》的心情,更难猜测,他在茕茕灯火下,运用理智利刃,剖析国情时的那种焦虑。
但可以肯定,这时的朱自清成熟了,成熟于白马湖爱的救赎,成熟于小平屋情的慰护。
望着朱自清屋子厅正中挂着的那幅照片,那炯炯的目光似乎还在寻觅那从门里、从墙头透进来的湖光山色。
桌上椅上旧物依旧,一尘不染,竟让人疑心他只是去了对面的学校授课,片刻就会回来。
老常的铃声(遇见)
赵华伟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5日24版)
老常一定是全校最守时的人,因为他的工作与时间有关。
老常生得黑,整张面皮犹如锅烟抹过,凭借与校长的故旧关系,在镇中学谋到了一份打铃的职事。
当最早的一道铃声响起时,我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望着黑乎乎的天空,会将每天的第一句话送给老常:
真是个催命不休的黑无常啊!
老常并不受我们爱戴,除了其所干的工作总是扰人清梦外,还因为他没老婆。
娶不到老婆的男人被称为“打寡汉”,被视为这个乡村社会的底层。
老常并不顾及这些,只将一挂铃铛敲得有声有色。
胆大的孩子从值班室门前走过时,会高声问一句:
老常,你是不是北京大学打铃系毕业的?
老常翻翻眼皮,恶狠狠地回着嘴,脸色也更加阴暗。
调皮的孩子还会趁晚自习时将铃绳扯断,或者打成死结系在树干上,为老常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
因此,就算深更半夜,也依然能看到老常抱着树身折腾的情景。
老常的饭量很大,一顿能下六个馒头。
饭点一到,他先去教师伙,将馒头一拿,打碗稀饭赶紧回屋,随后再奔学生伙,零星饭票出一点,又抱回来一堆馒头。
三两天一过,等馒头积攒得差不多,他就悄悄地装进蛇皮袋,送到公路边的饭店里。
几名馋嘴的学生在饭店开荤时发现了老常的秘密,老常很爽快,二话没说就帮他们结了“狗肉账”。
然而还是有学生嘴碎,让老师们也知晓了老常的秘密,跑到校长那里去告状,校长把头一晃说:
吃不掉的馒头都喂猪了,他讨个巧事也没啥。
既然连校长都这么纵容他,别人也就点不起火了。
正当大家以为风浪已经平息时,老常却把几名学生叫到了值班室,江湖道理一摆,点住脑门挨个骂了一通——看来,老常还有一副快意恩仇的脾气。
老常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就算看不到他的影子,也能从那富有节奏的铃声中,感知到他的存在。
可是有一天,熟悉的铃声突然中断了。
老常被派出所抓啦!
有人放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传话的人只说了结果,没给出原因,我们议论纷纷,一致归结为男女之事。
镇子是个大天地,老常连几个毛头学生的嘴巴都堵不住,更管不住镇上的风言风语。
政教处的马主任负责处理老常的事,走得急匆匆宛如火燎一般。
当我是个乡下人吗,老子是镇中学的职工,别人存车一毛五,凭啥收我两毛钱?
蹲在派出所里的老常,理直气壮地辩解道。
就算你是个大人物,也不能当场给人家两拳头吧?
打了人就得出点钱,不然难平和!
所长摊着巴掌反驳道。
老常不认罚,存车员不妥协,双方从下午三点一直僵持到晚上八点,无奈之下,所长只好把电话打到了镇中学。
于是,马主任奉命去领人,钱一缴认了罚,连拖带拽地把老常扯了回来。
老常心里不痛快,一路走一路骂,直到进了校门还在朝派出所方向张望呢。
不过,在经过那挂铃铛时,老常忽然闭上了嘴巴,望着飘动的铃绳摇了摇头。
老常不在,当晚的铃没人打,老校长只好亲自出马。
他在各个班级巡视时,不停地看着表,不知是怕错过了时间,还是在为老常担忧。
时间一到,老校长赶紧去打铃,一下一下地拽着,铃声单调而断续,完全失去了以往的飘逸和自信,就连老师们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幸好,学校的铃声只断了一天,就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预备铃自然轻快,两响一停;上课铃短暂急促,三响一停;放学铃舒缓自由,一响一停;每种铃声都带着明快的节奏感,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
无所事事时,老常就坐在门槛上嘀咕:
马主任老实,白给了人家两张“大团结”,要是按我的性格,他连个屁渣子都讹不到,不就是一存车员吗,呸……嘀咕完毕,老常阴沉的脸色开朗了许多,甚至还露出了胜利般的笑容。
我们只是听,不愿去接他的话,听得烦了,岔开话去询问他打铃手艺的事,老常嘴一咧,朝北指了指。
北京大学真有个打铃系?
我们诧异地瞪大了眼睛。
老常嘿嘿地笑着,一张黑脸皱成了橘皮。
人们倾尽一生所追求的,无非出人头地。
对于老常来说,他想要的也只不过是一个不被蔑视与轻贱的“大我”而已。
打铃,打出个说道来;做人,做出个说道来。
大埂古村小记
叶延滨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5日24版)
五月的浙西,烟雨蒙蒙,一座座青山隐现于缥缈的云雾间,洗出满目青翠。
此时出行,是种享受,呼吸那大山密林间透出的清新,忘情于青山绿水,任绵绵细雨一阵阵洗去都市生活积在胸中的尘埃。
我们一行前去常山县的大埂村。
大埂古村位于严谷山麓,东边是三衢石林风景区,西北毗邻开化国家地质公园。
古村的两位“邻居”皆是有名头的风景区,古村让人羡慕的生态环境,自然也是不用多说,一句“青山绿水怀抱中”,足矣。
前些日子,大埂古村被当地政府列入了“历史文化村落保护与利用重点村”,这次是文化部门的领导邀我们一行前往,一是想让我们感受一下大埂村尚没有进行“开发保护”、完全原生态的古村魅力;二是希望我们能从一个外来者的角度,为古村的保护开发提供一些建议。
在村子里走了半天。
村头村尾,花草林木,房前屋后,窄巷宽池,拐角遇见乡情,抬头就有惊喜,撞见许多让我心跳的场景,记下许多让我眼热的风情。
怕它们今后消失了,消失如擦身而过的老朋友,只剩下隐于雨帘的背影。
写此小记,留下二三履迹,不虚此行。
会所。
会所是现在大家都能理解的名称。
古村有两处岁月遗留下来的会所。
一间是吴氏宗祠。
最早建此古村的是安徽迁居的吴氏,定居后在此开矿经商,成为古村大姓。
吴氏宗祠始建于清代嘉庆四年。
岁月蹉跎,风雨侵蚀。
高墙石柱大门面的祠堂,已经残破得塌了一半屋顶。
不过那些残存的高墙,那些依然屹立的红砂石柱,那些精细雕刻的木刻配饰,足以让我们想到当年家族兴旺的气势。
另一间会所是半个世纪前,人民公社修建的礼堂。
现在这个礼堂依然是间公用场所,破旧的大门口,挂着几个木牌:
“文化活动室”“村邮站”“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室”。
人民公社对于年轻一代,已然成了过去的故事。
当年在这个礼堂里开会的年轻人,今天成了这所“老年活动中心”的常客。
墙上残留着过去岁月的印迹:
“人民公社好!
”“战无不胜的……”迎面在礼堂最醒目的舞台右墙上,是一幅新挂上的大标语:
“老有所养。
要支持老人,不要讨厌老人。
”每个字都有一尺见方,让这个礼堂平添了几分沧桑。
两间“老会所”,曾是古村的政治文化中心,现虽残破,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一路上,我总说一句:
破的修,旧的留啊!
古树。
古村有资格叫古村,最可信的依据正是守着村庄的那些古树。
村里三百年以上树龄的樟树和柏树有十多棵,它们骄傲地站立在村子的各个角落。
吴氏家谱记载的家训称,这些树木“护抱阳基,镇守水口”,“子孙永远不许盗砍”。
浓荫之下,子孙之福。
它们是古村最有资格的历史见证者,见证岁月的变迁,也见证好的村风民约如何荫泽后人。
我对同行的村干部说:
这些年,到处都说自己是老庙古迹。
我就把定一点,老庙新庙,不看菩萨,看庙里的树。
他笑了。
老宅。
老百姓各家过各家的日子,各家盖各家的房子。
大埂村星罗棋布的民宅,让我想起“二八月,乱穿衣”的景象。
早先的低矮民房,变成了水泥小楼。
穷怕了的老百姓兜里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盖新房。
这种事不需要村干部和政府太操心。
让人操心的是散落在古村里的旧日豪宅。
全村有十几处清末民初的老宅。
这些宅第多是徽派建筑风格,四围青砖高墙,马头翘角,与外界相通的高墙下的门窗,皆石砌石雕。
进门后是四合天井,室内是木结构的两层居室。
外围高墙石门窗,坚固结实,防火防盗。
内室木结构家居,宜居舒适,贵气典雅。
经过百年风雨之后,坚实的外墙残留几分豪门气度,内室的木头居室早已朽蚀。
走进一户人家,只剩老妪在这空旷的残楼里留居,同样恋着旧家的是檐上的燕子。
新巢刚刚筑好,小燕已伸头张望。
在新巢的左右,横梁上有一排老巢留下的旧巢痕迹,让人的眼睛一下子潮润了。
我说,老宅改造后,若是燕子还回来筑巢,那就真好!
方塘。
古村能聚百户千人,是因为有一眼清泉。
泉涌如注,筑塘蓄之。
大概是早年的秀才,给方塘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毓秀塘”。
方塘值得一记,是因为此塘由四个水塘合而为一。
第一塘是泉塘,蓄积饮用之水。
第二塘,洗菜蔬水果之水。
第三塘,洗衣清洁用水。
第四塘,清洗家具农具用水。
泉水依次流经四个水塘,最后流进灌溉渠道。
规矩方圆,环保生态,尽在不言之中。
古村风水好,青山在后,清水过门。
在家同饮一泉,是天赐的缘分,出门各奔东西,是一生的乡愁。
高兴的是古村将有机会“保护开发”,担心的是万一像有的地方新农村“万象更新”,新房新路后面只剩一张抹去记忆的白纸。
于是,写此短文,记大埂古村岁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指纹”。
写长还是写短(大地漫笔·编辑丛谈)
马涌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5日24版)
来谈谈写文章的长与短。
写长文章更难,还是写短文章更难?
严格地讲,这算不上一个问题。
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要求,并不是单纯只靠字数长短来划分,更谈不上孰难孰易。
但是如果非要说的话,直觉上讲,似乎是长文章更难一些——毕竟,诸如“驾驭不了这么大的题材”“驾驭不了这么长的篇幅”之类的评语,还是不罕见的,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长文难写”的第一印象。
不过回到编辑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平时对稿子的编辑处理,绝大多数时候却是在做减法——删。
这里面固然有版面有限的原因,但这也恰恰说明了,对于具备一定写作水平的创作者而言,对文字的“控制力”是比纯粹的文字“生产力”更亟须打磨的能力:
写作者在自己“写不出来”时往往都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却少有人能主动意识到自己“写多了”。
可见,能把长文写短,能把短文写好,也都不是一件简单事。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番老生常谈呢?
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喜欢写“短文”的来稿者似乎是越来越多了。
譬如写两三句诗,自称是“截句”的;或者写个百十字的小故事,冠以“微小说”“绝句小说”的。
诗歌是门玄奥学问,“绝句小说”等我也无甚造诣,对其文体本身没什么发言权,但直接的工作经验和间接的经典阅读告诉我:
短文不好写,想要在几行或者百十字里传递思想、讲述故事,而且还经得起品鉴,那简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一样的绝技了;反之,一个不小心,就容易沦为抖机灵、讲段子。
大道至简,是要在落尽繁华之后的,倘若把短章当做文学创作的捷径,恐怕是行不通的。
文不嫌短,只怕短而不精;文不惧长,只恐长而无趣。
写长还是写短,不应去赶什么“时尚”,当长则长,该短则短,这样才好。
丙申抒怀
陈特安
《人民日报》(2016年08月15日24版)
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旗红,万里行程,记忆永恒。
忆艰难险阻,豺狼凶顽;前轰后炸,血雨腥风。
革命将士,凌云壮志,摩顶苍鹰亮翅腾。
饥寒迫,历千辛万苦,依旧雄风。
破围追战堵截,看赤水娄山奇兵成。
过雪山草地,铁流堤决;雄关踏破,足响声声。
华夏豪杰,志坚骨硬,何惧风高彻骨冷。
开天举,有长征旗帜,紫气东升。
神州长荣
镰锤托起朝阳红,
南国枪响春雷动。
井冈星火燎原势,
万里长征缚苍龙。
士志凌云霄汉冲,
乾坤浩荡家国隆。
九五华章复兴梦,
七彩神州景长荣。
玉镯扣栏
日期:
2016-08-15作者:
介子平来源:
文汇报
介子平
才子情史,自古两个版本,一正史,一野史。
后人津津乐道者,定在野史,时过境迁,真假不再重要,一样的论世知人。
据说表妹纳喇惠儿进府,情窦初开的纳兰性德与之一见倾心,继而两心相许,海誓山盟,进而神魂颠倒,不能自拔。
然好景不长,哀乐无常,惠儿应召入宫,此乃旗籍女子必过的一关,心存侥幸,却还是一选即中。
纳兰遭此变故,从此一蹶不振。
惠儿入宫,起初为庶妃,康熙十六年八月升惠嫔,二十年十二月晋惠妃。
为康熙育二子,死后葬景陵之妃园寝。
文学作品中的演义,便精彩多了。
据无名氏 《赁庑笔记》 云:
“纳兰容若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
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
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夙因。
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彼妹一见。
而宫禁森严,竟不能通一语,怅然而出。
”传奇故事,妙就妙在离奇而能自圆。
纳兰为能与表妹谋得一面,竟趁国丧之际,假扮喇嘛进宫。
天遂人愿,二人果见于回廊。
梁祝楼台相会,祝英台唱道:
“记得草桥两结拜,同窗共读有三长载,情投意合相敬爱,我此心早许你梁山伯。
可记得,你看出我有耳环痕,使英台面红耳赤口难开;可记得,十八里相送长亭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出来;可记得,比作鸳鸯成双对;可记得,牛郎织女把鹊桥会;可记得,井中双双来照影;可记得,观音堂前把堂拜。
”然宫禁森严,惠儿已非民间女子祝英台,哪敢有这般大段唱词,吱一声都不可能,遂以玉镯扣栏,传递心声。
玉声细微而清脆,无意者不闻,有情人自知。
“她临去秋波那一转,铁石人,情意牵”,此时的纳兰,盘腿蒲团,不能起身,两眼远注,无限惆怅,先前说过的话,皆可当作承诺。
这个手印打给你,愿你平安过冬夏。
好事者推论,其《昭君怨》 便是为惠儿所作:
“深禁好春谁惜?
薄暮瑶阶伫立。
别院管弦声,不分明。
又是梨花欲谢,绣被春寒今夜。
寂寂锁朱门,梦承恩。
”
此一面,终成生离永隔。
之后的两年间,痴情纳兰借公务之便,时常探访回廊之处,始终未得再见一面,“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理性提醒,无济于事,虽如此,不死心,企盼御沟流叶、破镜重圆式的奇迹再现。
一样情怀,两处相思,痴心惠儿不堪情感折磨,吞金自尽,一命归阴。
纳兰悲痛欲绝,为之披麻戴孝,并于闺房题壁:
“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银墙,不辨花丛哪瓣香。
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
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
”此词为谁而作,待考,却是情感热烈到了十二分,刻画到了十二分。
一读兴叹嗟,世人争唱饮水词;再吟垂涕泗,纳兰心事谁人知?
打动他人者,必是打动自己在先,好诗好词大致如此。
曹植与甄宓也两情相悦一双,然有小人暗中施计,以桃代李,终使甄宓嫁曹丕。
才高八斗的曹植陷入痛苦泥淖,昔时恋人成叔嫂,再有相见,无言以对。
数年后,曹丕称帝,逼曹植七步成诗,之后贬出京城。
皇图霸业谈笑间,不胜人生一场醉,空遗满腔悲愤的曹植,过洛水,对河悲吟 《洛神赋》。
千古传诵之文,起初也都是作者写给自己的独白。
几十年后,乾隆帝读 《石头记》,只见其同,不见其异,遂惊叹“这写的是明珠他们家的事儿”。
纳兰容若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逝,撇下钟鸣鼎食、肥马轻裘,毅然追情而去,年三十有一。
做饺子馅的小龙虾
日期:
2016-08-15作者:
王忠范来源:
文汇报
王忠范
又回到北国老爷岭下的农村老家,写作写累了就下河蹚水捞喇蛄,仿佛回到孩提时代,多趣多乐,悠悠然,妙也。
这种东北人称为喇蛄的甲壳节肢动物,山里山外的河中都有。
查老字典才知道,喇蛄的学名叫红螯虾,是一种淡水小龙虾。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每每下河洗澡时,都会捕捉到一些喇蛄。
这小巧玲珑的喇蛄一身青黑青黑的硬壳,两根细细的长须,两只能开能合像钳子一样的趾角。
一不小心,手或脚被趾角夹住,疼得很,有时疼出眼泪。
但上岸后,架起干柴一只只烧着吃,又香得连蹦带跳。
最有趣的是跟大人晚间去打捞喇蛄。
天彻底黑下来时,我们这些孩子或拿带油脂的松枝或捆一把麻秆,点燃当作火把,沿着河岸慢慢往前走。
火焰一照,喇蛄就纷纷爬出水面,大人们便抬着片网打捞,用不了多长时间,桶和筐就装满了。
喇蛄多,就煮熟拍碎,包喇蛄饺子做喇蛄豆腐,既鲜亮又好吃,常常吃得我满脑袋是汗。
如今尽管人老了,河里的喇蛄也少了,然而捕捞中却有新的发现,更能品到生活的乐趣与滋味。
码完文字,心情好,便顶着烈日来到小河。
树荫里看花听鸟之后,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走进河水,顿觉凉快爽悦。
捞喇蛄不用往深水里去,因为喇蛄大多藏在河边的卵石中和水草里,很隐蔽。
我手拿筛子底的矮沿柳条筐,来来回回地蹚水,惊扰得那些喇蛄悄悄地拱出来。
我发现喇蛄眼睛尖,挺机灵的,当看你要去捉它时,便突然倒退躲逃,或仰起身很快顺水漂去。
可我迎着水流用筐打捞,它就难逃罗网了。
捞上来的喇蛄装进肚子大脖子细的鱼篓,还要封盖,不然它们会爬出来偷偷溜走,顷刻无影无踪。
看来不管什么动物都是有办法对付人类的,但总也没有人类的办法多。
随着时光的变化,喇蛄的做法也多了起来。
除了以前包喇蛄饺子做喇蛄豆腐以外,可先用植物油、料酒、老醋浸泡,接着炭火烧烤。
这夏秋间的喇蛄熟了后不但红出了亮光,而且黄满肉肥,蘸着葱花、蒜末吃,厚实嫩润,别有味道。
若加上油、盐、姜片、酱油、味精等佐料,爆炒或者清蒸,吃一口满嘴生香。
就着这美味佳肴,喝几口小酒,安然自得,心神悠悠。
我时而邀几位老友来同品共饮,更觉痛快,意味无穷。
自己的样子
日期:
2016-08-15作者:
陶文瑜来源:
文汇报
陶文瑜
一开始我想到的题目是笑傲江湖,“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我心目中的王锡麒老师,有点这个意思。
他是自学成才的人物画名家,似乎无师自通,却在水墨画创作上,开辟了一番别致而新颖的境界。
我想把他比作金庸小说中的那些英雄人物,郭靖、杨过、令狐冲、张无忌,他们全不是出自少林武当南拳北腿,因为特殊的机缘和自己的聪颖,努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