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的测算基于CGSS的实证.docx
《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的测算基于CGSS的实证.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的测算基于CGSS的实证.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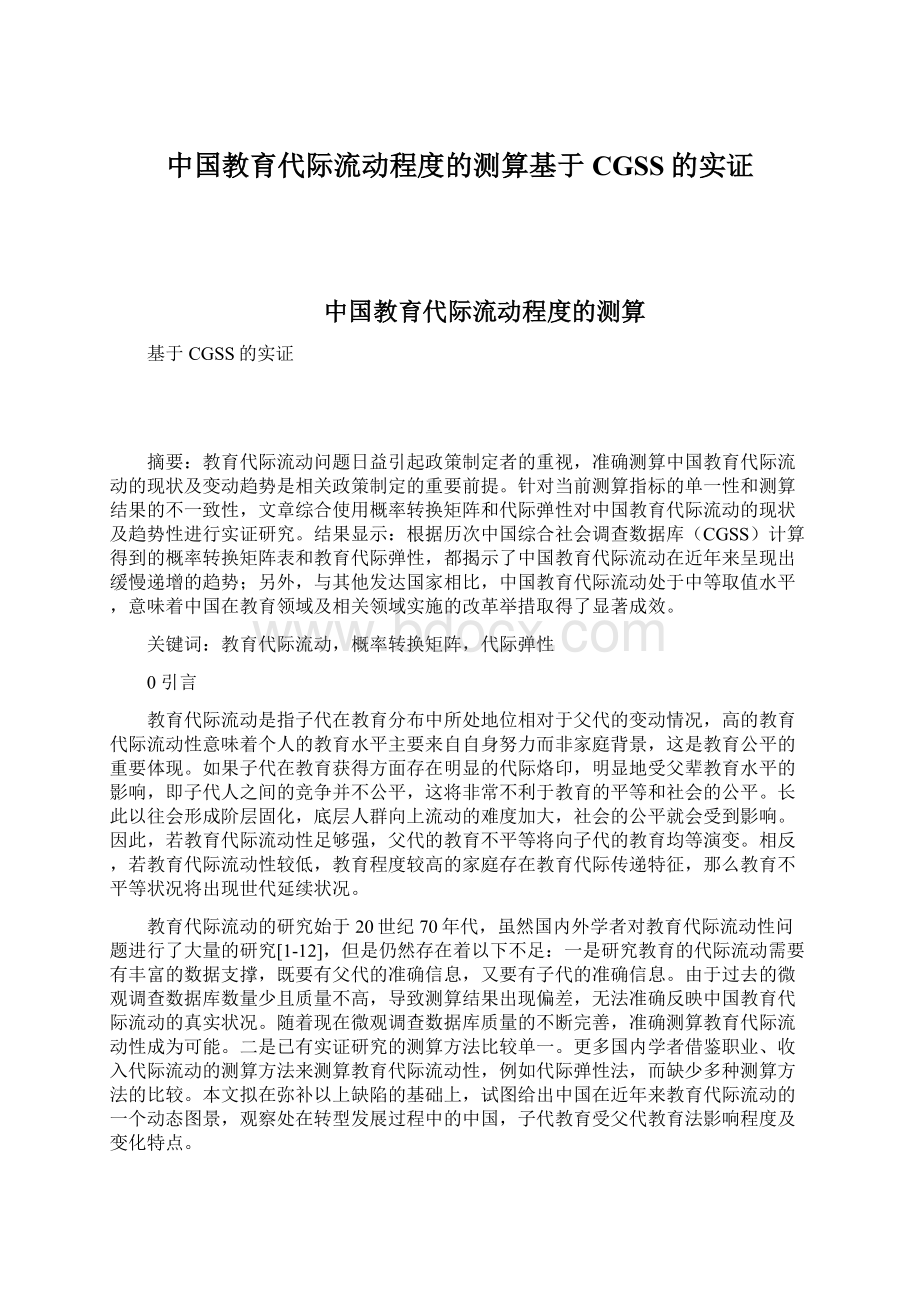
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的测算基于CGSS的实证
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的测算
基于CGSS的实证
摘要:
教育代际流动问题日益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准确测算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变动趋势是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
针对当前测算指标的单一性和测算结果的不一致性,文章综合使用概率转换矩阵和代际弹性对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的现状及趋势性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
根据历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计算得到的概率转换矩阵表和教育代际弹性,都揭示了中国教育代际流动在近年来呈现出缓慢递增的趋势;另外,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教育代际流动处于中等取值水平,意味着中国在教育领域及相关领域实施的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关键词:
教育代际流动,概率转换矩阵,代际弹性
0引言
教育代际流动是指子代在教育分布中所处地位相对于父代的变动情况,高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意味着个人的教育水平主要来自自身努力而非家庭背景,这是教育公平的重要体现。
如果子代在教育获得方面存在明显的代际烙印,明显地受父辈教育水平的影响,即子代人之间的竞争并不公平,这将非常不利于教育的平等和社会的公平。
长此以往会形成阶层固化,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难度加大,社会的公平就会受到影响。
因此,若教育代际流动性足够强,父代的教育不平等将向子代的教育均等演变。
相反,若教育代际流动性较低,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存在教育代际传递特征,那么教育不平等状况将出现世代延续状况。
教育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虽然国内外学者对教育代际流动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1-12],但是仍然存在着以下不足:
一是研究教育的代际流动需要有丰富的数据支撑,既要有父代的准确信息,又要有子代的准确信息。
由于过去的微观调查数据库数量少且质量不高,导致测算结果出现偏差,无法准确反映中国教育代际流动的真实状况。
随着现在微观调查数据库质量的不断完善,准确测算教育代际流动性成为可能。
二是已有实证研究的测算方法比较单一。
更多国内学者借鉴职业、收入代际流动的测算方法来测算教育代际流动性,例如代际弹性法,而缺少多种测算方法的比较。
本文拟在弥补以上缺陷的基础上,试图给出中国在近年来教育代际流动的一个动态图景,观察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子代教育受父代教育法影响程度及变化特点。
1测算模型的设定
1.1教育代际弹性模型
已有文献通常使用教育代际弹性这一指标来衡量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大小。
教育代际弹性越高,代际流动性越低;反之,代际流动性越高。
模型的方程式为:
lnEci=α0+βlnEfi+εi
(1)
其中,Eci、Efi分别代表子代、父代的教育程度,εi代表残差,参数β表示教育代际弹性。
式
(1)中没有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所以β涵盖了所有父代教育与子代教育相关的信息,这种相关性来源于基因遗传、父代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和家庭环境影响等多种因素。
1.2概率转换模型
概率转换矩阵法也是测算代际流动的常用方法,通过把学历层次分为六个等级,即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然后计算父代教育水平到子代教育水平的变化情况,构建一个概率转换矩阵表,如式
(2)所示。
该矩阵能够反映教育代际流动的大小,也能够反映教育代际流动的方向。
概率转换矩阵表中第i行j列的元素pij表示父代教育层次是j,且子代教育层次是i的概率。
该矩阵各行元素之和等于零。
另外,可以通过概率转换矩阵表构建以下几种概率转换系数:
(1)
。
M1计算的是概率转换矩阵主对角线上各元素之和,也就是父子教育层次相同的概率,因此M1被称为“代际传承系数”或“不流动系数”。
(2)
。
M2计算的是子代教育与父代教育之间的平均距离。
M2的数值越大,代表子代教育与父代教育的平均距离越大,表明教育代际流动性越大;反之,教育代际流动性越小。
(3)M3=1-|λ2(P)|。
λ2(P)表示概率转换矩阵P的第二大特征值。
根据陈琳(2011)对M3的解释,其取值越大,说明代际流动性越大;反之,代际流动性就越小。
2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2015年的五轮(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和2015年)调查数据。
该数据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对中国各省份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每隔一年或者两年(大部分是一年)进行一次调查,调查的密度大、范围广。
这套数据的综合性、连续性和全国性适合进行教育代际流动的研究。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首先,父母代的受教育程度是指父母中受教育程度的最高值,子代既包括儿子也包括女儿;其次,在所有的个体中,删除学生等未完成教育者;再次,选取信息完整的父子两代人;最后,根据以往文献对教育层次的分类和教育年限的设定,把各调查年份的教育层次统一划分为:
没有受过教育(包括不识字和私塾)、小学、初中、高中(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校和中专)、大专(不包括成人大专)、本科及以上(不包括成人本科)这六类,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3、6、9、12、15和16年。
3测算结果分析
3.1基于概率转换矩阵的测算结果
表1至下页表5是使用CGSS(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和2015年)数据库计算的五个概率转换矩阵。
通过分析发现,处于主对角线或者主对角线两侧的数据相对较大,而其他位置的数据相对较小,这说明我国整体而言具有显著的教育代际传递特征。
随着我国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教育代际传递将有助于维持我国整体的教育素质。
另外,父代教育是影响教育代际流动方向的主要因素之一。
父代教育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小,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反之,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而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小。
本文使用概率转换系数(M1、M2和M3)来描绘教育代际流动的变动趋势。
首先计算概率转换系数M1,也就是父代、子代教育一致的概率。
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国民受教育水平总体得到提升,今天的大学文凭可能只相当于昨天的高中文凭,所以考虑到这一点,计算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处于父母受教育水平上下一级之内的可能性大小。
通过计算得到M1的数值:
328.00、324.85、312.65、294.53、291.21。
从趋势上看,M1的数值缓慢下降,说明近年来我国教育代际流动性是缓慢提高的。
其次,M2的取值分别为:
3.09、3.29、3.36、3.62、3.74。
M2的数值总体上呈现缓慢递增趋势,这同样意味着教育代际流动性是缓慢增加的。
最后计算每一个概率转换矩阵的特征值,然后选择第二大的特征值,最后用1减去这一特征值(如前文所述M1=|1-λ2|),得到的结果分别为:
0.54、0.58、0.62、0.69、0.74。
该数值的总体趋势也是缓慢递增的,这也意味着教育流动性存在缓慢递增的趋势。
3.2基于教育代际弹性的测算结果
表6是根据代际弹性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
通过分析发现:
第一,父母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程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子女在最终教育成就上具有优势,父代的教育成就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导致教育的代际传递现象。
随着我国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代际传递将有助于维持国民整体教育素质。
然而,教育具有提高社会流动的作用,能够促进社会底层人群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当教育成为社会优势阶层为其子代谋求更多教育机会的手段时,则会出现教育的代际传递、社会地位的代际沿袭和阶层固化。
第二,随着时间推移,我国的教育代际弹性出现了缓慢下降,这意味着我国社会的教育代际流动程度不断增强,有利于农村家庭的子女突破其父母教育水平低下的劣势,通过自身努力实现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的提升。
第三,除了父母教育水平外,父母的政治资本(是否为党员)和职业(是否为农民)也对子女的教育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另外,性别变量也是显著的,说明我国的教育代际传递存在着性别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家庭中,父母一般对男孩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女孩,因此相对于女孩,父母可能更倾向于让男孩接受更高层次教育,而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动力不足。
3.3中国教育代际流动趋势性的原因分析
由前文的实证分析可知,中国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在近年来呈现缓慢增加的趋势,这与中国实施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从2001年起,国家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到2012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了4%,并于2016年达到了38866亿元,比上年增长7.57%。
教育财政支出能够显著降低父代教育、家庭城乡背景对子女升学的影响,从而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性[11]。
在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向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投入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第二,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迅速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时代。
2016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42.7%。
高等教育的扩张缩小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并且优化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对高等教育机会相对偏少的地区增加了供给,原本高等教育较发达的地区则增加较少,进而使整个教育机会供给和教育机会需求更加匹配,促进了教育公平,从而提高了社会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第三,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IEFR-HS)的统计数据,家庭教育投入的总量和所占比重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特征,反映了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的教育水平,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3.4教育代际流动的国际比较
下页表7列举了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代际弹性,选取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和挪威等教育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
通过分析发现:
教育代际流动状况在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性。
教育代际流动程度较高的国家有瑞典、挪威等,而教育代际流动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有美国、英国等;并且同一国家在不同年代的教育代际流动存在差异性,例如,美国和法国的教育代际流动呈现逐渐减弱趋势。
结合前文对中国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测算结果,中国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虽然低于瑞典、挪威等国家,但是处于国际中等水平的位置上,说明中国在教育领域及相关领域实施的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比较世界各国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状况,能够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会对教育代际流动性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如,丹麦、芬兰、挪威等北欧国家对贫困和偏远地区的教育投入比例相对更高,这种教育投入体制使得这些国家具有较高的教育代际流动性;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教育代际流动性会发生变化。
例如,美国和法国的教育代际流动呈现逐渐减弱趋势;第三,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教育的公平性和收入的公平性。
教育是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改善有利于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收入差距的改善。
例如,教育代际流动性较高的北欧国家有着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格局。
4结论
本文基于测算代际流动的概率转换矩阵法和代际弹性法,使用历次CGSS数据库对中国教育代际流动性的现状与趋势性进行实证研究,并就教育代际流动性进行国际比较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无论使用概率转换矩阵还是教育代际弹性法,中国教育均存在显著的代际流动性,父母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程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折射出社会阶层固化的特征;而且从趋势上看,中国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呈现出缓慢增加的趋势。
教育代际流动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社会正常流动的重要保障,一定程度的教育代际流动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
另外,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处于国际中等水平的位置上,说明中国在教育领域及相关领域实施的改革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参考文献:
[1]PlugE.EstimatingtheEffectofMother’sSchoolingonChildren’sSchoolingUsingaSampleofAdoptee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4,94
(1).
[2]CurrieJ,MorettiE.Mother’sEducationandthe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HumanCapital:
EvidenceFromCollegeOpenings[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2003,118(4).
[3]AkbulutM,KuglerAD.Inter-generationalTransmissionofHealthStatusintheU.SAmongNativesandImmigrants[R].IZADiscussionPaper,2007.
[4]RoyerH.SeparatedatGirth:
USTwinEstimatesoftheEffectsofBirthWeight[J].AmericanEconomicJournal,2009,
(1).
[5]RestucciaD,UrrutiaC.IntergenerationalPersistenceofEarnings:
TheRoleofEarlyandCollegeEducation[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4,94(5).
[6]ChecchiD,FiorioCV,LeonardiM.IntergenerationalPersistenceinEducationalAttainmentinItaly[R].IZADiscussionPaper,2008.
[7]HolmlundH,LindahlM,PlugE.TheCausalEffectofParents’SchoolingonChildren’sSchooling:
AComparisonofEstimationMethods[J].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2001,49(3).
[8]ChusseauN,HellierJ.Education,IntergenerationalMobilityandInequality[R].ECINEQWorkingPaper,2012.
[9]孙永强,颜燕.我国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10]马骍.教育代际流动的民族差异[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
[11]魏晓艳.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谁是“学二代”?
[J].中国经济问题,2017,(6).
[12]刘楠楠,段义德.财政支出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J].财经科学,2017,(9).
作者简介:
李修彪(1985—),男,山东日照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学;黄乾(1972—),男,湖北仙桃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