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邻三法.docx
《摩邻三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摩邻三法.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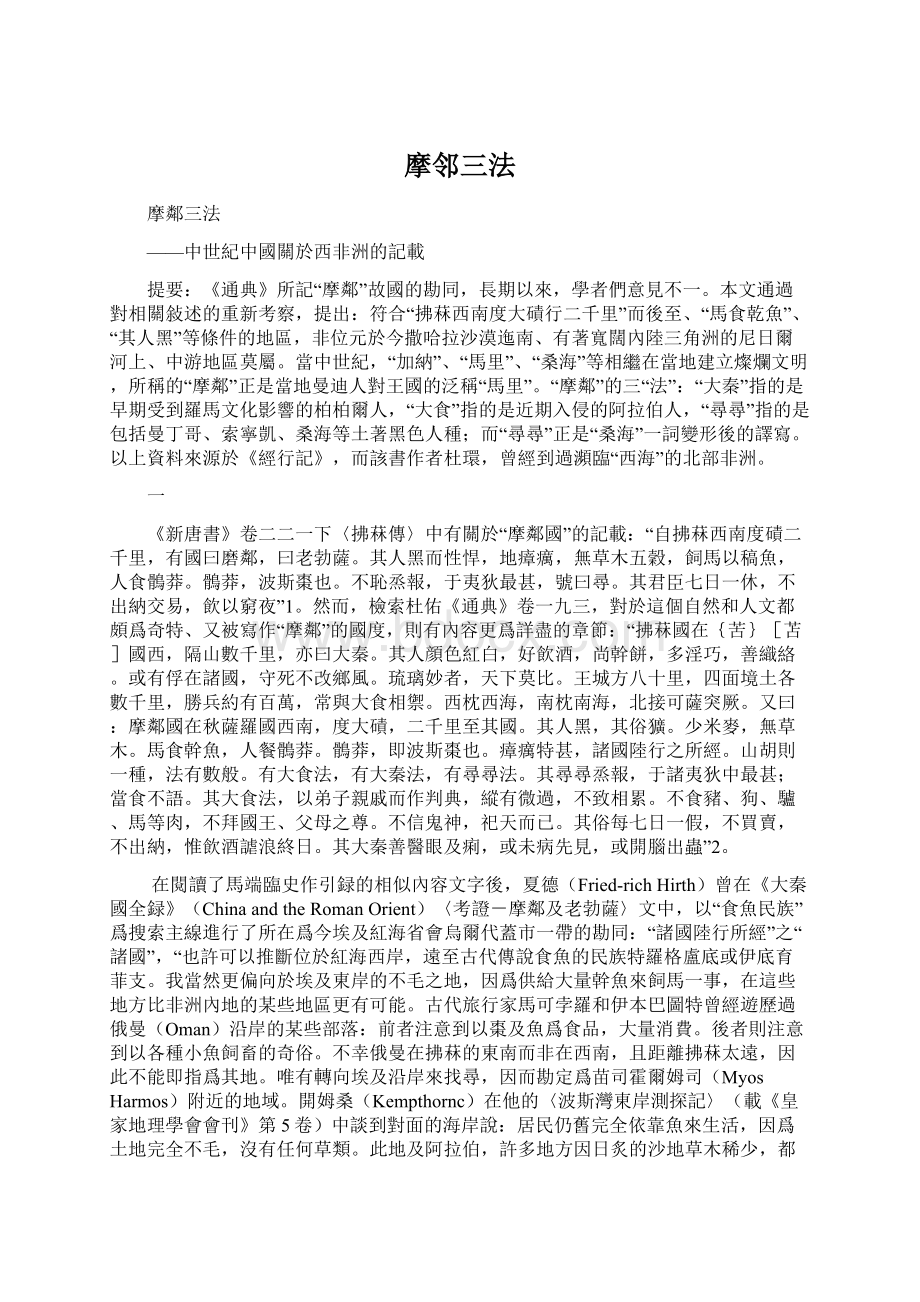
摩邻三法
摩鄰三法
——中世紀中國關於西非洲的記載
提要:
《通典》所記“摩鄰”故國的勘同,長期以來,學者們意見不一。
本文通過對相關敍述的重新考察,提出:
符合“拂菻西南度大磧行二千里”而後至、“馬食乾魚”、“其人黑”等條件的地區,非位元於今撒哈拉沙漠迤南、有著寬闊內陸三角洲的尼日爾河上、中游地區莫屬。
當中世紀,“加納”、“馬里”、“桑海”等相繼在當地建立燦爛文明,所稱的“摩鄰”正是當地曼迪人對王國的泛稱“馬里”。
“摩鄰”的三“法”:
“大秦”指的是早期受到羅馬文化影響的柏柏爾人,“大食”指的是近期入侵的阿拉伯人,“尋尋”指的是包括曼丁哥、索寧凱、桑海等土著黑色人種;而“尋尋”正是“桑海”一詞變形後的譯寫。
以上資料來源於《經行記》,而該書作者杜環,曾經到過瀕臨“西海”的北部非洲。
一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拂菻傳〉中有關於“摩鄰國”的記載:
“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
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癘,無草木五穀,飼馬以稿魚,人食鶻莽。
鶻莽,波斯棗也。
不恥烝報,于夷狄最甚,號曰尋。
其君臣七日一休,不出納交易,飲以窮夜”1。
然而,檢索杜佑《通典》卷一九三,對於這個自然和人文都頗爲奇特、又被寫作“摩鄰”的國度,則有內容更爲詳盡的章節:
“拂菻國在{苦}[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
其人顔色紅白,好飲酒,尚幹餅,多淫巧,善織絡。
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
琉璃妙者,天下莫比。
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
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
又曰:
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度大磧,二千里至其國。
其人黑,其俗獷。
少米麥,無草木。
馬食幹魚,人餐鶻莽。
鶻莽,即波斯棗也。
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
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
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
其尋尋烝報,于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
其大食法,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致相累。
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
不信鬼神,祀天而已。
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惟飲酒謔浪終日。
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2。
在閱讀了馬端臨史作引録的相似內容文字後,夏德(Fried-richHirth)曾在《大秦國全録》(ChinaandtheRomanOrient)〈考證-摩鄰及老勃薩〉文中,以“食魚民族”爲搜索主線進行了所在爲今埃及紅海省會烏爾代蓋市一帶的勘同:
“諸國陸行所經”之“諸國”,“也許可以推斷位於紅海西岸,遠至古代傳說食魚的民族特羅格盧底或伊底育菲支。
我當然更偏向於埃及東岸的不毛之地,因爲供給大量幹魚來飼馬一事,在這些地方比非洲內地的某些地區更有可能。
古代旅行家馬可孛羅和伊本巴圖特曾經遊歷過俄曼(Oman)沿岸的某些部落:
前者注意到以棗及魚爲食品,大量消費。
後者則注意到以各種小魚飼畜的奇俗。
不幸俄曼在拂菻的東南而非在西南,且距離拂菻太遠,因此不能即指爲其地。
唯有轉向埃及沿岸來找尋,因而勘定爲苗司霍爾姆司(MyosHarmos)附近的地域。
開姆桑(Kempthornc)在他的〈波斯灣東岸測探記〉(載《皇家地理學會會刊》第5卷)中談到對面的海岸說:
居民仍舊完全依靠魚來生活,因爲土地完全不毛,沒有任何草類。
此地及阿拉伯,許多地方因日炙的沙地草木稀少,都完全以幹魚和棗混雜而飼畜”。
至於所涉相關專名:
“秧薩羅國”,“或即耶路撒冷的對音”,而“拂菻西南之磧”,“無疑是這指西奈(Sinai)半島的沙漠而言”3。
已故張星烺先生,又曾在其《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第二編〈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的註文中提出了一項論證更爲嚴密的新說4:
“秋薩羅即‘Castilia’(卡斯提利亞)譯音,西班牙[中部]之古名也。
摩鄰,即‘MaghribelAksa’首一字之譯音。
此三字爲阿拉伯文,其義猶今人所稱之泰西,蓋其地爲奉回教者最西之地也。
又簡稱麻格力伯(馬格里布),宋代稱木蘭皮,即今摩洛哥”。
“《新唐書》所記可與《通典》互相參證,蓋秋薩羅亦古羅馬之一部也。
其爲今西班牙,毫無疑義。
《新唐書》與《通典》並似取材于杜環《經行記》,原文或即以秋薩羅爲拂菻之一部,故歐陽修等修書時,不稱在秋薩羅西南,而曰在拂菻南也。
拂菻之指羅馬帝國全境,不僅東羅馬一隅,此方亦可爲諸證據中之一端也。
老勃薩之名,不見杜佑記載,或爲其所刪也。
根據白洛克爾曼(C.Brockelmann)《回教古今史》(DerIslamvonSeinenAnfangenbiszurGegenwart)附圖,阿拉伯人稱摩洛哥以東之地方,自西經二度至東經五度,皆爲‘Tlemssen’。
西經二度、北緯三十五度,有城亦同名。
今代地圖有譯作特林森者,實則此字讀音應作脫勒姆森(特累姆森)。
老勃薩爲其之訛音,可無庸疑。
磨鄰與之並列,皆在拂菻西南,可知兩地必相鄰。
讀音與事實,皆相符矣”5。
逐一核對相關記載,不難發現:
以上兩種意見于行文都不能完全符合。
夏德的主張:
基礎雖在於“供給大量幹魚來飼馬一事”,而“秧薩羅國或即耶路撒冷的對音”、“自拂菻西南度磧之磧無疑是指西奈半島的沙漠而言”,實爲其論點的主要支撐。
可是,在這位學者所引《文獻通考》卷三三九的相關引文中,此國名乃“秋薩羅”而非“秧薩羅”6。
而西奈半島,據侯賽因·凱法菲等《埃及》附易蔔拉欣·艾敏·加利《埃及西奈的土地和居民》,總面積才四萬餘方公里;所稱“沙漠”,其實是“紅色、深灰色和綠色的砂岩構成的大的高地平原”7。
張星烺的主張:
以今西班牙爲“秋薩羅”,今突尼斯、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北部爲“磨鄰”,今阿爾及利亞同名省會特萊姆森市爲“老勃薩”。
從西班牙到馬格里布諸國,中間只有“大海”而沒有“大磧”;所行方向,除今拉巴特市西南一隅外,皆南或東南。
馬格里布諸國,儘管沿海盛産海洋魚,但遼闊的內陸縱深部份則不然。
特萊姆森城,曾經是入侵伊比利亞半島南部安達魯西亞的哈里發將領塔里克的駐地8。
不過,就其在歷史上曾爲著名的都會而言,據亨利·康崩(HenriCambon)《摩洛哥史》(HistoireduMaroc)第一部份《古代摩洛哥》第二章《阿拉伯人的入侵》,蓋在十三世紀當地建立了同名王國以後9。
註釋:
1 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一九七五年,頁6261。
2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萬有文庫》《十通》本,一九八四年,頁1041下。
3 北京,商務印書館朱傑勤中譯本,1964年,頁81、82。
4 又,戴聞達(J.L.Duyendak)《中國人對非洲的發現》(China'sDiscoveryofAfrica),北京,商務印書館胡國强、覃錦顯中譯本,一九八三年,頁15:
“《新唐書》還有一短條關於另一個非洲地方的記載:
就我所知該地在者一點上還未引起人們的注意,該地叫磨鄰(Malin),也就是米鄰達(馬林迪,Malindi)”。
至於作此勘同的原因,作者沒有涉及。
5 北京,中華書局朱傑勤校訂本,一九七七年,頁9、10。
6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萬有文庫》《十通》本,一九八四年,頁2659中。
7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黃運發、朱威烈譯編本,一九八三年,頁143。
8 《阿拉伯馬格里布史》第一卷第二章〈阿拉伯人對馬格里布的征服〉,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一九七五年,頁299。
9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一九七五年,頁30。
二
從前引相關記載,可知“磨鄰國”或“摩鄰國”有以下的主要特徵:
方位,在“拂菻”或其一部“秋薩羅國”的西南方,穿越“大磧”始能抵達;而其間距離,或途程總爲“二千里”、或過“大磧”後再“二千里”。
氣候,炎熱乾燥,即所謂“瘴癘”和“少米麥,無草木”、主食“鶻莽”亦“波斯棗”10。
地形,瀕海或傍河、湖,因爲只有符合這條才有可能“飼馬以稿魚”。
文化,兼有“大食”即阿拉伯、“大秦”即羅馬、“尋尋”即當地習俗的特點。
符合上述條件的所在地方,應該非今非洲西部尼日爾河上、中游地區莫屬:
這一地區,位元處阿非利加大陸內部。
年平均氣溫攝氏三十度以上,絕對最高溫度可達攝氏四十度以上。
年降雨量從西南向東北自一千三百毫米至二十毫米遞減,而年降雨量不足五百毫米的地區占總面積的大部份。
尼日爾河橫貫東西,在支流巴尼河彙入處形成盛産淡水魚類的內陸三角洲11。
就當時情況來說,這一地區正是上古時期受到羅馬文化影響、中古時期又滲入阿拉伯文化內容而同時保持本地文化的地區。
該地區居民,據顧章義先生〈非洲民族的由來與變遷〉一文:
曼丁哥、索甯凱、蘇蘇、古爾馬、莫西、桑海、豪薩等族爲“尼格羅”亦黑色人種,而弗拉尼、圖阿雷格、富爾貝等族爲膚色較淺的“歐羅巴”亦白色人種12。
當十世紀前、後,今尼日爾、馬里兩國的尼日爾河的中、上游地區,曾經存在過有著燦爛文明歷史的加納、馬里、桑海等三個王國。
費奇(J.D.Fage)《西非簡史》(AHistoryofWestAfrica)第一章〈起源〉:
“在九世紀時,雅各比不僅知道加納(Ghana),它有一位强有力的國王,他屬下還有其他一些國王,他們的領土內部都有黃金,而且還知道考考(Kawkaw)、加涅姆(Kanem)和馬勒爾(Maler)王國。
很難肯定所說的‘馬勒爾’是什麽意義,雖然這一定是尼日爾河上游通常叫作馬里(Mali)的那個曼迪人王國的字音轉訛。
考考通常被認爲是桑海王國首都的名稱,它的地點起初在庫基亞(Kukia),在尼日爾河中游一個島上,在現今提拉貝里(Tillaberi)上游大約一百二十哩”13。
這個肇國初期幅員不過今巴馬科市東南三百餘里之康加巴(Kangaba)及附近地區的“馬勒爾”亦“馬里”王國,在松迪亞塔亦馬里賈塔在位的時候、即西元1230—1255年間開始强大。
茲後,貝莉埃(G.G.Beslier)《塞內加爾》(LeSenegal)第一編〈黑人帝國與歐洲的滲透〉第一章〈人口繁殖和成群移居〉:
“到了十四世紀,邊界擴張到東面的加奧、南面赤道線上的森林地帶。
由於被征服的地方有許多金礦,曼丁哥(曼迪)族的國王就住在尼亞尼(今錫吉里)”14。
“加納”王國由來已久,恩諾·博伊歇爾特(EnoBeuchelt)《馬里》(Mali)〈歷史〉:
“根據傳說,西元622年前有過二十二名統治者,其後又有二十二名統治者。
八世紀末,在卡亞馬加西薩率領下,瓦加杜古帝國的索寧凱人佔領加納,此後把本帝國幾乎擴大到大西洋、塞內加爾河、包累河和尼日爾河上游地區”。
“在尼日爾河上游的東北,約在東經八度和北緯十五度的交點上,自三世紀以來就有一個柏柏爾人的國家,它的首邑加納的遺址可以在今日的庫姆比薩萊赫(Koumbi-Saleh)附近找到。
八世紀末,黑種的索寧凱人從南部入侵這個地區,奪取了政權,並在多次反復的戰爭中擴張統治,西達海邊,東至尼日爾河,南抵塞內加爾河和包累河”15。
“加納”王國的居民成份,十分繁雜,而稍晚時候,又多伊斯蘭教的信徒。
瓦德(W.E.F.Ward)《加納史》(AHistoryofGhana)第一章〈人口和史前史〉:
“當時加納是西蘇丹的一個大帝國,既有黑人民族,也有倍倍爾族,而且已經達到了高度的文化。
加納帝國在最盛時期統治奧多哈斯特的倍倍爾邦,這個邦佔據了通過沙漠同回族(伊斯蘭教民)的兩岸王國接壤的西部商路。
在尼日爾河以南,有一連串較小的黑人土邦,他們占住了尼日爾河和森林之間的草地;這些土邦有時也服膺加納帝國的統治”16。
“考考”亦“桑海”王國的最爲輝煌時期,乃在十四世紀掙脫“馬里”君主的控制以後。
不過,早在七世紀,其就已有過卓越的聲望和輝煌的基業。
埃德蒙·塞雷(EdmondSeredeRivieres)《尼日爾史》(HistoireduNiger)第二部份〈古代尼日爾〉第四章〈桑海人的疆域〉:
“第一個王朝迪亞的創建者,也是首先把許多散漫無組織的桑海家族集結起來的人,可能是一個從也門來的外國遊牧民,也可能是一個柏柏爾族的朗塔人,這大約是在西元690年;正是這個人建成了桑海人的第一個大城市庫基亞。
在十世紀,它的君主和奧達古斯特的酋長取得聯繫,他甚至和遙遠的瓦格拉和埃及也有聯繫。
第十五代國王迪亞科索伊是第一位改信伊斯蘭教的人,他將國都遷到了加奧(Gao)”17。
這個曾經稱雄于西部非洲古國的版圖,東南面曾經到達今布基納法索(上沃爾特)的東部和貝寧(達荷美)的西北部。
威廉·菲舍爾(WilhelmFischer)《上沃爾特》(Ober-Volta)〈歷史〉:
“桑雷(桑海)帝國把歷史事件重點放到加奧,並對東沃爾特地區進行了擴張”18。
羅貝爾·科納萬(RobertCornevin)《達荷美史》(HistoireduDahomey)第一部分〈祖先時代的達荷美各族居民與諸王國〉第二章〈各族居民〉:
“這個古爾馬人整體,至少在它的東部受到了桑海人的侵犯”19。
註釋:
10 “波斯棗”,稍晚流傳至廣東、福建、四川。
釋義楚《釋氏六帖》卷一八〈草木果實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刊本,1990年,頁383:
“《百一羯摩四》云:
西土之樹,形如此方棕櫚,獨生,其將至北方。
番禺有果如幹柿,號波斯棗”。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七〈金果〉,北京,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重印斷句本,1980年,頁331:
“成都府江瀆廟前,有樹六株,無他柯幹,頂上才生枝葉,若棕櫚狀。
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
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採摘。
泉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即四川金果也。
番中名爲苦魯麻,蓋鳳尾蕉也”。
11 當地所産的魚幹甚至遠銷到今科特迪瓦的一些地區;博·奧(B.Holas)《象牙海岸》(LaCoted’Ivoire)〈居民〉,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軍中譯本,1974年,頁28、40:
“丹人由於物質條件差,不得不適應山區避難的生活方式。
他們寧願在高山上種水稻和大面積種植柯拉樹,以便通過迪烏拉商人用柯拉果換取尼日爾的魚幹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阿肯人的黃金用途很廣:
首先用作酋長們的華麗飾品,其次可以作家族的藏金和王國國庫基金,最後作爲必需的貿易的貨幣,以購買蘇丹的羊毛製品、尼日爾的幹魚和後來的進口糧食”。
12 載《非洲史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刊本,1982年,頁96、97、100。
13 上海人民出版社於珺中譯本,1977年,頁8、9。
14 上海人民出版社伍協力等中譯本,1976年,頁17、18。
15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76年,頁34、51。
16 北京,商務印書館彭家禮中譯本,1972年,頁56。
17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76年,頁106。
18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77年,頁89。
19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76年,頁49。
三
《新唐書》所記“號曰尋”之“尋”,當如《通典》“有尋尋法”之作“尋尋”。
“尋尋”,與“桑海”一詞的衍生詞“SonghaiTye”、即“桑海人”音近。
“桑海”一詞,據《尼日爾史》第一部分〈自然概況和種族起源〉第二章〈民族〉:
最早出現在約作於西元1510年的《費希塔史》一書中,做“Songhai”,阿拉伯語作“Songnei”。
它最初是個地域名稱,後來引申才變爲民族名稱。
“一開始,桑海人就分爲漁民(索爾科人)和定居務農者(加加比人)”。
“桑海語本身表明,它含有大量的外來語,如阿拉伯語、柏柏爾語和豪薩語”20。
豪薩語,是毗近亦棲息在今尼日利亞西南部地區別一黑色人種豪薩人使用的語言。
不僅“桑海人”,就是屬於“柏柏爾人”的“圖阿雷格人”,據《塞內加爾》第一章〈人口的繁殖和成群移居〉,“是穆斯林,操阿拉伯語、塔爾吉語(Targui,複數即Touareg)和桑海語”21。
由此,無論當地的“黑色人種”、“白色人種”,都有多種文化影響的反映。
所稱“大秦法”,指曾在羅馬帝國治下的“柏柏爾人”舊俗;“尋尋法”,指定居當地的“桑海人”俗;而“大食法”,則指最近從東北方向進入的伊斯蘭宗教文化。
關於這後者,《上沃爾特》〈宗教力量和意識形態〉:
“儘管伊斯蘭教起源於國外,但它尋找進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途徑,要早至八世紀”22。
“磨鄰”或“摩鄰”,應該是“馬里”一詞的譯音。
不過,它不一定實指當時存在的“馬勒爾”王國。
當七、八世紀之際,據前文所涉:
在同一地區內稱霸的是“加納”和“桑海”。
這二個王國一東一西佔據著今尼日爾河的上、中游。
而就相關文字的地理描述來看,尤以“桑海”爲貼切,因爲它佔據著水産最爲豐富的內陸三角洲。
而“馬里”一詞,其原來意思仿佛與當地統治者的稱號有關。
《西非簡史》第二章〈西蘇丹和中蘇丹的大國〉:
“它的含義不過是主子或者國王居住的地方,因此是政治權力的中心,並引伸爲由那裏統治的地方。
阿拉伯的資料和當地的傳說中都有證據可以說明:
這一帶所有曼迪人的王國都能稱之爲馬里”23。
也就是說:
無論是當時已在“索寧凱人”治下的“加納”,還是仍在“桑海人”掌握中的“桑海”,在該地區的主要居民“曼迪人”都把他們泛稱作“馬里”。
除外,儘管後二者的語言,據葛公尚〈非洲各族的今昔〉一文,分屬“尼羅-撒哈拉語系桑海語族”、“尼日爾-科爾多凡語系曼德語族”24;但是,由於所處方位元相近,他們的語言仍能找到相似的地方;如《馬里》〈居民〉所提到的語序主語―賓語―謂語、單音節詞幹輔音在首母音在尾等25。
至於借用若干辭彙,自然很普通。
正是這樣,“桑海”成了“馬里”、“摩鄰”。
關於“老勃薩”,伊本·胡爾達茲比赫《道里邦國記》〈西方的情形〉提到:
“哈瓦利吉派的素福利統治的地方,有代爾阿(Dar’a),它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有很多人口,有銀礦。
它的南方可通往老勃薩國(BiladAl-Habshah)及稱作錐茲(Ziz)的城市”26。
“代爾阿”,應該就是伊斯蘭教哈瓦利吉派建立的羅斯圖姆王朝首都、今阿爾及利亞同名省會提阿雷特(Tiaret)市。
所稱的“老勃薩國”,可能是橫貫非洲大陸北中部,從印度洋岸、今索馬利亞的哈豐角到大西洋岸、今塞內加爾的佛得角整個黑人棲息區的泛稱。
艾卜·法爾吉·古達瑪《本賈法爾稅冊及其編寫》第三章〈關於文明大地所臨諸海之位置〉:
“這個海(紅海)有個海灣,此海灣起自老勃薩(Al-Habshah)地面,延伸到柏柏爾方面,故稱之爲柏柏爾海灣(KhalijAl-Barbari),海灣長爲五百密勒。
另一個海灣經過一個叫艾義拉的城市,從海灣的起點到這城市,全長一千四百密勒。
海灣的終點位於摩鄰(Maghrib,即馬格里布,此詞中譯本借譯並誤,下引同),它同綠海相接觸的部分長二百密勒。
此綠海又以地中海之名爲人所知,只知道它與老勃薩地面的西部邊陲相接;北方乃是摩鄰省的諸群島”27。
必須值出:
在這裏,徑將直布羅陀海峽外的大西洋一部也誤以爲是直布羅陀海峽內的地中海一部。
“大磧”東北的“秋薩羅”,大概是哈里發的官員在馬格利布地區站穩腳跟前、曾經在東羅馬人幫助下順利地進入凱魯萬(Kairouan)城、就任“埃米爾”達四至五年的庫塞拉所統治的領封。
馬塞爾·佩魯東(MarcelPeyrouton)《馬格里布通史》(HistoireGeneraleduMaghreb)第八章〈阿拉伯人進入馬格里布〉:
“在他西進途中,奧克巴擄獲了大批俘虜,包括某些領導柏柏爾人進行抵抗的首領,其中有一個名叫庫塞拉(Koseila)的逃跑了;他隨即加入了拜占庭人和柏柏爾人的聯軍。
庫塞拉在奧雷斯邊境的一次戰鬥中,似乎殺戮過一支阿拉伯的部隊,並親手殺死了奧克巴”28。
再晚,薩阿德·紮格盧勒·阿卜德·哈米德《阿拉伯馬格里布史》第一卷第二章〈阿拉伯人對馬格里布的征服〉:
當西元六八四年,“庫塞拉進入凱魯萬,統治了城裏的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仿佛成了阿非利加的國王”29。
庫塞拉在六八八年失敗以後,“柏柏爾人”又在女王卡希娜率領下起兵反抗哈里發的統治。
一直到七○二年或更晚,今北部非洲的西部地區才真正落入伊斯蘭軍隊的掌握。
正因爲庫塞拉曾與東羅馬結盟對付共同的敵人,其治下的“秋薩羅國”徑被視作“大秦”或“拂菻”的一部分。
而該“國”的南方邊界,也正是綿延數千里、阻隔“摩鄰”文明區域的浩瀚沙漠撒哈拉。
註釋:
20 頁50、51、52、53。
21 頁23、24。
22 頁205。
23 頁45。
24 載《非洲史論文集》,頁114、115。
25 頁73、74。
26 北京,中華書局《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宋峴譯註本,1991年,頁93。
27 北京,中華書局《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宋峴譯註本,1991年,頁244。
28 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74年,頁152。
29 頁235。
四
誠然,由於撒哈拉沙漠的阻隔,使貝寧灣北岸的西非尼日爾河流域與阿特拉斯山北麓的北非地中海沿線的文明發達區間的交往造成了相當的困難。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在上古時期這兩者曾經中斷了相互間的來往。
值得注意的是:
生活在西元前48至前420年間的希臘作家希羅多德(Herodoti),即曾在《歷史》(Historiae)第二卷中提到了極可能是今尼日爾河的那條向東流的“大河”:
“利比亞納撒蒙部落五個青年人,在一片廣大沙漠上進行了許多天之後,終於走到了一個平原。
正當他們採集果子的時候,他們看到一些比普通人要矮小的侏儒走過來;這些侏儒把他們捕獲並給帶走了。
他們被領過了一片沼澤地帶,最後到了一個城鎮。
有一條大河流過這個城鎮,流向是從西到日出的方向,河裏面可以看到鱷魚”30。
而生活在西元23至79年間的羅馬作家老普利尼(PlinytheElder)則在《自然史》(NaturalHistory)第五章中寫道:
“TheriverNiger(Nigri)hasthesamenatureasNile(Nilo).ItProducesreedsandpapyrus,andthesameanimals,anditrisesatthesameseasonsoftheyear.ItssourceisbetweentheEthiopictribesoftheTaraelii(TarraeliosAethiopas)andtheOechalicae;thetownoflatterisMagium”31。
羅馬人所稱的“Aethiopia”、“衣索比亞”,指的是其直接統治下的埃及、努米比亞、毛里塔尼亞等地方迤南的非洲部分。
儘管,他們對這部分大陸的南方極限並不十分清楚;然而,在他們所知道的大陸部分,卻肯定包括了被稱爲“摩爾人”的“柏柏爾人”和棲居於今幾內亞灣北岸的黑人部落先民所棲居的地域。
前一部分人,早在羅馬經營時期即與北方的當地人和征服當局發生了關係。
阿庀安《羅馬史》上卷第八章〈努米底亞事務〉:
“馬略請使團勸菩卡斯一切都服從蘇拉;因此,菩卡斯以募集新兵爲藉口,派遣使者到鄰近的衣索比亞人那裏去(他們的居地從東衣索比亞起,西達馬利泰尼亞的阿特拉斯山);於是,請求馬略派遣蘇拉到他那裏去商量”32。
後一部分人,他們的血緣遺傳甚至滲入到了今天生活在幾內亞北岸多哥的土著部落人中。
羅貝萬·科納萬(RobertCornevin)《多哥史》(HistoireduTogo)第二章〈多哥居民的繁衍〉提到:
“德國人弗羅貝尼多斯認爲多哥土著都自稱爲帕科克帕(單數爲庫帕)。
他認爲他們的體態與洛索人很相似,並指出:
從他們腦殼的形狀可看出古衣索比亞人的特點,他們的臉部有許多蒙古人類似的特點”33。
這些情況充分表明:
當中古時期,撒哈拉沙漠的南北兩端,始終存在著相當頻繁的居民遷移。
正象埃德·阿加依(J.F.AdeAjayi)、米切爾·克勞德(MichaelCrowder)《西非史》(HistoryofWestAfrica)第四章〈1500年前西蘇丹的早期國家〉(TheEarlyStatesoftheWesternSudanto1500)所說:
“TheintroductionofthecamelintotheSahara,atthebeginningoftheChristianera,causedasignificantrevolutioninthedesert.ConstantcommunicationwasmaintainedbetweentheBerbersonbothshoresof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