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docx
《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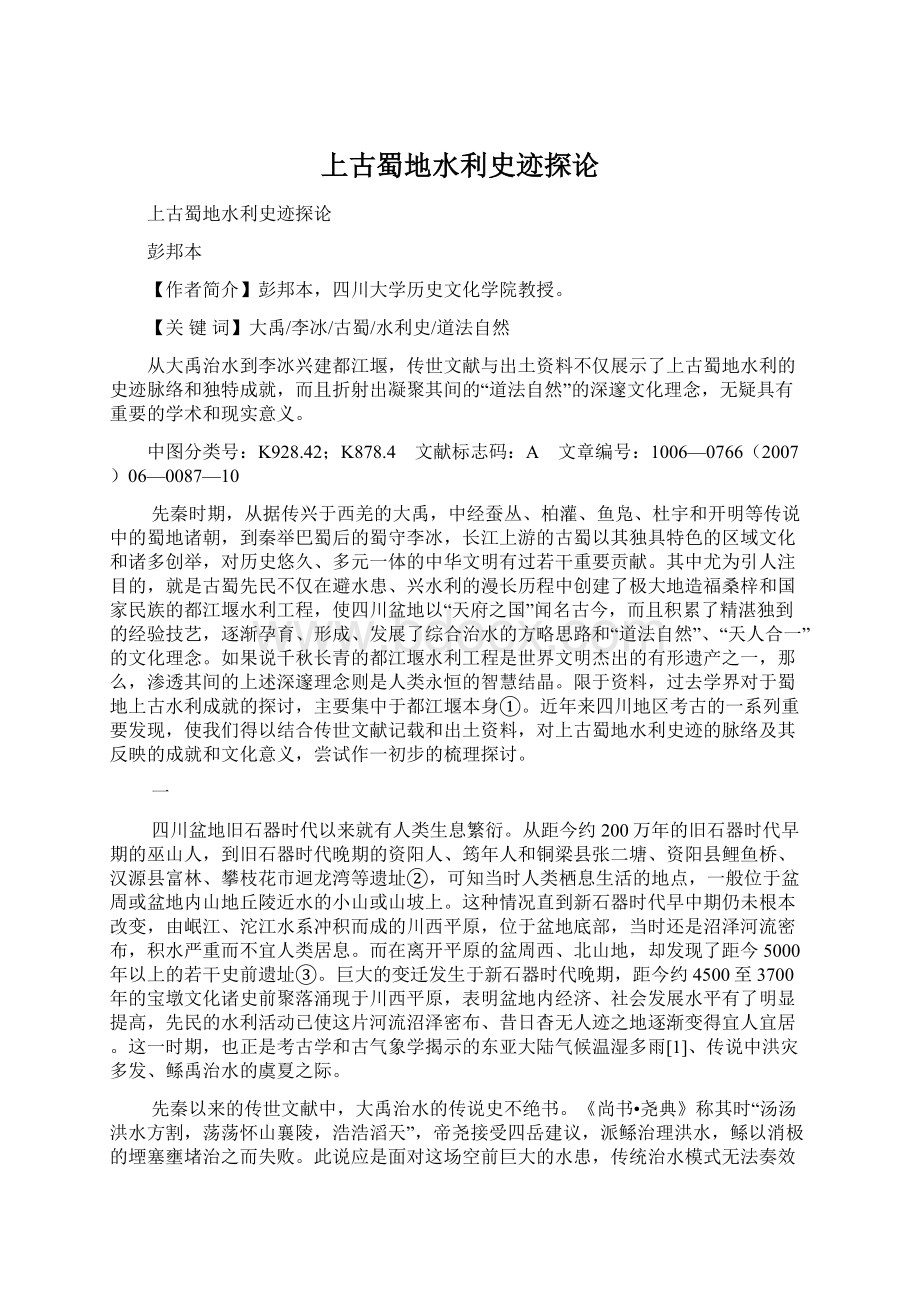
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
上古蜀地水利史迹探论
彭邦本
【作者简介】彭邦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关键词】大禹/李冰/古蜀/水利史/道法自然
从大禹治水到李冰兴建都江堰,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不仅展示了上古蜀地水利的史迹脉络和独特成就,而且折射出凝聚其间的“道法自然”的深邃文化理念,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
K928.42;K878.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2007)06—0087—10
先秦时期,从据传兴于西羌的大禹,中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等传说中的蜀地诸朝,到秦举巴蜀后的蜀守李冰,长江上游的古蜀以其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和诸多创举,对历史悠久、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有过若干重要贡献。
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古蜀先民不仅在避水患、兴水利的漫长历程中创建了极大地造福桑梓和国家民族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四川盆地以“天府之国”闻名古今,而且积累了精湛独到的经验技艺,逐渐孕育、形成、发展了综合治水的方略思路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
如果说千秋长青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世界文明杰出的有形遗产之一,那么,渗透其间的上述深邃理念则是人类永恒的智慧结晶。
限于资料,过去学界对于蜀地上古水利成就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都江堰本身①。
近年来四川地区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使我们得以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对上古蜀地水利史迹的脉络及其反映的成就和文化意义,尝试作一初步的梳理探讨。
一
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有人类生息繁衍。
从距今约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巫山人,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资阳人、筠年人和铜梁县张二塘、资阳县鲤鱼桥、汉源县富林、攀枝花市迴龙湾等遗址②,可知当时人类栖息生活的地点,一般位于盆周或盆地内山地丘陵近水的小山或山坡上。
这种情况直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仍未根本改变,由岷江、沱江水系冲积而成的川西平原,位于盆地底部,当时还是沼泽河流密布,积水严重而不宜人类居息。
而在离开平原的盆周西、北山地,却发现了距今5000年以上的若干史前遗址③。
巨大的变迁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至3700年的宝墩文化诸史前聚落涌现于川西平原,表明盆地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先民的水利活动已使这片河流沼泽密布、昔日杳无人迹之地逐渐变得宜人宜居。
这一时期,也正是考古学和古气象学揭示的东亚大陆气候温湿多雨[1]、传说中洪灾多发、鲧禹治水的虞夏之际。
先秦以来的传世文献中,大禹治水的传说史不绝书。
《尚书•尧典》称其时“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帝尧接受四岳建议,派鲧治理洪水,鲧以消极的堙塞壅堵治之而失败。
此说应是面对这场空前巨大的水患,传统治水模式无法奏效的反映。
《尧典》复载帝舜即位后,改命禹治之。
禹汲取教训,采取了新的治水方略,故《尚书•禹贡》云: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最近新发现的西周中期青铜器《
公盨》④,铭文开首即云:
“天令禹敷土,随山浚川。
”说明《禹贡》关于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及其传说,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前就已长期流播、记录成文而广为人知了⑤。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鲧作为领导治水失败的典型,与取得辉煌成功的禹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综合传世和出土资料考察,鲧时既留下失败的教训,也不乏实践的经验乃至建树可供后继者鉴取。
《国语•周语》称共工和鲧相继“壅防百川,堕高湮庳以害天下”,《世本•作篇》则云“鲧作城”,“鲧作郭”[2]。
后者的城郭实即前者的堤防,传说的两面反映的是二而一的史实[3]。
近年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大陆上的古城群,其夯土城垣实际就是与防御水患密切相关的封闭性堤围。
当然,倘进而论之,城垣还有军事防御的功能,而堤防的种类也有多种。
但在社会组织限于规模和水利技术发展水平,尚无力修筑大规模的沿江堤防的史前时代,往往只能围绕聚落建成封闭的堤围亦即夯土城垣以“壅防”水患。
在鲧禹所属的龙山时期,黄河与长江流域广大平原地区不仅已经聚落广布,而且其中比较重要或规模较大者,多已从早期的聚落围壕发展出城垣和壕沟复合体系。
此种情形,不仅由这些冲积平原上的聚落近水濒水的位置和地势所决定,且亦为当时东亚大陆正值温湿气候、水患多发的背景使然。
在川西平原上,与之大体同期的宝墩文化古城群的涌现,显然也与上述背景紧密相关。
此种主要由城垣和壕沟构成的集防洪和军事功能于一体的复合体系模式,在通常年份是基本能够抵御夏秋水患的,但在多年未遇的特大洪水面前却往往难逃灭顶之灾。
宝墩文化古城群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古城,在城垣建造方面为同一技术系统,即其城墙采用地面堆筑(而非黄河流域的开槽版筑)而成,一般在防御水患的功能上显然是有效的。
此期川西地域的古城群不仅在城址的规模和密集程度上展示了不低于域外的发展水平,而且在因地制宜避水患求水利方面亦具特色。
这些古城均顺着古河道流向的水脉和地脉兴建,巧妙地因应了水资源等自然条件。
如年代最早、面积最大(达60余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垣方向45度,与附近的铁溪河流向一致,而其南垣西段外至今尚存的宽约10米的低洼带应为城壕一类人工水道[4,5]。
这样的城址布局和走向,显然有利于避开和减轻水患。
又如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与紫竹等三处古城址都有内外双重城垣[6,7],双垣之间则为兼具防御和给排水功能的壕沟,此种多重复合体系,应具有更强的防洪功能。
温江鱼凫城尤具特色,根据1999年新发现的东城垣,证明其城垣形状呈规则的六边形,城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
该城没有采用通常的矩形城垣,而是因应水流地势而规划营建,可谓颇具匠心。
从建筑技术上看,其城墙发现卵石层与土层相间堆筑结构,显然有加固墙垣的作用。
城址内北部有一大致呈东西向的低洼地带,应为古河道。
而城址东部的河道,印证了东垣绝大部分毁于洪水的推断[8]。
蜀地略当传说中鲧禹时期的上述考古资料反映,古城或曰以封闭的堤围保护的聚落,其单个孤立的“壅防”、“湮塞”,在洪水面前确有明显的被动和局限性。
综合文献传说和出土资料可知,大禹时代的先民既合理继承了前辈筑城或曰堤围作为一般情况下兴利避害基本模式的传统经验,又于大灾之际汲取惨痛教训后,一改此前孤立地看待处置洪水的片面性失误,转以较为宏阔的思路对区域性的水土实施较为综合的治理,并且在继续保护巩固城邑的基础上改以疏导为消除水患的主要新措施。
根据《尚书》以来的文献传说记载,这种比较全面整体的标本兼治,历尽艰辛后终于大见成效。
在《尚书•虞夏书》中,当时“天下”洪水波及的范围甚广,所以《禹贡》反映的大禹治水广及江淮河济。
其间确应有古史传说在流传过程中将不同时间和地区的水患及其治理之史实素材加以“层累”地整合的可能,需要对其传说记载考订辨析。
而与本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禹治水是从何处开始的呢?
若按《禹贡》所云是起自冀州。
但从东周秦汉以来大量文献反映的禹族源流考察,其治水活动可追溯到其早期居息于岷江流域禹羌故地之时。
禹族早期生息于东亚大陆西部高原尤其今四川省岷江上游地区,屡见于文献所载先秦以来的传说和汉晋史籍,如春秋晚期的孔门弟子子夏就对鲁哀公说过“禹学乎西王国”[9],与《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之说同。
《史记•六国年表序•集解》引皇甫谧曰:
“《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当为《孟子》佚文,不见于今本《孟子》。
此外,《史记•六国年表序》亦云:
“禹兴于西羌。
”《新语•术事》、《盐铁论•国病》、焦氏《易林》卷十六、《蜀王本纪》、《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三国志•秦宓传》及其裴注所引皇甫谧《帝王世纪》和谯周《蜀本纪》等,皆有类似记载,并往往明确指出禹生于石纽。
地在西汉时汶山郡广柔县境,大体包括今四川北川、汶川、茂县境及都江堰市和什邡县境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云阳县旧县坪发掘出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碑文明确记载景云为大禹后裔,并云其“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述)禹石纽、汶川之会”⑥。
这一珍贵的新出土文献无疑是上引传世文献之说的重要佐证,可知“禹兴于西羌”作为东周以降广泛流传之说,应有相当的史实依据,因而屡为学界前辈尤其巴蜀学者所认同⑦。
而史前晚期源于远古羌族的大禹族群,必有一西兴东渐、辗转进入黄河中下游之历程[10,11]。
《禹贡》所记当是其迁徙中原以后之事,其疏导河川的卓越举措和整体方略,则应与其昔日始于蜀地的最初水利实践经验密不可分。
而在史传大禹受命领导的这次空前宏大的治水工程中,也包括《禹贡》所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等在蜀地开展的系列水利实践活动,应该就是禹族当初在岷江流域水利活动的史影。
宝墩文化古城群顺水而兴存发展,又遭受过水患严重破坏毁损的情形,既反映了当时气候温湿、洪水频繁的史实背景,又间接揭示了新的治水方略出现的必然性,也反映兴于西羌的大禹治水于蜀中的传说确实蕴涵有古老的史实素地。
《禹贡》所记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长江上游现存最早的治水记载。
岷山绵亘于与川西北邻接的甘青高原,是岷江的发源地,所以由此开始疏导的江,自然就是岷江。
在明朝以前,古书但凡单独称“江”之处,多指长江,并把岷江视为长江之正流。
直到晚明徐霞客通过实地考察,才将长江上游正流更定为金沙江。
所以《禹贡》所述,乃先民对岷江水系的疏导,其中最主要、最艰难的工作,是排泄地势低洼的川西平原积水。
《禹贡》中禹奉中原华夏联盟首领舜之委派着手的这项使命,实际应是宝墩文化中晚期蜀地先民在这方面长期艰巨历程的缩影。
宝墩文化迄今已发现八座古城,它们和陆续发现的若干次级聚落遗址、遗迹,在川西平原上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状遗址群,揭示当时存在着一个与同期中原唐虞集团类似的区域性族群联盟共同体。
由这样一个联盟主导开展夯筑墙垣、疏导河流之类区域性水利活动,在当时已完全可能,宝墩文化古城群夯筑方式的相同以至整个文化面貌的基本一致,即是反映。
该古城群和许多小型聚落遗址,一般都依傍古河道水流营建,说明平原上的积水沼泽已得到初步排泄整治⑧,这应与从岷江上游进入川西平原的禹羌民族支系密切相关。
在唐虞时代,禹族所自出的西羌,是西部的一个人口众多、很有影响的族群,也是古代四川盆地居民的一个主要来源。
羌人世居岷江上游,自古以熟悉水性、长于水工闻名,并由此形成悠久传统,故直到20世纪前期,成都平原上举凡打井、修堤一类工作,往往由羌民承担。
在传说的虞夏之际东亚大陆一些地方空前的洪灾中,川西平原洪水漫衍,积潦严重,须疏通河道以排除积水。
该平原主要由岷江和沱江两大水系冲积而成,从西北向东南微微倾斜,平均坡度约4‰,地面高程从西北端都江堰大约海拔750米左右,逐渐向东南递降至平原另一端金堂县的450米左右。
由于这样的地势,积洪宣泄的自然走势遂大致为由西北而东南。
传说中大禹率众对平原水系的疏导即顺此地势和水势,并由西向东开挖了一条人工河道以泄洪,即《禹贡》所云“东别为沱”。
此“沱”并非上述作为川西平原母亲河之一的沱江,一般认为即自今都江堰西南至成都东南与流江汇合之古郫江,但此水道并非全然人工开凿,应是充分利用了大致东向的自然河道,又在岷、沱水系众多紊杂的自然支派之间间或决口沟通而成。
大禹时代工具尚主要为石、骨、木器,但有限开挖较为疏松的冲积土壤以沟通相近河流支系并非没有可能,因而这条传说记载不宜轻易否定。
此举沟通了岷、沱二江,川西平原水情应大有改善。
而岷、沱水系的上述初步整治,为平原进一步的开发,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这次大规模水利活动,《禹贡》又云:
“华阳、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
绩。
”岷、嶓分别指岷江上游川西北以及川、甘交界处的岷山、嶓冢山,艺指树艺种植。
宋代学者王炎云:
“江汉发源此州。
方江汉之源未涤,水或泛滥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
今既可种艺,知二水之顺治也。
”[12]此说是。
沱指沱江,“沱潜既道”之道,高邮王氏父子指出即导[13],亦即疏导。
潜水,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引胡渭说,“一在巴郡宕渠县,一在广汉郡葭萌县”[12]。
即今嘉陵江支流渠江,及另一在今广元境内流入嘉陵江的支流。
这是传世文献中嘉陵江流域水利活动的最早记载。
嘉陵江发源于陕南,向南流经四川盆地,至重庆入长江,为长江上游最大支流,其水系包括渠江、涪江等大小诸多支流,是四川盆地的又一条母亲河,历史文化悠久丰富。
上世纪70年代末,重庆市博物馆对嘉陵江中下游初次进行考古调查,就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秦汉的文化遗址11处[14]。
2002年10—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渠江流域调查又发现了20多处先秦(包括新时期)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及石器采集点,并在该流域的宣汉县发掘了“20世纪末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遗存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东周时期。
看来,在治理今四川西部岷、沱流域的同时,大禹时代蜀地先民又对包括今川东、北地区的嘉陵江流域陆续进行疏导,并留下了上述悠久的传说。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
“嵞,会稽山也。
……《虞书》曰:
予娶涂山。
”段玉裁注:
“《皋陶謨》曰:
‘予创若时,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郑注云:
‘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
三宿,而为帝所命治水。
’《水经注》引《吕氏春秋》:
‘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
’”中原文献每将禹娶涂山氏与治水紧密联系。
蜀地现存最早的传世史籍《蜀王本纪》也云:
“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娶妻生子,名启。
”⑨[18]《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更明确:
“禹娶于涂山,……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
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
”该书在江州县(今重庆)下指出,“涂山,有禹王祠与涂后祠”[19]4,30。
《水经•江水注》:
“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庙铭存焉。
常璩、仲雍并言禹娶于此。
”[20]1053涂山地望历来有歧见,但上引《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和《水经注》涂山在四川盆地之说,亦可视为虞夏之时四川盆地治水活动之史影。
看来在大禹时代,蜀地先民就大致对四川盆地主要水系陆续进行过初步的疏导治理。
考察宝墩文化遗址群对水环境的处置遗迹,可知当时的基本治理思路或方略无疑已达到一定的综合水平,否则绝难成功。
成功不仅来自于综合整治的方略,更是这一朴素方略初步所涵的“道法自然”思想的胜利。
《淮南子•原道训》云: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
”“以水为师”,也就是所谓“道法自然”,这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哲学理念。
尽管在产生之初,这一理念还远不如后世系统严密,甚至还不很清晰,但有一点应是清楚的:
它源于先民对水性规律的认识和尊重。
此理念一经出现,必然伴随先民成败交织的一步步实践逐渐丰富深化,并对后世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
而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上游的蜀地,以其历史悠久、因仍自然、因地因水制宜的卓越实践及其经验总结,为这一古老的科学理念的形成完善,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
大禹父子开创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时代——夏朝以后,根据汉晋时期的传世文献,夏商以来,四川盆地曾先后存在过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等几个王朝⑩。
这些朝代及其史事在中原系统的史书中多已失载,但仍以传说为主要形式粗略地保存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古代四川的地方文献系统中。
证以近世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金沙遗址、商业街大型船棺群遗址等考古学资料,这应是先秦时期的五个区域性共主政权,其间既有雄长蜀地之相继关系,复有在共主状态下长期并存之史实[17]。
由于四川地区尤其成都平原河流沼泽众多的地理水文条件,上述诸王朝肯定都曾实施过有组织的甚至大型的水利活动。
蜀地上述诸朝中,除开蚕丛、柏灌二代史载迷茫难以具论外,鱼凫氏尤其是杜宇氏、开明氏时期的水利活动,在文献传说中已有迹可寻甚至有案可稽,而且在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中得到了相当的印证,使我们得以从中透视蜀地先民继大禹时代之后进一步发展了的水利思路及理念。
如鱼凫氏王朝,按照多数学者的研究意见,广汉三星堆遗址就是其昔日都城所在。
鱼凫即南方常见的鹰勾喙水禽鸬鹚,俗称鱼老鸹,先秦以来即已被驯化为重要的捕鱼手段,而鱼凫氏之名及相关考古与文献资料表明,其早期本为滨水渔猎族群,是夏商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共同体[22,23]。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金杖上精美的鹰勾喙水鸟图案,和三星堆文化遗址中多有发现的鸟头形陶器柄的鸟嘴,都以鹰勾喙为鲜明特征,学者多以为即文献传说中的鱼凫氏王朝神权政治和祖先崇拜的象征遗物。
照此观点,湖北宜昌中堡岛、路家河等长江中上游沿岸遗址所出类似的鸟头形陶器柄等大量资料,以及从鄂西到川东、川南、川西以至成都平原核心地带沿长江、岷江水系分布的若干鱼凫(鱼符、鱼复)地名,应是其族群迁徙、沿途居留建国立邑的历史遗迹[22]。
该族群最后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建立起鼎盛时期号令声威及于整个四川盆地以至汉中、鄂西等一些周边地区的王朝。
以上虽有待进一步的实证依据,但大体可从。
不管怎样,以三星堆古城为政治中心的族群同禹族一样,应也很擅长于水利,可惜因年代久远等原因,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早已经湮没无闻。
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三星堆古城的规划选址和建造布局略加管窥。
滨水建成的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而包括古城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共约12平方公里(11),是夏商时期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早期文明中心之一。
如此巨大的聚落,必须有防洪、供水、排水等全面的规划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不仅气势宏大,而且设计巧妙。
它北临鸭子河,马牧河蜿蜒穿城而过,这样的里外布局,显然有利于解决古城生产、生活以至保持和改善居住环境的用水、排水问题。
这两条河流尤其是鸭子河,只要按照大禹以来的传统,时或加以疏导,就能兼收水运和防洪排潦之效。
古城墙垣颇为宽大坚固,马牧河虽穿墙入城,但其河道不宽,易以人工手段控制水流。
三星堆古城垣始建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商周之际,之所以能够巍然矗立鸭子河畔达数百年之久,定然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措施和有效的水利制度为保证。
滨水跨河而建的城垣与水和谐地融为一体,透露其水利技术与理念意趣,较诸宝墩文化时代显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考古资料揭示,三星堆遗址废弃后,古蜀政治中心转为今成都市区金沙——十二桥遗址一带为中心的大型聚落,由之反映的古蜀历史也迷雾渐消而初显清晰。
而在传说中这时取代了鱼凫氏成为蜀地共主的,是约当晚商西周以至东周早期的杜宇氏王朝。
《蜀王本纪》记载其传说云: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
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
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
化民往往复出。
”大体相同的记载又见于东汉末蜀地学者来敏的《本蜀论》,惟《蜀王本纪》所云“女子名利”者,《本蜀论》作“女子朱利”,并直接称她“自江源出”,而无“井中”二字[20]1045。
江源应指禹羌世居的岷(汶)江上游地区,因而从地望和时间上看,这个神奇的传说蕴涵着一个重要信息:
与水和岷江密切相关的朱利及其族群,应出于自古长于水利的西羌(12)。
而“从天堕”云云,说明杜宇也同样来自西部高地。
相传来自江源一带的杜宇夫妻,将其在成都平原上的都城命名为郫,意即低平之地的都邑,传说就在今天郫县一带,由此建立起蜀地新的共主秩序(13)。
但近年来成都市区十二桥、黄忠小区和金沙等一系列商周之际重要遗址的发掘,揭示这些原本就相互连接为一体、沿古郫江绵延数里的大型聚落遗址,才和强大的杜宇王朝之都相称,而郫县一带至今尚无同期的类似重大发现。
上述包括大型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和大规模滨河祭祀场所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整体上构成一个分区布局合理、功能系统完备的中心都邑,且正好濒临古郫江水系而建。
考古发现揭示的城水亲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这座依水兴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顺应自然的深厚文化意蕴。
从临河矗立长达数百年的史实可以推知,杜宇王朝在水利技术方面也应该有相当高的成就。
十二桥遗址结构复杂、布局讲究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建筑群[20],说明当时的高级贵族住宅或统治机构就建于河滨,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提供平时充分的水利服务和安全支持,统治者是不可能如此布局的。
不过,能提供常年的安全,未必能保证永无忧患,揆之川西平原的地理水文形势,杜宇王朝也应当不止一次遭遇过严峻的水灾挑战。
考古发掘揭示郫江故道旁的上述大规模干栏式建筑群,最终都顺着洪水湍急的流向坍塌,就是当时发生过多年未遇洪灾的确切证据。
这种相隔若干年才可能突发的严重险情,与《蜀王本纪》中杜宇王朝晚期再次遭遇“若尧之洪水”的下述明确记载相合: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
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
望帝以鳖灵为相。
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
”这场洪灾发生的时间约在春秋前、中期,传说最终完成这次极为艰巨的治水使命的,是来自荆楚地区的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鳖灵。
鳖灵因治水成功而受杜宇氏禅让,建立起秦灭巴蜀前的最后一个古蜀王朝——开明氏。
如《蜀王本纪》所述,鳖灵的来历同样充满了神话色彩。
上古英雄或重大历史人物尤其开国之帝王被神化,以证明他拥有过人之处、特别是禀赋有与众不同的神圣资质以替天行道,是神权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的通例。
揆诸史实,鳖灵的到来,当然不会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族群,时间则不晚于春秋前期。
上述整个传说与水尤其密切相关,说明鳖灵一行也是一个水上民族或擅长水利的水滨民族。
应为鳖灵或曰开明氏族群遗物的成都商业街船棺等出土资料也揭示(14),他们死后也要回归船上,可见其文化习尚理念与水的关系何等亲近。
《蜀王本纪》所记鳖灵开凿的“玉山”,《本蜀论》作“巫山”,“巫”、“玉”二字盖因形近而讹,当以“玉”为是。
《华阳国志•蜀志》也记杜宇氏晚期,“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
可见玉山又曰玉垒山。
学者或认为玉垒山乃湔水即今白沙河的发源地,就是今都江堰市与汶川县交界之地茶坪山,应有所据。
但揆诸地理、水势和此山位置,其凿决与否,似难对川西平原水情有决定性影响,故鳖灵所凿“玉山”当别有所指。
《水经•江水注》云:
“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郭景纯所谓玉垒作东别之标者也。
”大禹时代至开明氏时逾千载,当初所凿沟通岷、沱二水系的人工引水河道可能早已淤塞严重甚或湮没,故此条记载,应是继大禹时代之后,开明氏对之再作整治以引岷入沱的反映。
而“作东别之标”的玉垒,就是川西冲积平原东端的泄洪瓶颈沱江金堂峡。
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的平原暴发洪水时,大量积水易汇聚于地势最低的金堂一带,金堂峡狭窄的河道使洪水宣泄不畅,往往导致平原水灾。
因此,鳖灵疏导治理岷沱水系,进而开凿拓宽金堂峡,终于成功地泄洪平患,故《蜀中名胜记》引旧地志云此峡口“相传为鳖灵所凿”[25]。
显然,对岷、沱二江流域从上到下再度疏、凿并举,既抓住了关键,又本末兼治,是大禹时代初具之“综合治理”方略和“道法自然”理念的一脉相承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开明时期的治水,应也经过了相当长久艰巨的曲折历程,非旬日所能奏效。
至于治理成效,当由于工具(尤其金属器的使用)、技术等条件的进步而有了很大提高。
鳖灵或者说开明氏王朝的治水活动,不仅在传世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在考古发现的此期水利遗迹资料中也得到了直接证实。
上世纪80年代,在成都市区指挥街遗址出土了东西向的一排6根柱桩和竹木编拦沙筐等遗迹遗物,时代不晚于春秋前期,应与防洪有关[26]。
在方池街及附近金河宾馆等遗址的发掘中,又发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多条卵石埂,显然是当时延伸于较大范围的同一大型人工水利设施系统的遗迹。
其中方池街遗址的东、中、西三条有规律地分布的卵石埂,整体呈Z字形,颇引人注目。
因地处现代建筑密集的市区,发掘面积受限,其中除中埂分别与东西二埂斜向相接而长约26米外,其余二埂均南北延伸颇长而不见其两端。
发掘者根据“石埂剖面形状大致都呈椭圆形,部分石埂上部被破坏,但下部埂脚埋入地层,仍呈圆弧状,卵石紧紧相挤,体现了使用竹笼的特点”,结合蜀中治水传统及成都抚琴小区商代遗址已有以竹篾固定、保护器物的出土资料等研究后明确指出,这些石埂均用竹笼盛装卵石砌成,是开明氏时期的治水工程遗迹。
具体用途则是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并初步推定其西、中两埂整体上为一倒人字形滚水、支水埂[27]。
从三条石埂的有计划分布,尤其是从其护堤、分水、支水和滚水功能分析,可知其已初具后世都江堰工程内江诸堤功能系统的意蕴,应是东周时期蜀地先民熟谙水性后的智慧体现。
这种在疏导的基础上更加复杂的水利技术设施,既是对大禹以来治水传统的继承,更是富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