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词学理论研究.docx
《古代词学理论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古代词学理论研究.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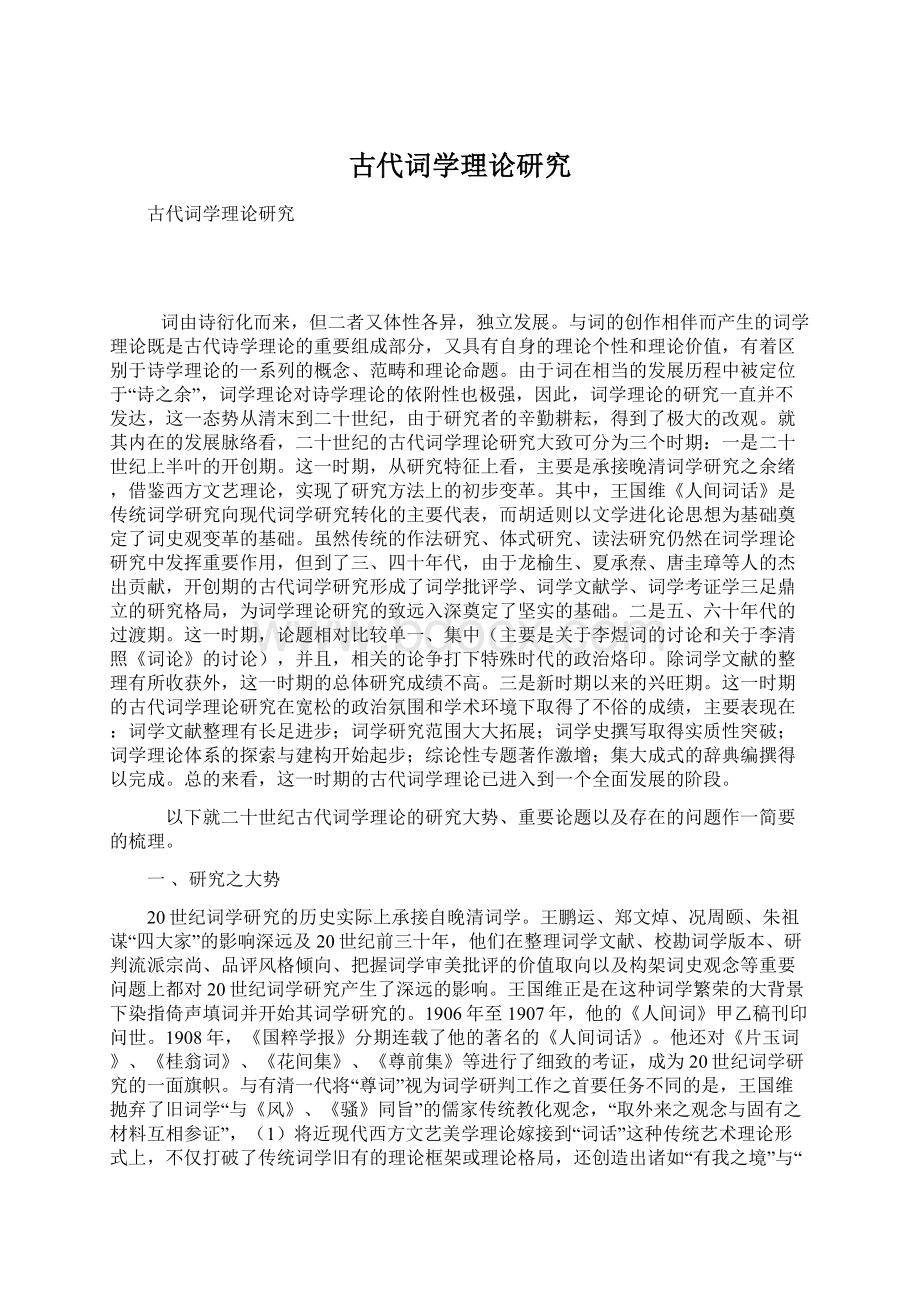
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古代词学理论研究
词由诗衍化而来,但二者又体性各异,独立发展。
与词的创作相伴而产生的词学理论既是古代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的理论个性和理论价值,有着区别于诗学理论的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
由于词在相当的发展历程中被定位于“诗之余”,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极强,因此,词学理论的研究一直并不发达,这一态势从清末到二十世纪,由于研究者的辛勤耕耘,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就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看,二十世纪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开创期。
这一时期,从研究特征上看,主要是承接晚清词学研究之余绪,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初步变革。
其中,王国维《人间词话》是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词学研究转化的主要代表,而胡适则以文学进化论思想为基础奠定了词史观变革的基础。
虽然传统的作法研究、体式研究、读法研究仍然在词学理论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到了三、四十年代,由于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人的杰出贡献,开创期的古代词学研究形成了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为词学理论研究的致远入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五、六十年代的过渡期。
这一时期,论题相对比较单一、集中(主要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和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讨论),并且,相关的论争打下特殊时代的政治烙印。
除词学文献的整理有所收获外,这一时期的总体研究成绩不高。
三是新时期以来的兴旺期。
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研究在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学术环境下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词学文献整理有长足进步;词学研究范围大大拓展;词学史撰写取得实质性突破;词学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开始起步;综论性专题著作激增;集大成式的辞典编撰得以完成。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古代词学理论已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
以下就二十世纪古代词学理论的研究大势、重要论题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一简要的梳理。
一、研究之大势
20世纪词学研究的历史实际上承接自晚清词学。
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四大家”的影响深远及20世纪前三十年,他们在整理词学文献、校勘词学版本、研判流派宗尚、品评风格倾向、把握词学审美批评的价值取向以及构架词史观念等重要问题上都对20世纪词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维正是在这种词学繁荣的大背景下染指倚声填词并开始其词学研究的。
1906年至1907年,他的《人间词》甲乙稿刊印问世。
1908年,《国粹学报》分期连载了他的著名的《人间词话》。
他还对《片玉词》、《桂翁词》、《花间集》、《尊前集》等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与有清一代将“尊词”视为词学研判工作之首要任务不同的是,王国维抛弃了旧词学“与《风》、《骚》同旨”的儒家传统教化观念,“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1)将近现代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嫁接到“词话”这种传统艺术理论形式上,不仅打破了传统词学旧有的理论框架或理论格局,还创造出诸如“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境界”与“无境界”、“主观之诗人”与“客观之诗人”、“造境”与“写境”、“隔”与“不隔”等一系列带有中西方文艺美学合璧色彩的概念或范畴,成为传统词学研究向现代词学研究转化的一个界碑。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同他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口号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的词学研究框架以及对词史的认识,又是同他的进化论文学史观密切相关的。
胡适尝试用古文---白话的消长起伏运动来建构文学史,他在《白话文学史》中将国语文学看成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认为“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并断言“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而白话文学史则是“活文学的历史”。
(2)从这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出发,胡适提出了自己的词史观,认为词经历了“本身”、“替身”和“鬼”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清代词学的复兴在胡适看来只不过是词“鬼”的历史搬演,其虚假繁荣的鬼排场后面却毫无生气。
他还将词本身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对那些缺少活的文学精神和艺术真美而充斥着“烂书袋”、“烂调子”的技术主义与工艺主义的“词匠的词”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总的来看,胡适在词学研究方面,主要是从旧文化批判与新文化建设的宏阔文化眼光出发,通过对文学进化论思想的阐释来实现词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文化哲学的眼光与批评方法不仅把词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科学学术的新阶段,更为后继者在文学学术观念的更新、现代词学研究意识的培养上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前半叶出现的三百多种各类文学史著作,不少著作在安排词史、词学史的时候都明显地接受了胡适的进化论文学史,而在具体的词学研究中,这种影响也清晰可见,如顾敦鍒《笠翁词学》一文就阐发了李笠翁词学的革命性,他说:
“我所以介绍笠翁的词学,不但因为他的学说有历史的价值,也是因他的意见,在文学革命以后的今日,还有指挥新作家的势力”。
(3)
与王国维、胡适等人以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文艺观念或进化论文学史观来讨论词学有别的是,不少研究者仍然以旧式研究方法来研究词学。
如蒋兆兰的《词说》以朱彝尊《词综》、万树《词律》为“词家必备之书”,以婉约为正宗来讨论词论、词法问题。
陈洵的《海绡翁说词》则师尊周、吴,以“严律”、“贵拙”、“贵养”、“内美”为论词之标准。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以论词之作法、体式、读法和研究方法为主的著作,如徐敬修的《词学常识》(上海大东书局,1925年)、刘坡公的《学词百法》(世界书局,1928年)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倾向则是断代词学史研究开始出现,如徐珂的《清代词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即是较早全面研究清代词学的著作。
这本2万多字的专论,引用谭献的评论把清词分为“才人之词”、“学人之词”和“词人之词”三种,并在“派别”一章勾勒了浙西派和常州派两家的发展线索及其影响。
在作者看来,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派词家推崇南宋姜夔、张炎,多在声律字句上用功夫,恪守旧法而较少创新。
与此相对照的是,作者给予常州词派在词史上以极高的地位,认为“自是以还,词学大昌”。
又由于词学理论缺乏系统的论著,评论家的观点、标准等多体现于选本之中,因而,作者深谙此道,特立“选本”一章,对《词综》、《宋四家词》等加以评述,分析了清代词选家们的理论见解。
该著也有不少缺陷,如论词基本上以常州派“意内言外、有厚入间”的理论主张为标准,对常州派常有过誉之词,而对浙西派的评价则有失公允。
如果说20世纪前二十年是现代词学研究的草创期的话,那么,三、四十年代则是中国词学研究的一个高潮期。
这主要表现在:
一、词学研究有了自己的刊物与阵地。
三十年代,龙榆生等人创立的词学专门性刊物《词学季刊》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词学原理性探讨的专著络绎而出。
如夏敬观的《词调溯源》(商务印书馆,1931年)、梁启勋的《词学》(京城印书局,1932年)、吴梅的《词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丘琼荪的《诗赋词曲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胡云翼的《词学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谢无量的《词学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任二北的《词学研究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等,都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
三、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开始形成。
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词史著作,如刘毓盘的《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和《中国词史大纲》(北新书局,1933年)、薛砺若的《宋词通论》(开明书店,1937年)等。
其中,刘毓盘的《词史》代表了词史研究的早期成就,查猛济曾在《刘子庚先生和词学》一文中高度评价说:
“近代词学大概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的,象朱古微、况夔生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象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只有《词史》的作者刘先生能兼顾两方面的长处”。
(4)四、词学文献的校勘或整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唐圭璋于1934年自行出资辑印《词话丛编》,收录词话60种(后又另辑25种重加修订),可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后世。
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解放后辑成)中的梦窗、南唐二主等12家10种年谱,也都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五、词学研究格局的基本形成。
在这一时期,词学批评学、词学文献学、词学考证学等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还相应地有了各自大师级的学术人物。
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三位词学大师鼎足而立,不仅在词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还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个性。
龙榆生长于词学批评学研究,用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学理论进行词学的宏观研究,对词的起源、发展、创作、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对词的审美特征和词史的发展规律等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讨与论证。
他的《研究词学之商榷》、《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词体之演进》、《晚近词风之转变》、《论常州词派》、《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颇具现代文艺美学意识的专论,打破了旧式词学侧重于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传统,开启了用现代文艺学新观点和新方法进行词学宏观研究的新理路。
夏承焘长于词学考据学研究,注重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订以及词乐、声律的研究。
他从一般词籍校勘深入到词乐领域,进行精密细致的声学考订工作,其《白石歌曲旁谱辨》、《姜白石词编年笺注》是白石歌词创作与乐律资料的百科全书。
他于词籍校勘之外,进行规模浩大的谱牒考订工作,是词学谱牒学的奠基人,其后出之《唐宋词人年谱》是治词者案头必备之书。
他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词法考订工作,编辑《词例》,其词例归纳为后学打开了不少法门。
这项工作与他早年的谱牒考订基本是同时进行的,几十年不曾中断。
此外,他还于考订之外,对词作家、词学理论也有深入的研究,如《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词律三考》等专文,也多是善于将词学考证结论或成果融入其理论思考的力作。
(5)唐圭璋长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是词学文献学的第一大家。
他穷毕生精力,致力于词籍文献的整理研究,除《词话丛编》这部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之外,他于抗战前编著的《宋词纪事》,按时代先后分列宋代词人(列词人279位),也是宋词研究中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其中“以宋证宋”的方法论原则对词集整理与词话研究也极有启发作用。
五、六十年代是词学研究的过渡期。
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论争:
一是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二是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讨论。
关于李煜词的讨论,是从1955年8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第64期发表陈培治《对詹安泰先生关于李煜的〈虞美人〉看法的意见》一文和同期詹安泰的答复开始的。
游国恩、谭丕模、邓魁英、聂石樵等人都参与了讨论,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李煜其人和南唐社会的评价;2、前期李煜词的爱情描写和人民性问题;3、后期李煜词与爱国主义问题。
后期的中心议题是“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
”,且开始涉及到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解答有“类似--共鸣”说、“情绪、感触--共鸣”说以及“典型--共鸣”说几种看法,最后以何其芳的“典型--共鸣”说为权威的解答。
1957年开始的关于李清照词及其《词论》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高→低→高→低的发展过程。
最初肯定的声音较高,繆钺、程千帆、谭丕模等人对李清照倍加颂扬。
1958年,由于“大跃进”思潮和当时教改形势的需要,李清照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遭到批判,李清照及其词作也遭到否定。
从1959年到1962年,对李清照词作及《词论》的研究与论争又趋活跃并出现了分歧,夏承焘、唐圭璋等词学大家也参加了讨论。
讨论内容主要涉及到:
1、关于李清照的改嫁问题;2、关于李清照词所体现思想情感的评价问题;3、关于李清照《词论》的评价问题。
主要针对的是她的“别是一家”说,同时还涉及到李清照对北宋诸词家的评论,以及李清照的词论主张与其创作实践是否一致的问题(后有详论)。
此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古典文学包括词学研究渐趋沉寂,对李清照及其词论的研究与争论也以一代词宗夏承焘的题为《“诗余”论——宋词批判举例》的带有时代总结性的文章而结束。
(6)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词学文献的校勘或笺注方面有一定的收获。
如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校订重印的清代张宗橚的《词林纪事》、杜维沫校点的《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王幼安等注释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廖德明校点的《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夏承焘等校笺的《〈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王幼安校点与校订的《渚山堂词话》和《词品》(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等。
新时期以来是词学研究的兴旺期。
这一时期,20世纪的重要词学典籍几乎全部整理重印,从宋代到清末的重要词人的作品集几乎全部整理出版,词学研究的整体学术氛围与此前的相比,得到极大改善。
词学界关于婉约派的正名问题、对“别是一家”的本色理论的重新评价问题等讨论更为深入,不仅各种富有开拓性的专著络绎而出,而且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也逐步形成,1981年开始创刊的《词学》(已出10期,后停刊)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交流与探索的理论园地。
在这一较好学术氛围中展开的词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词学文献资料的整理有了新收获。
词学理论资料的整理工作从八十年代开始取得明显的进步。
唐圭璋修订校改的《词话丛编》,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所收宋代至近现代以来词话增至85种,且一一作了标点,为迄今收入词论最多的资料书,是研究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资料巨制,在词学研究上具有集资料之大成的价值。
由他校注的《词苑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对词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刘石和周玉魁二人还分别对唐圭璋《词话丛编》中的标点体例混乱、标点体例不当、断句标点错讹等问题进行了指正,这种不以权威为迷信,善于发现错误、勇于指出错误的研究风气值得赞许。
(7)其它的收获有:
滕咸惠校注的《人间词话新注》(齐鲁书社,1981年)、许文雨的《人间词话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屈兴国的《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齐鲁书社,1983年)、武汉大学中文系编辑的《历代诗话词话选》、龚兆吉编的《历代词论新编》(北京师大出版社,1984年)、蔡桢的《词源疏证》(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王百里的《词苑丛谈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施议对的《人间词话译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等。
20世纪末收获的《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和《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两著对词学理论研究也极有帮助。
由于词为诗余的传统观念,加之词学理论对诗学理论的依附性也很强,词学论著向来不受重视,为之注释、解诂者则更少。
唐圭璋的《词话丛编》、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等虽收录不少词话著作,但词籍序跋类的散篇材料却未能收录,金启华等的《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和施蛰存的《词籍序跋萃编》在此方面可说是贡献甚巨,惜乎只裒集原文,未作注疏,就此而言,陈良运主编的《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就具有特殊的价值。
该著按词的历史发展顺序,共收录唐代至近代各类词学论著140家229篇,详加注释(绝大多数属于首次加注),并就其中的理论观点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作言简意赅的综合评释,对词学理论的研究和普及都极有帮助。
施蛰存、陈如江的《宋元词话》遍检散见于宋元各种笔记、诗话、野史、琐谈等著述中的词评、词论、词本事和词坛琐事,录得词话近千则,实可为唐圭璋《词话丛编》的补编。
据辑录者介绍,这一工作实际从抗战时即已开始,历尽战火与政治动荡,至世纪末才得以面世,所录宋人词话,仅将存世的宋人笔记过眼一遍,就极为不易,其间辛苦可以想见,此书可以说弥补了宋代词话专著独少的缺憾。
据悉,钟振振等人正在编撰《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这部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
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提及或使用过的。
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并且,编者“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以免学界继续以讹传讹”,(8)相信它的出版将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更大的便利。
在词乐、词韵、词谱等方面,新时期以来有不少收获。
如词乐方面,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8年重印了《羯鼓录》、《乐府杂录》和《碧鸡漫志》的合订本。
词韵方面,张保先、王珍所编之《词林新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以“十三辙”韵部系统为据编成,对诗、词、曲的写作很适用。
词律与词谱方面,《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钦定词谱》(中国书店,1979年)都有影印本出版,舒梦兰的《白香词谱》则分别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柳淇校订本和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顾学颉校订本。
杨文生的《词谱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列词谱120多种,附“词韵常用字表”及“普通话十八韵和京剧韵十三辙对照表”,对每一词牌征引历代词话中的相关评论,以便读者了解,然后列出平仄并附实例,或加按语进行解释,也很有学术价值。
在书目及论文索引上,新时期以来也有不小的收获。
如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所附曹济平辑录的《词学要籍简介》,依唐圭璋《词话丛编》所录八十多种历代词话传本,略述其书目版本、作者及卷数,并间附散佚词话,对初治词学者颇为有益。
张葆全主编的《中国古代诗话词话辞典》所附汤炳能编撰的《诗话词话研究论文索引》,以朝代为序,收录了1906—1991年间的研究论著目录,对词学研究很有帮助。
刘扬忠编著的《宋词研究之路》(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所附之《建国以来宋词研究重要论文索引》(1949—1987)、《1919—1949年宋词研究重要论文索引》、《台湾省宋词研究部分论文索引》和《日本及欧美宋词研究主要文献索引》(部分)对宋代词学理论研究也很有学术价值。
此外,刘尊明编辑的《词学研究论文索引(1993-1995)》和《1993-1995年词学研究论文索引(续补)》、中华书局出版的《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等,也都给词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词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大大拓展,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
新时期以前词学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李清照、王灼、张炎、胡仔、李渔、朱彝尊、陈廷焯、况周颐、周济、刘熙载、王国维等人,除对王国维、李清照、刘熙载等人的讨论较多外,对其它人的研究都只有一、二篇文章论及,且论述也大多比较简略。
例如,西谛在其读书杂记中曾对王灼的《碧鸡漫志》作简介说:
“自汉以后,乐府渐兴乃至先有音律,而后有文章,音律不能表现情感,而情感反受音律支配,中国抒情诗不大十分发达,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
宋王灼《碧鸡漫志》对于这一层有几段话说得极好。
”(9)至于如何“说得极好”,以下就语焉不详了。
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的对象明显增加,范围大大拓展,一些以前不曾为人所关注的词论家或词学理论现象都进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宋人选宋词”问题、清词选本的批评价值、杨慎的《词品》及其“词境”论、陈子龙的词学观、李渔的《窥词管见》、彭追孙的《金粟词话》、王士祯的词论、徐釚的《词苑丛谈》、舒梦兰及其《白香词谱》、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冯煦的词论、郑文焯的《大鹤山人词话》等,都有专门论述,其中不少还是词学研究中新开辟的领域。
在研究方法上,则基本实现了“从直观鉴赏到逻辑论证、从单一思维到综合研究”(10)的转换。
以对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研究为例,就可以看出上述特点。
新时期以前,有关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研究的文章约有四十多篇,而从新时期到九十年代初,文章与论著则增至二百多篇(部)。
新时期以前对王国维及其《人间词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境界”说、“隔”与“不隔”说的研究,以及对其唯心论思想实质的批判几个中心议题上。
从新时期开始,研究的视界则明显拓宽,研究方法也更趋逻辑化、多样化。
如从现代文艺理论角度分析“境界”的专文就颇为不少,这其中,从文学特征论分析“境界”说的有之;从范畴论分析“境界”说有之;从文学创作论分析“境界”说的有之;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境界”的有之;从文学鉴赏论角度分析“境界”论也有之。
对“境界”说所作的逻辑性理论阐发,既涉及到“境界”说的理论结构及其意义,也涉及到“境界”说的内涵与层次。
在探讨“境界”说的思想渊源方面,剖析“境界”说之禅宗意蕴的有之,梳理“境界”说与叔本华美学之关系的亦有之。
从中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的词学研究,范围更广、研究方法更趋多化样,入思方式也更趋合理。
三、专门研讨会的召开为词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如1983年11月在华东师大举办的词学讨论会,就婉约与豪放是否成派及孰为正变、词的诗化问题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90年6月在美国举办的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对词之美学特性与形式问题、词评与词籍的保存和词的接受、词学研究之未来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1)1991年10月,广西师大、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在桂林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诗话词话学术研究会”。
会议对有关诗话的定义和范畴、诗话词话的价值和意义、诗话词话今后的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94年10月,由《文学遗产》编辑部、湖北大学中文系、中国韵文学会词学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二十世纪词学研究走势学术研讨会”在湖北襄樊召开,会议肯定了新时期以来词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如加强了文化背景的描述和分析;总体框架走向以派代史,以体代史;强化整体把握;强化史的流程;多角度、全方位评论作家等等。
会议也指出了词学研究中的不足,如缺少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研究格局、研究对象、范围严重失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还提出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这些会议的共同特点是对词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以后需要努力的方向都极为关心,无疑,它们的召开对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是极有帮助的。
四、词学史研究取得突破。
六十年代中期,江润勋曾撰《词学评论史稿》(香港龙门书店,1966年),以人为经,以时代为序,介绍了自五代至清末王国维等历代重要词人或词论家对词学的有关评论,既有关于词学理论方面的主张,也有对具体词人词作的品评,是新时期以前词学理论史研究的主要收获。
从新时期开始,随着杨海明的《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黄拔荆的《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严迪昌的《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许宗元的《中国词史》(黄山书社,1990年)、萧世杰的《唐宋词史稿》(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等词史著作的络绎而出,词学理论与批评的编撰条件已趋成熟。
九十年代,终于有所收获。
谢桃坊的《中国词学史》将中国词学史的发展过程分为创始、建立、中衰、复兴、极盛和现代词学研究等阶段,首次勾勒了中国词学发展的大势。
方智范等人的《中国词学批评史》比较全面地描述了中国词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各个阶段的理论特征,还对词学批评本身的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词学批评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表现在:
词学批评对象的“狭深性”既是一种不可克服的缺陷,也酿就了词学批评自身的独创性特色;词学批评在其发展进程中时时表现出向古典诗学批评传统的回归和依附趋向,其出发点是竭力维护词体本位,却又显示了词学批评的自立性特色;批评观念的相对板结、凝固在一定时期内甚至显得滞后,却又造成了词学批评便于远距离观照的总结性特色。
可以说,这些逻辑性的结论是作者从对中国词学历史嬗变规律的细致剖析中自然引申而出,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更显示出建基于历史“深描”基础上的较强的理论整合能力。
此外,丁放的《金元明清诗词理论史》下编“金元明清词论”对金元至清代的词论发展历程、重要词论家的词论观点及其贡献也作了比较深入的清理。
五、理论阐发型研究开始起步。
旧式词学研究大多专写评点式的词话或只重文献的实证研究,理论的建构与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刘扬忠曾在《关键在于理论的建构和超越---关于词学学术史的初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