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 明初理学.docx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 明初理学.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 明初理学.docx(1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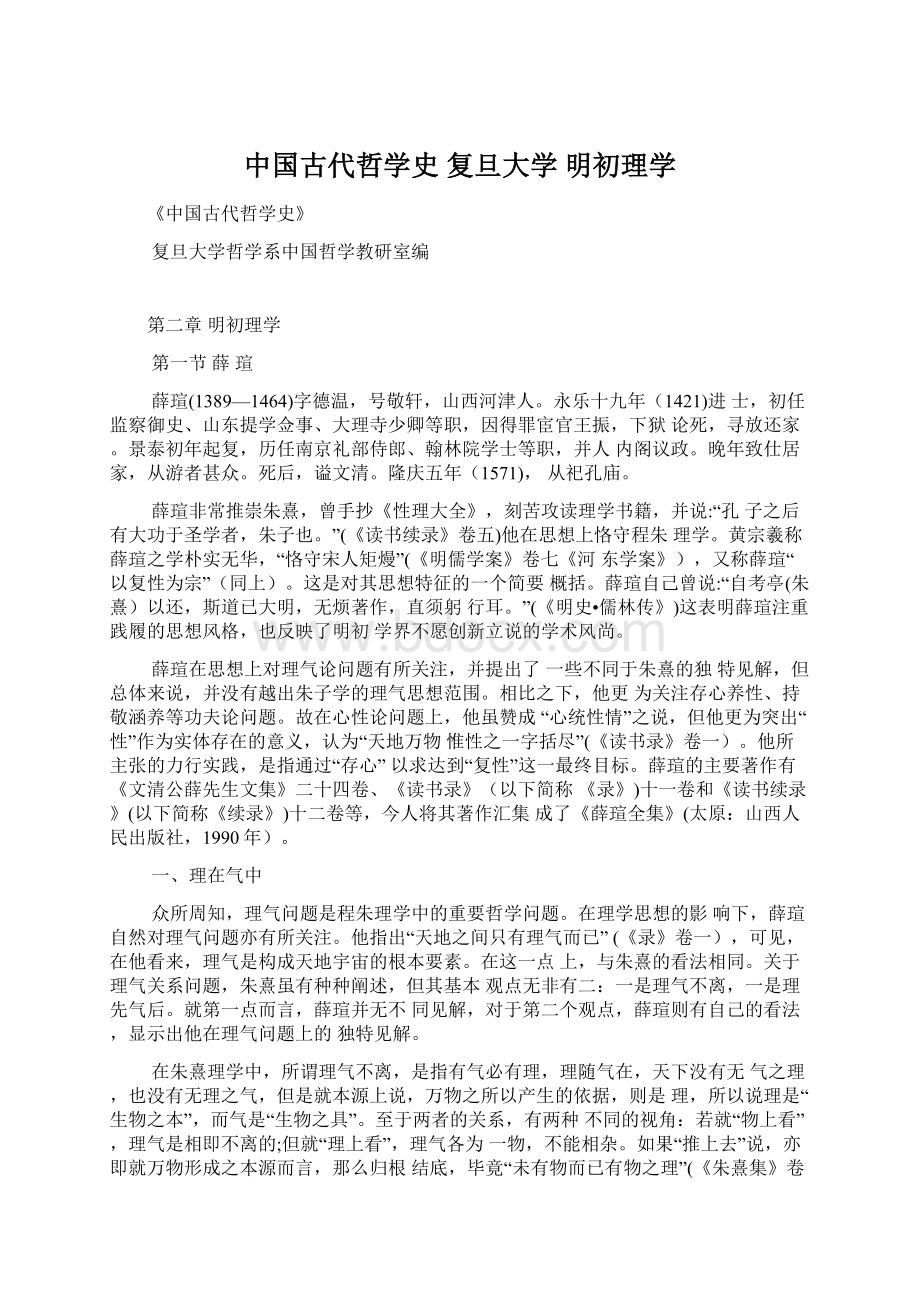
中国古代哲学史复旦大学明初理学
《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
第二章明初理学
第一节薛瑄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
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初任监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寺少卿等职,因得罪宦官王振,下狱论死,寻放还家。
景泰初年起复,历任南京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等职,并人内阁议政。
晚年致仕居家,从游者甚众。
死后,谥文清。
隆庆五年(1571),从祀孔庙。
薛瑄非常推崇朱熹,曾手抄《性理大全》,刻苦攻读理学书籍,并说:
“孔子之后有大功于圣学者,朱子也。
”(《读书续录》卷五)他在思想上恪守程朱理学。
黄宗羲称薛瑄之学朴实无华,“恪守宋人矩熳”(《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又称薛瑄“以复性为宗”(同上)。
这是对其思想特征的一个简要概括。
薛瑄自己曾说:
“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明史•儒林传》)这表明薛瑄注重践履的思想风格,也反映了明初学界不愿创新立说的学术风尚。
薛瑄在思想上对理气论问题有所关注,并提出了一些不同于朱熹的独特见解,但总体来说,并没有越出朱子学的理气思想范围。
相比之下,他更为关注存心养性、持敬涵养等功夫论问题。
故在心性论问题上,他虽赞成“心统性情”之说,但他更为突出“性”作为实体存在的意义,认为“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读书录》卷一)。
他所主张的力行实践,是指通过“存心”以求达到“复性”这一最终目标。
薛瑄的主要著作有《文清公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读书录》(以下简称《录》)十一卷和《读书续录》(以下简称《续录》)十二卷等,今人将其著作汇集成了《薛瑄全集》(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一、理在气中
众所周知,理气问题是程朱理学中的重要哲学问题。
在理学思想的影响下,薛瑄自然对理气问题亦有所关注。
他指出“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录》卷一),可见,在他看来,理气是构成天地宇宙的根本要素。
在这一点上,与朱熹的看法相同。
关于理气关系问题,朱熹虽有种种阐述,但其基本观点无非有二:
一是理气不离,一是理先气后。
就第一点而言,薛瑄并无不同见解,对于第二个观点,薛瑄则有自己的看法,显示出他在理气问题上的独特见解。
在朱熹理学中,所谓理气不离,是指有气必有理,理随气在,天下没有无气之理,也没有无理之气,但是就本源上说,万物之所以产生的依据,则是理,所以说理是“生物之本”,而气是“生物之具”。
至于两者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视角:
若就“物上看”,理气是相即不离的;但就“理上看”,理气各为一物,不能相杂。
如果“推上去”说,亦即就万物形成之本源而言,那么归根结底,毕竟“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熹集》卷四十六《答刘叔文•一》)。
这就是所谓“理先气后”的观点,也是朱熹理气论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一观点的实质是“理在气上”(严格地说,应该是“理在气之上、气之先”),这样一来,就与“理在气中”之说未免有所冲突。
原因在于,对朱熹来说,他始终不能放弃理本论的立场,亦即“理与气,此绝是二物”的立场,把理看成是某种绝对的实体存在。
薛瑄指出:
遍满天下皆气之充塞,而理寓其中。
(《录》卷二)
气之所在,理随在焉,夫岂有亏欠间隔哉!
(《续录》卷一)
所谓“理寓其中”、“理随在焉”,这也就是朱熹的“理气不离”的说法。
但是,薛谊所谓的理气相“寓”、理气相“随”,是强调理气之间无丝毫的“亏欠间隔”,亦即他一再强调的“理气无缝隙”(《录》卷六)、“理气浑然无间’’(《续录》卷一)、“理气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续录》卷七)的意思。
薛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其实是针对朱熹的“太极阴阳,决是二物”的观点(又可称为“理气不杂”的观点)而发。
在薛瑄看来,如果承认理气为二物,那么就必然导致“理先气后”的结论。
对于理先气后说,薛瑄提出了明确的批评:
或言: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气。
”窃谓理气不可分先后。
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
及动而生阳而天始分,则理乘是气之动而具于天之中;静而生阴而地始分,则理乘是气之静而具于地之中。
分天分地而理无不在,一动一静而理无不存,以至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理气二者盖无须臾之相离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后哉!
(《录》卷三)
“或言”,是指朱熹(参见《朱子语类》卷一)。
从这段批评中可以看出,薛瑄坚持认为即便在天地未形成之前,理气也必然是“无须臾之相离”,这就是所谓“理气浑然无间”的真实涵义。
这段批评的主要旨意在于:
“气”在天地未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这浑然未分的“气”中,就已蕴含着“理”。
按照我们的分析,薛瑄的意思是说,不论怎样“推上去”说,即便“推”到尽头,“推”到天地未分、动静未萌之际,“气”的存在也是永恒的;因此决不能认为在世界未形成之前,只有“理”而没有“气”。
既然“气”贯穿于天地之始终,所以“理”就永远不能“离乎气也”(《录》卷四)。
反之,如果以为理在气先,那么理就成了“悬空之物,而能生乎气矣”(同上),最终就会得出“理生气”的荒谬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从朱熹的理气不离的观点来看,他固然也能承认“理在气中”,但是薛埴所说的“理在气中”,显然在内涵上已与朱熹有异,确切地说,薛瑄只承认理气不可分先后,在此前提之下,才能说“理在气中”。
换言之,如果承认理在气先的话,那么归根结底,理气之间就会有“间隔”、有“缝隙”,而无法证明理气“浑然无间”。
所以,薛瑄的“理在气中”说,并不是就“物上看”的一种假定,而是就理气的整体关系而言的,这与朱熹就“物上看”的前提之下所说的“理在气中”说有着根本不同。
不过,薛瑄的理气论也有矛盾之处。
由于他反对“理先气后”说,所以他不能赞同“理气为二”的观点而必须坚持“理在气中”,但是,他又提出了“气载理,理乘气”、“理为主,气为客”以及“气有变,理无变”等观点,而这实际上就是朱熹的观点。
由此思路来看,理气毕竟为“二物”,是“乘”与“被乘”、“载”与“被载”的关系。
他又用“日光载鸟”的比喻,来说明理气的这种关系,其云:
“理如日光,气如飞鸟,理乘气机而动,如日光载鸟背而飞。
”(《录》卷四)可见,理气只是“载”与“被载”的关系,究竟而言,理气为二。
这是因为“理既无形,安得有尽”?
“聚散者气也,若理只泊在气上,初不是凝结自为一物”(《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如此看来,理是绝对恒的存在,是有形之气中的实体,这应当是朱熹固有的观点。
所以罗钦顺批评道,薛瑄讲的“理气无缝隙”虽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又讲“气有聚散,理无聚散”,事实上“一有一无,其为缝隙也大矣”(《困知记》卷下),意谓薛瑄的观点毕竟落人认理气为二物的窠白之中,这一批评是不无道理的。
总之,可以作如下几点归纳:
1)薛瑄强调“理气不离”、“理在气中”、“理气浑然无间”,这主要是就天地万物的形成过程以及就理气结构而言的。
2)然而,若就理之本身或者就物之所以为物的本原来看,理毕竟是物的“所以然”之根据,它是不会散尽消失的、绝对永恒的实体存在,这也就是朱熹的“理气不杂”的观念。
3)因此从本质上说,薛瑄的理气观仍然属于理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本观,而不能将其思想归于“气本论”或“气一元论”的思想类型。
4)他对朱熹的“理先气后”说、“理能生气”说虽有批评,显示出其思想的独特色彩,但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理先气后”说,因为他在宇宙本体论的问题领域,不能放弃理为绝对的观念。
二、此心惟觉性天通
我们知道,朱熹的理气论为其心性论奠定了基础。
同样,薛瑄的理气论在其心性论当中也有反映。
其实,在宋明儒学当中,宇宙论与人性论本来就是紧密相关的。
在薛瑄看来,由于理是永恒的,而气是易变的,因此在修养功夫上必须做到“以理制气”,与此相应,在心性问题上,他认为:
“性纯是理,故有善而无恶;心杂乎气,故不能无善恶。
”(《录》卷五)可以说,这是其心性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他看来,心性与理气是相应的,性与理一样,是绝对而纯善无恶的,心与气一样,是混杂而有善有恶的。
至于心与性的关系及其各自的本质特征,薛瑄指出:
天道流行,命也;赋予人,性也;性与心倶生者也。
性体无为,人心有觉,故心统性情。
(《续录》卷四)
首先,他认为性就是天道流行而赋予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其次,从人的生成构造的角度而言,性与心是同吋具备而不能分离的;再次,从本体的角度看,性体是无所作为的,而人心则是有觉有感的。
归结而言,结论就是“心统性情”。
这里所谓的“心”,是指人的知觉能力、意识活动。
既然心与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从心性结构上看,心性是不可分离的;然而由于性体是无所作为的,而心则具有能动的主宰作用、知觉能力,因此心能涵性,并能统括性情。
其实,这是朱熹理学的固有思路,并不是薛瑄的创见。
至于薛瑄的独特之处则在于:
一是强调了“性”作为实体存在的意义,一是强调了实践功夫须经由“存心”以实现“复性”为最终目标。
薛瑄一方面承认“心统性情”,同时他又认为“性”毕竟是“该众理”、“贯宇宙”的实体,指出:
•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
(《录》卷二)
然则性者万理之统宗欤!
理之名虽有万殊,其实不过一性。
(《录》卷五)
性非特具于心者,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也。
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动静之理皆是,凡天地万物之理皆是也。
故曰:
“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性无不在。
”(《录》卷一)
圣人之所以教,贤人之所以学,性而已。
(《录》卷三)
以上这些说法归纳起来看,薛瑄想强调的是:
“性”是万物存在的根源,性虽涵具于心,但只是表明存在论意义上的“在”或“有”,性体本身并不等同于心,换句说法,心与性不是本质上的同一关系,性与理则是一种本质同一,天地万物之理、耳目口鼻之理都无非是性体的表现。
因此,薛瑄非常赞同朱熹的“天下无性外之物,而无所不在”的观点,并断然宣称圣贤之为学为教,只一“性”字而已。
基于上述的思想立场,薛瑄进而提出了“尽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录》卷一)的观点,他认为“苟不知性知天,则一理不通而心即有碍,又何以极其广大无穷之量乎!
”(同上)然究其实,这一观点实是源自朱熹,朱熹将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中的“尽心”和“知性”的功夫顺序颠倒过来,以为必须穷尽天下众理之妙,方可谓全其心体之量。
然而,薛瑄对于朱熹那个通过格物才能做到“知性”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的见解,他指出虽就事物的表里精粗、本末得失一一格之,是皆“所谓格物也”,然“天下之物众矣,岂能遍格而尽识哉?
”所以重要的是,必须“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极,今日格之,明日格之”,“潜体积习之久,沉思力探之深”,如此则能达到万物之理与吾心之理“潜会而无不通”(《录》卷二)。
显然,薛瑄此说,既有蹈袭朱熹格物说的痕迹,也有“返心而求”的思想倾向。
特别是“岂能遍格而尽识”这一问,对薛瑄来说,其意义虽然还不明显,但对照后来兴起的心学思想,这一观点无疑是对朱熹的格物理论的根本怀疑。
既然“复性”是最终目标,那么具体而言,又如何做到“复性”呢?
薛瑄认为,复性工夫还须通过存心,而存心工夫主要就是“居敬”。
他强调“居敬以立本,穷理以达用”(《录》卷五),“学以敬为本”(同上)。
这是将“居敬”工夫视作根本工夫。
在他看来,居敬是避免心之“乱想”、身之“乱动”,并能时常保持“谨畏之心”(同上)而不至于迷失方向的重要实践手段。
可见,居敬工夫又必须落实到“心体”上。
那么,如何落实呢?
要之,就是祛除心中的私心杂念,他说:
“万起万灭之私,乱吾心久矣。
今当悉皆扫去,以全吾湛然之性”(《录》卷一),“心清则见天理”(《录》卷二),待到私心杂念悉数扫尽,则可达到“心中无一物”的境界,故说:
“学至于心中无一物,则有得矣。
”(《录》卷二)他在临终时,曾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
(《文集》卷五)意思是说,自己内心已经达到了与“性”、“天”相通融合的境地。
这应当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实践体验的忠实表述。
黄宗羲对薛瑄思想虽有微词,但对薛瑄此诗则有中肯评价:
“此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
”(《明儒学案》卷七《河东学案》)这一评判与薛瑄注重力行践履的思想性格是相吻合的。
总之,薛瑄的理气论和心性论基本上是对朱熹理学的一种注释而已,并无特别的创新。
他以“性”为宗旨,以为“性”是“万理之统宗”,故以追求“复性”为一切工夫的最终目标。
同时“复性”又须落实在“心”上,故他十分重视通过居敬来正心,最终的理想境界则是“此心惟觉性天通”。
应当说,薛瑄在明初思想史上是严守理学轨辙的典型人物,同时也应看到,他在心性体验上毕竟有过一番笃实的功夫,他的力行主义思想品格,预示着理学进人明代以后开始发生与宋儒不同的思想转变。
第二节吴与弼与胡居仁
吴与弼(1391—1469)号康斋,江西崇仁人。
他年轻时既放弃举业,一生未仕,以布衣终生,然而却于万历十二年(1584)得以从祀孔庙。
他与薛瑄为同时代人,但生卒略晚于薛瑄。
黄宗羲《明儒学案》却把吴与弼及其开创的学派列为全书之首,名为“崇仁学案”,而后是陈献章开创的学派——“白沙学案”,再后才是薛瑄的“河东学案”。
由这一特殊安排可以看出,吴与弼在明代思想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
我们知道,黄宗羲对明代思想史有这样一个基本看法:
“有明之学,至白沙(陈献章)始人精微。
……至阳明(王守仁)而后大。
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
”(《明儒学案》卷五《白沙学案》)由于吴与弼乃陈献章之师,故把吴与弼置于《明儒学案》之首,显然含有彰显陈、王一系心学的意味,甚至含有这样的意图:
将吴与弼视作开明代学术风气之先的人物。
故云:
“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
”(《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
吴与弼门下有三大弟子:
胡居仁、陈献章、娄谅。
王守仁曾经慕名而与娄谅见过一面,故娄谅可谓是王守仁的一日之师,黄宗羲称娄谅之于王守仁的思想成就有“发端”之功,但娄谅在思想上对王守仁产生了何种影响,并不明确。
据胡居仁的说法,娄谅与陈献章一样,在思想上都有“杂禅”倾向,其实也就是指偏于心学之倾向。
娄谅的著作今已不存,对其思想已无法明了。
陈献章作为明代心学的开创性人物,将在下节专门讨论。
这里我们将主要介绍吴与弼和胡居仁的思想。
吴与弼的主要著作有《吴康斋先生文集》(《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文集》)。
胡居仁的主要著作有《居业录》(京都:
中文出版社刊“和刻影印近世汉籍丛刊”本)以及《胡文敬集》(《四库全书》本)》
一、吴与弼:
身体力行
吴与弼年轻时,尝习举业,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圣贤之学”,“遂弃举子业”,亦即放弃仕途,自此惟以读书传道为一生志向。
他“尝叹笺注之繁,无益有害,故不轻著述”(《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与上述薛瑄所说“无烦著作,直须躬行”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既反映了当时儒者的学术风尚,同时也反映了吴与弼注重躬行实践的思想性格。
在其著作中,有《日录》(类似今日所谓的日记)一卷,真实记录了他平时刻苦实践的心路历程。
黄宗羲称他:
“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间,出入作息,刻刻不忘。
”(《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特别是“身体力验”一词,是对其思想特色的一个很贴切的概括。
在不事著述、讲究力行方面,吴与弼与薛瑄有相近之处,但是与薛瑄在理气论方面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的关心不同,吴与弼则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关心,同样,与薛瑄强调“性”字,主张“复性”工夫也有所不同,吴与弼更为注重“心”的问题。
他曾说:
“充满宇宙皆生物之心,满腔子皆恻隐之心。
”(《日录》)这后一句原是二程的话,“恻隐之心”就是道德之心。
这是说,宇宙和人生都充满着一种精神,就宇宙而言,自有其万物生长之规律,就人生而言,亦有一种道德精神,而且两者是可以彼此感通、互为一体的。
故说:
“将这身来放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同上)“存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
”(《文集》卷六《诗•道中作》)讲的就是人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精神埼界,这是自周敦颐以来特别为程颢所称道的“孔颜乐处”这一理学的精神境界。
由此看来,虽说其思想“一禀宋人成说”(黄宗羲语),然其精神趋向与其说接近于程(颐)朱(熹),毋宁说接近于周(敦颐)程(颢)。
那么,吴与弼所说的“心”有何具体内涵?
大致说来,有以下这些说法:
心是活物。
(《日录》)
心本太虚也。
(同上)
人心禀至灵。
(《文集》卷六《诗•晓起即事》)
(心是)虚灵之府,神明之舍。
(《文集》卷三《浣斋记》)
要而言之,心是指人的一种道德意识、知觉活动,从其根本特征来看,具有“虚灵明觉”或“湛然虚明”之特征。
由于人心易受后天的习染、环境的影响,人的“本心”也就未免容易收到扰乱而变得“浑浊”。
因此重要的是,必须以“敬义挟持,明诚两进”(娄谅《康斋先生行状》)的方法(实即程朱的居敬功夫),来整顿“自心”,收拾身心,使其恢复“湛然虚明”。
他说:
人须整理心下,使教莹净,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内工夫也。
嗟夫!
不敬则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万事从此坠,可不惧哉?
(《日录》)一事少含容,盖一事差,则当痛加克己复礼之功,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则应事可以无失。
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不可须臾也。
苟本心为事物所扰,无澄清之功,则心愈乱,气愈浊,梏之反复,失愈远矣。
(同上)
应当承认,上述所谓“常惺惺”、“敬以直内”、“静时涵养,动时省察”等说法,无非就是程朱理学所说的一套工夫论主张,并无特异之处,然而吴与弼再三强调“涵养本心”的重要性,他甚至说:
“玩《中庸》,深悟心学之要,而叹此心不存。
”(《日录》)将《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之工夫以及“存心”工夫称为“心学之要”,从根本上说,这与程朱理学所注重的向外求理、格物致知的为学方向有所不同,凸现其思想.爲有一种“返求诸Li”、I"丨内用功的趣向。
当然,吴4弼所说的“心学”,与我们今天所指称的“陆王心学”中的“心学”这一概念,/K内涵上是不同的,但是他的“返求沾已”的思想趣向对胡居仁和陈献G均产生了深刻影响,胡居仁且不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献章的心学思想未尝不是从刻苦“存心”的践履中开出。
总之,吴与弼在思想上并没有独特创新,其为学志向也不在于建构学说体系,他严格按照理学的方法,一生刻苦实践,注重“涵养本心”,提倡“安贫乐道”,追求一种“苟得本心,随处皆乐”(《日录》)的精神境界,非常强调“须用刻苦”(同上)、“努力向前”(同上)、知难而进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作用。
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出,明初理学对向外穷理、章句训诂之学的兴趣渐渐淡薄,转向对内在心性的涵养以及恢复“本心”等工夫问题的重视。
明末大儒刘宗周对吴与弼的思想曾有这样的评述:
先生(吴与弼)之学,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盖七十年如一日,愤乐相生,可谓独得圣贤之心精者。
至于学之之道,大要在涵养性情,而以克己安贫为实地。
此正孔、颜寻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动之间,悉归平淡……薛文清(薛瑄)多困于流俗,陈白沙(陈献章)犹激于声名,惟先生醇乎醇。
(《明儒学案•师说》)
应当说,这一评价和定位是符合吴与弼的思想实际的。
二、胡居仁:
主敬穷理
胡居仁(1434—1484)号敬斋,江西余干人。
《明史•儒林传》称:
“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斋……人以为薛瑄之后,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
”对其思想之特征作了大致的概括。
胡居仁入吴与弼门下后,遂绝意科举,一生不仕,居家读书,信从程朱理学,尤对居敬学说尊信不疑,在这一点上,胡居仁受到了吴与弼的深刻影响。
不过,在其他一些方面,胡居仁对其师说(譬如,有关“乐”的精神境界)则有所不取。
在吴与弼门下,胡居仁可谓是最为笃信程朱之学,其对同门陈献章、娄谅屡有批评。
关于儒学工夫的问题,胡居仁指出:
儒者工夫自小学洒扫应对、周旋进退、诗书礼乐、爱亲敬长、毕恭毕敬,无非存心养性之法,非僻之心在这里已无。
及长则主敬穷理并进交养,戒谨恐惧,诚恐一事有差,则心无不存、理无不在。
(《居业录》卷七)表面看来,“洒扫应对”与“主敬穷理”是分别针对孩提和成人而言,亦即古代所谓的“小学”和“大学”之别。
其实,作为“存心养性之法”,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是对于成人来说,更要自觉地做一番“主敬穷理”的工夫,而不能停留于“洒扫应对”的工夫层面。
那么,何谓“主敬穷理”?
首先,“主敬”也就是“居敬”,是程朱理学所主张的主要工夫,胡居仁对此有一番详细的分析:
圣贤工夫虽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戒谨底意思,敬有肃然自整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纯一底意思,故圣学就此做根本,凡事都靠着此做去,存养省察皆由此。
(《居业录》卷二)
敬该动静,静坐端严,敬也;随事检点致谨,亦敬也。
敬兼内外,容貌庄正,敬也;心地湛然纯一,敬也。
(《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
端庄严肃、严威俨格,是敬之入头处;提撕唤醒,是敬之接续处;主一无适、湛然纯一,是敬之无间断处;惺惺不昧、精明不乱,是敬之效验处。
(同上)
以上这些讲的都是居敬工夫的具体内容,其中涉及到戒谨恐惧、湛然纯一、端庄严肃、提撕省察、主一无适、惺惺不昧、精明不乱等内容。
所有这些说法,其实都没有超出程朱理学对居敬工夫的规定,胡居仁反复重申理学中有关居敬工夫的各个方面,只是突出了居敬工夫的重要性。
其中,“圣学就此做根本”一句,颇能反映他将“居敬”视作圣学的根本工夫这一思想特质。
然而,胡居仁又为何在另一方面强调“穷理”呢?
对于上述“主敬穷理并进交养”,又应如何理解?
先来看二段资料:
理与气不相离,心与理不二。
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益明,理明气清则心益泰然矣。
故心与气须养,理须穷,不可偏废。
(《居业录》卷一)吾儒心与理为一,故心存则理明……释氏则心与理二,故心虽存亦无理。
(同上)
在胡居仁看来,只讲存心而不讲穷理,这是吾儒与佛教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佛氏所讲的“心”是空无一物的,而儒家所讲的“心”则有“理”作为其真实内涵,由于儒家主张“心与理一’’(按,其实就是朱熹的说法),因此存心的同时,理亦须穷,换言之,两者“不可偏废”。
可见,穷理与存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然而,究极而言,正如“心存则理明”所表明的那样,存心工夫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从以上第一段资料来看,胡居仁的思路是:
由心存而气清,气清则理明。
换言之,工夫的顺序应当是:
由存心而养气而穷理。
也正由此,故胡居仁在另处则说:
“学者先当理会身心,此是万事根本。
”(《居业录》卷三)要之,他所说的“穷理”,虽也包括读书穷理的涵义,但是即物穷理、向外求知的意味却是比较淡薄的。
极端地说,在胡居仁的观念中,“理会身心”、“存心养性”未尝就不是“穷理”。
所以,胡居仁非常强调“体验”,即便是读书,也要结合自身的体验去加以理会,否则就不能将书本知识化为己有,他说:
“体验二字,学者最亲切,读书皆须体验,放自己身上来,不然书自书,我自我矣,济甚事?
”(《居业录》卷二)而在他看来,所谓“体验”,其根本方法就是居敬,因此在方法论上最终还是要回到居敬。
那么,什么叫“存心”?
胡居仁指出,儒家的存心与“禅家存心”不同,禅家的所谓存心,是指“空其心”、“制其心”、“观其心”,而儒家的存心则是“内存诚敬,外尽义理”(《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
也就是说,儒家的存心工夫是以主敬穷理为其真实内涵的。
所谓“内存”,是指“敬以直内”;所谓“外尽”,是指“义以方外”。
要之,从内在的心灵意识来说,存心是要求保持一种诚敬的道德意识状态,从心灵意识的外化作用来说,通过存心可以实现人的社会道德义务。
其中,敬的工夫是贯穿内外、动静的,无论有事还是无事,无论动还是静,都必须贯彻敬字工夫。
所以说:
“敬之所以贯乎动静,为操存之要法也。
”(同上)“敬”对于人的心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