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形词及多义词的区分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影响.docx
《同形词及多义词的区分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影响.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同形词及多义词的区分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影响.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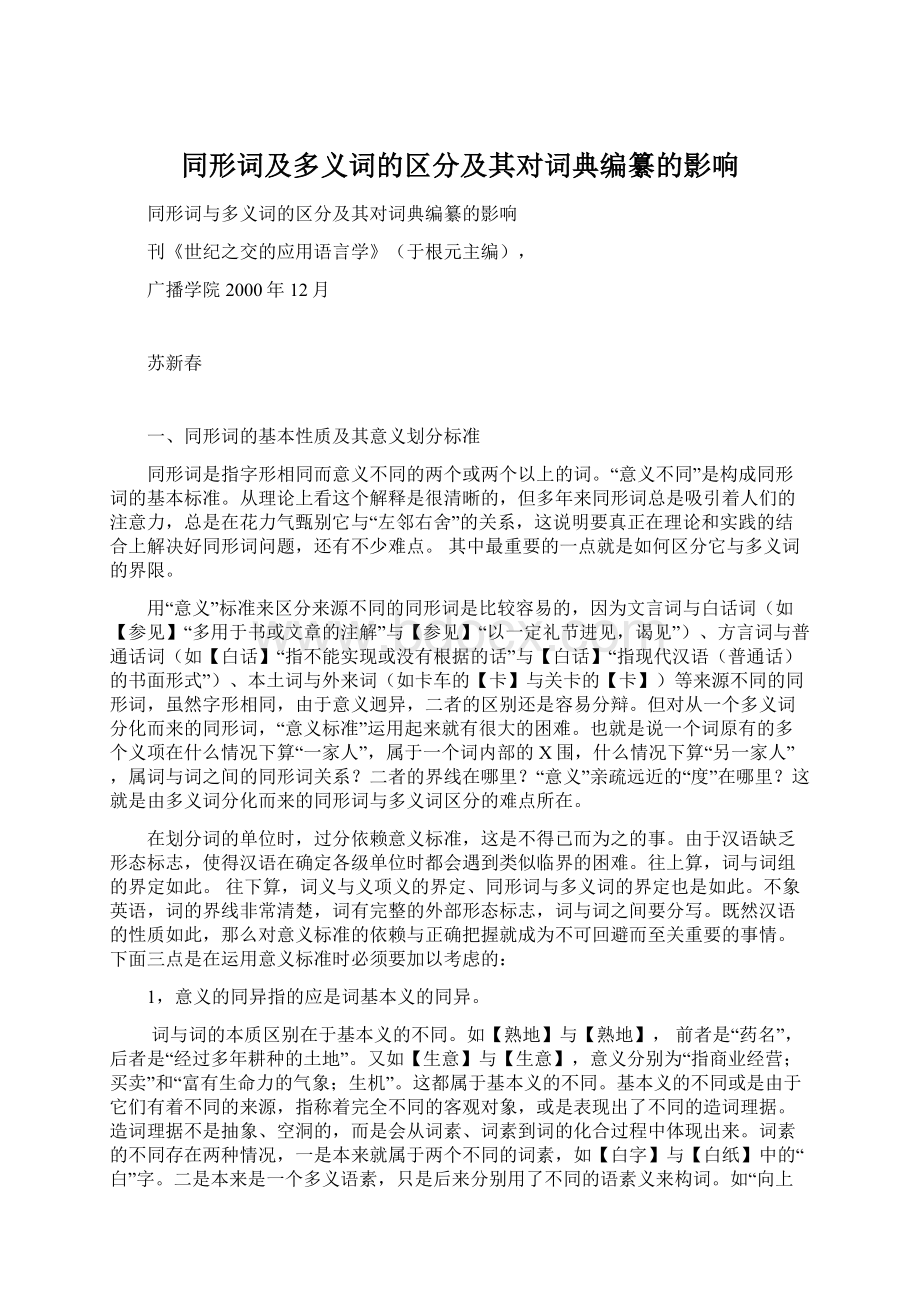
同形词及多义词的区分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影响
同形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影响
刊《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于根元主编),
广播学院2000年12月
苏新春
一、同形词的基本性质及其意义划分标准
同形词是指字形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
“意义不同”是构成同形词的基本标准。
从理论上看这个解释是很清晰的,但多年来同形词总是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总是在花力气甄别它与“左邻右舍”的关系,这说明要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同形词问题,还有不少难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区分它与多义词的界限。
用“意义”标准来区分来源不同的同形词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文言词与白话词(如【参见】“多用于书或文章的注解”与【参见】“以一定礼节进见,谒见”)、方言词与普通话词(如【白话】“指不能实现或没有根据的话”与【白话】“指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书面形式”)、本土词与外来词(如卡车的【卡】与关卡的【卡】)等来源不同的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由于意义迥异,二者的区别还是容易分辩。
但对从一个多义词分化而来的同形词,“意义标准”运用起来就有很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一个词原有的多个义项在什么情况下算“一家人”,属于一个词内部的X围,什么情况下算“另一家人”,属词与词之间的同形词关系?
二者的界线在哪里?
“意义”亲疏远近的“度”在哪里?
这就是由多义词分化而来的同形词与多义词区分的难点所在。
在划分词的单位时,过分依赖意义标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志,使得汉语在确定各级单位时都会遇到类似临界的困难。
往上算,词与词组的界定如此。
往下算,词义与义项义的界定、同形词与多义词的界定也是如此。
不象英语,词的界线非常清楚,词有完整的外部形态标志,词与词之间要分写。
既然汉语的性质如此,那么对意义标准的依赖与正确把握就成为不可回避而至关重要的事情。
下面三点是在运用意义标准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1,意义的同异指的应是词基本义的同异。
词与词的本质区别在于基本义的不同。
如【熟地】与【熟地】,前者是“药名”,后者是“经过多年耕种的土地”。
又如【生意】与【生意】,意义分别为“指商业经营;买卖”和“富有生命力的气象;生机”。
这都属于基本义的不同。
基本义的不同或是由于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指称着完全不同的客观对象,或是表现出了不同的造词理据。
造词理据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会从词素、词素到词的化合过程中体现出来。
词素的不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本来就属于两个不同的词素,如【白字】与【白纸】中的“白”字。
二是本来是一个多义语素,只是后来分别用了不同的语素义来构词。
如“向上级报告”的【上报】与“刊登在报纸上”的【上报】,两个“上”分别用的是“向上级……”义和“刊登”义,两个“报”分别用的是“报告”和“报纸”义。
可见,在语素阶段,多义语素的义项之间是有联系的,属于一个语素的X围,而当用这些义项来分别构词时,构成的词则属于同形词的关系。
这是构成同形词的一个重要来源。
再如【听信】(等候消息)与【听信】(听到而相信)、【下世】(来世;来生)与【下世】(去世)、【成家】(结婚)与【成家】(成为专家)等同形词,都是由于用了多义语素中不同义项的缘故。
象“信”的意义分别是“信讯”与“相信”,“下”的意义分别是“下一个”与“离去”,“家”的意义分别是“家庭”与“专家”。
近读报上有文说顾客受到不良商家的欺骗,广告上说“购房送家具”,购房后商家却说是帮助顾客“运送”家具,而不是按习惯理解的“赠送”家具来办。
这里就是商家玩弄了多义语素的把戏。
将这个例子进行语言因素的分析,它有着这样三个层面:
说到“送”有“运送”和“赠送”两个义,这时的“送”是指一个多义语素;说到“运送”“赠送”是两个词时,这两个是异义异形词;而当说到“(运)送家具”和“(赠)送家具”,它们是两个同形异义的短语结构。
词素义相同,而再生的词义明显不同的,也属于基本义的不同。
如【探子】“指在军中做侦察工作的人”和【探子】“长条或管状的用具,用来探取东西”。
【同房】“指家族中同一支的”和【同房】“婉辞,指夫妇过性生活”。
【油饼】“油炸的一种面食,扁而圆,多用做早点”和【油饼】“油料作物的种子榨油后成饼形的渣滓,如豆饼、花生饼等,可以用做饲料和肥料”。
这是由于词素义只是构词的原料,从词素义到词义中间有一个化合过程。
原料一样,化合过程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相同。
再就是多义词的分化。
在汉语史上两个义项曾经是有联系,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分化成两个不同的词,这样的例子也不少。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雕刻】的“刻”与【一刻钟】的“刻”。
但对多义词分化出来的同形词现象要从严认定。
判断的标准应以社会成员大多数人的语感为准,排除那些需要作专门的考证才能找到词义历史联系的现象。
多数人看不出其中的词义联系了,才能算是同形词而不是多义词。
当然这里面仍有一个度的问题,那么把握尺度的标准就是是社会成员而非专家的语感,是直觉而非考证的结果。
如【刻】,对这两个词义的联系一定要找到古代漏水记时的物具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这就属于“专家”的“考证”了。
又如【雨水】“由降雨而来的水”与【雨水】“二十四节气之一”,二者所指概念义明显不同,但后者又是从前者发展而来的,因为“其时我国严寒已过,降雨渐多”。
这也属于“专家”的“考证”的结果。
它们显然应看作是同形词而不是多义词。
2,同形词的“异义”不应涵盖词义引申造成的词义差别。
提出从严认定多义词分化出来的同形词,就是说多义词内部应该允许有差别的多个义项存在,同形词不应包括词义引申造成的那种派生性的词义差别。
既然我们在语言学理论上承认人类词汇发展的趋势是由单义到多义,也承认现在的词语绝大多数是多义词,那么承认在一个词的内部包含有多个有一定差别度的义项也就是必然的了。
只要是基本义相同,那么在基本义相同基础上因各种原因而派生、繁衍、延展、比喻、借代、蔓生出来的词义,都应算在同一个词的X围,都应算作多义词的下属义项。
“只要一个词的各个不同意义之间含有某些共同的,虽然距离很远的意思,而所有的词义都可以由同一个核心意义联系起来,只是和它有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的差别,那末,我们就以多义性为处理它。
”比如【照样】“依照某个样式”与【照样】“照旧”,【存心】“有意,故意”和【存心】“怀着某种念头”,【褒贬】“评论好坏”和【褒贬】“批评缺点;指责”,【公道】“公正的道理”和【公道】“公平;合理”。
二者之间就都存在着种种或浅或深的联系。
这类现象与“词素义相同,再生的词义明显不同”的区别在于,“再生词义的明显不同”指的必须是基本概念义的不同,而这里所说的则是在概念义相同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次要派生义的差别。
不注意区分这两种情况,就会混淆一个词的意义X围,或是把相差迥异的词义算作一个词的X围,或是割裂多义词内部的联系,人为地把一个词分成了几个词,
3,要有古今贯通的观点,不能绝对排除历时因素。
结构主义语言学是很注意划分共时历时的,区分的目的是专力于共时现象的研究,而把历时现象排除在外。
我国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以致在研究实践上往往忽视词汇的历史发展联系。
其实共时与历时只是一个相对概念。
在语言内部,古今词义的分立是相对的,联系才是绝对的;共时切分是相对的,历时连贯才是绝对的。
不把词汇放到历时的背景下来考虑,许多问题就不好处理。
象如何看待引申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有的词汇学著作“共时”得过分,在词义部分只谈词义的成分、词义色彩,不谈词的“引申义”,因为顾忌谈“引申义”是超出了共时的X畴。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割裂了语言的古今联系。
词汇发展不是无源之水,后起的词,后起的义,都是在已有的词身上发展起来的,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能因为古今相连相分的“度”难把握而就把“历时”一概抛弃。
不能古今大贯通,忽略了现代词汇的特点,也不要古今大割裂,见其一不见其二,视今不观古。
除了上面谈到意义标准的运用所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是在区分同形词时不能不加以讨论的。
一是如何看待语法属性的差异。
当两个词义的关系相当密切,但词性不同,如【惊醒】的“受惊动而醒来。
使惊醒”义与【惊醒】的“睡眠时容易醒来”义。
前者是两个分别为一般动词与使动动词的动词义,后者是形容词义,就算成了两个同形词。
词性的对立中有一类很突出的现象,就是名词与动词的对应。
如【追肥】“在农作物生长期内所施的肥料”义,与【追肥】“在农作物生长期内施肥”义;【作文】的“写文章(多指学生练习写作)”义与【作文】的“学生作为练习所写的文章”义。
在传统语言学中,名词义称为体,动词义称为用,这类现象可称为“体用同称”词。
上面这些例子都取之于《现代汉语词典》,它们都是一一分立,成为名一动对立、体一用对立的同形词。
那么怎么看待这种词义联系密切,而词性不同的词义呢?
是看作多义词好还是同形词好?
可从下面三点来区分,首先,体用同称的词,词义的联系算不算密切?
是不是基本义的相同?
如为肯定的答复,则应看作多义词,因为同形词的基本要求是基本词义必须不同。
其次,词性不同的词应不应该独立成词?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汉语词的语法属性相当灵活,兼类现象相当普遍,要将语法属性不同的词义都分立成不同的词,汉语同形词的数量会大大增加,汉语词汇的总数会大大增加。
再次,多义词内允不允许有词性的的差别?
答案是肯定的。
就拿大量存在词性不同的同形词的《现代汉语词典》为例,它的多义词中也存在着许多的词性相异的义项。
如【组织】有5个义项,其中“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
~人力/~联欢晚会/这篇文章~得很好。
系统;配合关系:
~严密/~松散”,两个义项之间就表现为名一动的对立。
【组合】有3个义项,其中“组织成为整体:
这本集子是由诗、散文和短篇小说三部分~而成的。
组织起来的整体:
劳动~(工会的旧称)/词组是词的~”,也是表现为名一动的对立。
【冠冕】有两个义项,“古代帝王、官员戴的帽子。
冠冕堂皇;体面”,一为名词义,一为形容词义。
可见,根据语法属性的不同而分词,在实践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二是如何看待语音差异。
理论上讲,语音不同,特别是声、韵、调的不同,一般都是不同的词。
但对基本词义相同,只是派生引申出现细微差异的词义,如果语音形式只出现声、韵、调、轻重音、轻音,或儿化音等某个要素的变异的话,是否也看作同形词?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可象上面,提出三个同样的疑问。
其核心问题仍是须基本词义相同,只是派生义相异。
略有变异的语音形式大都是用来区别、表征那些逐渐发生了变化的词义。
词义是第一位的东西,语音形式与语法形式、文字形式,都是第二位的东西。
不能因为语音稍有不同,就说它们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词?
在认定是多义词还是同形词中,根本还是要着眼于词义联系本身。
而决不能本末倒置,以起辅助作用的词的外部形式来取替词义这一根本标准的作用。
二、《现代汉语词典》同形词词目的调查
下面来具体剖析一下《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第2版)的同形词词目情况。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只讨论复音节的同形词词目。
词典共有复音节同形词1304个,合为639组。
下面依次显示同形词之间的语音关系、语法关系和词义关系的调查情况。
1,语音关系:
语音关系
同
轻声
轻重音
兼用
声调
声韵
总数
数量
220
154
194
44
14
17
639(组)
百分比
34%
24%
30%
7%
2%
3
100%
“同”是指一组同形词之间的语音完全一样。
“轻声”“轻重音”“声调”“声韵”分别指同形词之间语音差别的方面。
“兼类”是同形词之间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音差异。
下面每类各举一个例子:
“同”类。
“【抄袭】1把别人的作品或语句抄来当做自己的。
指不顾客观情况,沿用别人的经验方法等。
”“【抄袭】2(军队)绕道袭击敌人。
”对语音相同的同形词,《现代汉语词典》“凡例2a”中是这样规定的:
“形同音同,但在意义上需要分别处理的,也分立条目,在【】外右上方标注阿拉伯数字。
”
“轻声”类。
“【大人】dàrén敬辞,称长辈。
”“【大人】dà·ren成人。
旧时称地位高的官长。
”
“轻重音”类:
“【贷款】dài//kuǎn甲国借钱给乙国;银行、信用合作社等机构借钱给需要用钱的部门或个人。
一般规定利息,定期偿还。
”“【贷款】dàikuǎn甲国借钱给乙国;银行、信用合作社等机构借钱给需要用钱的部门或个人的款项。
”对轻重音的处理,《现汉》“凡例12”作了这样的解释:
“插入其它成分时,语音上有轻重变化的词语,标上调号和圆点,再加斜的双短横。
”用“轻重音”来区分同形词的,大多数是在名词与动词之间构成对立,在194例“轻重音”中有156例是在名词与动词之间出现,占到80%。
也有动词与动词之间的对立,如“【搭帮】dā//bāng(许多人)结伴。
”“【搭帮】dābāng托福;依靠;多亏”。
能方便插入其它成分的复合词最多见的就是动宾式的离合动词。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还没有用“轻重音”的差异来表现名词性同形词的。
“兼用”类。
“【丧气】sàng//qì因事情不顺利而情绪低落。
”“【丧气】sàng·qi(口)倒霉;不吉利。
”前者使用了轻重音,后者使用了轻声。
“声调”类。
“【出处】chūchǔ出仕和退隐。
”“【出处】chūchù(引文或典故的)来源。
”前者是上声,后者是去声。
“声韵”类。
声母或韵母不同,这是比较明显的语音差异。
如“【本色】běnsè本来面貌:
英雄本色。
”“【本色】běnshǎi物品原来的颜色(多指没有染过色的织物)。
”两个词的韵母和声调都有不同。
又如【作乐】zuòlè和【作乐】zuòyuè、【公差】gōngchā和【公差】gōngchāi,或是声母,或是韵母有别。
2,语法关系:
这里主要是指同形词之间词性的关系,调查结果如下表。
词性
名-动
名-名
动-动
其它
总数
数量
251
182
100
97
639(组)
百分比
39%
29%
17%
15%
100%
“名-动”类。
“【背书】背诵念过的书。
”“【背书】票据(多指支票)背面的签字或图章。
”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
“名-名”类。
“【本事】文学作品主根据的故事情节。
”“【本事】本领。
”
“动-动”类。
“【成家】(男子)结婚。
”“【成家】成为专家。
”
“其它”类的情况比较复杂,共有12种词性对应关系,每种多者20例,少者只有1、2例。
上述数据表明,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多,占到所有同形词的十分之四。
其中有一类现象很显眼,就是名词指事物,为“体”,动词指事物的功能,为“用”,可称之为“体用同称”词语。
《现代汉语词典》是将“体用同称”词语处理为不同的词目。
如:
“【赤膊】光着上身。
”“【赤膊】光着的上身。
”“【出品】制造出来产品。
”“【出品】生产出来的物品。
”全书“体用同称”词语共有110组,占“名-动”类的45.4%。
可见,对词性有差异的词义如何处理,也是直接影响到同形词设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3,词义关系。
语音形式和语法功能的区别,对词来说都是外部形式。
对外部形式的不同处理当然会影响到“词”的X围和词目的设立,但这却是较难统一的东西。
各家有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处理标准,都会给自身寻找到一个尽量合理的解释。
而对同形词之间词义关系的调查则是深入到了词的内部,它关系到同形词的基本性质和能否成立的基础。
尽管以往人们在处理具体同形词词时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在理论上对同形词的看法却是相当一致的,就是同形词必须是词义不同。
但下面的调查结果却使我们生出许多的疑虑。
词义关系
近引申
远引申
体用同称
异
总数
数量
100
166
115
258
639(组)
百分比
16%
26%
18%
40%
100%
“近引申”类。
近引申是指在两个词之间能明显看出词义引申演变的轨迹,如:
“【褒贬】评论好坏。
”“【褒贬】批评缺点;指责。
”这两个词的意义相当接近,二者都是把“褒”“贬”两个反义语素化合成词,表示对人的评议,只是前者提炼出的是中性词义,后者偏于“贬”义而已。
又如“【捕食】(动物)捕取食物。
”“【捕食】(动物)捉住别的动物并且把它吃掉。
”前者在两个词素中偏重于“捕”,后者则是“捕”和“食”两个并重,但这两个词义的密切联系是不言而喻的,把它们合并为一个词,列为义项的关系显然更恰当。
“远引申”类。
远引申是指在两个词之间能找出词义演变的轨迹,只是距离稍远,需作一定的分析才能弄清其中的关系。
如“【宾服】(书)服从。
”“【宾服】(方)佩服。
”又如“【吃水】(方)供食用的水。
”“【吃水】吸取水分。
”“【吃水】船身入水的深度。
”尽管它们的具体所指都有一定的距离,但词义联系却是内在而稳定的。
“体用同称”类。
体用同称尽管在语法功能上具有对立,但二者的词义联系是相当密切的。
如“【包饭】双方约定,一方按月付饭钱,另一方供给饭食。
”“【包饭】按月支付固定费用的饭食。
”意义联系如此密切的词语大可不必分立词目。
汉语词语的兼类相当普遍,将它们一一依词性而分词其结果是分不胜分。
英语词典都是标注词性的,但许多也是集中在一个词形之下。
如果要说因为词性不同而一定要分的话,那么现有多义词中也有不是相同词性的。
如“【劳动】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
专指体力劳动。
进行体力劳动。
”和是名词性,则是动词性。
词性的不同就分成不同的词目,这是一条不能自圆其说的规定。
“异”类。
“异”是指同形词之间的词义完全不同。
如“【盘缠】盘绕。
”“【盘缠】(口)路费。
”“【安心】存心;居心:
安心不善/安的什么心?
”“【安心】心情安定。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形异义词。
三、《现代汉语词典》同形词划分的特点
通过上面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的同形词设立具有这样的特点:
1,重视语音形式的差别。
几乎做到了两个词义之间只要有一点点语音差别的,都独立成词。
由于《现汉》在标音时是尽量根据实际口语来标音,因此凭借细微差异的“轻声”和“轻重音”分出的同形词所占比重相当高,达到392组,占所有同形词的54%。
对这部分只有细微语音差异的同形词进行词义关系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属于“近引申”的有76组,“远引申”的有100组,“体用同称”的有112组,“异”的有104组。
104组词义相差度大的“异”类在392组同形词中占27%,而另外73%的的则靠的是语音,这个数字突出显示语音差异在同形词分立中所占据的重要份量。
当然这也可以从词典的编排体例上解释,词典的基本排序方法是音序,语音不同的词目排在不同的地方,轻声的排在非轻声的后面。
由于前后列位不在一处,导致词目的分设,这种解释是比较自然的。
但从语音差异的揭示达到那么细微的程度,而且细微的语音差异所反映的大都是差异细微的词义,最后结果是将这些差异细微的词义分列独处,而不是同处一个词目的下面,这些都能显示词典的编纂者是将语音差异当作同形词分立的一个基本考虑点。
2,重视语法形式的差别。
《现代汉语词典》也是看重语法功能差异的,象名一动对应的同形词就有251组,占到39%。
语法功能相同的也不少,如“名一名”、“动一动”的就有282组,占到同形词总数的46%。
其中“近引申”的47组,“远引申”的81组,“异”的154组。
“异”类的154组在282组同形词中占到55%,这个数字比“异”类在所有同形词中所占比重为40%的数字要高,这说明《现代汉语词典》在处理词性相同的同形词时,对词义的区别程度要求较高。
其中尤其是看重“名一动”的对应,即“体用同称”类。
本来体用同称是汉语的一种典型现象,大量存在着。
还有许多在语言实际中也存在,但未在词目中分化出来的,如“建设”“学习”“端正”“清洁”,都同时拥有名词义与动词义,当然这牵涉到义项的概括、言语义与语言义等问题。
与语音差异相比,只是语法功能的分词标准执行起来难度更大,前后的出入很大。
这里有本身的问题,就是语法功能不同就分立成词,在理论上很难站得住,因为词义联系很密切的意义可以是语法功能的不同。
再就是语法属性不同就分立成词也没有因音序不同而分立的理由那样“客观”、“充足”。
在实践中执行这条标准也出现了许多疏漏,难以自圆其说。
如【劳动】一词有3个义项“人类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的活动。
专指体力劳动。
进行体力劳动”,其中的和就是体用同称,却又同列一个词内。
3,对词义的联系要求苛刻,重分不重合。
由于在语音和语法中强调了它们的差异性,因此必须会造成词义联系本来较为明显的也被分立出来成了另一个词。
根据上面的统计,真正属于基本词义不同的“异类”,只占到所有同形词的40%。
根据“同形词的本质区别应是基本义的不同”这点认识,如此看重语音形式与语法功能的差别,是不应该。
四、正确划分同形词与多义词对词汇理论与辞书编纂的影响
本文主X严格根据“基本义不同”这条标准来划分同形词,把同形词与多义词区别开来。
对有语音差异的多义词内部的义项,如果考虑到是为了纯粹的音序排列上的需要,不是不可以仍用现法,分列它处。
如果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词”的意义内部整体联系性,为了更好地把多义词与同形词区分开来,也可以处理为属于同形词的才分列,属于多义词内部的有语音差异的义项仍列于同一词目之下,只在义项下面标明所用语音。
词的语法功能的异同,则不应成为划分同形词的考虑因素。
尽管词性的差异与词义的差异往往是纠缠在一起,但由于二者并没有同步关系,特别是词义的引申变化并不局限在同类词性的X围,跨词性的引申大量、经常地出现。
这时要把语法属性来作为离析多义词,认定同形词的标准,肯定会捉襟见肘、进退为难。
根据“基本词义不同”的标准来认定同形词,对汉语词汇理论和词汇学习,对辞典的编纂,都有好处:
1,有助于保持多义词内部的整体性。
这是最重要的作用。
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是从理论上正确地划分“词”的X围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
这对汉语这样没有足够形态标志的语言是很有用的。
假如对意义标准尚不能做到一以贯之的话,那么词与词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复合词与复合词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将会更加模糊。
2,有助于人们在词汇学习与使用中,更好地理解义项之间的关系,了解义项的来龙去脉,及其与左邻右居的关系。
人们了解一个新词义,往往是把它与旧词义联系起来,探索新义的得义来由。
把有联系的多个义项放在多义词内作前后排列就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
在辞典中过细地切分义项,过多地分出同形词,使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独立的词义,于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好处。
3,精炼词目,控制数量。
同形词词目的划分,在实际语言使用中,人们并不在意这个义是属于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只是在前后联系、上下贯通时才会想到词与词的关系。
但在辞书编纂中却不同,如果是看作不同的词当然要分开排列。
由于过细地切分在理论上尚有许多站不稳的地方,在实践上也不会给人们带来认知和使用上的好处,只会增加同形词的数量,增加词目的数量。
这在不增加词义内容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增加了辞书词目的水分。
作者工作单位:
XX大学中文系教授
通讯地址:
XXXX大学XX12号301邮编:
361005
:
0(宅)、2181479(宅)
:
suxchjingxian.xmu.edu.